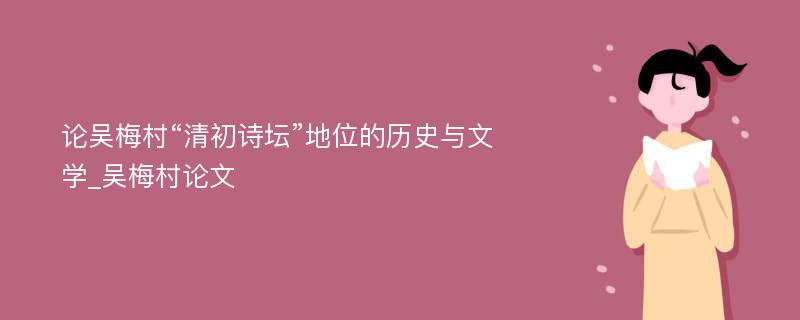
吴梅村登上“清初诗坛盟主”之席的历史与文学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清初论文,盟主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梅村作为明末清初之际的著名诗人,向为文学史家指称为“清初诗坛盟主”,然而,吴梅村之获得这一桂冠,是不是仅成立于泛而言之的“史评之词”层面上呢?本文考察研究了吴梅村在清初十年间的诗歌创作发展历程以及当时诗坛对其的认知,认为吴梅村之为“清初诗坛盟主”,除了他在清初十年间渐次推出的一系列诗篇佳作赢得盛誉以外,还在于他是前明遗老,受到遗民文化集团的拥戴,而当时遗民文化集团占据着文坛的主流地位。因而,吴梅村之为“诗坛盟主”,乃至成为当时文学社盟活动中的领袖人物,是明清之际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文化遗民反抗心态及梅村个人文学成就、社盟活动合力的产物,具有明清之际特定的时代特征。
一 时代背景与代际更替
原为明朝东北边疆地区的属臣建州卫,从努尔哈赤于1618年自称大金汗国(史称后金)起,先与明朝争战关外二十余年,到1644年乘机入关,定鼎北京,接着,迅速击溃李自成大顺、张献忠大西政权,摧灭弘光、隆武南明政权,短短几年功夫,竟用武力基本略定明朝天下。清廷兵下江南不久,即颁布剃发易服令,严令天下人民皆从清俗,清廷此举,遂使一姓家国的兴亡,朝代政权的更迭,增加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因素,激化了民族矛盾,顾炎武甚至于因而提出“率兽食人,是为亡天下”的呼吁,以区别一般意义上的王朝易代。清廷下剃发易服令后,使许多在清兵初下时未作顽强抵抗的地区,重新燃起了猛烈的武装抗清起义之火,这是汉族人民汉族士大夫为捍卫民族文化而奋起的抗争。清廷依恃它的由中枢政权统一调动指挥的强大武力,迅速扑灭了这些只凭一腔保卫民族文化义愤而蜂起的,但缺乏统一政权组织孤立地各自为战如昆山、嘉定、松江、江阴等地的局部起义,逐次平息反抗,平定局势。清廷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虽然占有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凭借这个武力优势,在其逐渐扩大的征服区域内,建立了有效的统治秩序,但是,人心的归附和认同,则尚需时日。在清初的一二十年里,存在着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庞大、坚持反抗心理和不合作态度最久的遗民群体,这个遗民群体占据着文化精神上的优势。这期间,遗民文学是文坛的主流,故国之思、黍离之悲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主旋律。自然,此际的诗坛盟主必出自遗民诗人。明亡清兴,时代剧变,文坛上也必然要出现人事的变迁、代际的更替,于是,吴梅村的崛起便应运而生。
梅村在甲申乙酉之前,虽于士林之中已有声名,但只是因为他少年高捷科第,位居太史、南雍少司成清贵之列,又兼为复社中坚,负清流之望,而于诗文之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梅村那时诗作虽然已有警拔之篇,但毕竟数量不多,才情尚未舒展,此其一;当时文苑负有盛名者如钱谦益,以诗坛老将,正雄踞盟主之位,海内景仰,如陈子龙,以颖异之才,为诗界健锐,别树一帜;牧斋力诋王、李七子,主张兼学三唐,不废宋、元,欲开一代宗风;卧子则继绍前后七子,极力鼓吹文学尚古、复古;牧斋立派虞山、卧子率众云间,两家旗帜鲜明,旗鼓相当,声势正盛;梅村年齿既晚,学诗亦迟,尚无力量与他们争胜抗衡,占主盟之坛一席地,此其二。及至乙酉南都覆亡,神州陆沉,世道沧桑,诗风诗道势将有所新变,梅村正逢其时,他亲身遭遇国变,目睹鼎革易代,感慨兴亡沧桑,情凝于中,发而为诗,创作出一系列杰出篇章,传播天下,为识者所叹赏推重。是时,诗坛旧宿,亦凋零铩羽,钱牧斋佥名降表,声望遂为之光焰黯淡,陈卧子慷慨殉国,英才惜乎于夭折中年,一时诗人之林,势将拥出新的诗坛盟主,梅村身为前朝遗老,复社名流,鼎革以来,不断推出诸多佳作新制,折服当世,士望于归,声名遂日益隆盛。到他于顺治十年为清廷万般逼迫,不得已而应征北上悲怆就道之际,梅村已俨然“为海内贤大夫领袖”(注: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执诗坛之牛耳了。当然,梅村之所以能成为诗坛盟主,海内贤大夫领袖,除了他的文学成就以外,他当时的遗民身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正是这一点,清廷一定要逼他出山,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更觉羞惭愧疚,以致陷于终身悔恨的痛苦境地。梅村后来曾悲叹“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注: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虽然是悲哀吴季子的不幸,亦是借此一吐自己的胸中块垒,他说陈圆圆“当时只受声名累”,“此时只有泪沾衣”(注:吴伟业《圆圆曲》。),哪里想到就在他结撰《圆圆曲》两年之后,这些话竟成了他自己命运的预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注:赵翼《瓯北诗话》。),清初十年时世的陵谷变迁,诗坛领袖人物也完成了代际更替,吴梅村渐以其丰赡的创作,宏富的才力,悲怀故国的深情,遂崛起而领一时之天下风骚。
二 创作成就赢得诗坛推重
吴梅村诗歌在艺术上最具特色与魅力的是叙咏明清之际史事的七言歌行体长诗,而使他在诗坛上崭露头角,最早受到当时诗坛名流激赏的是《洛阳行》。是诗写万历爱子福王朱常洵一生荣败始末。此诗在艺术上有独到之特色,叙议咏叹,穿插倒叙,波澜迭翻,景色烘托,营造气氛,转韵自然,一唱三叹,摇曳生姿,辞藻华丽,大量用典而精切得当。《洛阳行》作于甲申之变之前,但此诗于梅村诗歌创作发展道路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在内容上,为梅村用七言歌行体叙咏明清之际史事之诗所谓“诗史”的首篇,在艺术上,是所谓“梅村体”之滥觞。
本诗用典极多,如“茂陵西筑望思台”,“昭丘烟草自苍茫”,以茂陵、昭丘指代神宗。茂陵,汉武帝陵,昭丘,昭陵,唐太宗陵。又如:“青雀投怀玉鱼别”,“渭水东流别任城”,“廷论由来责佞夫”,“国恩自是优如意”,“总为先朝怜白象”,以青雀、任城、佞夫、如意、白象等指代福王。青雀,唐太宗之子魏王李泰小字青雀;任城,魏武帝之子曹彰封任城王;佞夫,周灵王之子王子佞夫;如意,汉高祖之子赵王刘如意;白象,南朝齐长沙王萧晃小字白象。以上历史上诸王均死于非命,皆切福王结局。又如“江夏漫裁修柏赋,东阿徒咏豆萁篇”,“帝子魂归南浦云,玉妃泪洒东平树”。南朝齐高帝子江夏王萧锋在藩封常忽忽不乐,因著《修柏赋》;魏东阿王曹植因遭文帝屡屡迫害,作《煮豆燃豆萁》诗;南浦云,唐高祖子李元婴封滕王,王勃《滕王阁序》诗:“画栋朝飞南浦云”;东平树,汉宣帝子东平思王刘宇死于封国,其墓上松柏皆朝向京城。用诸多典故写福王的悲剧,大都切其身份和遭遇。而“神皇倚瑟楚歌时,百子池边袅柳丝,早见鸿飞四海翼,可怜花开万年枝。”四句,则用汉高祖、戚夫人、汉惠帝、如意、商山四皓故事,来喻神宗、郑贵妃、光宗、福王、争国本的神宗诸臣,将一场极其复杂的宫廷争端,用一个典故四行文采斐然的诗句轻轻概括无余,真是绝大才力。至于“西京铜狄泣王孙,白头宫监锄荆棘”,用铜人泣泪,铜驼荆棘之典言福王国破身亡,则都是熟典了。驾驭典故,流畅自如,才气横溢,使人如入山阴道上,所以后人有谓梅村诗为“才人之诗”(注:乔亿《剑溪说诗》。)。
《洛阳行》以悲凉笔调写明末清初史事,为乙酉之后的名篇《永和宫词》、《琵琶行》、《萧史青门曲》、《勾章井》、《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圆圆曲》、《楚两生行》、《雁门太守行》和《松山哀》等七言歌行以诗写史的先声,而《洛阳行》所表现出的诗艺功力和艺术特色,也标志着梅村此类长歌已有元、白“长庆体”的风韵,初步形成了“梅村体”的艺术风格。在《洛阳行》问世不久之后,梅村与陈子龙相会于南京,子龙当面吟诵了《洛阳行》后,大加赞赏(注:事见《梅村诗话》。)。陈子龙天才横逸,文名卓著,心气极高,尤其在品骘诗文方面,从不肯假以人情而轻加推奖。他们的朋友宋征璧曾记其性情云:“大樽严于论诗,凡献诗者踵相接,大樽意态傲岸,若不足一顾者”(注:宋徵璧《抱真堂诗话》。)。所以梅村之《洛阳行》获得卧子的高度称赏,其诗之擅美一时应当之无愧。《洛阳行》还为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李雯所大大激赏,他有诗《寄赠吴骏公太史假满还朝》赞叹道:“况君风雅更清发,赋诗足以凝皇情,高节微吟神骨惊,此曲乃是《洛阳行》。会稽李官三叹息,嵩高明月延松声。一空海内文章伯,衙官七子何唐突。樊侯补衮穆清风,不与诸生同翰墨。”李雯亦是云间诗派中杰出人物,与陈子龙齐名,时称“陈、李”。梅村之诗得到陈子龙、李雯等诗界名流们的称赏誉扬,其诗名遂为腾扬。
乙酉之后,梅村痛切故国沦亡,难抑易世之悲,在其遗民生涯的八年中,又创作《永和宫词》、《琵琶行》、《萧门青史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圆圆曲》、《勾章井》等一系列以诗写史、哀痛明亡易代的七言歌行名篇。《永和宫词》作于顺治二年,写思宗田贵妃事。田贵妃美艳明慧,颇得思宗宠爱,诗起首便道:“扬州明月杜陵花,夹道香尘迎丽华。旧宅江都飞燕井,新侯关内武安家”。大有《长恨歌》之风情。而“宫草明年战血腥,当时莫向西陵哭。穷泉相见痛仓黄,还向官家问永王。幸免玉环遭丧乱,不须铜雀怨兴亡”;“麦饭冬青问茂陵,斜阳蔓草埋残垅”,“莫奏霓裳天宝曲,景阳宫井落秋槐”;比之《长恨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更为悲怆痛切。《琵琶行》作于顺治三年,写思宗宫中乐人白生善弹琵琶,明亡后流落江南,梅村听其奏乐,又闻在座的前明中常侍姚某诉说先朝宫中旧事,因生故国悲慨而作此篇。诗中亦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用相当篇幅叙咏白生身世,描绘了白生奏乐的情景,然而所发感慨之悲哀却远远过于白居易《琵琶行》,白氏《琵琶行》只是感伤自己仕途失意如年长色衰的琵琶商妇,而梅村《琵琶行》悲痛的是故国沦亡,南冠对泣:“换羽移宫总断肠,江村花落听霓裳。龟年哽咽歌长恨,力士凄凉说上皇。前辈风流最堪羡,明时迁客犹嗟怨。即今相对苦南冠,升平乐事难重见。……独有风尘潦倒人,偶逢丝竹便沾巾。江湖满地南乡子,铁笛哀歌何处寻?”此际梅村亡国遗臣的沉痛悲哀,远非白居易政治失意、蹉跎年华的感伤可比。然而,白、吴二人的同名之作,在艺术上实可相对比美,在诗的结构上,吴诗有意仿照白诗,而诗中着力描绘音乐的场面和渲染音乐的效果,白吴二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永和宫词》和《琵琶行》两诗,清代诗论家的评语都很高。清初魏宪谓《永和宫词》曰:“从繁华说到寂寞,是一部诗史”(注:魏宪《诗持三集》评语。),而袁枚则盛赞其为“神品”,又评道:“新声古调,寓事含情,具子安之高韵”(注:袁枚《吴梅村诗》录本评语。)。袁枚又评论《琵琶行》说“序既哽咽,诗复哀怨,以配江州,当无娣姒之恨。江州《琵琶》止叙一身流落之感耳,不如作此关系语,中有全用江州排场之处”(注:袁枚《吴梅村诗》录本评语。)。《萧史青门曲》作于乙酉之后顺治七年以前,写明思宗之妹宁德公主的身世,以公主在明朝时的尊贵荣华与国亡后的贫困落魄作强烈对照。诗先写昔日宁德公主出嫁时豪奢的皇家排场:“先是朝廷启未央,天人宁德降刘郎。道路争传长公主,夫婿豪华势莫当。百两车来填紫陌,千金榼送出雕房。红窗小院调鹦鹉,翠馆繁筝叫凤凰。”再以“扶携夫妇出兵间,改朔移朝至今活。粉碓脂田县吏收,妆楼舞阁豪家夺。曾见天街羡璧人,今朝破帽迎风雪。卖珠易米返柴门,贵主凄凉向谁说。”的穷困凄凉作强烈反衬,以公主命运的霄壤变化,寄托了梅村的易代沧桑之感。至于作于顺治八年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圆圆曲》,前者写弘光灭亡痛史,后者以春秋笔法刺叛将吴三桂,二诗一出,天下播扬,脍炙人口,梅村的诗名更为崇隆。《圆圆曲》中警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其诛心切骨之论,大为刺痛吴三桂。据况周颐《陈圆圆事略》记载,有谓:“当日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赂求毁板,梅村不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二吴的这一番公论,有几点可说,其一可见梅村当时的骨气铮铮,其二可见《圆圆曲》的流播之广,其三可见《圆圆曲》的诗史实录性质,其四可见《圆圆曲》的讽谴力度之重。梅村于乙酉之后写就的这几篇叙咏明清之际史事的七言歌行,在当时就天下传诵,一时赞誉之词鹊起,梅村诗名清声大振。《琵琶行》问世后不久,陈维崧在代他父亲陈贞慧致梅村的信中说:“明公人伦渊岱,风雅鼓吹,当今之王茂宏、谢东山也。仆……独以未见明公为恨。芳华终缅,裁明月以叙心;元辉自遐,伫白云而抽志,中怀蕴结,如何如何。唯是讽咏歌词,不去口实。昔年白下,《洛阳》叹羡于舒章;今适吴阊,《琵琶》服膺于圣野,又何异拍洪崖之肩,把浮丘之袖,符其霞举乎!”(注:陈维崧《湖海楼全集·与吴骏公书·代家大人》。)。维崧信中将梅村比为东晋之国家干城王导、谢安,比拟虽不伦,然已可见其对梅村的推崇备至,并特为提起《洛阳行》与《琵琶行》已被当世名家所叹服。舒章,李雯字;圣野,叶襄字;二人皆为当世文坛名流。洪崖、浮丘,均为传说中仙人名号。晋郭璞《游仙诗》:“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维崧是说梅村诗已臻神仙之化境。另一位遗民诗人姜垓则称颂梅村道:“大雅沦亡斯可悯,骅骝雕丧气俱尽,国朝翰林无此流,天下知有吴宫尹。……当时流涕谢圣明,即信白首甘丘壑。向来衷曲人不知,长歌短咏微有托,延秋门上啼乌鸦,江南红豆逢落花。朔漠来归汉公主,中貂长泣胡琵琶。此曲作时有鬼神,一读再读心咨嗟。……今人论人俱可怜,谁能将诗作史传。君不见太仓济南亦草草,百年以来胜者少。”(注:姜垓《流览堂残稿卷三·放歌行赠吴宫尹》。)姜垓诗中“延秋门上啼乌鸦”、“江南红豆逢落花”、“朔漠来归汉公主”、“中貂长泣胡琵琶”四句,则是指梅村的《洛阳行》、《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琵琶行》四篇长歌。延秋门是唐都长安城门名,杜甫《哀王孙》诗有句云:“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梅村《洛阳行》中有“遭乱城头乌夜啼”句,盖取杜工部“哀王孙”之意。《永和宫词》首句即云“扬州明月杜陵花”,田贵妃是扬州人,红豆、落花,其有相思、美人弃世之意。“朔漠来归汉公主”,即借指宁德公主在北都覆亡后流落民间事。至于“中貂长泣胡琵琶”一句则显然指《琵琶行》。姜垓称颂梅村的诗歌可作史传,将梅村的诗人地位推崇到百年诗坛少见其匹敌的崇高境地。太仓、济南即指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李攀龙,他们曾在晚明诗坛主盟三十余年,使天下诗风靡然从之,然而,姜垓尚称其“亦草草”,认为梅村诗歌的成就已经超过了凤洲和沧溟。姜垓这一见解,与李雯略同,前面引李雯诗有句云“一空海内文章伯,衙官七子何唐突”,皆认为梅村诗艺成就已超越七子。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但在那时,王、李七子的流风余韵尚在,名气仍然很大,李雯、姜垓将梅村凌驾于王、李之上,显然是极高的赞美之词。
梅村此际的七言长歌佳制累累,俱极精妙,如为友人姜埰、姜垓兄弟作于顺治四年的《东莱行》:“左氏勋名照汗青,过江忠孝数中丞。孺卿也向龙沙死,柴市何人哭子卿”;“回首风尘涕泪流,故乡萧瑟海天秋。田横岛在鱼龙冷。栾大城荒草木愁”;“鲁连蹈海非求名,鸱夷一舸宁逃生?丈夫沦落有时命,岂复悠悠行路心”。诗中纪念为国捐躯的友人宋玫、左懋第,抒发坚持遗民之节的心曲,悲凉慷慨,如变徵之音,直可断朱弦、裂锦帛、遏行云。又如作于顺治六年的《鸳湖曲》,写复社旧人吴昌时,此诗别是一番风情:“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旖旎多姿,无限柔媚。“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坯土亦难留”。乐极生悲,泰极否来。梅村在其七言长歌中常借转韵,翻出波澜,《圆圆曲》、《萧门青史曲》和这首《鸳湖曲》都是善翻波澜者。“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梅村的感慨,不仅在于悲慨吴昌时的遭遇,其实也深奇时世身世的感叹,这是他身逢易世后心中甘苦之言。《鸳湖曲》的艺术风格显然与《东莱行》别是一体,《鸳湖曲》以艳景绮情入手,写出伤世哀旨,实以起首之乐景,反衬主旨之哀情,是深得风雅三昧的。梅村此际的七言歌行,又擅作诸多不同风格,驾重若轻,如哀民生疾苦,刺清廷苛政的《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三首,向被论者目为可追肩媲美于元、白、张、王的新乐府。梅村此际诗作取得可观成就的当然不仅是七言长歌,他的拟乐府诗《行路难》一十八首,气格警挺,寄托遥深,论者方之鲍照;其他如七律、七绝、五古、五律等等,佳作甚多,不及—一枚举,在艺术上都有足可称道之处。其诗依咏叹之不同,能为多种风格,或悲凉慷慨,或哀婉凄楚,或清幽淡雅,或旖旎妩媚,然而大多辞采华瞻,格律精严,善于用典,形成梅村诗才气逼人功力深厚的特色。梅村此际已以其丰赡的文学成就卓然特立于当世,为当时文坛诸子所尊崇推重。顺治六年,云间遗民诗人彭宾曾有诗寄赠,诗中有句曰:“和璧蛇珠世希有,一逢周客皆难售,黄钟大吕出明堂,当时作者尽奔走。披谒龙门客不空,骚坛艺苑称宗工”(注:彭宾《偶存草·寄赠吴骏公宫尹》。)。盛赞梅村诗艺之高华卓绝,如和氏璧、如隋侯珠、如黄钟大吕、已折服同辈诸子,且为天下作者所景仰,奉为骚坛艺苑的大师宗匠。彭宾已视梅村为诗坛领袖。
三 虎丘大会登上文人社集盟主之席
吴梅村在天下士子集会之时,被共同推戴为盟主宗师,是顺治十年吴中慎交、同声两社在苏州召集的虎丘大会。这次大会是入清以来第一次文人大型社集活动,也是崇祯二年张溥在苏州尹山举行复社建立大会以来最后一次文人大型社集活动。
乙酉南都崩溃,复社已是散局,入清之初,清廷尚未有暇过问文人社集事,南方一班文人又纷纷建社集会,渐渐又形成声势,自然也有不少分歧与意气相争,当时名声最大是吴中的两个文社,慎交社与同声社。经包括吴梅村在内的文坛宿旧的和合,两社联合于顺治十年上巳之日,在苏州虎丘召集大会,弥合两社分歧。这次大会声势很盛,东南各郡到会的士人几近千人之多,这是继崇祯五年,张溥在虎丘召开复社大会以来,东南士人最盛大的一次社集,两会的时间已隔二十一年。据太仓十子之一王抃自编《王巢松年谱》记载:“(顺治十年)是年上巳,郡中两社俱大会于虎丘,……两社俱推戴梅村夫子。”是会,慎交、同声两社共同推戴吴梅村为盟主,调和双方冲突,合成十郡大社,大有重开当年复社之盛的声势。梅村以前朝清流大臣、复社元老、诗坛领袖,新一代士人共奉的宗师长者的身份出席这次社集,受到大会的尊礼,一时极为风光,但他抚今追昔,感慨亦足良深。他有《癸巳春日禊饮社集虎丘即事》四首记此集会抒其感慨云:“杨柳丝丝逼禁烟,笔床书卷五湖船。青溪胜集仍遗老,白帢高谈尽少年。笋屐莺花看士女,羽觞冠盖会神仙。茂先往事风流在,重过兰亭意惘然”;“兰台家世本贻谋,高会南皮话昔游。执友沦亡惊岁月,诸郎才调擅风流。一年故国伤青史,四海新知笑白头。修禊只今添俯仰,北风杯洒酹营丘”;“访友扁舟挂席轻,梨花吹雨五茸城。文章兴废关时代,兄弟飘零为甲兵。茂苑听莺春社饮,华亭闻鹤故园情。众中谁识陈惊座,顾陆相看是老成”;“绛帷当日重长杨,都讲还开旧草堂。少弟诗篇标赤帜,故人才笔继青箱。抽毫共集梁园制,布席争飞曲水觞。近得庐陵书信否?寄怀子美在沧浪”。梅村在诗中感慨故国的沦亡,旧友的凋零,张溥早死,陈子龙、杨廷枢、夏允彝等殉国,当年复社大会时的主将只剩他一个人了,虽然今日两社推戴,荣为盟主宗师,但追忆旧事,思及易代,不禁怅惘感伤。从诗意来看,他显然并未着意于个人的声望,然而,他却确实赢得了极为崇隆的声望,并在这次两社虎丘大会上达到了顶点。太仓十子之一王撰与会,自记盛况云:“十年上巳,吴中两社并兴,大会于虎丘,奉梅村先生为宗主。梅翁赋《禊饮社集》四首,同人传诵。次日,复有两社合盟之举,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注:顾师轼《吴梅村先生年谱》卷四中引王撰自编《王随庵自订年谱》。)我们可以想见梅村当时声望之崇、地位之尊的旖旎风光。
我们探讨了梅村在八年遗民生活中的创作发展历程,可以这样认为,梅村赢得诗坛盟主地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明亡之初,他显然还没有这样的影响力,只是在他乙酉之后的八年创作实践中,以其渐次问世的众多佳作宏制在文学同道们的不断誉扬之下,在遗民故国黍离之悲的文化氛围里,梅村才逐渐诗名腾起,到顺治十年,以这次虎丘社集为标志,他的文坛领袖地位终于为天下所共认。然而不久清廷即下禁止社集的严令,顺治十年上巳的虎丘大会成为文人大型社集活动的绝响,梅村也在其声望达到巅峰的同时,开始跌落,当年秋天他被清廷严诏逼迫心怀悲怨而就道北上,失去了保持八年的遗民气节和身份,遗民集团在文坛已不复存在领袖人物。十二年后,康熙四年,王士祯、陈维崧等人在如皋冒辟水绘园雅集,王士祯的崛起,标志着新的一代,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清代诗坛盟主登上历史舞台。
本文论述了吴梅村自甲申明亡至清顺治十年间以其文学创作成就赢得当时文坛的推重,成为公认的“诗坛盟主”之发展历程。需要指出的是,梅村作为诗坛盟主,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仅为文学史叙述中的品评杰出诗人之赞词,而是在他在世期间就被当世同道所共同推尊、认可的诗界领袖,文人社盟的盟主宗师,这乃是明代前后七子以来形成的文坛风气之余绪。前后七子的空同、大复、沧溟、凤洲之主盟诗坛,左右时代诗歌风尚,其历史意义更大程度上在于提出了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倡导了一种文学流派,诗学地位大于创作成就;而梅村则以他丰瞻宏丽的诗歌作品,从一个视角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风貌,反映了一个特定文化集团的时代心态,而这正是吴梅村及其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所在。
标签:吴梅村论文; 琵琶行论文; 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圆圆曲论文; 顺治帝论文; 鸳湖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剃发易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