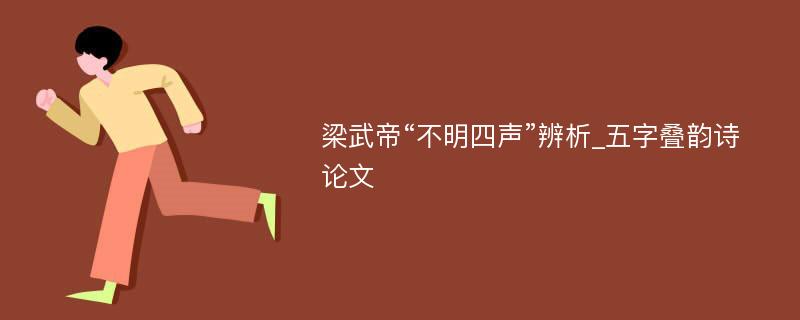
梁武帝“不知四声”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梁武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8)02-0065-05
治永明文学的学者,皆认为梁武帝“不知四声”。但是当我们来考查梁武帝关于四声的言论时,却发现梁武帝对于四声并非不懂,而是出于种种原因主观上加以排斥。
关于武帝与四声关系的文献材料主要有四则:
重公尝谒高祖,问曰:“弟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阳松玠《谈薮》)[1]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梁书·沈约传》)[2]
约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约也。(《南史.沈约传》)[3]
梁王萧衍不知四声,尝从容谓中领军朱异曰:“何者名为四声?”异答云:“天子万福,即是四声。”衍谓异:“天子寿考岂不是四声也?”(《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4]
这四段文字常常为研究四声者所引用,然梁武帝真不知四声吗?若真不知四声,何以前后会有“三问”?①
在上举四处文献中,《谈薮》所载最前②。梁武帝以“闻在外有四声”而问沙门重公,语甚好奇,莫辨是非,若说此时萧衍对四声不甚明了,尚可以理解。又据重公“以为能”的得意神态,可推知辨四声于当时并非易事,非人人之所能专。
《梁书》所载,则是武帝与周捨的对话。周捨在梁开国后,一度掌机密二十几年。《梁书·周捨传》载:“迁尚书吏部郎,太子右卫率,右卫将军,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捨素辩给,与人泛论谈谑,终日不绝口,而竟无一言漏泄机事,众尤叹服之。”周捨为《四声切韵》作者周颙之子,其“背文讽说,音韵清辩”,当亦是承其父能。周捨卒于普通四年,则武帝问周捨四声之事当在普通四年之前。《梁书》云武帝“雅不好焉”,只有知道四声为何物,才可以言“好”与“不好”。
《南史·沈约传》与《梁书·沈约传》大致相同。所可注意者乃在最后一句。《梁书》只云“竟不遵用”,《南史》却云“竟不遵用约也”。是不遵用沈约《四声谱》所定四声规律,还是不遵用“沈约”?学界一般认为是不遵用四声之意。不过,理解为不遵用沈约之意亦未尝不可。因为二者可以互为因果,并存无碍。若“不遵用沈约”解可通,则武帝与周捨所谈四声当别有起因。前引《梁书·周捨传》云周捨口实严密,则起因一事详略难得为外人所知。愚意以为沈约欲为台司,而周捨为之试探口风,却因四声之故而为武帝所抑。
《文镜秘府论》所载武帝与朱异的对话,最为晚出。朱异乃是在周捨卒后执掌机密的人,其职事相当于周捨。《梁书·朱异传》:“中大通元年,迁散骑常侍。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周捨卒于普通四年,则武帝与朱异的对话当在是年之后。此条所记与前三条相比,尤为详细。明言“萧衍不知四声”,并且记有萧衍“天子寿考岂不是四声也”的问话。此条所载盖有实有虚。所谓实者,萧衍问四声之目的神态,乃是“从容”,可见已不同于早年“何者为是”的好奇与无识,竟求教于沙门。所谓虚者,萧衍非不知四声,若于第一条云不知四声尚可,于此却万万不可能。平生三问,至此若还云不知,非愚即痴矣。或问,然于萧衍“天子寿考”之问如何解释?从第一条可见,臣子之所以云“天子万福”、“天子圣哲”一类语,乃是为博得武帝的喜悦。正如在《五字叠韵诗》联句中刘孝绰赋“梁王长康强”句一样,其用意奉承十分明显。然武帝对此却是全然不睬,所云“天子寿考”乃是以此为哂也,非从音声角度而发。陈寅恪云入声汉人本易分别,而口操吴音的萧衍当更易分别,今吴人精通文墨者稍加点拨即知入声为何物,何萧衍竟至再三而不能分辨耶?
梁武帝萧衍不知四声是假,有意排抑四声是真③。梁武帝何以要排抑四声?这当与梁武帝在政治、音乐、文学等方面的立场有关联。
武帝即位之后即着手进行正乐的工作。《隋书·音乐志》载天监元年武帝下诏正乐的事,时沈约等人应诏上书,但是并未令武帝满意:
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通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又制为十二笛,用笛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周代古钟,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5]。
武帝“正乐”的工作,体现出了刚断自专的一面④。名为“正乐”,实际情况是新制据多。或据旧乐,或据新声。如《乐府诗集》卷五十引《古今乐录》云:“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笛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又沈约作四曲,亦谓之《江南弄》云。”[6]《隋志》还载有武帝改制《襄阳踏铜蹄》的情形:“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弦管。”《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晋白纻舞歌诗》前引《唐书·乐志》云:“梁武帝令沈约改其辞为《四时白纻歌》。”卷五十六《四时白纻歌》下引《古今乐录》说:“沈约云:‘《白纻》五章,敕臣约造。武帝造后两句。’”此外,被诏而作的还有《梁雅乐歌》6首、《梁三朝雅乐歌》6首、《五音曲》5首、《梁鼓吹曲》12首、《梁大壮大观舞歌》2首、《梁鞞舞歌》6首,等等。
无论是改制旧乐,还是摹写新声,沈约一直参与其中。由于武帝对音乐文学持雅正的态度,只注重诗歌的自然音韵,而无意于人工声律⑤。沈约虽然早在永明年间倡四声,但在天监年间的创作却是不敢声张,对武帝的文学趣味只能采取依违的态度,应诏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今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两书统计,沈约所作乐府诗达87首之多,占其现存诗歌总量的41%。其中,乐府诗除上举《江南弄》、《襄阳踏铜蹄》、《四时白纻歌》数首外,还有《芳树》、《临高台》、《有所思》《长安有斜行》、《拟青青河畔草》、《团扇歌》等数首同题共作的作品。而在非乐府诗方面,萧、沈二人的同题作品则较为少见,仅《古意诗》1首,及《五字叠韵诗》联句1篇。
非但如此,沈约在齐梁之际的文坛地位也直接召来了萧衍的忌意。文学上,武帝即位后,俨然以文坛宗主自期、自许。而沈约获名于前代⑥,其声势达于新朝,故武帝以帝王之尊欲加超压,观其宴饮之时赐诗、令群臣赋诗赋文及与沈约赛栗事一事可知大略。
关于赐诗、赋诗赋文,史籍所载甚多,今仅据《梁书》略引数条天监年间事如下:
朏固陈本志,不许;因请自还东迎母,乃许之。临发,舆驾复临幸,赋诗饯别。(《谢朏传》。按:史载于天监二年。)
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丘迟传》。按:史载于天监三年之前。)
高祖因宴为诗贻惔曰:“尔是冠群后,惟余实念功。”(《柳惔传》。按:史载于天监四年以前。)
时高祖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为二百字,三刻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到沆传》。按:到沆天监五年卒,则知此事不当早于是年;又据《到洽传》,同时赋诗者还有到洽、萧琛、任昉等人。)
(谢览)尝侍坐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乃赐诗云:“双文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国华。”(《谢朏传附弟子览传》。按:此事史载于天监九年以前。)
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柳恽传》。按:柳恽卒于天监十六年,则此事当不早于是年。)
琛亦奉承陈昔恩,以“早簉中阳,夙忝同闬,虽迷兴运,犹荷洪慈”。上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勿谈兴运初,且道狂奴异。”(《萧琛传》。按:此事当发生于天监年间。)
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刘孝绰传》)
是时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之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王僧孺传》)
非但令群臣赋诗赋文,而且还以赏评者的身份对之加以品评。其例如下:
是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高祖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又诏为《石阙铭记》,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石阙铭》,辞义典雅,足为佳作。……”(《陆倕传》。按:史载于天监初年。)
(天监初)率又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其年,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舞马,诏率赋之。……时与到洽、周兴嗣同奉诏为赋,高祖以率及兴嗣为工。(《张率传》。按:赋舞马事又见于《周兴嗣传》,文字略有不同。)
御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匹。高祖谓昉曰:“诸到可谓才子。”(《到洽传》。按:到沆天监五年卒,则华光殿赋诗当不早于此年。)
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周兴嗣传》。按:史载于天监九年以前。)
初,高祖招延后进二十余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高祖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萧介传》)
天监十六年,始预九日朝宴,稠人广坐,独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诗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谓才子。”(《萧子恪传附弟子显传》引萧子显《自序》文)
如果文士的创作受到武帝的赏识,不但会受到金帛赏赐,而且还会得以升擢,如《袁峻传》载:“高祖雅好辞赋,时献文于南阙者相望焉,其藻丽可观,或见赏擢。(天监)六年,峻乃拟扬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赐束帛。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二十卷。又奉敕与陆倕各制《新阙铭》,辞多不载。”《梁书》还载有刘孝绰、王规、褚翔等人因文学创作而得以超拔的事例,虽然这些事发生在天监以后,却可以推知天监年间的状况。
武帝现存诗中与群臣相和未著于史籍的还有《清暑殿效柏梁体》、《五字叠韵诗》2首。柏梁体诗参与者有任昉、徐勉、刘汎、柳憕、谢览、张卷、王峻、陆杲、陆倕、刘洽、江葺11人,叠韵诗参与者有刘孝绰、沈约、庾肩吾、徐摛、何逊5人。
由上举诸例可知,参与其赋诗文者既有前朝老臣,又有新进少年。如谢胐、沈约、任昉、萧琛、柳惔、柳恽、谢览、王僧孺、到沆、到洽、周兴嗣、丘迟、王暕、陆倕、张率、萧子显、袁峻、刘孝绰等等。武帝对他们多所褒奖,品评诠衡,时以“才子”相许,俨然一代文宗。其中,谢朏、萧琛、王僧孺、张率等人皆得名于永明,与沈约虽有年辈之别(与萧衍却是大体属于同代),在文学创作上却属永明时代的人物。萧衍即位之后,对他们的创作品其优劣,正是借助于皇权的力量而进行文学的干预。
所以《梁书·文学传序》说:“(梁武帝)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同书《刘苞传》:“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宴坐,虽仕进有前后,其赏赐不殊。”《南史·文学传》也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临幸,辄令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
关于栗事,《梁书·沈约传》云:“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则知沈约在武帝面前迫于权事,不得不作出退让,然而又于心有所不甘。故使二人关系僵持不下。
武帝文坛宗主地位的自我体认,使得他的文学观念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坛。萧统编《文选》,其观念便是受到了萧衍的影响,这一方面已经为当今学界所熟知。一直到中大通三年,萧统去世之后,萧纲才在《与湘东王书》中如此评价当时的文风:“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事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梁书·庾肩吾传》引,《南史·庾肩吾传》同载)萧纲所批评的京师文体正是以萧衍为蒿的雅正文学观念。当萧纲入主东宫以后,以其为代表的宫体诗开始流行时,武帝也对此表示了不满。武帝的不满除了宫体诗诗体卑下外,当还有宫体诗“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同前)的原因。当然,此时的梁武帝因纠缠于皇位继承一事,并日渐倾心于佛教,于宫体诗的文学风尚已再无心深究,故将徐摛召去准备责让之时,却因徐摛“应对明敏,辞义可观”(《梁书·徐摛传》)而暂且不论了。
萧衍文坛宗主的自觉意识,与沈约在齐梁之际的文学地位直接构成了矛盾冲突。这大概是萧衍在梁初的一段时期内排抑沈约、排抑四声的一个文学因素吧。所以,在天监至中大通时期的梁代文坛,沈约四声理论并没有大行其道,反而面临来自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特别是当这一挑战来自皇权力量时,其后果自然可知。观萧统《文选》选诗、钟嵘《诗品》评诗即可知其声律论在梁初的艰难境遇。⑦其时,与沈约四声论同声相应的人物,除了天监前后的刘勰和中大同时期的刘绦外,自天监至中大通三年近30年的时间内几无任何人再加以深入探讨⑧。《梁书·王筠传》载王筠善于声韵,沈约将其《效居赋》草稿向他展示时,王筠的善识声韵使得沈约感叹道:“知音者希,真赏殆绝。”当王筠将诗作呈于沈约时,沈约再次感喟:“览所示诗,实为丽则,声和被纸,光影盈字。夔、牙接响,顾有余惭;孔翠群翔,岂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伫新奇,烂然总至,权舆已尽。会昌昭发,兰挥玉振,克谐之义,宁比笙簧。思力所该,一至乎此,叹服吟研,周流忘念。”沈约遇到王筠这样善识声韵的后进诗人,十分感慨。他曾对王筠说:“自谢脁跳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同前)又曾对其伯父王志说:“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谢朓见语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甚至有意效仿蔡邕赠书王粲的举措,表达死后要将平生所聚之书赠与王筠。又曾在武帝面前说:“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沈约对王筠的赏识溢于言表,在今天看来确为不实之誉。沈约作为一代文宗,何以如此?仅仅是出于对后进的无私奖誉吗?其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有对永明声律命运的考虑吧!
研究者注意到了永明文学到宫体文学的变化轨迹,却皆忽略了从永明文学到宫体文学的发展,实际上还存在着“梁初三十年”这样一个文学时段。这个文学时段,名义上是以沈约为文坛宗主,事实上是以萧衍为主导、以萧统为中心的文学新变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新变,主要表现为对永明细碎声律的反驳,以乐府诗(吴声、西曲)的自然音韵来对抗人工声律,以魏晋曹(植)、刘(桢)等人的古朴雅致来纠正永明时期沈(约)、谢(朓)等人的不良文风。直到萧统去世,萧纲继为太子,与在荆州的萧绎相为鼓应,才开始扭转这一“懦钝殊常”(萧纲《与湘东王书》)的局面。以萧纲为首的宫体诗风之所以在此一时期蔓延开来,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在声韵上对永明声律的自觉精研和努力回复亦当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不然,史家何以会有“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梁书·庾肩吾传》)的评论。“复逾于往时”不仅是针对于“梁初三十年”这一文学时段而言,它主要还是,或者说,更应该还是针对永明文学自觉追求声律而言的。
萧衍排抑四声,也是与他在政治领域内排抑沈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个角度来看萧、沈之争,他们的分歧不仅仅是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更是涉及君君臣臣的关系。萧梁建国是与沈约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的。建国之后,沈约并未获得他所期望的羽赞之职,反而是周颙之子周捨青云直上,取代了沈约等人的权位。究其原因,也正与废齐之时沈约的深度参与有关。萧衍出于政治上的讳避,故对沈约有所排抑。而沈约对废齐一事常心存蒂芥,难免于人面前谈及,至为萧衍所不喜,观其赤章之事可推知一二。《梁书·沈约传》载天监十二年沈约因张稷事而迕帝旨,回家之后便病了。“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关于沈约之死,唐佚名《灌畦暇语》还载有《鹿葱诗》一事:“沈约以佐命勋位冠梁朝,晚年诸进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约所为鹿葱诗,乘间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几得道士赤章事,遂大发怒。约以忧死。”⑨《鹿葱诗》如下:“野马不任骑,兔丝不任织。既非中野花,无堪麇(鹿)食。”这是一首咏物诗,其中有没有寓意,那就要看读诗的人有没有用意了。如果用事者以此诗为口实谗陷沈约,沈约也确难开释。野马是空中尘埃,兔丝是空中游丝,鹿葱则辛寒有毒。这三种事物都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东西。大概用事者是用此诗来印证沈约本人对身处之职有所不满吧。《梁书·沈约传》载有沈约晚年报徐勉的一段话说:“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语词甚为凄苦。钟嵘《诗品》评其诗“清怨”。“清怨”亦当是沈约在萧梁一朝十几年政治生活的写照,不止是针对其《怀旧诗》。沈约卒后,朝臣议谥为“文”,梁武帝认为“怀情不尽曰隐”,故谥为“隐”。在武帝眼中,沈约“怀情不尽”,则置他于何地?“谥”关乎人物的盖棺定论,由此可见萧、沈之间的微妙关系⑩。
由上述可知,梁武帝“不知四声”的说法是不可靠的。梁武帝平生四声三问,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差异,然而对四声的排抑却是前后一致的。梁初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永明声律论之所以未能大行,其根源便在于此。直到萧纲入主东宫以后,才以太子之尊大倡宫体,而永明声律也才得以借助宫体之风渐广门庭,最终演为唐代律体。
收稿日期:2007-10-10
注释:
①目前没有相关材料证明此四则记载的三次事件系同一事件的不同转述。
②《谈薮》为北齐阳松玠所著。公私书目著录书名与人名略有不同,然其为北齐人可确切无疑。
③本文所云梁武帝排抑四声,乃是针对文学创作特别是五言诗四声病犯的情况而言的。
④武帝的刚断不仅体现在正乐上,在天监年间礼乐制度的制作层面上皆体现了其刚断的一面。《梁书·武帝纪》:“天监初,则何佟之、贺玚、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
⑤据林大志先生《梁武帝的文学思想》(《求索》2005年第11期)一文统计,萧衍现存诗歌106首,其中乐府诗54首,占其诗歌总量的一半以上。又据邬国平先生《梁武帝与钟嵘〈诗品〉》(《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一文辨析,梁武帝的文学观念与钟嵘《诗品》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倡导自然音旨便是其中之一。
⑥钟嵘《诗品中》:“约于时谢脁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第1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⑦可参见陈庆元《萧统对永明声律说的态度并不积极——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一文(《文选学新论》,中国文选学会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157页),及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梁武帝天监六年沈约条按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⑧刘绦的生平已经不可确知,据《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任学良的注文以及《颜氏家训》之《风操》、《勉学》二篇,可知其人于大同中曾任尚书祠部郎,后去职不复仕。刘绦通《三礼》,著《先圣本纪》十卷,既为儒师,又兼通文史。其声律论的内容载于《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及西卷《文二十八种病》、《文笔十病得失》中。其声律论的价值意义在何伟棠《永明体到近体》(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第五章第二节有专门讨论。
⑨《灌畦暇语》,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于沈约《鹿葱诗》下引(第1658-165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书今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本。
⑩武帝对于永明人物排斥还体现在对于范缜、王亮、萧琛等人身上,似乎不止于沈约一人。其原因也不尽一致。关于此点,笔者有另文详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