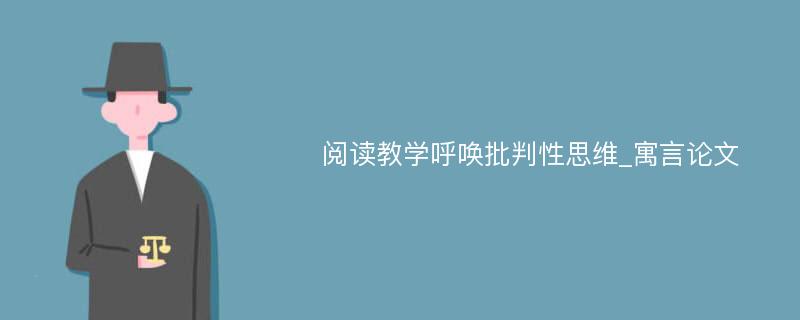
阅读教学呼唤批判性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阅读教学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愚公移山》是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教学案例不计其数。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一是1981年钱梦龙老师发表在《语文战线》上的教学实录,二是2005年郭初阳老师发表在《教师之友》上的教学实录。在我看来,钱老师的这节课前无古人,至今后无来者,鲜明地体现了他“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在这节课里,我见识了一位天才教师游刃有余的优雅和举重若轻的智慧。郭初阳老师是新时期崛起的一位有个性、有想法的教师,他一改《愚公移山》传统的文本理解,课堂教学呈现出另一番面貌,让人耳目一新,却也给人以强烈的陌生感、颠覆感和尖锐感。在这节课里,我不仅看到了郭老师试图摆脱传统课堂的匠心,还看到了他试图突破传统文化窠臼的野心。 两节课内容有别,风格迥异,但在教学上还是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思维取向。比较两个课例,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批判性思维在文本解读和课堂教学中的内涵、价值与意义。 文本解读的学术边界 《愚公移山》选自《列子·汤问》。鉴于列子其人的复杂性,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探幽发微,无助于对《愚公移山》的理解;《列子》一书之真伪与篇目之正误至今存疑,从文化谱系的角度研究《愚公移山》,似乎也难有大的发挥余地。[1] 《列子》向来被视为道家之书。在《汤问》一节中,“愚公移山”与“夸父逐日”并出,告诫人们要以愚公的“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为榜样,以夸父的“期功于旦夕”[2],恃能以求胜为警戒。愚公名虽为“愚”,却以违背常理又接近大道的方式获得了成功,他那种超出日常限度的恒心与专注,与庄子笔下的那位“承蜩”的“佝偻”一样,切中了“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体“道”之道;而智叟,名虽为“智”,乃“俗谓之智者,未必非愚也”[3],他的“聪明”与心机,均停留在感觉、经验与常识的层面,终似浮云蔽日,恰恰构成了求“道”的障碍。总之,摒弃急功近利之心,杜绝旁逸斜出之念,方能不断接近于“道”。 有意思的是,后世对《愚公移山》的阐释,却与这散发着浓厚黄老气息的观点渐行渐远。特别是当其脱离了《列子》这个略显杂乱的文本系统,以一个独立的寓言故事出现时,它被迅速地、几无痕迹地纳入了儒家的主流话语中。最典型的当数宋人陆游。据詹丹教授统计,陆游在诗歌中不下10次咏及“愚公”,或抒壮怀如《杂感》:“蹈海言犹在,移山志未衰。何人知壮士,击筑有余悲。”或抒愤懑如《自嘲》:“太行王屋何由动,堪笑愚公不自量。”显然,陆游将自己的悲鸣投射到“愚公”身上,在他的吟诵中,“愚公”成了矢志不渝、壮志难酬的悲剧英雄。[4] 到了现代,《愚公移山》则被植入了新的观念,甚至被纳入了现代性的革命话语体系,成了革命动员和政治激励的兴奋剂。傅斯年说他的人生观就是“愚公移山论”,他在强调积极进取的同时,也将“为公”意识以及文明的累积进化意识注入这个寓言,以批判老庄阮籍的“齐生死,同去就”的“达生观”,隐逸、遁世、涅槃的“出世观”,沉溺于物质享乐的“物质主义”以及主张“人为道德而生”的“遗传的伦理主义”。在傅斯年看来,这些都是“左道的人生观念”。作为“五四”一代人,傅斯年对《愚公移山》的解读,加强了“愚公移山”的“正道”色彩。[5]毛泽东则将这个传统的神话故事变成了政治寓言,寄托了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豪情壮志。现代中国人多是通过他的“老三篇”来理解《愚公移山》一文的。 人们对《愚公移山》的理解虽千差万别,但核心还是愚公的艰苦奋斗精神。从一个“体道”的寓言故事到一个砥砺践行的励志寓言,这固然与儒家文化、革命文化强大的融纳与整合功能相关,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愚公移山》本身的文体形式和叙述结构。这就像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无论怎样,再多的哈姆雷特也必须以莎士比亚的那个哈姆雷特为基础。 《愚公移山》本是一个寓言故事,这是解读文本必须尊重的基本事实。文体决定了文本理解的方向和路径。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混淆寓言与历史、传记与传说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反过来又以历史的眼光苛求寓言,拿传记的标准否定传说,文本解读的随意性可见一斑。什么是寓言?直白地说,就是为了寄寓某个道理而刻意“编”出来的故事,一般来说,这个故事简洁、清晰,结构的指向性明确。在古希腊文中,“寓言”是“其他”与“言说”的合体,即“另外一种言说”;“寓言”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讲”的或者“写”的一个故事。[6]显然,“编”寓言就是为了“说”道理。既然如此,寓言的“编”法就与一般小说创作不同,它要服从讲道理的需要,要服从要讲的那个道理的逻辑,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逻辑或者生活逻辑、社会逻辑。比如《农夫和蛇》(《伊索寓言》),它刻意渲染农夫之善与僵蛇之毒,以此说明不恰当的善心只能招来祸患。其中一些细节,如“冻僵”,就不合乎蛇的冬眠习性;冬眠的蛇也不大可能睡在路边;农夫的善良也超出了正常的限度,不太合乎生活常识与常理。但是,有谁会因此而指责它呢?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个故事所包含的明辨善恶的道理。 是寓言就该以寓言的方式来阐释。其他目的或者其他方式的阐释,比如上述政治化、革命化的阐释,都应该基于这个学术性的解读。当然,“戏说”除外。 《愚公移山》是个典型的寓言结构。故事的结构很简洁,就是“两个对比”:“一大一小”的对比(见郭老师课例)与“一智一愚”的对比(见钱老师课例)。弱小的人移动了巨大的山,这是个事实判断(文本事实);俗世中的“愚”与“智”在故事中发生了错位,这是个价值判断。如何基于这个事实来作出价值的界定,取决于每个人对这个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因果关联的理解,因而解释的张力很大。其实,无论是老子的“无为而不为”,还是孔子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都能在其中找到解释的空间;荀子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与《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能在此找到逻辑上的支点。但显然,比起道家来,基于日常伦理与功利情怀的儒家更能在其中找到共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道家的寓言衍变成为儒家的箴言,而原初的写作动机反倒被人忽略了。 《愚公移山》就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传达了关于“力行”等道理。判断《愚公移山》好不好,应该看《愚公移山》的文本要素与结构能否传达出这个寓意。 在文本理解上,钱老师由语言到意义,循着文本的自身线索,步步推进,分析“移山”的动因(“痛感迂塞之苦”)、目标(“确知移山之利”)以及行动根据(“深明可移之理”)等要素,凸显愚公之“智”。钱老师的解读因其“守正”而显得清晰稳健。钱老师并非没有意识到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他的机智在于,他将关于《愚公移山》的争议作为思考与切入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突出文本自身的组织结构与表达逻辑。[7]这看似波澜不惊、质朴无华,却与愚公的“无心而为公”一样,反而避开了节外生枝的风险,在更高的层面上切中了文本的核心。 与钱老师相比,郭老师的解读跨越了许多边界,他的意图在于“解构”: 1.钱老师认为愚公“确知移山之利”,但郭老师则认为,愚公解决了自己“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的麻烦,但“山阻碍人的出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换句话说,原来阻挡自己的山,如今阻挡别人去了,愚公只是“利”了自己。 2.钱老师认为愚公“深明可移之理”,郭老师则认为,要做到“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要有“双重的要求”:第一,血缘的不断;第二,思想的不变。显然,愚公无法保证。再者,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山并非“不加增”。 3.钱老师认为愚公造福后代,郭老师则认为他贻害子孙,因为愚公“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了他子孙,剥夺了他子孙生活的自由”,导致后人“不能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因此断言愚公是“害群之马”。 4.从根本上质疑愚公移山的动机。虽然名曰借张远山的观点,但看郭老师如此刻意地引用及渲染,显然心有共鸣:愚公移山不过是上演给天神看的一出“苦肉计”,甚至也不排除他与天神还有“更多更多的不可告人的东西”,借此“帮助建立帝的秩序”。由此得出愚公狡猾、毒辣、可怕,是阴谋家等评断。 郭老师的观点遭到了许多质疑。有老师在商榷文章中为愚公辩护。如,“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原本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可见愚公并未损害他人;“山不加增”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人缺乏科学常识;以中国传统的“孝道”为愚公辩护,言下之意,愚公贻误子孙应由传统文化买单;等等。我觉得,如此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回避问题的根本,反而会让问题变得混杂不清。其实,从寓言的文体性质来思考,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郭老师也承认,《愚公移山》是一个人生寓言,表达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儒家的一种非常健朗的、非常积极的精神”。既然如此,在“编”寓言的过程中,选择性地屏蔽一些因素,比如移山会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夸大或强化一些因素,比如“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虚拟一些神话因素,比如帝的出手相助……这不就是寓言创作的基本手段吗?其实,读寓言的人都知道,连“移山”本身也只是个象征,只是个隐喻,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费尽心思地去考证太行、王屋二山的地理内涵。 《愚公移山》并非历史文献,虚构、夸张、移情乃是寓言的基本创作手法,而这恰恰是《愚公移山》独特、别致和匠心之所在。不是像常人那样立志搬家,而是固执地选择移山,那才是愚公;违背常理,子孙无穷,挖山不止,那才是“愚公精神”。正是这种违背常识与有悖常理的情节设置,才使寓言有了深远的寄托。教师的责任,就在于给这些不合常理的情节一个合理的解释,帮助学生把握故事不同于常理的寓意,准确地理解愚公的精神实质。不去揣摩情节设置的独特用意,不去理解故事的良苦用意与匠心,反而怪罪它不合常理,那真是误解加曲解,无异于焚琴煮鹤。 关于愚公与帝的勾结问题,已超出了学术性的文本解读范畴,属于“戏说”“水煮”“恶搞”一类,无中生有,不足道也。相反,钱老师的解释虽然中规中矩,却是合情合理:“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使山神害怕,天帝感动,文章这样写,恰恰是写出了愚公挖山的精神感人至深。”帝的感动以及他的出手相助搬山,归根结底服务于寓言的寓意:天道酬勤。 当然,郭老师关心的,其实并不在于寓言本身是否合理。他的用心,更在于寻找“隐藏着中国人非常喜欢的,或者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密码,文化的密码”。包括他引入“外教”的评点,无非希望在对比中凸显传统文化的乖谬。这是个很大胆也很有创意的教学构想。的确,神话和寓言是民族文化的蓄水池,寓言里隐藏着民族文化的密码与基因。比如《愚公移山》中的“智”与“愚”这对并举的概念,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 但是,《愚公移山》的文本分析与借“愚公移山”来质疑传统文化,这是不同层面的两件事情。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秉持的逻辑却截然不同:前者考量的是故事与寓意之间是否具有合理而充分的逻辑关联,质疑的应该是“这个故事能否传达这个寓意”;后者考量的则是故事所负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是否合理,质疑的应该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编励志故事”。从逻辑上看,只有证明这个故事合乎中国人的逻辑与思维方式,才能证明它确实隐藏着中国人的“密码”,才能凸显其与现代文化的抵牾与悖逆,才能达成文化批判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郭老师显然犯了南辕北辙的错误。他似乎在嘲弄故事本身的荒谬性,结果却让他的文化批判落空了。在课堂结束前的师生对话中,我们看到,郭老师没能说服学生,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学生依然回到了郭老师竭力否定的观点。从这里,也可见文本结构的先在规定性与内核的相对稳定性。 教学意义上的阅读,本质上应是一种学术性的阅读,无论是为了“立”,还是为了“破”,都要尊重文本自身的要素、结构与逻辑,基于客观的文本说话,基于文本的事实说话,基于文本的逻辑说话,这是文本解读的学术边界。抛弃了这些,就是“戏说”。“戏说”当然也有其文化与艺术上的独特价值,但若将教学与“戏说”混同,那就将阅读教学的价值与意义从根子上取消了。 学术性的解读,还必须是非功利性的。不能先设定一个目的,按图索骥;不能穿凿附会,牺牲文本自身的逻辑迁就功利解读的需求。比如,因武松打了如今的珍稀动物老虎就去否定《水浒传》的文本价值,因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而质疑《背影》的经典地位……乍一看只是一些无聊和荒唐的噱头,实际上却透露出我们在文本解读上学术意识与理性精神的欠缺。 基于批判性思维的文本分析,追求文本事实、历史背景、文化逻辑和人性情理的统一,在考虑各种要素的意义上强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追求一种综合意义上的“合理性”解释。即使是质疑,也未必就是为了否定;不仅合理质疑,更要合理解释,并综合评估各种解释的关系与合理性。在孙绍振先生看来,这其实就是“学术性”的核心内涵。显然,这与很多人推崇与热衷的意在标新立异的“求异思维”不同,与追求惊听回视的轰动效应的“翻案式”解读不同,与为了达成文本之外的功利目的而进行的“颠覆式”阐释更不可同日而语。 教师主导的主体性限度 文本解读只是阅读教学的一个方面。以什么方式在师生之间达成对文本的理解,不仅体现了教师的学术水准,也反映了教师的思维方式与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对师生关系的理解和对自我的角色理解。 孙绍振先生用“主体间性”来概括现代师生关系,同时他也肯定了钱梦龙先生关于教师主导作用的观点。“主体间性”是教育民主的哲学基础,也是对话教学的理论前提。但是,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不能以牺牲学生的主体在场为代价。在教学的意义上,学生的主体性存在,如孙绍振先生所说,关键在于“尊重学生的思考过程,哪怕是错误的”[8]。思维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是通过思维的“过程性”体现出来的。直接从起点到终点,从文本到结论,没有一个分析、论证、评估、反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遗憾的是,在课堂上,我们看到的常常是教师的思维与思想,而学生的思维与思考始终处在从属与追随的状态,他们的思维被教师的主导作用遮蔽了。 郭老师的课堂,看起来充满了对话与思想碰撞,有时候,扑散的火花甚至让人陶醉和兴奋。但在骨子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理念先行、思维专断、精心设套、强势诱导的教师,所谓的对话与质疑,更多的是学生在教师预设与诱导下的机械反应而已,比如以下这个教学片段: 师:苦肉计,那也许他们(天帝和愚公)有更大的阴谋呢?也许这更加能够帮助建立帝的秩序呢?可能他们有着更多不可告人的东西,所以他们要上演一出戏。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愚公,他给我们的形象,感觉有点…… 生:(轻声)狡猾。 师:有点狡猾,是吧?甚至有点阴险,甚至还有点…… 生:毒辣。 师:毒辣,可怕!怎么这个蠢老头,竟然是一个阴谋家?(众笑)成了个谋略家,太厉害了! 在这个环节里,郭老师连续用“有点”“甚至还有点”这样的表达,用刻意留白和省略的办法,似乎给学生预留下了空间。但在其假定的事实和预设的逻辑之下,学生还有什么选择呢?由狡猾到毒辣,再到阴谋家,在“众笑”的欢快与轻薄之中,愚公形象被糟蹋了。这样的诱导与“套供”,比起直截了当的“满堂灌”和“填鸭式”教学更可怕,因为学生的思维被控制,但学生不自知,不自觉,思想与思维就这样给魅惑了,给取代了,给消解了。 教学不可能没有预设,但郭老师的预设意图单一而直接,学生的回答多停留在近乎本能的刺激反应层次上,多维的比较与独立的反思明显不够。是预设问题,还是预设答案;是预设思维方向,还是预设思维路径;是预设解决问题的要素与策略,还是预设解决问题的程序与方法,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总体上,我们似乎更注重后者,而忽略前者。一旦答案、路径和方法都预设好了,那么,学生的主体性到哪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教师的功能定位,普遍认同的是韩愈的“传道受业解惑”。在历时性的文化传承意义上,这个说法有其合理性;在共时性的教学活动中,这样的理念却可能妨害师生之间的民主关系。“传”“受”“解”这样的动词,不由分说地将学生置于接受者、继承者的位置,而剥夺了他作为对话者、理解者、质疑者的身份。殊不知,对话才能达成真正的理解,理解才是建构的基础。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知识中心”以及基于“知识中心”的“教师中心”,存在的土壤越来越贫瘠。在观念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是复杂的,认知是多元的,而人则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只是一个“摸象”的“盲人”,都只能在特定的层面和角度上认识真理,谁也不能以真理自居。借用哈耶克的命题,我们是时候摆脱知识的自负与理性的僭妄了,这恰是批判性思维的精髓之所在。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的谦逊才可能是理性而真诚的,师生的对话才可能是平等、开放从而是有效的。 不仅如此,对话也是教学相长的前提。承认时代与自我的局限,尊重学生作为一个“元”的独特性和独创性,对话才可能给“教”带来“长”的可能。在文本解读中,教师虽然有着专业的素养与经验,但也可能被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观念和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思维习性所蒙蔽,造成对文本的麻木与隔膜;而恰恰是知识和观念处在建构中的学生,因其“未完成性”而可能有“裸读”的可贵发现。这恰恰是实现教学相长的宝贵契机。 学生的主体性越是保持独立性与开放性,教学就越可能走向澄明与有效。 钱老师的教学可圈可点,看钱老师与学生的对话,就像欣赏一出古典主义戏剧,起承转合,严丝合缝。不过,也正是这种流畅与完满,让我产生了一些联想与担忧:教师的主导作用会不会遮蔽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呢?常识告诉我们,思维一旦进入文本的“深水区”,必然伴随着纠结、停顿、中断、迷茫与滞涩。 钱老师预设的结论是“愚者不愚”。这看似与《列子》的原意相同,但内涵并不一样。在《列子》中,愚公愚钝、倔强、守拙、固执,他因此而接近了大道。显然,这里的“大智若愚”是认知和实践意义上的判断。钱老师在分析愚公移山的“动因”“目的”以及“行动根据”的大部分时段里,强调的也是其认知与实践上的“智”;但在讨论“愚公不愚”的时候,却悄无声息地将这个认知与实践问题转化成了功利与道德问题。请看他的教学片段: 师:我想先给你们讲个事。我们上海有一位公共汽车售票员,对待乘客非常热心,是个学雷锋的标兵,《文汇报》上登过他的照片,很多人都写信表扬他,说他服务好。但也有些小青年说这个服务员“赣头翰脑”,这是我们上海方言,就是傻里傻气。这是什么道理?还有雷锋,有些人不是也叫他—— 生:傻子!…… 生:有的人是从为自己的角度来看的,就说他是傻子;有人是从他为集体做好事来看,感到他是好的。 师:哦,讲得真好!就是说要从什么角度看问题了,用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来看待这样一件事。这位同学的观点你们同意不同意? 钱老师这样解释自己的教学:“介绍学雷锋标兵,为了引导学生从更高层次理解‘愚公不愚’的道理。”事实上,钱老师做到了。钱老师借助“雷锋”这个道德内涵极其鲜明的词语,完成了从“认知层次”到“道德层次”的跳跃,学生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我们如果用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观点去看愚公,他不仅不笨,而且还‘大智若愚’”的结论。 这就背离了原文的逻辑与宗旨:《愚公移山》讲的是认知问题和实践问题。不管动机怎样,目的为谁,只要违背了笃志抱一、心无旁骛的原则,那就是“愚”,就会失败。钱老师的“愚公不愚”是“动机论”的逻辑,则可能引向这样的理解:无论愚公的认知和行为怎样,只要他动机高尚,就是“不愚”的。如此解释“大智若愚”,其实是以动机的善恶讨论替代了认知是否合理、实践是否有效的讨论,结论可能是:无论认知多么糊涂,无论行为多么荒唐,只要动机高尚,就是“智慧”。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思维误区,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习惯于这种道德主义逻辑,再荒唐的认知和行为,都能找到高尚的动机来辩护。 假设一下,如果允许学生在没有任何暗示或引导的情况下,比较一下愚公与这位售票员的“大智若愚”,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思维过程,至少能给学生留下一些宝贵的疑虑和不满足感。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结论是真理,但我们可以做的是,为学生继续探寻真理留下一种可能性。而一旦我们给了结论,某个思想的种子可能就此死亡。 我们的阅读教学喜欢在文本之上来一个迁移或者升华。这是个需要加倍审慎与理性的环节。离开了具体的文本与具体的问题,而去嫁接或者抽象出一个“更高层次”的结论,其间的逻辑风险是可以想象的。 并非为尊者讳,钱老师的理解显然受限于1980年代的政治与文化思潮,瑕不掩瑜。然而,30年过去了,我检索《愚公移山》的教学案例,发现这种“大智若愚”的思路,依然大行其道,几乎成了《愚公移山》的“标配”内容。可见,思维的惯性力量多么强大,而文化与思维上的自我警惕与反省多么重要。 30年前,钱老师的一节课,甚至改变了文言文教学的课堂模式;10年前,郭老师的一节课,极大影响了文本解读的理念。在某个意义上,这两个课例已经有了“范式”的意义。正因如此,才有解剖和评价的必要。在我看来,不仅文本阅读需要批判性思维的介入,课堂教学也需要一场批判性思维的洗礼。批判性思维是以理性和开放性为核心的理智美德和思维能力的结合,既是一种追求公正思维与合理决策的思维技能,也是一种秉持多元、理性与审慎的人格。在文本分析中,批判性思维是学术性的基本前提;而在教学行为中,批判性思维则是平等对话、合理质疑与省察性反思的人格保障。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育人中学王宇老师的帮助。她提供的实验教学真实地展示了当代学生对《愚公移山》的认知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