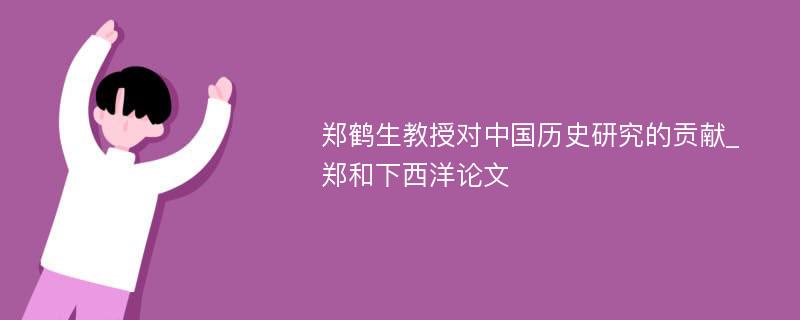
郑鹤声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论文,教授论文,贡献论文,郑鹤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人物
郑鹤声教授学术研究的领域很广,除中西交通史外,诸如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文献学、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亚洲史等,都有精深的造诣,并取得了很多成就。
先生字萼荪,浙江诸暨人,生于1901年5月19日,逝世于1989年4月20日。他在解放前曾长期供职于国立编译馆和国史馆,先生担任常务编审和纂修,并兼任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教授;解放后一直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教书育人,著述不辍。先生一生勤奋,著述甚丰,从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汉隋间之史学》开始,到1989年《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的正式刊印,由他所写的并且出版了的专著不下30部,尚不包括未能出版的专著和已经发表的论文。就这些成就而论,我个人认为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主要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海外交通史三个分支学科。
一、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巨匠
先生从事历史学的研究,是从中国历史文献学开始的。而先生之所以首先专志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又是与其长兄郑鹤春和老师柳诒徵的帮助与指导分不开的。
郑鹤春长先生10岁,早在先生上小学之时,他就已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文史地部。待先生上中学时,他已经大学毕业,每逢回家探亲,便向先生介绍文史的基本知识,并将其大学讲义留下来供先生学习。待先生考入大学后,他又用自己的薪金为先生购买了数千册书籍,建立起家庭图书房,专供先生放假在家时利用。先生在回忆家庭对他的影响时曾说:“我的父亲、母亲和大哥都希望我做一个读书人,回家之后,所有家庭和社会杂事,都不要我去费心,这也使我养成一种沉静的性情,我一生中潜心研究学问的兴味,就在这样一个优良的家庭环境中养成,在以后的生活途中,我每逢回忆这些往事,都深深地感到一个人有好的父母兄弟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1920年,先生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文史地部。当时,在该部主持史地教学的老师分别是柳诒徵(1880—1956)和竺可桢(1890—1970)。他们为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专门筹办了《史地学报》,选择学生的优秀论文在上面发表。先生在校学习期间,就曾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4篇《地学考察报告》和5篇史学论文,从而树立起学术研究的信心。柳诒徵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详细阅读自己所指定的正史书籍,并写出心得笔记交给他批阅分析,使学生们丝毫不敢马虎。先生正是在师从柳诒徵读书期间,系统地阅读了“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等书,为自己研究历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柳诒徵对于版本目录学也极为重视,并要求学生注意对文献和史料进行分类整理,从而培养了先生对于目录文献学的兴趣。先生在东南大学毕业时,曾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撰写成10余万字的论文。柳诒徵老师不仅将这篇论文推荐到《学衡》杂志上分期连载,还推荐到中华书局单独出版。
1925年,先生于东南大学毕业后,即应聘到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教。出于教学之需,先生曾就“二十四史”的基本内容分别撰写成讲义,共26册,交云南高等师范学校油印;同时油印为讲义的,还有先生编写的《正史汇目》、《亚洲诸国史汇目》和《中国史学史》。先生编写的这些讲义,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的才华,也得到了商务印书馆何炳松的高度重视。1928年,商务印书馆正式为先生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几年间,先生有《班固年谱》、《袁枢年谱》、《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概要》(与郑鹤春合著)、《司马迁年谱》、《杜佑年谱》等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1932年间)。另有《荀悦年谱》、《刘知几年谱》、《司马光年谱》、《徐光启年谱》等书,虽已在商务印书馆付排,但却不幸毁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火之中。此外,先生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还出版有《四库全书简说》(南京中山书局1933年出版),并有《史学概论》与《史料学》作为讲义,分别在中央大学和山东大学油印。
在先生的心目中,历史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明确地告诫青年学者,不要怕当“史料派”。只有论据充足,立论才可能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对于学术界某些人随心所欲地摘引一点史料而做长篇大论的学风,或者干脆从概念出发来演绎历史的不良倾向,先生十分不以为然。他向学生指出,搜集资料,贵在于勤,贵在于恒。有些资料即使暂时用不着,也要注意保存和整理。先生一生就曾辛辛苦苦地搜集整理和汇编了很多有用的专题史料,除前述已经出版的《郑和下西洋史料汇编》外,一直未能出版的还有曾费10年之力整理而具有《清会要》雏型的《东华录类编》(1600万字,南京解放时移交给出版总署后下落不明)、80余万字的《黄河志文献编》、近20万字的《历代孔子研究文献目录》、80余万字的《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等。
那么,如何来掌握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呢?先生特别重视史部目录学的作用。他于1929年从昆明回南京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时,专门为学生开设了“中国史部目录学”的课程。他认为,如果一个学者不从目录学入手,就很难掌握各种历史文献的具体内容及其史料价值。他所撰写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从介绍我国史书的渊源和史部的位置入手,详细地叙述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和史目正录、别录与今录的流别,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历史文献分类法,并且结合史料学和西方历史文献目录学对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的今后发展进行了阐述。从这部书的内容可见,先生所论述的史部目录学,已超越了清代学者们所介绍的目录学为各种文献篇目及版本的学问范围,而成为揭示历史文献目录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迄今为止,该书还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史部目录学专著。此书曾在50年代和70年代又分别由上海和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再版。
先生还认为,研究历史并不能仅仅限于历史类文献,还有必要旁涉其它非历史类文献。同时,针对本世纪初学术界中所出现的蔑视民族文化的思潮,先生专门著写了《中国文献学概要》,以期改变当时存在的“号为学人,而叩以本国文献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对者”的情况。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还将它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书店为此也曾先后多次重印该书。直至最近,复旦大学和上海书店仍决定将先生所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和《史学概论》,收入到“民国丛书”第二编中,予以再版。屈指数来,先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已独领学坛风骚近70年。毫无疑问,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巨匠。
正是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先生早在1928年就明确地把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史学的胚胎时期(先秦)、昌盛时期(汉隋阶段)、衰落时期(唐明阶段)、蜕分时期(清代)、新的发展时期(清末民初),从而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他的这一学术体系,对当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影响。
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
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出版)一书中,曾对当时学术界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表了如下评论:“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历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
在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下,所产生的近代史著述很多,如陈怀、高博彦、吴贯因、魏野畴、邢鹏举、罗元鲲、梁园东、沈味之诸先生的著述,各有长处。其最完善的为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民国十八九年,郑先生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中国近世史,曾编有讲义,共二十八章,起自明季,至民国年止。此书即系根据讲义改编而成;全书体大思精,甚为赅备,惜迄今仅出二册。”
顾颉刚在这里所提到的《中国近世史》,最初是先生给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学生授课的讲义,约80万字。讲义在两校分别铅印和油印后,一时洛阳纸贵,希望得到这部讲义的人很多。但先生却认为自己的这部讲义还只是急就之章,于是又发宏愿向南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苏州、宁波、扬州、武昌等地书肆购买有关史料书籍,用以全面修订这部《中国近世史》。在当时,收藏家们和各图书馆都以搜罗宋元版本为贵,而先生却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不为人们注意和重视的中国近代史料,所以一时所获甚丰,多为罕见的海内孤本和稿本,如曾从清朝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后裔中获得邓与林则徐查办鸦片的有关文件,从其他人手中购得完整的清季以来的《政府官报》、《政府公报》等。当先生费数年之力将那部书稿修订完就时,不料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南京沦陷,修订好的书稿也毁于战火。至1944年,在出版家的一再要求之下,先生只好将那部《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稿交南方印书馆出版。先生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对“上古中世”与“近世”作了明确的区别:“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古中世之区别有三: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一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通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一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中国近世史之开端,当自新航路之发现始。”由此可见,先生之所讲的中国近世史,实即中国近代史。他之所以将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定在新航路发现后西人东来的16世纪,是他认为自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已使中国开始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自后中西关系的演变、民族思想的发展、近世革命运动的产生,都渊源于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在解放前,他曾明确地反对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他说:“我国坊间出版之中国近世史,率以鸦片战争为开始,则为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不探其源,则其源不明。”今天看来,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年对于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的这些意见,仍然有着它的理论价值。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完全定于鸦片战争一说,他所坚持的那种学术体系也被打入冷宫。尽管如此,先生还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他不仅参加了建国初期教育部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编定委员会的工作,参加了中国史学会主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编辑工作,并为此而捐献了多种自己所珍藏的海内孤本资料,而且还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并发表了10余篇论文。
为了有助于人们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先生在30年代还曾编制一部《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这部《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起自1516年,终于1941年,每年分“阳历”、“阴历”、“星期”、“干支”四项,按日对应,相互查对十分方便。在该书的前面,先生还专门分中国年号、日本年号、朝鲜年号、干支纪年、西历纪元诸项制做了一个《近世中外年号纪元对照表》;书末还附了一个完整的《太平新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也便于人们查对日本、朝鲜、太平天国时期的历日。先生之所以以1516年作为始年来编写此书,则是由于该年有葡萄牙人拉费尔·佩雷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附帆来华,自此以后,“海航大通,欧美文明,骤然东来,国际问题,因之丛生,所有活动,几无不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者。中西史日之对照,较之上古中古,其用更繁。”显然,该书的编写原则是与他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相互一致的。该书的作用,正如中华书局在1980年所写《重印说明》中所言及的:“本书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内容较为详备,为研究清史及近代史必备的工具书,现已很难买到。兹商得编者郑鹤声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的同意,转由我局出版,以供读者之需。”由此可见,该书今天仍是人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先生还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学术界对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虽然早在1914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就出版了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但由于当时还处在中华民国建立的初期,严格地说,它还不是一部“历史”研究书籍。先生所写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于1943年在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在该书中,先生明确地把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主要线索,并按革命的发展将中华民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1.辛亥革命推倒满清为第一阶段;2.北伐完成,打倒军阀为第二阶段;3.抗战建国为第三阶段。”由此可见,先生匠心独运,自成机杼,在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上充分地考虑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因素。可以说,先生这部《中华民国建国史》,在40年代初期的中国学术界,还是空谷足音。
三、郑和研究最有成就的专家
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自19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势力的增强及其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西方学者开始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最早进行这一研究的有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F.Mayers),他曾利用明朝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材料进行研究,于1875年间在《中国评论》的第3期和第4期上用英文连续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探险》的长篇论文。接着,俄国驻华使馆医师贝勒(E.V.Bretschneider)也在该刊上用英文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和西亚诸国的交往》,再次论及郑和下西洋。此后,英国人菲律普斯(G.philips),荷兰人 施古德(G.Schlegel)、戴文达(J.Duyvendak),法国人沙畹(E
.Chavannes)、高第(H.Gordier)、伯希和(P.Pelliot),美国人柔克义(W.Rockhill),日本人藤田丰八、山本达郎等也在翻译介绍郑和下西洋资料的同时,对郑和下西洋的具体数次、时间、地点、船舶、航海图等问题也做了考证和研究。而在中国国内,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自本世纪初开始,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也把研究的目光投向郑和下西洋,期望通过宣传这一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空前壮举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树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首先揭开国内研究郑和序幕的是梁启超,他于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除对郑和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外,他还就西洋的一些具体地名进行了考证。后来,直到1934年,又有孙伯恒、李长傅、向达、张星烺、许云樵、冯承钧、夏璧等人纷纷从事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纵观这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还都是以现有文献为依据来进行的,重点是对有关文献进行考证和校注,仍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
1935年,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之年岁》,从而在学术界开始了以文献资料结合碑刻等其它资料进行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新阶段。先生在这里所指的新史料,是他从明朝嘉靖年间钱谷所编的《吴都文粹续集》中,发现了郑和等人于宣德五年第7 次下西洋前夕所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的碑文。根据这块碑文,先生认为《明史》所记的有关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时间有误;他明确地把《明史》中所记载的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出使旧港之行排除在七下西洋之外,并将郑和第2次至第6次下西洋的时间做了具体更正。不久,又从福建长乐传来发现郑和等人曾于宣德六年第7 次下西洋时在当地所立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石碑的消息。先生遂于1936年夏亲往福建长乐,进行实地考察,并于同年11月6 日在《大公报》上发表《访问长乐郑和天妃灵应碑杂记》,说明两碑所记内容的大致相同。于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时间、航行路线和抵达的国家有了较为准确的结论。从此,学术界也受先生发现郑和下西洋新资料情况的鼓舞,出现了广泛调查郑和下西洋新资料的热潮,使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先生本人也在《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的发现过程中,增强了对郑和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并决心继续致力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从此,他开始大规模搜集郑和下西洋资料,上图书馆抄录具体文献,下各地调查文物遗迹,托友人注意有关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生在1936年春探访南京静海寺时,又从该寺西侧厨房壁间发现一块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残碑。该碑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所乘的船舶分别有二千料海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和八橹船,为它碑以及其它文献所未载。日寇占领南京时,该碑遭毁于战火,幸有先生在当时对碑文及时拓片,从而保存下这一珍贵的石刻材料。
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先生于4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版了《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初版,台湾胜利出版公司1979年再版)与《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两部专著。《郑和》是一部研究专著,书中对郑和出使经过、目的、海外航行情况、使团成员组织、出使结果、宝船制造等问题考证极详。《郑和遗事汇编》是在《郑和》一书的基础上,并结合新搜集的资料而写的一部专著,书中对郑和的家世、生平、历次出使西洋的情况、有关郑和遗迹与轶闻介绍详尽。这两部专著的出版,是郑和研究学术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正如黄慧珍、薛金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一文中所指出的:“《郑和》、《郑和遗事汇编》是四十年代郑和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二书汇集材料丰富,内容广泛,考证详确,是郑和研究史籍资料、文物遗迹资料的综合,是献给郑和研究者必要的参考书。”
进入80年代时,先生又通过齐鲁书社向学术界推出了他与其哲嗣郑一钧合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分上、中(上)、中(下)、下四册,共190余万字。上册出版于1980年,系统介绍了郑和家世、 生平和时代,郑和使团人力和物力,郑和使团的航海技术等有关郑和本人、郑和使团以及郑和下西洋历史背景方面的历史资料,中册两本出版于1983年,系统地介绍了郑和时代海外各国的概况,郑和出使经过,郑和出使对中外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历史资料;下册出版于1989年,系统介绍了郑和在海内外的遗迹、文献,以及后世评价郑和下西洋方面的历史资料。这部书将各种散见的文献材料和实物史料,分类整理成为一部最系统的郑和下西洋资料工具书,极便于研究者的查阅引用。可以说,这部书是先生50年从事郑和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是他贡献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该书出版后,被人们誉为是一个世纪以来郑和研究资料的“小百科”。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表明,先生是国内外研究郑和最有成就的专家。
先生并不仅仅只是重视史料的学者,他非常注意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性。早在1928年,当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和军民的事件发生后,先生即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对明朝初期倭寇侵扰中国及其中日交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以史学家的卓异眼识,及时向人们提醒中日关系问题;先生又针对英国殖民者侵占中缅边界上的江心坡的事件,先后发表《江心坡与国防》和《江心坡问题》两篇文章,从历史文献角度阐述了江心坡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先生还专门发表过《历史教学与国防教育》的论文,强调历史知识对于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就是被先生“牵挂”50年的郑和研究,他的每一部有关著作的问世也带有经世致用的特点。《郑和》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当时写作和出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激励国民,抗日救亡,以历史上伟人之功业,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从中得到力量。”而《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的问世,又为对外开放时代的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毫无疑问,先生对学术的经世致用性的重视,源自于他的深深的爱国之情。正象他早年在一首诗中所说的:“四壁图书中有我,我以著述献中华。”
1996年4月20日,是先生逝世7周年的忌辰,作为一名弟子,我谨以此文表示对先生的怀念之情和深深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