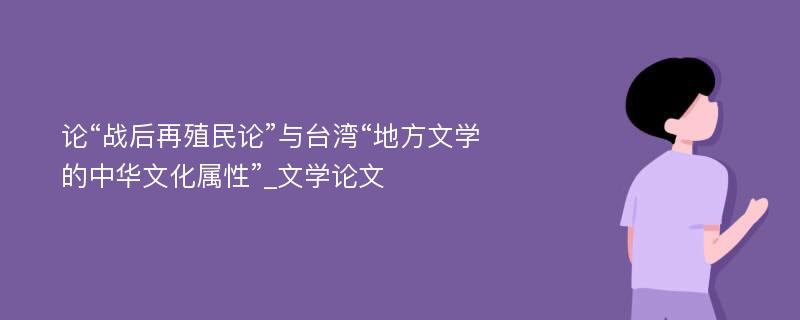
评“战后再殖民论”之要害——兼及台湾“乡土(本土)文学的中华文化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中华文化论文,乡土论文,要害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1995年的“本土化”问题论争、1997年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纪念引发的斗争、1998年对于“皇民文学合理论”的清算之后,近一两年来,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人间派”等台湾文坛统派力量,又发起了对于陈芳明著写《台湾新文学史》中所持错误史观的批判。
“偷换概念”
陈芳明宣称其撰写《台湾新文学史》时采用的是“后殖民史观”,即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经历了殖民、再殖民与后殖民三个阶段。殖民时期指日据时代;再殖民时期“则是始于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止于1987年戒严体制的终结”;解严之后为后殖民时期。
“殖民”这个词作为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使用时须遵守逻辑学上的“同一律”。如果故意用另外的含义取代固有的含义,造成似是而非的思维混乱,此谓“偷换概念”。“殖民”行为的认定,至少有三个要点,一是其行为主体是某个作为殖民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强国;二是它向海外扩张,侵犯异族异国,为的是掠夺资源;三是在它的统治下,殖民地经济凋敝,民生贫困。以此对照当代台湾,以“殖民”来指称国民党当局显然并不恰当。
陈芳明解释道:战后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戒严体制,“这种近乎军事控制式的权力支配方式,较诸日本殖民体制毫不逊色。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将这个阶段概称为再殖民时期,可谓恰如其分。”后来在与陈映真的争辩中又称:“国民政府的来台接收,被定义为殖民政府,始于1947年上海出版的《观察》杂志。这份由储安平主编的重要政论刊物,在当时就已指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方式较诸日本的台湾总督还要严苛。”在这里,陈芳明将“殖民”概念与“戒严体制”做了“偷换”,以“统治严苛”作为将战后台湾定性为“殖民社会”的主要依据。然而,“戒严”、“统治严苛”等和“殖民”并不能划等号。“殖民”固然会带来严苛、残酷的统治,但反过来,“统治严苛”并不一定就是“殖民”,否则,就可推论出统治也很“严苛”的奴隶社会、中世纪和现代某些专制国家亦为“殖民”社会,岂不荒谬!
须指出,陈芳明之所以不惜触犯学术研究之大忌而“偷换概念”,乃是因为“殖民”这个概念,包含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占领和掠夺的含义。通过这样的置换,国民党当局就成了“外国”或“异族”的殖民统治者,国民党当局作为官僚统治阶级和台湾民众的“阶级矛盾”,也就被置换为“民族矛盾”或“国”与“国”的矛盾,台湾民众反抗国民党官僚统治的斗争,也就成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斗争,其包含的“台独”政治意涵,其煽动台湾民众针对“中国”的敌对情绪的目的,都至为明显,必须加以揭露和肃清。
对历史事实的漠视和歪曲
不过,陈芳明文学史观的要害,更在于他以所谓对“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或者抗拒的态度为分野,将当代台湾文学划分为“官方文学”和“民间文学”,并以这两种文学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主线,建构其“文学史”。他宣称,战后弥漫于岛上的中华民族主义,并非建基于自主性、自发性的认同,而是官方“透过严密的教育体制与庞大的宣传机器”强制性、协迫性片面灌输的结果,因此,“台湾作家对民族主义的认同就出现了分裂的状态,认同中华民族主义的作家,基本上接受文艺政策的指导;他们以文学形式支持反共政策,并大肆宣扬民族主义。这种文学作家,可以说属于官方的文学。另一种作家,则是对中华民族主义采取抗拒的态度。他们创造的文学,以反映台湾社会的生活实况为主要题材,对于威权体制则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判讽刺,这是属于民间的文学。”
这样的文学史建构固然颇富“创造性”,但它完全违背了历史的事实。这里不妨先引用一段颇为精彩的话,它发表于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之时:
亲爱的同胞,我在这地方要慎重的告诉你们,我们是明末汉民族中最有血气、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民族意识、最有奋斗力的……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遗传着大陆民族的血统,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五大强国中的大中华民国……最后我将与大众合唱,中华民国万岁!汉民族万岁!
这篇充满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激情的文章,不是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的教材,而是出自后来成为“台独”运动始祖的廖文毅的手笔。廖文毅是个如假包换的台湾人,绝非“官方”;当时台湾刚光复,国民党在台行政机关尚未正式成立,还来不及进行任何思想灌输和教育,因此廖文毅当时的表白,纯是自发的,是“自主性的认同”,而非陈芳明所谓的“官方强制性、胁迫性的片面灌输”的结果。当时的普遍情况是:尽管经过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同胞固有的“中华民族主义”并未泯灭。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台湾同胞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其欢欣乃至狂喜是不难想象的,其流露出“中华民族主义”的激情,也很自然。这个事例充分说明陈芳明的论调与历史事实的差距有多大!
台湾“乡土文学”的中华文化属性
在陈芳明的文学史建构中,六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思潮,显然属于“抗拒中华民族主义”的“民间文学”的范畴。乡土文学后来被改称“本土文学”,甚至成为“独派”作家的一面旗帜和身份符号。然而,所谓“乡土文学”其实有着格外深厚的中华文化属性。与被陈芳明纳入“官方文学”范畴的“乡愁文学”相比,乡土文学的中华文化属性之强烈和纯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中华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的社会,重视乡土情谊成为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种特征至少可上溯至孔夫子。从《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处处可见重视宗族乡党,劝导人们安居守土的教诲。儒家强调“分田制禄”,“制民之产”,使人民“死涉无出乡”;并施行礼乐之教,使长幼有序,老穷不遗,“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此即儒家的乡土之教。
中国人的亲土观念,不仅与儒家的乡土之教有道德上的联系,同时亦有“报本返始”的宗教上的联系。中国古人深信,人生时立足于土,死时亦归于土。“天、地、君、亲、师”五大崇拜对象中,“土地”(管理一小地面的神,即“社神”)由于它的亲切、善良、宽容、慈祥,使中国人感到与他最为亲切。中国人普遍有祭祀社神的仪式,其目的即为了报答家乡土地的哺育之恩。中国人无论离乡多远,生前深怀乡土之情,死后亦希望自己的躯体归葬于乡土。
中国文化重视乡土情谊的特征,体现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其具体表现有:
1.家谱、族谱与地方志的发达;
2.方言和会馆的盛行——汉语方言在中国人当中,特别是一些曾发生迁移的人群如闽粤、台湾和海外华侨中,具有特别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功能,在于维系乡土情谊,人们凭借这种地方性的乡土语言,互相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彼此作同乡人的亲切认同;
3.地方戏曲与田园文学的繁盛——在中国各地都有反映自己地方文化特色并深受本地人民欢迎的地方戏曲,在很长时间内,它是使儒家教化能直贯乡村底层的最有效手段;
4.乡土谚语与地方性学术流派的丰富——乡土情谊重在“乡土”,故中国古代学术流派亦多以地方命名,如“关学”、“洛学”、“浙东学派”、“泰州学派”等等。
以此对照台湾的“本土”族群(即福佬、客家等)的风俗民情及其“乡土文学”,可说若合符节。如,不仅台湾福佬族的主要祖籍地闽南一带重视修写家谱、族谱,同样的,移民到了台湾,普遍续修家谱、族谱,于是有了“唐山祖”和“开台祖”等名目。又如,台湾地区流行着闽南方言和客家方言,即使曾经遭受国民党当局的禁压,仍无法禁绝,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殊不知,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中国文化重视乡土情谊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又如,地方戏曲曾是台湾乡村民众节庆娱乐时的最爱。鲁迅的“乡土文学”曾写过“社戏”,而台湾的乡土文学中,有关演地方戏、野台戏的描写,更是俯拾皆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标准的乡土文学”,则表现出对土地的格外深厚的感情。此外,1970年代曾有对于日据时代“盐分地带文学”的挖掘,引起文坛的瞩目,说明台湾乡土文学中,同样产生了地方性的文学流派,并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由此可知,部分台湾省籍作家最引以自豪、将之当作旗帜聚集其下的“乡土文学”(或“本土文学”),并不像陈芳明所说的是“抗拒中华民族主义”的产物,相反,它是最具中华文化深厚意蕴的东西。应该说,无论是怀念故土的“乡愁文学”,或是标傍“扎根本土”的“乡土文学”都根源于中华文化的“重视乡土情谊”这一基本特征,但相较而言,“扎根本土”甚至比“怀乡”更切近中华文化之核心。不像属于“海洋文化”的西方人,其移民或殖民具有某种无限扩张性,中国人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离乡背井、迁移他乡。到了一个新地方,移民们荜路蓝缕,建立家园,当能够立足生存之后,他们就想安定下来,扎根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怀乡”仅产生于离乡背井或移民之初,它是暂时的、局部的、非常态的;而扎根乡土才是中华文化永久的、整体的、常态的倾向。这种不可移易的源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人“安土重迁”、热爱乡土秉性,在数百年来由闽粤一带移居台岛的台湾同胞身及其创作的“乡土文学”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因此,陈芳明所建构的文学史将“乡愁文学”归于“中华民族主义”,却将“乡土文学”与“中华民族主义”或中华文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违背学理,也违背历史事实的。
乡土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关联
“乡土文学”与“重视乡土情谊”的中华文化特质的深层、内在关联,使得台湾文学对于“乡土性”的追求,在一般情况下(即未受“台独”派刻意地扭曲、割裂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情况下),必然和对于“民族性”的追求粘结在一起。台湾文学发展的事实和我们这一学理上的判断有着惊人的一致。1970年前后兴起的乡土文学思潮,是在反拨被视为背离民族传统、“恶性西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背景下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其旗帜上即写着回归“乡土”、“现实”,同时也写着回归“民族”、“传统”。这并非偶然的巧合或某个人的杰作,它们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基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是二而一的东西。
以被视为“本土派”文学理论泰斗的叶石涛为例。1965年叶石涛所撰《台湾的乡土文学》及其后的一系列文章,某种意义上宣示了台湾乡土文学在60年代的再出发。当时的叶石涛反复强调“坚强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乡土色彩”乃是台湾省籍作家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叶石涛固然也颇为强调台湾文学有别于大陆文学的某种特殊性。然而,这种特殊性并未脱离中华民族文化之共同性,甚至有时这种“特殊性”就体现在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更为热烈的拥抱和坚持。如作为中华文化重视乡土情谊特征之载体的“乡土文学”,台湾比大陆声势就更为浩大。又如,台湾由于其遭受异族殖民统治的特殊历史际遇,反而对民族文化传统有一种特别的珍惜。叶石涛曾写道:“省籍作家的小说特别富于坚强的民族性,这可能是由沦陷50年的惨痛体验所致。在那恐惧的日子里,本省的土地和人民被割裂——和祖国大陆分开,在异族的蹂躏之中备尝亡国的痛苦。这一惨痛的记忆永远提醒省籍作家唯有保持民族风格,才能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心灵和处境。”如果说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的话,这无疑就是这种“特殊性”的重要之点。由此说亦可证明陈芳明割裂“乡土文学”与“中华民族主义”(确切的表述应是“中华民族文化”)之谬误。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
乡土性和民族性的深层内在关联,使得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本土化”,乃是针对“西方而言的“本土化””而非1980年后被扭曲成针对“中国”的“本土化”。因此当时文学思潮的弄潮儿们,大多秉持着“中华民族主义”,陈芳明本人就是如此。70年代初,他是新生代诗社“龙族”诗社的重要成员。1973年7月,他写了《“龙族”命名的缘起》一文,宣称自己“即是最初想起这个名字的人”,并回忆了当时的情况:那时大家已有一致的目标和理想,只缺少一个“可以代表我们个性”的名字,它必须“稳重、宽宏、长远,而且是中国的”。当时的提议很多,如云族、狮族、太阳、天狼星……等等,但大家都不满意,因“这些名字并不代表什么”。直到陈芳明和萧萧不约而同想起“龙族”这个名字时,大家才停止争论。陈芳明写道:
龙,意味着一个深远的传说,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崇敬的形象。想起龙,便想起这个民族,想起中国的光荣和屈辱,如果以它做为我们的名字,不也象征我们任重道远的使命吗?从此,龙族便正式诞生,像发亮的星球出现在夜里的窗口。
陈芳明这段富有文采的文字,表达的正是浓郁的“中华民族主义”情感。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主义”在台湾是一种历史、客观的事实,它就存在那里,存在于台湾民众的精神内里和日常生活中,存在于包括乡土文学在内的台湾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谁也没有办法抹杀和否认。正如叶石涛自己所说的:“既然台湾是来自大陆的汉族为主的移民社会,那么汉族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台湾人的血肉,舍弃了它,台湾的移民社会也就失去了核心的伦理道德。”由此也可知道,“中华民族主义”是“自发”、“自主”地存在于台湾广大民众中,绝非陈芳明和某些“独派”人士所谓的“出自官方强制性、胁迫性的片面灌输”。相反,倒是80年代后“独派”宣扬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和“抗拒中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才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刻意的灌输。而且,这也正是陈芳明建构其文学史,特别是抛出“战后再殖民论”的目的之所在。为了达此目的,陈芳明不惜触犯学术研究之大忌,偷换概念,罔顾和歪曲历史事实,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陈芳明采用上述手段,将“殖民”、“反共”、“戒严体制”、“军事控制式的权力支配”等罪名,加诸“中国”、“中国取向”、“中华民族主义”等的头上,其目的在于抹黑“中国”,丑化乃至恶魔化“中华民族主义”,煽动民众对于“中国”的敌对情绪,宣扬“脱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倾向,其危害不可低估,绝不能“听之任之,久而成患”(陈映真语)。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学理上对其谬误加以批驳,正本清源,澄清视听,也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