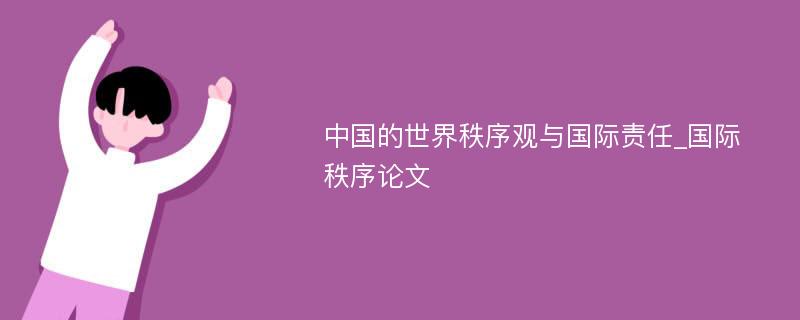
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与国际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秩序论文,理念论文,责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有认识中国特性的需求,希望中国发挥积极的大国作用。中国人也在审视自己的传统与特性,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与发展策略。为此,探讨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以及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就具有了时代的重要性。
一、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
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想法,现在还不是很明确,因为今天的中国本身处在一个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完成,中国在国际上的身份与地位还没有真正定型。
人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感兴趣,除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以外,还因为觉得中国可能跟别的大国不一样,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大国。但这个“特色”到底在什么地方,特别是这个特色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将怎么体现,会体现在何处,还不是十分清晰。关于中国未来的走向,如中国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国际秩序,随着实力的上升,中国如何将理想的国际秩序变为现实,人们还存在一定的困惑。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想知道中国的崛起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是带着“中国会与别的国家不一样”这样一种预设进入这个话题的。这里所说的中国的不一样,不是因为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造成的,而是一种内在的不一样。即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外部约束条件下,中国会做不同的事情,这时,人们才觉得有进行专门研究的价值。否则,人们不用专门研究中国,只要把研究重点放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上就行了。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还不长,加上中国处在转型的过程中,因此,对中国世界秩序理念的研究,可能还是要从历史中找线索,以发现一些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的因素。
关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对该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不过,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一些方面,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1.重视稳定和秩序,害怕乱世和混乱局面
对于稳定与秩序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张德胜认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的文化发展,线索虽多,但大体上是沿着“秩序”这条主脉而铺开,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个“秩序情结”。① 追求秩序和躲避动乱是中国一个突出的文化取向,这一点,已经深嵌于中国人的效用函数之中。
中国人历史上认为最好的政治是“国泰民安”,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按照《礼记·礼运》的描述,“大同”社会的特点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②
这一段不长的经典论述,体现出中国秩序观的许多深层内容。突出的一点是,在“大同”的理想社会中,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并不是很高,它追求的并不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不过是所有人“皆有所养”。也就是说,大家都能吃饱饭,安心过日子,就已经很好了。相反,在物质财富之外,它着力强调了社会秩序的方面,除了“男有分,女有归”之外,“盗窃乱贼而不作”也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指标:“外户而不闭”,即出外不用关家门。这在西方政治中很少被作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指标来对待。但在中国古代,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而明确的体现。史载,唐太宗贞观时期(627—649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旅野宿”,③ 这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中国政治对秩序的强调,同时反映了中国人(有时可以通过加总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中国政府的政治态度中)效用函数的一个特点,即对风险的规避。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中国人的效用函数是高度“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型的。虽然也许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型的,但中国人可能比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更不喜欢风险,有着更强的风险回避的倾向。④
在夜不闭户的说法背后体现的是一种高度安全感的实现。对夜不闭户的强调与追求,反映的是对这一高度安全状态的重视,以及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状态的回避。高度的风险厌恶,在大同社会这一理想社会模型构想中的反映,表现在它对于积极的物质追求方面说得不多,且目标定得很低,而对于“盗窃乱贼不作”,“外户而不闭”,这些对负面状况的规避方面的内容却给予相当程度的强调。
在《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世外桃源”,体现了很多中国人的向往。从实质上看,“桃花源”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其富足,而在于其没有战乱、生活平实、和谐有序,所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在于里面的人生活过得有多富,而在于其烦恼少。即使在今天,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突出标志物是“天安门”,“天”和“安”两个字放在一起,希望“世界和谐”、“天下平安”的倾向也表现得颇为明确。
有人说中国古代政治是“儒表法里”,表面上是儒家的一套,背后还有法家的一套。⑤ 这种说法有其现实基础。⑥ 但另一方面,儒家和法家在春秋战国时候的提出,都是针对两个时代问题:一个是如何使天下混乱的局面恢复秩序,一个是如何富国强兵。只是他们在何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手段的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我们现在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我们也可以说,恢复秩序和实现发展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而且,总体上秩序的重要性排在发展之前。
孔子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学说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在某些时期,他甚至被推崇到比君王更高的地位。⑦ 但孔子对富国强兵不太感兴趣,对于重建社会秩序则锲而不舍。他谈富强之道,总走不出治与乱的大框架,认为只要大家讲礼仪了,有秩序了,就自然国富民强了。这个观点推到极致,就是后来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也就是说,只要大家都尊老爱幼,推己及人,统一天下就像在手掌心里转东西那样容易。
有一次,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⑧ 在孔子看来,你只要在家行孝、与兄弟友爱,这实质上已经是在从政了,不一定非要当官、当政治家才是在从政。把这样的观点推广到今天的国际社会,就认为,只要每个国家都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实行科学发展观,不无理欺负别的国家,就已经是在从事国际政治活动了。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儒家的这套观点中不切实际的内容很多,但它却能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定于一尊”,在诸子百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在后来长时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有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家以建立秩序为终极关怀。⑨ 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理论的指向,与中国人的偏好有基本的契合。
在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它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理解事物、指导行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对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向产生一种路径依赖的效果。儒家思想的制度化、社会化所带来的客观效果,使稳定与秩序在中国人的偏好函数中处于一个非常高端的位置。
可以说,孔孟的这些想法,影响了非常大的一批人。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给皇帝上书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⑩ 在苏轼看来,如果我们强调道德建设,而不搞经济建设,虽然经济不发达,国家不强大,却可以长时间生存。如果不抓道德建设,狠抓经济和国防建设,虽然国家富有和强大,却会“短而亡”。显然,苏轼在这里提出了两种选择,一是“贫弱但长存”,二是“富强却短暂”,在这两者中,他明确地选择了前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是苏轼写给皇帝看的,体现的是他严肃认真的想法,反映的是他真实的偏好选择。
有意思的是,宋朝(包括北宋与南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实践了苏轼所说的“贫弱而长存”,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朝代之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鸦片战争后,面临深重的内忧外患,以及来自西方殖民体系的强劲挑战,还顽强地坚持了70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或许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直到今天,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的影响依然很明显,我们所说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从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孔子关于秩序与发展的关系的那套逻辑,只是中间添加了“改革”这样一个环节。
前几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天下体系”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批评,就是建立在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乱世这一条之上。赵汀阳认为,当今世界的最大政治难题是:一个整体上无序的世界,一个暴力主导的世界。而西方国际理论对此无能为力,所以要提出批判,(11) 这与孔子的想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而试图用一个理论框架重建世界秩序,也就成为赵版“天下体系”的终极关怀。
对秩序的追求和对混乱的回避,同样体现在“和谐世界”的提法中。从概念上说,“和谐”本身内在地是一种有序状态,它是一种大家相互保持宽容态度的、和平相处的秩序状态。这种秩序是与冲突、不稳定状态相对立的。
2.秩序的内涵及建立的手段和方式
如前所述,中国世界理念的第一个特征,是把建立秩序或确立有序状态置于效用函数中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并且在秩序与富强等其他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会优先选择秩序。在这之后,产生的后续问题,一是中国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二是用什么手段和方式建立这样的秩序。
儒家推崇的核心是秩序,但它推崇的不是任何秩序,而是认为等级秩序更为现实可行。同时,儒家赞赏的也不是任何等级秩序,而是一种特殊的等级秩序,即等级间和谐的秩序,是一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2) 的关系。在这样的秩序中,虽然客观上有等级的分别,但在“信”、“义”、“亲”等的作用下,能够实现关系的和谐,人们各安其位,形成一种和谐的“序”。
在这一秩序中,维护等级间关系的主要不是暴力(当然任何时候政治都必然要以一定的强制力为后盾),而是对社会规范的尊重。使社会规范发挥作用的方式,则是通过教化、社会化等方式,实现观念的内化,并辅之以一定的外部激励。对观念的高度重视,是这种秩序模式的一大特色。
在国际关系层面,朝贡体制是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等级秩序的典范,它是在中国总体上处于实力优势地位的背景下实行的制度,这个制度不是在外部压力下建立起来的,应该说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偏好和行为模式。(13)
朝贡体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它是一种松弛的等级秩序,它的等级性我们不用回避。(14) 这个等级秩序,在名义上的不平等比较明显,但实质上的不平等很少,综合起来看,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关系。具体地说,在名义上,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有分别的;但在实际利益的分配与交换中,则比较平等,甚至对周边国家常常有比较明显的倾斜,这推动了一些周边邻国参与朝贡体制的积极性。
朝贡体制并不以中国榨取其他国家的利益为特征。在政治上,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内部事务基本持一种不干涉的态度,周边国家不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安全上的威胁,反而常常觉得向中国朝贡有助于增强其在国内的合法性,有助于其政权的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实现。(15) 这方面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明确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他在《皇明祖训》中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16)
从总体上确立了一种以被动防御为主的周边战略,这一政策在明朝从总体上说比较好地得到了遵循。
在经济上,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厚往薄来”的政策,(17) 在这一政策下,朝贡国可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以至于他们往往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增加进贡的人员数量。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琉球使节要求进贡时增加接贡船一只,康熙帝同意了琉球方面的请求,从此琉球每次到清朝来的贸易贡船实数为三只,而且接贡船和贡船一样,每次到来时也带有大量贸易人员与货物。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琉球使节又以“海阔人少,往来不便”为由,要求免除接贡船的关税,并且将原定人数增加,康熙帝最后决定将琉球人数增加到二百人。(18) 相似的情况,在朝贡关系中屡见不鲜。
与此相对照,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虽在名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但实质上还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且在这种关系模式下,利益冲突很多、很频繁。(19)
(2)它是一种强制程度很低的地区秩序安排,中国只要周边国家表面上接受中国的领导,对其他方面不是太关心。
低强制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一秩序安排范围内的强制程度很低,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在朝贡体制下,中国对朝贡国总体上实行的是一种“怀柔”的政策,对属国的内政绝少干涉。即使是对于像朝鲜、琉球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在王位的继承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历来由它们自己作主,并不须看中国的眼色行事。中国对各邦国新君的“册封”,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其王位继承有实质上的决定权。如琉球国王尚穆,即位于1735年,直到1756年才受乾隆皇帝的册封。19世纪下半叶,当日本于明治维新后在朝鲜问题上野心初显,并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时,恭亲王奕忻等奏报与日使谈判经过时指出:“臣等查朝鲜虽隶属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2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清朝重臣的认识与看法。
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下,不存在中国在经济上对朝贡国进行殖民掠夺的企图,“厚往薄来”政策的目标是形成和平、稳定、有序的双边关系,维护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在一定意义上也实现“守在四夷”的防御思想。在具体的政策执行时,中国更多地使用“软性”的“柔化”政策,试图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因此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评论清方封爵时说:“琉球越在重洋,圣天子授之王即以示尊宠,亦政不欲遥制之尔。”(21)
这种低强制性,反映出中国在处理与朝贡国关系时,在外交目标上的定位和需求很低,并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完成。
朝贡秩序低强制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在,不把这种秩序安排强行向外做广泛的推广。这一秩序的扩展逻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通过提高自身吸引力的方式,而不是强制的方式,把他国纳入相应的国际秩序安排。孔子相信,只要本国坚持“道之以德”,就能引来他国的归属,实现“近者悦,远者来”,“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2) 二是基于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想法。(23) 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秩序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来去自由的。周边的一些国家,即使进入了这一体系,也可以再离开。这是一个对周边国家来说有着极大自由度的、弹性很强的秩序安排,它并不是一种凭借中国的实力优势,把这些国家强行聚合在一起的地区秩序安排。这一安排背后的利益考虑与行为逻辑,在班固的一段话中表述得十分清楚:
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24)
正是因为中国在这一秩序安排中追求的物质利益目标不高,主要在于形成一种稳定、有序的状态,因此,才会有中国对于部分外国献民献土行为的谢绝,这种情况,一直到清朝时期都存在。雍正五年(1727年),苏录遣使入贡,并请求内附,清帝没有答应。(25) 乾隆年间(1736—1795年),又发生了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的事情,乾隆帝也加以拒绝。乾隆皇帝认为,哈萨克的行为虽然出于其自愿,但中国与周边打交道的目的不过是“羁縻服属”、“俾通声教而已”,并不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因此加以拒绝。(26)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乾隆称“若哈萨克、若布鲁特,俾为外国而羁縻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27) 对外邦内附请求的拒绝,以及乾隆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体现了中国目标的有限性以及对外行为中高度的自我克制。
中国在朝贡体系中体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与近代以来,欧洲席卷世界,把整个世界强行纳入其体系,包括以炮舰打开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国门的做法大相径庭,也与今天某些西方国家试图在全世界强行推广其制度形式和价值观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3)它也是一种制度化水平比较低的秩序安排。在朝贡秩序中,除了有很详细的礼仪、仪式方面的规定,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具体的机制、组织并不多。不像现在的国际体系,组织、机构、机制、章程、规范、条约非常多、非常复杂。朝贡体制与现在的类似商业契约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条约体制在性质上存在着很大差异。
从表现上看,在这个体系下,东亚地区的战争比欧洲少得多。总体上说,在古代国际关系体系下,东亚国家的生存更有保障。套用建构主义者的说法,“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国际体系的洛克文化,(28) 在亚洲可能更早就实际存在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处于实力优势地位的东亚地区的传统秩序,是一种息事宁人、大家之间相安无事就好的秩序,也是一种比较现实的秩序安排;是一种以中国的硬实力为基础,但与今天相比更多地强调软实力的地区秩序安排。(29) 在这一秩序安排下,优先强调的,是每个国家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儒家特别强调修身,所谓“为政以德”(30),“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31)。在国际关系的意义上,国家的“修身”,就是各自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这是形成更高层面的有序状态的重要基础。
二、中国的国际责任
中国关于世界秩序、国际社会的观念,对中国的国际责任观会产生内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履行自身的国际责任、做负责任大国,就是儒家所说的“修身”在国际层面的一种实现。但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有了更大的复杂性,并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不同类型的责任问题
要有效地分析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态度,首先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责任,即作为道德规范的国际责任,和作为大国政治工具的国际责任。
对于国际责任问题,当然可以而且也需要从法律、道义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应该说,这是国际责任的本义之所在。20世纪初,奥本海(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heim)等国际法学者把国际责任界定为国家对国际社会的不法行为而担负的义务:“在国际法上,国家对于它的违反它的国际义务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是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的地位所附加的。……不遵守一项国际义务即构成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32)
此外,人们也可以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寻找国际责任的依据。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从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角度出发,认为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就是因为它们承担了其负有的特殊国际责任,他认为大国有义务去促进国际平等、维护秩序和维持均势等等。(33) 在他看来,仅有硬实力的强大,如纳粹德国或拿破仑法国那样,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负有特殊的责任,是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相称的。布尔特别强调了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所有国家都认为秩序最终是优先于正义的”,因此,大国“必须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秩序的行为”。(34)
上述两种意义上的责任,对中国来说都很容易理解和认同。但在把负责任概念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相联系的时候,还有一种另外的用法,即把“负责任”作为一个起着政治工具作用的话语来使用,使其成为对中国施压的手段,这种用法显然背离了负责任含义的初衷与责任概念的道德分析和法理分析。
近几年来,探讨“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或“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时,人们往往难以回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纽约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佐利克提出中国应负起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强调中国在外交上面临着很多“机会”,可以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如在朝鲜核问题,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伊朗核项目问题,以及与美国合作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中国都可以有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空间。为此,他觉得需要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35)
从其内容看,佐利克似乎是把美国给中国分派的一些任务,用中国所应该履行的“国际责任”的话语给重新包装了一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哈佛大学的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则远为坦率得多。他指出,“在美国政策界,当人们称这个或那个国家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时,他们通常是指这个国家是亲美国的,或者说这个国家很少与美国发生分歧,并能通过国际机构来解决这些分歧”。并且,美国对“负责任”一词的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它通常是指一个国家遵守所谓的“游戏规则”,但另一方面,“美国政策界很少有人尝试给什么是‘游戏规则’下定义”。(36)
显然,“负责任”在界定上的这种模糊性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它使美国在评判他国行为时拥有高度的自由解释的空间,从而可以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问题领域上更好地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具体到中美关系中,这也显著地增大了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难度。一方面美国认为“负责任”标准的制定权在其手中,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并且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只要陷入美国的逻辑,就注定难以取得好的结果。(37)
两种不同责任——即作为道德规范的国际责任和作为大国政治工具的国际责任——同时存在,而且其背后的逻辑和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存在根本不同,(38) 这为一些国家把国际责任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提供了某种方便。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两种责任往往混为一谈。用博弈论的说法,就是形成了混同均衡。在实践中,常常发生的情形是,对方表面上说你要从道义上负起责任,但一谈到责任的具体内容,却处处涉及的是国家利益考虑。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说十分不利。
当准备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时候,中国需要对这两种责任做明确的区分,表明是要在第一个意义上负责任,而不是在第二个意义上负责任。这种区分的一个困难在于,即使中国努力把这两者分开,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会努力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为混为一谈是它们的利益之所在。它们要混同,中国要分离,这两种努力都有其合理性。在一些西方国家试图混同的情况下,中国更应该努力去分离二者。分离的一个作用在于,可以使中国更好地看清在国际责任问题上存在着的双重标准,或者至少是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标准。
(二)负责任的标准问题
负责任的标准,并不是可以完全孤立地脱离环境背景来谈论的。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负责任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可能会有重要的不同。
《庄子·胠箧》中有一段对话: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盗跖的回答,论述了盗贼的行为规范,实际上也是确立了他眼中盗贼的“负责任”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39) 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为了权力与生存而斗争,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国际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带有一些“弱肉强食”的特征。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战争与冲突不断,每个稍微大一点的国家都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军备。当前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虽然在经济上面临如此多的困难,其军费开支却仍然保持在超过6000亿美元这一高得惊人的水平,而且这一开支甚至还在继续增长。2010年12月17日,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2011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包括战争拨款在内,美国国防预算总额将进一步达到7250亿美元。(40) 这些事实可以反映关于美国偏好的很多真实内容。
因此,当中国要负责任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标准是什么,是由谁定的?在这样的标准下,中国负责任的做法,是不是“费力不讨好”,甚至是费尽全力也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
在负责任问题上,美国有美国的标准,欧洲有欧洲的标准,非洲有非洲的标准,中东国家有中东国家的标准,周边国家有周边国家的标准,这些标准相互之间都不一样,甚至其中的某些内容相互冲突。如果我们试图令所有国家感到满意,或者即使是令其中的某一方感到高度满意,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在国际责任成为大国政治博弈工具的背景下,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做了多少,美国或者西方国家都可以说你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们的利益在于这么说。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说法,是一种对其有利的行为策略。
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不是负责任大国,这个标准不能由其他国家来定,而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例如,胡键认为,“西方大国是根据其国家利益来确定中国国际责任的”,为此,他提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不应该由西方大国来认定,而只能是中国根据自身能力和国家利益来确定”。在他看来,“国家利益是确定中国国际责任的根本依据”。(41)
这种说法的基本动机可以理解。显然,由西方国家掌握确定一国是否“负责任”的标准,这没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负责任的标准,一般来说也不是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是不是负责任者,这确实不是自己说是就行。而且,我们所说的做“负责任大国”,是要做一个被别人承认的“负责任大国”,而不是要做一个自说自话的“负责任大国”。即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别人承认自己是负责任的,因此,这个标准不能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另外,也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利益作为判定是否负国际责任的依据。一般来说,负国际责任,总要在利益上有所损失。又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又要尽国际责任,这两个目标很难完全相容。由自己确定负责任大国标准的提法,只能看作是在标准任由别人制定的情况下,中国人的一种无奈的诉求。
关于国际责任,也许确实可以产生一个客观标准,但现在也确实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可操作的标准(特别是,美国并不希望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谁的嗓门大就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但中国的嗓门显然是不大,这就给中国造成了一个“责任陷阱”,并出现了一个两难的局面,进入这个陷阱,或者不进这个陷阱,都有一定的代价,并不容易选择。所以,有人说“中国责任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中国威胁论”可以置之不理或者针锋相对,“中国责任论”则由不得中国不回应,否则可能会落得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结果。(42)
(三)国际责任的成本收益问题
任何一项国际行为,都有成本收益的问题。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现代化的问题尚未获得完全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做一个利他的行为体显然并不现实。在自身能力有限,发展的环境还很复杂,面临着很多外部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于做负责任大国做一个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成为很有必要的事情。
国际责任的成本收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成本与国际环境高度相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形成以下一些基本的认识:
第一,与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相比,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负责任,其成本要高很多,有时要高很多倍。这里的国际环境,既可以指国际大环境,也可以指一国面临的小环境。如果一个国家在一战前或者二战前的欧洲,说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冷战时期,要做负责任大国,显然也很难。
第二,朋友多时,与朋友少时,负责任的成本不同。
第三,别人信任你时,与别人不信任你时,负责任的成本也有很大的差别。别人对你的先入为主的印象,也是你负责任时必须面对的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在有国际话语权和没有国际话语权的情况下,负责任的成本有很大不同。要想以比较小的成本,让人形成你是负责任大国的印象,这要以强大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为前提。如果国际话语权不足,即使做非常多的工作,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也可能不被认可为负责任国家。
第五,有领土、领海争端等国家间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时,与没有这方面的争端时,成本差异很大。负责任有时容易被别人理解为你会在谈判中做一些让步,会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较高程度的克制,从而会对利益分配的方式产生影响。
第六,当一国准备对国际社会负责任时,还要看有多少其他国家准备这样做。如果大家都负责任,那么它做负责任国家的成本就会低很多;如果大家都不准备负责任,那么它做负责任国家的成本就会变得很高,其处境与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笨蛋”(suckers)相似。(43) 其结果是,付出很高的成本,得不到好的结果,所得到的甚至可能是最差的结果。
除上述一些方面以外,中国面临的一个麻烦是,做负责任大国这个问题,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天然难以处理的关系混合在一起。客观地说,崛起国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它面对的环境往往是不利的。如果霸主国要做负责任大国,就相对容易。在做负责任大国的成本与一国的实力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当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负责任的成本可能下降,收益却会上升;而在此之前,成本往往很大,收益可能很小。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转折曲线,做负责任大国,也就相应地存在着一个时机问题。
我们试图以“负责任大国”的提法来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试图化解霸权国对崛起国施加的压力,这可能不太可行,因为其代价太大。做“负责任大国”和化解崛起压力,这两者并不在一个平行的逻辑机制上起作用。对霸权国来说,即使你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任国家,但你要挑战它的霸主地位,这也是它无法接受、不能答应的。
中国在负责任问题上,面临的是战略上相对孤立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本身增大了负责任的成本。如果试图通过负责任的方式来打破战略孤立,其成本会变得极高。相对可行的是,试图通过“负责任大国”的提法,及一些配套的做法,来表达自己善良的愿望,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疑虑,减小对外关系中的一些阻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提法或许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其作用总体上是有限的、辅助性的。如果这种提法,被国际社会中的很多国家同时拿来做机会主义的利用,则很可能产生实际上的负面效果,这是要加以注意和警惕的地方。
此外,要考虑未来的战略空间,不要为了在目前改善国际形象,而堵死了未来的战略空间。讲过的做负责任大国的话,可能会被别人拿来,在特定的时候将你一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中国不负责任,这会造成我们工作上的被动。所以,在负责任的问题上,中国不如模糊一点,不要做明确的承诺;不如少说一点,多做一点,至少以后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说得多而做得少,会不必要地提高国际社会的期望值,却无法加以满足,反而会起到负面的效果。
三、结语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具有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即使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影响下的东亚秩序安排,也在历史上实际运作了很长的时期,这显然是中国的理念与当时国际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不再居于历史上那样一种优越的实力地位,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也显著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必然会更加务实。但来自于传统的影响也并不会简单地消失,而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过去国际社会与国际秩序的理念中,有一个把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过程。
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念相似,在中国的国际责任观中,也体现出了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负责任大国”这一陈述,表达了中国自身目标的有限性,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一个自我克制的、乐于合作的行为体,表明中国在意图上不准备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并存在着愿意维护国际与地区稳定的政策动机。第二,对他国做比较善意的想象。这种善意想象是中国宣示“负责任大国”主张的一个重要逻辑基础。同时,还抱有一种“善有善报”的期望,希望开启一个良性循环的通道和进程,通过这种方式,使世界变得更为和谐,更为美好,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4)。单方面宣示要做负责任大国的做法,显然与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所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策略有很大不同,其背后也承载着不同的期望与理念。第三,对于这种善良愿望被国际社会中的一些行为体拿来做机会主义运用的可能性,中国似乎没有进行足够充分的评估,暂时似乎也没有充分有效的应对方法。
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从大时间尺度的视野来看,中国历史上长期在其所处的国际体系中享有实力优势地位,在对外交往中具有较强的安全感,加上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在相应的范围内承担起国际责任,而对于承担国际责任的代价则体会并不深刻。此外,中国对于履行国际责任的内涵的理解,与当前居于国际社会主流的很多西方国家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要放在中西交汇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中国在负责任大国问题上,不可能完全采用西方的标准,而且西方也没有明确的标准。从根本上说,中国要做的是一个符合自身期望的负责任大国,是一个首先要让中国人自己满意的负责任大国。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相应地调整其期望值,以实现双方关系的更好调适,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注释:
① 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② 《礼记·礼运》。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④ 20世纪90年代初期,江泽民同志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16字方针,虽然有当时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具体政策考虑,但“减少麻烦”、“不搞对抗”显然也符合中国人一脉相承的“风险规避”型的政策考虑。在大国关系的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这样的方针。
⑤ 如赵鼎新认为,汉武帝治国施政之术的核心在于“尚法尊儒”,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将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上则将法家学说作为统治权术来运用。参考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1页。
⑥ 即使在独尊儒术之后,汉宣帝也曾对其太子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显然,在具体实现秩序的政治现实中,儒家和法家各有其存在之处和有用之所,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此后儒家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作用的上升趋势。“霸王道杂之”的说法,见《汉书·元帝纪》。
⑦ 参见冯友兰的观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⑧ 《论语·为政第二》。
⑨ 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⑩ 《苏东坡集》卷五一《上皇帝书》。
(11)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2) 《孟子·滕文公上》。
(13) 古代中国的偏好是否能够传递到今天,或者其中的什么内容能够传递到今天,什么内容发生了变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还很难形成明确的结论。
(14)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这种模式扩展到国际社会,自然会带来一定意义上的不平等,正如孟子所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一种正常情况。即使如此,费孝通先生同时也指出,“在西洋现代社会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15)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这么简单直截,在一些时候,朝贡关系的内容会变得很复杂,这也是正常的情况。
(16) 朱元璋:《皇明祖训·首章》。
(17) “厚往薄来”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朝贡国的贡物,增加对他们的回赐;二是对朝贡国实行优惠的贸易政策。
(18) 柳岳武:《传统与变迁:康雍乾之清廷与藩部属国关系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26页。
(19) 对这两种不同体系模式的比较,另可参考Davad 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1.27,No.4 (Spring 2003),pp.57—85; David Kang,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David 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2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第1页。参考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1) 周煌:《琉球国志略》,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卷九,第195页。
(22)(30) 《论语·为政》。
(23) 苏轼在《王者不治夷狄论》中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
(24)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
(25)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2页。
(26)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五四三,“二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27) 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另参考柳岳武:《传统与变迁:康雍乾之清廷与藩部属国关系研究》,第79页。
(28)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9) 当然,完全排除硬实力的作用,在任何国际秩序安排中都是不切实际的。
(31) 《大学》。
(32) 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
(33)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83页。
(34) 同(33),第183页。
(35) 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2005,http://www.ncuscr.org/files/2005Gala_RobertZoellick_Whither_China l.pdf.
(36) 以上内容来自陈舟对江忆恩的访谈,见陈舟:《美国的安全战略与东亚——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访谈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37) 使情况更加复杂化的是,当我们提中国要做负责任大国的时候,除了道义方面的考虑之外,可能确实有减轻战略压力、改善国际形象、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等方面的考虑。中国的这种需求和期望,正好可以被一些西方国家加以利用。
(38) 从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样一句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要争论不休,就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同的责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9) 当然,无政府状态不等于无序状态。
(40) 参见新华网,“美国众议院通过2011财年国防预算案”,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18/c_12892987.htm.
(41) 胡键:“‘中国责任’与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
(42) 袁鹏:“中美关系:新变化与新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5期。
(43) 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笨蛋”的策略是,当对方背叛时,自己采取合作的态度,由此得到的收益是最低的。关于囚徒困境博弈的分析,可以参考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44) 《论语·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