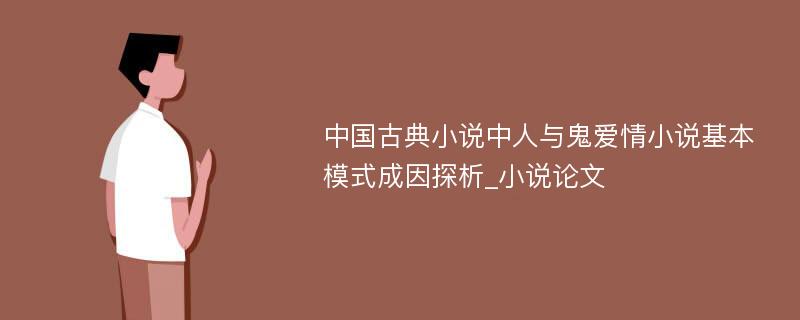
文言小说人鬼恋故事基本模式的成因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论文,成因论文,说人论文,模式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2-0055-06
一、传统阴阳观及阳精崇拜
中国古代描写人鬼相通的文言小说中,“男人+女鬼”成为一种基本的人物结构关系模式。其中的“男人”形象不少是处于离家孤独状态中的书生行商,而“女鬼”形象则往往是生前充满着哀怨愤恨之情的大家闺秀。以往的研究中较为注重分析造成女鬼哀怨的社会家庭原因①,而对形成这一人鬼相通模式深层次的性别差异心理及其观念来源则关注不够。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性别差异心理与传统的阴阳观念密切相关。在古老的《周易》中,男为阳,占据乾卦;女为阴,占据坤卦。以生命活力来看,人为阳,鬼为阴,男人乃阳中之阳,女鬼即为阴中之阴。这种传统的“阴阳”观念在文言小说中往往导致人物关系方面的“阴阳调和”的描写,也就是书生类的纯阳男人与至阴女鬼的交接配对。但是与原始的阴阳观念相比,后出的道教阳精崇拜观念对文言小说中此类描写的影响则更为隐性。比如在道教的理论中强调男性的阳精是生命力的源泉,许多道教养生家在强调“欲不可绝”的同时,也竭力提倡节欲保精,认为无节制的性生活会耗费人体内的元精(即肾精,体现在男子身上即为阳精),从而损人寿命。《黄庭内景经》言:“结晶育胞化生身,留胎止精可长生。”②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中则说“道以精为宝,施人则生人,留之则生身。”③ 吴筠《元气论》中称人之生是“受元一之气,为液为精”。因为在道教看来,“阳精”是人类生命演化生成的重要元素,至阳之精更是具有强力的“生人”效果,是人(包括女子)的生命力的源头。在这种传统“阴阳”观念的笼罩下,文人笔下自然就有了阳精崇拜的痕迹,这直接影响到了女鬼形象的塑造,她们往往有着还魂返生的强烈愿望,而惟一途径就是大量攫取男子的阳精。比如《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中写还魂术,其中就有“陶出阴阳”,言“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尔”云云。
人鬼相通小说受到阳精崇拜意识的影响,这种崇拜意识也成为此类小说中女鬼角色定位的重要原因。出于人类求生本能的反应,在相当数量的小说中,女鬼即使具有相当大的超自然神通力,她们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要复活,重返人间家庭生活。而女鬼复活的途径需要“与生人久处”,也就是需要不断地与男性交媾,得到蕴含着生命活力的阳精滋养,进而获取强大的生命力。早在《搜神后记》中就有《李仲文女》,可以说是一则反映这种阳精崇拜观念的典型故事: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而昼见,衣服熏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
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
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夫妇情至,谓偕老,而无状忘履,以致觉露,不复得生。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④
类似情节在唐宋文言小说中还有《谈生》、《毕令女》等故事⑤。在这些离奇的故事中,尽管女鬼的复生行为最终都失败了,但她们通过努力都已开始体生血肉,这正是由于得到了男人阳精生命之力滋养的缘故。当然也有极少数复活成功例子,如《徐玄方女》⑥。在大部分此类故事中,女鬼都是因为受到外力阻碍而中止了复活的进程,导致最终重返人间愿望的破灭。随着唐宋之后文言小说创作的不断发展,文人对阳精的崇拜出现了强化的倾向,并因崇拜而出现自我珍惜甚至吝啬的心态,比如很多文言小说的描写中都认为男子过量射精是对身体极大的损害。在明清文言鬼怪小说中,常见的情节就是女鬼与书生交合,最终使得该书生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甚至丧生。比如清中叶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鬼妇话别》中就有“阴剥阳”的说法⑦,阴质的女鬼与男人交合,即使并非出于恶意,最终也会危害到男子的身体健康。更有一些故事记载女鬼就是借与生人交合之机大量吸纳对方的阳精,这类描写就带上了令人恐怖的色彩。如《夷坚志·佛寺画像》记载一书生习业僧寺,被寺内附身于一幅人像上的殡宫女子之鬼魂引诱致死。家人寻至僧寺,发现了这副画像,“其像以竹为轴,剖之,精满其中”⑧。唐宋以后文言小说中的女鬼们,已经不再是楚楚可怜地祈求男人的帮助,而是往往会采取主动诱惑、积极攫取的姿态,这类女鬼形象在明清文言小说尤其是《聊斋志异》中有着生动丰富的表现,女鬼形象的这一变化在文化观念的转变方面来看是意味深长的。
总的来说,古代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者与接受者们都相信能够使女鬼们重获生命的惟一途径是摄入阳精,因而都认为男子的阳精具有创造生命的力量。基于这种源自古老的阴阳观以及后来道教阴阳修炼术深刻影响,能提供出至阳之精的男子在小说的描写中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是女鬼重返阳间的惟一指望。因此此类文言小说中描写的人间角色就必须是男子,尤其是年轻气盛的纯阳男子。而在故事的推演过程中,此类纯阳男子就会面对女鬼的复活乞求,并经受来自女鬼的各种色利诱惑和道德考验。
二、夹缝中的文人矛盾心态
文言小说中“男人+女鬼”的基本模式得以确立,还与历代文人自身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包括作者人生体验在小说角色中的自我投射,以及文人在传统观念影响下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
历代文言小说的作者几乎全是男性。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说,多数男性作者在讲述这类神怪故事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主人公身上,有意无意中选择接近自己立场地位的角色类型作为故事主角。因而中国文言小说“人鬼恋”故事中的男主角多数如作者一样是在科举途中跋涉的书生,或是碌碌无为的中下层官吏。
在人鬼相通小说中,阳间男人的地位明显高于阴间女鬼。显然人都会有贵生恶死的本能,虽然此类故事中的女鬼们大多美若天仙,有时候还具有很大的神力,但她们毕竟已经丧失了生命活力,只能在阴间存在。如果她们安心于自己的存在方式,那倒也罢了,可是她们偏偏不甘心于阴间存在,而是盼望着能够重返人世间。她们是阴间的身,却有着一颗阳间的心。她们明白,重新获得“生命”才是最根本和最珍贵的,美貌与神力等因素相比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而小说作者则会本能地抗拒让作为自己化身的男性主人公跌落到鬼质的地位,因为鬼作为需要被拯救或者被消灭的对象,跟活人原本就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在具体的小说描写中,女鬼总会对活人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女鬼是比活人低等的异类。世俗的男子虽然需要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需要得到女鬼的帮助,但却有着女鬼极度渴求但又永远难以回复的“生命”。
儒家“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等传统观念与中下层文人窘迫的生存状态相冲突,同样也是儒生们产生对“女鬼”需求的重要原因。传统儒家提倡儒生们凡事以符合仁义礼教为重,求取真道,忠君爱国,对荣华富贵则要看淡。追逐金钱财富历来被视作商贾末流所为之事,清高的文人们大多标榜不屑。但精神世界之外的寒窗之苦,物质生活清贫的现实,又使得那些寒儒们感到精神的迷惑孤独。于是在书房旅舍的寒窗枯灯下,书生们往往会陷入迷茫幻想,而“女鬼”这个特殊的意象此时便会应运而生。汉魏六朝时期人鬼相通小说《谈生》,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故事: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以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发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其儿以为郎中。⑨
故事中的穷书生贫寒交迫,乃至中年无妻,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孤独寂寞、一无所有者。然而,年少貌美又出身王族的女鬼竟然会翩然而至,不但主动与他成为夫妻,为他生下儿子,临别又馈赠宝物让他脱离贫困,最终还使他一跃成为王族认可的富贵女婿。这个故事传达的是当时生活潦倒的庶族儒生们一场精神自慰的白日梦。当时的贵族高门为了维持血统纯正与权利的延续,严禁与庶族通婚,否则便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寒士们很难与贵族之女交往,更难凭借婚姻关系而一朝发迹、改变社会身份,登上富贵高位。然而当那些贵族小姐成为鬼魂之后,便成了不再受世间礼俗的约束、来去自如的自由身。这样一来,贫士们也就有了与她们往来交欢的想象机会。再发挥一下浪漫想象,凭借着这层关系而得到贵族在仕途上的认可与照顾,也就更是锦上添花的好事成双了。庶族贫士们内心有着期盼升入富贵阶层的强烈要求,他们渴求财富但又要维护清高的人格形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获得巨大的财富,但又对个人安贫守道于心不甘。于是,多情而又多财的女鬼往往就成为贫士们的最佳幻想对象。
儒家传统观念中对性的暧昧态度也影响到了“女鬼”的身份定位。性的需要是人类的本能,但是长期以来,儒家文化观念中一直将“性”看成是耻于公开谈论之事,如果不是为了繁衍家族后代,单纯追逐性爱快感便被认为是道德堕落。在礼教的束缚下,社会地位低下的书生往往处在对女色极度渴望但又可望而不可即的尴尬处境中。他们需要发泄的通道,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启齿,于是就将自身的欲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女鬼身上。从人鬼相通小说诞生开始,由于书生文人本身的审美需要,女鬼们的外貌大多被描绘成天仙绝色。女鬼的社会身份也随着时代女性审美侧重点的转移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从六朝时的高门贵族之女变为唐宋时期的世俗妇女,再到明清时期成为市井中的歌女舞娘。明代中期以后小说中的女鬼,往往在容貌出色之外还显示出高雅的文学艺术修养,主动自荐枕席,与男子发生密切关系。这样的描写体现了在繁荣的市井社会中,道德伦理风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文人们敢于把为了快乐而追求性爱的要求公然表达出来。当然在现实社会中,过于直露的描绘容易招惹麻烦,于是文人便把艳遇交合的想象力投射到阴间的女子身上。那些富有才情又纵情冶艳的美貌女鬼,主动与书生沟通交往,如此主动而又自由的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确实是很难找到的。而书生与女鬼的交往,可以夜来朝去、来去自由,不必承担家庭道德责任,消弭了来自社会舆论压力和协调家庭关系的无数麻烦,这样的美事自然成了文人在文言小说中最为津津乐道的性幻想对象,而敢于与男子调笑偷情女子的鬼质身份也就自然被定型了。
三、美色与美德的对立
人鬼相通小说中描写的女鬼形象往往有着美丽容貌和仪态万方的身姿,而现实社会中的美德贤惠女子则大多姿色平常。文言小说创作中显然是把女鬼的美色放在第一,而对女鬼美德的描写则是隐性的,甚至是被忽略的。这种把美色与美德对立起来的观念,还有明清时期文言短篇小说中普遍存在着重色轻德的描写倾向,都是值得注意的。
中国传统观念中有着“女色祸水”的说法,即认为美丽的女子很可能会自恃美貌而骄横缺德,给家庭和朝廷带来灾难与不幸。汉代刘向曾在《列女传》中将理想女子的美德归结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而与这六种美德对立的则是“孽嬖”,即倚仗美貌而求荣不贤的女子。史书上记载的或淫或妒的反面女子角色不少都有着美艳姿色,美貌是女子生存竞争的最大资本,同时也成为对男子的最致命的诱惑。从历代描写人鬼相通的文言小说看,女鬼们大都具有极其美丽的外表,但大部分故事都是同一个叙事模式——男子与不明身份的美女缠绵之后,却发现原来“美女”的真身是一具骷髅。男子因此大受惊吓,有人当场吓死,有人大病一场,有人从此疯癫。《太平广记》有《郑奇》一事: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宿止多死亡,或亡发失精。郡侍奉掾宜禄郑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吏卒白楼不可上。奇曰:“我不恶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接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死妇,大惊,走白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⑩
故事中的美妇人实际上是一具行尸女鬼,郑奇与之接宿,隔日便腹痛身亡。《幽明录》中也记载了类似的事情:“钟繇忽不复朝会”,行止异常,寮友问得其与“美丽非凡间物”的美艳女子来往,便断定其“必是鬼物”,后果然发现其为大冢中的女尸(11)。洪迈《夷坚志》的《刘子昂》一则中,贪恋“好妇”美色的刘子昂最终在道士掘地三尺后见到了“好妇”的真身:“但巨尸偃然于地,略无棺衾之属,僵而不损”,审视之后果然“盖所偶妇人也”,刘“大恶之,不旬日而卒”(12)。后来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画皮》故事,情节大抵相同,这些作品中透露出将美女视为淫邪丑恶亡国坏家之罪薮的观念。似乎不少文言小说的作者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女性一旦美丽妖艳,就必然诱惑男人,如果不注意修养道德,就很容易成为邪恶的象征,其结果必定是要害人害家,甚至祸国殃民。美丽的女性和丑陋的鬼物,在传统观念看来都有着“作恶为害”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两者在文言小说作者的笔下很容易就发生形象重叠而相互关联起来。
汉代佛教传入中土,对中国传统的妇女观也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中国佛教中的女性观,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改造了印度佛教最初的女性观念。早期印度佛教虽然也有轻视女性的倾向,但还没有达到公然排斥和鄙视的程度。早期佛教经典中虽然否认女性佛的存在,但还是承认妇女经过修炼可以获得正觉。大乘佛教尽管同样否定女性成佛的可能,但它又主张诸法本净,众生本净,心性本净。且佛性与生俱有,理论上说一切修持者只要认真修习皆可成佛,所以也不排斥女性获得正觉的可能。与印度佛教不同,中土佛教各派教义中大多将女性与佛性直接对立起来。如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佛经、汉代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中有这样一段:“乞求取足,是中一食,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欲也……天神献玉女于佛,欲坏佛意。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去!吾不用。”(13) 这段经文原意是告诉修持者须在人生各种享受方面注意节制自己的欲望,所谓爱与欲指的是世人对物质享受的追逐。但汉语翻译成“献玉女坏佛意”,就含有女色会败坏佛性修炼的意思。后人往往引用这段话来强调女色与佛性的天然对立,从而加强了对女性的普遍误解和指责。可以说,这样的误解正是中国传统的“红颜祸水论”对佛经经义的改造和渗透。在这种观念的长期笼罩下,文言小说中的“女鬼”形象往往就带有负面的色彩。她们表面上看是美艳动人、楚楚可怜的,而实际上则是令人恐怖的鬼怪。如清代《夜雨秋灯录》中的《东邻墓》一则,男主角儒生解必昌,因为修整了临近的古墓而得到亡妓女鬼的感激。这位美貌的女鬼不但以身相许,还教解生如何结交大盗,买官媚上,之后又出于妒意让大盗遭到官军的捕杀。虽然小说中并未有一字谴责这个女鬼,但从结局东邻之墓被身怀异能的大盗招雷劈毁,也不难看出作者对女鬼害怕和厌恶的心态。而对男主人公解生,作者则竭力赞他的“仁厚”:“妓与盗,冤冤相报,可谓酷矣。而于解君,则报之以殷恳,惟恐后焉者,何哉?无他,为其能有情耳。”(14) 故事中的种种丑恶之事,皆出于女鬼的教唆,与解生自己毫无干系。女鬼多洛霞这个美貌的女性在作者笔下成为了社会道德之“恶”的化身。
但是同样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把女鬼写成要害人伤命的凶恶之物。相当多的女鬼对生人恰恰是有益无害的,比如生子避祸,辅翼晋身,天赐横财,这些行为都是女鬼对男人很重要的帮助。并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女鬼出身官宦高门,比如《崔少府墓》中的崔氏女乃是高门之女(15),《紫玉》中的紫玉乃是吴王小女,皆情真而又热烈(16)。可见美丽多情、知书达理、温柔体贴是不少女鬼共有的特点。为什么在惧怕女鬼的文化背景下,又会有这些近乎歌颂女鬼的因素存在呢?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前文所提到的男性自身审美与需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由于道教妇女观的存在,多少中和了一些儒、佛两家对女性的诋毁。道教崇尚贵柔守常,推崇女性阴柔的特质,以不争和柔顺为处世原则,又从“阴阳平衡”的角度主张某种程度上的男女平等。与中土佛教强调女性不能成佛相比,道教认为男女都可成仙,且任何阶层的女性都可以修炼成仙。当魏晋道教逐渐发展后,又提出了男女同道便可一同飞升的观念,并且魏晋时期的女仙数量也与男仙不相上下。从女仙和女性在道教中的地位来看,确实有着与男性平等的迹象。道教的“尊重女性”主要是建立在修道基础上,道教感兴趣的是强调男女阴阳的缺一不可,在修炼活动中承认男女是互为伙伴的关系。道教愿意尊重女性是因为在贵柔守雌的思想作用下,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仙。所谓男女双修中的地位平等,并不意味着男女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是强调作为修道合作伙伴的同等地位,双方的性别身份已经被忽视,仅仅是将对方视作修炼的“工具”。至于更加等而下之的阴阳采战术,其主动施行者绝对是男子,女性更是被物化成“炉鼎”之类的修炼器具,事实上完全成为男子宣淫的发泄物。由于道教妇女观实际上是物化女性,所以女性并不能在这种过程中真正得到“人”的地位与尊严,而实际上会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从众多的人鬼相通小说中可以看到,无论女鬼生前是出身高门贵族的官宦之女还是小家碧玉,抑或是风情迷人的风尘女子,不管是吴王之女紫玉,还是《秦女卖枕记》中的王女,这些为寒士打通了晋身之路的女鬼,最终总是沉沦幽冥。即便已经为男主人公留下子嗣的女鬼,也没有资格和可能随着她们的孩子一起回到阳间。在这种为了男子的晋身和家族繁衍的故事中,一开始就将女鬼们放在了家族繁衍工具的位置。即使在那些出于主人公自身情感或欲望需要而形成的人鬼相恋故事中,也往往不是将女鬼复活视为恋情的最终归宿。当然,还是不能否认有真正情深如海的人鬼恋存在,也有的男子一往情深地爱着女鬼。如《绿衣人传》中,赵源与绿衣女子虽无前生渊源,但今世人鬼情深。绿衣女魂散之后,赵源“感其情,不复再娶,投灵隐寺出家为僧,终其身云”(17)。赵源不以人死情断,终身不娶,两人虽不得白头偕老,亦可谓一往情深。诸如此类的小说故事还有《桓道愍》(18)、《王道平》(19)、《挑绣》等(20),《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但从历代人鬼相通小说的整体来看,这类描写真爱真情故事的数量实在不多。在大多数故事中,女鬼最终若非以附身借体或投胎转世的方式还阳,就不可能与生人相守终身;并且有的男子本已是有妻室的,又或者在同一时间段内,单身男子同时遇上两个不同的女鬼轮流服侍欢好;而那些没有能够还阳复生的女鬼多半要为自己的情郎撮合促成一段上佳的姻缘,找一位更符合阳世标准的美女闺秀顶替自己的位置,使情郎身边不至于空虚。因此与其说男子是将女鬼作为精神恋爱的对象,倒不如说是女鬼成为填补男子情欲空白阶段的精神调剂品,或被在现实中生活贫困、难觅配偶的男子当成其精神满足的工具。此类性想象的升华,即《红楼梦》中贾宝玉所云之“意淫”。
四、结语
人鬼相通小说中的“男人+女鬼”的配对模式,从深层意义来说是基于古老的阴阳观中的阳精崇拜,其后在传统观念及男性心理的影响下成为了文言小说创作中的某类定式,而这种定式中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又是极为丰富的。尽管人鬼相通故事的描写在整个古代小说史上并没有很突出的地位,但其长久的存在过程却可以给研究者很大的启示。作为古代文人直接书写并阅读的文本,作者与读者间的相互影响最终使这种类型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反映出了各个时代中文人们的各种层次的需要。至于女鬼的文化身份,从汉魏六朝文言小说中所表现的女鬼适应家族繁衍的需要,到唐宋时期小说中女鬼表现出来的高尚人格被社会尊重,直到明清时期小说中的女鬼在情感与事业等更高层次方面与书生文人产生强烈共鸣,随着历史进程推进文言小说的发展,女鬼的形象越来越人性化,其文化影响力也逐渐加大。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文言小说中的人鬼相通故事,实际上记录了历代士人在两性关系方面的逐渐感悟和觉醒。情节离奇的文言小说是由作者记录下来的关于自己也关涉到文人群体的心理情感历程。因此,文言小说中的人鬼相通故事即使情节结构有着不少雷同,但其对于文人心态以及社会史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注释:
①参见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143、248、431、484、535、659页。
②《黄庭内景经·呼吸章》,宋张君房编辑《云笈七籤》卷十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③南朝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文物出版社1988年影印明正统间刊《道藏》第十八册,第483页。
④⑥旧题晋陶潜《搜神后记》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第24页。
⑤⑧(12)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乙志卷七,第238—239页;甲志卷十九,第166页;乙志卷五,第111页。
⑦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姑妄听之》四,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493页。
⑨(15)(16)(19)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2—203页,第203—205页,第200页,第179—179页。
⑩(11)(1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新一版,第2508页,第2509页,第2525页。
(13)《佛教十三经》,国际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14)清宣鼎:《夜雨秋灯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17)明瞿佑:《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一版,第104—107页。
(20)清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二编卷三《挑绣》,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一册,第139—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