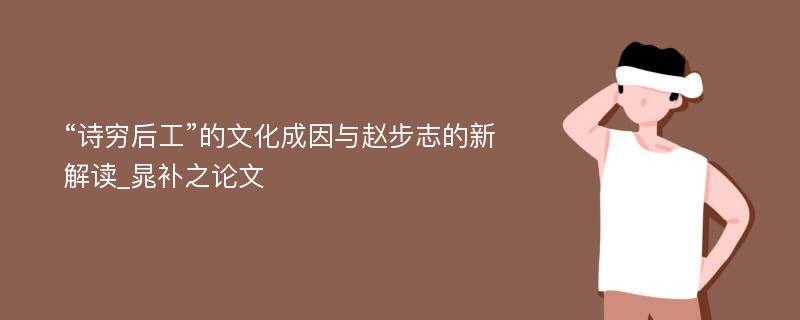
“诗穷而后工”的文化成因与晁补之的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穷而后工论文,成因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7)02-0116-04
一、问题的提出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自欧阳修首次提出以来,已得到后世诸多文学批评家如李维桢、孙承恩、贺贻孙、王国维、钱钟书、童庆炳等人的认同;并且也确实得到了文学史发展事实的印证:自古以来有成就的文学家,无不以“穷”而能“达”。作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也因此受到当代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概言之,对“穷而后工”的当代阐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诗穷而后工”理论渊源的细致考察。学者们认为“诗穷而后工”与孔子的“诗可以怨”,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以及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一脉相承的,并且,诸多阐释着眼于作家物质贫困与精神困窘两方面的思考。如童庆炳先生认为:“穷”是指诗人坎坷的生活遭遇,以及与此遭际相联系的人生的痛苦、焦虑等情感体验。[1] (P30)桂栖鹏、张学成等人认为“穷而后工”说有着深远的理论渊源,[2] 其直接来源是韩愈的“不平则鸣”说,[3] 文章还以此上溯,认为南朝钟嵘的观点、汉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以及孟子的磨难说等,均为“诗穷而后工”说的源流。钱钟书先生认为此命题乃承接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传统一脉,其对怨诗的传统不乏精彩论述,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另外,赵成林等人也将其源流推延到以“怨”言诗,将“诗穷而后工”视为孔子“《诗》可以怨”观念的发展。[4] 大部分的研究者认为,“诗穷而后工”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代表,它内在地要求诗人要能对社会、人生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和批判意识。
其次,学者们就“穷”因何能致“工”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切入点多集中在“诗穷而后工”中隐含的创作论问题以及文学抒情性的特征等问题上。童庆炳先生认为:“诗人”之“穷”,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诗人之“富”,正是在穷中,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满、独特的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1] (P30)邹强借助西方现代主体理论,从文学本体、作家主体、接受主体三个层面展开探讨:作家“穷”之后往往暗合了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需要作品具有真情实感的要求,同时,“穷”之潦倒也成就了文人的创作心态,激起他们的创作欲望。[5] 许家竹指出“诗穷而后工”说深刻地揭示了作家的生活遭遇与人生体验对其艺术成就的决定作用,并从作家的创作实践角度阐释了造成诗穷而后工现象的诸多原因。[6] 总之,此类探讨多是对“诗穷而后工”的内在意旨进行阐释,说明无论物质方面的贫困或先达后穷还是主观精神方面的“穷困失意”都能使作者得到最深刻的人生体验,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便具有一种动人心魂的力量。
很明显,学术界以及前人对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命题和中国文学史中“诗穷而后工”的现象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虽然对“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命题的源流进行了追溯,但对这一命题成熟于北宋的文化成因与学理依据分析不足。其二,对“诗穷而后工”的阐释过于单一化,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欧阳修的阐释,对于“穷而后工”中包含的文学本质问题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晁补之对“诗穷而后工”问题的新解读为契机,试分析“诗穷而后工”盛于北宋的文化成因与晁补之对这一命题的理论贡献。
二、“诗穷而后工”的文化成因与学理依据
宋代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中非常重视对文学本源性问题的探讨,文学本质、诗歌技法等问题都在宋代的诗话或文章论著中有所论及,特别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源动力问题,宋人有着异于前人的理论自觉。比如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素来就有苦难成就诗人的传统,但直到欧阳修才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为“诗穷而后工”做了最后的总结与概括:“(诗)盖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能穷人,乃穷者而后工也。”[7] (P295)
翻检典籍,不难发现,北宋时关注“诗穷而后工”的不止欧阳修一人,对此,王安石、苏轼、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都广泛认同,几乎成为时人评诗论诗的关键词。如王安石在《哭梅圣俞》中云:“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阮以身投,坎坷坐老谁当尤。”[8] (P383)张耒《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中也谈及:“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词。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词,殆出此耶?”[9] (P752)贺铸亦有相似的表述:“诗解穷人语未工。”(《留别僧讷》)苏轼亦曾评钱济明之诗云:“又知诗人穷而后工,然诗语朗练,无衰气。”(《答钱济明三首》)又说:“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僧惠勤初罢僧职》)陈师道在评价王安国的文学成就时说:“其穷甚矣,而文义蔚然,又能于诗。惟其穷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谓人穷而后工也。”(《王平甫文集后序》)李之仪评论东坡诸人追崇陶渊明诗风的原因时也持此论:“张文潜、晁无咎、李方叔……三人者,虽未及见其赋之则久矣,异日当尽见之。以是知穷而后工者不为虚发。”(《跋东坡诸公追和渊明归去来引后》)晁补之的类似表述,待下文详论。显然,欧阳修之后的北宋诸位文人对“不平则鸣”或“诗人固穷,穷而后工”的观念有深刻的体会和认同。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宋人说理意识浓厚,理性精神强的特点导致的。
北宋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学批评的发达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其中,文官政治促使新兴知识分子登上政坛与文坛,他们引领政治、学术以及文学批评出现了非常活跃的气氛和景象,宋人爱说理,且以议论为主要争论手段。这是任用文官,且对科举进行重大改革的统治策略的必然结果。宋代统治者鼓励文人执政,并提高谏官地位,鼓励言事,从宋初的王禹偁到北宋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父子等,都曾上书言事,慷慨陈词,可见,当时的言论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宋人也因此形成了好议论的风气。此种风气影响到文学创作领域,更加促进了文学评论的繁荣。不少文学家都对前代以及当代作家及其创作,加之各种文体、艺术风格进行了热烈的批评与讨论,表现出旗帜鲜明的主体意识,造成宋代艺术批评领域成果的空前繁荣。
其次,从理性层面分析文学活动,很多诗人在文论或诗话中涉及了许多本质性的文学问题。
北宋之前,虽然诗歌出现了以唐诗为代表的巅峰时期,但对文学创作理论性、规律性的探索却为鲜见。这种沉闷局面到北宋时期终于被打破,对文学规律的探索与研究成为很多作家或者批评家的自觉行为。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文学创作体裁如诗歌,到此时已经发展成熟,同时,也与宋人好议论的品格有着直接的联系。以宋时较为重要的诗话与词话为例:诗话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成为首创,后继者蜂起,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品种。肇始于晚唐五代的词,到北宋时期也出现了杨绘的《本事曲》,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本专门的词学论著。北宋中期文坛最为重要的作家以及最引人注目的对象,当然非苏轼及其门生好友莫属。如秦观、晁补之、黄庭坚、张耒、陈师道等,他们有着很多关于诗学、词学创作规律问题的探索与讨论,并且在争论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和问题。
再次,从学理依据上看,“诗穷而后工”的观念是“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诗学领域内的典型反映。
诗文革运动的主要精神是经世致用,针砭时弊,积极发挥文学为国为民的社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对“文以载道”有着不同于理学家们宣扬三纲五常、生发社会教化作用的理解。他所理解的“道”,多接触到直接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欧阳修将社会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指出文学内容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实际的重要意义,其文学观直接影响到诗学领域。欧阳修论诗,重视美刺劝诫,触事感物,反对无病呻吟,“穷而后工”命题的总结与提出,便是他对涉及诗人生活遭遇和社会实践对文学创作成就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典型概括。
最后,从文学家们的个人境遇来看,“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也是北宋中期文人苦难多病的生活写照,其中很多人就是“诗穷而后工”的亲身实践者,此处学界已多有探讨,不再详述。
可见,“诗穷而后工”的文学观念受到宋代文人的集中推崇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时代精神与作家个人际遇互相激荡的产物,也是宋人心理偏于理性、冷静思考的产物,更是对宋以前文学史发展演变规律以及自身创作经历总结的产物。
三、晁补之“诗穷而后工”说的意义
宋代诗文经苏轼发展至晁补之一代,已自辉煌逐渐走向黯淡。前代人的成就成为他们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文学创作与理论总结留给他们的空间亦少得可怜,因此,如何与黄金时期的文章大家们接踵,就成为焦点问题。“苏门四学士”要摆脱苏轼的影响绝非易事。作为与苏轼同时或者稍后的作家,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尴尬。这是后苏轼时代文人的典型特征,也是北宋文学与文化走向没落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这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的文学创作中,也典型地体现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晁补之的诗文中,何以如此清晰地看到苏轼的影响,以及缘何他对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文学观为何如此谙熟。
但与欧阳修等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式的艰苦磨难的人生基调不同,晁补之对“诗穷而后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海陵集序》中,晁补之集中表述了他对“诗穷而后工”的新理解,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胆大而又不脱于时的晁补之。北宋初期功利现实的文学追求使得参与诗文革新运动的作家们的理想是将文章与道德、文学与功用间的关系点明、说透,要想文章道德齐修,达到诗品、文品、人品合一的境界,就非得经历一番磨难不可。而晁补之却不这么认为,他的出发点是典型的文学无用论:“文学,古人之余事,不足以发身。”(《海陵集序》)在他看来,无论是赋诗言志、异士纷起的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文采斐然、名家辈出的秦汉晋唐,虽然文学创作日渐兴盛发达,但并未改变文学无用之性质,特别是自汉以后,“而言辞始专为贤雄夸虚张听者为夺”。(《海陵集序》)应制取宠始终是文学的一大功能,对外在形式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内容的更新,文学形式方面的变化使它离社会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因此,它的无功利性就越来越强了。
晁补之进一步指出古人之有大成就者,无不是以功业立身,若仅善于言辞,却不足以发身。即便是在唐代如大诗人李白与杜甫,却也是“于唐用人安危成败之际,存可也,亡可也”,(《海陵集序》)所以文人诗人之事业,很少能真正起到经邦济世的作用。“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资而经生”。(《海陵集序》)为文如此,为诗更是如此。文学既是古人之余事,“至于诗,又文学之余事”,(《海陵集序》)换句话说,诗是比文还缺乏现实功用的东西。而从文学史来看,大部分的诗人都是穷途末路、潦倒一生,对一些著名诗人来说更是如此,诗人穷困是因为诗本身无功利的特点决定的,在重文重诗之北宋时期,晁补之有如此见解是够大胆的了。在他看来,“诗穷而后工”首先可以理解为“诗人少达而多穷”,这就比欧阳修等人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诗穷而后工”在欧阳修等人眼中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晁补之却看到本质,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与文学乃非功利活动的本质有关系,它不足以资世经生,也不足以换取功名利禄,所以导致诗人多穷困窘迫。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南宋时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将欧阳修与晁补之两人观点并列的良苦用心了。
但晁补之又绝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和唯形式论者,做诗不可以无病呻吟,也不能仅仅是练词铸句,文学艺术更大的魅力在于,它在“不足以发身”的同时,却能在精神上给予人更大的支撑力量!作为一个与苏轼等人有着共同追求的文学家,晁补之坚信,心中的“道”——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的目光永远都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当坚守的。文学史上那些终有所成的作家,就在于他们能够坚守贫困,在文学事业中坚持自己的信仰与理想。用晁补之的话说,就是“虽数用以取诟而得祸,犹不悔,曰:吾固有得于此也,以其无益而趋为之,又有患难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贤乎!”(《海陵集序》)只有在这种“不悔”精神的支撑下,“诗穷而后工”才真正成为可能,它更为强调文学的内在精神与对人的巨大支持作用。这就是晁补之的可贵之处,他不仅突破陈规,还世人一个真正的文学真相,诗的真相,而且并未走向唯美主义或如同宋初以才学为上的“西昆诗人”或同时的以技巧为工的“江西诗派”,而是担当并坚持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和操守。可以说,晁补之的观念要比简单比附儒家思想,像白居易、韩愈等人那样直接强调诗要有补于世的口号更深一层,他更为看重文学创作背后给人精神的历练及对个人道德修为的提升作用。
由此看来,晁补之并非简单模仿欧阳修等人的观念,而是有着独立的理论建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文学,古人之余事,不足以发身”、“至于诗,又文学之余事”等非功利的文学本质观,接触到了导致“文人固穷”的内在动因。即便是在对文学形式的追求盛极一时的魏晋南朝时期,文学无用的观点也未曾有人提过,可是晁补之却是在儒家功利文学观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提出这种观点,这在当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宋代文学发展到晁补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无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在理论建树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有着较成熟的文学观点,特别是关于宋代文人中流行的“诗穷而后工”的观念,他更是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他的文论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被遮蔽在唐宋八大家的光辉之下,少有人问津,这不得不说是宋代文学研究中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