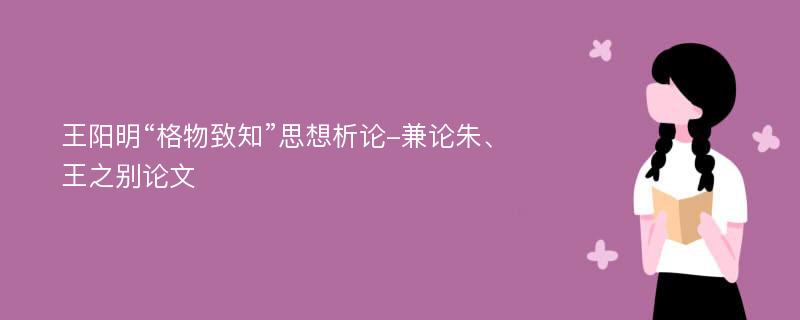
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析论
——兼论朱、王之别
吴 瑶
摘要: 王阳明所理解的“格物”不同于朱子的格至事物之理,而是正其意念以归于正,因此,“穷理”在王阳明的理解中是指通过正自己的意念而存天理,“致知在格物”是在事物中落实自己的良知。基于此,其认为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是无关身心的外在经验知识积累,其无法贯通自然知识和道德良心,即使朱子补充“敬”概念、作《格致补传》等举措在其看来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其支离工夫带来的弊端。其批评朱子析“心”、“理”为二,提出“心即理”的论断,并由此重新对“格物致知”等概念进行诠释,力图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构建一套根本的、易简的入道工夫。
关键词: 格物;致知;《大学》;王阳明;朱子
四书之一的《大学》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之一,自唐代大儒韩愈将其援引入其代表作《原道》,《大学》在儒学的地位就开始发生变化,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在南宋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看来,韩愈发掘出《大学》的重要内涵,彰显了《大学》本身的重要价值,此举虽大有功于儒学,但是对于《大学》中核心概念——“格物致知”的理解和诠释还不够充分,未能免于择之不精、语焉不详之弊[1]512。朱子本人也非常重视《大学》,对其“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2]2。“采而辑之”,即对散乱的《大学》加以编次,分为经、传两部分,形成《大学章句》;“窃附己意”即为《大学》作注,兼采各家,形成《大学集注》;“补其阙略”即对《大学》缺失的“格物致知”部分作传,形成《格致补传》。经由朱子,《大学》从《礼记》中的一篇普通篇章正式成为了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的《四书》之一,并成为后世近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目。朱子对《大学》的体例、注释和地位的看法基本为后世所接受。
再次是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方式调整。壮拳文化作为壮人的传统身体文化,理应在壮人恋土保守的性格中得以确切传承,但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方式变了。当壮拳不再是经济洪流中的“枝头俏”,也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境遇。“爷爷教拳要是收徒弟学费,咱家早就是这条街最富的了”“没时间学,学了也不能当饭吃”[27],恪守古训、弟子五千、曾经风光无限的壮拳大师农式丰在面对当今生产方式改变的情况下也难逃扼腕垂泪、无奈孤独的命运。
在MATLAB上实现了AdaCode,并使用真实trace进行仿真.真实trace取自802.11n长距离mesh网络实验床的一条20公里长的链路.在该链路上使用Pktgen发送UDP数据包,在接收端记录收到的每个数据包的下列信息:接收到的时间、序列号、RSSI值、接收状态(CRC出错、接收正确)以及CRC出错数据帧的内容.然后用此数据做为trace输入到MATLAB,对AdaCode进行仿真评价.为真实记录丢包和出错的信息,在无线网卡驱动中关闭了MAC层的重传功能.开启了无线网卡的混杂模式,使得出错的数据包也能上传到MAC层而不被丢弃.
然而,明代大儒王阳明却并不全然同意朱子的做法。其《年谱》有载,“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物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3]1384。王阳明认为,朱子所订的《大学章句》,无论编排次第,还是义理把握,都未能完全合乎圣人之旨。在他看来,《礼记》中的《大学》古本本身就清晰明了,自成一篇,没有经、传相分的必要;另一方面,其不同意朱子将“格物”作为《大学》的第一要义看法,并认为朱子所作的《格致补传》也是不必要的。王阳明的这番批评并不是私心自用地针对朱子,按照他的表述,是为了阐明圣人之道,以示后学求道入学之由,因此其自言“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4]154。
而朱子和王阳明之所以存在着这样的不同意见,首先源于二者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在《大学章句集注》首章中,朱子对“格物”的解释是“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所不到也”[2]4。将“格”解释为“至”并非朱子首创,其承袭于小程子,出自《尚书·舜典》“舜格于文祖”,即舜通过精进不已而达至先祖的美德。然而,单单一个“至”字很难将“格”的意思说清楚,其既没有说明该如何“格”,也没有说清楚要“格”到怎样的程度。因此朱子进一步说“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所不到也”,即要求穷尽事物蕴含的事物之理,做到表里精粗无不到。在《格致补传》中,朱子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2]7,基于此,其常常以“穷理”来解释“格物”,“格物”的要求就是穷究事物之理,“穷理”也就是做“格物”的工夫,因此,在朱子看来,二者只是同一工夫的不同面向,“格物”强调接于事物,“穷理”强调穷究道理。另外,“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5]2800,朱子多次提到,所穷之“理”既包括天地间的事物存在的所以然之理,也包含人伦界的所当然道理,这些都是“穷理”的范围。
此外,王阳明还提出,就“格物致知”与“诚意”而言,应当“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3]1384,“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3]88根据王阳明对“格物”的理解,其是对意念做“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为善去恶的工夫,这样的格物工夫实际上就是“诚意”的工夫,只有以“诚意”为主,正其意念和推致良知的工夫才能有所着落,而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在王阳明的理解里只是在积累经验知识,但却无关乎自己的身心,与王阳明所真正关切的修身为善或者《大学》所言“明明德”没有直接关系,由此,朱子才会认同小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论主张,在“致知”之外补充“敬”,由此以“格物”增进知识的获取,以“敬”促进道德的达成。王阳明认为,如果“敬”如此的重要,儒家的学者怎么会粗鄙至此,遗落一个如此重大的字眼和环节,而有待于千年后的人来补充?他认为这恰恰说明朱子的理解存在着不合原义之处,以致不能融贯。
在《大学问》中,王阳明阐释了其对“致知”的理解,“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1]425-426,此处“后儒”指向朱子以及后学,其认为,朱子所谓的“致知”只是在扩充知识而已,这并不是《大学》“致知”的本义,《大学》的“致知”是要推致心之良知。对于“致知在格物”,王阳明采取了与朱子全然相反的理解。朱子曰:“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1]425-426“致知在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1]3493在朱子看来,《大学》八条目,其端始和紧要功夫都在“格物”。王阳明则认为,良知为“意”之本体,是善恶、是非的判断依据,因此“致知”是“格物”的前提,这样才能使得事物归其正,因此“致知在格物”在王阳明看来就是“致吾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4]100,也就是在事物中落实自己的良知。
然而,王阳明则认为“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4]13。对于“物”,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4]13,王阳明认为“物”是“意之所在”,比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4]13,由之可见,王阳明所理解的“物”是与“意”密切相关的,其不再是朱子所谓的事物之理,而是根于意念的发动和落实而呈现。
同时,王阳明也不同意朱子将“格”解释为“至”,他认为,朱子训“格”为“至”,需言“穷至事物之理”乃通,因此重点在于“穷”与“理”,因此光言“至”不足以解释“格”[4]104。对于“格”,王阳明的解释是“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在其看来,“格”是“正”的意思,因此“格物”就是使所发的意念归于正,使所发的意念全为善念。基于对“格物”理解的差异,王阳明对“穷理”的诠释也有别于朱子。“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4]15。因为将“格”理解为“正”,因此凡意念即于物,则需要做去其不正以归于正的格物工夫,而这样的工夫也就是存天理,因此,“穷理”在王阳明的理解中,并不是朱子所谓的穷尽事物之理,而是通过正自己的意念而存天理、去人欲,从而敞明自己的“明德”。
“创新”、“改革”、“实践”是各个高等院校在教学过程中不变的主题,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在高等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总结,我们坚信:只要坚持坚持改革创新并不断进行实践总结,一定能够走出符合当代高等教育教学的实践模式,培养出符合国家发展、社会需求的创新型技术应用人才。
朱子对“致知”的解释是“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2]17。对于“致”的解释,朱子说:“致之为义,如以手推送去之义”[1]472,即推扩之义,而“极”则表明要推之于极处,方是知致。同时,根据朱子的论述,格物与致知也并非全然不同的工夫,其非常看重“致知在格物”的“在”字,他说“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2]6,也就是说,“致知”的完成是通过“格物”来实现的,“在”就表明了“致知”要落在“格物”上。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7,朱子认为,心有知,物有理,对于物理的穷尽能够敞明心中的知,这就是“致知在格物”的原理,这里隐含着朱子对于物之理和心之知的一致性的看法。基于此,在朱子的论述下,“格物”和“致知”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面向,且格物是所以致知,而吾之知随格物不断地推扩。
这其中,核心的困境就在于自然知识和道德良心如何贯通的问题。王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4]263按照朱子对于“格物”的理解,纵使去事事物物上穷其理,但这又和自身的意诚、心正有什么关系呢,它如何能促使心正、心诚呢?并且,将“格物”的工夫标榜为第一义的做法还会导致严重的弊端。当郑朝朔向王阳明询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的时候,其言:“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辩?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辩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4]11。在他看来,“格物”并不是全然没有意义的,涉及到具体事亲之事的时候,其中的礼节也仍旧需要讲明、学习,但是一两日讲明即可,并不是最为紧要的工夫,最重要的是在事亲过程中“心”是否纯乎天理、是否有人欲夹杂。如果只是强调朱子所说的“格物”,强调对事物当然之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仪礼的施行恰当与否,而忽略内心是否纯然天理,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伪善的戏子的情形,表面上从事于仪礼之事,心中却私意充杂。这既没有为学者指明一条恰当的学习路径,同时也给君子小人的分判带来了麻烦。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上述特征是由集体所有制性质所决定的,尽管不能完全等同于专业合作社,但基本运行规则依然接近于专业合作社,或者说是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本精神设计的。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也要求新成立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到工商部门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要求进行登记,当然具有削足适履之嫌,但应该看到,社区股份合作社除了成员的封闭性,完全按股份分配盈余等特点外,在其他方面还是和标准的专业合作社比较接近的。
由是,王阳明指出“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4]89,他认为,朱子关于“格物”的论述,有着不务诚意而专以格物的倾向,其弊端在于支离,只是从事于各种格物的工作,但却很难内向收摄。由是,朱子添加“敬”来弥补知识与德性的缝隙以及所作的《格致补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反使《大学》简明的工夫更为支离。
而王阳明对此的解决方案就是对“格物”、“穷理”、“致知”等概念进行重新诠释,由此力图实现一套根本的、易简的入道工夫。他的重新诠释是建立在其对“心”与“理”的关系的阐释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4]89,心、意、知、物皆是理的不同表现,因此“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4]89,格、致、诚、正,虽然名称相异,然只是一事,是同一工夫的不同方面。同时,他据此批评朱子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3]44-45,他认为,根据朱子“格物”的主张,“理”与“心”分别成为了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因此是析心、理为二。这不同于他“心即理也”[3]8,“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3]14的主张。
事实上,朱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今日明日积累既多,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矣”[5]408,但这里的“心”是已然天理贯通的“心”,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其全体天理,与理为一,心即理,理即心。然而,即使这样,在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心”和“理”还是存在着差别的。其言:“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1]528可见,朱子认为“心”是管摄“理”,而不直接等同“理”。针对朱子所言,王阳明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3]42。他认为,朱子虽然通过对心、理关系的论述,极力想要弥缝二者的距离,但是由“与”字,便可见其终究为二者,也正由此,王阳明开始了与朱子不同的对《大学》的解读和建构。
王阳明在龙场“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3]1354,开始主张反求诸身以“致良知”,而不是只求于事物之理,由是,他通过对《大学》“格物”“穷理”“致知”“诚意”“正心”的重新界定,建立起他自身的《大学》工夫论体系,并以此来挑战朱子所奠定的关于《大学》的系统解读。本文主要围绕着王阳明对朱子的对话来论述其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阐发,并简要梳理了其对朱子提出的几点主要质疑及其内在缘由。而王阳明对朱子的批驳是否成立、他所构筑的《大学》简易工夫是否优于朱子的建构,则需要在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去解读和判定。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王守仁.传习录注疏[M].邓艾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5]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99.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16-0116-03
基金项目: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806010155)
作者简介: 吴瑶(1990—),女,四川乐山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儒家哲学、宋明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御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