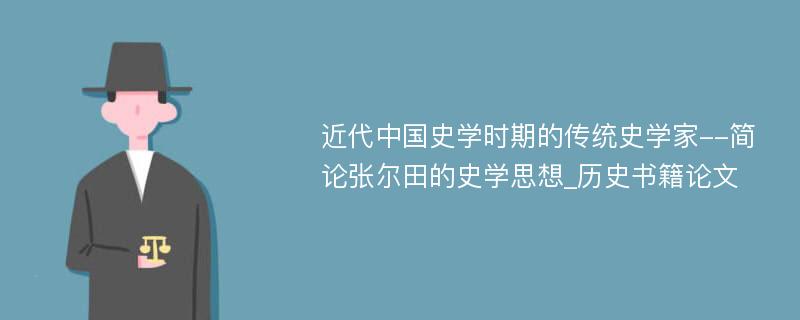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史家论文,转型期论文,近代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晚号遁堪,浙江钱塘县人。清末,曾任刑部广西司主事、苏州试用知府等职。民国建立后,以遗老自居,隐居上海。后入清史馆,参与《清史稿》纂修达十年之久,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燕京大学,著有《史微》、《玉溪生年谱会笺》、《清列朝后妃传稿》、《遁堪文集》等,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史家。张尔田交游广泛,隐居上海时,曾与王国维、孙德谦齐名交好,人称“海上三君”,定居北京后,与陈垣、钱穆、邓之诚等著名史家都有密切交往。但在现今的史学史研究中,张尔田长期处于被遗忘的状态。① 本文介绍张尔田的史学思想,并将其放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以引起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者的重视。
张尔田精研刘知几、章学诚等中国史学理论大师的著作,并长期从事史学研究,对史学宗旨、目的、方法、体例等史学理论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其成名作《史微》,是清末民初著名史论著作之一,对于中国传统史学流变以及中国古代学术体系提出了系统看法,时人曾将之与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相提并论。② 同时,张尔田身处中国新旧史学交替之际,其对史学宗旨、方法等的兴趣并不仅仅停留在赓续传统史学,还表现在对“新史学”的思考上,这些看法、思考更多的散见于其他著述中。故本文结合张尔田的其他论著,从其对传统史学和对“新史学”的批评两个方面讨论张尔田的史学思想。
一、张尔田对传统史学的阐发
对于中国史学传统,张尔田在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流变、治史态度、史学方法等方面皆有论述,而尤以在史学方法方面的论述较多。③ 现分项介绍于下:
(一)“中国学术之重要,莫历史若也”——史学地位论
《史微》一书以“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为宗旨,所以定名为《史微》,是因为他本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六艺皆古史,而诸子又史之支与流裔也”。④ 因此,《史微》也是一部论述古代史学的著作,尤其对于古代史学的发展演变做出考察。
他认为,中国史学发源于上古的史官之学,黄帝始立史官,考察史学也应该从黄帝开始。后世史官制度逐渐发展,出现左、右二史之分,至周代又分为五史。诸侯国亦开始各有其史,“求其位号,一同王者”。此时史官地位尊崇,职务重要,史官之学亦包罗广泛。但是,“自汉宣帝改太史公一官位令,奉行文书,于是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班固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道统既异,官亦无足轻重矣。史学之亡,盖在兹乎?”随着史官制度的转变,史学亦发生巨大改变。因此,他认为中国史学应以司马迁为界,划分为“古史”与“后世之史”两大阶段:
故论古史当始于仓颉,而终于司马迁。《史记》一书,上以结藏室史派之局,下以开端门史统之幕,自兹以后,史遂折入儒家,别黑白而定一尊,虽有良史,不过致谨于书法体例之间,难以语乎观微者已。(《史微·史官沿革考》)
“古史”与“后世之史”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宗旨和内容上:
史学自东周失官,流为道家。吾于道家未分之前,求史之旧学,其惟六艺乎?盖六艺者先王经世之书,皆掌诸柱下,皆太史所录,非如后世仅以编年纪传为史而已。章实斋有言:“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惟其无定名,固天人之故、政教之原、体国经野之规、宰世御民之略、皆得以史目之。惟其有成法,故《诗》以导志,《书》以导事,《礼》以导行,《乐》以导和,《易》以导阴阳,《春秋》以导名分,不相合而相为用。(《史微·史学》)
可见,“古史”之学即“史官之学”,其内容是古代帝王的经世之术,其载体则是六艺,“六艺者,上古之通史也”。其次,“古史”与“后世之史”的区别还体现在“史体”之异:
后世之史,纪事而已,纪言而已。古史则不然,其纪事也,必并其道而载之;其纪言也,必并其意而载之。有纪事、纪言而道与意因之而见者,《尚书》、《春秋》、《礼》、《乐》是焉;有载道、载意而事与言因之而见者,《易》与《诗》是焉。(《史微·史学》)
统而言之,古史学为古帝王经世理民之术,其载体就是六艺,内容包罗广泛,在性质上有类于历史哲学,体例上纪事与载道不分;后世史学,则沦为编年、纪传,侧重记载,道与事分离,在内涵、功用、体例上皆有重大变化。⑤
中国古代关于史学流变与地位的讨论,主要围绕“经史关系”问题展开。⑥ 在这一点上,张尔田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并加以发挥,通过对“古史”和“后世之史”加以区分,将经学史学化,强调了史学作为中国学术源头和主体的地位。但是在经学衰落,现代学术分科逐渐建立的情况下,仍然囿于“经史关系”的老命题,显然难以清楚描述史学的地位。因此,他在晚年曾试图用现代科学术语对历史学的地位做出论述:
中国人不喜研究物理,无西洋之纯粹科学;又不甚研究心理,无西洋之纯粹哲学。而中国学术所据以研究之对象,则事理也。欲研究事理,即不能不凭籍事实。一事也,具体观之则为事实;抽象观之则为理论。中国学术,大都乞灵于此,而历史则搜集事实材料之总汇也。⑦
既然中国学术由研究事理得出,研究事理需要凭籍事实,历史学是搜集事实的学问,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学术之重要,莫历史若也。”
(二)“史学以记载为本”——史学宗旨论
关于史学宗旨的讨论,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张尔田也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同班固关于史学“历纪古今成败祸福存亡之道”的论述:
史家之目的,班固所谓“历纪古今成败祸福存亡之道”尽之矣。道犹路也,谓人类动力推进之路也。历史本全世界人类动力推进之一过程,而所谓“古今成败祸福存亡”者,则人类推进过程中之一波纹耳。老子观此而悟道,则教人葆之以虚。孔子观此而悟道,则教人用之以中。其他若墨家也,法家也,杂家也,虽所术不同,而言治言理,无有不凭籍于历史者。⑧
可以这样理解:历史学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记述,而历史记述的功用则是为了“悟道”。本着对史学目的的这种看法,他批评了传统史学中的褒贬传统:
或曰:前人之论史也,“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然则独非史家目的欤?曰:此盖以《春秋》之法为史法,而不知史固自有其法也。《春秋》之法,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此孔子之教经也。非所论于历史也。历史若以褒贬为目的,则不过一家之言耳,必不能通百家之用矣。⑨
对于历史知识的性质,他也一反新史学的普遍意见,认为史学并不完全等同于科学:“史也者,变动不居者也。所用之因果律,本于其他科学严格不同。”⑩
与西方史学注重解释不同,长于叙事,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之一。(11) 他对新史学中流行的“新考证学派”注重“考史”的治学方法颇不以为然,而认同传统史学中重视“记述”的史学方法。他自己亦在《答梁任公论史学书》中提出“尝谓史之难为,不难于考古人之史,而难于自作一史”。(12)
这样的史学主张,并非张尔田一人所有。同在燕京大学的邓之诚,亦有相同的主张,他说:“之诚端居读史,历数十年,深信史学以记载为本,颇与时贤异趣。晚乃得君(张尔田)。君素服膺章学诚、龚自珍,唯此不敢苟同,余皆与君合,以是称至契。”(13) 可见,强调“史学以记载为本”,是当时除新考据学派之外的史学家一种较为普遍的主张。
大致来说,史部书籍有考史、论史和著史之别,考史之作意在考据,论史之作重在解释,著史之作志在记述。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互有偏重。杜维运曾指出:“以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较,中国史学以叙事为大宗,西方史学则以解释为首要。”(14) 由此可以看出,张尔田、邓之诚等人“史学以记载为本”的主张,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特点的坚持,也是对“新考据学派”之婉转批评。
(三)“体例”与“义法”——历史编撰学思想
刘知几、章学诚是中国史学界讨论史学方法的大师,张尔田精研刘知几、章学诚学说,对史学方法和义例问题颇为注意。清史馆的十年纂修生涯和历史研究实践,更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强调史学“叙事”、“记述”功能,也必然导致对历史编纂学方法和技巧的重视。因此,张尔田在生前发表的论史文章中,对此问题再三致意,其中较为集中的是刊登于《学衡》杂志上的《史传文研究法》一文。(15) 张尔田曾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史传之文”(16),这篇文章很可能即由当时讲稿整理而成。在此文“总论”中,他提到:
今既讨论史传之文,不揣擣昧,勒成一书。先论体例、义法,为讲史文之前方便(自注:借用佛典名词),隐括古说,使就绳墨,即所谓不变者也;次论铨配、撰结诸方法,推见良史之才、学、识所由本,为讲史文之正宗分(自注:亦用佛书名词),则不佞心得为多,即所谓至变者也;而以考究史职之得失,与夫所以养成史才之道,为余论终焉。庶几秉笔之士,有涂辙可循。
可见,《史传文研究法》本是作为一部历史编纂学专著来写的,其中包括史书体例、编撰方法、史官制度以及史家修养等多个方面。但在《学衡》上仅刊登四章,并非全豹,其他章节亦未见于其他报刊和作者文集,似为未完之作。因此我们今天只能就此四章展开讨论。
《史传文研究法》四章分别为第一章“总论”、第二章“论史与其他叙事之文不同”、第三章“论史有成体之文与不成体之文”、第四章“论史有六家三体”。大约正相当于作者计划中讨论“体例”与“义法”的部分,包括“体例”和“义法”合称“义例”,是中国传统史学史书编纂方法论的基本范畴,包含史书形式、史事取舍、记事断限、史文繁简等多方面史学方法问题。(17) 以下即分“体例论”和“义法论”两部分来讨论张尔田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体例论”指其对史书体例的看法,“义法论”指其对于史书编纂方法和技巧的讨论。
1.体例论
(1)“成体之文”和“不成体之文”。作者认为史部书籍有“成体之文”和“不成体之文”之别。“不成体”之史籍有三种,即“史稿”、“史纂”和“史考”。历代国史馆记录当代事迹的纪传体史书以及实录、起居注等,因“皆随时撰缉,以备后史采择,而略具史才者”,故只是“史稿”;各种专门记录某一方面内容的史籍,如“有关于掌故仪制”的通典、通考、会要、会典、通礼、仪注、则例、格令等书,“有关于舆地”的方志、风土记等,“有关于谱录”的家传、年谱、四部书目等,以及杂记史事的书籍如《北梦琐言》、《东京梦华录》等,因“大都聚敛而成,其事大都渔猎所得,或为官修,或为私属,虽不能尽如史稿之纯,而实足为作史者之笔削”,故可之称为“史纂”;考证史实的书籍,如《古史考》、《五代史纂误》一类,即所谓“史考”。史稿、史纂、史考还不是史。
我们知道“史考”、“史纂”概念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已经提出,章氏认为二者皆非史学,主要是从史学目的来说。张尔田在二者之外又加入“史稿”一项,认为三者皆不得为史,则主要是从体例与内容的完备性立论。此下,他遂转入对“成体之文”的论述。
(2)“六家三体”与“一体论”。在中国史学史上,刘知几首先提出“六家二体”概念。张尔田在刘知几说法的基础上,提出史书有“六家三体”。所谓“六家”,指的是记言家(《尚书》家)、记事家(《春秋》家)、编年家(《左传》家)、国别家(《国语》家)、通史家(《史记》家)、断代家(《汉书》家)。但是“后代所行,《左传》、《史记》、《汉书》三家而已。三家之中,又分二体,二体维何?则一曰依年铨次之体,二曰依类叙述之体而已。依年铨次之体亦谓之编年体,依类叙述之体亦谓之纪传体。前者为左氏之遗,而后者为马班之衍。惟此外则尚有一体,是曰纪事本末体”,此即为作者所说的“三体”。
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体论”,认为“编年也,纪事也,纪传一体皆足以赅之”。为什么呢?理由有三:首先,纪传体中包含了编年与纪事的要素。他说:“观夫本纪之为体也,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而相续,一朝大政,纂要勾元,拟诸邱明,岂非同轨。”此是说,“本纪”部分相当于编年体。“至于天文以下诸志,或以大致沿革为始终,或以庶绩废兴为经位,言行并载,本末兼赅。袁枢纪事,又足何矜?若为诸志但详典章掌故,而于行事首尾或嫌太略,则司马迁本有《秦楚之际月表》,专详刘项大事;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亦列大事记一栏,神而明之,非无前准。”此是说,“志”这一体裁即相当于纪事本末体。其次,纪传体在兼有编年、纪事要素之外,还有二者不具备的优点和长处。用他的话来说,即是“若乃事当冲要,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不枉道而详说;论其细则纤芥无遗,语其粗则邱山是弃,似有编年、纪事二体所未周,而必假纪传始能曲备者矣。”最后,纪传体可以损益变通以适应后世要求。他认为,纪传体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志等体裁在历代皆有增损变通,以适应当代历史记述要求,在现代,我们也可以本着此精神对纪传体加以变通发展,以适应现代的要求。为此他举曾参与修撰的《清史稿》为例:《清史稿》把可以归入旧目的归入旧目,如把法律归入“刑志”,陆军、海军归入“兵志”,教育、警察、审判、官制分别归入“选举”、“职官”志中;对不能归入旧类的则增创新目,如增加“交通”、“邦交”等志,改“宰辅表”为“军机大臣表”,改“藩镇”为“督抚年表”,“儒林”、“文苑”传之外增立“畴人传”。他认为这些“皆因旧史,改弦更张之,已足应变无方矣。固不必缅规越律,纷纷然破坏史体,而后谓能毕乃事也。”
对于有些学者提出“国家体制变了,史书的体例也应该改变”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不通史学”。首先,“本纪”的目的是记录“一代大政”,“古者,政自天子出,固不能不以天子编年。……岂沾沾焉为帝者一人续家谱哉”,因此“‘本纪’之体,于一人私传截然不同。纵使国体变更,而大政不能无出,发号施令,考绩敷猷,岂异帝时。‘共和’表年,有先例也。必谓‘本纪’有滥天子,自可以皇甫谧、何茂林之例,改为‘世纪’,或依竹书纪年之例,称为‘年纪’。至于一期元首,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者,则付之于列传”。而“世家”一体,他认为班固《汉书》就已经不用,并把雄长一方者,写入“载记”,至薛居正的《五代史》,则统归入列传。这些都表明纪传体史书因时变更,可以不断发展的特点。
总之,他认为本着“有之既可增,则无之亦可减”的精神,“后来所有,而为前代所无者,但当于列传中多列篇目,废臣工之标题,以叙社会人物。吾未见古人成规不能适应于后世也”。可见他对史书体例的看法是极为保守的。但同时,他对纪传体史书优点的强调,对我们理解古代史书和继承发扬中国史书传统似亦不无启发性。
2.义法论
《史传文研究法》第二章“论史与其他叙事之文不同”中对于“铨配、撰结诸方法”也略有涉及。他指出,史书以存真为目的,对事实之显著者,史家据事直书即可。但是对于史事并不清楚明白之处,史家如何记载呢?他指出了三个方法:其一是“睹指知归,见微知著”之法。这种方法是指,在“其事之隐微,与其人之密忽,亲之者既未宣之于言,传之者亦恐或有失实”之时,“苟有一二流露于事实,则作史者亦必谨书之,使人睹指即可以知归,见微或可以知著”。即是说,当事实在似有似无之间时,作者可以把其中一些确凿的情况记录下来,以使读者可以推见当时的情况。
其二是“微词示意”之法。是指在传闻异词的情况下,作者可以用委婉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举了一个例子:
如魏郭太后为明帝逼杀,当时有两说。据《汉晋春秋》谓:文帝崇郭后而赐甄后死,即命郭母养其子明帝。明帝继位,数向郭后问母死状,遂逼杀之,使如甄后故事以殓;据《魏略》,则甄后临殁,以明帝托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说甄被譖死不得大殓之状,帝哀感流涕,令殡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说,则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后之说,则郭死后,明帝始知旧事而以恶殡也。此两说当时盖莫衷一是。陈寿《三国志》于《甄后传》,既大书被谗赐死事矣,而于《郭后传》但云“太后崩于许昌”,盖甄之赐死系事实,故传书之,郭之逼杀系传说,故传不书,而以“崩于许昌”四字,略见其不在宫闱,则传说之不为无因,可以知之矣。
其三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法。是指在事实明知确凿无误,而所搜集证据却不足以证明的情况下的编写方法。我们看看他举的例子:
如《春秋》:“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云:“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盖史之所凭者事,而事之所凭者证据,证据苟不能见信于人,则留之以待后来者之审定,而不敢以己之所知,变异其真。史所以贵阙文也。
在以上指出的三种方法之外,他还在《与大公报副刊编者书》之二“论史例”中提到古人还有“两载之法”:其或经史家再三审定,而仍有疑而未决者,则有两载之法,留之以待后人之存参。如太史公于“老子列传”,用几个“或”字,即是其例。(18)
张尔田以上所指出的四种方法,是对中国传统史书中在出现表述疑难问题时所采用方法的总结。这其实是对自刘知几《史通》以来注重探讨历史编纂学方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现在看来,他所指出的四种技巧,细致深入,确实发前人所未发。不但对后人理解传统史书有帮助,对于后来的著史者也有借鉴意义。
此外,他还在以《与大公报副刊编者书》(19) 为名的一系列论史书信中,就清史纂修以及其他史学问题发表看法,其中注意的也主要是史书体例和撰写方法、技巧问题,不再赘述。
综合而言,在张尔田看来,史学以“存真”为目的。为了“存真”,史学应该注重“记述”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因此,相对而言,“著史”比“考史”更加重要。而为了“著史”,史家应该重视对著史方法的研讨,这样,历史编纂学方法应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而其取法对象,则在中国传统史学。他认为,在史书体例上,纪传体史书,实集众体之长,经过变通,仍然具有活力;在记述方法上,传统史书的表述技巧,亦多有高妙之处,值得后来著史者借鉴。
张尔田自认为是“浙东史学”之后劲。其弟张东荪称其“成《史微》数十万言,自谓演浙东遗绪”,(20) 邓之诚亦称其“欲自谢山,以窥黄、万,遥接东莱、伯厚、身之之绪,以光大浙东史学”。可见从张尔田自身来说,他是以浙东的史学大师作为取法对象的。章学诚曾指出“浙东学派”的特点在于“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反观张尔田,在其学术思想体系中,历史学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写作大量历史学著作,并主要以史学家名世,这与浙东学派注重历史研究的特点是相一致的。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他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记述,并且提出了史学重在记述的思想,这些也和黄宗羲、全祖望等人注重文献之传的治学特点有相通之处。
二、张尔田对“新史学”的批评
王汎森指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清民初梁启超所开展的“史学革命”;第二阶段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动;第三阶段是社会史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这三个阶段及其史学流派可以统称为“新史学”。(21) 同时他认为,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史学中逐渐出现了新、旧两派之分。在1949年以前,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所领导的研究工作在多数专业史学研究机构中占据主流地位,是二三十年代最有力量的学派。因此所谓的“新派”,主要是指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学派。我们这里所指的“新史学”也主要是这一派所代表的史学。“新史学”运动大致包括有胡适所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活动。这三个运动在时间上连续而起,虽然在治史倾向上略有异同,但是体现出大致相同的治史风格,因此可以称之为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共同特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治学方法上注重实证性研究,推崇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并认为它与科学方法有相通之处;二是在治史观念上,强调怀疑的态度并抱有进步发展的历史观。这一派学者,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或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因此他们所代表的史学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研究上影响的体现。
所谓的“旧派”,则成分较为复杂。它首先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指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其次,表现在史学研究上,它指的是新史学的反对者和批评者。这两者之间虽然有联系,但是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很多学者在文化观上是以传统派自居,但是在史学研究上却备受新派学者的推崇,像王国维、陈寅恪等人。
在史学研究上,张尔田作为“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对新派史学展开了激烈批评。具体说来,他对新派史学的批评主要针对胡适所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和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批评的侧重点则集中于“新史学”所标榜的考据方法和疑古态度两项。
(一)对考据学风的批评。自20年代开始,胡适发表一系列文章,推崇清儒的治学方法,认为其体现了科学精神。(22) 自此,乾嘉考据学借着人们对科学方法的追求,成为“新史学”的主要治史方法之一。因此,余英时在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之时,亦称其“是以乾、嘉考证学和西方兰克以后历史主义的汇流为其最显著特征”。(23)
针对新派学者推崇乾嘉考据的风气,很多旧派学者不以为然,而其出发点,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传统史家多认为新学者是乾嘉汉学翻版,他们大多不满乾嘉以来唯考据是尚而不能兼顾义理的治学风气,认为这种学术风气使得学问严重脱离社会”。(24) 这一判断也概括出了张尔田对新史学批评的基本立足点。
张尔田虽然自认“幼时所最喜用心者,乃系干燥无味之考据”,(25) 而且在考证上亦有传世之作,但是由于深受章学诚学说和今文经学的双重影响,在其成学以后的学术体系之中考据的地位很低。他并不完全否定考据的功用,但认为考据只是学者的初门,治学必以微言大义为旨归。(26)
对于新学者们的国学研究,他有这样的评论:
虽然,我辈中国人也,国学真精神、真面貌,我辈自当发挥之以贡饷于世界,而断不可以远西思想先入之说进。有先入之见,则吾之国学,非吾之国学矣。休宁、高邮所用以考核经史之术,其有合于科学方法与否,吾所不敢知。即谓其全合乎科学方法,以吾国学之殊方,有断断乎非仅恃乎科学方法所能解决者。考据之学自是一家,我辈生千载后而上读千载古人之书,比于邮焉,此特象胥之任耳。故东原自诡舆夫。今误认舆夫以为乘舆者,吾不知战代庄、墨、荀、孟诸大哲,无考据又将何以为学也?考据家所凭以判是非者,厥为证据。然学之为道,固有不待验之证据,而不能不认其为成立者。(27)
这一段评论,大致有三个要点:第一,国学研究不应该以西方的思想为指导,这隐指胡适“径依西学来讲国故”(28) 的取向;第二,考据学方法不能领会国学的全部内涵;第三,考据学所讲求的证据,并非学术的必由之途。前两点为当时大多数新史学批评者所同具,而第三点似为张尔田所首发。
(二)对疑古思潮的批评。胡适在《国故研究的方法》中提出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态度。(29) 这种怀疑的态度为顾颉刚所继承,顾氏并结合崔述等人的辨伪传统和今文经学的影响,发展出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运动。对古史的怀疑态度虽不能说是整个新派史学的共同特征,但是因为顾颉刚所领导的古史辨运动中的广泛影响,“疑古辨伪”之风一时有弥漫史学界之势。疑古思潮的盛行,也引来各方面的强烈批评。例如王国维便指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不分: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又云:“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30) 即隐将矛头指向疑古思潮。钱穆在1939年写成的《国史大纲》中亦称顾颉刚的古史观为“极端的怀疑论”,应加以修正。(31)
针对当时盛行的疑古辨伪思潮,张尔田亦写有《论伪书示从游诸子》(32) 一文展开批评。他一方面指出古史伪造之说,使中国文化发展成为无源之水,在理论上不通。另一方面他并不完全否定“疑古”,认为“疑古可也,伪古则不可也”。“疑古”亦须有断限,所当疑者,“文字前后之参差,年月人地彼此之殽错”,所不当疑者“若夫群经有家法,诸史有义例,一时有一时习尚之殊,一时有一时信仰之别”。而“伪古”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以辨伪之见观书,必无一书可读,以辨伪之见论事,必无一事可信”,“如此则不但颠倒理论,抑且变乱事实,事实一经变乱,则不但无经抑且无史,直无异取吾国三千年文化而摧拉之也”。可见,他所主要关心的是疑古学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潜在破坏作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他指出辨伪学者存在“拘牵后代时势”以观察古人的倾向,在方法上多用“反证”,而忽略“本证”。此外,他认为疑古学者的根本毛病是“以外国之心理治中国之书”,以至于“由不了解而妄疑,由妄疑而执,而又有现代化观念先入为主”。针对这种风气,他提醒学者应该注意治学态度问题,提出“治学莫要于治心,治心之道无他,一言以蔽之曰‘玄囿’,务使吾心依乎其位,而不为风会所左右”。这对于新派学者的治史态度提出了质疑,强调新学者在治史时存在着先入之见。同时,为了扭转当时新史学中盛行的疑古风气,他提出研究历史“宜恕不宜苛断”的观点,认为“我辈居今日而论古史,宜恕不宜苛断”,因为“古史未必尽非,而今之所测亦未必尽是”,并进而主张“与其改之而失,毋宁留之而失”,因为“留之而失,是非尚可考索;改而失之,则罅隙全泯矣”。(33)
三、应关注近代“传统派”的研究
以上我们从阐发中国史学传统和对“新史学”的批评两方面,阐释了张尔田的主要史学思想,以窥近代中国新旧史学思想的激烈冲突之一斑。在史学宗旨上,张尔田坚持“史学以记述为本”的传统史学观念,这导致他对新式考据史学和解释史学的激烈的批评;在传统史学日趋式微的形势下,他试图阐发传统史学方法和体例的内在精蕴,探讨“著史”之法,以延续史学传统;为了应对新史学疑古倾向的冲击,他提出了“论古宜恕不宜苛断”的治史观点。总而言之,张尔田是传统史学的守护者,也是近代“新史学”的纠偏者。虽然他游离于史学发展的主潮之外,史学观念未免保守,但他对新史学弊端的批评及其对传统史学的阐发,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在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过程中,新、旧史学的论争一度颇为激烈。张尔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吴虞日记》记载,“(马幼渔)又以张尔田荐朱毅信示予。尔田尚有给黄晦闻一信,大致谓北大诸人,渐趋于新,渠辈古调独弹,当坚固团体,以求自保地位”(34)。可见早在北大任教时期,张尔田已经是立场鲜明的旧派了。(35) 此后,作为学坛老辈,他成为新派学人的著名反对者。这样的立场,一直保持到晚年,并使之成为传统派的重镇之一。著名史学家、文化保守主义重要代表钱穆,晚年曾回忆到,“以余一人所交,在北大如孟心史、汤锡予,清华如陈寅恪,燕大如张孟劬,其他南北学者如马一浮、熊十力、钱子泉、张君劢诸人,余皆尝与之一一上下其议论,固同对适之有反感,而中央大学教授柳翼谋,明白为一文,力斥章太炎、梁任公与胡适之三人”。(36) 显然,在钱穆眼中,张尔田是当时旧派史家重镇之一。他的观念虽然保守,但在新旧学人中却并不乏知音。如《学衡》杂志主编吴宓就曾感叹,“今又恨不早二十年遇孙(德谦)张(尔田)二先生,则不致游嬉无事,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37) 此外,杨树达、夏承焘等人亦皆对张尔田尊重、推崇有加。(38) 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中心是从西方引进新思想、新理论,使那些坚持中国传统的学者大都退居边缘,成为所谓的“失语群体”,(39) 史学领域也不能避免这种现象。张尔田的形象遂逐渐从现代学者的学术视野中淡去了。
早在1939年,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中国近代史学有三派:“传统派”、“革新派”和“科学派”。尽管现在对近代史学流派有这样那样的划分,但是钱穆所说的三派,当时却实有所指,不容否认。
大致来说,近代中国史学流派纷呈,代际转化极为迅速,总体趋势是追随西方,“新史学”占主流地位。这使后来的学术史研究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新派”史家。大陆学者的中国近代史学史著作如此,海外的相关研究也如此。但是,正如桑兵所指出的,民国学界并非新派独大,老辈学人依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40) 因此,在回顾20世纪史学史时,也开始有部分学者关注传统派史学家的影响。如唐德刚就将中国传统史学派、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同列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41) 王尔敏则在唐德刚的基础上,提出了“主流”与“非主流”的概念。
尽管研究者对近代史学流派的划分和判断各有不同,对于传统派史家的命运和价值的判断亦各有不同,但却提示我们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应该扩大视野,关注传统派史家和非主流史家的研究。20世纪史学的主线是科学化和西化,这使我们对传统史学批判有余而理解、继承不足。在中国人文研究摆脱西方中心取向而“再出发”的今天,(42) 对传统史学进一步深入的考察,或许会给我们新的视角。从这一点来看,回顾清末民初“传统派”史家的思考与实践也许不会没有意义。
注释:
① 丘炫煜:《章学诚文史校仇学对后世的影响——以张尔田、孙德谦为例》(台湾:《国立侨生大学先修班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是较早从学术史角度专题论述张尔田的文章,可惜因两岸悬隔,虽经多方搜寻,迄未得见。近期,台湾佛光大学朱振宏博士为笔者复印邮寄此文,特此感谢。关于张尔田的师友交游情况,张克兰的《张尔田学术·师友叙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第6期)可参看。关于张尔田参与《清史稿》纂修情况,请参看张笑川《张尔田与〈清史稿〉纂修》(《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② 关于《史微》一书要旨,可参看严寿澂:《〈史微〉要旨表诠》,载于张尔田著、黄曙辉点校:《史微》,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关于《史微》在清末民初学术思想史上的影响、意义和地位及其与《文史通义》的关系,参见拙文《经史与政教——从〈史微〉看张尔田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解读》,《史林》2006年第6期;《传承与衍变——〈史微〉与〈文史通义〉之比较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③ 杨翼骧、乔治忠二先生曾将中国史学理论体系概括为史学宗旨、史学地位、史学方法、史家标准、治史态度、修史制度、史籍优劣、史学流变等概念范畴,本文对于张尔田史学思想的分析借鉴了其中部分概念。(参见杨翼骧、乔治忠:《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载于杨翼骧《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8页)。
④ 《史微·凡例》第2页,民国丛书第五编,本书据五孱守垒1912年版影印。
⑤ 张尔田在《与大公报副刊编者书》之二“论史例”中曾说:“中国历史,大都专记治乱兴衰古今存亡之道,以供宰世者之用,居大多数,与历史哲学相近。(自注:此指古史而言。若后代族史已渐离其本质而偏重叙事矣。)”也大体指的是这个意思。载《学衡》第66期,1928年11月。
⑥ 杨翼骧、乔治忠:《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收入杨翼骧《学忍堂文集》,第392页。
⑦ 张尔田:《论中国文化及其宗教道德》,《汉学》第一辑,1944年9月,第17页。
⑧ 张尔田:《论中国文化及其宗教道德》,《汉学》第一辑,第17页。
⑨ 张尔田:《论中国文化及其宗教道德》,《汉学》第一辑,第17—18页。
⑩ 张尔田:《论中国文化及其宗教道德》,《汉学》第一辑,第18页。
(11)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149页。
(12) 张尔田:《答梁任公论史学书》,载《遁堪文集》,王钟翰辑录,民国三十七年排印本。
(13) 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民国人物碑传集》,第451页。
(14) 杜维运:《王夫之与中国史学》,载于《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5页。
(15) 张尔田:《史传文研究法》,《学衡》杂志第39期,民国十四年。本节引文除特别标注之外,皆引自此文,为行文简洁,不再一一标注。
(16) 《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17) 杨翼骧、乔治忠:《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载于《学忍堂文集》,第395页。
(18) 《学衡》第66期,1928年11月。
(19) 《与大公报副刊编者书》共六篇,一刊至三刊登于《学衡》第66期;四刊至六刊登于《学衡》第71期,1929年。
(20) 《史微》“目录”后张东荪校记。
(21) 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32—35页。
(22) 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53—54页。
(23)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0页。
(24) 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111页。
(25) 《与大公报副刊编者书》之五“论研究古人心理”,《学衡》第71期,1929年,“文录”第9页。此信写于1929年4月13日。
(26) 张尔田:《塾议一》,《遁堪文集》卷一,第12—13页。
(27) 张尔田:《与人论学术书》,《遁堪文集》卷一,30页。
(28)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29)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载于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版。
(30)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1章“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1)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
(32) 张尔田:《论伪书示从游诸子》,《遁堪文集》卷二,第6—10页。
(33) 张尔田:《答梁任公论史学书》,《遁堪文集》卷一。
(34) 《吴虞日记》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5页,“1921年8月14日”条。
(35)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36) 钱穆:《维新与守旧》,《钱宾四先生全集》二十三册,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9页,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3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192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0页。
(38)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83、84、85、91页;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31页。
(39)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0) 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载于《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41) 唐德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载于《传记文学》第51卷第4期。
(42) 余英时:《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载于《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标签:历史书籍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读书论文; 春秋论文; 清史稿论文; 新史学论文; 纪传体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东周论文; 历史学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