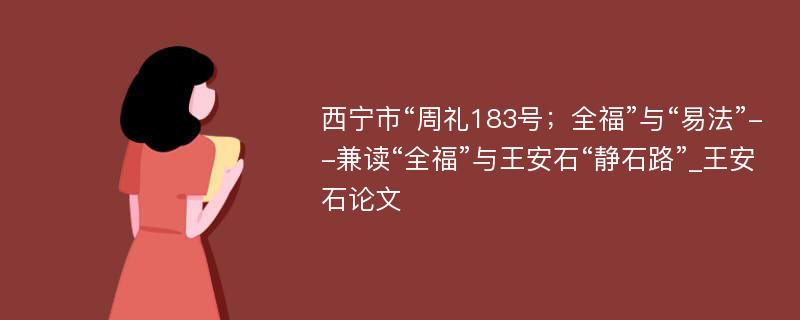
《周礼#183;泉府》与熙宁市易法——《泉府》职细读与王安石的经世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礼论文,理路论文,王安石论文,泉府论文,熙宁市易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14)04-0023-11 北宋熙宁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史学界对此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①。然而,既有论著侧重讨论市易法的内容、运作及各种拓展性课题,对法度本身的深度解读及其学术内涵则未予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学界对王安石政治改革背后的“学术立场”和“经术体系”仍有隔膜,尤其是王安石是否以经术“文饰”政治的相关争议始终存在②。这层障碍的“突破口”在于如何评估王安石之学术与实践:可否抛开其学术思想体系而单论变法?王安石所申明的“学术立场”③是否应该被充分重视?新学与新法之间有着怎样的深刻关联?继而可追问:王安石以政治实践为特征的《周礼》学在新法中如何呈现?其中的政治理论如“泉府法”、“比闾什伍制”等如何被解释、应用于变法实践?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王安石为何如此执着于《周礼》制度?是“复古”“法古”,还是“文饰私意”“自我作古”,抑或还有更深层的内涵? 总的来说,学界对熙宁新法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普通政治史、制度史层面,或徒研究其政而不考其学,或只论其学而不及其政:一方面,研究者不太倾向于站在王安石立场上体会其反复申明的“学术本位”;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者对王安石经术体系的认知相对欠缺,对新法政治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的经术义理、样态不够敏感,人云亦云地认定其为一般性经学参考甚至是比附经义,而忽略了王安石作为学者型政治家的特殊意义;此外,由于政治、经济观念的差异或局限,也会影响学者对王安石学术、政治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因此,新学对熙宁变法的渗透与影响、新法中所呈现的《周礼》学体系——其理念、创设及其在现实中的困境——始终未能得到正视,而其学术在熙宁政治中的生长、呈现与作用至今也未被充分地讨论过。 本文致力于这一薄弱区域,并适度引入传统意义上的“经史相参”方法④。该方法实本于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以“经”释“法”的基本思路。笔者力图抛开各种定势思维,回归于王安石本人的“学术立场”及新法解释——考“学”以观“政”,论“政”以知“学”。本文首先从王安石经术体系及政治实践的最基础部分——“释法”(即王安石等人对新法做出的经学解释与义理解释)层面说起。以市易法为例,探究市易立法中的“泉府”叙述,对照《周礼》泉府原初的经学语境,并以此为“纲”来分层次讨论王安石的市易理念。 一、《周礼》泉府与熙宁理财之法 《周礼》学在王安石政治、学术体系中独树一帜,倾注与重视程度非他经可比。而均输、青苗、市易等理财法度,则被王安石明确定位于是对《周礼》泉府法之继承,其间争议颇多的“开阖敛散”、“泉府赊贷”、“国服之息”、“国用取具”说皆出乎此。 (一)熙宁期间以泉府释法、争议以及相关政治事件 熙宁期间与《周礼》泉府相关的立法辩论等政治事件众多,现将主要材料罗列于下,以简单考察新旧两派对泉府法的关注点或争议点。 1.熙宁二年二月,朝廷议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问使陕西钱重及边谷积储之法,王安石为之首论泉府,云:“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又云:“至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然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先王之法,更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⑤ 2.熙宁二年九月,行青苗法,后又置常平官。“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⑥。其介入者有韩琦、欧阳修、文彦博、范纯仁、李常、孙觉、范鎮、苏辙等。因官方以泉府释法,故大臣奏疏中对泉府说法多有不同程度的回应⑦。 3.青苗法致内外异论,王安石请以韩琦疏⑧为标靶“画一申明”常平新法⑨,故有“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⑩,即“制置司疏驳事件”(11)。韩琦转而又疏驳之,此即著名章疏《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由此,王安石与韩琦、新旧两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针对泉府释法的“隔空”较量。 4.熙宁五年十一月,因市易务卖果实事件,神宗以事之繁细质问王安石。王安石引“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12),说明市易收购、市易零售、市易征商之合理性。 5.熙宁五年十一月,议论市易务果子行事,王安石录“泉府”、“廛人”事白上,曰“此周公所为。”(13) 6.熙宁七年二月,神宗论财用不足及理财之方。王安石以《周礼》征税系统(泉府征商及廛人“五布”等)论市易征税之合法性。并言现今问题不在征税过多,而在于“不均”与“兼并”(14)。 7.熙宁初,神宗主青苗法,曰:“此《周礼》泉府之职,周公之法也。”其后有司马光比之以王莽之法。[1](p.92)熙宁七年四月,言及市易利害,神宗论市易之本旨在于《周礼》泉府之意。元丰五年七月,再次申明(15)。这三次为神宗单独议论市易与泉府之关系。 8.泉府法在王安石文集中亦有多处议论,如《上五事札子》主论保甲、市易、免役三法“师古”之意,其论市易曰:“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贯之,令民以岁入数万缗息。”(16) 以上诸条可大致勾勒出熙宁时期朝野对《周礼》泉府的集中讨论,这类议论在变法前期频次较高,甚至一度因王安石与韩琦之正面交锋而成为常平论战的主题之一。新法出台初期,异论方兴,官方急需申明法意,作为立法依据的泉府法自然会被推至台前议论。对新法决策层而言,《周礼·泉府》的意义是多元的,既是均输、青苗、市易等立法依据,也是整个熙宁理财的宏观方向,从根本上说则是王安石实践型《周礼》学的主体内容之一。 (二)泉府与王安石之理财逻辑 熙宁新法以理财为中心。王安石所述“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17)五事中,青苗、免役、市易三法直接涉及自上而下的财政体制改革,和戎与保甲二事亦事关理财。经制横山、拓土洮河、汉蕃市易等须以成熟而稳健的军事财政运作为保障;保甲法的推出则实现了军事资源、军事财政的重新分配与转移(18)。故新法始作,王安石首推理财议案。早在议置条例司前夕,神宗与王安石议论陕西军储时已现端倪。在北宋,军事财政与国家财政成为一体(19),陕西军储又是缘边军事之基础,由缘边军事财政(粮储、通货、物流等)的现实诉求而引发的对国家财政运作体制的重新考量,继而导向相应的理财方案,体现了新法决策层面最初的理财逻辑。同时,王安石也将这层理财逻辑更加的明确化、“义理”化,《乞制置三司条例》云: 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20) 此段文字点明了王安石经制理财的精髓。以“义理”论政施政是其高度理性化政治思维的体现。“义理”(或“理”)一词在熙宁史料中频繁出现,凡讨论关键问题时大有一种事事言“理”、处处言“义”之感(21),体现在理财方面,则别有一套谨严有序的政治逻辑。首先,在经义上,申明国家理财的意义。以孟子“义利”之辨为理财“正名”,“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22)又《周礼》冢宰以九职任民、均节财用,理财乃为国本。“任民以其职,然后民富;民富,然后财贿可得而敛;敛则得民财矣;得而不能理,则非所以为(义);均节财用,则所以为义也;治其国有义,然后邦国服而其财可致也;能致邦国之财,然后为王者之富;富然后邦国之民可聚,聚而无以系之则散,系而无以治之则乱”[3](p.49)。或以《孟子》或以《周礼》言,皆是王安石“理财正辞”之意(23)。其次,理财当有途径、有重点,前引文字点明了其基本“着力点”——财、义、均、通、制、权、术。这些“着力点”通过熙宁千丝万缕的新法体系得以展现。第三,泉府法为上述“着力点”提供了原始依据,王安石称之为“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总之,不管是“义理相通”还是“精神相契”,泉府法意与当下之理财诉求在王安石这里得到了高度统合,使其成为政策理论基础的不二之选。 关于泉府法意、泉府精神与熙宁理财之间的内在关联,需要通盘考量均输、青苗、市易法等,将另文专述。前文已简述泉府的理论意义与新法的理财逻辑,下文则需要从经典文本及制度细节入手,通过对照市易法内容以及王安石的经义解释,在具体政治语境中解读泉府法的基本原理。 二、《泉府》职细读与王安石的市易论证 《周礼·地官》大司徒职下有“司市”一官,为市官(24)之首,其法最后一条曰:“以泉府同货而敛赊。” 郑玄注云:“同,共也。同者,谓民货不售,则为敛而买之;民无货,则赊贳而予之。”孙诒让的解释更为具体: 敛谓敛之入官,赊谓贳之与民。市货不售则敛之,民有急求则贳之,或敛或贳谓之同货,所以通有无而齐赢绌之数也。……凡市官以公货同之于民,其事掌于泉府,而司市亦总其成焉。[4](p.1059) 郑玄以“共”释“同”,孙诒让加之以“通有无而齐赢绌”之说,实际上,“同”、“共”、“通”、“齐”四字可在此互训,见泉府通融有无之意。货之不售则物贱,民间稀缺则昂贵,而泉府或敛或赊的“同货”之法,通过政府有效营运,将所敛市场“不售”物货(孙诒让谓之“公货”)赊贷与所需之民,是为古时物资融通、互补、周济之法,亦即后世的平准功能。在物质资料并不充裕的时代,泉府的意义在于借助敛散、疏导、流通来平衡各种物质资源。 关于这一点,《周礼·地官》“泉府”职记载更为详细: 泉府(一)掌以市之征布,(二)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三)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四)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五)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六)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 马端临《文献通考》将此段文字置于“市籴考”之“均输市易和买”之首,意将泉府法作为“开阖”、“敛散”、“轻重”之理论始源。那么,市易法度如何“祖述”以上文字?如何在具体实践中承其“意”?以上问题都需要通过泉府制度、市易运作并结合王安石对泉府法意的阐释细细斟酌。为方便行文、理清条目,以下就前引泉府职内容依数字所标顺序逐条阐释。 (一)泉府征商与廛人“五布”:市易征商的合法性兼及郑侠奏议中的市例钱问题 “掌以市之征布”者,布,泉也,钱也。征布,即《周礼·大宰》九赋之“市赋”,如后世之商税。泉府负责敛藏各种“商税”,与另一市官“廛人”构成“官联”(25)。《周礼》廛人职云:“廛人,掌敛市絘布、緫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五布”即五种商税。《孟子·公孙丑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赵注:“廛,市宅也。”王安石认同先儒以国中之地为廛,故释“廛而不征”者,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26)。孙诒让云:“凡民居在里为民宅,在市为邸舍,其区域并谓之廛。”[4](p.1083)因而,有学者释“廛布”为地税。江永《廛人》注云:“絘布者,市之屋税;緫布者,货贿之正税;廛布者,市之地税也。”[4](p.1081)质布,王与之云:“质人所税质剂者之布也,质人买卖之质剂,如今田宅,官给券以收税,谓之质布。”[4](p.1082)罚布,郑注云即犯市令者之罚泉也,即罚款之类。《廛人》市赋五布,并入泉府而藏之。泉府有“征”、有“藏”,有“泉”、有“物”,通融而藏用,构成了泉府“同货”——敛、赊、贷——的财用基础。 王安石以泉府论证市易,都大提举市易司实际上充当着操纵“开阖敛散之权”的“泉府”角色。至少从运作上看它同时具备泉府的两项基本职能:商税征收与物货赊贷。物货赊贷是市易务承担的首要职能,也是市易继承泉府法的最直接体现。不过,决策层对都大提举市易司有着更高的期待,这是王安石精心培植的、以“开阖敛散”为杠杆、操控驾驭国家财政的“经济官衙”之一[2]。所以,在市易法实行后的几个月内,在京市易务(即都大提举市易司前身)就顺利接管了榷货务、都商税院、杂买务、杂卖场等,也就意味着它掌控了包括在京商税征收、仓储、杂卖在内的多种重要职能。 为表达市易征商及市易零售的合法性,王安石引《周礼》征商为神宗说法: 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27) 这是针对外界对市易务买卖果实等质疑,王安石所回应的一段文字。其中王安石引述泉府以同货形式向民间收敛滞物“以待买者”,是针对市易收购与零售,下文另述。这里主要探讨王安石用《周官》征商来论证市易征商之合法性。《周礼》征商,在地官司市、泉府、廛人等职中有明文记载,前文已述。那么,市易征商又是如何?王安石怎样从理论到实践论证其合理性?在回答这些问题前,本文先以争议较大的“市例钱”为中心,对市易征商作简单概述。 市易征商前期包含三部分内容,市易息钱、罚息以及市例钱。市易法通行借贷模式,作为贷款方,官方向商户收取息钱以及逾期之罚息无可厚非。熙宁初,王安石与韩琦辩论“青苗息钱”时,明确以泉府借贷之“国服之息”以及息钱的现实取用来论证官方借贷收息之合理合法,详见下文“国服之息”条。相比之下,市易征商中最值得争议的当属“市例钱”以及后来为行免行法而出现的“免行钱”。后者即行户缴纳一定的免行钱可免去祗应,免行与否皆取自愿,类似免役钱,是一种替代性缴费,构不成新摊税种。唯独可议的是市例钱,历代学者多引郑侠奏议,将其作为一种商业税之外的附加税,批评其苛细扰民。奏议内容如下: 建言者以诸门及本务税钱额亏折,皆是官员饶税过多,而吏人受财共偷瞒,不知乃为市易拘拦商旅入务官买,以致商旅不行,税乃大亏也。遂立条约,专拦皆有食钱,官员不得饶税。专拦取钱依仓法,官员妄饶税,并停替,仍会问诸处,每商旅纳官税一百文,及专拦所得市例钱几何。诸处申,约官税一百,专拦等合得事例钱十文。官中遂以为定例,每纳税钱一百文,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以给专拦等食钱。已而市易司作弊,于申收事例钱项,即声说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为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谓所收之税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钱十文,只如苧麻一斤收钱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却问客人别要事例钱一十文。(28) 郑侠这段批评提供了诸多信息,文中晓示:市例钱(29)面向客商收取,收取原则是“每纳税钱一百文,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用途为“给专拦等食钱”。地方各级税务有栏头(专拦)若干,在走私路口稽查商税,偷税漏税者由栏头补收(30)。专栏在获得“食钱”的同时受仓法约束。可见市例钱是据商税按比例征收的专门管理费(31)。商家缴纳这笔钱,使市场中有了权责明确的管理者,不仅可以防范偷漏税,监督市场秩序,同时也将胥吏纳入规范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吏人从中上下其手,刻剥诛求,这和熙宁时“禄胥吏”的整体理念是一致的,也体现了市例钱的规划用途与“有偿性”。此外,因其“食钱”性质,郑侠又别以“事例钱”称之,明确体现了市例钱的“专款专用”性质。因此,从其法理上看,不便轻易将其认定为是凭空增加、刻剥商旅之恶税或附加税。(32) 再仔细阅读郑侠所奏,这篇看上去大肆声讨市例钱的疏文多有可疑之处。内提到三种有关市例钱的收取规定:其一,每纳税钱一百文,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为“官中定例”;其二,市易司“声说”“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即市例钱十文起征;其三,“及法行”,原“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变成“所收之税(商税)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钱十文”。郑侠因而举例,“只如苧麻一斤收钱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却问客人别要事例钱一十文”,这看上去非常荒谬,如何商税是五文而市例钱却要达到十文?岂不是市易司公然作弊?此弹劾看似有理,但其中包含着不易察觉的“个案混淆”和“假象制造”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按市易司规定,每纳百文税,缴六文市例钱,不足十文按十文征收。以苎麻为例,按郑侠提供的信息,一斤征收五文税钱,则二十斤苎麻纳税百文,收六文市例钱,至三十三斤左右,才收十文市例钱。那么,市例钱不足十文也按十文征收的状况仅限于交易量低于三十三斤苎麻的客商。即便如此,十文起征原则仍有可能对小本买卖的走贩有所不公,而后来市易司规定二十文以下的市例钱免收(33),已经堵上了这个漏洞。 第二,郑侠的核心批评指向市易司在市例钱起征点上“作弊”。原规定“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在法行之后变成“所收之税(商税)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钱十文”。这样的“作弊”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可能?“只如苧麻一斤收钱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却问客人别要事例钱一十文”,如郑侠所说无误,那么,除非一个客商携带两斤苎麻(或等价物)以下货物来市易务投卖时,才符合他说的“缴税不足十文”状况,因为两斤苎麻的商税已足十文。如果商人所携货物在二斤到三十三斤之间,则收十文市例钱虽嫌多,却依然符合按“市例钱”而非“税钱”不足十文收十文的规定,市易司“作弊”一说就无从谈起。 在现实市场中,苎麻这样的货物,客商(商旅)动辄百、千、万斤买卖,郑侠所攻击的客商携“两斤以下苎麻”(商税不超十文)投卖的情况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郑侠奏疏的问题在于其制造了一种“理论”或“极端”可能性,并以此作为“个案”来攻击市易司、市例钱之弊。我们姑且不怀疑其为“公平”起见,站在客商立场向政府讨说法,但如此“举证”则很容易将常人思维导向那个背离常理、不合情理的“比例”——市例钱和商税发生了逆向的2∶1的比例关系,这不可能不引起众人的“恶法”情绪。 回过头再来看王安石借《周官》征税体系对市易征商的大体原则做出申明: 今古非特什一之税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其絘布、总布、质布、廛布之类甚众。关市有征,而货有不由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古之取财,亦岂但什一而已。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耳。(34) 结合两段关于《周礼》征商的引文,王安石遍举泉府、虞衡、廛人五布、关市之征来说明征商自古已有,并未设定下限,性质与酒税法相同。且与古时相比,现今问题不出在征取源头——征税过多,而在于分配——“不均”与“兼并”问题。而事实上,分配之不均与兼并问题从政府调控来看,则有必要通过征取环节来调节(35)。因此,针对现实经济运作而面向商人的不同形式的征取(市易息钱、罚息、市例钱、免行钱),在王安石看来合乎情理。而从宏观角度来看,市易运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市场管理的多种诉求,促成了市易法中不同形式的征商。市例钱的征收因事关“吏禄”,实际上又联动着熙宁另一套法度——“吏禄仓法”。可以说在市易征商问题上,王安石在经义、理念、现实分配方面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解释。 即便如此,市易零售、征商依旧被反对者斥为琐细烦碎、有辱国体之事,王安石如何为这种新型的政府经济行为“正名”?政策条例是否因其繁琐细碎就没有了存在的道理?王安石云: 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政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则须爪甲。体有小大,所任不同,然各不可阙。天地生万物,一草之细,亦皆有理。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 在经学解释后,王安石讲述了“细大并举”和“细”处之“理”,以人身肌体、天地万物来比拟国家的整体运作,意为国家制度政策方面的制定与运作需要通过这种“全局性”思维完成。“一草一木”皆有其义理,看似琐细之事,在国家机能的发挥上往往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故王安石言:“细大并举,乃为政体。” (二)“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官方收购模式的承续与拓展(36) 泉府“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即泉府收敛滞销物货,这是泉府同货法的第一步。在外界质疑市易务买卖果实时,王安石亦通过此条证明市易收购的合理性,“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不过,泉府法只是提供了一种“政府收购”的经济模式,市易法则根据具体复杂的经济环境对“官方收购”形式有了更加丰富的措置与延展。参看熙宁五年中书所奏市易法: (1)欲在京置市易务,监官二员,提举官一员,勾当公事官一员,(2)以地产为抵官贷之钱,(3)货之滞于民者为平价以收之,(4)一年出息二分,皆取其愿。(5)其诸司科配、州县官私烦扰民被其害[者],悉罢之,并于市易计置,(6)许召在京诸行铺户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它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为一保。(7)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8)勾行、牙人与客人平其价,(9)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钱买之。(10)如愿折博官物者仍听,(11)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12)以上并不得抑勒。(13)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寔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14)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37) 仅根据法条判断,所标第(3)条“货之滞于民者为平价以收之”和第(7)条“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与官方收购直接相关,但所对应的收购行为不同:前者针对个体商户,类似面向散户的收购;后者则面对客商,属于官方大宗收购。 官方收购程序在整个市易体系中有什么功能或充当什么角色?泉府收购“滞物”用于同货、平准,市易收购在原理上与其相似。如果将市易运作视作一套完整的经济程序,那么,收购处于程序中的“上游”,而中下游则包涵由收购引发的诸多经济职能。整套“市易收购”所涵盖、衔接的内容有: 第一,明确收购意向,即“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 第二,专业经理人根据市场定价,“勾行、牙人与客人平其价”。 第三,根据本地行户市场需求订购,“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钱买之”。 第四,允许客商折博官物,即官商之间形成的现货市场交易,“如愿折博官物者仍听”。 第五,进入抵押程序,允许客商“分期付款”,依半年或一年送纳。“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 第六,规定利息,采取相对低息模式:“若半年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 第七,以官方诸渠道收购的物货为基础,开展平价零售交易:“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寔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 第八,助力科买,利用市易务在市场、物资、信息方面掌控力与便捷性,作为其附加型业务。 这是市易收购所覆盖、延伸出来的各种经济行为。在市易收购问题上,王安石并未在运作细节上赋予更多的经义解释,只是从原理层面说明市易收购来自于泉府收购理念。对王安石而言,“经术”走向“世务”的理念传承(“法意”)才是市易法整体汲取的关键因素。从宏观层面看,王安石从“万变不离其宗”的泉府法那里——以“官买程序”为结点,结合了现世多方面的经济因素和经济机构职能,对官营经济进行全面深化与拓展。市易收购致力于在政府掌握的优势资源和平台——仓储(官方仓储空间)、信息(客商与行商的供需诉求)、交通或物流(一定程度上利用客商的运力以及首都开封在全国经济网络上的枢纽作用)、专业经理人(牙人、勾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巨大的、通过市易收购完成的“物资资源库”,从而实现政府层面的各项经济职能:采购、借贷、分销、折博、零售、科买等。此处,我们可以充分联想到同样作为“库源”的敛藏机构——泉府,它的原理、功能与运作机制,在千余年后的熙宁新法中隐然复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市易法条规定的是法度的基本模式与预期走向,现实中具体运作、发展与变异,限于主题和篇幅,皆另文分析,不再展开。 (三)“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定价程序以及市易零售 郑司农云:“物楬而书之,物物为揃书,书其贾,楬著其物也。”“揃”、“笺”声义略同,《说文·竹部》:“笺,表识书也。”又《说文·木部》:“楬,楬橥也。”故孙诒让疏云:“物楬而书之,谓每物揃书其贾直于杙,附著其物之侧以表识之也。”[4](p.1096)泉府收拢市物后再次出卖需要定价,因而此条可以视为泉府之“定价程序”。 市易运作中,既有针对客商的物货收购、给予行户的物货赊贷,又有面向大众的零售业务,无论是收购、赊贷还是零售,自是免不了类似泉府的定价程序,所谓“勾行、牙人与客人平其价”(38)。市易务聘请牙人作为经理人帮助官方与客商协商收购价格。牙人是市场交易中从事媒介性活动的经纪业者,一方面,牙人帮助斡旋双方买卖,协商评定价格,或直接代客商卖;另一方面,在买卖过程中,保证公证交易,作成合法契约文书,呈报官府,并代官方收取牙契税等。由于对价格、流通、仓储等信息了如指掌,牙人在定价问题上有实质性的发言权。而在买卖过程中,需要立契的对象交易众多,买卖双方与官府之间需要进行频繁的交涉,因此牙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承担了双方经办人的角色(39)。 本条王安石议论的关键不在于定价问题,而在于“以待不时而买者”。郑注云:“不时买者谓急求者也。”孙诒让云:“谓来买无定时,急求待用,若下祭祀、丧纪是也。《汉食货志》载王莽时,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先郑云急求,即刘歆所谓欲得者也。”[4](p.1096)不管是百姓之“急求”还是“欲得”,“以待不时而买者”即泉府将收拢滞物重新投入市场,这就涉及到市易法的另一个争议话题——市易零售。于是,因外界对市易务买卖果实、梳扑等质疑,王安石云:“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也就是说泉府收拢物货,并不只为平准市场和自我消化,泉府运作亦有一个完整的从“收购”到“投卖”、“分销”的程序。在市易法中,这个重新面向市场的投卖与分销程序则透过行户赊购与市易零售来实现。 原则上讲,官方收购滞物之后因市场之所需而进入零售阶段,如果是收购“滞”货而“待”买者,说明是由政府承担市场流通中最困难的部分,并负担仓储和等待买家的时间成本,这样就必然导致整买零售。其售卖“滞物”“不言几钱以上乃买”,意为《周礼》未言明像果实、梳扑等碎细之物不能收购,零售额度未设下限,故王安石以为市易务未尝不可“介入”部分中小型零售业务。若其商品的确处于“滞销”阶段,那么,政府的批量收购无疑会助其解决成本与销路问题。从经济原理上看,即是将官方资本注入市场,提供市场最急需的“流动性”和“秩序”(40)。 法理上固然如此,然而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市易务能否完整地承担起收购滞物、疏通市场、平衡供需之责而非仅仅为其营私、收益考虑,并在零售过程中合理地把握政府营运与个体零售之间的关系,则需另当别论。法意之本善未必能够尽数落实于操作过程中,这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而言都是莫大的难题。 (四)“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抵押程序 郑司农云“抵,故贾也”,郑众意为泉府当以收购原价卖与所需者。郑玄不以为然,以为“抵实柢字,柢,本也。本谓所属吏主有司是”,即以“抵”为所在地之有司(管认机构)。这个解释完全根据对文排比而来。清儒并不认同郑玄注,江永云:“自比长、邻长以上,皆可谓之主有司。其为公邑稍县都,仿乡遂之制,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与食采大夫然后谓之主也。从泉府买一不时须之物,必关白大夫,恐难乎其为买矣。”[4](p.1097)此说已对郑玄注构成有力反驳。 此处“抵”依郑众注释为“故价”,或依照郑玄释为“所主吏”都显牵强。郑玄不取郑众之意,而清儒又觉得郑玄解释不妥,那么“抵”的意思究竟为何?笔者只能借助“抵”在早期典籍所呈现的意思稍作推测。《管子·小问》:“寡人之抵罪也久矣。”尹知章注:“抵,当也。”《战国策·中山策》“臣抵罪”之高诱注以及《史记·汉高祖本纪》“伤人及盗抵罪”之司马贞索隐引韦昭云均以“当”释“抵”。“当”即相当之意,回过头再看《泉府》“买者各从其抵”,此“抵”似亦可解为“当”,即相当之物、抵当之物,在行文中可理解为后世的物产抵押。泉府赊贷二法,不管是赊买或是借贷,都存在延迟支付问题(41),理论上应该有相应的担保行为或物业抵押。 那么熙宁立法者对泉府此条又是如何理解?中书所奏市易条文“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与泉府法条中的“买家各从其抵”意思接近。又根据当时其他官方行文,确实也将泉府职“各从其抵”之“抵”理解为“抵当”之意。比如述“太府寺”之职: 货有不售,则平其价鬻于平准,乘时赊贷,以济民用。若质取于官,则给用多寡,各从其抵。(42) 此处完全是照搬泉府“各从其抵”了,元丰改制后,太府寺统摄原都大提举市易司职能,其所述“各从其抵”自然是通乎熙宁市易法条款所规定的“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之意。从逻辑上讲,买者根据抵当物力多少赊买,比买者依泉府收购原价购买物货或者买者各从其所主有司,都要合理得多。市易法常用的抵当物力主要包含田宅契书、金银等有价物,若无抵押,前期借贷亦可通过结保来实现物货赊请。 (五)“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泉府赊法与政府“赒济” 这一条主要讲赊买问题。根据经文及注疏,赊买之法限事、限时、有抵、不取息。孙诒让云:“凡赊,从官买物,而约期以付贾,不得过旬日、三月,而不取息。”[4](p.1097)王莽复古改制,照用此法:“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颜注云:“但,空也,徒也,言空赊与之,不取息利也。”[9](p.1182)较之泉府法,几乎是文、意皆合了。只是泉府用收购之滞物与民,莽法则用工商之贡赊贷。 赊买属延期支付,即先期消费官方物货,后期限时偿还,形式上与贷事并无本质区别。因而泉府赊贷法在后世往往并称,合指借贷之事。然而赊法不收息,又必关丧纪风俗缓急之事,则更像是官方向民间展开的针对性的赒济项目,因此只设基本抵押,所限时间内不取息。 熙宁市易法虽没有针对特定事项“不取息”,但对于葬丧祭祀等事关风化的缓急之事也有类似的关照。熙宁七年四月,参知政事冯京曰:“开封祥符县给散民钱,有出息抵当银绢米麦缓急丧葬之目,如此七八种,小民无知,但见官中给钱,无不愿请,积累数多,实送纳不得。”(43)市易赊法最初规定:“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44)可见市易结保赊请之法门槛较低,三人结保即可赊请钱物,且所设二分之息也合情合理。普通百姓自然“无不愿请”。由于事关缓急之需,请领之时往往难以顾及之后的偿还能力,这样无形中也给官方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与压力,造成“积累数多,实送纳不得”。元丰元年,都提举市易司王居卿以百姓借贷多不能偿还而建议改制。于是,结保赊贷模式罢去,一律采取契书金银等抵当模式,并适度降息(由原来的二分降至一分半,后更降至一分二厘(45)),无抵当者不再给予贷款。 (六)“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国服之息”之激辩 泉府此条出现了熙宁时新旧两派关于常平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国服之息”。“国服之息”与下文的“国用取具”曾是王安石与韩琦关于“青苗息钱”辩论的重点,其中心问题在于青苗借贷是否应当收息?收多少息?息钱可否国家取用?辩论直接关系到政府借贷收息的合法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有必要将“国服之息”论证纳入市易解释范畴,因为除了借贷对象不同外,市易之借贷形式、收息、取用原理与青苗借贷相似。而在经解层面,泉府“国服之息”更直接对应的当是市易息钱,因为泉府主关商贾借贷而并未言及小农借贷。 “以国服为之息”的说法,先郑、后郑各有解释: 郑司农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玄谓以国服为之息,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 郑司农(郑众)以为,国服之息即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即以所在国物产为息,原则上取其易得。韩琦正是采用了郑众的解释:“臣谓周制有从官借本贾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变所贷钱,使输国服,即以为息也。此所谓王道也。”(46)其在“国服”解释上倾向于郑众注,承认贾者从官借贷之制与应付之利息,但还息之法是令其输所在地之“国服”,即物产。王安石则采郑玄注,郑玄谓以国服为之息,“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也。王安石以为“以国服为之息,则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也。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47)。显然,郑玄强调的不是所在国的物产差别,而是民众从官借贷钱物之后,以个体劳动、经营来偿还利息的基本义务,王安石在这一点上承续了郑玄的意见。 至于泉府贷民,出息几何,经实无明文。郑玄又云:“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用《周礼》通行的说法即“二十而一”。《周礼》“载师”任地之法:“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4](p.962)郑玄泉府取息之法,大抵参照了载师任地出税法。载师任地制税凡五等,最低“园廛二十而一”,最高“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郑玄借“园廛之田”二十而一为说,只是约合其意,但却为后世关于息钱轻重的争论敞开了空间。 青苗法最初所规定取息,或有三分,以河北为最;或有二分,京西、陕西等路依此;或“当纳本色,不收其息,或止收一二分之时多少相补”(48)。条例司云:“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49)“二十而五”之说,即是从载师“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王安石以为,从无息至二分之息(惟独河北三分,为例外情况),比起《周礼》最高之息“二十而五”不为高。然而,反对者对此不以为然,孙觉云:“《载师》所任,自园廛二十而一,至漆林二十而五,其征五等,而漆林之征最重。以其末作妨农,所以抑之使归本色。今农民乏绝,将以补耕助敛,乃欲二十而五,以比漆林之征,则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与《周礼》之意相违甚矣。”(50)孙觉以为,《载师》征税法旨在重农抑商,本末自当有别。常平借贷本为农事,故息钱收取不当以条例司采用的“漆林之征”为准。(51) 综上所述,新旧两派关于“国服之息”的论争主要聚焦于两个层面:第一,“国服之息”的息钱来源。条例司主张以个体劳动所得为息,韩琦认为当以本国物产所出为息,不管是哪种说法,其实都认可利息本身,只是经解差异而已,不足以构成双方实质性分歧。第二,息额基准。旨在表明政府收息高低,是论争关键所在。王安石比对最高息法(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以为青苗收息并不算高;韩琦则以“至远之地”即《载师》所云“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为说,并将一年两次借贷的二分次息换算为岁息四分,明政府取息已经远远超过《周礼》所述(52)。 因泉府无收息之明文,故从郑玄注开始已是臆测之词,后世争论不过根据己意来论证而已,皆以己方认定的经义为据,客观看来不必太纠结孰是孰非。但不管按哪一方为准,熙宁元丰期间,政府借贷收息的总体标准是一至二分之间(市易借贷通行二分之息,但后来实行金银抵押贷后则低至一分二厘),比起动辄百分之百的民间高利贷(“倍称之息”),实属低息(53)。 三、结语 本文以《周礼》泉府职为“纲”,将泉府经义、王安石的经学阐释与市易法内容贯穿其中。这样的研读一方面可以深入理解《周礼》泉府法,在有限的经文语境之外,实践性的市易语境的引入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泉府内涵——从泉府经文到后世的经世致用,也可以通过泉府法来理解市易法背后的学术内涵。 这种交叉式研读的可能性源于两者原理的共通性以及王安石对两种法度的关联与论证。在王安石的经术体系中,古今两种法度都是在“国家敛散”“政府借贷”模式下展开的一系列经济行为,其具体的历史背景、经济模式可以不同,但基本理路则相通。此外,这种研读方法更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使某些重要的政治经济话题,诸如国家财政、政府经营、官营经济等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视域或理论体系中敞开,并进行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承续性探讨(54)。这或许正是变法时期的王安石坚持要将经术引入新法以体现“古法今用”、“法意”继承的用意所在。 同时,这样一种研读模式需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正心态”,正视两种法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王安石变法研究者,不仅需要注意并理解王安石所论泉府的基本内涵及意义,更需要考察市易运作过程中对这层经术内涵的理念承续,不至于使王安石所学、所述与所施政因研究盲区而人为割裂。另一方面,即便王安石如此频繁地引经说法,也不便将两者机械地对应等同。客观地说,泉府法更像是一种官方经济运作的理论模式,除了一些概括性的纲目条文之外,经文中很难找到更丰富、完整的细节内容。市易法则完全不同,这是一套现实立法,背后有着复杂而具体的历史环境、经济环境,是王安石等综合多种因素、诉求而设计的一系列官方经济运作模式。这并不是简单地对读或照搬泉府法就能明了,其中既有基于现实因素的综合考量,也有基于经义理念的创新与发挥。 说到底,泉府法是“死”的,而市易法却是“活”的,这个“活”的成分需要我们在古今之间、理论与现实之间、个人观念与政治实践之间来合理把握。换个角度,对王安石来说,市易法本身就是对《周礼》泉府的“活的注疏”,故王安石之“言”——经义注疏与立法解释——固然紧要,但王安石之“行”——制度的创设与施行——更是其新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的孔子所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2](p.3297) 注释: 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市易法研究在研究理路和思维模式上有所转变。梁庚尧先生在写《市易法述》中体会到,大陆老一代学者过多关注市易法“裁抑兼并”等社会政策属性,而较少关注市易法在国家财政方面的措置与努力。故其研究进一步转向梁启超在《王荆公》书中对市易法所做的基本设定或判断,包括市易法的缘起、国家专卖与国家财政诸层面。这种思考模式被视为“一种有关王安石与新法研究的新解释传统逐渐在形成,或许也可以说一个旧的解释传统的复兴”(参见梁庚尧2007年10月《〈市易法述〉的写作过程》演讲稿)。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从市易法看中国古代的官府商业和借贷资本》,载《大陆杂志》,第85卷1期,1992年;[日]熊本崇:《北宋神宗期の国家财政と市易法——煕宁8·9年を中心に》,载《文化》,东北大学文学会,1982年;[日]宫泽知之:《宋代的城市商业与国家——市易法新考》,载《中国近世的都市和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梁庚尧:《市易法述》,收入《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版;李晓:《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制度》,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这些论著在考察市易运作基础上,大多关注法度背后国家财政、都市商业、借贷资本、政府购买、军事财政等重要课题。 ②当时反对者对王安石“泉府经制之术”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假先王遗迹,志在聚敛;其二,复制王莽法,用先王之言以欺世;其三,名托《周礼》之制,实效管桑之术。参见范纯仁:《上神宗乞罢均输》、《上神宗论刘琦等责降》,载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0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5、1190页;李常:《上神宗论青苗》之一、二,同上书卷110、卷113,第1203、1227页;陈襄:《上神宗论青苗》,同上书卷114,第1247页;文彦博:《上神宗论市易》,同上书卷116,第1273页。 ③关于王安石政治改革中的“学术本位”与“学术立场”,史籍中皆可考见。如熙宁元年,王安石越次入对时云云,参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9,北京图书馆影出版社印《委宛别藏》本,2003年;同书同卷王安石论天下事云云;熙宁四年五月,神宗与王安石论租庸调法与田制问题云云,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四年五月癸巳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419页;另参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6,《礼乐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02~706页。 ④文中所体现的方法论为:将王安石提出的经学概念、理论回归于原初的解释情境,或者说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解读王安石的经义阐释。 ⑤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09,吕诲《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注引,第1182页。 ⑥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3。 ⑦参见本文注②,另参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19页;范镇:《上神宗论新法》,《宋朝诸臣奏议》卷111,第1207页;孙觉:《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24页;欧阳修:《上神宗论青苗》,《宋朝诸臣奏议》卷114,第1248页等。 ⑧参见: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宋朝诸臣奏议》卷111。 ⑨王安石云:“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可辨也。”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8;另参吕公著:《上神宗乞罢提举常平仓官吏》,《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16页。 ⑩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3。 (11)参见: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20页。 (12)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条,第5827页。 (13)同上条,第5828页。 (1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二月己未条,第6129页。 (15)神宗云:“朝廷设市易法,本要平准百货,盖周官泉府之政。”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甲申条,第7892页。 (16)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41,《上五事札子》,第440页。 (17)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41,《上五事札子》,第440页。 (18)保甲法在财政方面实现了两项“封桩”,一为保甲替代正兵而实现的“禁军阙额封桩”,二为保甲民职所省却的原耆户长、壮丁、坊正等支酬(雇直)。这些数额庞大的封桩财物后来大量支与府界及诸路提举保甲司,充保甲教阅、赏赐等费用。绍圣初章惇云:“元丰中,始遣使遍教三路。先帝留神按阅,艺精者厚赏,或擢以差使、军将名目,而一时赏赉率取诸封桩、耆长,或禁军阙额,未尝费户部一钱。”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之38,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 (19)参见宫泽知之:《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收入刘俊文主编,张北译:《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0)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70,《乞制置三司条例》,第745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王安石议论文字,多以“义理”、“理”之所在为说,由于数量过大,在此不一一例举。 (22)王安石云:“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自注:如曲防遏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公立书》,第773页。 (23)熙宁初,王安石云:“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6。 (24)按:市官即管理市场、征收市赋及敛藏之官员。 (25)《周礼》大宰职“以八法治官府”,其三曰“官联”,郑注云:“联,读为连,古书连作联。联谓连事通职,相佐助也。” (26)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72,《答韩求仁书》,第764页。 (27)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条,第582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28)参见郑侠:《西塘集》卷1“市例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文献通考》引郑侠奏议文字略有异同,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07页。 (29)笔按:宋代史料一般会出现三种说法“市例钱”、“市利钱”、“事例钱”,三者关系需要厘清。官方正式条文中一般称“市例钱”,亦作“市利钱”。郑侠奏议中用“事例钱”称“市例钱”,则以“市例钱”之所用而言,门局所收市例钱用于专栏食钱,故将“市例钱”称作“事例钱”。郑侠又解释:“有司当立法时,取专拦所得事例钱以供专拦逐月食钱,不曰‘事例钱’而以‘市利’名之者,盖取《孟子》所谓‘有贱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为名,是贱之也。”参见郑侠:《西塘集》卷1“市例钱”。 (30)参见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收入《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1)郑侠奏议云:“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以给专拦等食钱”,又别以“事例钱”称之,非常明确体现了市例钱的“专款专用”性质。 (32)在法理上,税与费有严格的区分,大致有三个标准:1.看征收主体;2.看是否具有无偿性;3.看是否专款专用。以此判之,则市例钱显然是“费”而非“税”。故学者若以附加税称市例钱,是未能明晰税与费的区别。古人自然不会明晰区分税、费概念,但学者若以未经辨析的现代概念(如附加税)名之,则显轻易。 (33)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巳条,第6147页。 (3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二月己未条,第6129页。 (35)这与当前国家通过专项税费征收来抑制投资过热产业(如房地产)、去泡沫化以及抑制贫富差距原理相同,都是在征取与分配环节做文章。古人自然不能了解其中的国家经济调控原理,但现代学者在研判过程中,则要有明确的意识,不便随古人云而云。 (36)本段涉及泉府与市易两种制度间的比照与对读,对于这种对读的可能与意义需略作说明:1.王安石明言市易法继承泉府,而泉府又以官方收购和借贷为运作之枢纽,故有必要考察泉府之核心运作机制以及市易对此的继承与拓展,否则无从了解王安石秉承的泉府法意。2.《周礼》经与熙宁新法之间的参照因王安石的经术与实践成为可能,故参照、对读的展开主要有两条线索:其一为王安石所述所言,即经术与立法之间的解释言论。而言论所未及或未全处,则必待观其制度与施设的展开,此即第二点,以立法实践为线索。故笔者以为,不如此则不足以知王安石“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之意。熙宁七年二月,面对众非议,王安石激动而言:“市易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癸丑条,第6119页。 (37)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15。 (38)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条,第5623页。 (39)关于牙人的市场角色及其经济职能,参见斯波义信著,庄景辉译:《宋代商业史研究》第五章“商业组织的发达”,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 (40)按:对于市场而言,充分的流动性是其活跃的保证,而流动性除了依赖货币供给之外,还需要充裕的空间和及时的交易信息,这是纯粹自由市场中最稀缺的资源,因此需要专门的机构提供仓储、物流和经济信息对接。因此,这样的政府行为可以说是以商业活动的形式、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与秩序的服务,而不能简单地看做“与民争利”。 (41)孙诒让注云:“凡赊,从官买物,而约期以付贾,不得过旬日、三月,而不取息。贷则从官借物,而约期以偿物,得过旬日、三月而有息。”参见:《周礼正义》卷28,“地官·泉府”,第1097页。 (42)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 (43)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乙亥条,第6155页。 (44)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元丰二年正月己卯条,第7196页。 (45)元丰二年十九日戊午,诏将京师抵当借贷法行之诸路,再减其息钱:“应置市易务处赊请钱,并依在京市易务法,听以金银物帛抵当,收息毋过一分二厘。”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27。 (46)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6。 (47)参见王昭禹:《周礼详解》卷14,“泉府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程元敏以为:“考其说略合郑玄注……意其即述王安石之说。”参见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三)《周礼新义》,第212页。 (48)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3。 (49)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3。 (50)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12,孙觉《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第1225页。 (51)韩琦的反驳更为详细,但因多关青苗息钱细节,故不作深论。详见韩琦:《上神宗论条例司画一申明青苗事》,《宋朝诸臣奏议》卷112,第1221页。 (52)韩琦云:“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间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也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同上。 (53)参见乔幼梅:《宋元时期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及其附表1“宋代高利贷发展利率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54)限于篇幅,本文未引入泉府以外的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同货、敛散、平准、借贷等相关理论与实践,有待别文专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