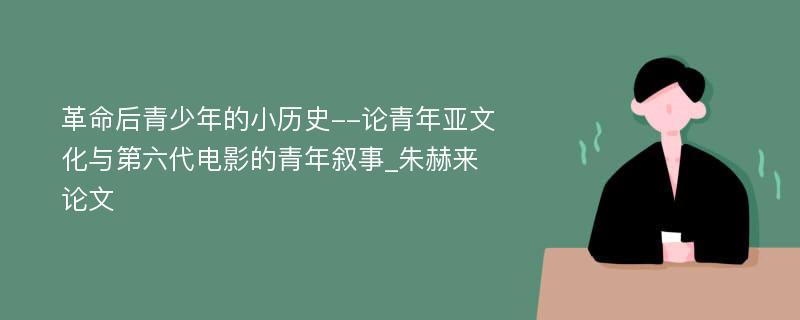
后革命时代的青春期小史——论青年亚文化与“第六代”电影的青春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春期论文,文化与论文,第六代论文,青年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第六代”电影里,成长的青春是他们密集表现的一个主题,这些青春电影以青年人为书写对象,以他们个人的青春经验和成长历程为叙事内容,具有明显的青年亚文化特征。在“第六代”电影出现之前,青春电影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历史中是在场的缺席者。虽然《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青春之歌》、《青春万岁》、《红衣少女》等电影都是以青春生活为表现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青春特征,但是青春主题被更多地赋予了国家、民族、革命等意识形态内容,青春被定义为个体为了革命事业而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阶段,个人成长的历史叙事被营造为宏大历史叙事的载体,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消泯自我的集体主体意识压抑了青春本在的残酷性、私密性、自在性,青春成为意识形态宏大历史叙事的注脚。而基于宏大启蒙叙事的冲动,作为1980年代电影先锋的“第五代”电影也没有将青春作为他们的电影内容,一个青春或者成长的故事是无法满足“第五代”历史反思和民族人格重构的人文理想,个体的成长叙事或者有,也是作为“父辈”的或者“历史”的见证人存在。真正渴望并最终见证了自己的青春和成长的电影是“第六代”电影。青春在这些电影中显示了它残酷而又感伤、脆弱而又坚强、矫揉造作而又纯粹真诚,茫然若失而又信念坚定的复杂形象,青春和成长的个人叙事从国家民族的集体叙事中脱颖而出,昭示它人性的自然的状态——一片“化冻时分的沼泽”。摇滚乐、暴力、秽语、毒品、嬉皮、朋克、文身等青年亚文化形态在电影中的出现表明了这些青春叙事的个人性、边缘性和叛逆性,它们是生长在青春的沼泽里的标志性物种,藉由它们的存在,我们得以认识这青春的颜色、背景和深度。
一、无主题变奏:摇滚乐神话与“新青年”的反叛想象
当崔健在舞台上第一次高唱《一无所有》的时候,张元、王小帅、路学长和娄烨等“第六代”电影人正在北京电影学院上二年级,这是1986年。崔健作为一个时代的青年领袖引领了一代人的成长,而摇滚乐则契合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的文化心理,“第六代”电影人对于摇滚乐的推崇在于摇滚乐的内容和形式是代表这一代人精神走向的艺术符号。高亢的嗓音、嘈杂的电声音乐、狂欢的现场演出、摇滚乐手个性的另类生活、甚至摇滚乐天生的西方背景在1980年代后期的中国无疑都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反抗的性质,摇滚乐被蒙上了一层启蒙的神话色彩,而摇滚乐在1989年事件中的在场使这个神话达到顶峰。“第六代”电影人显然意识到了摇滚乐致力于个性解放的反叛精神和非凡的艺术表现力所具有的先锋性和前卫性,不约而同地在电影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摇滚场景和摇滚青年。但是在我看,“第六代”电影的摇滚乐影像显然还具有一种“解神话”的性质,在这些1990年代的电影中,摇滚乐的反抗功能已不再与整个社会的革命性改造相联系,而仅仅是年轻人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途径,摇滚乐从神话的云端跌落下来,还原了其作为一个青年亚文化的本质。其实,崔健在《一无所有》的呐喊之后的创作预示了这摇滚乐神话趋于自我瓦解的虚无本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显示了《一无所有》的一代人的内心世界依然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教义,于是也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虚伪:“你别想知道我到底是谁,也别想看到我的虚伪。” (《假行僧》)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我飞不起来了”。 (《飞了》)不再飞翔的青年跌落凡间,迷失于都市的迷津而无法自拔。于是张元叫他们或者自己《北京杂种》,管虎称呼他们或者自己《脏人》(《头发乱了》),这命名之中充满了精神的迷茫、身体的创伤、理想的衰竭和生命的焦虑,当然也不缺乏一种自我调侃的勇气。
1992年,张元投拍《北京杂种》,1993年完成,同年完成的有关摇滚乐题材的电影还有娄烨的《周末情人》,管虎的《头发乱了》,路学长的《长大成人》于1995年拍摄。这四部电影是“第六代”电影中涉及摇滚乐题材的最重要的影片,除摇滚之外,暴力、毒品、性等为主流社会侧目的边缘性内容均在电影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摇滚乐题材的电影在1993年前后集中出现显然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的政治气候在1990年代中前期的一些变化,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社会的政治气氛逐渐由紧张而趋向宽松,另类的文化产品有了通过审查的可能;另一方面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彻底结束以后,信仰丧失带来的精神真空往往会由愤怒和绝望来填充,对于青年来说摇滚乐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宣泄途径。从广场上返回庭院的青年在摇滚乐的喧嚣中打发时日,摇滚乐在此时扮演了双重的角色,其一是唤起反抗的功能,青年在身体的扭曲、声音的分裂和精神的幻觉中完成了个体政治反抗的想象;其二是疏导反抗的功能,既然反抗和革命已经在文化的幻觉中完成了,青年还有什么理由走上街头聚会或者游行?“第六代”电影关于摇滚乐的作品在 1990年代前期的密集出现其实是关于一代青年在理想的乌托邦破灭后、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记录,这些作品、特别是《北京杂种》强烈的纪实性显示了电影作者为一个青年时AI写作真的历史目的。
摇滚乐作为一种影像资源在“第六代”电影里集中出现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反映了摇滚乐在那个时期的文化现象中的重要地位。而《北京杂种》对于摇滚人生活的原生态记录,则使它成为这些摇滚乐电影中最突出的一部,它显现出的诸多文化症候代表了其他几部电影共同的特点。首要的特点就是肮脏。场景的脏,北京仿佛被笼罩在一个灰色的罩子里,人与物都影影绰绰恍如幽灵;生活的脏,电影一开始就是男女两个人在讨论打胎,然后是性乱,斗殴;语言的脏,人们的话语中永远带脏字,否则就不会说话,于是统统都是一帮《北京杂种》。脏就是“第六代导演对于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生活的概括。其次是孤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无论是在台上拨弹出噪声并嘶哑歌唱的人,还是在台下呐喊蹦跳的观众,因为孤独所以旁若无人的表演,其实参与摇滚乐并不是试图摆脱孤独,而是更充分的享受孤独,或者说摇滚乐本身就是邀请人们去捕捉处身人群中的孤独。“‘北京杂种’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悲凉感和残酷感以及因缺乏目标和人际交往而产生的孤独感。”[1](P136)最后当然是关于反抗的,摇滚乐反抗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崔健的《一块红布》等音乐里表达地非常透彻,但是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种反抗的个人性,就像《北京杂种》里标榜的那样:“我们都是由着性子活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社会异己分子,”青年从来不惮于成为社会的异己分子,只有在这种“异类”的状态中才能为这被成人把持的社会注意,才能发现自己价值所在;“玩摇滚的目的不是摇滚本身,而是为了标新立异;标新立异的目的同样也不是它本身,而是不甘于沉沦,去追求与众不同的更时尚的生活”;[2](P243)更时尚的生活也不是它本身,而是让这个世界认同自己并自我认同。也许摇滚乐本身并不怎么让人舒服和快乐,但是它却成为自由、独立、平等或者还有性感的一种极其强烈的个人化表达,人们消耗掉的是汗水、泪水、力比多,获得是一点点微薄的尊重和满足。
《北京杂种》的结尾是黎明时分,婴儿的一声啼哭迎来了灿烂的万丈霞光,《周末情人》里的拉拉出狱的时候迎接他的除了凯迪拉克,还有一个叫拉拉的婴儿,这两个新鲜、光明、纯洁的婴儿飘落到崔健的专辑《无能的力量》的封面上时,完全变做了一副颓唐无奈的模样。这是一个绝妙的隐喻,摇滚乐是无力的,艺术是无力的,这种人类童年时代的声音无疑象征着一种反抗、挣脱和对峙,问题是它决不会试图再引发一种革命或者解放,所以反抗终归变成逃避,对峙当然也只是虚张声势的游戏,摇滚乐只是一种时尚的娱乐。不过,也许摇滚乐“这种‘迷幻旅行’包含着对既成社会塑造出来的自我的废除——一种人为的、短暂的废除。但是人为的或‘私人的’解放却以一种歪曲的方式预示了社会解放的紧迫性:革命必须同时是一场感觉的革命,她伴随的必须是社会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重构,并创造出新的审美环境。”[3](P37)
因此,摇滚乐还是一种创造新感性的美学元素,而“第六代”的摇滚乐电影试图表达的也许就是摇滚乐所带来的这种新的审美环境,一个关于青春残酷的审美空间。
二、残酷的青春:成长的挫折与青春期躁狂症
人类个体在童年时代是一个分裂的生命体,生命支离破碎的感觉使我们非常脆弱和渺小,我们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识与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一样,凌乱、飘忽不定、无从把握。当孤独的个体某天忽然开始重视自己身体的变化,开始对于世界有了自己的解释,开始从他者的死亡中感觉到自己死亡的可能,那么青春开始了。伴随青春而来的不仅是喜悦和兴奋,更多的是烦恼、忧伤、痛苦、恐惧以及莫名的虚无,因为个体主观的判断、想象和欲求与客观的世界相距如此遥远,青春个体不能不将自己放逐于社会象征秩序之外,构成了具有青春亚文化特征的青年社群。为成人社会秩序所漠视并自我边缘化的生命状态使个体的青春天生具有了残酷的本质,个体的成长不可避免与人生最极端的状况——暴力、死亡、人格分裂猝然相遇。
“第六代”电影的青春叙事以反映为主流文化压抑的亚文化形态为能事,其实无论摇滚文化还是毒品文化等亚文化形式,都以身体形态的极度扭曲、感性的极端释放为终极追求,这些显然与理性、中庸、保守的成人社会格格不入。青春躁狂症并不是被压抑而产生的精神强迫症,而是青年反抗压抑从而自我确认的身体体征和精神印记,青春残酷的根源因此来自于因社会象征秩序的压抑造成个体的成长挫折从而导致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是一种象征性的分裂,它具有明显的外在社会行为表征。这些表征在“第六代”的青春影像里以不同的重点表述出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是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落差,极端的暴力与内心的怯懦成为不能须臾分离的联体兄弟;《极度寒冷》是对死亡的迷恋,生命的终极体验与艺术的最高追求被离奇地结合在一起;在《青红》是性压抑后的性侵犯,爱在两个极端中寂静地丧失等等。无论青春的个体怎样地奋力挣扎,有一点是注定的,那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成长为我们理想的那一个,而且个体也永远得不到曾经期盼的那份爱,凡是我们最终得到的都是涩味悠长的青果。
人生的春天总是与爱情的发生相伴而生,怀春的少年也总是不能遏止自己欲望的洪水,情欲的表达与满足却往往被社会的禁忌和他者的存在所阻断,青春的伤感与沮丧于是首先源于青果之爱的苦涩。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还是《任逍遥》,性意初萌的少年的初恋对象总是那些年龄稍大的女性,然而这些女人只把他们当作未长成的孩子,从来不会对他们有爱欲的兴趣,少年的初恋注定以失败告终。在这几部电影中,特别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米兰和《长大成人》里的付绍英都是那种体形丰硕的女人,在整体形象上俨然具有母亲的意味,这就使“我”——电影的叙事者以及主人公的初恋具有了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个体的初恋内容更多程度上依赖于性本能的指导,丰硕的女性往往是最有号召力的性感符号;另外一个方面是对哺乳期的留恋,婴儿时期无知无畏的安全感是人生任何阶段的向往;还有一个是通过爱一个接近成人世界的女人完成对成人社会的冒犯,这是个最原始的身份证明方式。不过这些女人总是属于那些与她们年龄相仿、在竞争中获得了社群集体认可的人们,于是“我”只有证明自己,然而这种证明却依然是孩子般地幼稚,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只能爬上最高的烟囱来证明自己的勇气。挫折往往不是来自于追求的不成,而是来自于幼稚成人仪式的被嘲和自嘲。暴力于是在所难免,赤裸裸的身体的施虐和受虐是受推崇的成人象征性仪式,身体的创伤是成长的纪念。青春总是在暴力中绽放它最炽热、残酷的花火,人生只能在他人或自己的痛感中获得最终的证实。
在“第六代”导演看来,没有暴力过的青春根本就不算青春。《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任逍遥》、《十七岁的单车》等都不缺乏暴力奇观,青春个体的尚勇斗狠每每充满镜头,血流满面的大特写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青春的血脉里仿佛流淌的都是刀子。性的冲动或者力比多的压抑固然是一个原因,但青春时代暴力的生成往往与怯懦联系在一起,最残暴的人一向不是那些强力者,而是胆怯地跟随在强力者背后的追随者,他们最急于证明自己,所以一有机会就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的兽性。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与六条胡同的混混械斗的一场戏,“我”在真正的打斗中慌张得茫然失措,当对手落单被围时,“我”毫不犹豫地上去一顿板砖,手黑得连自己人都害怕。掩饰自己胆怯的最好办法就是非比寻常的凶残,这就是青春的暴力法则。在我看,青春暴力是对成人社会象征秩序的语言暴力、规则暴力和权力暴力的反弹,而且成人社会特别是在一些极度压抑的历史时期对于青春暴力的镇压从来无比酷烈。王小帅的《青红》即是一例,小根与青红的爱因为青红父亲或者其他社会秩序的压抑而演化为一次性侵犯后,成人社会对他的惩罚就是剥夺他的生命,女人的贞洁或者生命只属于这个“父权”的社会秩序,并被“他”支配和分派,对于小根生命的剥夺也是对于青红青春的剥夺。所以青春的暴力不过是象征秩序暴力的一种预演和模仿,真正残酷的不是血腥的暴力本身,而是青春暴力的荒谬与虚无。这就是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叙事里对于暴力的一次次矢口否认、不断改写的原因——所有青春暴力导致的往往不是个体期盼的尊严而是更大的屈辱,暴力的反抗实际上是一种对暴力的屈从。
死亡意识的出现是青春开始的一个标记,而个人的成长总伴随着死亡而完成,他者的死亡是证明个体在世的外在标示,而个体自身的“死感”是感受自我存在的内在证据,青春总是缠绕着死亡的梦魇。青春暴力导致的死亡其实在“第六代”电影中并不多见,只有娄烨的《周末情人》阿西的杀人和被杀算得一例,大陆电影审查制度对于暴力的限制是青春暴力而造成的死亡在电影中缺席的重要原因。“第六代”电影中对于死亡描述的极致是《极度寒冷》,主人公齐雷在四季的轮回中模仿死亡的仪式证明了死亡的永恒在场,对于生命极限的体验在超脱的人与庸俗的人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只有可以自由选择的人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自杀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自我选择,而不是被选择。行为艺术自然有表演的成分,事实在于齐雷的四次死亡仪式是一种演义,但最后死亡真正实现却是一个纯粹个体性的事件——他独自于立秋那天在乡间的树下割腕自杀,没有观众也没有摄像机。死亡的意义最终还是归于个人,并没有其他启示他人的意义,我认为王小帅并没有试图揭开死亡的真相,死亡永远没有真相,而是表达了对于一个青年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于死亡个体的人性的尊重。
青春的残酷表现在电影里时往往会流露出强烈的自恋感,当《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孤独的浮在水面上时,前面的青春的暴力梦魇仿佛是托起他生命的水面,天地一片空寂,只有他的身体是唯一可识别的生命。青春的残酷是浪荡子在被成人秩序象征性去势前的放纵,青春个体的自恋情结是个体对未被阉割之前的完整“身体”的象征性呵护,成长与成长的挫折在所难免,如何进入成人世界就成了一个问题,没有人愿意遵循“父”的生命轨迹,因为“现实之父”是那样的碌碌无为,虽然重蹈覆辙不可避免,但寻找“精神之父”就成为一种需要。
三、寻找的寓言:出走的青春与“父”的幽灵
“金羊毛”的传说是有关寻找主题的故事原型,伊阿宋率领希腊勇士历经磨难,得到了金羊毛,自己也锻炼成为一个英雄。金羊毛可能就是荣格的统一而整合的人格的象征,这个整合的人格达到了,个人就处于自我实现的境界。所有有关寻找的叙事其内在的核心无一不是在寻找自我,只不过这个完美自我会投射于一个外在的目的物身上,自我就物化为金羊毛、圣杯、佛舍利或者其他一些神圣而珍贵的物什,寻找必然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艰难路途。在革命文艺中,这种历尽精神和肉体的种种磨难,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英雄的叙事比比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是其中的经典文本。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原名《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即是对于这部革命经典的仿拟,戴锦华认为这种仿拟是“后现代式的重写”,是“出生于60年代的一代人所遭遇的后革命的社会与文化现实,断裂且破碎的意识形态,制造着某种特定的文化匮乏和焦虑,因而呈现出了第六代所倾心的‘长大未必成人’的叙述主题。”[4](P525)
《长大成人》是后现代的重写不错,不过在我看来,这种重写的意义在于一个后革命的历史语境为个体自我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从而摆脱了革命时代的一统性意识形态对于个体人格的集体性塑造,同时个体人格的实现以象征性的离家出走为代价,并以对一个目标的寻找为必由的途径。出走的象征性在“第六代”的青春叙事中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父亲”的缺席或者弱势,主人公不得不转而寻找另外的精神之父,精神之父仿若幽灵出现在这些青春叙事中,在《长大成人》是行踪不定、琴心剑胆的朱赫来,在《极度寒冷》是冷漠深沉、工于心计的老曹,在《昨天》则是虚无缥缈的披头士——约翰·列侬。认同于一个精神之父并非认同于“父之名”的社会象征秩序,我更愿意将这个“精神之父”看作是一个个体欲望的聚合物,是自我人格完善的内在驱动力。作为“第六代”开山之作的《妈妈》,现实中的妈妈——圣母与投射圣光的——上帝之间的结合,显示了个体自我纯化,以上帝之子自我认同的幻想。所以在这些电影中从并不缺乏“俄狄浦斯”情结,象征性的弑父在电影伊始就早早完成,那就是自我人格想象外化的“精神之父”对于“现实之父”的取代。
《长大成人》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存在一种互文的关系,或者根本就是发生在后革命时代的保尔的故事。电影中周青的许多生活场景与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故事场景往往存在着耦合的关系,比如电影隧道中经历地震的一个镜头段落,与随后我翻看小人书中保尔站在隧道前与朱赫来攀谈的情形是完全对应的。1976年的地震是一个隐喻,表示一个主导着大众心灵的伟大舵手的驾崩,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然后就是“朱赫来”恰如其分地出现。在这个对于革命经典文本的仿写中,“朱赫来”与周青关系显然不同于小说里朱赫来与保尔的关系,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为有效询唤依据的精神引导已经不适合于周青的长大成人,电影中的“朱赫来”不是一个革命导师,而是一个人性或者人道主义的偶像。“朱赫来”并没有有意识地引导周青的成长,而是以自己的人性力量影响着周青人格的形成。在周青的讲述中,“朱赫来”是他上一代人中的典型,周青对于“朱赫来”的讲述有一个无意识塑型的过程,“朱赫来”在周青生活中的昙花一现使他只能而且必定是周青想象中的那一个,这种想象甚至需要外在的事实予以加固:因为一次事故,“朱赫来”的骨头植入了周青的体内。这是一块快乐与痛苦交织的主体性碎片——“要下雨了,我的脚又痛起来,”这也是后革命氛围中个体主体性构成的象征性元素之一。在《长大成人》中,“朱赫来”与朱赫来、周青与保尔身份的想象性置换以朱赫来的见义勇为和我对朱赫来未竟事业的完成而事实上实现,个体自我的主体性得以完成,长大由是成人。
精神之父的幽灵同样也存在于其他一些“第六代”电影之中,但他们具有各自的象征性意义。《极度寒冷》里的老曹无疑担任了齐雷的精神之父,他也是其他行为艺术者的精神性父亲,这个“父亲”角色的形成在于他是这个艺术领域的权威和终极的阐释者,没有他的在场,你的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就会打折扣,他象征了艺术领域的一个“父权”秩序。电影似乎故意的显示老曹故弄玄虚的一面,譬如少言或者言语沉缓,永远都是一种轻蔑的审视态度。老曹在电影中实际上是齐雷自我度量的一把尺度,其意义在于齐雷将之设置为横亘于艺术乌托邦边界的一个门槛,老曹是他获得自我感觉的一个镜子。《昨天》的情形似乎更为直接,贾宏声在自己生日的时候直接掴自己老子的耳光:“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活着吗?你活的有意思吗?你快乐吗?”与其说是在打他父亲不如说是在打他自己,与其说是在质疑父亲不如说是在质疑自己,与其说是约翰·列侬这个“精神之父”杀死了“生身之父”,不如说是想象的自我或者未来的自我杀死了过去和现在的自我,而这种自我的分裂分别影射于“精神之父”和“生身之父”。所以,所谓“父的幽灵”不过是我对于未来自我或者自我乌托邦的想象,是青春个体的一个精神幻象,个体欲望投射的神义象征,藉由这种神义的庇护,个体欲望的实现获得伦理的合法性。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使个体的选择有了不同的方向,个体主体的生成不再如革命时代那样拘泥于一个单一的英雄模式,人仿佛是在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镜头下活动,个体的人格形象破裂成碎片,在频闪的镜头中变换着难以言说的复杂镜像。
在“第六代”电影的影像系列里,我们约略可以抽象出一条按照时间递延排序的青春历史,它们是文革的青春——《阳光灿烂的日子》,《牵牛花》,《青红》;1980年代的青春——《长大成人》,《站台》;1990年代前期的青春——《冬春的日子》,《周末情人》,《头发乱了》,《极度寒冷》,《北京杂种》;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青春——《扁担姑娘》,《苏州河》,《十七岁的单车》,《任逍遥》,“第六代”电影人从来没有丧失青春书写的热情,在他们之前还没有哪一代导演这样热衷于叙述自己的成长历史,也许个人化的艺术生产就是一个自恋者的独语,作者的影像似乎永远只为自己而做。这是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一个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和“后文化大革命”的“后革命”时代,一个人们不再相信有关历史和政治的“元叙事”的时代,伟大历史主题和伟大历史人物的“大型叙事”让位于渺小个体的“小型叙事”,而关于青春的叙事又是从个人的历史叙事上飘零的碎片,它并不致力于解释这个世界,而是反映了个体对于这个世界最初的否定。
标签:朱赫来论文; 一无所有论文; 青年亚文化论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文; 音乐论文; 暴力电影论文; 第六代导演论文; 北京杂种论文; 青红论文; 极度寒冷论文; 头发乱了论文; 周末情人论文; 长大成人论文; 摇滚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