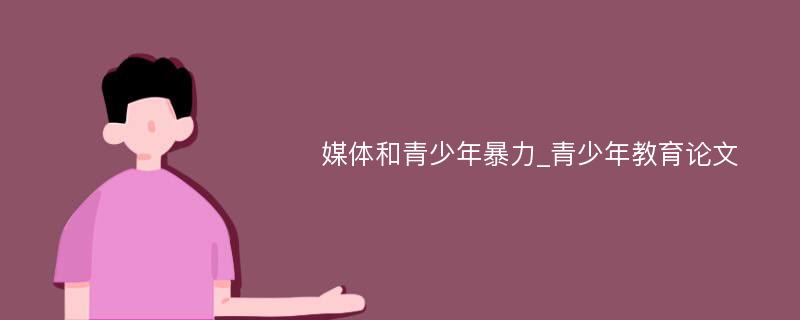
媒体与青少年暴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暴力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少年暴力是社会中最常见的暴力形式。有许多个人和社会的因素影响了青少年暴力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媒体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看电视通常起自2岁,8~18岁的青少年每年约观看1万部带有暴力的电视节目。当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地接触众多媒体的儿童青少年数量更是越来越多,媒体对青少年暴力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对媒体影响青少年暴力的特点和机制进行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媒体影响青少年暴力的实证研究
(一)电视和电影
有许多实验室研究探讨了接触电影或电视暴力是否会在短期内增加青少年的暴力行为。结果发现,跟不看暴力影片的青少年相比,看暴力影片的青少年会出现更多的攻击行为。Bjorkqvist(1985)[1]随机选取5~6岁的芬兰儿童观看暴力或非暴力影片,然后由两个事先不知道儿童看什么类型的片子的评判观察记录他们在一间屋子中的玩耍情况。结果发现,与看非暴力影片的儿童相比,看暴力影片的儿童显著出现更多的身体攻击和其他类型的攻击行为。Josephson(1987)[2]随机选取了396名7~9岁的男孩,在他们看过一些暴力或非暴力的影片后,让他们玩游戏并记录游戏中每个男孩攻击其他男孩的次数,结果发现,看暴力影片的男孩显著出现更多的暴力行为。我国学者曾凡林等人(2004)[3]也研究了观看电视暴力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青少年观看暴力镜头的频次和兴奋水平程度越高,情绪宣泄越少,表现出的攻击行为倾向就越多,且男生的攻击行为比女生多,工读学校学生比普通学校学生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Leyens等人(1975)和Park等人(1977)的研究还发现,即使在类似监狱这些管理严格、反对暴力的地方,暴力影片仍能产生严重的身体攻击行为。
除媒体对攻击行为的直接影响外,还有许多实验研究了媒体对攻击性思想和情感的影响。大量的研究都表明,接触媒体暴力会增加儿童和青少年的攻击性思想和情感,使他们更能接受暴力。Thomas和Drabman(1975)发现,当看到两个儿童打架时,看暴力影片的青少年比看非暴力影片的青少年会更慢去叫大人调解,暴力影片似乎使儿童更能接受暴力。同样,Malamuth和Check(1981)[4]发现,在大学生看了数日暴力电影后,他们对他人对女性使用暴力的接受程度会增加。Zillmann和Weaver(1999)[5]随机选取一部分大学生看4部影片,有暴力和非暴力两种,看完影片后对所有被试进行敌意评估,结果发现,看了暴力影片的大学生比看了非暴力影片的大学生显著出现更多的敌意。
进一步,过去40余年的大量横断研究都表明,青少年的身体攻击、言语攻击和攻击性思想与他们平时看电视或电影暴力的数量有关[6]。Mcleod等人(1972)以中学生为样本,研究了看电视暴力和攻击行为间的相关,结果发现看电视暴力时间越多,出现攻击行为也越多。Belson(1978)以英国12~17岁的男性为样本,发现在过去6个月,重度电视暴力观看者比轻度电视暴力观看者多报告了49%的暴力行为。同时,这种相关在年幼的青少年身上表现更为明显。Huesmann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观看电视暴力和攻击性的相关在6~10岁的男性被试身上显著,而在20岁的被试身上不显著。
同时,也有许多纵向研究考察了媒体暴力对攻击行为的影响。Eron和他的同事用纵向研究法,抽取了来自哥伦比亚、纽约的850名青少年,发现男孩8岁时接触的媒体暴力与他10年后,即高中毕业后的暴力行为存在明显相关。Milavsky等人(1982)[7]从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选取7-16岁的样本研究了电视暴力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在3年时间里共进行了15次调查,结果发现,不论横向还是纵向数据的分析都表明,电视暴力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在男生和女生身上都极为明显。上世纪70年代末期,Huesmann及其同事在5个国家也采用横向、纵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电视暴力的影响[6]。横断研究表明,接触电视暴力和攻击行为在所有国家都呈正相关。但早期接触电视暴力对以后攻击性的影响程度随性别和国家有所不同。在美国,即使考虑进她们早期的攻击性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业成绩,女孩早期接触电视暴力对以后的攻击性仍有显著影响。而对于男孩,单纯考虑电视暴力不能预测他们以后的攻击性,但那些在童年早期经常看暴力电视的男孩以及报告说对电视中的暴力人物有强烈认同的男孩,会被同伴视为最具攻击性。在该研究开始15年后,再次对美国样本中的300多名被试进行了调查,他们此时大多20岁左右。结果发现,媒体暴力对严重身体攻击行为有明显的延迟影响。童年时期接触电视暴力和成人早期的攻击性显著相关,男女都是如此,童年期接触较多电视暴力的成人与接触较少的相比,前者显著有更多的身体攻击行为。
Johnson等人(2002)[8]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他们长达17年对被试看电视对其行为影响的一项研究。研究刚开始时,被试还只有1~10岁,在其后的17年中,这些儿童一直在接受各种测试和调耷。研究人员通过长期的跟踪调查和详细统计发现,年龄在14岁左右的少年儿童如果平均每天看电视在1小时以内,当他们长到16岁时有5.7%的人有过激行为,平均每天看电视在1~3小时的上升为28.8%。研究人员还对平均年龄为14岁左右的男孩和女孩分别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对男孩来说,平均每天看电视不超过1小时的成年后只有8.9%的人会有过激行为,每天看电视在1~3小时的成年后有32.5%的人会发生过激行为,而每天看电视3小时以上的人发生过激行为者占45.2%。对于女孩来说,发生过激行为的比例分别为2.3%、11.8%和12.7%。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电视、电影暴力不但会对攻击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还明显地影响青少年的攻击性思想和情感,这一结果不但被大量的横断研究证明,同时也得到了大量纵向研究的明确支持,而且接触越多,影响就越大。
(二)新闻
报纸上有关暴力的报道是否鼓励暴力行为的研究还比较少,多数都是时间序列研究,即在密集报道一起暴力事件前后,比较社区暴力发生率的变化。总体来说,这些研究支持了传染效应的观念。Berkowitz和Macaulay(1971)[6]的研究曾发现,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些谋杀案之后(包括暗杀肯尼迪总统事件),暴力犯罪的数量暴涨。而更多的研究表明,一个名人的自杀会增加其他人自杀的可能性。
(三)音乐电视和流行歌曲
音乐电视受到关注是因为其中常充斥暴力,迄今为止,还很少关于接触音乐电视怎样影响青少年身体攻击行为的实证研究。但学者们已进行了不少关于音乐电视如何影响攻击性思想和态度的研究。Johnson等人(1995)[6]的研究发现,看了贬低女性音乐电视的年轻女性,对约会暴力的接受程度高于控制组的女性。另一项针对年轻男性的研究中,Johnson等人(1995)[6]发现,接触暴力音乐电视会增加在假设冲突情境下对暴力的认可度。类似的,Hansen和Hansen(1990)的研究发现,接触反社会主题摇滚音乐的大学生与未接触反社会摇滚音乐的大学生相比,前者更能接受反社会行为。Wester等人(1997)则研究了没有影像的暴力歌曲对青少年攻击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跟没有接触暴力歌词的被试相比,接触暴力歌词的被试将他们与女性的关系看得更为敌对。最近,Anderson等人(2003)[9]也报告了关于歌词影响的5项系列实验,结果一致发现,有暴力歌词的歌曲增加了青少年被试的攻击性思想和攻击性情感。
Roberts等人(2003)[10]的研究发现看MTV的数量与三到五年级儿童的打架呈正相关,而且,看MTV多的儿童总是被同伴报告比其他儿童有更多的言语攻击、更多的关系暴力以及更多的身体攻击,教师也认为他们有更多的关系暴力、更多的身体攻击,并且不乐于助人。Rubin等人(2001)[11]则进一步发现,喜欢重金属和快板音乐的大学生比喜欢其他类型音乐的大学生报告有更多的敌意态度。重金属音乐的歌迷对女性持有更消极的态度,而快板音乐的歌迷则更加不信任他人。Took和Weiss(1994)[6]同样发现,喜欢快板和重金属音乐与低学业成绩、学校中的问题行为、吸毒、拘留以及性行为相关。
(四)影像游戏
现今人们对影像游戏的关注已经超过了前面几种媒体,这一方面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玩影像游戏,同时这些游戏多数都包含暴力。另一方面,影像游戏是一种互动性的媒体,青少年不仅是一个受动者,而且也是一个主动参与者,这有可能使他们受到更多的影响,更具攻击性。尽管有关影像游戏对青少年暴力的影响还未像电视和电影的影响那样得到广泛研究,但已有关于影像游戏的研究其结果与电视和电影的极为相似。在过去的20年里,已有20多个研究评估了青少年期(包括青少年晚期的大学生)暴力影像游戏和攻击性的关系。大量的相关和实验研究都支持暴力影像游戏和攻击性存在相关。Irwin和Gross(1995)评估了玩暴力和非暴力游戏的男孩的身体攻击情况,结果发现,那些玩暴力游戏的男孩会对同伴使用更多的暴力。Bartholow和Anderson(2002)[12]发现,玩暴力游戏的大学生随后实施的高强度惩罚是那些玩非暴力游戏的大学生的2.5倍。Fling(1992)在一组11~17岁的被试身上发现,玩暴力影像游戏与自我及教师报告的攻击行为都呈正相关。Anderson和Dill(2000)[13]则发现大学生中玩暴力影像游戏和实验室侵犯行为有关。
同时,人们也研究了暴力影像游戏对青少年攻击性思想、情感和生理唤醒的影响。Calvert和Tan(1994)发现,玩暴力影像游戏显著产生更多的攻击性思想。还有一些研究用其他方法来评估攻击性思想,结果发现了同样的影响。Anderson和Dill(2000)[13]的研究发现,玩暴力影像游戏和攻击行为呈正相关,学业成绩与玩影像游戏呈负相关,暴力影像游戏会增加攻击性思想和行为。Lynch等人(2001)在对初二、初三年级学生的研究中也发现,暴力影像游戏与攻击性态度和行为显著相关。进一步,人们还发现,玩暴力影像游戏的时间和攻击性明显相关。Anderson和Dill(2000)[13]的研究发现,玩暴力影像游戏的时间越长,就会出现越多的攻击行为。Ihori等人(2003)[6]分两次每半年左右对日本五、六年级学生接触影像游戏的时间进行调查,结果也表明,接触影像游戏的时间和以后的暴力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五)网络
目前,还很少关于接触网络对暴力行为影响的研究正式发表。但由于网络的可视性和互动性,预计它的影响应该和其他可视化和互动媒体相一致。
二、理论上的解释
(一)早期的观点
为解释媒体暴力对儿童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影响,在过去的30年中,学者们已提出了多种的理论和模型。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童及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是观察学习的结果,儿童不仅从榜样那里学习具体的行为,而且也学习概括化、复杂的社会脚本(一套关于如何解释、理解和处理各种事件的规则),且大多是自动和无意识的。强调信息加工的心理学家则提出了攻击图示的启动和自动化模型,认为暴力情景能激活攻击性思想和情感的联结,促进攻击性图式的提取,造成暂时性解释偏向,歪曲随后的知觉,使新事件被认为具有攻击性,因此增加了暴力应对的可能性。频繁启动攻击图式,更使这些攻击图式可在长期内易于获得,导致长期的攻击偏向。而Dodge等人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认为,儿童对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所作解释和反应,依赖于5个认识步骤的结果,即“评价—解释—寻找反应—决定反应—作出反应”,儿童不能按顺序对输入信息进行加工,或在某个环节发生偏差,都有可能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6]。
另一些理论则强调了其中情绪和唤醒的作用。Zillmann的唤醒和兴奋迁移模型认为[14],媒体暴力会增加皮肤的导电性,提高心率以及唤醒的其他生理学指标,对儿童青少年有明显的兴奋作用。而且,这种兴奋和唤醒能够迁移:一方面,加强个体当时的任何行为倾向;另一方面,若一个人错误地的将自己的唤醒归咎于其他人对自己的激惹,相应作出攻击行为的倾向也会提高。而情绪的去敏感化模型认为,不断接触媒体暴力会使个体对暴力的消极情感反应去敏感化,使其不再像从前一样对不愉快的身体唤醒作反应,从而更轻易地使用暴力,且对暴力受害者的同情心和帮助也会减少。
(二)近期的观点:一般攻击模型(CAM)
近期关于青少年暴力形成机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数Anderson和Bushman(2002)提出的GAM(General Aggression Model)[15]。该模型融合了众多前人的观点,是一种较为综合的观点。
GAM首先包括个人变量(如敌意特质、对暴力的态度)和情景变量(真实世界中的暴力或媒体暴力)两个输入变量,这两个变量相互作用来影响个体当前的内部状态。在个体的内部状态中,认知(如攻击性脚本、敌意思想)、情感(如敌意的感觉)和唤醒(如心率、血压)之间彼此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能够相互激活和提升。然后,通过认知、情感和唤醒的相互作用来影响个体对攻击行为的评估和决策(如伤害者的意图是好是坏)。评估过程包括即时评估和再重估两种,前者是一种快速的、几乎无意识的评价,导致冲动行为,后者则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在即时评估之后发生,产生更为深思的行动。
GAM认为暴力影像游戏对青少年暴力形成的影响有长期和短期两种效应。在短期效应中,暴力影像游戏作为一个情境变量起作用,导致攻击性认知、情感和唤醒的增加,从而增加攻击行为。Anderson和Bushman(2001)最近的一项元分析研究确实明确地发现,暴力影像游戏会导致攻击行为、攻击性认知和敌意情感,并提高生理激活水平[15]。
在长期效应中,该模型认为,暴力影像游戏通过以下方式来影响攻击行为:形成攻击性的信念和态度,制定攻击性计划和攻击行为脚本,作出攻击性预期,使个体对攻击具有高度脱敏性,这些因素使个体的人格逐步趋向攻击性。与此同时,长期玩暴力影像游戏,不仅改变个体的人格,也改变个体周围的环境:当个体变得富有攻击性时,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与老师、家长和以前同伴的交往减少,结交一些富有攻击性的新同伴,在与新同伴的交往中,观念发生变化,活动场所也会发生变化,从而新形成的人格变量与新的环境变量一起再一次开始对个体行为影响的新的循环。
同时,该模型还可解释青少年攻击性的发展,认为在青少年的不同时期暴力影像游戏有着不同的影响。跟中、晚期的青少年相比,暴力影像游戏对早期青少年的影响更为明显,这是因为早期青少年所经历的高度生理唤醒和由暴力影像游戏引起的内部状态唤醒相互作用会导致内部状态唤醒更高的累积水平,从而导致更多的攻击行为。而评估过程在青少年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在更多的情境中,早期青少年不经过认知评估就冲动行事,由于影像游戏的攻击性会提高内部状态的唤醒(如边缘系统的活动和性激素的释放),在玩影像游戏后,这一影响更会被加强。相反,晚期青少年的决策将变得更理智和更具评估性,即使玩影像游戏后紧接着是一个伴随敌意认知和情感的高唤醒状态,但由于晚期青少年认知能力的提高以及边缘系统活动和性激素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攻击行为会少于早期青少年。
三、中介因素的影响
虽然媒体通过大致相同的机制作用于儿童青少年,但各个青少年所受的影响却有不同。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个体特质、媒体内容和社会环境这些中介因素,研究它们在其中的促进或妨碍作用。
(一)个体特质
年龄和性别。研究发现,媒体暴力的影响在年少的青少年身上最大,同时在两性间也有差异。大量的研究发现,男性攻击性行为多于女性。Lindeman(1997)[16]研究了11~14,14~17岁青少年在假设人际冲突情境中的反应,包括两种攻击类型:直接攻击(如鄙意的嘲弄)和间接攻击(如散播谣言),结果发现,对假设冲突情境的攻击性反应,男生也比女生更常见,但这两种攻击类型男女身上都表现出了曲线模式:攻击性反应在11~14岁间增多,而在14~17岁间减少。Loeber等人(1998)的研究同样发现,真实的身体攻击在13~15岁间达到顶峰,随着个体进入青少年晚期而减少。
个体的攻击性。研究表明,媒体暴力对高攻击性的个体比低攻击性的个体影响更大。最可能变得高攻击性的儿童是那些一开始就具有攻击性并且看了大量电视暴力的青少年,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Bandura(1977)的“相互决定论”理论:不同的人寻求不同的媒体内容并为这些内容所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攻击性的儿童不会受暴力形象的影响,研究表明,媒体暴力对那些早期低攻击性儿童以后的攻击行为也有显著影响。而有些研究则发现暴力媒体对高、低攻击性个体的影响是相同的,甚至有时会发现低攻击性的个体比高攻击性的个体受媒体暴力的影响更大。
(二)媒体内容
攻击性罪犯的特质。由于对罪犯的认同会增加其行为对观看者的影响,所以很有必要考虑罪犯的哪些特质会导致认同。结果发现,观看者最可能认同那些和自己相似的攻击性人物(如年龄、性别和种族方面)(Bandura,1986,1994)。但有时,罪犯整体的吸引力、权利和魅力似乎比观察者自己的这些个人特质更重要,如研究发现,在70年代后期美洲儿童会更多模仿白人男性演员的行为,而不是与自己相似的美洲演员的行为。
描绘的合理性和攻击结果。根据观察学习理论,当暴力被描绘得很合理时,观看者更可能认为他们对冒犯者作出攻击反应是正确的。Berkowitz等人的多项研究发现,认为媒体暴力是正当的信念会提高愤怒者攻击先前激惹他的人的可能性。Bandura等人以及后人的大量研究更是十分确凿地证明,对暴力进行奖励的媒体内容会增加观看者的暴力行为。同时,人们还研究了呈现暴力受害者所遭到的消极后果的影响,结果发现,观看暴力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会对认同暴力的观察者产生替代性惩罚,从而减少媒体暴力对观察者行为的影响。
(三)社会环境
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媒体对青少年暴力影响的大多数研究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实证研究的结果大多数是相似的,但也有例外。如Huesmann和Eron(1986)[6]发现,在以色列集体农场成长的以色列儿童身上,观看电视暴力和暴力行为间不相关,而在郊区成长的儿童身上这两者存在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对暴力行为严厉制裁的文化环境减少了从媒体上习得暴力行为。同时,Comstock和Paik(1991)[17]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儿童平均看更多的电视和电视暴力。虽然这种与经济地位相联系的看电视习惯不能完全解释媒体暴力与青少年暴力的关系,但低经济地位儿童大量接触媒体暴力确实可能是造成他们成人时更多暴力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父母的影响。即使仅从逻辑上讲,父母也是媒体暴力对儿童影响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儿童青少年的态度、信念和行为是接触媒体的结果,但他们也会将他们所看的与其他人,尤其是父母和朋友进行讨论,而他们的最终反应是这些人际影响的结果。有许多研究支持这一观点,Singer等人(1986)[6]的研究发现,父母在孩子观看电视时主动介入,如经常评论电视的真实性、合理性以及其他影响孩子学习的因素,孩子受媒体消极影响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Nathanson(1999)[18]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家长与孩子讨论电视暴力的不正确性或者禁止孩子接触电视暴力,则他们的孩子要比其他不这样做的家长的孩子表现出更低的攻击性。甚至还有研究表明,家长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可以减少孩子受暴力电视的影响,进而降低孩子的攻击性态度。
四、媒体与青少年暴力预防
媒体是传播人类文化、知识与价值观的基本工具,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全球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儿童青少年对电视、电影、互联网等的使用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在美国的研究发现,除了上学和睡觉,孩子花在媒体上的时间比其他任何活动都多。25%的六年级学生每周平均看电视超过40小时,这比他们在学校的时间还要多,看电视最多的年龄是在8~13岁。8~18岁的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周玩影像游戏1.2~7.5小时[6]。在中国,由全国青少年协会发起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80%的中小学生将看电视作为最主要的课外活动,每天用于看电视的时间普遍都在100分钟以上,学生利用互联网聊天、玩游戏、观看不健康内容的时间,要远远多于网上学习的时间。最近在广州市小学三年级及初二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广州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看电视47分钟,节假日上升到175分钟,47.7%的学生表示玩过电子游戏机,他们平均每天玩43分钟,节假日上升到90分钟,36.6%的学生上网是玩游戏[9]。
而另一方面,NTVS曾连续3年调查了美国电视上暴力的数量和内容,发现61%的电视节目都包含暴力[6]。所有的暴力节目中,只有4%描述的是反对暴力的主题,其他96%将暴力作为叙事性的、影片手段来娱乐观众。而且,电视上的大多数暴力都被魅力化和一般化:44%的暴力包括了值得效仿的迷人的罪犯,40%的暴力场景中都包括了幽默,75%的暴力场景中没有出现对暴力的立即惩罚和谴责。45%节目将“坏人”刻画为不用对他们的攻击行为受到惩罚。电视上对51%的暴力行为描绘为没有痛苦,47%没有伤害。在孩子看的卡通片中,普遍对伤害的描绘不切实际。影像游戏中的暴力更是比电视和电影中多得多。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89%的影像游戏包含有暴力(Children Now,2001),而2/3的儿童报告说他们喜欢暴力游戏。
因此,如何处理媒体与儿童青少年的关系是一个关乎广大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社会问题,结合前述媒体与青少年暴力关系的众多科学研究与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要想善用媒体、减少媒体对青少年暴力的影响,尤其有必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对儿童青少年和民众进行正确的媒体使用教育,使全社会都认识和重视媒体暴力对儿童青少年的危害。前文所述的大量实证性科学研究用确凿、详实的数据已客观充分地表明,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效应的角度来看,媒体暴力都会极显著地影响青少年的暴力,这种影响不但反映在外部行为上,同时还表现在暴力思想和情感上。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措施教育身在其中的儿童青少年,要他们提高认识和觉悟,自觉地识别、拒绝和远离暴力媒体;同时,广大的家长、民众和政府也要提高觉悟,充分认识媒体暴力的危害,拒绝和控制媒体暴力。
第二,鼓励家长对青少年接触媒体的监管。前文对中介因素的讨论已清楚地显示,家长对青少年接触媒体的监管有利于减少媒体暴力对青少年的不利影响,甚至是不论家长如何的干预都能达到这种效果。因此,我们的家长不但要有正确、科学的认识,更要有实际的行动,为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与成才,切实担负其监管和教育的责任。
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受到媒体暴力的影响,不准孩子看电视,甚至干脆把电视关掉,束之高阁。但要知道,面对无限丰富的传媒世界,现在的孩子有着多种多样的选择,不让看电视可以进录像厅、不让在家上网就上网吧,而这些地方就更难监管,其潜在的不利影响会更大。可以说,对于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媒体,家长要堵是堵不住的,明智的做法是,家长指导孩子接触媒体,并与他们讨论其中的内容,让孩子学会明辨是非,减少媒体暴力的影响。
第三,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努力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据我国有关部门抽样调查显示,65%以上的工读学生,50%以上的少年犯,其违法犯罪行为均跟直接接触不良的暴力媒体有关。因此,政府应加强文化市场监管,严格审查面向未成年人的影像、游戏产品,查处含有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和恐怖、残忍等有害内容的产品。而传媒界更要加强自律,不能一切向钱看,要增强社会责任感,把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与国家未来发展放在经济利益的前面,积极研发和生产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视听和游戏产品。
同时,还要强制执行黄金时段不得播放渲染凶杀暴力的电视或广告,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子游戏经营场所的管理,坚决落实未成年人不得进入营业性网吧的规定,在网吧终端设备上安装封堵色情、暴力等不健康内容的过滤软件,推广绿色上网软件,为家长监管青少年在家庭中的上网行为提供有效技术手段。
第四,制定更为严格的媒体内容分级标准,并坚决贯彻和执行。媒体内容分级制度是为了控制媒体对社会或政府不良影响而采取的传媒界与政府间的一种中和措施。最早对媒体暴力分级的是电影界,在20世纪初电影刚开始普及时,一些宗教组织和社区就发明了一套对含有色情或暴力影片定级的办法。后来,分级的范围渐渐扩展到唱片、电脑游戏、电视节目等。例如,1990年美国政府规定对那些含有明显的色情或暴力以及鼓吹犯罪和吸毒歌词的唱片,都必须贴上“青少年不宜歌词,需家长指导”的标签;1994年,视频游戏业界也建立了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把美国所发布的视频游戏分成“E”(所有人)、“M”(成人)和“AO”(仅限于成人)等几个级别。从此以后该委员会对7000多个游戏进行了上述分级,其中有近500个游戏为“M”级别,即这些游戏不适合17岁以下未成年人。1997年10月,由民间组织、政策制定者和电视业者共同协商制定的电视节目分级制开始全面推行,这一分级制和锁码晶片配合应用,可让家长在家中锁住某些级别的电视节目。所有这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将这些做法跟中国社会和青少年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订更为严格的媒体内容分级标准,以实现对媒体暴力和青少年接触两方面的控制,净化环境,减少青少年暴力。
标签:青少年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