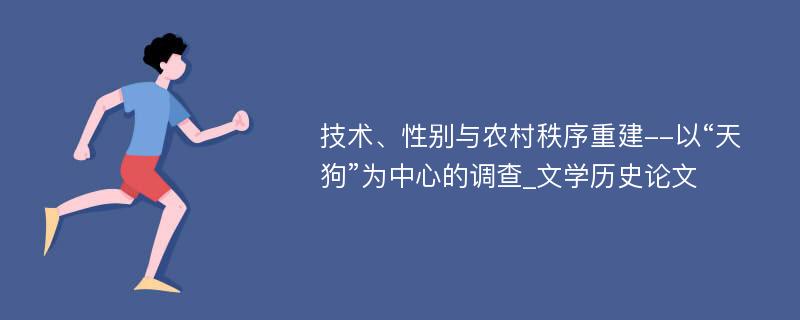
技术、性别与乡村秩序的重构——以《天狗》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狗论文,乡村论文,重构论文,秩序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贾平凹多姿多彩的创作生涯中,发表于1985年的小说《天狗》(《长城》第2期)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作品。然而,当我们今天以“倒放电影”的方式去回溯贾平凹漫长的创作历程,再去讨论《天狗》的位置的时候,却会发现,这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需要被重新解读的承上启下的“转折”意味在里面——1983年、1984年连续发表的“改革三部曲”(《小月前本》①、《鸡窝洼人家》②和《腊月·正月》③),被认为实现了“非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④,使贾平凹在当时广受好评,成为其“在现实主义的路上迅速地走向深入和成熟”的重要标志⑤。然而,随着《天狗》这一批“1985年小说”的发表,批评家们敏锐地发现,那个为世人所熟识的“商州”因为叠加进了浓郁的“悲剧意识”和强悍的“性意识”描写⑥,而笼罩上了“独特的色彩和情调”⑦,使得贾平凹原本饱受赞赏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出现了某种令人困惑的变化。如果接驳上其后《五魁》、《美穴地》等这一路退居到民国背景而更加扑朔迷离的“商州”叙事,或者可以更为肯定地说,《天狗》这一批“1985年小说”,成为了从现实主义的“商州”向神秘主义的“商州”的一种过渡,也开启了贾平凹创作一种耐人寻味的转型。
在通常的以1985年“叙事革命”为中心的新时期主流文学史阐释框架中,像《天狗》这一批作品所指向的贾平凹创作的变化,似乎很难被收纳进去,也很难得到合适的阐释。尽管贾平凹曾经含蓄地承认其与1985年“叙事革命”之间的关联:“我读拉丁美洲的文学,就特别合心境,而又悟出许多东西”⑧,“关于视角……严格地说,我是1985年以后,这方面才慢慢自觉起来的”⑨,然而,与文学主流相错位的感觉大概也时时困扰着他:“当别人写‘伤痕’类的作品,我写了《满月儿》,当别人写改革类的时疾,我写了《商州初录》,似乎老赶不上潮流”,“我的写作似乎老同一些潮流不大合拍,老错位着呢,不是比别人慢半拍,就是比别人早半拍”⑩。这些看似矛盾的说法,相当分明地透露出作为当代文学写作者的贾平凹,既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以1985年“叙事革命”为中心的新时期文学主流的资源,又有着不能与文学主流同步的困惑、遗憾以及更多的骄傲在里面。
在这样的情形下,当我们试图重新来阐释《天狗》这一批作品及其所负载的变化的时候,或许讨论的空间就需要被进一步放大:不仅仅要在贾平凹创作历程中来分析这些作品的“转折”意义到底何在,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于探讨这些作品“转折”意味对于当时的文学主流而言,到底又指向了什么:是一次不成功的加盟主流文学的举动,抑或是对主流文学观念的一种潜在挑战,还是暗示了某种至今尚未被命名的新的文学面向?
某种意义上,对《天狗》的重读就是建立在上述问题意识之下。
手艺/技术的嵌入与乡村能人的重塑
作为叙事的开端,既不“富饶”又不“美丽”的丹江口边的“堡子”,成为了《天狗》讲述1980年代中期陕西乡村故事的背景。在这一富有意味的“风景”设置中,可以看到贾平凹对于旅游手册意义上的“乡村”知识的一种有意识的挑战,即“富饶美丽”作为通常意义上的乡村描述方式,其实是与现实中“贫瘠”的乡村形态有着巨大的反差的。而故意要强调这样的反差,显然,正与前面所说的贾平凹在“视角”上的觉醒有关——如果引入“改革三部曲”作为一种参照的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叙事者更多是作为一个审视者而非亲历者出现在小说中的。这种外在的叙事视角,明显带入了一种具有俯瞰性的“现代”眼光,使得乡村的落后、窘迫历历可辨;但有意思的是,对于旅游手册意义上的“乡村”知识的略带反讽性的批评,又使得这种“现代”眼光还不能简单地落在“城市”克服“乡村”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中来加以理解。由此,贾平凹对于“堡子”的叙事姿态就显得很暧昧,既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却也不是恪守经典现代性原则的,而是因为似乎游离于两者之间而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性的。
可以说,这一姿态奠定了《天狗》的基本叙事基调,在随后开展的“堡子”故事中,这一基调被进一步地扩展开来。尽管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改革三部曲”的人物格局和故事脉络,但《天狗》对其的续写还是饶有意味的: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能人,井把式李正首先审时度势,凭借自己出众的打井手艺,首先在“堡子”这个临江却缺水的地方站住了脚跟。很显然,李正应该被归入门门(《小月前本》)、禾禾(《鸡窝洼人家》)等新时期乡村能人的谱系中来加以理解——他们目光敏锐,行动果敢,最为关键的是,拥有可以发家致富的独门手艺,从而可以使自己从只会在土地上刨食的广大贫苦农民群体中脱颖而出。在这里,“打井”这一手艺在社会转型期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清理。作为前工业时期的技术,“打井”手艺显然是与农耕时代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社会息息相关的,然而这一似乎带着历史倒退气息的技术,却在1980年代前期成为了改造“堡子”吃水困难的最为重要的手段,这其中,不难看出叙事者对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隐含的批判,即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堡子”中人类似于饮水这样的基本生存问题,需要借用小农时期的“打井”手艺才能解决问题。因此,“打井”这一似乎越过了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而横空嵌入新时期的传统技术的复活过程,显然蕴含着以基本人性的要求而有着对社会主义时期责难的意味在里面。就这一点而言,《天狗》可以说相当忠实地延续了“改革三部曲”的遗绪。
有差异的地方,是叙事者同时还凸显了李正这样的先富者其手艺的难以为继以及由此面临的伦理道德上的困境。尽管,在“改革三部曲”中,贾平凹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将这一问题作为思考的重点:“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虚浮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适用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的环境呢?社会朝现代化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之风的萌发呢?这些问题使我十分苦恼,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11)但很显然,王才战胜韩玄子的过程,已经证明了“历史进步”带来的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问题,可以通过“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经济结构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行为”(12)的确立而得以顺利解决。但在《天狗》中,这一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却又一次以更为严重的方式浮上水面。当李正将“打井”当作是独门绝技秘不示人的时候,有关这一农耕时代的手艺的命运就又一次伴随着其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而浮出了水面:对于手艺的独占性,很大程度上,使得李正遭遇到了《鲁班的子孙》中小木匠的尴尬,如何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取得与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认同,特别是在利益分化导致乡村原有共同体解体的时代?仅仅凭借“暴发户”式的财富积聚,李正显然并无力完成这一新的个人声望的建构以及向更高的阶层的流动;相反,当他甚至要自己的孩子放弃优异的学业成为这一古老职业的唯一传人的时候,来自于妻子、孩子、徒弟众口一词的反对,已经宣告了,李正所选择的个人角色、所依傍的手艺以及这些因素背后的个人独富的梦想,尽管展示了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处在各种力量绞缠博弈的社会转型期,事实上,更多还是显示出了其力不从心的一面:传统乡土社会所遗留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结构,必然会引申出对知识的尊崇和对手艺的贬斥;社会主义乡村共同体的历史残存,显然与“独富”的观念格格不入;现代社会对更高级的组织化和社会化的新技术的询唤,其实也无法真正接纳“打井”这种纯手工的一脉单传的古老技艺。也就是说,依托于“独富”式的发家梦想,李正及其技术,因为单纯地指向独占式的利益,不仅使得其自身率先“原子化”,而且切割了原有的宗族、地缘、血缘等关系,因而挑战了既有的乡村秩序和伦理关系,潜伏着破坏乡村原有“社会关联度”的危险(13)。
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一旦李正被定位成一个充满了“小生产者的优点和缺点”(14)的前现代“劳动者”时,事实上他及其所依赖的技术已经无法取得足够的合法性,其作为社会转型期过渡角色的悲剧命运就此奠定:在小说中,“打井”手艺成为了让人悲喜交加的双刃剑,既可以让李正发家致富,同样,也可以猝不及防地让他成为一个半身不遂的残废人,同时耗尽之前所攒的家财。这一悲剧命运设计,不仅宣告了李正凭借落后的传统手艺试图“独富”的实践在转型期中国的破产,甚至还要通过使其成为不完整的男人而将其逐出正常人的世界,让他承受非同寻常的屈辱、折磨和煎熬。在这里,叙事者试图借助传统的因果报应模式对功利化的农村改革者进行严厉的道德审判(而不是像“改革三部曲”时代那样尽力维护)的意图,可谓历历可辨。
与李正的没落命运形成呼应的,是原本穷途末路的天狗及其所挟带的新技术的崛起。作为李正式的农村能人的替代者,天狗甫一出场,其面目就带有某种“异端”色彩:“此角色白脸,发际高而额角饱满,平日无所事事,无人管束,就养兔逮兔、钓鱼、玩蚂蚱的嗜好,天生的不该是农民的长相和德行,偏就做了万事不如人的农民。”(15)很显然,天狗的形象、趣味、生活方式等不能被轻易纳入常规的农民范畴,如果联系到他的多愁善感,他对于民歌、民俗的擅长,他俨然可以被当作是一个隐居于民间的“游手好闲者”,甚至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而将农民知识分子化,正是1980年代前期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文学书写者们常常会的一种有意识的文学修辞(16),通过将叙事者的知识分子主观意识投射到农民身上,无论是观看乡村生活的视野,还是讨论乡村问题的深广度,都可以被撑大。而对于《天狗》这部作品来说,将天狗知识分子化,显然还有着调和“改革三部曲”所提供的韩玄子(旧时乡村知识者)、王才(新一代致富农民)二元对峙结构的意味在里面,当天狗本身就是以兼具农民和知识者特质的复合型形象出现,并成为李正的取代者的时候,可以说,在贾平凹的视野中,转型期社会的基本行进动力就不再来自于“技术”本身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需要通过知识与技术的更有深度的博弈和整合来重新审视技术的有效性与有限性,才能赋予技术推动社会发展新的力量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狗该如何掌握更有合法性的技术,特别是解决原有的技术伦理问题,就成为贾平凹试图衔接“改革三部曲”的脉络“接着讲”的重点所在。刨“黄麦管”做刷子,作为天狗离开打井生涯后的第一份独立掌握的手艺,在“断奶”的意义上,见证了天狗对于更有合法性的技术的探索。有意味的是,天狗发现这一手艺的过程,是被安置在“进城—回乡”的叙事框架中的。正如有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在当代文学传统中,存在着一个外来者(代表先进力量的工作队)的进入从而导致乡村变革的“动员—改造”结构(17),在《天狗》中,可以看到贾平凹对这一经典结构的挪用和改写。正如陈奂生必须要上城才能改变“熟人社会”对其的固有认识、收获新的尊敬以及借由这种尊敬带来的新的现实利益一样,天狗的进城(尤其进的还是省城,而非贾平凹更喜欢的县城)既是一种生计所迫,却也成为了改变命运的契机——尽管“贴着墙根走”,也遭遇到了小偷,他还是在城市中觅得了农民在乡间所无法发现的商机。在这里,贾平凹显然是复制了“城(文明)—乡(愚昧)”的二元结构,“城市”仿佛是巨大的金矿,成为了农民发家致富的灵感源泉,也因此构成了对乡村的巨大压抑;但天狗的主动进入,却也可以让人感觉到某种令人不安的挑衅气息,蕴含着一种不甘于“城乡”既有固化等级秩序的意味在其中。在这个意义上,天狗制作并贩卖黄麦管刷子的行为,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对城市及其所代表的现代商业运作模式的单向度认同,但也与王才那种据守于乡土世界一隅的生产经营模式有着明显的差异——黄麦管生长于乡间,在物质匮乏和流通不畅的时代,一旦物尽其用地被制作为一种生活工具,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经济形态,而且渗透进了城市,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天狗对于黄麦管的利用,带着一种非刻意而为而是因势利导的审美色彩;在黄麦管手艺展开的过程中,自然、乡村、器物、技术、农人等等,呈现出彼此协调的和谐之气,其产生的那种劳动时自在而愉悦的感觉,显然与天狗局限在井下的那种憋屈压抑不可同日而语,也是与天狗在城市中体会到的那种尴尬窘迫所无法比拟的。
当天狗与技术的关系被放置在这样复杂的城乡关系格局中来设计的时候,大概可以窥见贾平凹的野心和挣扎之所在:“比方说我,内心就充满了矛盾。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好像农裔作家都是这样。有形无形中对城市有一种仇恨心理,有一种潜在的反感,虽然从理智上知道城市代表着文明。……再譬如说对个体户,咱也看得来,城市个体户做生意代表一种新力量,但从感情上总难接受。表现在作品中,就有这种矛盾心理,既要从理智上肯定,又在感情上难以顺利通过。”(18)今天重新来讨论这样的曾经在1980年代颇为流行的话语逻辑,或许可以先将过于简单因而很有问题的“文明—愚昧”阐释模式悬置起来,从更为复杂的格局去把握到其间所谓的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实质。尽管欲说还休,然而作者对城市的仇恨甚至抵抗意识清晰可辨,其间既流露出了作者有因自己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而无法与时俱进的深深苦恼;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于“城市个体户做生意”这一新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方式侵入乡土世界的强烈隐忧。立足于这样的充满了内在情感张力的表述,可能才能理解作者为何会瞩意于塑造天狗这样兼具农民和知识者特质的人物,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天狗寄托了叙事者既向往城市所代表的个体户生存法则却又时时有所怀疑甚至心怀怯意的脆弱心态,而这,显然要比其之前对于门门、王才在“独富”道路上理所当然的获胜的全面肯定要引人深思许多。
在单一的以城市为模版的发展主义终于成为主流的1980年代中期,叙事者显然只能将内心的犹疑和怯意转化为一种审美态度,而无法将其提升为一种可以与之对抗的强有力的力量,因而小说很快就安排了具有乡村抒情色彩的“黄麦管”手艺在市场重压下的无疾而终。但仿佛是作为一种不甘心的退却的妥协之物,新的技术也就随之登场:作为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蝎子”只能是天狗这样擅长养蝈蝈的人才会注意的游戏之物,然而误打误撞,“蝎子”的药用价值及其蕴含的巨大市场效应,恰恰就是在蝇营狗苟的众人的忽略中被天狗这样的“游戏之人”所发现,并且天狗通过阅读“养蝎子的书”这样的“现代知识”进一步将“蝎子”所隐含的财富优势固定住并发挥出来。更有意思的,如果说“打井”是适用于乡民的手艺,扎“黄麦管”更多是满足城市人的需求的话,那么“蝎子”技术所指向的,恐怕是泯灭了城乡差异的泛指意义上的“人”/“病人”。由此,“蝎子”技术的出现,分明又暗含了叙事者的一种企图超越城/乡、文明/落后既定规范、询唤面目模糊的具有普遍意味的“人”的用意在里面。
无论如何,建立在各种偶然性因素拼合基础上的新的致富技术,通过制造技术的实用性面目和非实用性的获取途径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为天狗的人生制造了传奇色彩,与“天佑好人”的民间道德伦理传统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回应关系;另一方面,实际上是渲染了天狗此次成功的非功利性及其技术经过“现代知识”论证后获胜的历史合法性与必然性,从而使他可以与孜孜求富的众人形成明显的差异性。尤其当天狗甚至能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大度地将蝎种及独门秘诀无私地传授给堡子中的其他人,更是强调了天狗作为新一代的乡村技术专家,终于能实现个人闲适的生活趣味与“招夫养夫”所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的完美对接;同时努力克服李正式的“独富”的个体户理想,以“蝎子”为中介探索了乡村新的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道德与技术的双重完满;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在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中做出单一抉择的风险。
这样看似完美的养蝎子技术的设计,显然寄托了贾平凹对于乡村社会转型的新的乌托邦理想:技术本身如同“蝎子”一样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它必须掌握在天狗这样的人手里,才能从游戏之物变为经济作物,然而却又不会完全功利化;同时,技术必须要转化成人人可以共享之物,才能完成从“毒物”到“药物”的转变,真正成为改变乡村社会的正面力量。在这里,“技术”显然已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掌握技术的“人”成为这一乌托邦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这个“人”不仅要有超出常人的“先进性”和“道德感”,而且还要能以“道德化”的技术为核心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乃至共同体,从而在现代技术/利益嵌入乡村社会结构并成为摧毁乡村原有结构的主导性力量的时候,不至于堕入到“原子化”的危机中去。
然而,问题也就产生了:天狗这样经过美化的乡村能人是否真的可以担当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正如有研究者所批评的:“看来作者所要表现的便是主人公在征服自己本身时迸发出的这种强大的道德力量。正是这种传统道德玉成了一个硬汉子、一个‘不是圣人’的‘怪人’的形象。”(19)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天狗的“怪人”形象昭示了其与历史条件不相匹配之处,甚至被认为倒退回了传统道德,其间的反讽意味恰恰是在提醒我们,仅仅立足于道德化的个人,天狗在多大意义上能够指引出“第三条”乡村未来之路——既不是传统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也不是以利益为导向、以城市为模版的急功近利的乡村?天狗通过新技术的播撤所试图形成的新的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到底是指向了超越传统“熟人社会”的更为合理有序的“共富”型乡村形态,抑或隐含了未来的高度组织化的同时也是掠夺乡村资源的“现代产业”的雏形?小说结尾处不置可否的暧昧处理,暗示了叙事者尚无力在这样的层面上作更为深入的推进。
手艺/技术、劳动价值与妇女的溃败
当手艺/技术的横空嵌入引发乡村社会巨大变动的时候,在乡村社会的内部,像“家庭”这一通常意义上的“私空间”,是否也会因为裹挟在此变动过程中而受到影响;手艺/技术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力量,是否在参与了乡村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重构的同时,也会冲击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作为一个很早就被认为“擅于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角度切进生活”,“通过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做反映农村生活新变化的大文章”的作家(20),贾平凹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显然也融汇进了《天狗》。
隐现在手艺人李正的背后,“师娘”这个无名的乡村妇女一开始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忍辱负重的“屋里人”形象:她温婉内敛,尽管看不惯丈夫倚仗手艺而不讲情面,但碍于丈夫作为家庭顶梁柱的权威地位,而只能“软言软语”地规劝,却无济于事,无法有效地介入到因手艺的重新兴起而引发的社会秩序的重构中去;她恪守本分,当丈夫囿于传统的“子袭父执”的观念而强行勒令儿子退学来学打井的时候,传统的贤妻良母本色使她近乎本能地推崇知识,然而其中流贯着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气息,仿佛出土文物一般不合时宜,根本无法与丈夫“有了手艺,还不是一辈子吃喝”的强大现实逻辑相提并论。只有回到了诸如说亲、过生日等家长里短的日常琐事中,回到乞月、对歌这样散发着古老气息的传统民俗中,师娘才是得心应手的。在这里,应对外部世界事宜的无力与处理家庭内部琐事的从容,构成了明显的反差,在师娘相当分裂的身影背后,可以看到横亘在家外/家内之间越来越清晰的边界线,看到这一边界线如何强有力地切割了家庭成员不同的生活场景与活动空间。
如果引入贾平凹之前的小说作为参照,可以发现,同样置身于手艺取代土地成为家庭收益最重要来源的时代变革格局中,师娘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袭了小月(《小月前本》)、烟峰(《鸡窝洼人家》)、黑氏(《黑氏》)等人的性情气质,但其命运走向显然又与之有着鲜明的差异:小月和父亲一样从事着艰苦的田间体力劳动,但开始依托于恋人门门的爱折腾而梦想另一种远离土地的体面生活;烟峰借助婚姻的变故,逐渐摆脱单一的体力劳动转向更有经济效益的“养柞蚕”,与技来农民禾禾过上了志同道合的富裕生活;黑氏在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后,不仅从家庭妇女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饭店老板娘,而且开始自主掌握自己的婚姻。与她们相比,师娘凭借丈夫李正出色的打井手艺,似乎已经实现了她们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的目标,但从走向这一目标的过程来看,师娘却分明呈现出鲜明的退却倾向——从社会空间逐渐退却到家庭空间,从经济利益显著的主要劳动退却到不被重视的家务劳动,从与男性的并肩奋斗退却到“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分工,从小月们已然拥有的对于自我婚姻家庭生活的自主掌控退却到逆来顺受地接受丈夫作为家庭权威的各种安排……
搁置在小月们的奋斗史中,师娘的遭际显然是令人困惑的:为什么师娘在手艺/技术嵌入的时代会拥有和小月等人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和小月们相比,师娘的命运到底是一种例外状态,还是一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必然?
或者可以援引贾平凹自己的说法,来解释从小月到师娘其间的矛盾和断裂。对于贾平凹而言,“师娘”这一类型妇女的出现,似乎只是他的理性与情感矛盾挣扎的结晶:“对于传统的女性,从感情上觉得好,从理性上分析,又觉得她们活得窝囊没意思得很。人物都体现了这种东西。传统和现代的,道德的和价值观的等等,这些矛盾一直在我身上存在。”(21)这种矛盾挣扎也体现在贾平凹对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首鼠两端的游移态度上:“以你所言的‘女菩萨’式和‘女妖’式的女性,我喜欢的,两种特性能结合起来最好。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少见。换一个角度,‘女妖’式的(这个词可能不大准确),也可以看作现代性的吧,‘女菩萨’式的是传统性的吧,我是倾心于前一个的,却也难丢下后一个。”(22)如果与上文所述的叙事者对于现代/传统、城/乡、文明/愚昧的暧昧态度对应起来看,大概可以理解作者对于传统妇女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以及企图弥合不同类型妇女的苦衷所在。某种意义上,着力塑造师娘这一类传统妇女,恐怕还不能完全从男权中心主义文化角度来加以批判,而更应看作是作者对高歌猛进的乡村技术发展主义道路以及与此形成呼应的乡村“现代性”妇女的一种警惕和反拨,是企图在现代/传统间寻找某种平衡点的策略在妇女形象塑造上的一种体现。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叙事格局中,小月们的道路显然还是被乐观地指认为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而师娘更多只是寄寓了作者一种带着某种政治不正确意味的情感怀旧。
然而,如果引入今天的乡村妇女生存现实作为比照的话,就会讶然于历史的吊诡:当师娘“活得窝囊没意思得很”的命运在今天成为乡村妇女越来越普遍的生存状态,当越来越多的乡村妇女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师娘的道路沦为养老育幼、困守乡间/家庭的“留守妇女”,当小月们的奋斗最终蜕变为在世界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妹卑微而忙碌的身影的时候,就不免会感慨1985年的贾平凹的睿智与盲区:师娘的命运其实倒是具有普遍的预言性的,而小月们的乐观更多却只是昙花一现的“现代性”幻象。这样一种颠倒的历史结果,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提醒我们恰恰不能将师娘视为历史的例外状态,或者是小月们急速飞奔的剩余物,而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小月们全力规避却仍然不得不面对的不期然的结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来梳理从小月到师娘的乡村妇女人生轨迹,或者就应该摒弃简单将乡村妇女区分为现代型/传统型的做法,而需要将她们放在同一历史脉络、同一人物谱系中去,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其命运的内在共性。由此,如何在小月和师娘之间,探寻初衷与结果形成巨大反差的缘由,就成为重新结构化这一乡村妇女谱系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乡村社会变动发动机之一的手艺/技术在乡村妇女命运变迁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就有必要被认真讨论。
白馥兰(Francesa Bray)对于中国“男耕女织”传统的演变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在她看来,古代中国所形成的“‘男耕女织’的规范至少在劳动层面上表达出夫妻之间的分工是互补性的,而不是从属性的关系”(23),因为“织物对于社会纽带的铸造和加固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妇女织的布也把家庭连接进社会之中”(24)。到了宋代之后,随着“纺织”的专业化和商业化进程,熟练的男性产业工人逐渐将妇女排挤出这一行业最富技术含量的岗位,才导致“妇女的经济贡献被遮蔽或被边缘化”(25)。上述考察表明,劳动分工本身其实并不能直接决定性别等级关系,劳动价值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劳动者的差异性评判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在这其中,技术的专业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参照这样的思路,再来考察从小月到师娘的乡村妇女人生历程,可以发现,手艺/技术一步步进入乡村社会肌理的过程,其实也正是妇女逐渐从社会领域中被驱逐出来的过程:电力水龙(《小月前本》)这样高效的农业新技术对于乡村的占领,暗示了效率已成为评判劳动价值的最重要的指标,而乡人或主动或被迫地加入,正是表现了乡村世界对这一“现代”劳动标准的某种意义上的认同;养柞蚕(《鸡窝洼人家》)、打井(《天狗》)战胜甚至取代农业生产,预示了对更高的劳动价值的追求获得了合法性,而低价值的农业生产就此处于劣势;开饭馆(《黑氏》)进入乡村日常生活,宣布了一种与高价值的手艺/技术相适应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而养蝎子(《天狗》)这样的新技术的大获全胜,则揭示了“现代知识”如何参与了对新技术的论证最终使劳动价值体系得以定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有关劳动价值和劳动者关系的新的逻辑被逐渐建立起来,核心内容包括,机器对于体力的克服,手艺/技术高于单一土地经营的商品价值链的建构(26),城市凌驾于乡村之上的权力等级关系被逐渐认可,等等。而作为这一逻辑建构的关键,则是对男性在手艺/技术方面引导者地位的强调。无论是门门之于小月,禾禾之于烟峰,还是李正/天狗之于师娘,由于超前地掌握了政策和手艺,他们都被设计成是强者的形象,毫无疑问地成为变动中的乡村世界的引领者,同时也是乡村妇女唯一可以依傍的对象。相形之下,在劳动价值差别化的时代,对更高劳动价值的追求一定会造成激烈竞争的态势,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乡村妇女处于劣势——从公共劳动中退出来,从手艺/技术形成的新的劳动领域中退出来,甚至从第三产业中退出来,正是因为在转型期中国乡村“权力”、“资本”和“劳动”的不平衡的博弈格局中(27),只占有劳动资源的乡村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所决定的。而师娘,正是这一溃退的群体的缩影。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古老的“招夫养夫”风俗在1980年代的重现以及师娘对此风俗的默默接受。当手艺人李正因为天怨人怒而现世报地成为残疾人之后,师娘终于不得不独自来面对养家糊口的难题。然而早已从社会领域中溃退到家庭、也没有在新的手艺/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她,显然没有能力来应对这一变故,也因此面对丈夫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提出的“招夫养夫”方案,她居然别无选择。在这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古老风俗复活的历史条件:个体劳动化的手艺/技术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反过来也使得单个家庭一旦遭遇风险将只能独自承担;对高劳动价值的追求间接造成了妇女从主要劳动领域的溃退而依附于拥有手艺/技术的男性,然而风险一旦产生却又要求她在需要的时候支撑起家庭赡养的重担,而她却只剩下了唯一资源——身体。可以说,“招夫养夫”正是上述无法调和的悖论落实在现实操作层面的一种畸形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招夫养夫”从风俗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小说还描写了这样的细节:“堡子里的干部,族中的长老,还有五里外乡政府的文书,集中在井把式的炕上喝酒,几方对面,承认了这特殊的婚姻。”(28)如果注意到“招夫养夫”的家庭模式并不是私相授受的产物,而是经由政府、长老、村规民俗等各种力量协商而成的结果的话,那么,仍然简单地将其看作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种奇风异俗,显然是不合适的。在这里,可以看到“行政嵌入”和“村庄内生”(29)这两种不同的力量如何共同作用,征用了“招夫养夫”这一非常态的习俗,以维持基本生存为出发点,稳定了转型期中国的乡村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招夫养夫”之所以成为现实,不仅有来自于丧失劳动力家庭养家糊口的生存压力,有来自于底层贫苦农民没有能力娶妻的窘迫心情,更有来自于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原子化”之后产生的对于底层家庭以维持稳定而不是以介入救助为目的的乡村治理策略因素,当然,这种治理包含着对于既有乡村“礼治秩序”的挑战和调整的意味在里面。
无论如何,对于师娘来说,当她接受并进入了“招夫养夫”所形成的特殊的家庭结构之后,意味着她必须应对和处理特殊的家庭伦理道德形态。一方面作为这个“两夫合一妻”的“奇观”家庭的黏合剂,她必须意识到这一基于生存目的而组合起来的家庭的功利性和脆弱性,因此如何在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井把式和正在担负起家庭主要劳动责任的天狗之间,寻找到维持彼此关系的平衡点,显然是一个难题。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发现,来自于民间的伦理道德形态,如“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知恩图报”的传统,“助残扶弱”的习俗等,结合师傅的悔恨及天狗对于师娘的朦胧情愫,以师娘始终不渝的善良为中介,转化成了一股强大的情感力量,构筑起了三人相互理解、彼此体谅的有效通道,同时聚合了这个家庭所有的能量来应对转型期乡村的各种风雨。当这个家庭在这样的情形下被重新组织起来时,甚至会让人误以为是1950年代初期的乡村生产互助组某种程度的复活。而这一联想,显然有助于拓展我们的思考:当手艺/技术的兴起一定程度上肢解了乡村共同体之后,这一共同体的碎片是否还存在着借助新的契机重新整合的可能性,而反过来可以弥补手艺/技术所造成的某种乡村社会的动荡?
另一方面,也必须意识到,这个家庭既然是在极鲜明的功利目的下被重组,那么,如何处理作为交易品/献祭品的妇女的身体,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小月前本》中,“自主的‘爱欲’的苏醒”(30)就已经作为女主人公被外面的世界召唤而出的“现代”意识的表征而被叙事者细腻地描述出来,在《天狗》中,有关身体以及附着于身体之上的欲望被搁置由“前现代”还魂到当代的“招夫养夫”的特殊框架中,而更有了讨论的空间:作为当事人,师娘显然很清楚“招夫养夫”的特殊家庭要彻底稳定下来,不能只是在形式上,不能仅仅借助于掺合了各种要素的伦理道德所产生的情感动员力量,而需要在实质上实现自己身体的转移——从残废的手艺人转移到年富力强的新一代乡村能人。这一转移既遵循商品交易的规则,也得到了乡村各种势力的默许,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主人公对此的自觉挑战:当师娘怀着感恩与羞耻交混的复杂心情靠近天狗的时候,天狗尽管早已心仪,却仍然断然拒绝。如果只是在身体解放的“现代”意义来讨论这种拒绝,当然会把这种拒绝理解成是一种前现代的性禁忌之物,但如果能理解天狗并不是为了得到师娘而是为了不忍心看师傅一家受苦才接受“招夫养夫”,那么就能体悟到这种拒绝并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道德立场,而更多是拒绝了以手艺/技术作为交换身体的工具,是拒绝了一种将要在1980年代之后通行一时的利益交换法则,从而显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是征服外界时爆发出光辉,出奇的是在征服自己本身上,也真正显示了人的能量”(31),因而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
井把式李正的自杀使得这个充满了压抑和悲情的身体故事变得简单了许多,不仅解脱了他自己,也使得天狗不再需要承受形而上思考的重负和道德上的自我加压,使得师娘不需要成为1990年代之后大量出现的以身体换取物质的娼妓的雏形,这显然标志着“现代”市场公平法则终于凭借着常态化的家庭的复归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同时也意味着转型期中国乡村家庭内部崩溃的痛苦和反抗经验被轻易地置换成了一个现代通俗版的俄狄浦斯故事,作为前提,重复的依然是“现代”技术终于战胜了史前手艺的传奇。
搁置在1980年代中国乡村转型的大背景下,应该说,《天狗》相当完整地展现了手艺/技术的嵌入对于乡村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劳动因新的价值标准进入而导致的分层化,乡村原有共同体的解体,家庭风险的无可规避,妇女沦为弱势群体,民间伦理道德和奇风异俗被激活……也因此,触及到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来回应上述问题。贾平凹在小说中显然已对手艺/技术的单一驱动力、对以城市为模版的发展主义、对现代/传统的二元划分模式等已有所怀疑,然而似乎还没有能够找到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来描绘和处理转型期混沌的乡村变动景观,因而骑墙、折中、调和甚至乌托邦的想象,成为他解决现实问题的叙事策略选择。有鉴于此,或许可以说,从“改革三部曲”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商州”过渡到神秘主义的“商州”,并不是如贾平凹自己所说的是为了提升艺术水准而转型为“意象化”写作(32)的结果,而倒可能是因为作者对于《天狗》中所呈现的变动中的“商州”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无法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进一步加以推进,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可以说,贾平凹于1980年代中期的创作转向并没有真正脱离以1985年“叙事革命”为中心的新时期主流文学史阐释框架,在远离现实“政治情结”上,(33)它们其实是分享了同一种资源。
注释:
①发表于《收获》1983年第5期。
②发表于《十月》1984年第2期。
③发表于《十月》1984年第4期。
④费炳勋:《贾平凹三部中篇新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小说评论》1985年第2期。
⑤⑥费炳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第79-101页。
⑦邓楠:《理想爱情的建构、解构与颠覆——论〈天狗〉、〈五魁〉和〈废都〉三部爱情小说的价值取向》,《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
⑧(11)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27页,第423页。
⑨(18)(21)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⑩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12)蔡翔:《行为冲突与观念的演变:读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读书》1985年第3期。
(13)贺雪峰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变迁的研究表明,利益的介入使得“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松散。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联系弱化了,利益联系尚未建立且缺乏建立起来的社会基础,村民因此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土豆’,村民已经原子化了”。见《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页。
(14)(19)杨聚臣:《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讨——略论贾平凹的商州人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15)(28)贾平凹:《天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41页,第75页。
(16)不仅仅贾平凹早期创作中有此倾向,1980年代前期出现的文学作品如张炜的《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和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都有类似的将农民知识分子化的叙事选择。
(17)蔡翔:《革命/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74页。
(20)蒋荫安:《柳暗花明又一村——读贾平凹的三个中篇》,《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
(22)李遇春、贾平凹:《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谈录》,《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23)(24)(25)[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186页,第147页,第186页。
(26)这一价值链的建构事实上还得到了政策的支持,1978年底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四条是发展副业、多种经营和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27)徐勇认为,“在中国,权力、资本和劳动这三种资源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的配置构成处于不均衡状态。权力是独占的,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则是无限供给的。这就决定了只占有劳动资源的农村农民在治理过程中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参与博弈。”见徐勇:《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序言》,载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7页。
(29)徐勇指出,20纪以来中国“乡村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见徐勇:《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序言》,载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页。
(30)黄平:《贾平凹与80年代“改革文学”——重读贾平凹“改革三部曲”》,《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1)贾平凹:《天狗》,《中篇小说选刊》1985年第5期。
(32)贾平凹将好的小说理解为是内涵因丰富而模糊的“意象化”小说:“我后来写东西,尽量故事情节两句话就能说清,但内涵上,到底要说啥,最好啥也说不清。有时作家也说不清,是模糊的。意象在那指着,但具体也给你说不出来。”见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33)贾平凹认为自己1980年代初期的小说“政治情结更重一些”;而“八十年代中期写的东西才放松,才有一种新鲜感、生气感,蓬勃向上的生气感”。见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