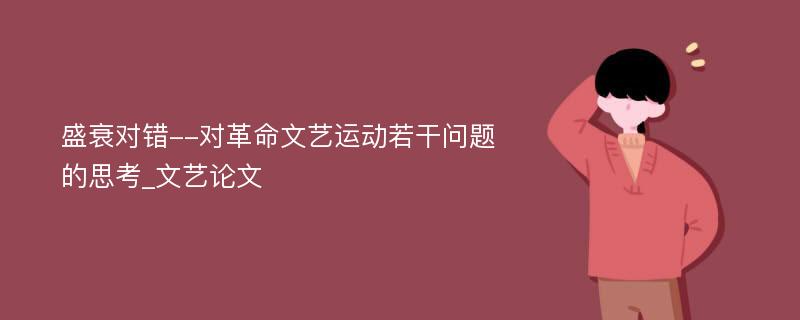
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对革命文艺运动中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是非非论文,风风雨雨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一直把文艺当作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早在1916年,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大声疾呼:“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发难性文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中国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鲁迅在三十年代也说过:“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邓小平、江泽民的两个《祝词》,文艺在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
对于这一点,过去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虽然国民党文人早就攻击过,“共产党徒”把文艺“束缚”于“政治的羁绊之下,虐杀文艺的本质”,是十分“恶劣和浅薄”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艺术论》,载《民间文化周刊》第七期),但在进步文化工作者中间,对此都持有肯定性的共识。
不必讳言,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不但对这个问题有争议,而且争论得很激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有的文章批判“文艺与政治的联姻”,仿佛过去文艺工作出现种种弊端,其源盖出于把文艺纳入到革命事业的轨道中来。在谈到今后文艺的出路时,出现了“告别革命”、“远离政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回到文艺自身”等主张。仿佛要使文艺获得生机,就必须让它从民族使命、社会使命中挣脱出来,回到纯艺术的王国中去。对于“回到文艺自身”,要区别不同的情况。不少人使用这个提法,是强调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要重视文艺的特殊功能。这当然是积极的。但如果是指文艺要从革命和建设的大业中解脱、逃逸出来,这就很值得探讨了。出现争议是不奇怪的。随着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对各种问题、包括文艺问题持不同的立论。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看待文艺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的关系?在回顾八十年来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
其实,把文艺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非始于共产党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十分强调文艺对于国运兴衰的作用。他们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俯视千秋,横眺六极,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无文学不足以新民”。梁启超的主张是大家所熟悉的。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氏把小说的作用估计得大了一些,但他看到了文艺的重大启蒙意义,第一次把小说摆到文学殿堂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十分有眼光的。后来小说艺术异军突起,以至取代诗歌成为中国文学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和梁启超等人的着力提倡是很有关系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艺术而艺术、为游戏而艺术的主张有一定的市场,但始终成不了大气候。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他甚至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于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王国维是学术大师,他在古代史、戏曲史研究上有卓越贡献,他的《人间词话》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学力作。但他关于美的本质的观点,关于文艺和政治、道德相分离的观点,却是违反科学、违反历史前进潮流的。相比起来、梁启超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要积极得多。现在,有些研究文艺史的著作全面肯定王国维,贬低梁启超。我以为是欠公正的。
把文艺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不是共产党人的异想天开,不是几代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盲从之举,不是文艺史上一段荒诞的插曲,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文艺自身发展的必然。中国社会发展到近现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时代呼唤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呼唤着革命。新文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历史要求下应运而生的。文学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哪里?在形式,在语言,在叙述方式、表达方式?这些因素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动力在于社会生活。当然,社会生活要通过创作主体产生作用。正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从根本上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变革。新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使命赋予作家以新的创作素材,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激情和艺术灵感。也正是思想内容的变革,从根本上带动了艺术形式的创新。文学艺术有自身的特点。它是高浮在空中的一种意识形态,难以急功近利、立竿见影。它离不开美,离不开形象,离不开作家的独特个性。它不宜作时代的传声筒,对受众的影响主要是潜移默化。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背离社会需要和时代使命,而意味着它必须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完成时代使命。时代使命不是外加给文艺的额外负担,它恰恰赋予文艺以新鲜的内涵和蓬勃的生机。革命要摧毁腐朽事物,更要创造新生事物。贝多芬写过《英雄交响曲》,肖邦写过《革命练习曲》,它们都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经典名篇。谁说革命不能创造艺术?可以这么说,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新文化。正是在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伟大潮流中,造就了众多的新文艺杰出大师和优秀作品。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过去,我们在处理文艺与革命全局的关系问题上,出现过失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把文艺驱入实现政治阴谋的轨道上去。教训是很深刻的。新时期以来,党中央调整了文艺政策,许多同志也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四人帮”是搞阴谋的。就革命队伍内部来讲,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没有看到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尊重艺术规律,不认真把握文学艺术的特殊性能,要求一切进步文艺都直接地去实现具体的政治任务。譬如“左联”成立的时候,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拼活的斗争”。创造社作家在二十年代末曾经猛烈攻击过鲁迅,这除了某种宗派主义情绪作崇外,和他们对革命文艺的简单化理解也有关系。他们认为一切文学都是宣传,不像鲁迅那样,既看到这一点,又辩证地认识到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艺。鲁迅的小说的确没有直接配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认为它没有时代意味。“阿Q 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我们不必再专事骸骨的迷恋, 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
二,看不到新文化本身是多层次的,没有把对党员作家的要求和对其他进步文化人的要求区别开来,对作家艺术家提出了过高过急的要求。譬如二十年代末,蒋光慈曾提出,革命作家要“向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左联”成立的时候,也曾提出“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今天看来,这些提法的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失误,既不能漠视,也不能夸大。中国革命文艺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标志着党领导文艺走向成熟。建国之后,文艺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出现过种种失误。但是,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失误不占主导地位。上述两个问题,也是局部性的问题。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革命文艺还处于幼年阶段,尽管一些年轻的革命文艺家提出过简单化的意见,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中坚力量还是提出了许多很中肯、很有远见卓识的主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其中个别提法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沿用了。但总的说来,它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结合起来的光辉文献。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如果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失误看成革命文艺史的全部,势必导致全盘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如果从上述失误中引出文艺不能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结论,势必导致文艺工作的改航改向。
新时期伊始,党中央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文艺方针政策作了重要调整。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这一调整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多次讲话、党的有关文献,已经讲得很清楚了。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同时又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促进派,要为这一伟大事业服务,“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980年1月, 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同时强调,“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很清楚,党中央调整文艺政策,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发挥文艺的特长,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认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脱离革命和建设的大局,就意味着它可以不承担教育和宣传的义务,不再是实现崇高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这就完全是南辕北辙。鲁迅在七十年前讲过:“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是因为它是文艺。”鲁迅又说:“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为什么深得艺术真谛的鲁迅,明确宣称左翼作家就是要把文艺“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这很值得深思。
否定文艺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密切联系,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在“重写文学史”中,已经有不少文章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告别革命”等作理论依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很不实事求是的述评。大批左翼作家、解放区作家、革命作家,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赵树理、柳青,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成果受到不同程度的贬低以至否定。对于鲁迅,则把他描绘成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肯定他的前期,贬低他的后期,否定成为马克思主义战士之后的鲁迅。对于置身于民族兴亡之外的象牙塔里的文人,则把他们抬到文学史的主流位置上。甚至对周作人等劣迹昭著的汉奸文人,也出现了高密度的吹捧文章。仿佛投身革命、以笔为武器的作家是走错了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和才华,而那些安坐在象牙塔里的作家,才真正沿续了艺术的血脉。二是误导了当前的创作。既然过去文艺家投身于革命是“错误”的,是“断送了艺术的前程”,那么,文艺家就应该远离政治、远离时代、远离群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消退了,创作的时代色彩也淡化了。“私人化”、“私语化”写作成为很时髦的追求。仿佛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这一切都与艺术无关,真正的艺术就应该是纯粹的自我宣泄。一些创作满足于展示私人生活的小天地,甚至竞相展示个人的隐私、个人的生理欲望。与此相联系,文艺的娱乐功能被片面地夸大了,不是让娱乐和教育统一起来,而是抛开健康的思想内容去搞什么纯娱乐。有的甚至完全钻到钱眼中去,用低级下流的东西去换取市场效益,用感观刺激去代替审美娱悦。至于有些作品丑化中国革命的历史,丑化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其后果更是可想而知的。出现上述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理论上的误导,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从“左”的方面把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简单化、狭隘化,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危害;从右的方面根本否定和切断文艺和革命事业的联系,也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革命文艺是长期在腥风血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今天,我们已经从革命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年代。社会生活状况与过去大不相同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更多样了。毫无疑问,文艺工作的方式方法,文艺创作的内容、形式、题材、风格,也应当有相应的变化。无可否认,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在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年代,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很集中。今天,人们的关注点、兴奋点更多了。那么,我们的文艺还要不要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答案是肯定的。江泽民同志去年提出,共产党人要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这不仅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对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热切期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目标是明确的,道路是宽广的。正如邓小平生前指出的:“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广”。“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们既不能脱离时代的使命和共同的目标,也不能把这一问题简单化、狭隘化。
二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文艺运动中,一直鼓励作家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左联”成立的时候,就鲜明地提出:“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毛泽东在《讲话》中告诉延安作家:“‘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中外文艺史上,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形象、审美的反映,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争取者,还十分强调要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斗争。恩格斯呼吁作家描写“叱咤风云”的无产者。毛泽东那封著名的关于京剧《逼上梁山》的信,曾被“四人帮”用来作为攻击“文艺黑线”的重磅炮弹。廓清“四人帮”的歪曲,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封信的巨大理论分量。毛泽东指出,在旧时代的文艺舞台上,历史是被颠倒的,人民成了“渣滓”,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成了舞台的主人公,这种颠倒的历史应该再颠倒过来。在毛泽东看来,劳动人民要在现实生活中争取主人公地位,也要实现在文艺舞台上的主人公地位。这当然不能理解为对旧舞台的全盘否定,更不能理解为文艺作品只能以普通劳动者作为主角。无产阶级要批判继承中外文化遗产,我们的文艺要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文艺的总体格局。从总体上说,普通劳动者在文艺舞台上的地位如何?这不仅是个题材问题。新时代的文艺,如果根本不反映自己的时代,根本不反映时代的主人公,或者反映得很微弱,那么它怎么可能积极地推动时代的前进?
观察中国现代文艺史,可以看到一个很醒目的现象。早期的许多革命文艺家,都经历了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转换。鲁迅就是很典型的一位。他早期信奉进化论,立志疗救民族精神。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著中,他提出“尊个性而张精神”,“培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鲁迅认为倘若“国人之自觉至”,则“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但鲁迅很快就看到了“个性解放”的局限性。二十年代初,他发表了杂文《娜拉走后怎样》、小说《伤逝》等。在鲁迅看来,娜拉从家庭出走,算是争得了“自由”,但社会状况并没有改变,她只能有两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笔下的子君,是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冷对世俗眼光的蔑视,通过自由恋爱和涓生结合了。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子君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最终,她离开涓生,回到曾被她视为牢笼的旧家庭,郁郁而逝。在还没有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鲁迅就以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刻的洞察力,敏锐地看到了,离开了经济、政治的解放讲个性解放,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是思想的飞跃,它不能不引起创作主题、题材的巨大变化——从写个人的苦闷、彷徨、追求到写群众的疾苦和斗争。曾经以《女神》名扬天下的郭沫若,后来出版了诗集《恢复》、童话体小说《一只手》等。曾经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文坛的丁玲,加入“左联”之后写了《水》、《某夜》、《消息》等。这些都体现了创作追求的巨大变化。
应当承认,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并非一蹴而就,并非立即在艺术上取得辉煌成果。在早期表现革命的作品中,有许多简单幼稚的成分。鲁迅就批评过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并对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深感不满。周恩来也说过,三十年代初革命作家写的作品,有许多远不如曹禺的《雷雨》等深刻。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创作上的变化,它是前进还是倒退?如果只是囿于个别作品的成败得失,而不是把它们放到整个历史前进的潮流中去考查,那么就不可能看到这种变化的巨大进步意义。八十年代以来,文艺史研究中出现了“丁玲现象”、“何其芳现象”等说法,认为他们挥笔表现群众的斗争生活后,政治上前进了,艺术上倒退了。如果孤立地看个别例证,那么这些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如果全面、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种说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有些革命作家从写自我转入写群众后,没有马上在艺术上取得成功?
一,中国早期的革命作家,大多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很了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的生活并不熟悉。对于他们来说,表现封建势力对个性的压制、摧残,表现知识分子的苦闷、追求,是得心应手的;表现工农群众的生活,需要一个熟悉、磨炼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无产阶级文学是新生事物,必然有一个壮大成长的过程。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出现了文学高峰期,产生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刚刚从娘胎中呱呱坠地,怎么可能马上是成熟、完美的?新生事物往往既带有生气,又带有稚气。对于历史,是不能苛求的。
尽管革命文学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带有浓厚的稚气,但它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也就能够一步步走向成熟。如果我们拿四十年代解放区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和左翼作家在亭子间里写的革命小说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进步的足迹。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无疑都扎实、成熟多了。建国之后,我们产生了《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红岩》等著名的长篇。它们不断再版,远播海内外,教育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盛传不衰。历史事实证明了,表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绝不是把文艺引到“非艺术”的轨道上去,它恰恰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新生面,给艺术之花带来了强大的生机。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过去在表现群众、表现时代的问题上,出现过种种错误的主张和做法。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提法,对创作产生了不小的误导作用。六十年代初,有人提出“大写十三年”,造成的后果更是十分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提出了“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写反走资派的英雄”论,造成的恶果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大写十三年”论,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重要理论依据。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理论庸俗化,也否定了党一贯倡导的“三并举”方针。在这种理论看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统统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否则就是脱离以至有害于自己的经济基础。从这个理论出发,大批文艺作品被打成毒草,文化领导部门被说成“外国死人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新时期以来,我们大力纠正在文艺表现群众、表现时代上的“左”的偏颇。这是完全必要的。为什么过去会长期出现简单化的理论和实践?极少数人是搞阴谋、搞投机的,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头脑过热,以至把正确的东西推向极端、推向它的反面。我们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纠正错误的东西,又保护正确的东西,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表现群众采取否定的态度。现在有没有走极端的情况?我以为是存在着的。例如,过去有人把表现群众推向极端,今天就要“背向群众”,以“表现自我”为创作的最高目的;过去有人把表现新时代推向极端,今天就要“背向时代”,大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沾边甚至格格不入的东西;过去有人把重大题材推向极端,今天就要大写身边琐事,甚至大写个人隐私。用一些人的富有理论色彩的语言来概括,就是要回到“五四”、回到个性解放上面去。马克思主义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承认个性解放的。文艺创作是独创性的精神劳动,尤其需要弘扬作家艺术家的不同个性。但个性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加以支持。创作个性要和创作的民族性、人民性结合起来。“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是针对着封建主义的,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今天,如果把个性解放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业割裂开来,以此作为对表现群众、表现时代的扬弃,那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当前,不少作家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精心创造展现时代风云的作品。比起改革初期来,一些作品在表现社会矛盾、刻画当代人物上有所深化。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不少佳作出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之手。他们通过独立思考,通过对新时期文艺实践的反复比较,认识到表现群众的重要性,坚定执著地要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时代风云、倾吐人民心声。这是很可喜的。在充分估量成绩的时候也要看到,创作现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一面。邓小平指出的“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有的作品也写当代的普通劳动者,但和真正的工农群众相去甚远:昨天还是下岗工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款,住宿于宾馆之中,谈判于宴席之上,出入有私车,陪伴有小蜜,仿佛这就是反映了“历史的巨变”。这种描写,体现不出创业的艰苦,体现不出生活中的真实矛盾,老百姓看了只能发出苦笑。著名作家张平有一次到工厂采访,工人们对他说,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来采访他们,“有时候来些采访的人,大都是想在企业里弄点钱的,或者是那种属于广告性质的象征性的采访。”“从来没有人真正问过我们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在想什么……那么多的编剧、导演、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厂长经理和大款们身上?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吗?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给忘记了抛弃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写一些反映我们工人让我们工人看的作品?”这些话很值得深思。总之,我们的文艺要不要着力表现新时代的群众,怎样真实而生动地把他们表现出来?这仍然是值得郑重思考的问题。
三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这样一个重要意见:“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毛泽东看来:深入生活,实现文艺工作者同群众的结合,是贯彻工农兵方向的根本保证。自《讲话》发表之后,深入生活一直是我们党指导文艺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邓小平在《祝词》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
一切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家,都承认文艺来源于生活。毛泽东不仅承认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观点,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参加社会实践对文艺创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作家不仅要有丰富的艺术实践,还要主动投身到人民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中去,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不仅为了获取创作素材,作为革命的文艺家,还要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净化和深化自己的思想感情,达到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才有可能创造出深刻表现群众生活和心声的优秀作品。他的这一主张从根本上推动作家改变对群众“不熟、不懂”的状况,促使一批又一批表现新时代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这一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已经被大量创作实践所证明。
文艺家要不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这并不是一个很神秘的问题。如果是为艺术而艺术,为个人而艺术,如果你所从事的文艺就是一种自我宣泄、自我慰藉,自然无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如果是为人民而艺术,为多数人而艺术,如果你要表现群众的业绩、人民的心声,那么毫无疑问,就要深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去。否则,只能凭空编造,当一个鲁迅所不希望看到的“空头文学家”。深入生活不是保证创作成功的全部条件,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有生活积累不等于笃定能写出好作品,没有生活积累却注定写不出好作品。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要积极主动地深入生活,但他们的成功和丰富而非凡的生活阅历,深刻而独到的生活体验,都是密不可分的。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所说的诗外功夫,就是生活。
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风,已经刮得很猛烈了。这种否定,经常拿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突破口。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按照这种观点,毛泽东提倡“大众化”,号召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就是“意味着降低文化的水平去迁就农民”。因为“大众”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是“落后”、“愚昧”的。“大众化”的结果是降低了整个民族的文艺创作。“知识者的个性(以及个性解放),知识给他们带来了的贵族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在这里都没有地位以至消失了。头缠羊肚手巾,身穿土布衣裳,‘脚上有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取代了一切。‘思想感情方式’连同它的视野变得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国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见了……这便是延安整风运动后所带来的近现代中国文艺历史的转折点的变革。”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又盛行起“民粹主义”说。它是从国外贩来的,除了重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的基本观点外,还给毛泽东扣了一顶大帽子:“民粹主义”。论者借口民粹派主张“到民间去”,把毛泽东关于深入群众的思想和民粹主义挂起勾来。论者还借口民粹派倚重农民、否定资本主义、幻想建立农民式的乌托邦,把毛泽东关于创立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学说打成“乌托邦”,断言它“顽强抗拒一种现代性”。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否就意味着把前者“降低”为农民?首先要看到,农民并不只是落后、愚昧,作为劳动者,他们的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和历史上的农民已经大不一样了。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中国的改革也是首先在农村打开局面的。中国农民在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中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无论革命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之中都涌现出难以计数的优秀分子。这些人乐于奉献、敢于牺牲、勇于拚搏、善于开拓,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习?还要看到,毛泽东提倡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决不是要把知识分子变成普通农民,把新文化变成农民文化。他要求革命的文艺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归根结蒂,这是为了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新文化,也就是中国现、当代的先进文化。这怎么就是“降低”了作家,“泯灭”了作家的个性?这怎么就是从“五四”精神“倒退”,宣扬“农民思想”?现在,有一种舆论竭力把毛泽东思想同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按照这种舆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把前者同中国的封建传统结合起来;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说成农民思想,正是为这种舆论提供佐证。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是的,毛泽东毕生大力提倡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针对“五·四”新文学的某种欧化倾向,毛泽东号召作家学习群众的语言,研究民族传统的文艺形式,对前者加以提炼,对后者加以利用和革新,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文艺。这决不是什么“降低文化的水平去迁就农民”,也决不是什么对“现代性”的“顽强抗拒”。中外的许多文艺大师,都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艺中吸取养料。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继承者,为什么就不能从民族民间的传统文艺中吸取养料?难道一旦进行了这种继承和吸取,就意味着复旧和倒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纠正了“五·四”新文化中的某种片面性,是他对中华民族文艺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在毛泽东看来,文艺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就要适应群众的需要。这种适应不仅包括内容,也包括艺术形式。适应不是迎合,而是为了提高。只有首先适应,才能进一步谈到提高。他在《讲话》中深刻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说,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要“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普及,要“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论述不但适用于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当代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现在,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他们还要不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解决个体和群体,创作主体和服务对象、创体源泉的关系问题,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废止的。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期,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无论在物质力量还是宣传手段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国内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利益主体越来越多样,贫富差距比过去拉大了许多许多。在这情况下,是否真正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边,是否真正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这对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是严峻的考验。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于口头上怎么表示,而在于是否真正在思想感情上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西方敌对势力要对我们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他们正通过种种渠道,拉动一些人离开党和人民,投入“新自由主义”的怀抱。当金钱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力量的时候,国内也有种种因素诱惑一些人离开人民、离开社会主义。不是时兴“傍大款”么!有些人不仅在经济上傍大款,也用文化来傍大款;不仅傍上本土的大款,还要傍大洋波岸的大款。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唯西方之鼻息是仰。通过“傍”,有些人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了。是“傍大款”还是走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路?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大约不是无的放矢吧!走后一条路是很艰辛的,不可能一夜走红、一夜暴富、一帆风顺,也许还要经历磨难、经受嘲讽。但经过马克思主义长期教育和经受长期风雨考验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多数是有志气的。笔者深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和人民群众相结合这条路。他们会甘于清贫、甘于寂寞,永远做人民的忠实代言人,永远坚守社会主义文艺的园地,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鲜艳的社会主义文艺之花。
标签:文艺论文; 鲁迅论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