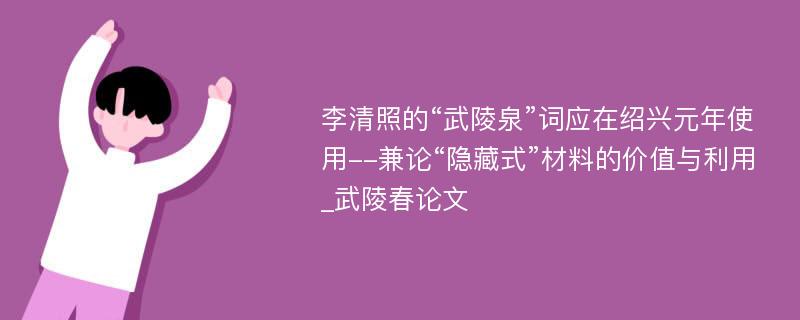
李清照《武陵春》词应作于绍兴元年考——兼说“隐性”材料的价值和利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性论文,元年论文,应作论文,李清照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一些问题,但要解决又苦于没有材料,此即孔子所言“文献不足征”。所谓没有材料应指两种情况,一是的确没有材料,一是有材料但因不容易被发现而暂时处于“假亡佚”阶段,这一类材料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通常以隐性的状态呈现,我们称之为“隐性材料”。事实则隐藏在间接材料的背后,要从这些材料中寻找出足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资料,非要经过认真细致的爬梳不可。这里试以李清照《武陵春》作年的考订,来说明隐性材料的价值和利用。
关于这首词的作年,至今尚无疑议,一般认为是绍兴五年,根据是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明确说她绍兴四年十月“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而双溪又是金华风物。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注: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附《李清照事迹编年》即据《打马图序》云,李清照绍兴五年春赋《武陵春》词。凡文学史、鉴赏词典、诸家论述,只要交待此词的作年,皆莫能例外。
从《武陵春》所表述的情感以及“物是人非事事休”句来看,此词的写作时间应是其夫赵明诚新亡不久,不可能如现在通行编年的说法迟至绍兴五年(1135)。理由如下:第一,赵明诚去世在建炎三年(1129)八月,绍兴五年距赵离世已六七年光阴。据《李清照事迹编年》,绍兴二年夏秋间发生李清照再嫁张汝舟旋又离异之事,如果说《武陵春》词作于李再嫁之前,则“物是人非事事休”是怀念赵明诚,如果说作于绍兴五年,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叹,其所指就难以确定。显然《武陵春》词怀念的是赵明诚,且在赵亡后不久。
第二,《武陵春》词所述情绪与《打马图序》所述在金华的心境不符。《打马图序》描写了她南渡以来流离迁徙,现在卜居金华得以安定,才有兴致可重新操起久违的博弈游戏。其时“意颇适然”,非往日可比,这时不可能写出《武陵春》“只恐双溪舴猛舟,载不动,许多愁”的如此沉重哀伤感情。现节引《打马图序》如下:
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自南渡来流离迁徙,尽散博具,故罕为之,然实未尝忘于胸中也。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泝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乍释舟楫而见轩窗,意颇适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不独施之博徒,实足贻诸好事。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者,始自易安居士也。
可以看出李清照在写《打马图序》的心境,轻松、愉快,纵论博弈,精研打马。仿佛又找到少妇时的乐趣。
我们认为《武陵春》词应当作于绍兴元年(1131)。这和李清照生平行迹未必不合。因为根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云:“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这里所标示的时间具体,行走的方向明确,当属可信。绍兴辛亥,即绍兴元年,这里是说春三月始动身赴越,不是说三月已至越州。从衢州到越州,婺州(州治在金华)是必经之地。李清照漂泊无定所,其漂泊处多有停留,时间或长或短,此次能在婺州停留是理所当然的。从衢州到婺州距离较近,据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五“上婺州东阳郡保宁军节度”载:“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衢州一百三十里,东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二里,自界首至越州二百四十八里”,即衢州至婺州为一百九十里路程。不知李清照在三月的哪一天动身,但到婺州之时正是“暮春三月”之末或是初夏之首,这和词中“风住尘香花已尽”在季令上相合。因山溪春深,故有“闻说双溪春尚好”之句,“闻说”用得准确,毕竟不是真正看到。再说,时距赵明诚去世约一年零七个月,这一年零七个月时间,李清照孤苦零丁、颠沛流离,受尽磨难,在此景况中她就更加思念赵明诚,这一情绪在《武陵春》词中得到充分表现,其“物是人非事事休”之叹,抚今伤昔,无比凄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从《武陵春》词所提供的信息看,李清照经金华停留时间的长短,都与词的写作没有矛盾。此后李清照离开金华去越州,到达越州的时间已是四五月间。
可以这样说,我们能见到有关李清照去金华次数的记载仅有两则材料,一则即为通常人们所说的《打马图序》中的“绍兴四年十月”;一则是《金石录后序》云“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前者是直接的记载,后者则是隐含的记载,但是准确和真实的记载。
《武陵春》词是写金华的风物,因此,人们可以将《武陵春》词的写作时间写在绍兴五年,同样也可以将《武陵春》词的写作时间定在绍兴元年,到底应定在何年,关键是看《武陵春》词的内容、写作情景与李清照生平遭际最相合的时间,而不能先入为主,笃守陈说。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显性材料的价值,更应该关注隐藏在材料背后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的语气来看,《武陵春》词当是李清照首次来金华,而且是刚到金华时所写,写初来乍到的感受。“闻说”的内容有二:其一,“双溪”,这是金华风景优胜之地;其二,“春尚好”,尽管其他地方都已“风住尘香花已尽”,但双溪“春尚好”。如果依《李清照事迹编年》,李清照绍兴四年冬十月避地金华,直至次年春三月才赋《武陵春》词(按,据“风住尘香花已尽”语,当在春末夏初),于情于理皆不妥。
关于《武陵春》的内涵,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云:“其词情凄恻,不但有故乡之思,且寡居凄寂之情,亦跃跃纸上。”大致得之。李清照过去曾写过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表现出对赵明诚的相思之情,其中有句云:“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武陵人,用刘晨、阮肇的典故,唐宋人多用此典,如唐王涣《惆怅诗十二首》之一云:“晨肇重来路已迷,碧桃花谢武陵溪。”宋黄庭坚《水调歌头》:“春入武陵溪”,“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谪仙何在,无人伴我白螺杯。”晁元礼《虞美人》:“刘郎惆怅武陵迷。”可见李清照用此典,透露出她对赵明诚爱的深度,由爱之深转为忧之切,担心赵明诚入武陵而不返。因此,可以推测,“武陵人远”的想法在李清照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记,或许他日将“武陵人远”意思说与夫君听,赵明诚则会说,佳人胜溪女,武陵不足迷。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孤苦无依,益思夫君,故初至金华,听人说起双溪,由双溪又念及武陵溪,正好选择《武陵春》一调来倾吐衷肠。这样理解,不仅可以进一步理解李清照选《武陵春》调名之由,而且也为“物是人非事事休”是悼念赵明诚多了一点佐证。
另外,有一种看法认为《武陵春》作意与李清照改嫁有关,《草堂诗余别录》云:“后改适人,颇不得意,此词‘物是人非事事休’,正咏此事。”有人申述了这一观点,认为李清照受张汝舟之骗,是受害者,而张是贪狠的诈骗者。“物是人非事事休”既是对亡夫的悼念,也有对恶人的诅咒。但持此观点的前提是系《武陵春》词作于绍兴五年,显然这一前提不足信。关键是《草堂诗余别录》的观点和后入申述的观点都未能将《武陵春》的写作时间充分考虑进去,只认为“人非”之“人”不是赵明诚而是张汝舟。李与张的婚姻短暂,事在绍兴二年夏秋间,如依旧说,事隔三年后,至绍兴五年李清照写《武陵春》重提与张的关系,意义何在?况且绍兴五年李清照在《打马图序》表述的是一种动乱后得到安宁的闲适情绪。
可以确定李清照在金华的作品除《打马赋》、《打马图序》、《武陵春》外,还有一首《题八咏楼》涛。八咏楼也是金华一景,诗云:“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这首诗和《武陵春》词的情绪不同,而与《打马图序》的心境相近,其创作时间当是通常人们所认定的李清照卜居陈氏第的绍兴五年。
以上的考订结论尽管在解说《武陵春》词时有优于旧说之处,但不敢说一定正确,我想至少可备一说吧。而考订中最能起作用的一则“隐性材料”(“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并没有明白告诉人们李清照本年经过金华,所谓经过金华是隐藏在“由衢赴越”的记载之后的。正因为我们面临的材料是有限的,而文学史上存在相当多的问题还需要去解决,所以我们要合理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充分挖掘文献资料的价值,即有理有据去恢复古人因行文的用意或特殊需要而被简省了的文字,而这些在当时并不重要的被简省了的文字对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作家作品却是重要的。当然,文献资料虽是“隐性”的,但它是客观的,这和一般性的推理不同,如果将隐性材料凭主观臆断而赋予无限的不确定的意义,那就会有违解决问题的初衷了。
这里我想再简要说一下另外两种方法。第一,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比较,使“隐性”变为“显性”。如孤立看李清照的《武陵春》词的形式,其独特性就处于隐性状态中,如将《武陵春》在形式上和此前同调的词作一比较就能发现,李词在形式上有一特殊之点未为今人注意,就是和以往的调式稍异。此前《武陵春》词皆48字,末二句为七五式,而李清照此词49字,末二句为七三三式。过去一种说法是:“‘载’字衬。”(《古今词统》)将“载”看作是衬字,讲不通。李清照精于词学,追求新意,在写作《武陵春》词时作了一点“变调”处理。虽为一宇之增,但有值得探讨之处。第二,通过对零碎散乱的材料归纳整理,使“隐性”变为“显性”。在上述有关李清照词作年考证中,除将“由衢之越”外补上必经婺州的简省文字外,其他也用了归纳的方法。在另一篇讨论李白入京待诏翰林的身份的文章中,也是使用的“隐性”材料作归纳整理的,结论是李白待诏翰林的身份是道教徒,此处从略。
但有一种情况,材料是明晰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我们“视而不察”,这肯定不是“隐性材料”,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向来是被当作“诗”来看待的,因此有人在分析这首“诗”时就说陈子昂标举诗歌革新,倡兴寄,崇风雅,故在诗歌体式上打破传统,开“以文为诗”的先河。其实,“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云云,见于陈子昂的好朋友卢藏用的《陈氏别传》,原文是这样的:“子昂知不合,因钳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之知也。”这里的表述相当清楚,“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其中“诗”“歌”并举,分明说“前不见古人”云云,只是伴随某一节拍或旋律的信口吟唱,而不是“诗”。“诗”“歌”在卢藏用那里分得一清二楚,这和今天我们将诗歌连用与散文相对应的概念不同。所以卢藏用在编陈子昂集时,并没有将“前不见古人”云云当作诗收入。(注:参见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杜,2001年,第39-41页。我们讨论的重点和目的不同。)知道这种关系,在讲《登幽州台歌》时才能心中有数,而不至于在诗歌体式发展史上夸大它的意义。《陈氏别传》的材料显然不是“隐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