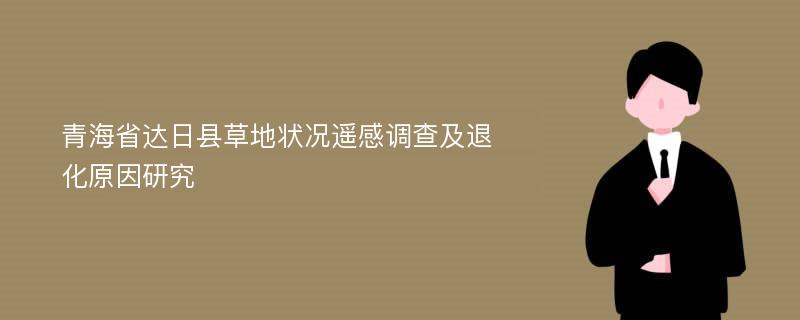
卫亚星[1]2000年在《青海省达日县草地状况遥感调查及退化原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草原退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本研究对青海省达日县草地状况进行了遥感调查,并对退化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本研究采用3S技术,即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将美国气象卫星NOAA/AVHRR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地球资源卫星TM影象用于草原监测,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研究,证明此方法调查草原植被速度快、精度高、成本低。 达日县退化草地调查,以遥感技术为主,将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技术和地面实地采样技术相结合;将历史资料(1985年畜牧业区划报告、草地类型图、草地等级图、季节牧场图、地形图等)与1997年资料(NOAA资料、TM资料、野外测产资料)相结合,经图像处理和综合评判后,以分算到乡的形式,提供达日县土地利用(总面积、密灌、草地、可利用草地、黑土滩、裸岩)、草地级别、产草量、载畜量(理论载畜量以及冬春场和夏秋场载畜量)、产草量季节变化等方面的资料和图件。 本研究主要利用1997年4月15日~10月15日每半月1次的NOAA数据,求算出各幅影像的NDVI值,然后与同时间在地面测定的牧草产量之间按同名点进行统计计算,建立了以植被指数为自变量X,以单产为因变量Y的对数关系式:Y=249.137~*LgX-347.213,相关系数r为0.823。 调查表明,1997年达日县可利用草地总面积为10 793.36km~2,其中5级草地5 203.379km~2,6级草地5 590.283km~2,分别占可利用草地的48.30%和51.70%;理论产草量、可食牧草量和采食总量分别为345.4537万t、278.7811万t和139.3906万t;理论载畜量、冬春载畜量和夏秋载畜量分别为100.24、87.25和125.2万羊单位。 通过对比1985年和1997年两次草地畜牧业资源调查的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可利用草地面积减少,黑土滩面积增大;可利用草地中高等级草地比重减少,低等级草地比重增大;草地产草量和载畜量下降。 草地退化有人为和自然条件两方面的原因。达日县的理论载畜量从1985年的172.43万羊单位,逐年下降到1997年的100.24万羊单位,其实际载 畜量也由 1985年的 125.76万羊单位(52.of万头只)波动到 1997年的 120.90 万羊单位(约50万头只),故达日县草地过牧。本研究也表明亚洲腹地极干 的荒漠气候对达日县草地有深刻影响。 过牧是达日县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由于全球气温升高所引起的荒漠化, 也是处于半干旱一半湿润干旱区的达日县草地退化、大片黑士滩产生的重要 原因。但合理的放牧制度,对延缓和阻止荒漠化过程(黑土滩的形成)的作用 是巨大的。
陈全功, 卫亚星, 梁天刚[2]1998年在《青海省达日县退化草地研究 Ⅰ退化草地遥感调查》文中提出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地面调查等多种技术,通过对达日县1985~1997年地面观测资料和遥感影像的对比分析,确定了该区可利用草地系数、可食牧草系数和牧草利用系数,建立了草地资源遥感动态监测模型;模拟计算了全县及各乡的草地资源产草量、理论载畜量、季节牧场载畜量和草地生长动态;并且分析了全县草地资源退化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绘制了草地产量、载畜量和草地分级等图件。上述研究结果,对达日县草地资源的持续监测及严重退化的高寒草甸的治理,可提供科学的依据。
周华坤, 赵新全, 周立, 唐艳鸿, 刘伟[3]2005年在《层次分析法在江河源区高寒草地退化研究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说明以江河源区退化高寒草甸为对象,利用层次分析法,探讨了高寒草地的退化原因和恢复治理措施的有效性。结果表明:长期超载过牧和暖干化气候是导致高寒草甸退化的主导因子,贡献率为65·99%;伴随草地初始退化出现的鼠虫和毒杂草泛滥危害是加速高寒草甸退化的重要因子,贡献率为15·03%;人类不合理干扰造成的高寒草甸退化也不应忽视,贡献率为9·64%。各个恢复治理措施组合权重的分配格局相对均衡,其中围栏封育和划区轮牧(E2)与控制放牧强度(E1),效益较好,组合权重达0·3007。层次分析法可为草原管理,防止草地退化、恢复治理退化草地、优化利用草地资源提供定量依据。
卫亚星, 王莉雯, 刘闯[4]2009年在《利用遥感手段监测草场退化》文中指出利用遥感手段监测草场地上生物量的变化,对防止草场退化,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TM数据建立了青海省达日县1986年和2000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形库和属性库,统计出了该县的各种土地覆盖类型面积值。研究结果表明,14年来,达日县草地面积减少了830 hm2,草场退化形势严峻。研究同时表明,利用遥感数据监测草原具有其它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
马轩龙[5]2008年在《基于3S技术对青海省草地资源生产力的监测》文中研究说明本次研究基于“3S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草原监测技术路线,对于青海省各地区2007年草地资源生产力进行了调查。并基于季节放牧和关键场理论的思想,在对青海省草地放牧承载能力进行评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引入了农林副产品对于整个放牧系统的潜在贡献,并实际计算了贡献程度和贡献率,将之折算为家畜单位。通过本次研究,对于草原监测中的数据使用及处理方法、产草量模型的建立、K系数的计算以及整个技术流程都有了更加深刻和系统的认识。本次研究证明,基于理论载畜量的放牧超载评定存在很大的不足,无法真实的反映草地实际放牧利用现状,因此引入关键场的概念,使得对于草地的家畜实际承载能力有更加准确的估算。同时,要对草地的放牧超载程度进行评定,除了考虑草地资源的生产力之外,有必要将其它因素对于放牧系统的贡献也考虑进来,并进行换算,使得最终计算出的放牧超载率能够更加客观的反映草地的真实超载情况。本次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草原监测遥感数据的使用在本次对青海省2007年草地资源生产力的研究过程中,大量的使用到了NASA提供的可以免费下载的MODIS植被指数产品,经过本次研究的总结,MODIS在进行大范围的草原植被监测中具有覆盖范围大、分辨率适中、时效性好、数据质量有保证以及免费下载等优势,可以作为大面积草原监测的遥感数据。2.各地区的产草量回归模型及K系数由于不同地区在自然资源以及放牧利用模式上的差异,在对我国草地地上生物量进行遥感估测的时候,要分地区并且针对各地区内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放牧利用特点,分地区计算三个K系数并建立不同的草地地上生物量回归模型。这种分区计算的思想,体现了地区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草地资源的现状。青海省各地区K系数及产草量回归模型如下:西宁:K1=0.882733 K2=0.866041 K3=0.673094 y=0.0383x~(1.3173),相关系数(R~2)=0.4044上式中,y为草地地上生物量,x为NDVI影像像元值,下同。海东:K1=0.857973 K2=0.862901 K3=0.680636 y=27.986x~(0.5306),相关系数(R~2)=0.4061海北:K1=0.863196 K2=0.888339 K3=0.655066 y=0.0156x~(1.3961),相关系数(R~2)=0.4321黄南:K1=0.907119 K2=0.889341 K3=0.654232 y=0.1384x~(1.2016),相关系数(R~2)=0.4246海南:K1=0.883994 K2=0.865800 K3=0.674699 y=2.7992x~(0.7728),相关系数(R~2)=0.4035果洛:K1=0.897720 K2=0.883677 K3=0.645573 y=0.0131x~(1.4092),相关系数(R~2)=0.4091玉树:K1=0.879160 K2=0.874059 K3=0.647286 y=0.2915x~(1.0206),相关系数(R~2)=0.4710海西:K1=0.879487 K2=0.880886 K3=O.6525096 y=6.0081x~(0.6967),相关系数(R~2)=0.40423.农林副产品对于放牧系统的贡献牧民除了在草地上放牧家畜之外,还有其它的饲养手段,譬如补饲和定居等。这些因素对于整个放牧系统的贡献必须定量化的考虑进来,才有可能对于草地实际的放牧超载程度进行一个准确的计算,使结果更加接近于真实情况。通过一定的折算标准,青海省各地区2007年农林副产品对于放牧系统的贡献分别是:西宁市85.9万羊单位(SU),海东地区103.24万SU,海北藏族自治州30.29万SU,黄南地区8.8万SU,海南地区32.7万SU,果洛地区1.2万SU,玉树地区4.5万SU,海西地区23.6万SU。4.青海省2007年草地放牧超载情况根据青海省各地区2007年实际家畜数量,以关键场载畜量为基础,结合农林副产品对于对放牧系统的贡献率,2007年青海省各地区草地超载率分别如下:西宁市69.18%,海东地区97.9%,海北藏族自治州-32.2%,黄南地区73.3%,海南地区255%,果洛地区38.8%,玉树地区58.4%,海西地区-29.7%。
黄晓宇[6]2017年在《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生态健康评价与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文中认为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属于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也是青海省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三江源的自然环境不但关系到省内各民族同胞的安居乐业,甚至影响全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过去的几十年,三江源的生态环境逐渐退化,土地呈现荒漠化态势、水土流失等问题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对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进行生态健康评价和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利用遥感影像数据、景观数据、气象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结合目前通用的生态健康评价模型(P-S-R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试验区县域生态健康评价;运用CASA模型估算NPP,计算得出试验区的景观价值,最终以各县所处生态健康水平为依据制定补偿调整系数,得到试验区的生态补偿标准。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两个主要结论:(1)2010到2014年,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生态系统整体维持初步健康水平,其中海南藏族自治州整体生态健康水平呈下降态势,大部分区域由亚健康水平转向不健康水平;黄南藏族自治州整体生态健康水平略有下降,但始终以健康水平为主;果洛藏族自治州整体生态健康水平呈上升态势,始终以健康和很健康水平为主;玉树藏族自治州整体生态健康水平呈下降态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唐古拉山镇的生态健康水平显著提高。(2)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的补偿标准为341.97×108元,其中治多县的补偿标准最高为66.57×108元,尖扎县的补偿标准最低为2.13×108元。将生态补偿尺度扩展到州县级别,得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生态补偿值为45.01×108元;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生态补偿值为22.59×108元;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生态补偿值为74.45×108元;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生态补偿值为173.4×108元,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唐古拉山镇的生态补偿值为26.52×108元。
刘纪远, 徐新良, 邵全琴[7]2008年在《近30年来青海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的时空特征》文中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MSS图像、90年代初期TM图像和2004年TM/ETM图像支持下,通过三期遥感影像的直接对比分析,获得了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空间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70年代以来青海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的主要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是一个在空间格局上影响范围大,在时间过程上持续时间长的连续变化过程。研究发现,三江源草地退化的格局在70年代中后期已基本形成,70年代中后期至今,草地的退化过程一直在继续发生,总体上不存在90年代至今的草地退化急剧加强现象。草地退化的过程在不同区域和地带有明显不同的表现,如在湿润半湿润地带的草甸类草地上,发生着草地破碎化先导,随后发生覆盖度持续降低,最后形成黑土滩的退化过程;在干旱、半干旱地带的草原类草地上,发生着覆盖度持续降低,最后形成沙地和荒漠化草地的退化过程。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草地退化可以分为7个区,各区草地退化在类型、程度、范围与时间过程方面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周强, 刘林山, 张镱锂, 陈琼, 张海峰[8]2011年在《高原牧区草地变化对牧民粮食安全的影响——以青海省达日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粮食安全在概念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关注农业区粮食安全的同时,牧业区粮食安全的研究也值得重视。论文从青海省达日县牧区牧民食物能量折算入手,构建了最小人均草地面积和草地压力指数两个计算方法,并以乡为基本单元,对各乡粮食安全进行定量计算。计算结果表明:达日县1987—2007年最小人均草地面积和草地压力指数呈增加趋势,1997年粮食安全区、警戒区、短缺区、危机区4个等级均有分布,至2007年该区域已全部演变为粮食短缺区和危机区,主要原因是草地退化严重,人口数量增加,人均草地面积减少以及技术和物质投入不足,牧业生产条件恶化。
李惠梅[9]2013年在《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及补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江源是我国江河中下游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但在近几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三江源区源区草地植被退化退化严重已经使源头水源涵养能力急剧减退,并已直接威胁到了长江、黄河流域、乃至东南亚诸国的生态安全,国家自2005年始在三江源区大规模实施生态移民和限制放牧等工程以缓解草地退化的格局、并逐渐恢复和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三江源生态保护及补偿工作至今已7年有余,源区草地植被和湿地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生态经济和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问题,其中以依赖当地草地资源而生存、三江源区的最主要经济主体——牧户的福利和发展是尤为重要且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牧户的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而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计划的前提是牧户的福利不下降或得到科学合理的补偿,在补偿不到位或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牧户参与三江源生态保护行为将极有可能使牧户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牧户的生活甚至陷入贫困化的威胁,既不符合公平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又容易挫伤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的积极性,影响三江源草地生态恢复及保护的效果和速度。因此,研究牧户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的福利内涵及变化情况,以牧户福利得到改善为目标制定补偿标准和调整补偿机制,激励牧户继续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对最终持续推进三江源区中后期的生态保护开展和维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结合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千年生态系统报告的核心思想,界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中人类福利的内涵,并对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在牧户福利优化的基础上核算了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过程的补偿标准,并以行政区划为界线提出了各县的补偿次序、不同补偿性质的补偿标准和不同的发展保护模式。本文结合森的能力框架探讨了福利的内涵,界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功能对人类福利的内涵,指人类在生态系统生产和利用中的自由选择和能力,而贫穷指可行性能力和发展的受限,即福利的下降。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破坏将严重威胁人类福利(尤其是穷人的福利),关注强烈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贫困人群的福利,并科学有效的实施生态补偿通过外部效应内部化,以激励生态保护的行为进而实现生态保护和人类福利改善的双赢。本文以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的牧户为研究对象,分别以参与三江源草地的生态移民和参与草地限制放牧的牧户为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的生活、健康、安全、社会关系、环境、社会适应、自由、生活实现和幸福等9项功能的状况,并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确定了不同层次功能的权重,并认为福利各功能之间是递进式的即低阶功能的实现程度会促进高阶功能的实现,最后分别评价了三江源移民和限制放牧的牧户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前后的福利变化情况。研究表明,三江源移民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后福利水平下降,主要是由于失去草地使用权后导致收入的下降、资源使用和参与环境管理的自由受到严重的影响、移民以前在草地放牧生活中形成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被割裂使社会关系的支持功能下降、移民的生存技能未得到提升进而影响到了如社会适应、生活实现和幸福感等高阶功能的实现,使移民的福利功能下降;牧户参与限制放牧后的福利水平略有提升,是由于牧户限制放牧后虽然使其收入水平有了一定的下降,但居住条件和医疗保障等各功能的提升使生活、健康、安全和社会关系、坏境等各功能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并且牧户使用草地的权益比移民限制程度小、并且牧户并未大规模迁徙因而社会适应能力受损不明显,使限制放牧牧户的福利水平略有提升。可见,牧户参与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行为使其收入水平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收入水平能维持日常的生活所需时,牧户的其他福利功能的改善能使牧户的福利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当收入水平下降显著,而牧户的其他生活能力未得到提高和其他福利功能尚不能实现时,牧户的福利往往会明显的下降,甚至陷入贫困化。因此,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牧户的收入能力和自然资源产权承载的其他福利功能都是牧户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补偿过程中均应该被重视、被补偿,尤其应该在低阶福利功能如收入被补偿的基础上,关注自由和生活实现等高阶功能的补偿和提升。本文通过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均衡分析发现,要使牧户的福利水平不下降或改善牧户的福利水平,则必须提高补偿标准和减少牧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因此,在提高补偿标准的基础上,更要考虑如何通过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提高牧户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层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升牧户的就业技能和可行性能力,让牧户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帮助通过非放牧式的生计方式转变和其他多种途径经营来获取经济收入,获得比放牧收入更高的收入才有可能会逐渐带动牧户逐渐减少和放弃对草地的依赖和利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草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而形成牧户的可行性能力的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的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本文通过文献分析认为生态补偿是贫困减缓的重要机制,在生态保护行为意愿和福利损失的基础上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明确界定利益相关方和区域的生态保护责任,构建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福利均衡,才能引导牧户实现主动参与式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人类福利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本文基于三江源地区2002-2010年的气候因子数据,模拟了近十年以来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后的植被覆盖度(NPP)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核算了自2005年保护以后三江源各县的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增加情况;研究表明,三江源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在2005—2010年表现出先缓慢下降而后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三江源草地生态恢复及保护行为在逐渐起效,体现出三江源草地生态由降低退化的速度演变为生态环境逐步恢复及改善的趋势特征;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在区域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海拔比较高、气候比较恶劣和退化严重的区域草地生态恢复比较慢、保护效益增加值比较小,增加幅度最大的是甘德县,单位面积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了1.086万元/km2,唐古拉乡和曲玛莱县的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增加量分别为0.221万元/km2和0.637万元/km2,增加量最小;自2005年保护以来的5年中,三江源区每单位面积草地的保护效益增加值为0.902万元/km2,并拟将各县的草地生态保护效益增加量作为激励三江源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的奖励性补偿标准。本文分别计算了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因草地资源使用权被禁止或被限制而在实际和理论上损失的经济收入(机会成本)和各项参与成本。牧户的福利损失是理论上应该补偿给牧户以保持福利均衡的,三江源移民和牧户实际机会成本损失价值分别为4.2846万元/户和1.6478万元/户;基于草地理论载畜量而核算得到的三江源牧户平均参与成本为3001.63元/hm2,平均机会成本损失为750.458元/hm2,由于各县的海拔高度、草地退化程度和交通通达度不同而使三江源各县的参与成本和机会成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补偿的过程中应该被补偿的参与成本内容和标准各不相同。本文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结合牧户的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的意愿,研究了牧户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为避免使福利受损而应该获得的最小受偿意愿额度,并作为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保持福利不下降的参考补偿标准。研究表明,三江源牧户中约66.7%的牧户表示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牧户参与保护行为后福利水平至少不变或不下降是牧户参与保护意愿概率提高的重要保障,区域工作机会较多、生计方式比较丰富和生态保护外部性认知水平高的牧户参与生态保护响应的意愿较高。可见,让牧户分享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益、促进牧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和提升牧户的就业水平让牧户的收入水平得以保障并提高,是促进牧户的保护积极性的关键。三江源生态移民基于平均值和中位值的受偿意愿额分别为1.2886万元/年·户和2.05668万元/年·户,限制放牧的牧户基于平均值和中位值的最小受偿意愿额分别为0.6733万元/年·户和1.14316万元/年·户,移民因草地生态保护行为中草地使用权被限制程度大(被禁止)和损失比较高,因此移民的受偿意愿高于限制放牧的牧户。本文以三江源的行政区划为界线,基于草地生态恢复效益和补偿效率计算了补偿优先度,结合三江源草地的生态退化恢复难度而划分了补偿区域的优先次序,并探讨了各区域的补偿标准和发展模式。将保护效益增加最明显和优先度最高的三江源杂多县、达日县和玛多县列为优先补偿区,该区域通过生态移民来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而移民得到最高的激励性质的补偿标准,即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参与成本之和来补偿,同时应该参照移民的最小受偿意愿额2.05668万元/年·户;将保护优先度最低和恢复难度最大的唐古拉乡、称多县和治多县划为重点保护补偿区,同样通过生态移民来保护,并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和实施成本作为鼓励兼补偿性质的补偿标准,并使补偿标准参照移民的WTA;将优先度次之的久治县、班玛县、曲玛莱县和玉树县列为次级补偿区,实施限制放牧,并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机会成本之和来补偿牧户的福利损失,并使补偿标准参照牧户的WTA即1.14316万元/年·户;将保护效果疲软的其他区域列为潜在补偿区域,可以在限制放牧的过程中适当发展绿色经济,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交易成本之和来补偿,以改善牧户福利和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三江源牧户福利优化为目标,提出了应该对牧户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的经济收入损失和各种福利功能进行补偿,并核算了三江源区域可持续的、激励性质的补偿标准,以期望通过提高补偿标准和实施差异化的补偿,在改善牧户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提高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实现三江源保护区生态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在今后考虑如何提升牧户的可行性能力和加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并构建整个三江源源头和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以解决补偿资金不足和实现福利均衡,是实现可持续保护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涂军, 熊燕, 石德军[10]1999年在《青海高寒草甸草地退化的遥感技术调查分析》文中认为应用遥感技术探讨了巴颜喀拉山北坡,青海省达日县段退化高寒草甸草地的成因、分布、面积和遥感判译标志,将研究区内高寒草地划分为5个类,2个亚类和3个退化草地型.重点分析了高山草甸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和遥感影像特征
参考文献:
[1]. 青海省达日县草地状况遥感调查及退化原因研究[D]. 卫亚星. 甘肃农业大学. 2000
[2]. 青海省达日县退化草地研究 Ⅰ退化草地遥感调查[J]. 陈全功, 卫亚星, 梁天刚. 草业学报. 1998
[3]. 层次分析法在江河源区高寒草地退化研究中的应用[J]. 周华坤, 赵新全, 周立, 唐艳鸿, 刘伟. 资源科学. 2005
[4]. 利用遥感手段监测草场退化[J]. 卫亚星, 王莉雯, 刘闯. 自然灾害学报. 2009
[5]. 基于3S技术对青海省草地资源生产力的监测[D]. 马轩龙. 兰州大学. 2008
[6]. 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生态健康评价与生态补偿标准研究[D]. 黄晓宇. 青海师范大学. 2017
[7]. 近30年来青海三江源地区草地退化的时空特征[J]. 刘纪远, 徐新良, 邵全琴. 地理学报. 2008
[8]. 高原牧区草地变化对牧民粮食安全的影响——以青海省达日县为例[J]. 周强, 刘林山, 张镱锂, 陈琼, 张海峰. 自然资源学报. 2011
[9]. 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及补偿研究[D]. 李惠梅.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10]. 青海高寒草甸草地退化的遥感技术调查分析[J]. 涂军, 熊燕, 石德军.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