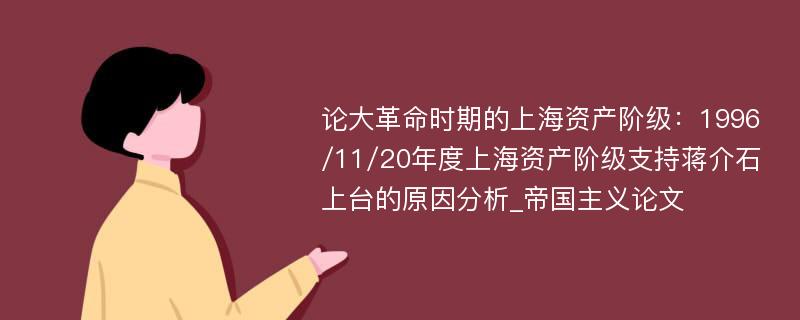
论大革命时期的上海资产阶级——兼析上海资产阶级支持蒋介石上台的原因RQ收稿日期:1996-11-2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阶级论文,上海论文,收稿论文,大革命论文,蒋介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K262. 8
何干之在其《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中说到:“是谁给蒋介石以反革命的决心和力量呢?是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驻防上海的武装和它的分裂政策,是上海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援。于是,蒋介石就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策动下,布置史无前例的反革命政变。”那么,上海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支持蒋上台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还未见有文专门的探讨。以往的著文都是侧重论述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其中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上海资产阶级支持蒋上台的原因,但都不全面。笔者认为全面、深入地研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全面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
五卅运动以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风暴的推动下,接受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军阀”的口号,逐渐倾向革命。虞洽卿在1926年6月的一次讲演中声称:中国人民已决心取消不平等条约,不达目的不止,同时,对于阻害贸易的军阀政治,决不能置之不问。[1]包括一些上层资本家在内,许多人对北伐战争进行了实际的支援。但与此同时并在这之后不久,上海资产阶级为什么又从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转而支持蒋“清党”呢?
首先要从他们所从属的阶级的矛盾性格上寻找原因。上海资产阶级在他们形成一个集团之前,由于他们存在着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舞台上,“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政府的积极性”。[2]他们参加了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和随后的收回路权、矿权的斗争。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组织商团,“参加光复上海之役”。[3]可以说上海的独立是革命党人与上海商团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4]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他们主张市面上的美货,经过总商会检查贴上印花后,即可出售。实际上使贩卖美货为合法的行为,公然破坏这一爱国行动。[5]在辛亥革命中,当上海商界纷纷要求将盛宣怀的官僚买办产业充公赔偿时,作为江浙资产阶级代表的陈其美却以沪军都督的名义,两次发布文电,反对没收盛氏产业和追查其罪状,说“现在没收私人财产,似未足以折该家属之心。”[6]辛亥革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联系也更加密切,更具有妥协性;但另一方面又因战后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发展,使民族工业发展受挫,所以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也进一步加剧,这就促使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转向革命。五卅运动中,以总商会为代表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要求解决五卅事件,要求改造租界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廨,取消“四提案”等反帝斗争目标上,与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群众是一致的,以此成为联合斗争的政治基础。从具体活动来说,上海总商会签署了罢市命令,对总罢市的迅速实现有重要作用;对经济绝交和抵制英日货斗争,其根本态度也是支持的,开市以后还进行了组织和倡导,促进了这项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承担了募捐筹款的任务,从经济上支持了罢工斗争的持久进行。上海总商会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经收的募捐款,总计洋236万元,银43.3万两。[7]这笔巨款,是发放罢工工人生活费的最基本来源。以上这些是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主要活动内容,对上海乃至全国五卅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以总商会为代表的上海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不像工人阶级和市民群众那样彻底和坚决,而是表现过动摇和妥协。例如,就“商界已先行开市”这点来说,纵然罢市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是很有限的,但总商会之所以决定开市,正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减少他们的损失。据查,公共租界各马路因罢市损失合计银367.8万余两,又洋775.4万多元。[8]其中福建路计商号229家,共损失375899元,[9]平均每家商号达1700多元。特别是当土部局停电后,总商会和上海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妥协,由热衷疏通栈货到鼓噪英日货通销,由尽力募捐援工到鼓动和斡旋复工,对五卅运动产生了消极的作用。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态度,似乎带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运动的初期他们都能热情支持并参加,但最终的结果都以妥协而告结束。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他们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外来的侵略和压迫,是始终处于对抗地位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会参加到反帝统一战线中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暂时没有外国竞争者,所以上海资本家们能够扩展到原先为外国势力所支配的制造业和现代银行业中去。到了1924年,由于外国竞争势力卷土重来而结束了中国资本家的‘黄金时代’。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工业家们的经济危机,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是可恨的。中国资本家面对着的,不仅是那种因通商条约规定的只纳百分之五关税的进口货物的竞争,[10]而且还面对着那些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工业的竞争。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工业比中国人自己的企业拥有较雄厚的投资和较高超的技术条件”。[11]当然,由于帝国主义是有种种特权以及在资金、设备、技术、能源、原料等方面的明显优势,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以工业原料为例,“除榨油业之大豆,国产差堪自给外,余则几无一业能完全脱离舶来原料而独立者”。[12]能源供应对外依赖性也很大,上海的工业用煤,主要依靠进口。[13]这样当然要受制于人。这是上海资产阶级在运动中支援和妥协的根本原因。
历史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国共合作、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矛盾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引用了北京《晨报》上的两句话,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他们对北伐的态度正是这样。北伐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统一全中国。因此他们同情北伐,支持北伐。但是当北伐就要成功,工农运动蓬勃兴起,革命向纵深阶段发展之时,他们又退缩了。资产阶级是依靠资本剥削而生存的阶级,它不能容忍影响资本剥削、危及自身经济利益的工人运动。而当时的工人运动都是靠共产党来领导的,自然他们就把满腔的怨气往共产党身上发泄。
被工人运动力量吓破了胆的上海资本家,这时便狂乱地寻找国民政府中右翼势力结盟。在1927年3月底,蒋正处于与武汉国民政府左派分裂过程中,并着手在南京建立他的反动政权,所以“蒋介石表现出了他是上海资本家天然盟友的样子”。[14]蒋早年就在上海活动过,与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这一点,其它著文大都有介绍,此不赘述。
二
由于工农运动(本文限于篇幅,重在介绍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左”倾错误,便促使上海资本家迅速地向蒋介石一边靠拢。
“1926年广东北伐的革命战争事实上乃是五卅运动之直接继续,从群众的反抗示威,抵货罢工,进一步而至于更高的斗争形式——武装的革命战争”。[15]在当时,北伐战争与工农运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以武汉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武汉的罢工运动,“震动于全国,影响于世界;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世界一样。这一事件,在帝国主义的英国议院里引起了讨论……在中国的中部及长江下游,资产阶级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责国民政府不当援助工人,高呼国民政府赤化,……”。[16]武汉罢工运动之所以如此蓬勃的发展,固然是受了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但更重要的原因乃是武汉工人的生活太苦——工资太少,工作时间太长,待遇过于恶劣。北伐军到达武汉不到两月,武汉总工会会员已扩大至30万人,工会扩大至200个左右,9月以后罢工浪潮便一天高过一天。同时,农民运动亦迅速发展,“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17]群众革命力量一经发动起来,它们就获得了其自身的生命力,而不可能将其限制在“民族革命”的狭隘目标之中。就在这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工农运动中“左”的念头出现了。请看下面的事实。
北伐军初到时,忿于北洋军阀统治的实业界、金融界和地主,纷纷表示效忠革命事业。然而渐渐地,他们对“农工团体日益增长的权势和蛮横”,心怀不满,惶惶不可终日。1926年11月,武汉总商会抗议“工人要求过渡”。[18]总商会向武汉中央商民部转呈意见书,说:“钱业店员工会成立,提出各种条件。并于钱店设立支部,各店经理无法维持。汉口钱店原有一百五十余家,今停闭者一百一十余家(钱业公会意见)。……工会成立,店员店东意见隔阂。一经质问,即援引各店权操之店员之例而为恐吓。店员良莠不齐,踩盘抑介渔利,客多恨之。行东不敢质问,恐发生禁锢黑房,戴绿帽子游街等事。工会成立,薪资加倍,而又长支乱扯,一不如意,则曰压迫行员,我报告工会,以反革命论。工会自行减缩工作时间,早晚以九时为起讫,稍逾规定时间,即侮辱殴毁。店员自由解放,实力商家群相离汉,市面无恢复之日,工员多失业之人。店员行动,无在不与店东为仇,无在不与现行保护工商业者中小商人及小资产阶级政策大有危害。三四家设一工会支部,费用要店东负担,稍有异言或失词,童子军团、纠察队即刻上门,店东谁敢归店?”[19]由于国民政府没有能够有系统地、计划周到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而是要工人自发地起来斗争,以改善过于恶劣的生活;又由于党和工会没有足够的干部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加强工人的组织纪律,而当“左”倾错误出现之后,各方面又采取强迫的办法(如逮捕工人),就不能不激起工人的愤怒,以致发生恶性循环。
在3月和4月初试图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武汉城里充满了口号、标语、集会和游行示威,有些宣传画上直接写着:“打倒资本主义”,[20]促使已经过激的武汉无产阶级提出了许多更加苛刻的要求:要求预支2至3年的工资,要求每年发给15个月的工资,要求每年4周假期,工资照发,外加阴历年两周休假,阳历年3天休假和一切革命节日休假。家有婚丧大事,付给六个月的额外津贴。工人无故被解雇,付给相当于3年的工资。人力车夫索价尤高,客人一到江岸码头,他们便涌来围住,不许客人自拿行李,然后每件提包索取5元,车价高出正常要价的许多倍。[21]
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资产阶级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2)工人群众在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现象。以武汉较大的企业纺织工厂为例,据调查,当时纺织厂除因厂主潜逃或发生工潮而关闭的泰安、大丰、宝丰等家外,继续维持的有中新、裕华、一纱等家。这些厂的工人群众,从1927年1月到5月,因集会或游行而停产达十四次之多,每一日昼夜损失两工。由于规定病假工资照发,所以病假人数激增,每厂都在一百人以上。工人怠工现象也不断增长。[22]加上休息日增多和其他原因,使得生产额急剧下降。1927年3月申新厂的生产额较1926年9月减低约30%,裕华厂在同月的生产额较1926年10月减低约30%,第一纱厂同月的生产额较1926年9月减低约55%,[23]情况是相当严重的。(3)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分的斗争方式。由于当时工会在政治上都执行着一种政府机关的职能,因而在斗争中往往表现出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工厂商店,强取什物,强制雇工,对待劳资纠纷,往往以武力解决。工人纠察队也履行执法机关的职能,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也承认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总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24]但是处在当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形势下,人们的精神“愈益混乱不堪,大家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25]在这种动摇、犹豫的情况下,共产党和工会的同志们没设法拉资产阶级一把,即让他们有利可图,这无疑是把资产阶级推向了反动势力一边。
这些“左”倾错误在当时造成很坏的影响。正如刘少奇同志说的那样,“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加上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走上了另外的路途。”[26]
由于武汉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影响,1927年1月的武汉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蒋介石一到武汉,武汉就极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在宴会上说,当前的基本任务应当是进军上海,因为上海能为全国的繁荣创造条件。个别发言暗示,镇压工人“骚乱”是胜利完成国民革命的前提。武汉资产阶级不通过国民政府而向蒋提供借款(蒋向武汉资产阶级借足了300万元“私人借款”。)[27],这表明资产阶级想到外界寻找出路,以保证在整个中国进一步发展工商业。他们想把赌注压在能够带来“安定”的人身上。[28]武汉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不能不影响到上海资本家们的行动向背。
更何况,进入1927年,上海地区更是工潮迭起,罢工规模越来越大,仅据2月19日至24日五天的统计,罢工人数即达414600余人。[29]3月21日参加第二次总同盟罢工的工人竟达80万人。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上海已经成立了500多个工会,并有一支5000人的工人武装队伍。工人对资产阶级提出了政治、经济上的各种要求,触及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加上工人运动中发生某些“左”的倾向,如任意捕人游街,提出一些使企业无法承担的过高经济要求等,引起上海资产阶级极度惊慌。他们害怕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可收拾”,但还想在革命中谋取自己的利益,取得地位,因此对工人运动只好勉强表示支持。当工人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连虞洽卿亦答应为总工会筹款。[30]工会提出条件与厂主谈判,一般都能“屏息忍受”,有的资本家还自动给工人增加工资。[31]但是当白崇禧的北伐军到达上海后,革命队伍严重分裂,他们对工人的态度就变了,转而希望白、蒋能消弥工潮,“保护”自己。上海纱厂联合会主席荣宗敬在3月23日总商会召集的会议上说:“工潮不决,纷扰无已,根本解决,须请白总指挥发统一命令,解决工潮,乃可复工。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32]虞洽卿等并联合十九个重要团体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准备“竭商人之全力,促政治之改良”,镇压“毁工厂而捕店主”的共产党。[33]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处在动摇状态之中,无疑应从经济上寻找原因。从经济上看,他们要求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以便在中国自由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内受军阀的压迫,外有帝国主义为强敌,加上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关税无权自主,洋货倾销,无力与外商竞争,致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自由地发展。他们为了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有时同情、支持甚至参加革命,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与帝国主义者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部分人并在原料、机器设备、金融等方面与外国资本有依附关系,还有不少人和封建地租剥削有牵连,有的既是资本家、又是地主,一身而二任。因此,在形势逆转,革命力量受挫折的时候,他们就附和支持反动势力,并且他们从自身阶级的最大利益考虑,幻想依靠反动阶级来消灭共产党,抑制工农运动,以保护自身的利益。但是我们还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后,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向右靠拢,如果说这是资产阶级两面性起着主要作用,那么,政治上把资产阶级作为打击对象,经济上采取过“左”的政策,亦应该说是原因之一。当时民主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资产阶级仍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如果对他们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在政治上争取,在经济上保护,是可以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成为团结对象,留在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从而使蒋更加孤立。
长期以来,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人们总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的。这虽然正确,但不全面,因为人们忽略或不承认当时“左”倾错误存在的客观事实。刘少奇同志于1937年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说到,长期以来,我们不承认大革命时期也有“左”倾错误,还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大革命时期有“左”倾错误,谁就是机会主义。这就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啊!
上海资本家之所以把蒋介石捧上台,除了上面介绍的两点即阶级矛盾性格使然与当时工农(农运未介绍)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加剧了他们的态度转变外,就在这时蒋这一边除了他本身具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外,而且他还采取了笼络资本家的政策,加上帝国主义的压制、利诱,促使上海资本家迅速地投向了蒋的怀抱。这两点原因以往的著文大都涉及过,这里不再论述。
注释:
[1]《上海总商会日报》6卷6期。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03页。
[3]任持公:《上海商团光复上海纪略》,《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03页。
[5]和作揖:《一九○五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6]《时报》1911年11月24日。
[7]《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1926年9月编制。
[8]1926年5月5日《新闻报》。
[9]1925年9月19日《民国日报》。
[10]海关税的实际税率,在1926年只是3.8%,1927年为3.5%,参阅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建设》,华盛顿1956年第5—7页。
[11][美]小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8—29页。
[12]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
[13]《上海总商会月报》5卷7号,1925年7月。
[14][美]小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1页。
[15]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5月版,第179页。
[16]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982年5月版,第199页。
[1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页。
[18]维什尼亚柯娃—阿基莫娃:《在起义的中国度过的两年1925—1927回忆录》莫斯科1965年版,第318页。
[19]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传记文学丛刊之二十一,1963年台北版,第223—224页。
[20][苏]А.В.巴库林著,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274页。
[21]参阅《严酷的事实——鲍罗廷在武汉》,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第36页。
[22]武汉中央工人部调查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报告书,1927年6月29日。
[23]武汉中央工人部调查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报告书,1927年6月29日。
[24]《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文史资料专辑》,1980年南宁,第439页。
[25]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卷第494页,引自詹娃斯P.哈里逊《走向权力的长征》,纽约,1972年版,第109页。
[26]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载《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总第22期),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1980年3月5日。
[27][苏]А.В.巴库林著,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53页。
[28][苏]А.В.巴库林著,郑厚安、刘功勋、刘佐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61页。
[29]《申报》,1927年4月9日,2月27日。
[30]《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4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3页。
[31]《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法及其职任拟案》,1927年3月6日见《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第324页。
[32]《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193页。
[33]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1页。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中国工会论文; 中国武汉论文; 上海论文; 历史论文; 武汉生活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民族资产阶级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