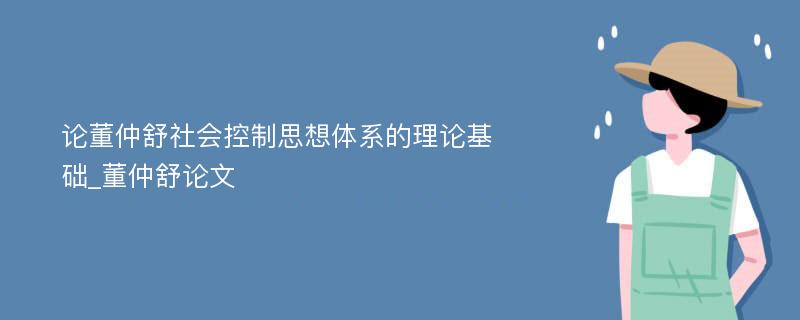
论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思想体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6)05-0074-04
“社会控制”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两千年延续,其中传统的社会控制思想及其执行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影响深远。为了“大一统”理想社会的实现,董仲舒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并为加强其体系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建构了一个以“大一统”为社会控制的理想目标,教而后善的人性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为社会控制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其社会控制思想奠定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入研究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并分析其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当今时代社会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思想、政治的大一统——社会控制的理想目标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提出绝非偶然,实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是对前代思想家“一统”思想的继承和总结。《诗经·小雅·北山》中讲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周朝对一统天下的生动描绘。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白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 (p174)以政令是否统一作为检验一国政治有“道”与无“道”的标准。孟子和荀子则分别明确提出了国家“定于一”和“一天下”的主张。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列国纷争,破坏了这种统一的局面,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们为此而痛心疾首,围绕着如何实现社会的稳定而各抒己见,驳难不已,以期恢复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状态——大一统。汉王朝的建立虽然结束了分裂割据,然而诸藩的存在却时刻威胁着王权的稳固,特别是七国之乱之后,加强中央集权已成为汉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也是平民要求社会稳定安宁的呼声。正是这种情况下,董仲舒提出了其“大一统”理论,并以此作为社会的理想目标和全部理论的落脚点。
何谓大一统?在《天人策》中,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特别是《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系统地构建和阐述了他的大一统理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 (p1523)在董仲舒看来,大一统是天经地义、永远合理的,是天地不变的常理,古今共同的原则,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春秋》着力阐发的大旨。并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论述:“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2] (p1523)“《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3] (p113)“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3] (p425)在董仲舒看来,《春秋》倡大一统,以一元为始而正本,王者乃国之元本,上承天意,以统一天下。把“一”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天地运行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把“一”落脚到社会政治中,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如此,“大一统”被赋予了至上性、神圣性和惟一性的特征。
具体说来,董仲舒的“大一统”,首先是指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的一统。董仲舒反复强调的“天道”、“人道”,实质上是指整个结构的均衡、稳定和持久,其“人道”就是人间世事的统治秩序。在他看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有赖于国家的一统。他对《春秋》中“一”字作了神秘主义的解释:《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皆统归于“一”,“一”是天的运行原则,受命于天的君主需奉天道,统一于天,天下万民统一于王,这就是大一统,这就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春秋》之法。在《天人策》篇中,董仲舒极力颂扬了这种大一统局面:“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2] (p2511)
其次是指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一统。政治上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有赖于思想上的一统。在董仲舒看来,这个统一的思想就是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立儒家思想为一尊,以儒家的仁德思想为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 (p2523)在他看来,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一统,不仅是大一统的重要内容,更是大一统得以实现的思想保证。
第三,大一统的核心是加强中央集权制,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独尊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大一统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要归结为政治上一统于天子,加强封建皇帝的权威。为此,董仲舒把人君放在元、本之重位来说明以德化民,天下归于心对一统天下的重要作用。他说:天子者,“号天子之子也”。“天子受命于天”,是“国之元”、“国之本”,人君“受命”乃“百神之大君”的“天意之所予也”。也就是说,皇帝是以神圣的天之骄子身份,根据天意来统领天下和号令一切的。王者的任务就在于使天下壹于正,即归于一统。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正者,王之所为”的论断。王者须承天意,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则远近都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2] (p2503)这样,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因此具备了至上性、神圣性和惟一性的特征。
董仲舒从“大一统”社会控制的理想目标出发,对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合理性进一步展开了系统的论述。
二、待教而后善的人性论——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人性问题,董仲舒以前的许多思想家都曾进行过论述。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对人性的看法,并以此作为其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理论前提,论证了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董仲舒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也反对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了“性者,天质之朴也”[3] (p376)的人性学说。他认为,性是人的一种天生的素质,人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而是“贪仁之性两在于身”,人性兼具“贪仁二气”、“善恶两质”。他指出:“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3] (p363)既然贪仁二气,便不能说人性是善或恶。人性本身只能具有善质或恶质,善或恶是善质或恶质外化的结果,就如米与禾、丝与茧、雏与卵的关系一样。“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3](p365)也就是说,善虽出于性,但性与善有所区别,犹如米出自于禾中但与禾区别一样。善不是与生俱来的,善形成于后天的教育。“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3] (p376)以此说明“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的道理。董仲舒认为,“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3] (p365)在他看来,性为自然之质,是“天之所为”的“止之内”,而善则是教育的产物或结果,是“天之所为”的“止之外”的“人事”。总之,作为天质之朴的性之所以能善,全在于王教,人事中的善是教化的结果。因此,善“不当于性”,性也“不当于善”,两者不是一回事,人性只能说有善质、恶质,而不能说是善或恶。
“性待王教而善”是董仲舒人性论的核心。董仲舒强调性待王教而善,其目的在于强调“王教之化”的作用。在他看来,从善性的完成来说,离不开王者的教化,而从王者的角度来说,化民成性是王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王教在董仲舒看来又是承天意以从事的,是执行天的意旨。“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3] (p376)董仲舒这里把人性说成是天质之朴,具有善质而未能善,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其目的就在于引出圣王承天意,教化万民的任务,为皇权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人的等级制度永恒化提供理论根据,其社会控制理论也由此更加神圣了。董仲舒这里“把王教说成天意,这实际上就把王教的任务神秘化了,因而也就使董仲舒的人性论具有了神秘性质。”[4] (p250)
董仲舒对人性有善质及恶质,须经过教化才能为善的探讨,实质上是论证了社会控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3] (p376)正因为人有善质,经疏通、引导方可为善行,因而社会控制才是可以奏效的。另一方面,正因为人有恶质,若无有效的控制,则必然导致恶行的出现。因此,没有社会控制机制的建立,善质就不可能外化出来成为善行。社会控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
董仲舒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性进行了考察并作了区分。在他看来,人性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种,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其中,“圣人之性”是善的,“斗筲之性”是恶的,这些极善、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没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故不能叫作“性”。“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3] (p367)“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3] (p375)“中民之性”即是除了“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这两种极端以外的占绝大多数人的“万民之性”。在董仲舒看来,“圣人之性”是过善之性,他们的性是先天即善的,应排斥在所论人性之外,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处于主体的地位。“斗筲之性”则是只有恶质不具善质的斗筲之徒经教化终不能为善。“中民之性”不但为数众多,而且其性既非“至善”也非“至纯”,而是“贪仁之性两在于身”,既在他们身上既有“善端”又有“恶根”,兼具善质和恶质。因此,经王者、圣人之教化可以弃恶从善或由不完全的善发展为完全的善,当然若教化不力,亦可以为恶。“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2] (p2503)在他看来,通过教化,使民众自觉地遵守封建礼仪制度,于是一个“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3] (p324)的局面就会出现。
三、天人感应的宇宙观——社会控制的合理性论证
为论证社会控制的合理性,董仲舒抬出了“天”作为其社会控制思想的形上根据。
“天”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是万物之本。“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昭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暗、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大礼之终也。”[3] (p33)在董仲舒看来,宇宙万物统一于天,天是万物之源、百神之君,“人之曾祖父”,人类社会全部内容之根据。受命于天的君主奉天道,统一于天,天下万民则又统一于王,这就叫大一统。
为进一步论证人君统一于天,万民统一于人君的政治大一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董仲舒提出了其“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理论。
首先,董仲舒认为,天不仅为人之本,也与人相类。“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3] (p329)人不仅形似,而且天还和人一样有情感,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甚至认为人的道德也与天同类。“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3] (p385)总之,天是放大了的人,而人则是缩小了的天,天人相类,天人相通,天人合一。
其次,董仲舒认为统治人间的君主,其君权也是上天所赋予的。“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也就是说,天子之命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所以在他看来,只有德侔天地者,皇天才“佑而子之,号称天子”.[3] (p518)天子,“号天之子也。”[3] (p509)人君“受命”,乃“百神之大君”的“天意之所予也”。有情感有意志的天通过授权于君王,间接行使着对人间的统治权,直接行使统治万民权力的则是受命于天的君王。在他看来,从历史上看,历代君主都是从上天那里得到受命,然后才得以称王的。如“汤受命而王”,“文王受命而王”,后继者也是如此。为把君王描绘成为一个可与天地之道相通的神灵,理所当然的民众统治者,董仲舒从造字上进行了论证。“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3] (p401)在董仲舒看来,天、王、民三者,必须是王法天,民法王。有意志有情感与人相类似的天既然是万物的主宰,因此受命于天、统一于天的君王在人间建立君权独尊的大一统政治,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
显然董仲舒的“天”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董仲舒关于天的认识和天人合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汉代儒学向着神秘主义转化的形成,使传统儒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具有了类似宗教的束缚力。”[5] (p82)董仲舒正是用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必然性,论证了其全部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可以说,他的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的提出都是以“天”为根据的。
在刑德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天道大者在阴阳”,天是以阴为权,以阳为经,贵阳贱阴的。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天”的“好德不好刑”,故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应以德治为主,在社会控制上才有了“德主刑辅”;在人伦关系上,董仲舒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3] (p432)一切事物都可以分成阴阳两类,阴永远处于从属地位,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阳尊而阴卑,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所以,君应为臣纲,父应为子纲,夫应为妻纲;另外,作为社会控制保障的官僚体系结构的设立也是由天所决定的,因此,设置官吏“皆合于天”。董仲舒专门作了《官制象天》篇,对官制的设置进行了具体论述。
董仲舒深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君权至上带来的危害,因此,在他的社会控制体系中,君主既是社会控制的主体,又是受控制的客体,用君主的自律进行君主的自我控制。他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2] (p2503)但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这种自律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于是在君主之上,抬出了一个高于世间一切的“天”,试图通过“天”给君主以制约。在他看来,既然天是高于君主的特殊权威,天就完全有资格做君主的监护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意也。”[3] (p28-29)试图通过“天”威给予君主以制约。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3] (p272)在他看来,天立王并不是为了君主个人,而是为了天下万民。只有那些安乐民众的人,天才会授予他王权;而对于那些贼害民众的君主,天则会收回对他的授命。“天常予,天常夺”。因此,必须顺天行事,而逆天命者,必受惩罚。“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2] (p2469)也就是说,仁爱的天是诚心希望人君能好好地进行统治的,所以它先降灾害,以示谴告。如果人君不能醒悟,它就再降怪异,以威震人君。如果人君还不知变,天就只好收回王权。上天收回授命的方式,在董仲舒看来,则是民众起来推翻暴君的统治。董仲舒称之为“有道伐无道”,并认为这是顺天理、合天意的。天对那些好好进行统治的人君,则会“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效。”[3] (p116)总之,灾异的出现,是与国家的政治得失和历史的治乱兴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董仲舒一方面为人间至高无上王权的建立和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通过上天降下灾异,对人间的君主进行谴告,从而为这至高无上的王权找到了制约力量,这一点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样,董仲舒的社会控制过程便形成了一个由天控制君主,君主控制百官,百官管理万民,天又顺乎民心的一个自我调节系统。
董仲舒所构筑的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由于本于“天”,从而由天的神圣性而具备了合理性、权威性,由人性的“待王教而后善”而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其社会控制思想也因此而成为天经地义,不可怀疑的了。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体系就是建构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而层层逐步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