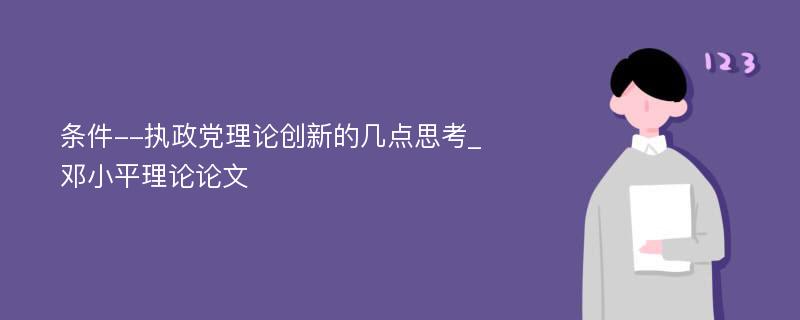
重点#183;关键#183;条件——关于执政党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条件论文,重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06)04—0017—04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执政党的理论创新是执政党的生机所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理论创新方面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它必然成为我们党不断保持的生机活力的保证。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理论创新这一重大问题,就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
一、潜心研究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执政党理论创新的重点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理论创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以下简称“三大规律”)的不断深化认识和解读达到的新高度。执政党理论创新不在于形式上、概念上提出“新”的东西,而在于其是否科学地反映了三大规律,是否实际地推进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实现和要求的满足。这是一个不断再认识的进程。
20世纪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基础上起步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全方位的理论创新。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客观事物矛盾展开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具体历史局限性,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理论判断方面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缺陷和失误,没有科学反映客观规律,导致在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较量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困难重重,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既呼唤理论的创新,更要求正确把握理论基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
而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由三大规律展现的历史无限性和共产党人认识能力的历史有限性,决定了对真理的认识不能一次穷尽,这不仅需要对三大规律不断再认识,而且要充分认识在特定条件下共产党人认识的有限性。这就决定了执政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而且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认识和解决面临的亟需解决而又能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清醒地指出:我们党“只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而对于“不成熟”的问题则“不必急于解决”。[1] 面对事物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或认识能力还不足的时候,急是没有用的。这就要求执政党不应和不能沉湎于那些现实不紧迫、又没有充分条件解决的重大命题,那些自己不熟悉的问题,那些自己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对于那些现实不紧迫、又没有充分条件解决的重大命题,执政党应当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只是明确其解决的基本方向,而不是着力于过细的考究。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而在七大时,毛泽东说道:“关于共产主义……没有强调。”[2] 为什么不强调?就是因为那是长远之后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场大论战,实际上谈的是当时许多没有提上行动日程的问题,论战双方都很激烈,都以“捍卫”、“发展”为己任。事过境迁后,邓小平在80年代回顾的时候时说道:“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3] 也正是由于深刻总结了经验教训,邓小平对解决面临的问题时,总是分清什么是现实可以而且必须解决的,什么又是应由后人去解决的。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解决了祖国统一的问题,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和演变,他没有替那些国家的先进的人们越俎代庖。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4] 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中深刻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5] 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关于共产主义的描绘和过渡途径的构想所引出的教训,毛泽东在50年代末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的经验教训等等,都是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并记取的教训。
正因为有所不为,不在不当为之处耗费精力,才能在当为之处尽力而为,从而实现既有为更有所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国最大的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理论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的正确态度,聚精会神、心不旁骛、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取得了累累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断回应实践的呼唤,在理论创新方面不断前进。如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成果相继问世,具体地回应了时代呼唤进行理论创新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二、以充分的论证来说服和教育干部群众是执政党理论创新的关键
执政党的理论创新是执政党的行动指南,这就必须为干部群众所共识。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有重大历史性突破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问世经历,不追溯民间的探讨历史,仅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高层的探讨进程而言,也可以看出一个创新观点在执政党内得到确立之不易。邓小平1979年11月就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而198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1975—1982)》的时候却没有收入这一重大创新,一直到1994年10月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才收入;1980年邓小平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讲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7],而1983年出版《邓小平文选(1975—1982)》的时候却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8],一直到1994年10月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才恢复作者当时的提法;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时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的谈话中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9] 从邓小平1979年深思熟虑提出问题,到1992年十四大的确认,这个历史进程对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
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理论创新是来自实践经验的升华,只有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相当充分积累基础上进行升华,才能有说服力地教育干部群众,首先是执政党的高层。正反经验教训的对照比较既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也是使理论创新成为干部群众认识创新理论并用之于指导实践的基础。这就要珍惜一切历史经验教训,绝不要搞虚无主义。邓小平关于“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0] 的教诲,是需要经常体会领悟的。没有多年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的探索实践,没有这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研究,没有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各种体制运行中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脱颖而出。
当执政党某一个理论创新问世的时候,有的人常常愿意回顾在这之前已经有过的努力。显然,对任何的先驱贡献的尊敬,是很对的。而更重要的是应当研究那些先驱贡献没有能够成为执政党的共识,成为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财富的原因。这当然有体制的因素,还有其他种种原因。而当时创新理论本身论证的不充分,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任何理论创新固然源自实践,但并不是实践的素描,更不是对一时、片断的实践的素描,而是对实践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本质的概括抽象。其之问世需要费功夫、花力气地透过现象表象去深入把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需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本质和规律“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11] 而“懂得”的人如果不能用大量的充分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来说明论证创新的理论,从而使人们认识、接受;或者足以说明论证创新的理论的大量的充分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处于萌芽状态的创新理论必然步履艰难。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无奈。这种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努力营造良好的氛围和体制,会有助于这种无奈减少到尽可能低的限度。这就既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和体制,也要求进行理论创新的志士仁人当自己的创新成果不为社会认识的时候,既要对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坚持,也要检讨理论中存在的不足,并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才能逐步使人们认识。
三、造就良好的氛围和体制是促进执政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科学创新不能一次完成,更不能一蹴而就。理论创新是一个进程,在进程中出现认识上的偏差,既是无奈,更不可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正常的。而且偏差的出现常常成为正确的先导。关键是要用科学的态度不断进行再认识,造就良好的氛围和体制促进执政党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理论建设的实践表明:重大的危险不在于理论探索进程中出现偏差乃至错误,而在于缺乏对创新理论的包容和尊重。
理论创新作为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本质的认识把握,需要进行不断的全方位的再认识,这就要靠集体智慧,靠集思广益,而不能是少数人,更不能只是个别人。这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求自由的思想理论研究氛围和体制机制。如同列宁所说,探索理论研究的新境界,“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2]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为反对思想禁锢,推进理论创新,也讲过许多极其精彩的话,这些至今对我们仍然极有启迪意义。
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任务,需要鼓励和支持科学的理论创新,尊重和保护全党全国人民理论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应当没有异议的问题,也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必然。然而,如何处理思想理论活跃与社会稳定、统一行动的关系,是一个必然要面对和需要认真解决好的问题。
在20世纪的实践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以保持行动统一而把理论创新的权利垄断为自己独家所有是斯大林的一个“创造”。在斯大林完全一统天下之前,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民主的,《真理报》上辟有争论专页。在20年代党内大争论中,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为名,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把列宁主义泛化和神化,于是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就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等论著中,确立了自己对阐明列宁主义、阐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的不容置疑的绝对地位。在30年代的造神运动中,斯大林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他代替所有人思考、做结论,其他人只能照本宣科。这就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取消了自由的理论研究。当时,李可夫这样说过:“如果既无争论、也不讨论;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就像一个人似的,想的完全一样,那才不可理解,那才是荒谬之极和咄咄怪事了。”他辛辣地说道:“如果政治局的成员只是相互看一眼,他们就会在一切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政治局就不成其为党的领导机关了。”“如果把一切争论都看成是倾向的话,那就干脆摆上些玩偶和木头好了。”[13] 而实践使李可夫的悲怆成为了现实。斯大林以反对派别活动为名,在先后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及其支持者的同时,一笔勾销了党内平等的、正常的意见交锋,与斯大林意见不同,便被上纲为“反党集团”,一切都听命于斯大林个人。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以很大的勇气来揭开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盖子,但在理论问题上又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一言堂”。毛泽东在50年代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双百”这样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方针。但是,“左”的猖獗使这样一个好的方针并没有能够贯彻下去,反而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专制。思想专制,不容异见,使科学创新变为不可能。
邓小平在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思熟虑地回顾反思的基础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道:“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14] 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理论创新的普遍性。营造良好的氛围是理论创新的一个大前提。
创新必然意味着改变,这就会影响到现实正在执行的政策和正在推进的工作;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因思想混乱而影响正常工作的进程,这是不能无视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在保护理论研究自由的大前提下,认真解决好具体实施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应在不影响、不妨碍党的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使理论研究的探讨在一定的、适当的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具体探索和在实践加以解决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基本原则就是邓小平说的:“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规定。”[15]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党和人民利益的要求。但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这决不能成为否定理论研究自由的口实。1980年邓小平在强调全党行动统一的时候就同时指出:“我们要坚决发扬党的民主,保障党的民主。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16] 这里邓小平就提出了造就良好的体制是执政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条件。当前我们党要坚持“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勇敢地修正种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不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失误和错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就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执政党理论创新的良好氛围和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