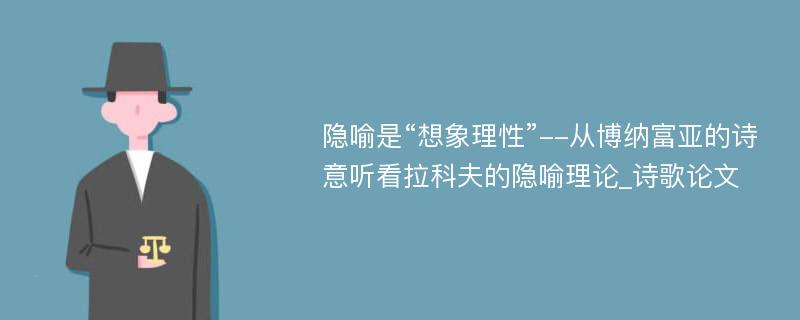
作为“想象理性”的隐喻——自博纳富瓦的诗意聆听辨析莱柯夫的隐喻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意论文,理性论文,理论论文,博纳富瓦论文,莱柯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1-0015-09 隐喻在诗歌创作、赏析和评鉴之中的重要作用历来为人们所关注,但如何理解此种作用,却始终存在着种种分歧。美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认知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莱柯夫(George Lakoff)及其合作者自上世纪末开始撰写的一系列隐喻研究论著可以说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隐喻的种种陈见和偏见,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围绕他的基本论点,国内外已有广泛深入的讨论,在此不必赘述。本文试图结合一个具体案例来对其诗歌隐喻理论进行引申性辨析,并由此探寻聆听作为基本的本体隐喻的可能性。 莱柯夫论诗歌隐喻 基本疑难 在成名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莱柯夫与约翰逊(Mark Johnson)已经颇为雄辩地证明了隐喻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之中的根本地位,从而确认了隐喻作为一种根本的认知形式而非单纯语言修辞手法的重要作用。但当我们带着这些洞见转向对诗歌隐喻的分析之时,仍存在着一些疑惑有待澄清。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或应该,对诗歌进行概念结构上的分析?通观莱柯夫与特纳(Mark Turner)在《超越冷静理性》一书中的分析,读者难免会有些许疑问:即便其中的分析怎样细致、严谨、自洽(consistent)地描述了诗歌中的基本隐喻及其相互之间的推演(inference)及映射(mapping)关系,但它是否遗失了诗歌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换言之,在此种理性化的审视目光之下,一首优秀诗歌中最为迷人的那种神秘莫测的意蕴或充满惊奇的震撼是否会荡然无存? 莱柯夫与特纳对此当然有着清醒的意识。但在他们看来,此种对于诗歌的流俗见解亦体现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已经着力批判过的“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种种症结,(188-89)即将诗歌隐喻归结为极端私人的感觉和想象,由此强调诗歌的不可“解”乃至不可“说”的神秘。基于莱柯夫与特纳的论证,此种流俗见解实际上恰恰贬低了诗歌本应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因为它最终将诗歌的创作和鉴赏抽离于我们的生活,并将其局限于狭隘的领域(诗人的游戏)之内。既然隐喻对于我们的生存起着本质性的结构化(structuring)的作用,而诗歌又往往是隐喻生成和运作的最佳试验场,那么诗歌隐喻的深刻影响就绝不应该被低估。他们进一步指出,不能将诗歌隐喻片面归结为主观或客观的任何一极,而应认识到它游弋于理性和想象之间的那种中介地位(a third choice)。(Lakoff and Johnson:185)隐喻的根源在于基本的概念认知结构,但当它们以想象的方式来对概念的内涵进行“部分性”(partially)地推演、拓展和引申之时,却同样展现出充分的自由和开放性。 虽然这些洞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激动人心的,但其中亦显露出莱柯夫诗歌隐喻理论的一个根本症结。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将自由归还给了诗人,但此种自由的局限性仍然十分明显。从根本上说,诗人从来不会是新隐喻的创作者,而至多只是对既有隐喻进行不同调制的工匠而已:“一般的概念隐喻因而并非个别诗人的独有创造,而毋宁说是一种文化的成员用以对其经验进行概念化的某种方式。”(Lakoff and Turner:9)莱柯夫与特纳在别处亦多次或明或暗地肯定这一基本点,但正是从这里足以生发出一系列的批判性质疑。还是让我们结合他们的具体阐释来澄清这一疑点。 关于新意义的创生,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已经有所涉及,而在《超越冷静理性》之中,则有着进一步的细致描述。比如,他们谈到诗人是如何利用那些“基本”隐喻(书中用common、basic、conventional等词来形容此种基本性),将它们“组合,拓展,并结晶于有力的意象之中”。(51)在后文里,他们进一步将诗人处理隐喻的手法归结为拓展(extending)、精制(elaborating)、质疑(questioning)和构织(composing)这四种。(67-72)但即便是最后一种自由度最高的构织,最终也无非是对基本隐喻的不同排列组合而已。莱柯夫与特纳似乎也觉得这样的分析过于限制了诗人的自由,所以多少安慰性地补充说道:“数量相对较少的基本概念隐喻可以被概念性地组合,并由此表达于无限丰富的语言形式之中。”(51) 显然,诗人仍然没有获得创造新的基本隐喻这一根本权力。由此我们不得不在其文本中去探寻一些隐约的启示,以期引导我们对此进行别样思索。首先,莱柯夫与特纳确实在以上的隐喻手法之外又提及了一种无法归类的“非同寻常”(unusual)的创造途径,(54)但随后对其却几乎无所涉及。这一方面是因为,既然“非同寻常”,自然就无从、也不必对其基本规则进行细致界定和解析;但另一方面,这里也恰恰揭示出莱柯夫等人的诗歌隐喻理论的局限之处,以至于他们最终也不得不从“别处”去补充说明此种非同寻常的根源。 “基本”隐喻及其哲学内涵 诗人真的无法染指基本隐喻吗?要真正回应这个问题,必先理解何为基本隐喻,它们到底又为何“基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解释。 首先,从功用上说,一个隐喻是基本的,意味着它是“概念上不可或缺的”(indispensability),(Lakoff and Johnson:56)或它的运作总是“约定性的、无意识的、自发的”。(80)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基本隐喻往往和前语言、前概念的具身认知能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所列举的三种基本隐喻——方位(orientational)、本体(ontological)和结构(structural))——之中,第一种指向肉身及其与空间的关系,而第二种则是基于彼此分立(discrete)的肉身及由此衍生出的内/外边界的复杂关系。由此,隐喻之根在于非隐喻性的在世经验。在这个基本的具身认知的层次之上,诗人的想象确乎无用武之地。 但在由源自基本经验的基本概念隐喻向着更为普遍抽象的概念的运动过程之中,却展现出一种不可缩减的开放性。莱柯夫与约翰逊在书中对谚语(proverbs)的隐喻性意义的生成运动的描述带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对谚语的理解,总是要相关于一定的预设和价值所构成的背景,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同样的隐喻可以引向迥异的解释。”(187)可见,虽然谚语亦可以归结为隐喻的一种,但其运作方式却多少相异于莱柯夫的概念隐喻理论的一般原则:根据后者,隐喻之间的推演关系最终是围绕更为抽象复杂的概念展开的,具体的、与经验更直接相关的基本概念通过隐喻关系对抽象概念的丰富内涵进行部分性展现;而对于谚语来说,方向则似乎正相反,是从具体的概念隐喻出发,在不同的“背景”之下被引向不同的方向。但仔细想来,此种自下而上的运动亦并非仅仅局限于谚语的情形。在诗歌隐喻的运作之中,不同的价值预设和更为普遍的哲学原则不是每每也已经在发挥着根本性的中介作用吗?在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下向着未知方向开放,这或许才是诗人创造新隐喻的“非同寻常”的方式。实际上,莱柯夫与特纳亦花费了整章的篇幅讨论“宏伟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这个重要哲学背景,但这番繁冗枯燥的论述却并未能有效揭示哲学与隐喻的真正关联。 就这一要点,还是利科(Paul Ricoeur)在其经典之作《活的隐喻》中给出了相当重要的提示。在总结性的最后一章中,他一开始就明确强调将哲学思辨和诗歌隐喻相区分的必要性: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过渡”。(利科:353)因而,仅仅意图以哲学的方式来“复现”(reproduire)诗歌的隐喻(拉科夫的理论多少接近这一点)是不充分的,更为关键的是要揭示诗歌隐喻之中所展现的独特的哲学思维形态,将隐喻的“语义潜能打开其他的表达空间,即思辨话语的空间”。(411) 以往将“哲学话语”和“诗歌话语”关联在一起的纽带正是“类比”,而利科结合思想史的线索证明类比概念在哲学思辨中其实并不占有核心地位。实际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之中,莱柯夫等也指出,隐喻要比类比更为根本。是隐喻创造出新的类比关系,而并非是以类比为前提才能构成隐喻。利科接下去结合海德格尔的《理由律》一文指出哲学思辨与诗歌隐喻相平行的另一种可能性,更值得我们思索。类比最终旨在实现不同领域或等级之间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而实际上,哲学和隐喻都意在实现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逾越”(trans-gression)或“转移”(transfert),(利科:357)这其中的关键机制是“断裂”而非“连续”。柏拉图最早将此种转移描绘为心灵“由感性向非感性的形而上学转移”,(392)即所谓“第二次航行”;与此相对应,诗歌隐喻亦是“由本义(propre)向转义(figuré)的隐喻式转移”,(392)即从具象向抽象的转移。如此看来,在这两种运动之间似乎存在着颇为完美的对应,这也是为何在经典的哲学体系的根源之处都能发现典型的隐喻(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太阳”隐喻)。但结合黑格尔的“扬弃”(Aufhebung)概念和德里达在《白色神话学》(La mythologie blanche)中所描绘的“损耗”(usure)运动来看,此种对应并非是完全和彻底的。毋宁说,哲学思辨只是在隐喻所敞开的丰富而广大的思索空间之中选择了一种可能的途径而已,比如:“并不是隐喻支撑了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大厦,而毋宁是形而上学掌握了隐喻过程,以使它服务于自身的利益。”(410)换言之,隐喻的活力和生命并非全然“耗尽”于既定的概念体系之中,而恰恰是隐藏于那些——用莱柯夫的说法——“未使用的成分”(unused portion)之中。仅仅是解释(“理解”)隐喻是不够的,相反,隐喻需要不断被“激活”。此种激活亦并非单纯回归隐喻的原初语义层次,而同样是要在哲学思辨和诗歌隐喻的张力之中来展开:只有在一定的哲学概念体系的背景之下,我们方可洞察到隐喻之中尚隐含着的“成分”;同样,对这些隐含成分的揭示其实更意在激发新的概念思辨的可能性。用利科的话来总结:“隐喻是活的还表现在它将想象的动力(l'élan)置于概念层次的‘更多思想’(《penser plus》)之中。”(421) 博纳富瓦的诗意聆听 海德格尔在《理由律》中已经将“聆听”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隐喻:“思想就是倾听和观看。”(利科:391)①而考虑到“看”与视觉隐喻在柏拉图传统中的核心地位,“听”作为基本隐喻的重要的启示性作用就更为明显了。下面我们即结合当代法国诗坛上最着意于诗意聆听的博纳富瓦的代表作《杜弗的动与静》(Du mouvement et de l'immobilité de Douve,1953)②来进一步阐发这个基本隐喻的哲学张力。诚如很多学者指出,此诗凝聚着博纳富瓦对于诗歌的最为核心的观念。(Kalb:525)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涵盖全诗内容,我们仅选取首尾呼应的两段来进行细致分析。 “序幕”:聆听,肉体与空间 让我们先来领略一番《杜弗的动与静》的震撼序幕中所描绘的声音风景中的种种“意象”(images)。根据莱柯夫的提示,虽然诗歌中吸引我们的往往首先是意象,但它们至多只能起到引向或推进隐喻的功用,而不能等同于后者。隐喻所揭示的是概念之间的根本关系,这是单纯意象所无法实现的。 全诗首尾贯穿,由视觉的“戏剧”始,终结于声音之“真正地点”。开篇即奠立了这出戏剧的基调:“我”与“你”之间的一场对话。“你”首先以视觉(看见)展现在“我”的面前,带着所有那些剧烈的运动(奔跑、搏斗)和浓重的色彩(白色、血)。看似这是一场充满生命活力的表演,但却骤然引入了另一个主题,或真正的主题——“死亡”。全诗标题中的“动与静”,实际上指向的正是更为根本性的生与死的主题。从表象上看,死是生之否定(第2节中大量使用否定词)和中断(折断、裂开)。然而,死并非彻底的空无,更不是异于生的彼岸(生之终结即是死之开端),相反,在诗人的笔下,死与生紧密纠缠在一起,诗歌开始处所引用的黑格尔的原文已鲜明指出这一要点。死如无处不在的穿越着、渗透着(pénètre)的风,将本来浓重、窒闷、充塞、“没有出路”(sans issue)的“在场”化为虚幻的“表皮”(robes),恰似那缠绕着夜之石的藤蔓幻化出“没有根的脸”。由此,在第4小节中,作者肯定了生与死的同时性,在“每一个时刻(à chaque instant)”,我们都既在出生,又在死亡。 然而,这并非怎样抽象深奥的哲学命题,恰恰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生存体验:当我们出生时即已经开始迈向死亡,当我们茁壮成长时即已隐含着衰退的痕迹,正如在生命力达致接近顶点的盛夏亦已然隐约奏响衰颓的节奏(“衰老的夏天”)。死如隐形的风,首先渗透、“清空着”(démeubler)身体,再不断侵蚀、动摇、“驱赶”(pousser)着仍然沉重的“头颅”。这里,躯体的下(腿、地下河)和上(头)明显构成了身与心的隐喻。③死亡从侵蚀肉身开始,逐渐动摇、瓦解着身/心之间的等级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肉体是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生死纠葛的戏剧的“真正地点”。破裂的血管、燃烧的手臂,最终导致的是最能标志主体和意识的“脸”之“退却”(reculer)。消逝的脸④这个隐喻在前文藤蔓幻化的图案中已经埋下伏笔,在后文还将不断衍生出变奏:如“树枝在她的脸上激战”、“脸这个字不再有意义”、“你的脸为不在场”等等。而迄今为止我们所点出的种种令人惊叹的意象都汇聚在这个意象之中,凝结成全诗序篇的第一个基本隐喻:死就是消逝的脸。诚如《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详尽解析的那个经典隐喻“爱是旅程”(LOVE IS A JOURNEY),本来含义丰富但又一言难尽的抽象概念“爱”,在向着具象概念“旅程”的映射和推演之中顿然间衍生出种种具体可行的理解途径。在这里,死亡这个令人焦虑惶惑但又晦涩深奥的终极概念在脸这个极为明晰而具体的意象概念之中亦启示出蕴含无尽的思索空间。脸作为器官,作为轮廓,作为内在心灵的可见表达等等,都在“消逝”的微妙运动之中引发读者进一步探问生死之谜。 死虽然具有终结的强力,但它穿透肉身和头脑的步调却总是隐约的、难以洞察的,正如“缓缓”逼近的阴影之“崖岸”(falaise)。正是在这里,引入了声音的契机。死之侵蚀,正如风之渗透,或“升腾的雾”,逐渐抹去生之形迹,也逐渐使得视觉让步给听觉:“扯掉目光”。这个动机只隔了短短一节便再度奏响,这时死之隐喻合着“稀奇古怪的音乐”翩翩起舞:即便死亡穿透了我们的肉体,抹去了我们的面容(“透入脸的地下部分”),但“我们扯掉目光”,哪怕“眼睛正在腐烂”,“眼睛塞满石膏”,仍然可以彼此倾听。或者说,此种回响着死之韵律的倾听才是“我”和“你”之间的本真沟通?“那一声喊叫打破了你守夜的恐惧”,这“一声”既是肉体内部的毁灭力量的强烈爆发,又是突破死亡的浓重包围和锁闭的绝望呐喊和“搏斗”(lutte)。这一声,无论怎样微弱——“我听见她发出响声(bruire)⑤——但仍由你传达到我,并形成共鸣和交响。由此,为死亡所不断侵蚀的“溃败的生命”重新凝聚(rassemble、ressaisie)为在场。 然而,重现的在场已然经受了死之渗透,并在声音的媒介之中展现自身(“重新找回的躯体”),这个世界已然与目光主导的世界迥然有别。首先,声音的运作与象征死亡的风与雾颇为相似,皆以无形、遍在的穿越和渗透为特征,由此与形体消释的肉身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在肉身空间的最高处”:这里的“高处”已不再指示头部及其所标示的主体和意识,而更是指示肉体内在的强度汇聚之所,即“无声的极限处”,因为后文所描绘的都是肉体的瓦解和碎裂。其次,目光操控的世界有着明确的边界和秩序,而声音笼罩的世界则呈现出融合、蔓延和交织的面貌(“苔藓”、“蜘蛛的光线”)。况且,声音的运动更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们在空间中不断散射、折射,逐渐碎裂为无限微小的声音碎片(“沙子的命运”)。在如此的声音世界之中,以往由主体和自我所掌握的普遍必然的“知识”不再有效,由此敞开了一个向着不同方向发散的“隐秘知识”的空间。视觉首先捕捉和呈现的是明确的“意象”,但死亡之回声穿透你我的肉身,直达那冰冷浩瀚的“内在的海”。在那里,“意象不再出现”(où les images ne prennent plus⑥),但我们彼此归属。这种种线索皆将我们引向声音和空间的本质关系,而所有这些复杂多变的关系又都是围绕着已然经历“变形”的肉体所展开。 这里所涉及的明显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所论述的第一种基本的概念隐喻,即基于肉体的原初空间感知的方位隐喻,只不过作者集中描述的“上/下”的基本方位在博纳富瓦笔下逐渐消释,转换为由聆听所主导的开放、多元的——借用德勒兹等的术语——“平滑空间”(le lisse)。这并未从根本上削弱莱柯夫隐喻理论的深刻性,而只是提示我们,即便是“基本”隐喻亦已经体现出不可还原和简化的多元性。《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亦明确提示我们,对概念及其结构的研究一定要回溯到感性经验的“自然维度”:“颜色、形状、质地、声音,等等。”(235)但显然,作者们唯一关注的上/下的空间方位是难以涵盖所有这些基本维度的无可穷尽的隐喻潜能的。 “尾声”:肉身,在场,与“地点”(lieu) 经由序幕的宏大铺陈,声音在随后两组诗中逐渐成为主导线索:我的声音、杜弗的声音以及种种别样的声音(“一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彼此交错、回响、渗透、萦绕在字里行间,袅袅不绝。⑦在我们这篇短论中自然无暇细致展现其中堂奥,但确实应该跟随莱柯夫的启示进一步探寻第二类基本隐喻即“本体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的踪迹。 基于莱柯夫与约翰逊的阐释,本体隐喻实际上要比空间方位隐喻更为根本,因为肉体与空间之间的本质关联仍要以其自身的实体存在为基本前提:“我们是实在的,皮肤的表层划定了区分我们自身与世界其余部分之间的边界。”(29)包裹着我们的皮肤区分开内与外、自我与世界,由此进一步形成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个体性的分化。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在世经验。 然而,当莱柯夫等将空间隐喻和本体隐喻如此明确地分别加以论述之时,似乎也无意中将读者引向一个可能的误解,即将个体的肉身存在和空间场所之间进行明确区分(distinction)。实际上,他们对本体隐喻的论述虽然细致入微,但恰恰忽视了个体和空间之间的原始关联。而对于博纳富瓦,此种关联却始终是他关注的要点。换言之,“地点”、“场所”作为自我—肉身—世界的际遇,始终是他诗歌的一个核心主题。当然,一旦我们将场所视作这样的汇聚之所,那它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位置,而变成了事件和行动发生之地。(Lawall:411-17)这也是《杜弗的动与静》尾声的标题“真正的地点”的用意所在。 同样,场所也呼应着前文的一个主导概念,即“在场”。“在场”是博纳富瓦诗歌中的另一个关键主题。他1981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开讲辞的标题正是《意象与在场》(“Image and Presence”),其中他首先坦承自己受到巴特所谓“客观诗歌”观念的深刻影响,并强调从符号转向存在(大地、世界、他者)的必要性,这一点贯穿于他日后的诗歌创作之中。很多论者都将此种倾向归结于他对于纯粹的“物”本身的关注,根据是他的早期代表作《反-柏拉图》(ANTI-PLATON)的开篇第一个重要词汇:cet objet(这个对象)。诚如文思博(Steven Winspur)所言,运用ce(cet)这样的指示形容词正是为了拒斥既有的概念和命名体系,以策略性的手法来切近、呈现事物本身的那种本原性的存在。(45-46)但实际上,cet并非仅仅指向物,而同时也指向我们与物或他人相照面的场所。简言之,“这个对象”与“这处场所”(this place)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下面就让我们结合《杜弗的动与静》尾声的文本深切体会“真正地点”的奥义。 序幕中以“消逝的脸”和聆听为主导的基本隐喻结构将我们带向一个流动、多变、渗透、碎裂的生成—微观(devenir-micro)的世界,但这并非全然无形无迹的一团混沌。相反,彼此呼应、穿透、回响的声音仍然引领“你”和“我”汇聚于际遇的“地点”(“给走近的人空出一个位子”)。而“这个”地点,正是锚定存在的流转而又散布的中心。这里,皮肤所划定的内/外的隐喻结构不再有效:那个走近的人“没有房屋”,失去了包裹内在自我的表层和界限,变为在黑夜大地上游荡的个体,“吸引”(tenter)他的只有暗弱的“一盏灯的声音”。这个通感意象奠定了尾声部分的基本隐喻框架。灯的声音似乎是难以听闻的,即便是怎样宁谧的夜里,但那“一点点火”的意象却激发出更为悠远绵长的声音意境。围绕灯的意象可以展开多种隐喻途径,但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基于想象现象学的阐释带给我们当下的讨论更多灵感——博纳富瓦自己亦曾认真聆听巴什拉授课。在专论《灯之光》的一章中,他敏锐地揭示出,灯光意象的最深刻含义正在于其独特的时间性隐喻:“缓慢流驶中思考的时光。一位诗人,火苗的遐想者懂得把这缓慢的绵延置于表达灯的存在的句子本身之中。”(217)这里,绵延的时间、深邃的思索和言语的声音都汇聚在这个浓缩的视一听通感的隐喻之中,这也是为何巴什拉随后援引的诗句都将灯光和声音关联在一起:“合奏”、“讲话”乃至“沉默”,都开启着不同的声音意境。同样,在博纳富瓦的笔下,真正给游荡的个体带来慰藉的也正是“词语”,这样的词语不仅是有形的“象征”或“符号”,更是与声音和气息密切相关的“祈祷”(oraison)。祈祷,无论是否发声,都带着声音的韵律,涌现自肉体的最深处,趋向超越的境界。第二节标题给出的具体地点“布朗卡西小教堂”(Brancacci)似乎明确限定了这里的宗教氛围,然而通观尾声部分乃至整部诗章,最根本的关系首先仍然是个体(“我”与“你”)之间的关联与对话,而非个体与超越的神明之间的互通。正如第一节最后“隐约”(因为视觉已然退却)看到的“桌子”,将灯火、话语都聚集于会晤和攀谈的场所。 第二节是一个明显的转折,之前的主题“死”与“脸”再度呈现,但却笼罩在浓重的宗教氛围之中。不过,追寻“不朽”和“永恒”的旅程注定是一条“徒然之路”,因为最终朝圣者所“紧紧握住的”只能是一个苍白的“影子”。即便是那些描绘着救赎和希望的伟大寓言的宏伟“壁画”,最终也只能沉陷于浓重的夜色之中。在这夜里,我们所能听到的唯有一个个朝圣者那孤独的脚步,最终汇聚在一起,消逝在声音的汪洋之中。正是这“大水的声音”将“我”从神圣的梦境中唤醒,再度继续对生死之谜的遐想(songe)。这亦是一场“战斗”,试图从时时处处纠缠着生的死亡之浓夜中“重新赢得”(reconquis)“在场”:“阴影必须复活,会是在夜里并通过夜。”即便我在“源头”和“绝壁”上所探寻到的都只是死之幻影,是那张消逝的面孔(“败北的夜的脸”、“被抛弃的面孔”),但在融化于“泥土”的肉身之中,仍有生命的蓬勃的欲望“开花”。那源自“死亡世界”的最深处的声音,无论是绝望的“喊叫”,还是微弱的“抽泣”(sangloter),都向“我”启示着另一种“永恒在场”的可能性。只不过,这里的在场不再仅仅是物之实在,也不再指向超越的神显,而更是我们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隐秘幽灵”(mon démon secret)——那个隐约出没于整部诗篇中的独白的声音、杜弗的声音、一个声音、另一个声音。 在接近终结之处(“蝾螈的地点”),诗人总括了自己的思路,由此回归到“更深邃的源头”。在生—死—复活的辩证循环之中,经由死这个中介的否定环节,思索探寻到肉身与大地乃至整个宇宙相互联结的真正源始的起点:“通过全部身体的迟钝整体与星辰连接”,意识和精神正是从这最原始的物质之中涌现。因而无论是在坚硬的石头上,还是在如石头般凝滞的蝾螈的目光之中,我们都能聆听到“心永远跳动”。这才是诗人从巴特的“客观诗歌”的宣言之中所真正领悟到的哲理。“纯粹物的寓意”,正在于我、你,以及宇宙间万物在肉身的原始层次之上的真正相通。消逝的脸、一盏灯的声音,所有这些隐喻都在揭示这一番关于大地意义的深刻哲理。诚如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y)的精彩点评:“需要重新‘有’一个世界,一个可以居住的住所;这个住所既不是‘别处’,也不是‘地狱’,而是‘这里’。”(博纳富瓦:10)由此,让我们欢庆“白昼跨过夜晚”的胜利,在回响着脚步和话语声音的“真正的场所”之中痛饮“白日之酒”。 余论:隐喻向哲学的“转移” 在前文的缕述之中,我们已然尝试了种种由基本隐喻向着哲学原则(由可见向不可见,由感性向非感性领域)进行转移的可能性。在全文最后,尚有必要对博纳富瓦诗歌隐喻运动所牵涉的种种哲学背景进行一些补充性的反思。 在当代法国诗坛,博纳富瓦无疑是最具哲学气质的一位。其相关论述散见于大量的访谈和讲座之中。不过,虽然关于博纳富瓦的研究文献不少,但其中大部分都集中于生平、创作手法和语言技巧,探讨哲学背景的确实凤毛麟角,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圣奥宾(F.C.St.Aubyn)的早年之作《伊夫·博纳富瓦:第一位存在主义诗人》。然而遗憾的是,作者显然过于急切地将博纳富瓦的诗歌纳入到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的哲学体系之中,而无暇耐心地从诗歌隐喻的具体分析入手,逐渐向着哲学领域进行转移。同样,斯塔罗宾斯基为《诗集》(Poèmes)所作的序言虽然堪称迄今为止对博纳富瓦的哲学背景最为清晰深刻的阐释,但作者仍然大部分时间都沉浸于关于世界和存在的抽象思辨之中,涉及核心词语(“土地、住所、简单的事物”)(博纳富瓦:16)和基本隐喻(主要是“火”)之处寥寥无几。看来他并未真正理解文末那段诗人的重要引文中指向聆听与肉身的两个要点:“两个声音”的意象,以及概念和“化为肉身的呼喊”之间的本质关联。(26)这也是为何直到最终,作者还是无法真正解释“两个世界”在诗人的笔下如何凝聚为一个整体或坚实的在场,而只能借助于“瞬间平衡”这样极为含混而勉强的解释。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二重性在《杜弗的动与静》之中确实比比皆是:白昼与黑暗、生与死、看与听、身与心、上与下、幻影与在场,等等。但如若不从“两种声音”(我与你、“一个声音”与“另一个声音”)的对话、回响、穿透的交织关系的角度出发,似乎始终无法最终解决这一系列的辩证疑难。麦卡利斯特(James McAllister)在其精彩论文《折射之声:伊夫·博纳富瓦的诗歌写生》中就将此种我和你之间的回声关系作为理解博纳富瓦诗歌的核心隐喻,极富洞见:“你(Thou)的形象仅当为一个声音激活之时方才开始成形并行动,这个声音对自身无所言说,但却迫切想要证明一种难以捕捉的存在。”(94)他同时引入了出自《无光的一切》的另一个重要视觉隐喻“曲面镜”(le miroir courbe)来与回声的听觉隐喻形成呼应。基本隐喻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开放关联,也同时敞开了激活隐喻的新途径,所有这些无疑都为诗歌隐喻的研究进一步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注释: ①参见耿幼壮:《倾听: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感知范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章第2节。 ②以下该诗引文皆采用树才译文。(博纳富瓦:152)必要处根据原文稍作修正。 ③参见《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第4章中对于上与下的隐喻所基于的“实在根基”(physical basis)的讨论。 ④在《千高原》(Mille Plateaux)的“颜貌”一节以及《感觉的逻辑》(Logique de la sensation)中,德勒兹和瓜塔里也同样深入论及了这个主题。《杜弗的动与静》在很大程度上与弗朗西斯·培根的画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⑤法文本义为微微作响。 ⑥prendre译作“出现”并无不可,但它做不及物动词时的那种丰富意蕴却无法生动表达“凝结”、“粘滞”、“成活”等含义。这些都比照出视觉意象之“静”与声音海洋之“动”的反衬关系。 ⑦“声音”(Voix)的隐喻日后还将屡屡出现在博纳富瓦的诗作之中,尤其是《无光的一切》(Ce qui fut sans lumiè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