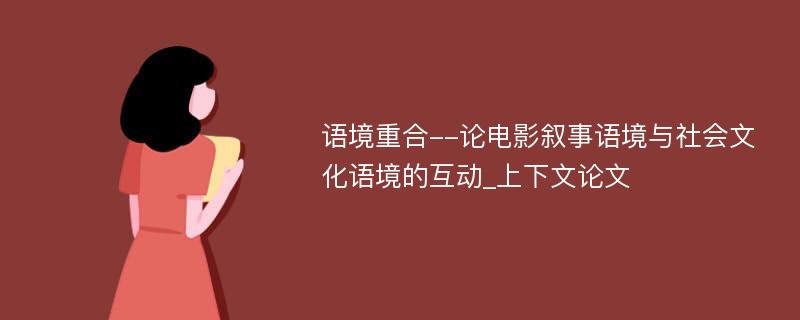
语境重合——论电影叙事语境与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互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互动论文,社会文化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制品,一种艺术商品,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形式,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产出地的社会经济“标记”和制作者的意识形态的“背景”。而这种“标记”和“背景”在不同的影片中,则有不同的显现方式:它们有的是以表现题材直接触及社会生活,反映观众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有的是以塑造人物性格的时代特征为中心,以人的精神世界映衬现实世界;有的则是以影片的叙事主题和现实的社会主题的“交叉”、影片的叙事语境和现实的文化语境的“重合”,引起观众对影片的共鸣……
中国武侠影片,作为中国电影中的“国粹”,自然具有鲜明的出品地的文化特征,同时它又具有一种独特的现实性:它向坐在黑暗中的观众映现出一个耀眼的梦幻世界的同时,也向他们传输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模式,一个理想的现实形象。由于武侠电影特定的历史情景和表现题材,实现这一切目标的途径都不可能通过直接的方式,而只有通过影片的叙事主题和社会主题的“交叉”、影片的叙事语境和现实语境的“重合”,才能实现。为此,对武侠电影的语境研究便成为我们洞悉其精神主旨必须进入的领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武侠电影所呈现出的种种“奇迹”。
我认为:电影理论研究的宗旨,从根本上讲应当是一种电影的语言形态和电影的语言意义的研究,而其中电影语义的研究又是电影语言学的核心环节。而要想准确、全面地把握电影语言的意义就必须将电影本文的叙事语境与电影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进行交叉阅读,从电影的叙事本文与社会的历史本文之间寻找到两者的互动关系。从而确定本文作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要讲述的真正的叙事主题。
一
将作品的意义与社会历史意义统而观之的辨析方法,在中国古代实际上就具备了它的早期形态。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孔颖达《正义》说:“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可见,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数句”成言、“数句”成义的问题,即字义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春秋笔法”虽然历来强调的是一字见褒贬,但一字的意义则必须有数句的语言环境,才可以真正显现。在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里说:“人之将计就计,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忘也。”这里刘勰所注重的依然是整体形态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语言的上下文之间交互的生成关系。不过,作为一位古代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更关注的还是艺术语言的美学风格问题,而不是语言本身的结构问题。袁仁林《虚字说》:“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语言的上下文对语义的直接制约作用。清代的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也说,“诵《古礼经》……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义乖。”戴震在此虽然所强调的是阅读者自身的阅历对本文意义的理解有着重要的限制,但他所说的这些超越语言自身,但同时又和语言义密切相关的事,实际上涉及的也是语境的问题。只是它们已越出语言上下文的范围,而属于情景上下文范畴的事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陈望道先生就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提出修辞要适应情境和题旨的理论。在这本中国第一部修辞学著述中,作者提出了写作的情景问题。所谓“情境”指的即是写文章或说话时所处的种种具体环境,而构成这种具体环境的又包括六种因素(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7 页—第8页。该书初版于1932年。):
第一、“何故”,讲的是说与写的目的——是为劝化人的还是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
第二、“何事”,讲的是说与写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讨论等等。
第三、“何人”讲的是说与写的对象(双方),是谁对谁说(写)的,即写/说者和听/读者的关系——对象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
第四、“何地”讲的是说与写的地方——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是城市还是在乡村。
第五、“何时”讲的是说与写当时是什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
第六、“何如”讲的是怎样的写与说——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
作为语境研究的一种学说,陈望道先生所指出的这六种因素,具有它的合理性,虽然它是发表在三十年代,但至今我们在研究语言意义的表述及其生成的具体过程时,依然还不能跨越这六种范畴。近几年来,语境研究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重,有人提出语境是“语用学的第一要素”;语境是“修辞学体系的灵魂”。语境问题显然已成为语言学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二
西方在古希腊时期,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就多次接触到了语境问题。他说:“一个名辞是具有许多特殊意义或只有一种意义,这可以用下述方法加以考察。首先,察看它的相反者是否具有许多意义,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属于种类的还是属于用语的。因为在若干情形下,即使从用语方面亦可立即察觉”。(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0页亚氏所谓的“用语方面”, 指的其实就是语言的使用方法、其中也包括语言的上下文所构成的本文情境。
在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在语言哲学中曾提出了“索引词语”(Indexical expressions)的观点。 他认为词语的意义有可能通过许多途径产生,为此,在不知道其使用语境的情况下就不能确定其指称的词语。为此,要想弄清词语的意义就必须回到词语原初的情景之中,查到它本来的生成语境。
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23年在为奥格登和理查兹所著的《意义的意义》这本书所写的补录中, 提出了“情景的上下文”(context of situation)”。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是“行为的方式”,不是“思想信号”,“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纠合在一起,语言环境对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注:《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5期)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对语境问题也有论述。他认为,在研究语义问题时,人们必须牢记非语言因素的作用。在涉及到一外句子的真实性条件时他说,人人都相信,真实性条件或多或少和语义表达有关,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了一句话的真实性条件。离开句子的上下文,哪怕是最简单的句子,也不可确定其真实性的条件。(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 1982年版第76页—第80页)作为一代现代语言学家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在他的转换生成理论中,还提出了“语境自由(context—free)”和“语境制约(context—s enstitve)”的语言规则。
现代语言学不仅十分强调语境在语义确认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就语境本身的划分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性的观点:瑞典的詹斯·奥尔伍德、拉斯·冈纳尔·安德森和奥斯坦·达尔合著的《语言学中的逻辑》一书中关于语境问题的论述,主要就是关于语境分类的。他们认为自然语言中大部分语句都是在这种或那种方式下依赖语境(context—dependent)来表述意义的。为了真正了解一个语句,必须知道关于这个语句陈述时的情景。他们还把语境分为“内涵语境”(intensional context)和“外延语境”(extens ional context)、 “晦暗的(opaque)语境”和“明显的(transpa rent)语境”。 (注:《语言学中的逻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第164页。)1950年,弗斯在他写的《社会中的个性和语言》中,把“context”(上下文)的含义加以引伸,认为不仅一句话的上句或下句,一段话的上段或下段是“con text”,而且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称之为“context”。弗斯把前者看作由语言因素构成的上下文, 把后者看作是“情景的上下文”。这种语境观正是我们今天所认可的,我们在这里也时常是在这种意义上,才使用语境的概念。
翰理德是继弗斯之后功能语言学派的又一个代表人物。他于1964年提出了“语域”一词。为了突出“语域”与语境的区别,翰理德又提出了“场景”、“方式”、“交际者”作为语言环境的三个组成部分。他说:“场景是话语在其中行使功能的整个事件以及说话者或写作者的目的。因此,它包括话语的主题。方式是事件中的话语功能因此它包括语言采用的渠道——说或写,以及语言的风格,或者叫做修辞手段——叙述、说教、劝导、应酬等等。交际者是指交际中的角色类型,即话语的参与者之间的一套永久性或暂时性的相应的社会关系。场景、方式和交际者一起组成了一段话语的语言环境”(注:王建平《语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植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7页。)
三
语境,仅就电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叙事语言的上下文对于影像意义生成的决定性影响。这方面在世界电影艺术理论中,已有许多突出的建树。从普多夫金著名的“普多夫金效应”到罗兰·巴特的“本文”,对此都有深刻的论述。
然而,当代的电影语境研究不仅是一种关于电影叙事语言上下文之间影像语义的研究,它更注重的是内在于电影的叙事语境与外在于电影的社会语境之间的互映和互动关系。电影的语境研究不同于那种将影片的叙事本文与社会历史完全割裂开来的本文分析,也不同于那种将影片内容与社会现实“对号入座”的所谓电影社会学。二者的基本区别是:
1.电影社会学只研究社会与影片内容的对应关系,注重的是影片中的人物身份与社会中的同类人的相互关系,主张的是题材决定论,在电影与社会之中更加注重的是,寻找电影中直接的社会意义。
电影语境学注重的是影片的叙事主题与社会潜在的文化主题之间的重合关系,侧重研究的是电影与社会在象征意义上的相互关联,而不以人物的身份和影片表现的题材作为研究的基本依据,更注重的是影片的主题意义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同构关系”。
2.电影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社会哲学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电影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决定影片表现内容的重要依据,社会是第一位的,而电影是第二位的。电影语境学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语言哲学的基础上,它不解决电影与社会谁是第一性(本体论)的问题,而更注重的是电影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范围内所建立的“语义场”的释义问题,而社会环境只是构成这个“语义场”中的一个对应的环节,两者之间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隶属关系,而只存在语言生成过程当中的相互对应、相互说明的映照关系。
3.电影社会学始终关注的是电影的文学意义,也就是说,更多的是把电影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力证,以此来说明艺术的社会学意义,至于说明的对象是电影、是电视,还是戏剧、还是歌舞,电影是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个定义,而电影的语境学的方法只适用于电影与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研究,电影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是主题,是构成整个电影语境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被研究的范例。
从根本上讲,电影的语境研究是打通电影语言的叙述情境与社会的文化情境的一条通道。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电影的叙事主题是如何撞击社会的历史主题,同时还可以看到社会的文化思潮是如何汇聚到电影的叙事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电影的叙事语境与社会的文化语境之间复杂而又重要的承转关系。中国武侠电影中的《黄飞鸿》系列片虽然讲述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清末民初之际,但是影片中所叙述的诸多主题依然是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即怎样面对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输入、怎样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当这些历史的内容在影片中变成一种象征性的寓言的时候,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历史处境即成为这个寓言得以解开的一把钥匙。这种叙事主题与社会主题的重合,使这部影片在深度模式和观众达成了理解的前提,尽管故事是发生在100多年前,然而, 主题的同一性消除了这个故事与现实的历史/时间差距,从而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四
在关于中国武侠电影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较多的注重的是对题材、对风格、对作者的研究,而往往忽视了关于武侠电影生成语境的研究,如果把中国武侠电影作为一个“历史本文”,它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一方面是通过对影像的平行阅读来实现,另一方面又必须将影片的“叙事本文”与它共生的“社会本文”联系起来,进行“交错阅读”才能真正地领悟出影片的真实意义。通过对电影语境的研究,我们发现在中国电影史上许多论争和辨析除了论争双方各自的观点的交锋之外,双方在语境上的差异实际上是造成诸多争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电影语言的表述方式是非对话性的,这就是说,电影语言的接受对象——观众在一般的情况下并不能与影片中的人物进行对话式的交流,所以电影语言只有讲述与接受的过程,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过程。它由一般的由双方构成的人物对话模式变成了一种由单向的表述与接受所构成的语言模式,这种语言模式为我们在进行电影语境的研究方面带来了相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它电影的作者(讲述者)与观众(接受者)不具备一般语言对话时双方所共知的语境。也就是说,在作者创作一部影片时所占有的各种语言环境,在这部影片放映时观众并不占有。为此,即使删除主体在个人因素上的种种差异,电影语言的对话双方也不具备共知的语境。其次,由于语境上的差异,极易造成对影片的“误读”。有鉴于此,电影语境的研究就在于要把电影语言中各个有意义的语言因素同非语言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即要把由视听影像语言构成的“叙事的上下文”,又要把由非语言因素构成的“情境的上下文”联系起来,才能够真正阐述电影语言的完整含义。
尽管可能有些导演对影像的建构、组合并不在意,而有的导演对影像的设置和联系又特别用心;但这些个人的主观因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电影的制作过程一旦完成,影像一旦出现在银幕上,并与某种语境(上下文)相“接壤”,它就具有“超越本文”的语境意义。众所周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败退于台湾,中国从此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在五十年代以来,港、台地区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反清复明”为主题的古装武侠影片。在这些影片中,主导的叙事动机始终是复仇:复个人之仇、复家族之仇、复国家之仇。国家的正面形象都是以过去/未来的形式出现的。现实的国家权力不是被东厂太监所控制,就是被外戚、奸臣所篡夺。这样,构成影片中国家形象的心理基础便是观众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期待,而大众这种心态正符合于那时台湾当局的社会政治需要:国家政权本来是我们的,江山本来是我们的,但现在不是了。要想……,就得……。于是,影片特定的叙事语境与外在于影片的现实语境形成了相互“接壤”、相互融合的格局。银幕上一个“光复故国”的历史神话,与现实中一个“光复大陆”的政治神话,这两种本文系统的叙事主题也在同一个时空坐标上翕然相汇,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媒介保持了高度的同一。台湾的片商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台湾当局暗送秋波,并以此为影片的发行放映大开绿灯。然而,随着历史巨流的奔涌,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光复大陆”成了一种永久的历史笑谈。武侠电影昔日潜在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今天的电影观众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因为整个的社会政治语境已经使其不再具有相互“接壤”的现实基础。
许多武侠影片都是以乱世作为叙事背景,影片开始便是阴云密布,狂风肆掠,哀鸿遍野(《新火烧红莲寺》);有的客栈中煮的竟然是人肉,衙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乱世伏魔》);要么就是宦官专权,横行霸道,江湖上一片血雨腥风(《新龙门客栈》)。在这种叙事语境中,观众自然期待着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一个拯救芸芸众生的大英雄,尤其是在个人的生活境遇与影片中所设置的这种叙事情景有某些类似的“重影”时,观众对影片美满结局的渴望其实就是一种对现实的“集体梦想”。任何一部电影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欢迎,不仅在于它有非常诱人的外部形态,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所蕴涵的心理内容是否与观众相同一。一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时常赢得电影的经济市场,其实首先是由于它把握了电影观众的心理市场,它能够将观众的精神与观众的社会心理有机地“缝合”在一起。
五
对美国人来说,越南战争无异于是一场“世纪的恶梦”。自1969年美军对北越实施空袭以来,美军便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战争陷阱。战场的失利,引起国内民怨沸腾。一贯对美国政局保持着敏锐嗅觉的好莱坞,此时便拍出了一部直接表现越战的影片《丛林战火》(The GreenBerets 1968),本想为颓丧中的越战美军打气, 不料该片“直奔主题式”的创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还引来了诸多的斥责。在这种情况下,好莱坞决定改变原定的策略,不再直接以尴尬的越南战场为题材,而是分别以“韩战”和“二战”为背景,重新拍了两部战争影片。一部是表现美军野战医院的战争喜剧片《陆军流行医院》(M.A.S.H),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另一部就是1970 年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拍摄的反映二战时期美军著名将领巴顿的影片《巴顿将军》。巴顿的扮演者乔治·斯科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导演沙夫纳于1941至1945年在海军服役时曾亲身参与巴顿指挥下的西西里战役;这些战争经验对他们的创作无疑大有裨益。担任该片高级军事顾问的美国五星上将、是当年曾长期与巴顿共事的布莱特雷将军。
美国当时的在任总统尼克松这位被美军在越战中的频频失败而弄得束手无策的鹰派总统,在反复看了数遍《巴顿将军》之后,对其大加赞赏,并终于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轰炸柬埔寨!如果说,当年的巴顿改写了“二战”的历史进程的话,那么,银幕上的巴顿又改写了“越战”的历史格局。以表现越战的“美式伤痕电影”而名躁影坛的好莱坞导演奥立弗·斯通在谈到这部影片时明确地说:“我认为该片是为数不多的几部直接改变美国历史的影片之一,其影响超过了《刺杀肯尼迪》。我相信,正是《巴顿将军》促使尼松决定轰炸柬埔寨,以使越南战争升级。”但是,究竟是什么使尼克松看了《巴顿将军》之后,做出了轰炸柬埔寨的历史性错误呢?显然,尼克松当时所处的历史境遇与巴顿在影片开始时所处的叙事语境是相互“重合”的。巴顿刚来到北非突尼斯战场时,美军军心涣散,损失惨重。巴顿正是在这种颓势下力挽狂澜,以其特有的勇猛和机警在非洲战场打败了由“沙漠之狐”隆美尔所率领的德国军队。编剧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生花妙笔,导演富兰克林·沙夫纳的奇特想象,乔治·斯克特的出色表演,最终使银幕上的巴顿将军成为了一个极易被人们所认同的银幕偶像。70年代初也正是美军在越南困难重重的危机时期。尼克松,这位对越南战争的胜负具有直接历史责任的总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想重新唤起昔日美国军队驰骋战场的雄风。然而,尼克松的致命失误在于他所处的立场——他必然混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战争!虽然都是美国军队,但是,军人的士气、战场上的胜败最终都将与这场战争是一种什么样的战争密切相关。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侵略战争,即便有铺天盖地飞机、坦克也只能称雄于一时一事,而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作为越战时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只能是失败的尼克松,而巴顿则永远是巴顿!
在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一部影片由于它的叙事语境与历史语境的重合,会对它的观看者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讲,影片中巴顿将军的胜利,既是属于历史上那位远征欧洲的巴顿,也是属于好莱坞这座巨大的梦幻工厂。
标签:上下文论文; 电影语言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文学论文; 巴顿将军论文; 尼克松论文; 剧情片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