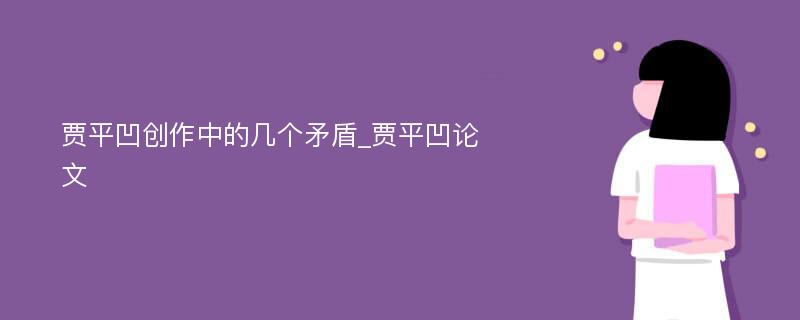
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矛盾论文,贾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入话
贾平凹的创作,在跨世纪的中国文坛上,不可小觑。贾平凹踏上文学之路二十余年,一直都处于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在新时期文学的不同段落,和他自己的每一个发展演变阶段,都有不俗的表现,都留下了可评可点的作品。贾平凹是当下为数极为有限的雅俗共赏、人气最旺的作家之一。就市场而言,他是“纯文学”作家中最受读者青睐的:他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废都》、《土门》还是《高老庄》,其发行量之巨,都令人惊叹中国读者的胃口之好;他的各种文集选集,对市场进行轮番轰炸,一波又一波,其版次和数量,在大陆作家中恐怕是难有比肩者;在文学圈子里,他也常常是个热门话题,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最重要的是,贾平凹正处于年富力强、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段,在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和对小说艺术的领悟上,都是臻于成熟的时候。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贾平凹当前创作中暴露出来的几个矛盾,就非常有必要在这里指出来,加以讨论,以便让正当烈火烹油之势的作家,能够变得警醒,有意加以克服,从而取得新的突破。
在自我与作品之间
贾平凹的小说新作《高老庄》,以及曾经惹出很多麻烦、激起很多风波的《废都》,都是以作家自我的某些生活阅历为蓝本,加以艺术的提炼和生发而成书的。在《废都》的后记里,贾平凹把它称作是“安妥我灵魂的”一本书,并且直白地倾诉了自己一系列的人生挫折;这些现实中发生的变故,部分地写入庄之蝶的故事里,更重要的是,由此造成的幽愤积郁、悲痛难抑的作家心态,使得读者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贾平凹=庄之蝶”的对应关系,使得《废都》中氤氲的悲凉之气,似乎获得了强大的现实依据。在《高老庄》中,也不难见出作家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的某些重合之处,比如,作品中离乡与还乡、离婚与再婚的男主人公子路,就让人联想到作家自身的某些经验。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最熟悉的东西,自然是有诸多便利的,得乎心而应乎手,常有举重若轻、事半功倍之功效。贾平凹的近作中,自我的心灵传记色彩,恐怕在中年一代作家中是最强的。
然而,正是在这种有意无意地造成的作家自身与作品内容的相应和之中,贾平凹混淆了作家个人生活和作品中的庄之蝶和子路之间应有的界限,不为人察觉地损害了作品的丰富性和独立自足性。
这至少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作家为作品主人公设定的身份——这在《废都》和《高老庄》中都是展开作品的前提,——往往是以不证自明的方式出现,缺少可信性。就人物而言,庄之蝶名列西京城的“四大名人”之首,但是,他作为著名作家的一面,他何以在西京城有那么大的声望,却很少在作品中加以表露;恰恰相反地,作品极力描写的是他“江郎才尽”的困窘,是他指望从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女性身上汲取东山再起的力量。子路身为著名教授,他在高老庄所作的方言调查,也太“小儿科”了;如果不是把庄之蝶和子路的显赫名声都与贾平凹自己的文学成就联系起来,他们两个人的身份识别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作家的自我迷恋,或者个人臆想——作家自己的失落也好,得意也好,都没有经过很好的艺术过滤,就不加掩饰不加节制地进入作品,投射到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缺少了必要的中介和转换,损伤了人物的形象深度。比如说,庄之蝶对自己的性能力的反复炫耀和欣赏,就大大地偏离了作品对一个浸淫在传统文化中的著名文人的定位,而使他接近于《金瓶梅》中荒淫无度的西门庆的心态。子路对于西夏的腿长和身高的赞赏,在《高老庄》中再三再四地重复出现,造成细节和情感的繁琐和雷同,恐怕也是一味地驰骋意气,满足于倾泻生活中的感受而缺少艺术的推敲所致。
第三,作者自身的情感和思考,往往大于作品的生活图景和艺术形象,庄之蝶也好,子路也好,在许多方面都不足以担当起作家的意图。作家自己对作品的诠释,不知不觉地超出了作品自身。
请试言之。经过多年的历练,贾平凹对自己的创作,自信而从容,在上述两部作品的《后记》中,他都把自己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思考直接地倾诉出来,用理性的文字印证感性的作品。但是,稍加比较,就可以明了,作家想要诉说的东西,与作品的内容之间,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作家的意图,未能很好地实现。如前所述,在《废都》中,庄之蝶与作家在后记中所表白的个人生活遭遇之间,在痛苦的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作家所遭遇到的种种痛苦,父亲病故,妹夫早亡,自己染病,婚姻破裂,陷入一场身心交瘁的诉讼,以及因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而感到的焦虑等等,并没有一一印验在庄之蝶身上——我不会幼稚到要求作家自己与他笔下“夫子自道”式的人物完全重合,我要说的是,作家在对作品人物进行艺术处理的同时,却没有对人物的情绪基调作出相应的调整,而是一味地借助有限的人物倾泻自己无限的感伤:庄之蝶所遭受的挫折要远远地低于和小于作者,但是在情绪上,庄之蝶却比后者还要激烈许多,绝望许多,这容易被作家自己和读者所忽略,但却造成作品的虚夸有余,沉实不足。在《高老庄》后记中,贾平凹申诉自己的“世纪末”情绪和人到中年的身心交瘁,并用以阐明自己的创作动机,这会给粗疏的读者和懒惰的批评家提供解读作品的现成路径,但是,分析作品,在子路的还乡过程中,却未必能够产生这样深切的感受。子路回乡祭祀已故的父亲,是履行人之子的义务,但是,初涉故土,他更多地是“衣锦还乡”,是向乡亲们炫耀年轻漂亮的妻子西夏以证明自己的“艳福”,以及努力地要在如鱼得水的家乡“种”下自己的儿子。此后,《高老庄》的故事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子路与西夏和菊娃之间的感情纠葛,一条是在地板厂和葡萄园,在蔡老黑和王文龙之间为争夺乡村的霸主地位以及争夺菊娃的斗争……如果说,子路还乡而痛感于高老庄人的“矮”,是隐喻大于形象,是把自己娶了个身材高大、年轻漂亮的姑娘的得意之情借题发挥到淋漓尽致;那么,他对于菊娃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患得患失的心态,和无法摆脱的潜在的占有欲望,恐怕和“世纪末”情绪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把子路的一己悲欢(而且是非常细微的悲欢,这种悲欢离庄之蝶的悲怆都相去甚远)与九十年代被人们挂在口边的“世纪末”一词拉扯在一起,自以为是在高扬“世纪末”之旗,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赶时髦,是一种“媚俗”或者“媚雅”而已。
这种作者大于作品,作者的主观情绪大于作品主人公所能提供的情感依据的弊端,恐怕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在于对个人经历到艺术内容的转换上的处理不当。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所描述的琵琶女,在这一点上是耐人寻味的。琵琶女本人的生活经历,盛极而衰,红粉飘零,已经具备了浓烈的悲剧色彩,她的琵琶技艺,和她的内心感遇,也足以令人叹惋,因此,才会有“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的艺术效果;但是,在琵琶女这里,她创造的艺术形象是远远大于其个人身世的感叹的,所以,才会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才会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才会给白居易,以及通过白居易的诗歌遥想琵琶女风采的我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若是她只会诉说个人哀伤,一味地“凄凄惨惨戚戚”,那大约就和反复地向人们诉说“我真傻,我只知道冬天有狼”的祥林嫂差不多了。当下的贾平凹,在“未成曲调先有情”和“低眉信手续续弹”地倾诉胸中块垒方面,已经是炉火纯青,但是,他能不能在宣泄个人哀伤的同时,能够“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能够“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丰富自己的艺术境界和艺术表现力,这值得作家深思。
形象与理念
与作家自我表白大于作品蕴涵相适应的,是作品的意念大于形象。
贾平凹的创作,曾经有过转益多师的阶段,例如,在拉美文学在中国盛行一时之际,他就摹仿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结构而写出《商州》。不过,近十年来,他的艺术取法于中国传统,尤其是明清小说的趋向越来越明晰,《红楼梦》等作品成为他心目中的标高。而且,他从这些作品中所得到的益处,也是非同一般的。我这里指的是曹雪芹的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腻而流畅的描写。从《废都》、《白夜》、《土门》到《高老庄》,都以对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抒写见长,以家长里短、杯水波澜和民情风俗画卷取胜。子路还乡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为父亲做三周年祭祀的前前后后,高老庄男女老少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在作家笔下娓娓道来,曲折有致,如行云流水,舒展自然。能够把琐碎的、平凡的日子写得有滋有味,别有韵致,是贾平凹的过人之处。
然而,《红楼梦》的艺术高度,毕竟不是轻易地可以达到以至超越的。曹雪芹的艺术功力,既表现在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集大成式的融裁经典而自铸伟辞,和他对于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上,更表现在他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人物的深入刻画,和对于作品中的虚实相生、真幻相形的两个世界的浑茫一体感的营造上。
就此而言,贾平凹塑造人物的能力,构造现实的与形而上的两个世界并且使之交相辉映的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先说人物。子路的个性中,有两个着力点,一是对于自身的“矮”的自惭形秽,从而非常得意于娶了人高马大、姿色过人的西夏,加倍地补偿了自己的一大块“心病”;一是对已经离婚的前妻菊娃放心不下,牵挂不已。依照作品中的解释,他和西夏结婚,以致在高老庄的土炕上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交合,是要进行人种改良,对于高老庄世世代代出矮人的现象进行矫正,甚至把问题提升到汉族与异族血统间的交流的高度去思考之,似乎他与西夏的结合,不仅是对于改变高老庄人种的积极贡献,而且还关乎汉族人种的改良和优化。这真是,男女之道,微言大义存焉。本来嘛,子路选择妻子,盼望子嗣,都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是关涉小家庭的事情。古汉语的教授,固然要在课堂上传承文化,弘扬文明,要有特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是,面对妻子,不必满口之乎者也,夫妻造爱的时候,又何必一心一意地想着“为万世继绝学,为生民开太平”,一定要孕育出如此这般的宁馨儿来。正像庄之蝶,在与风流可人的唐宛儿厮混的时候,却扬言要从爱情中汲取力量和灵感,激活创造力,要写出经天纬地的大作品一样虚伪。戏不够,理念凑,此之谓也。
其实,这是把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复杂化,把个人的潜意识和负疚心理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谎言掩盖起来。人都有一种补偿心理,换言之,人们都向往和希望获得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这是心理学一再地证明过的。作为知青一代而为人父母者望子成龙的心态非常普遍非常迫切,个中情由,与这一代人普遍地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此抱憾终身是互为因果的。子路出身于乡村,愿意娶城里人为妻,子路个子矮,想借西夏的高个子以弥补自家的缺憾,这本来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是,在此之前,作为大学教授的子路和作为农妇的菊娃,在两人的身份、地位等条件都很不相等的情况下离了婚。尽管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其自己的不幸,其中有各自的隐衷,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在这离婚事件中,菊娃受到了更大伤害,这却是一目了然的。社会和人们,习惯于同情弱者,连子路自己,在陶醉于西夏的修长健硕之余,也常常对菊娃心存愧疚。作品中赋予子路的关于人和种族的退化的思考,以及他为此而作出的“自觉承担”,就显得非常可笑,经不起推敲,不要说他和西夏在高老庄的一次次的“床戏”了无成绩,就是给他们发个特许证,让他们一连生出十个八个儿女来,高老庄人的命运,现代人的身心失调、生命力退化,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吗?岂不是荒唐至极!——十余年前的莫言写作《红高粱》,在痛感当代人的“种的退化”的时候,以充满传奇浪漫的笔调,极言“我爷爷我奶奶”的“白日宣淫”,一来是为了给孔孟之乡、礼义之邦“脸上抹黑”,有一种游戏色彩,二来,余占螯和戴凤莲都是高度地传说化、神话化了的人物,是“既能喝酒又能爱,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草莽异数,岂是凡人可以摹仿的?到了《高老庄》,贾平凹是“反其道而行之”,是要用今人的对于性欲的永无餍足势成饕餮,去克服前人遗传下来的生命委顿,惜乎选人不当,让子路和西夏这两个充溢着世俗气味和生活实感的人物去担当起“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即倒”的使命,不禁令人想到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的事件,往往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说穿了,这不过是子路把自己的离婚和再婚,以这样“宏伟”的命题包装起来,掩饰自己面对菊娃的尴尬心态而已。
子路的形象之所以树立不起来,甚至不如《废都》中的庄之蝶,根本上是因为他只是高老庄的一个匆匆过客。庄之蝶在作品中是处于生活的漩涡之中,他与别的几位名人之间的错综关系,他陷身于其中的名誉权诉讼,他和几个女子的恩恩怨怨,使他在作品中处处占据了主角的位置。子路呢,功成名就,而且带着红粉佳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而且还抱着“创造优良品种”的奢望,踌躇满志,得意洋洋。然而,仅仅在西夏和菊娃之间既受宠又尴尬既忘形又忘情,是不足以让子路的形象丰满起来的。他对于故乡的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旧情重温,故地重游,从民情风俗的层面上,给他增添了许多新的观感,但是却不能深刻地切入高老庄当下的精神命脉中去。那是蔡老黑、苏红、王文龙、庆来们的世界,是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也无意于去过问的一个他人的世界——子路口口声声以高老庄人自居,以农民自居,可是,他真正关注的,是乡村的文化,是乡村文化所能够给他提供多少做研究的资料,而不是现实中的乡亲们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高老庄对于他,只不过是一幅活生生的风俗图画而已。高老庄的生活洪流,泥沙俱下,波澜起伏,但这些都引不起子路的兴趣,与他的切身利害无关。他的兴趣只是在西夏和菊娃身上。一旦对菊娃感到了绝望,他就决绝地声称,“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这从事理上讲不通,他的母亲还在村子里,他怎么可能诀别高老庄?但是,这却充分地证明了他狭小自私的心胸中,连母亲都未必占有多少分量,何况是那些乡里乡亲呢?在已经是文化名人的子路那里,农民出身,成为他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识别标志,他和农村现实的血脉联系,却早已断绝了。他教训要抱打不平,为蔡老黑请律师做辨护的西夏说,“你要清楚咱的身份,咱是探亲回到高老庄的!……”这种局外人的心态,既揭示了子路的心灵蜕变,也使他失去了卷入乡村现实,于沧海横流中展现性格深度的契机。
比较起来,倒是新来乍到的西夏,对于了解乡村生活的热情要高得多。作品中的很多生活画面,通过西夏的眼光展示出来,因此多了一层陌生化的效果。在高老庄,她跑的路多,见的人多,对于高老庄的历史与现状,都表现出很大的了解和参与的热情,洋溢着一种旺盛而清新的生命活力。可是,她的风尘仆仆,四处奔波,也只不过是揭示出高老庄的生活一角,她不甘于只作外来人,想要融入乡村生活,但要实现这一愿望,恐怕还要假以更多的时日呢。
这样地,从还乡者和外来人眼中,从两个人的不同视野不同感受中,展现高老庄的乡村图画,而且写出新意,是绰绰有余,相得益彰;但是,风情画卷,没有深刻的人物支撑,未免会缺乏必要的深度。子路是把人当画看,对他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人物没有多少深入了解的热情,西夏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处于对人物的了解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中。因此,《高老庄》是风情画有余,人物深度不足;人情世态有余,历史深度不足。作为过客的子路和西夏,不足以在乡村的冲突中充当主角,他们的眼界的局限,又限制了经由他们的感知对于乡村里的风云人物和时代精神的深入开掘。
形而上与神秘主义
再说神秘主义。在否定了理性万能和绝对真理之后,神秘主义大行其道。从古老的周易,到新发现的特异功能,从民间嫁娶、公司开业择取吉祥喜庆的日子,到卷土重来的看风水算命相,都构成了当下的生活景观和文化景观。
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神秘主义,也成为营造形而上的意境的一种终南捷径。人们越来越注意,要把写实和写意,把生活实感和玄妙境界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对于作品的有限生活内容和情感蕴涵的超越和升华。随着社会上神秘主义思潮的坐大,一些作家也开始借助于它,去渲染作品的空灵悠远的氛围。贾平凹的创作中,就汲取了这些因素,他的《高老庄》和《废都》一样,其神秘主义的印记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废都》中的天文异象,四朵“妖花”,收破烂老头的歌谣,奶牛关于生活的思考,以及那一部难以破解的奇书,比如说,《高老庄》中小石头的无师自通的怪诞图画,西夏的匪夷所思的奇特梦境,白云湫的神秘莫测的传说,高老庄人的扑朔迷离的历史,迷糊叔的“深意藏焉”的歌谣,以至关于再生人的显形……凡此种种,都被作家以随意的即兴的方式融入了写实的生活细节之中,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开拓了作品的形而上境界。
不过,坦率地说,贾平凹在表述神秘主义的内容时,却往往是信手拈来,随意点染,因而经不住深入推敲的。造成其失察的,有多种原因,比如说,关于白云湫,进行了那么多的渲染,花费了那么多的笔墨,把它与高老庄人的历史兴衰联系起来,就像是相声里的“打包袱”,裹了一层又一层,把劲势憋得足而又足,把读者的胃口吊得高而又高。因此,要么不作交代,要么就必须把包袱抖响,抖出石破天惊的感觉来,如古人谈论诗歌艺术时所言,前有玄浮,后须结响。西夏被白云湫迷得走火入魔,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去探险;在反复的浓墨重彩的铺垫和渲染之后,读者自然渴望追随西夏,一睹白云湫之奥秘。不料,读者在盼望西夏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火爆刺激的时候,却发现是大大地上了一当,西夏和苏红还没有接近白云湫,就半途而返,大煞风景,让我有权力怀疑作家是故弄玄虚,是拿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当然,被戏弄的却不仅是读者而已,它严重地伤害了作品的“文气”,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明了作家的艺术功力的欠缺。
还有,神秘主义能不能够成立,关键是在于作家自己是真相信还是假手段,是确信其有,真实地诉说,还是半信半疑,姑妄言之,抑或只是一种叙述策略。现在的文学读者,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成长起来的,都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接受教育的,因此,要让读者接受神秘主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家自己是否就相信神秘主义和鬼神文化,是“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还是“为文而造情”那种玄虚渺冥的神秘感,是从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还是为了追求神秘感而制造出来,为神秘而神秘地充满了“人工气”。马尔克斯在谈到他的《百年孤独》中的魔幻色彩时就说,作品中那些在他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情,在南美大陆却是和现实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是人们深信不疑的。《高老庄》却未必能够让人信服这些神秘现象的确有其事,而是怀疑作家把神秘主义当作了作品的“调料”。
在1997年的《美文》杂志上,贾平凹曾经著文《十幅儿童画》。称赞西安的一对孪生兄弟——敦煌和龙门在八岁以前的绘画,并且夸奖其有神秘色彩。到《高老庄》中,这就脱胎换骨为小石头笔下神秘莫测的种种画面。然而,我观《美文》上所刊的绘画,固然感到了儿童画的自信和想像力,赞叹其笔力和线条,却难以像贾平凹所称道的那般入境。到《高老庄》中,作家为了加重其神秘的氛围,又对这些儿童画进行了“拔高”:敦煌和龙门的父亲是搞美术的,他们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环境的熏陶,耳濡目染,获得悟性,近水楼台先得月,小石头的画画才能却是天然习得,无师自通,受之于天,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孪生兄弟生活在现代城市,从卡通和科幻片中汲取绘画素材,小石头却是一味地驰骋想像力,能够慧眼穿透人的身体,凭空地画出人体骨骼来,而且一块都不错,一块都不少;孪生兄弟并没有预测和遥感的能力,小石头却能感知远处他人的死亡……这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先生评述《三国演义》的话来,刘备忠而近伪,诸葛亮智而近妖。为何?用力过度,过犹不及也。城里的孩子龙门画出恐龙起舞,情有可缘,《侏罗纪公园》、《恐龙特急珂赛号》等影视作品,和风行一时的恐龙模型玩具,都会触发他的想像力;让下肢瘫痪、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石头去画恐龙,却真是勉为其难。正像在《废都》里,要让牛开口说话,表达作家对于城市文明的批判,是故作高深实为败笔一样,为了营造神秘主义的气氛,而把种种奇迹强加在小石头身上,再次地证明了理念与形象的不相称,神秘的表象与肤浅的内涵的不相称。
女性理想与男权主义
贾平凹的创作,是从描写理想中的青年女性起步的。他最先引起人们注视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就是写了两个纯真活泼的农家少女。在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真纯天然、美丽善良的女孩子,是他歌吟的主要对象。此后,他的一系列创作,也总是给予女性人物以相当重要的位置的。《二月杏》、《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是如此,《浮躁》、《废都》和《高老庄》亦是如此。这在和他同年龄的男性作家中,是非同一般的。阅历的增长,世事的洞明,经沧桑历苦痛,不但没有使他放弃这种对于女性的痴情苦恋,没有粉碎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女神,相反地,哪怕是在满目苍凉的“废都”,在焦灼不安的“高老庄”,他似乎都是在越来越无所羁绊地渴求着女性的拯救和关怀。陷入人生困境和精神危机的庄之蝶,想要挣脱吞噬他的灵魂和肉体的毁灭之都,他在与唐宛儿、柳月和阿灿的交往中,获得对自己的肯定,对精神的和肉身的能力的肯定,以便能够在艰难困苦中再度崛起,再造辉煌。子路从精神上来说,是庄之蝶的形象的延续,只不过,他是沉浸在赢得西夏这样的理想女性青睐的喜悦中,在衣锦还乡中自我满足自我肯定,向乡亲们尽情地展览自己向城市作战的“战利品”;然而,他内心深处仍然有着种种遗憾,在故乡热土上,仍然不停地向西夏索取着,希冀着借助于她的力量,实现子孙后代的优化组合,乃至实现拯救高老庄人命运的幻想。
在这样的比较之下,子路和庄之蝶,说他们都是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小男人”,大约不为过错。这里的“拜倒”,有两重含义。一是说他们都需要女性向他们伸出救援之手,超渡他们出苦海得新生,二是说作家常常不惜折辱他们,以对比的方式,在光彩夺目的女性对比之下,反衬出他们的卑劣猥琐来。子路回到高老庄以后,他的种种农民的劣性在西夏面前就全盘地暴露出来,令西夏吃惊,也令读者吃惊。
把目光放远一些,就会发现,出现在贾平凹笔下的女性,似乎都是或多或少地带着动人的光环的。作家可以把男人写得很坏,写得卑鄙龌龊,他却舍不得让他笔下的女人学坏变坏,他就没有写过一个坏女人!就是在《废都》中与主人公打名誉权官司、把他拖入是非纷争、令他苦恼不堪的景雪荫,庄之蝶为她进行种种辩护还不算,到子路还乡的时候,还要再次用同情的口吻与菊娃谈到她。对待曾经有过精神恋爱关系而最终反目成仇的女性,尚且如此地怜惜,对于已经离婚却一直割舍不下的菊娃,就更上一层楼了。不只是已经离婚的子路对她旧情难忘,高老庄的两大能人蔡老黑和王文龙,也无不被她迷得颠三倒四,争相讨取她的欢心——尽管说,作品中并没有多少笔墨,让我们相信菊娃有多少可爱可敬,会让这些占尽一方风水的杰出男人们人见人爱;说得自私一点儿,她还有一个下肢瘫痪的孩子要带要养,却全然没有因此而给王文龙和蔡老黑的狂热降降温,令他们一味地执迷不悟,徒劳不已。个中原因,只能说菊娃的魅力不可阻挡了吧。西夏在陪着子路还乡的过程中,对于子路的母亲,对于坚决地排斥她冷淡她的小石头,乃至对于高老庄的乡亲,都已经到了一种圣爱的高度,宽宏大度,豁达开朗,很自然地就接受了乡村中的种种陈规陋习;甚至,对于子路一直是牵扯不断、情丝万缕的菊娃,她也毫无警觉和猜忌之心,仍然要为把菊娃带到省城去而开放绿灯,这样的女性,除了贾平凹,还有谁能写得出?
因此,说贾平凹是男作家中最会写女性的,最具有怜香惜玉之心的作家,恐怕是的评。凡是出现在他眼界里的女性,都被他极大地理想化了。问题在于,这种理想的核心何在?如果说,在贾平凹创作初期,他对于年轻女性是抱着一种精神崇拜,如他所效法的孙犁那样,在她们身上发现美的极致,发现生活的闪光,那么,时至今日,他对于女性的理想就现实得多了,是由美而及于性。就《废都》和《高老庄》中的女性描写而言,其一是要风姿绰约,年轻美貌,环肥燕瘦各擅场,形神情态自不同。其二是要善解人意,体贴入微,能够讨得丈夫或者情人的欢心(菊娃与子路分离的原因,就是她的性格太强,不顺从)。其三是要年轻,要有生命活力,不但是床上的功夫要好,还要有积极主动的“奉献精神”,从而能够激发起已经人到中年、身心交困的男性主人公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冲动和激情,在性事中获得超值享受。
于是,在对女性的尊重和理想化的表象后面,隐藏着的是男性的欲望,是男权主义的目光。更进一步地,在子路和庄之蝶的心目中,都是或隐或显地存留着齐人之福的旧梦,不由自主地向往着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的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在《废都》中,就显示着庄之蝶的“贤妻美妾俏丫头”的家庭图式:牛月清—唐宛儿—柳月,对应着《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后宫”中的吴月娘—潘金莲—春梅。子路还乡中,对于西夏和菊娃,总是抱着一妻一妾的幻想,在对西夏流露出由衷赞赏和无尽欲望的同时,子路又和菊娃藕断丝连,不无苟且之举;而且,作者还借母亲和乡亲们之口,反复地谈论着妻妾成群的合理性,有意无意地为他的行为寻找依据,给子路虚弱的内心打强心针,使他能够在西夏面前撑住面子,挺起胸脯,能够理直气壮起来。
这样地,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讲,贾平凹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理想,往往是拖着沉重的陈腐的封建主义的阴影的;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按照作家的理想化的要求描写女性,所有的女性都是被作家所严密控制和操纵的,她们是为了表达和满足男性作者和男性主人公的理想和需要而存在的,他们离开了男性,就不足以独立成人,不足以在作品中和生活中自为地生存,更难以独立自足、获得完整的个性。也可以说,她们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是作家理想中的“妻性”、“妾性”和“准妾性”,以及当软弱的男主人公万分失意时提供保护和安慰的“母性”,成为作家的传声筒,而不是血肉丰盈、形象充实的圆形人物。这当然会给贾平凹的创作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就是贾平凹笔下的男人和女人。夫子自道式的男主人公,过分地理想化而失真的女性,限制了作品的人物深度,与作家的创作意图背道而驰,让我们读出了双重的反讽意味:寻求理解、反复倾诉的男主人公,让我们发现了他们陈腐和卑俗的生活梦幻,以及那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责任感”掩盖下的欲望(如子路借助西夏改变高老庄人种乃至汉族人种的狂想);在被置于至高无尚的地位的、涂抹上神圣光环的女性身上,我们看到的不过是男性的充满欲望的目光所照亮的那些部分。因此,在贾平凹的庄严的诉说中,感受到了滑稽,感受到了幽默和嘲讽,这算不算是另类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