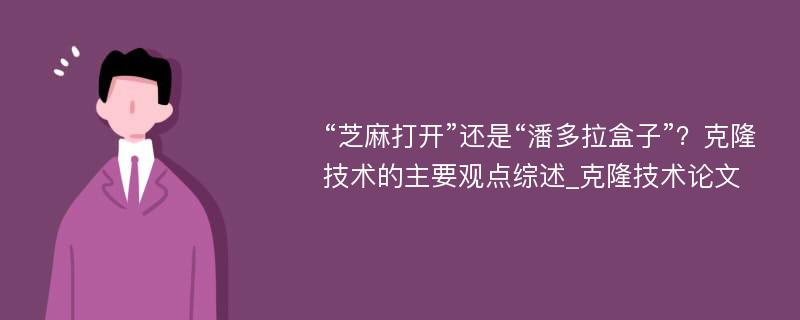
“芝麻开门”还是“潘多拉魔盒”?——关于克隆技术的主要观点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潘多拉论文,述评论文,芝麻论文,观点论文,魔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2月23日世界上第一头克隆羊“多利”(Dolly)诞生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以来,有关克隆技术及克隆人的讨论一直沸沸扬扬,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隆技术不断成熟完善,继克隆羊之后克隆兔、克隆猪、克隆猴等不断获得成功。照这样的速度下去,过不了多久人类将很有可能“遭遇”克隆人。但是,是否应将克隆技术引向人类自身却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讨论,各国政要、科技界专家、各阶层人士纷纷发表评论,意见此起彼伏、相持不下。转眼间5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人们对克隆技术及克隆人的态度日益明朗,目前,国际上对于此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人的尊严在于他的独一无二性”
其主要观点是:克隆技术破坏了人的尊严,并将导致一批疯狂的科学家进行克隆人的实验。克隆人将给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道德问题、生死观念以及人种优化带来巨大的冲击,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各国政府应立法禁止任何组织进行有关克隆人的研究,并进一步加大对生物技术的监控,进而取缔一切有关克隆技术的科学实验,以保证人类社会的秩序以及人种生生不息的繁衍与发展。
持这种意见的大多是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们认为,克隆技术是一项危险的技术,是“生物学原子弹”,它是继核技术后人类面临的又一项技术难题,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事实上,克隆羊多利一出世以来就引起了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恐慌,各国政府也对这项技术持否定怀疑的态度。美国科学界对克隆绵羊的反映是强烈的担忧。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医学伦理中心的教授黛安娜·也特尔斯说:“伦理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问:如果能够复制人,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另一位伦理学家埃里克·帕伦斯说:“只有傻子才不会对此感到震惊,我们对这些科学家取得的这项成果感到惶恐不安。”曾参与研制原子弹的英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约瑟夫·罗特布拉特把这项技术的突破与原子弹相提并论,他说:“有关无性繁殖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下去,有可能走上比核武器更危险的道路。”(注:金可溪:《关于克隆人的伦理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美国白宫对此反映迅速。1997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禁止把联邦的资金用于克隆人,并责成美国伦理学咨询委员会调查这项新技术引发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并且在90天内向他汇报调查结果。他说:“鉴于我们最珍视的信仰和人性的观念,我自己的看法是,克隆人必然将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是诞生在实验室以外的奇迹。”(注:《克隆:潘多拉的魔盒?》,《科学世界杂志》1997年第5期。)另外,加拿大、德国、阿根廷、法国、印尼及世界卫生组织都表示反对克隆人的研究,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也表示不支持克隆人的研究。另外,加拿大、德国、阿根廷、法国、印尼及世界卫生组织都表示反对克隆人的研究,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也表示不支持克隆人的研究。
那么,克隆人究竟会带来哪些后果呢?他们认为:首先,克隆人会给伦理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因为克隆人在外貌、体形等生理特征上将会和提供体细胞的人很相似,甚至是一模一样。另外,在克隆人的过程中会涉及到这样三种对象:体细胞核供者、去核卵供者和孕育者,三者可为一人,也可分为三人。他们和克隆子代的生物学关系和社会关系如何确认呢?是以父子相称还是以兄弟相称呢?因此克隆人彻底搞乱了人伦关系,因为夫妻、父子关系是最基本的人伦关系,而在克隆人那里,真正的人的夫妻、父子关系消失了,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道德也就消失了,克隆的人类就是一个父将不父、子将不子的人类。其次,克隆人使人类的基本定义发生了改变。人类是通过男女两性繁殖起来的,克隆人使性交相分离,变成了在实验室里制造人,使人类丧失了尊严。再次,克隆人会造成人类性别的单一化。目前,“单亲无精生殖技术”已经可以使女人生孩子不需要男人的贡献,女同性恋者可以通过克隆技术拥有自己的孩子而不需要男人的精子。当然,由于缺乏男性基因,她们的孩子都是清一色的女孩。这样,势必会造成人类性别单一化,带来社会问题。最后,克隆人不利于人种的进化繁衍。“整个自然界的物种进化是个自然过程,从物种进化看,进化靠变异,靠基因突变,突变积累了才能分叉,分化出新物种,这样才有物种的多样性。但克隆技术的基因完全来自同一个个体,来自单亲,克隆的物种完全是单纯的、保守的,形成不了物种的多样性,克隆技术不是进化的手段,它是反进化的,人类必须靠正常的婚姻,正常的两性结合才能发展,正是人类进行不断的男女婚配、组合,这样发展下来,人类才越来越聪明。”(注:《克隆:潘多拉的魔盒?》,《科学世界杂志》1997年第5期。)(卢圣拣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
(二)“科学本无过,庸人自扰之”
其主要观点是:克隆技术不可能复制出完全意义上百分之百的人,人的社会属性是在后天中形成的,社会属性才是决定一个人的首要标志。另外,克隆技术可以广泛的运用于医药、自然保护和基因工程中,从而为人类造福。因此,克隆技术应该得到提倡,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克隆人体胚胎的目的也是为人类提供生理器官和战胜疾病服务,不应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冷遇。
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大批科学家和业内人士的看法。2001年8月,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意大利著名胚胎学家西弗里诺·安蒂诺里医生宣布,他将于2001年11月实施人类首次克隆人的实验。这一消息一下激起千层浪,虽然他一再宣称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帮助人类治疗疾病,帮助不孕夫妇生儿育女,但他还是成为众矢之的,被一些人称为“疯子”。无独有偶,就在同一月的2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先进细胞技术公司”(ACT)捷足先登,率先克隆出人类胚胎。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同时发表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宣称他们的结果可能“代表着一个医学新时代的开始,表明人类离治疗性克隆的目标已近在咫尺”(注:Gary Stix著:《究竟什么克隆出来了》,《世界科学》2002年第4期。)。他们虽一再声明,治疗性克隆——与旨在培育婴儿的生殖性克隆大不相同——将为我们提供用于治疗糖尿病、麻痹症等现今不治之症的干细胞,但还是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消息传出后,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向国会发表演讲,表明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坚决不允许各类科学组织进行克隆人的研究。
鉴于反对者一直将目光定在克隆人与被克隆体完全一样的错误认识上,主张进行克隆技术和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专家认为:利用克隆技术并不能得到两个或多个和前人在意义上完全相同的人,尽管克隆人在外形和体格上同亲体十分相似,但并不是完全相同,正如这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即使克隆人与亲体在外形等生理特征上完全一致,但他们的意识、个性、性格、气质、脾气、感情等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经历中形成的,不是克隆技术可以解决的,这要受到社会生活环境、教养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即是说,我们只能复制出躯体,而无法复制一个人的思想。遗传学上有一个经典公式:外型=基因+环境,只要两个人生活环境和事物结构不一样,他们的外形也绝对不会一模一样。可以设想,即使克隆出一个爱因斯坦或希特勒,把他们放到人烟稀少的山区里,使他们受不到教育和接触社会,没有学习和人生经历,那他们也就成不了科学家和战争狂人。那些担心克隆技术会被坏人利用,从而克隆出一批危害人类的千古罪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他们声称,克隆技术远非那些无端肇事者所说的那样会带来世界末日。克隆人是会给人们带来一些问题,但人类还是有力量解决这些困难。克隆技术的真正价值在许多方面会给人类带来福利,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不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为科学的发展让出一条道路来,或者至少不要人为地去遏制它的发展。
(三)“克隆是把利弊双刃剑,关键在于人类理性的把握。”
其主要观点是:克隆技术和任何科学技术一样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会给我们带来福利,也会给我们造成伤害,这主要看我们怎样去利用它,以便我们在得到好处的同时把可能的危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克隆既然已经出现,我们就应该坦然地面对它,完全没有必要象一些人那样整天惶恐不安、惊慌失措,以为世界秩序大乱,人为的夸大克隆技术的危险;但同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违背人类意志进行一些严重威胁社会的不人道的研究,培育出一些“人兽”或“兽人”来,甚至是一些三头六臂的怪物出来,那就真是天下大乱了。总之,克隆既能造福人类,也能危害人类,关键在于人们怎样用理性去驾驭。
这种观点代表了国际国内一大批人士的看法。他们认为主要是要加强社会控制。社会调控主要有三个层次:政府行政干预、法律的强制规定和道德的自我约束。政府的行政干预主要通过控制研究经费的流向得以实现,政府可以禁止向研究人体克隆的项目拨款,而对于医学和育种目的的克隆动物研究则可以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在立法层次上,应通过法律规定禁止人体克隆实验,但不能因此而阻碍了其他生命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伦理道德约束方面,应着重加强科研人员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徐友渔先生说,除了新闻媒介的呼吁和研究人员的职业道德约束外,关键是要立法,制定一套规则。凡是涉及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的研究,都要置于舆论的监督和政府的管控下,而这必须要从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经济成本效益的角度进行论证,决定克隆技术的发展方向。中科院的研究员杜淼先生说:“我觉得科学发展对人类是有利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用法律解决,有利的一面要值得发扬和鼓励。”(注:《克隆:潘多拉的魔盒?》,《科学世界杂志》1997年第5期。)
(四)反思:科技与人
1978年试管婴儿成功后,这一技术就始终被两种不同的意见包围着,从生育与节育、代理母亲、安乐死、人工受精,生命科学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争论。当原子能显示出巨大威力时,爱因斯坦也因其在二战中杀害太多人而深感痛悔,小羊“多利”的诞生以及美国克隆出人类胚胎再次引发人们对遗传工程技术的伦理、对科技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担心和忧虑。可谓沸沸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西方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曾对科技与人的关系进行过系统全面的阐释。他们援用韦伯的合理性范畴及其理论,提出科技进步会导致人遭受全面奴役的理论。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所提出的基本诊断是:“工艺(即科技)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注: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纽约1972年版,第121页。)他们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工具的复杂化、精确化,反过来会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力的增强,人愈益沦为科技的奴仆;科技异化为与人对立的客观力量,由摆脱自然强制性的工具转为统治并威胁人类生存的工具。他们审视到了科技对人的负面效应:“在科技进步的鼎盛时期,我们看到的却是对人类进步的否定:非人性化,人遭到摧残,审讯‘常用的’一种手段——严刑的恢复,原子能的毁灭性发展、生命圈的污染等。”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的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打上太多意识形态的色彩,将科技与人的发展绝对对立起来,其实宣扬的是一种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宿命论。马克思看到了科技对人类的不利的一面,但他坚信科技对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他把科技首先看成是历史有力的杠杆,看成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373页。)当今,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航空航天等新科技革命正日益改变着这个世界的面貌,科技悲观主义并不可取。不过科技发展如何同社会发展相适应、科学技术使用中如何兴利除弊,保持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如何防止科技转化为压抑人的手段,这又是我们在追求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