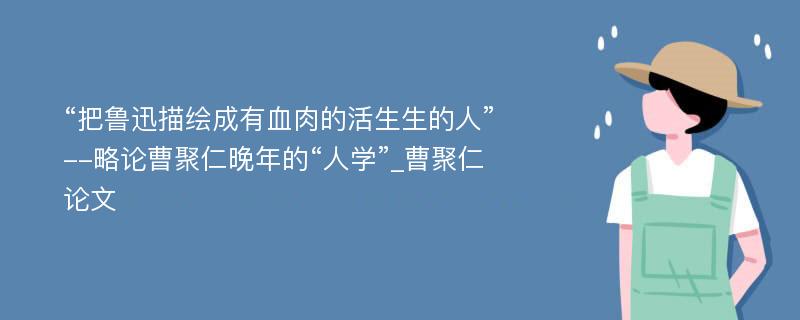
“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评晚年曹聚仁的鲁迅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有血有肉论文,活人论文,晚年论文,曹聚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聚仁虽然早在大陆时期就登上了文坛,和鲁迅等人过从甚密,是海派作家重要的一员,但他的4千万字以上的著作,,有近3/5 完成于香港(在大陆出版了26种,在香港出版了43种)。1950—1972年,他在香港生活、写作,成了地道的香港作家。《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是他的两种主要研究著作。
他做过近20年的新闻记者,加上他和鲁迅交往甚密(仅鲁迅给他的书信就多达44封),鲁迅是和他同桌吃饭、一室闲谈的文友,他本人又十分尊敬鲁迅,他说过“假如时间稍微推前一点,我就在杭州赶得上做他的学生(他教的杭州两级师范,便是我们一师的前身)”(注:曹聚仁《鲁迅年谱(20)》,香港《文艺世纪》1959年新年特大号(1 月出版)。)。所以,由他作传是合适的,至少他不会去相信那些推想和神话般的玄谈,更不会按谁的旨意去图解。他完成于1956年的《鲁迅评传》,便是他独立思想的产物。
该书28章,前面是“引言”,后面依次为:绍兴—鲁迅的家乡、他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在日本、辛亥革命前后、民初的潜修生涯、托尼学说、《新青年》时代、在北京、《阿Q正传》、 《北晨》副刊与《语丝》、南行——在厦门、广州九月、上海十年间、晚年、《死》、印象记、性格、日常生活、社会观、青年与青年问题、政治观、“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文艺观、人生观、他的家族、他的师友、闲话。前面16章,为生平史实,后面12章,为鲁迅面面观。这种构架,与郑学稼、王士菁均有不同。
1967年出版的《鲁迅年谱》分上下卷,上卷为年谱,计11节,依次为小引;幼年:1881—1897年,少年:1898—1901年,日本留学:1902—1909年,辛亥革命前后:1910—1911年,在北京:1912—1916年,五四前后:1917—1926年,南下:1926—1927年,在上海:1928—1936年,病逝。下卷为“作品评论及印象记”,作者周作人、茅盾、(英)H.E.Shapick马珏、阿累、陈源、张定璜、曹聚仁、景宋、内山完造、邓珂云。另有悼诗及挽联。附录有“鲁迅生平和著作年表”。其中,上卷曾在香港《文艺世纪》连载过,后经过修正和补充。下卷则是作者过去和邓珂云合编的《鲁迅手册》的修订本,比过去编得更有代表性。其中陈源致徐志摩的信,充满了攻击鲁迅的内容。曹聚仁之所以要收入,是因为鲁迅自己觉得这是难得的反面教材,曾同意编入《关于鲁迅及其他》一书,亦可见鲁迅胸怀之宽广。
曹聚仁研究鲁迅,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自始至终坚持认为鲁迅是人,反对把鲁迅神化的观点。他曾当着鲁迅的面说过:“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注:曹聚仁《鲁迅评传·引言》。)在他看来,要在表面上把鲁迅形容得伟大的人,“也许表面上是褒,骨子里是对他的嘲笑呢!”而在思想上,曹聚仁也认为鲁迅并不纯粹:“他的思想本来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的。一定要把这些矛盾之点掩盖起来;或是加以曲解,让矛盾消解掉,那是鲁迅所不会同意的。鲁迅赞许刘半农送他的对联:‘魏晋文章’,‘托尼学说’,那就一切歪曲都没有用了”。(注:曹聚仁《鲁迅年谱(20)》,香港《文艺世纪》 1959 年新年特大号(1 月出版)。)这与有些论者极力否认或削弱托尼学说对鲁迅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这表现了曹聚仁作为一位史家求真的一面。鲁迅赞同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兼容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与尼采超人的学说”(注:参见刘心皇《鲁迅这个人》,台湾东吕图书公司1986年6 月版。); 他有为人亲善的一面,同时还有“绍兴师爷的脾气”, 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基于鲁迅不是圣人的思想,曹聚仁不赞成把鲁迅批判过的人都看成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便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是太天真了——鲁迅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这些看法有合理的成分,像徐志摩、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如因鲁迅批判过就抹杀其作品及其影响,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批判顾颉刚,连其考证工作也加以否定,这是“党同伐异,气量偏狭”的表现。但是,被鲁迅痛骂过的王平陵、黄震遐,与顾颉刚不同,他们从事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有靠山和背景,不能因其年轻就低估他们的能量。在这方面,曹聚仁的评论未免有书呆子气。
曹聚仁研究鲁迅,处处注意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鲁迅,而不是以偏狭的政治眼光或“阶级斗争为纲”的眼光来衡量鲁迅的一切文学活动和实践,因而他不满王士菁在其《鲁迅传》中把鲁迅在上海10年当作被围攻的时期。他认为,“新月派”、“第三种人”、林语堂和鲁迅的笔战,均是文艺观不同的争论,而谈不上围攻鲁迅。“真正围攻过鲁迅的,倒是创造社的后起小伙子,《洪水》,‘太阳社’那一群提倡革命文学的人”。这种看法,不失为一种崭新的看法。因为文学论争多半是由文学问题引起的,不见得都是阶级搏斗。而创造社诸君子对鲁迅实行错误的排斥、打击的方针,甚至污蔑鲁迅是什么“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法西斯蒂”等等,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围攻”。过去的文学史家往往偏袒钱杏村等人,对“第三种人”则一棍子打死,这是“左比右好”的思想在作怪。
鲁迅曾被国民党通缉7年而未被逮捕,其原因何在?曹聚仁认为, 鲁迅在上海10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原因是,鲁迅的名声和地位,一方面受中共组织所掩护,一方面又为国民党特务所不敢触犯(投鼠忌器)。曹聚仁在这方面虽不及后来的刘心皇拿出足够的证据说明自己的判断,但这毕竟言之成理。而且,曹聚仁在香港研究鲁迅时并没有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是谈自己的实感而不是在为谁辩护。应允许这样的观点存在,才能体现百家争鸣的精神。
曹聚仁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比如,王瑶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把那一(指左联)时期,当作鲁迅领导文学运动的时期”(注: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9月版,第138页。)。曹聚仁认为此说不符合事实,因为“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社会科学联盟,或戏剧工作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他们对于鲁迅,只当作同路人看待——他们有其领导文化运动的路线,并非要鲁迅来领导”他在《鲁迅研究述评》一文说得更明确:“若干文化运动,如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都不是鲁迅所领导的,一定要把这些文化工作写在鲁迅史上,对于他,也只能说是一种莫名奇妙的讽刺。”(注:曹聚仁《鲁迅年谱(20)》,香港《文艺世纪》1959年新年特大号(1月出版)。)曹聚仁这里讲的“领导”,主要不是指思想上的, 而是指担任的实际职务。冯雪峰说过:“左联和鲁迅是相互发挥的”,“在那时候,只要有鲁迅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不倒,左联就不会倒。鲁迅斗争的顽强和他的权威实在起了决定的作用”。这里讲的是鲁迅的权威(并非是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所产生的效应,因而曹聚仁引出来的结论是“左联依靠着鲁迅,而不是鲁迅领导左联”。这样理解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不是贬低鲁迅,而是还鲁迅以本来面目。尤其是大众语运动,1934年夏天由曹氏与陈望道、夏丐尊、徐懋庸、金仲华、陈子展等人提倡,然后向鲁迅征求意见。那篇在大众语运动中产生广泛影响的《门外文谈》,是应曹聚仁的请求写的。鲁迅在大众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不是领导作用,这种看法是站得住脚的。
在研究鲁迅小说方面,曹聚仁也有新的发现和大胆的诊断。如论《阿Q正传》,曹聚仁曾说过鲁迅也是“阿Q”(注:曹聚仁《鲁迅评传·引言》。)。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丑化鲁迅,其实,曹聚仁不过是说明“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注:曹聚仁《鲁迅的一生》, 台北新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12月版,第61页。)。这“中国人”当然也包括鲁迅,也包括曹聚仁自己在内。但曹聚仁并没有荒唐到把《阿Q 正传》看作是鲁迅自传体小说,只是认为它“是一篇典型的现实的讽刺小说”(注:曹聚仁《鲁迅的一生》,台北新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12月版,第163页。)。
曹聚仁对《在酒楼上》这个短篇也相当重视,认为这是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正如他自己所推荐的孔乙己一样”,因为这篇小说“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怀”(注:曹聚仁《鲁迅的一生》,台北新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12月版,第165页。)。 曹氏原以为吕纬甫的原型是鲁迅的朋友范爱农,“后来才知道其中虽有范爱农的成分,但大部分还是鲁迅自己的写照”。尤其是有关蝇子飞了一小圈后又回来停在原来的地点的议论,以及先前到过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的感慨,“是把真的鲁迅勾划出来了,他就是吕纬甫”(注:曹聚仁《鲁迅的一生》,台北新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12月版,第166页。)。 但曹聚仁并不是认为吕纬甫的精神就等于鲁迅的全部,鲁迅后来就飞到更高更远之处,没有“停在原地点”上。我们应该准确、全面地理解曹聚仁对吕纬甫的评价,而不能一听到鲁迅“就是吕纬甫”便认为贬低了鲁迅的光辉形象。
曹聚仁和冯雪峰是先后同学,且两人均是鲁迅的挚友,但他们对鲁迅的看法有重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于冯氏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看鲁迅,而曹氏却站在无党派的立场透视鲁迅。对冯氏的《回忆鲁迅》,曹氏认为其中对鲁迅的评价有拔高之处,里面有“教条主义的错误”。他最反对的是冯氏对《彷徨》和《野草》的评论,不认为《野草》的思想和感情不健康,而认为“鲁迅一生的作品中,《野草》是最好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最接近尼采思想的”(注:曹聚仁《鲁迅的一生》,台北新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12月版,第163页。)。曹氏和冯氏的看法见仁见智,很难说谁是谁非。不同的研究角度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多种结论比一言堂好些。
对《故事新编》中的《采薇》,长期以来未受重视。而曹聚仁认为:“鲁迅和笔者所谈:《采薇》中的‘阿金’是很重要的;他创造了阿金,就等于创造‘阿Q’,阿金也和阿Q一般普遍地活着的。”(注:曹聚仁《鲁迅的一生》,台北新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12月版,第173页。)可是,有人认为鲁迅写阿金是为了讽刺某类人物(以“鹿脯”和“卢布”谐音为例),曹聚仁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牵强。还有,曹氏认为“《一件小事》只能算是一篇杂文。《明天》是一篇阴暗的小说。”(注:曹聚仁《鲁迅的一生》,台北新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12月版,第58页。)这些看法也很值得重视。
在体例结构上,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也有独到之处。该书不完全按纵的线索流水账式的叙述鲁迅的生平,而是抽出诸如“托尼学说”、“青年与青年问题”、“文艺观”等专题单独评说,这样给人以结构上的立体感。由于这是作家写的评传,且是鲁迅当年好友写的评传,故行文中所穿插的一些回忆文字,使读者感到亲切,可读性甚高。至于《鲁迅年谱》,深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尤其是胡适所撰的《章实斋年谱》的影响。具体说来,曹聚仁编的年谱,除列举鲁迅作品的著述时间外,把凡是可以表示鲁迅思想发展的变迁沿革的材料,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在列举鲁迅作品时,不是客观的介绍,还掺入自己的评价。如谈到《白光》这篇真写狂人的小说时,将其和《狂人日记》比较(注:见《鲁迅的一生》第69页。)。谈到《中国小说史略》时,便对其学术特色作出评价(注:见《鲁迅的一生》第321页。),尽管文字不长。 历来的鲁迅传记,一般只说好话,尽量不谈传主的局限。曹聚仁则既报喜又报忧,既说鲁迅的长处也说其短处。
曹聚仁研究鲁迅的工作,在香港学术界口碑甚佳。现代文学史研究家李辉英曾说:“曹聚仁先生写这部评传是因30年代初期和鲁迅的来往还很密切,对于鲁迅只消察言观色,就已是上好的材料了——直到今天为止,可以大胆地说,还没有任何鲁迅传超过曹著这一部。”(注:《跋〈鲁迅评传〉》。)曾经三次向曹氏索要“评传”的周作人,在致曹氏的信中也说: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尊书引法郎士一节话,正是十分沉痛。常见艺术家所画的许多像,皆只代表他多疑善怒一方面,没有写出他平时好的一面,良由作者皆未见过鲁迅,全是暗中摸索,但亦由其本有戏剧性的一面,故所见到的只是这一边也。(注:《跋〈鲁迅评传〉》。)
当然,许多内地学者对曹聚仁的鲁迅研究有保留,因为曹聚仁的评价确实还有不少值得质疑之处。
一是鲁迅是否是“同路人”的问题。曹氏认为:“我们得承认鲁迅自始至终是‘同路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共产党员,否则我们就无从解释鲁迅回复徐懋庸的公开信以及他写给胡风的几封信了。作为一个‘同路人’,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贡献也是同样伟大的。”(注:见《鲁迅的一生》第164页。)他说的“同路人”, 含有鲁迅并未加入中共组织,但仍靠拢中共,与中共同走一条路的意思。这与胡适认为鲁迅晚年“反共”(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58年5月4日)。)的说法完全相反。因曹氏说鲁迅是“同路人”而将其打入反鲁乃至反共行列,是黑白颠倒的表现。但这里讲的“同路人”,在内地学者使用时有特定的政治含义,故这一词是否准确、科学,值得讨论。
二是鲁迅是否属于“自由主义者”。胡适曾和周策纵说:“鲁迅是我们的人,鲁迅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注:周策纵《五四思潮得失论》,台北《中国时报》1987年5月4日。)无独有偶,曹聚仁也认为鲁迅“只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义感很强烈,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前驱战士”(注:《鲁迅评传》第226页。)。这种判断是有偏颇的, 它带有曹聚仁本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如上节所述,曹聚仁赴港后,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和“自由主义者”自居,对内地50年代初期的新气象有赞有弹,结果遭受左右两派的夹攻。鲁迅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其思想境界比曹聚仁高得多,其政治立场亦比曹氏坚定,旗帜更为鲜明,这从鲁迅批评曹氏1933年所写的《杀错了人》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对同一政治斗争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注:参看鲁迅《“杀错了人”异议》,《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曹聚仁把鲁迅说成是“ 自由主义者”,未免有谬托知己之嫌。本来,曹氏与鲁迅“有一段极机密的交游”(注: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鲁迅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凭这点,他可以像当年有人说“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样说“我的朋友鲁迅”。曹聚仁没有以此去炫耀,这是他人品高尚的表现。但他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决定了他不时会以自由主义者的眼光去审视鲁迅,以自己的好恶去评价鲁迅。这样,鲁迅就难免被这位台港文坛有名的自由主义者打成自由主义分子。这客观效果上是谬托知己。关于这一点,曹聚仁在《鲁迅与我》中曾坦率地表白过:“在鲁迅身后20年,我才开始写《鲁迅评传》,后来又再三易稿,写成了《鲁迅年谱》,真的是谬托知己了。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的结尾上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鬻,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或许我也是这样的‘无聊之徒’呢!”(注: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鲁迅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想不到曹聚仁竟不幸而言中。 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无法理解鲁迅讲的下列话:“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注: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注: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三是鲁迅是否戴着假面具演戏问题。1945年后,曹聚仁曾任苏州国立社教学院教授。他在该院讲课,曾对学生说:“人总是人,人是带着面具到世界来演戏的,你只能看他演得好不好,至于面具下面那个真实的人,那就不是我们所能看见的。……依我的说法,鲁迅为人很精明很敏感,有时敏感过分了一点。我们从他的言论中,听出他对青年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而且上了无数次当,几乎近于失望,然而,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属于青年,所以他对中年人,甚至于对他的朋友,都不肯认输,不肯饶一脚的,独有对青年,他真的肯让步认输……。”这里讲的鲁迅敏感乃至过分敏感,上过许多青年人的当,均是事实,但他并未由此改变对世界属于青年的看法,这是因为他善于辩证地看问题,还有他早年信过进化论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人格分裂,戴着面具在演戏。演戏云云,是曹聚仁的人生观。他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强加在多次反对过“做戏的虚无党”的鲁迅的身上,是很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鲁迅实际的。
从根本上说来,曹聚仁是拥鲁的,对鲁迅是相当尊敬的,和郑学稼们水火不容。他虽然号称不偏不倚,其实是“形中实左”。他受过右派及左派的围攻,又曾3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请他吃过10次饭, 在贫困的晚年对国家的前途仍感到乐观。仅凭这一点,内地应重印他的《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至少作为内部出版吧。
标签:曹聚仁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鲁迅年谱论文; 鲁迅评传论文; 读书论文; 野草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