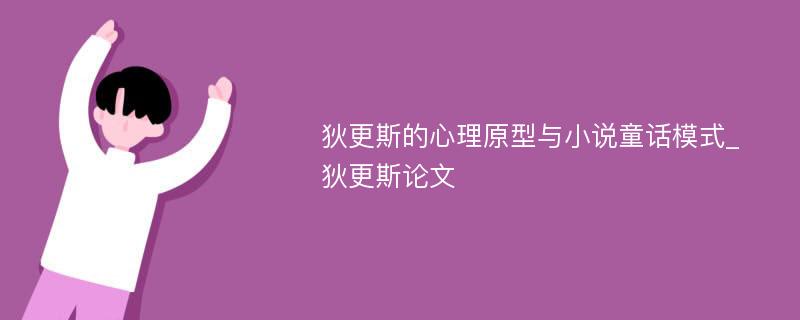
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童话论文,模式论文,心理论文,狄更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文学起源的角度看,童话是原始的文学,它与小说有相似的结构形态。“童话是原始民族信以为真而现代人视为娱乐的故事”;“童话是神话的最后形式,小说的最初形式。”①从创作者的角度看,原初的童话是民间的集体创作,单个文人创作的童话那是后来的事,但文人创作的童话保留了原初童话的模式。马克思将希腊原始初民的神话喻作“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作为“神话的最后形式”的童话,从起源的意义上讲,其实也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具有原始初民的那种原始思维的特征。马克思之所以把原始初民比作人类的童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始初民和童年时期的人相似,都处在蒙昧阶段,在情感——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精神内质上具有同构性。所以,童话虽不等于儿童故事,它也不一定是专为儿童写的,但它隐含了儿童的情感——心理结构以及思维模式,因而它往往和儿童的心理相契合,童话也往往成了儿童文学。
狄更斯的小说固然不是儿童文学,但其深层却隐含了童话模式。认识狄更斯小说中的童话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狄更斯创作的奥秘与风格。
狄更斯小说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他是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家中最杰出的。”②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家也是从童年、少年走向成年的,许多作家都从童年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然而,极少有作家象狄更斯那样在创作心理上如此依恋童年的情感与经历。英国评论家奥伦·格兰特说:“作为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儿童生活和童年经历是成年后的狄更斯关注的中心。”③我们有理由认为,狄更斯的心理原型是与童年的情感——心理紧密相联的。
狄更斯早期的童年生活是愉快而美好的,但以后很快笼罩上了阴影。后来的童年是一段缺乏欢乐、忍受屈辱的生活经历。这种生活与体验在他心灵中留下的印痕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灵的创伤。
应该说,欢乐美好与辛酸屈辱这两段童年生活体验对狄更斯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后一段生活的辛酸与屈辱反衬出了前一段生活的欢乐与美好,也激起了他对人性的美和善、对人类生活的幸福与光明的向往。前一段生活体现着人性的美与善,后一段生活使他看到了人性的丑与恶,而经历了丑与恶的考验后的他,依然保持着对美与善的美好情感,并且把这种体现着童真、体现着美的自然人性的童年生活作为人生的理想。
成年后的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这种人道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的,虽然狄更斯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促使狄更斯的思想与基督教结缘的则是“儿童”,也即人性的自然纯真以及美与善。在《圣经》中,儿童被看作是善的象征,自然纯真的儿童与天堂的圣者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圣经》认为保留了童心也即保留了善与爱。狄更斯人道主义的核心是倡导爱与善,他希望人们永葆童心之天真无邪,从而使邪恶的世界变得光明而美好。他在遗嘱中劝他的孩子们说:“除非你返老还童,否则,你不能进入天堂。”④狄更斯把美好的童年神圣化和伦理化了,因而童年或儿童成了他心目中美与善的象征。
狄更斯对儿童的崇尚,除了与自身的童年经历、与《圣经》有关外,还受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评论家奥伦·格兰特认为,狄更斯关于儿童的观念,是“他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继承来的,这种观念表达了成年人的忧虑。”⑤确实,狄更斯关于儿童的观念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布莱克等十分相似,而这些作家也都与基督教观念有联系。华兹华斯十分崇拜天真无邪的童心,认为孩子的伟大灵性高于成人,认为孩子具有上帝的神圣本性,因而对儿童充满虔敬之心。至于狄更斯与布莱克,“虽然我们没有根据说狄更斯曾经读过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但是,他的小说和布莱克的诗在儿童问题上是十分相似的。布莱克把儿童作为人的自然的、自由的和天然的生命力来歌颂。”⑥狄更斯对人道主义思想的推崇与宣扬,虽然有基督教的泛爱思想和传统人本主义思想成份,但在精神内核上却与他的儿童观念密切相关,或者说他的人道主义是以实现儿童那样的天真、善良、自然、纯朴的人性和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儿童的纯真与善良→基督精神→人道主义,这是狄更斯从精神意识到情感心理的三个层面和渊源关系。这是一个有层次的“三位一体”。
对童真的崇尚,把儿童神圣化,既使狄更斯永久地依恋着自己的童年生活(从另一个角度讲又是自己的童年生活促使他崇尚童真并把儿童神圣化),又 使狄更斯深层精神——心理上成了永远长不大的“精神侏儒”,他的意识深处有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儿童情结”。这就使他的创作心理原型带上了儿童心理的特征。他总是用儿童的心理,用儿童的眼光去描写生活。正如安·莫洛亚所说的那样:“我们要记住,这些五光十色的景象是通过一个小孩的眼睛来观察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一个富于新鲜感的、变形的镜头来观察的……狄更斯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两重性特点:他见多识广,却又以儿童的眼光看事物。”⑦狄更斯的这种带有儿童精神——心理特征的心理原型在创作中的投射,就使他的小说在众多的现实主义作家中显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用童话模式反映现实生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飘浮在“真空”中的童话式人物。
童话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以超历史、超社会的面貌出现,他们没有具体的生活时代与背景,甚至也没有明确的国藉和生活地点。他们要么以“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座漂亮的王宫”的方式被介绍出来,要么以“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樵夫”的方式被介绍出来。在这种虚幻的环境中活动的人物形象,也失去了现实感。他们通常不是一个现实人物的性格实体,而是人类或民族群体的某种伦理观念或道德规范的抽象符号。因此,他们一般也不与具体的生存环境(其实在童话中,除了那虚幻的世界外也不存在具体的生存环境)发生冲突,而只是与某种对立的道德观念或伦理规范发生冲突,所以,这类人物形象是抽象化或道德化、伦理化了的。既然童话人物是超历史、超社会、抽象化了的,因而,他们的性格也往往是凝固化的,也说不上性格与环境的关系了。
狄更斯的小说所描写的社会环境当然是真实、具体而可信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客观实在的生存环境之中,这个生存环境是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社会现实的写照。然而,生活在这个生存环境中的人物却似乎有一种飘忽感。他们并不完全按照自己生存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的逻辑在生活,而是依照自身观念、自我意志和主观逻辑在生活,而环境倒是时时会合乎于他们的主观逻辑与意志的。所以,实际上这些人物是虚幻化和抽象化了,他们的性格自然也就凝固化了。《匹克威克外传》通过匹克威克俱乐部成员的漫游经历所反映出来的英国19世纪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与广阔性是为人称道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狄更斯在这部成名作中所显示出的现实主义功力。但是,这部小说中人物与故事的可信度是极低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物性格及人物的行动与环境之间缺乏内在联系,而且,作者在创作中几乎很少顾及这种联系。狄更斯差不多在设想出了匹克威克等人物之后,再把他们安置在那个天地里,就放心地让他们去东游西逛、笑话百出了。无论地点如何变化,无论时间如何向前推移,也无论这些人物怎样在不同的游历环境中受到挫折乃至吃尽苦头,他们永远一如既往,不变初衷。因此,时间与环境对这些人物的性格是不起作用的,时间与环境的迁移只是为他们提供演出闹剧的新场所;人物对时间与环境也丝毫不起影响作用。于是,他们就仿佛飘浮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飘浮在一个时间停止运转的世界里。这正是童话式的时空观和艺术境界。这位上了年纪的匹克威克始终代表着人的善良天性,他无论走到哪一个邪恶的世界里,永远不会改变这种既定的善良天性。他是一个永远快乐,永远只看到世界之光明的理想主义者,其实就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儿童”,或者说,他已返老还童,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讲,人越到老年,心理意识上越走向童年。这个“儿童”就是美与善的象征。因而,可以认为匹克威克是一个典型的童话式人物。
狄更斯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是颇为人称道的。与成人形象的塑造一样,这些儿童形象也是富有童话色彩的。在他的笔下,一个出身贫寒的儿童,天性善良,面对的是饥饿、贫困。还有恶人与他作对,就象童话中的正面主人公总要碰到女巫、妖魔的捉弄一样。这些不幸的儿童历经磨难,却秉性不移。他们总是一心向善,并永远保存着善良的天性。《奥列佛·退斯特》中的奥列佛、《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儿、《尼古拉斯·尼古贝尔》中的尼古拉斯、《艰难时世》中的西丝、《小杜丽》中的小杜丽、《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双城记》中的露西,等等。对这些人物,作者往往一开始就把他们安置在“善”的模型中,所以他们走到任何地方,经受任何磨难,都代表着善。在他们身上表达了作者对人性善的坚定信念与美好理想,正是这种信念与理想,使这些人物成了抽象观念的象征。大卫生性是善的,那么,不管是处在何种恶劣的环境中,也不管与什么样的恶人在一起,他始终保持着善的本性,永远是人性善的代表,他的性格几乎从童年到成年都是一贯不变的。特别突出的是小耐儿、西丝、小杜丽、露西等女性形象。她们几乎不是来自生活和存在于生活之中的人,而是从天上飘然而来的天使,是一群专事行善的精灵。她们是狄更斯在生活中失落的,而在心灵中永存的那个理想的女性。他总是沉缅于自己的想象与理想中追寻与塑造这类形象,所以,他笔下出现的也就是这么一种童话的境界与精灵似的女性形象。
同这些“善”的人物形象相对,狄更斯小说中常常又有一些代表“恶”的人物,这类“恶”的代表人物,也往往是观念的化身,他们的性格特征也不以环境与时间为转移。因而,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由于被抽象化以后,通常是善恶好坏分分明明。好人永远行善,坏人永远作恶。这正是童话人物的模式,也恰好合乎了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儿童的期待视野。
二、由悲到喜、善恶有报的童话式结构
童话所展示的生活本身是虚幻的,它借虚幻的情境表现道德的、伦理的观念,从而达到训喻的目的。在童话中,善恶两种势力斗争的结局其实一开始就已明确,但作者总要借助一段曲折的故事来最终阐明。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训喻的力量。既然结局总是善战胜恶,那么,这段曲折的故事也往往从善弱恶强开始,让代表善的人历尽磨难,最后证明善的力量的强大,善是会无条件克服和战胜恶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永远一片光明灿烂。童话也就形成了一种基本固定的结构模式:从“贫儿”到“王子”或者从“灰姑娘”到“王后”,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狄更斯当然不会自觉地用童话模式来建构小说的情节结构,然而他的经历、他的深层情感——心理却决定着他在不自觉中进入到了童话式的创作境界里。他看到现实的社会结构制约和扼杀了人类的天性,愚蠢和残酷的枷锁使人性扭曲,但他又相信人性在本质上是善的,它最终能摆脱重重羁绊从而完善起来。他对人性的这种信念是从不动摇的,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表现了狄更斯天性的善良。他就是以这种近乎儿童的天真去看这个世界的;因而总以为光明多于黑暗,光明总可取代黑暗。这正是永远长不大的狄更斯的天真可爱之处。然而正是狄更斯的这种精神——心理上的“长不大”,使他在人与社会的认识上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自己就象那位善良的匹克威克先生一样,认识不到时代的变迁,觉察不到他们以往遵循的思想、道德和宗教原则已经遭到破坏,觉察不到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日益趋向崩溃。与之相反,司汤达、巴尔扎克则已感觉到了由于时代的变迁所造成的人与社会的变化。“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很早就注意到了他们身边所发生的变化。现代小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的现代小说,哈代对英国的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原因只是由于作家以及社会中日益增多的人们开始对作为社会基础的宗教和哲学的信条产生了怀疑”。⑧当同时代的这些作家已经为“文化地震”的来临焦灼不安时,“长不大”的狄更斯怀着儿童的天真与浪漫,做着善必然战胜恶的童话式美梦。所以,他的小说结构也往往是童话结构模式的翻版。
狄更斯的小说情节通常是曲折多变的,但好人不管怎样遭难受辱,最终都有好结局,因而他的小说在深层结构上大都是由悲到喜,善恶有报的童话模式。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合乎狄更斯的乐观主义思维方式,也外化出了他儿童式的天真与浪漫。这种结构模式既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理想的体现,也是他儿童式心理原型投射的结果。
三、超现实逻辑与童话式的神奇
在童话中,不管善恶势力的冲突如何尖锐,也不管情节如何曲折离奇,由于正面主人公的命运总是取向于喜剧式的,故事的结局总是团圆式的。因而,在具体情节的描述中,作者往往抛开生活的现实逻辑,而以幻想式的超逻辑去推动故事情节朝着大团圆的“终点站”发展。因而,作者常常象巫师术一样,把各种人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还常常让超人的神力来为人物排忧解难,使情节朝着既定的方向推进。我们知道,童话的情节描述,常常带有神奇色彩。比如说,《灰姑娘》中的善良的女巫婆总是在灰姑娘需要她时一而再地出现,用她的神力瞒过灰姑娘的后母和众人,使她得以参加王子的舞会并结识王子,最后与王子成婚。《森林里的睡美人》中,作恶的女巫给美人带来了恶运,而另一位善良女巫用她的法术挽救了美人的灾难,让她只是受伤后酣睡了一百年。而正当一百年满之际,英俊的王子到来了,唯独他看到了睡着的美人。他的吻,解除了作恶女巫施加在她身上的魔力,使她苏醒了过来。王子也就得到了她的爱,从此他们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诸如此类的描写中,都运用了巧合手法,这种巧合是为了让故事情节导向既定目标而精心设计的,其中刀痕斧凿之迹十分明显,而这在儿童的心灵世界中却产生了神幻奇特的艺术效果。因为儿童的天性就是好幻想和追求新奇,他们往往不按照成人的逻辑与方法分析事物。童话中的超观念逻辑法则也正是儿童观察世界的逻辑法则。
在狄更斯小说中,众多的儿童形象所面临的那个世界常常是充满邪恶的。他们善良却总是那么弱小,他们的对立面常常是作恶的成年人,这无形中出现了童话中弱小的善良者与“巨人”、“怪兽”、“女巫”、“妖魔”相对抗的虚幻惊险恐怖的情境。比如,奥列佛在济贫院里遇到的凶恶的本布普和在伦敦遇到的盗窃头目费金,给尼古拉斯带来灾难的灭绝人性的叔叔,小耐儿身边的恶人奎鲁普,大卫的继父摩德斯通,把匹普作为捉弄与折磨的对象的哈维仙老小姐,等等。在狄更斯的小说世界中,这一系列不无邪恶的人物,都是给不幸的儿童们制造人生障碍的罪魁,他们身上拥有“巨魔”或“作恶女巫”的原型结构。这些善良弱小者总是想尽办法与凶狠而强大的“巨魔”或“女巫”展开斗争,他们的处境十分险恶,但又常常能巧遇外力的帮助从而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狄更斯作为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他所描写的“外力”,当然不会是童话中善良女巫之类的超自然力量,而是生活中体现善良与正义的人或事。不过,在描写这种善良与正义的人或事时,狄更斯的创作心理是儿童化了的。他为了让弱小者逢凶化吉,常常一味地从主观情感出发,近乎随心所欲地让一些人或事出现在小说中,从而改变主人公的命运,至于这样写是否符合生活的现实逻辑,他是不很在意的。对此类现象,安·莫洛亚说得很正确,“狄更斯对自己从事的文学创作中的真实性极其漠视,他随时都可以变更小说的线索”⑨,“每逢遇到难以处理的情节时,他就依靠简单的手法——巧合。”⑩失去双亲的奥列佛一直命运多舛,在遭到歹徒蒙克斯穷追不舍的危难之际,意外地遇到了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勃朗罗绅士,这位善良的绅士制服了蒙克斯,并从他口中得知奥列佛是蒙克斯父亲未婚时生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写下了将财产分给奥列佛和他母亲的遗嘱。于是,奥列佛成了大笔遗产的继承人。小杜丽在备受蒙难、毫无希望之际,意外地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一夜间成了巨富。为了解除匹普的危难,狄更斯让一直在捉弄匹普的“女巫”式人物哈维仙老小姐在一次偶然的大火中自焚而死。11年后,匹普从国外回来时,恰好在哈维仙老小姐旧居的那片废墟上与他早年一直追求的艾泰拉重逢。《双城记》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它照样有此类神来之笔。在监狱中度过了18年的精神病人梅奈特医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他18年前在巴士底狱写的控告信正好落到了当年被他目睹的被害者的军人德伐石夫妇手中,并且信中要控告的恰恰是她女儿露茜的丈夫代尔那;当代尔那即将被送上断头台时,一直爱慕着露茜而外貌酷似代尔那的卡尔登,以梨代桃走上了断头台。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被认为是狄更斯小说中“第一次摆脱了那种必不可少的夸张虚构”的作品,“在这部书中他几乎完全满足于对真实性很强的种种事件的描绘。”(11)然而,这部小说也照样以童话式手法来表现作者的自身经历。大卫在危难中找到了姨婆;在旅行中巧遇青年时代的同学斯提福;天真的爱弥丽被斯提福诱骗,遭抛弃后几乎九死一生,流浪途中巧遇善良的渔妇从而得救;经受挫折后的爱弥丽回心转意,向忠心地爱着她的海姆忏悔,并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宽恕。而此时海姆却在海上遭受风雨袭击之际为了救一个遇险的难民而殉身,他和他所要救的人的尸体,双双漂到了正给他送信的大卫的脚下,海姆所要救的人正是骗走他的意中人的那个斯提福。诸如此类的描写,从表现技巧上看,正是安·莫洛亚所说的“百年的巧合”,而由于“巧合”频繁出现,因而人们常责怪狄更斯小说不真实。然而,这类描写却实实在在是狄更斯的风格。显然,更主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技巧上巧合手法的运用问题,还体现了狄更斯始终一贯的创作心态与审美心理。如果从思想内容上看,这类离奇的人物与事件描写,是表达了乐观浪漫的人道主义者狄更斯的善恶有报的观念,而在创作心理上看,驱动狄更斯进行此种描写的正是他那儿童式的情感与心理。狄更斯自己就象一个亲切地期待着出现奇遇,使弱小者获救的儿童,因而他在小说中创造“奇遇”,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审美需求,也正合乎自己的期待视野,正象阅读《森林中的睡美人》的儿童从睡美人的复活中满足了好奇心也实现了审美期待一样。所以,从深层意义上看,狄更斯小说中的“百年的巧合”甚至“不真实”,实际上蕴涵了儿童认识世界的那种超现实逻辑,因而,他的小说的情节描述与其说是背离生活真实的“牵强附会”,不如说是童话式的神奇风格的体现。谁能要求一个童话作家在创作时必然在生活的现实逻辑上亦步亦趋呢?谁又能因为一个童话故事的神奇性而指责它“不真实”呢?而狄更斯恰恰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出色的“童话”作家。
从狄更斯小说中存在的童话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说的艺术世界,是经由他那带有儿童心理特征的主体心理原型过滤和变形了的19世纪英国社会,其中的主观表现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狄更斯是用儿童的心理和童话模式去表现现实生活的。这种创作模式的优与劣我们姑且不论,不过,从狄更斯当时在读者中所享有的声誉和以后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所拥有的地位看,他的小说创作是成功的。而且,狄更斯小说的这种童话模式正是他的小说风格的本质特征之一。对此,我们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扫瞄器”就出现了一个“视觉盲点”。狄更斯小说的这一风格特点因其具有“非现实主义”之嫌而难以被认可。如果狄更斯这样一个被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的本质特征被看成是“非现实主义”的话,那么,是否我们那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过于狭隘或排他性太严重了呢?
注释:
①赵景深:《童话学》,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4页。
②③[英]奥伦·格兰特:《狄更斯引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英文版,第92页。
④⑤⑥同上,第95,35,95页。
⑦[法]安·莫洛亚:《狄更斯评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⑧[英]雷克斯·华纳《谈狄更斯》,见《狄更斯评论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⑨⑩(11)[法]安·莫洛亚:《狄更斯评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8、81、49页。
标签:狄更斯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艺术论文; 环境描写论文; 人性论文; 女巫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