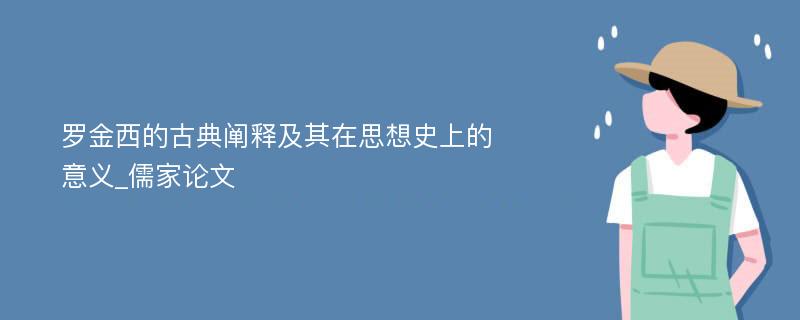
罗近溪的经典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就“克己复礼”的诠释而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己复礼论文,思想史论文,意义论文,经典论文,而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5-0072-008
引子:十多年前的一场争论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儒学家——何炳棣和杜维明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儒家经典诠释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克己复礼”中的“克己”一词应释作“修身”还是应释作“‘克制自己’的欲望”?前者为杜氏的观点,后者则是何氏的观点。① 何氏认为“修身”一词虽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涵义,“但修养或修身在中英文里的主要意涵则是倾向于积极方面的”,他以各种史料记载为据,从而断言:“克己”的“‘克’字,一定非是‘约也、抑也’不可,决不能作其他解释。”对此,杜氏一方面表示并不完全反对何氏的这一见解,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孔子这一观念不是意指人应竭力消灭自己的物欲,相反,它意味着人应在伦理道德的脉络内使欲望获得满足。事实上,‘克己’这个概念与‘修身’的概念密切相接,它们在实践上是等同的。”② 要之,在杜氏看来,“克己”作为一种修身工夫,未必如后儒所理解的那样,只是涵指“克去己私”。
本文无意回到何、杜两人之争论的是非纠缠当中,本文旨在指出,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虽然须以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文字涵义为基础,但在根本上又不同于经学考据的文字训诂,经典诠释应当更为注重思想义理的内在脉络,否则经典解释就有可能蜕变成一种“饾饤”之学。若从哲学而非纯史学的立场出发,基于儒学的精神方向在于“为己之学”③ 这一观念立场,故而从“克己复礼”的命题中完全可以阐发出“修身”的积极意义,而这一解释也无疑是符合儒学思想之精神的。我们从16世纪以降明代心学的思想发展中可以发现,在“克己复礼”的问题上出现了几乎是颠覆性的重新解释,而且这一解释与清初的一些所谓反理学的思想家或考据学家(如颜元、戴震等)亦有某种趋于一致的现象,尽管后者的思想立场与明代心学大异其趣。我认为,对于经典文本的创造诠释,乃是思想家与文本的对话之结果,通过对经典文本中某些传统观念的诠释转换,不仅文本的思想意义是可以被重新发现的,而且对于哲学家来说也是建构其思想言说的必要方法。
一、三种解释方案
《论语》中有关“克己复礼”的一段记载是这样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
在汉代经学的训诂传统中,“克”被释为“约”,意谓约束;“己”被释为“身”,意谓自身。魏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马融注:“克己,约身。”宋邢昺疏曰:“克,约也;己,身也;复,反也。言能约身反礼,则为仁矣。”可以说,上述解释是宋以前的主流见解,其中“克己”并没有“克去己私”的确切涵义,更没有将“复礼”解释为“复返天理”之意。邢昺还引用了隋儒刘炫之说:“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1—p2502] 刘炫此说可谓开创了宋儒释“克己”为“克去己私”之先河。
及至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亦即以“私欲”来解释“己”字。譬如,程颢云:“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2—p18] 朱熹云:“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3—p131]“克己复礼,去其私而已矣。”[4—p2453] 朱熹的这一解释具有典范意义,也代表了宋代理学家的一般看法,甚至到了明代仍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即便是王阳明,亦以克去己私来理解“克己”,如:“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5]“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5] 阳明的这一观点与其在理欲问题上也坚持“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立场有关。事实上,在宋明理学的观念体系中,“克己复礼”与理欲问题有关,理—欲的对立紧张正可用克己—复礼的对应关系来加以理解和诠释,克去己私才能恢复天理的解释思路也正印合了去得一份人欲便是存得一份天理的理学观念。用朱熹的说法,亦即“私欲净尽,天理流行”[3—p132]。
然而对于阳明来说,良知即“真己”这一良知观念是其整个心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由此立场出发,便有可能导致对“己”字的重新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到了阳明后学的时代,关于“克己复礼”就逐渐形成了第三种新的解释。除了后面将要集中讨论的罗汝芳(号近溪,1515—1588)以外,阳明弟子王畿(号龙溪,1498—1583)、邹守益(号东廓,1492—1562)以及泰州学派的王襞(号东厓,1511—1587)、王栋(号一庵,1503—1581),都在“克己”问题上对汉儒以及宋儒的传统解释提出了质疑。龙溪指出:
“克”是修治之义,“克己”犹云“修己”,未可即以“己”为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义。(《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六《格物问答原旨》)④
这里将“克己”解释为“修己”,意同“修身”。龙溪的思路是:不能将“克己复礼”与“为仁由己”的两个“己”字拆开来看;由后一“己”字可以推出前一“己”字不能与“欲”划上等号;既然“己”非私欲之意,那么“克己”的“克”字也就未必是克制之意,而应当理解为具有积极意义的“修养”之意。东廓亦云:
“克己复礼”,即“修己以敬”。……历稽古训,曰“为己”,曰“正己”,曰“求诸己”,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未有以“己”为私欲者。“问仁”本章,三言“己”字,曰“为仁由己”,正指“己”为用力处。在《易》复卦,以“不远复”颜氏子,而《象》之辞曰“以修身”,则修身之为克己,自是明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七《论克己复礼章》)
这里东廓根据各种经典文本的记载,明确指出“克己”应理解为“修身”,而反对“以己为私欲”的解释,此与上述龙溪之意基本相同。虽然在阳明后学中,王、邹两人的为学主张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两人之所以在“克己”问题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其因在于两人对于良知即“真己”的心学理念坚信不疑。对于他们来说,良知是构成“己”的本质,因此“己”非“一己私欲”之解释所能涵盖,这应当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共识。可以说,“未可即以‘己’为欲”以及“未有以‘己’为私欲者”的见解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心学立场所推出的必然结论。
王、邹的上述见解在阳明后学中决非是偶然现象。根据耿定向(号天台,1524—1596)的记载,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号心斋,1483—1541)之子王襞“释‘克己’即‘能己’,以天地万物依己,不以己依天地万物”,耿天台称这一见解“盖承传乃父立本旨也”,意谓王襞的观点乃是继承了王艮的思想旨意。天台进而指出:“即察王君(按,指王襞)当下心神真能承服父学,欲以其学通吾侪,别无一纤尘襟,便是能立己。吾侪当下心神惟是求学,更无些子势位在胞中作障,便是克己。”(《耿天台先生全书》卷八《观生纪》)可以看出,将“克己”释作“能己”或“立己”这一对“克己复礼”的重新诠释在泰州学派的思想传承过程中已然形成了一种重要特色。另一位心斋弟子王栋更是明确地指出“克己即修己以敬”、“克己之非去私”,其云:
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而先儒莫不从此进修,只缘解“克己”为“克去己私”,遂漫衍分疏,而有“去人欲”、“遏邪念”、“绝私意”、“审恶几”以及“省察防检”纷纷之说,而学者用功,始不胜其繁且难矣。然而夫子所谓“克己”,本即“为仁由己”之“己”,即谓“身”也,而非身之私欲也。“克”者,力胜之辞,谓自胜也。有敬慎修治而不懈怠之义。《易》所谓“自强不息”,是也。……故乾以自强言之,示天下以法天之学也。告颜子而以“克己”言之,示颜子以体乾之道也。(《重镌一庵王先生遗集》卷上《会语正集》)
王栋在这里触及到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宋代以来理学家所竭力主张的“去人欲”这一思想口号能否从《论语》有关“克己”的观念叙述中得到理论上的支持?王栋的结论是否定的。其理由是:“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而“先儒莫不”从“察私防欲”一路作实践功夫乃是误解了“克己”的真正涵义,孔子所说的“克己”决不能作为“察私防欲”的理论依据。此处所谓“先儒”虽没有指名道姓,然从其下文所列“去人欲”、“遏私意”等主张来看,所谓“先儒”显然是指程朱一系的思想人物。
至此我们有理由说,将“克己”释作“修己”、“能己”、“立己”,反对以“克己”作为“察防私欲”的依据,这些观点主要是针对程朱理学而发。而在阳明后学当中,对此问题有更为全面的理论阐述,则莫过于罗近溪。
二、“原宪宗旨”与“孔颜宗旨”
罗近溪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他在拜师颜均(号山农,1504—1596)之前,也深信“克去己私,复还天理”这一朱熹理学以来的传统观念,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制欲”才能实现“体仁”[6—p266]。对此,山农给予了当头一棒,提出了“制欲非体仁”⑤ 这一著名命题。通过山农的指点,近溪终于意识到“体仁”方法并不在于“制欲”,相反“体仁”本身直接意味着“制欲”的达成。也就是说,“体仁”与“制欲”原本不构成紧张对立之关系,“制欲”不是“体仁”的前提,相反“体仁”才是首要工夫,故云:“人能体仁,则欲自制。”[7—p249] 事实上,在近溪思想的成熟形态中,“体仁”与“制欲”已经完成了根本的转化。此一转化虽与山农的指点有关,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近溪自身对“克己”问题的重新理解和诠释。
先来看一段近溪有关“克己”问题的论述:
《传》(指《传习录》)曰:“太阳一照,魍魉潜消。”是矣。若云“克去己私”,是原宪宗旨,不是孔颜宗旨。盖孔子求仁,其直接名仁,惟曰:“仁者人也。”夫“己”非所谓“仁”耶?[7—p249]
这段话的前面两句,稍后再议,其后面一句是说,“克己”的“己”字,就是“仁者人也”的“人”字,既然“人”就是“仁”,难道“己”不是“仁”吗?近溪对“克己”的重新解释,实起因于这一根本疑问。按近溪之意,己即人,仁即人,因此“克己”不能理解为是对“己”的克制。由对“己”的重新解释,必然涉及到对“克”字的理解问题。按传统的训释,“克”谓“胜”,故“克己”意味着战胜自己,其前提是“己”乃是应当被战胜的对象。然而按照近溪的疑问,若说“己”只是“私欲”的代名词,是必须禁绝的对象,那么“人”的存在难道就是如此的一无是处吗?若以孟子对“仁”字的解说为准,仁即人,人即己,那么,“己”又怎么能被视为战而胜之的对象?故此“克”必非“胜”字之意,“己”必非“私欲”之表征。那么又应如何解释呢?在披露近溪的答案之前,再来看上述引文中的前面两句。
首先是阳明的一句话:“太阳一照,魍魉潜消。”(《王阳明全集》卷五《与杨仕鸣·辛巳》)“太阳”是喻指良知本体。这一比喻是说:良知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太阳”,“良知之明”犹如太阳的光芒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照耀人心,使得人心中的魑魅魍魉无所逃遁。也就是说,良知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近溪将这一比喻用在讨论“克己复礼”的场合,其意在于指出:我们必须充分相信自己心中原有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果以为只有“克去己私”才能“恢复天理”,则在为学方向上已然有错,未免与“自信本心”发生偏离。应当指出,近溪通过上述比喻所欲阐明的观点是符合阳明心学的基本精神的。阳明通过对“良知即天理”、良知“无所不在”等观念的强调,肯定了良知心体的绝对地位,天理并不构成与人心的对立紧张,而是内在于人心中的、“当下即是”的本质存在。因此,人心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决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能动的。尽管人心亦会有私欲,但这只是人心的一种遮蔽状态,人们只要顺其心中的一点良知发动,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和扭转这种遮蔽的、非本质的状态。要之,人之本心是可以信赖的。由这一信念出发,人们就应该对自己抱有积极的、自信的态度。近溪正是基于这一良知心学的立场,认为既然“自己”不再是消极的存在,既然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那么从根本上说,“己”就不应该是被克制的对象。可以说,近溪对“克己”作出重新诠释的根据就在于此。
接下来一句:“若云克去己私,是原宪宗旨,不是孔颜宗旨。”这是近溪的独到见解。所谓“孔颜”,是指孔子和颜渊。但为何说“克去己私”之解释并不符合孔颜宗旨呢?要解答这一问题,须先解释何谓“原宪宗旨”。原宪是孔子弟子,即原思,名宪。《论语》中有《宪问》一篇,为原宪所记,其第二章云:
(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3—p149]
原宪是问:如能克制住“克、伐、怨、欲”这四种心态意识,“使不得行”,是否可以称得上做到了“仁”呢?所谓“克、伐、怨、欲”,按朱熹的解释,分别是指:“好胜”、“自矜”、“忿恨”、“贪欲”。对于原宪的问题,孔子答以“为难矣”、“吾不知”,意谓若要真正做到克制“四者”,使其不行,这是很困难的,即便做到了,是否就意味着“仁”的实现,也是我所不知道的。显然孔子所表明的是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对于孔子的这一表态,朱熹有一个解释:“仁则天理浑然,自无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3—p149] 并引程子之说,指出:
人而无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难也。谓之仁则未也。此圣人开示之深。
克去己私以复乎礼,则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则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潜藏隐伏于胸中也。岂克己求仁之谓哉?[3—p149]
可见,如何消除“克、伐、怨、欲”实与“克己复礼为仁”的问题有关。按程朱的看法,“克己复礼”与克制“克、伐、怨、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克去己私”意味着恢复天理,而克制“克、伐、怨、欲”,令其不行,却未免留有“病根”,犹如治病,只治标而未治本,故不为孔子所许。这是程朱对所谓“原宪宗旨”的一种理解。
须指出的是,在《论语》有关“问仁”的众多记录中,“原宪问仁”和“颜渊问仁”具有典型的意义。对于颜渊问仁,孔子从正面答以“克己复礼为仁”,而对于原宪问仁,孔子却在不置可否的语气中表露了否定的态度。这就是近溪所理解的“原宪宗旨”和“孔颜宗旨”之别。这一理解应当亦为程朱所认同。但是,近溪却将“克去己私”对应于“克己复礼”的解释思路等同于“原宪宗旨”,则不得不说这是近溪之创见。近溪显然对于原宪的“克”、“欲”两字有特别的关注,在他看来,此二字正可与“克去己私”相对应。因此如果将“克己”理解为“克去己私”,就等同于原宪将“为仁”理解为克制“克、伐、怨、欲”。这就是近溪为何判定“克去己私”是原宪宗旨而非孔颜宗旨的原因。
再从第二句联系到第三句来看,近溪的思路终于明了:“克去己私”不能合理解释“仁者人也”。本来,这两句命题并不构成解释关系,但是近溪将诠释视角经过转换之后,却令人发现:“克去己私”实质上乃是“原宪问仁”的思路,所谓克制“克、伐、怨、欲”,无非就是“克去己私”之意。由于原宪之说不为孔子所许,所以孔子回答颜渊问仁时所说的“克己”也就必定不是“克去己私”之意。更为重要的是,在近溪看来,孔子以“仁者人也”来“直接名仁”,难道“克己”的“己”不是“人”?不是“仁”吗?这就是“夫‘己’非所谓‘仁’耶?”这一提问方式的真实涵义之所在。至此,我们终于了解到近溪对“克己”的重新解释与他所欲确立的人即己、己即人,人即仁、己即仁这一仁学思想有关。正是基于这一思想立场,所以“己”绝非是恶的表征、克治的对象。⑥
可以说,近溪从“仁”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克己”,这是他在“克己”问题上的一个独特的诠释视角,同时也与他坚持认为“求仁”是孔孟宗旨这一对孔孟儒学的总体理解有关。事实上,近溪对“克己”的解释,是建立在他对《论语》文本乃至孔孟宗旨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反过来,通过对“克己”的重新解释,近溪认为可以了解到“求仁”为何是孔孟宗旨的理由。这里显然存在着“解释学的循环”:由对文本中字句词义的了解,进而通观全书旨意;由对全书旨意的把握,进而判定字句词义的确切意涵。就近溪而言,“克己”一词如何与“求仁”宗旨加以整合,这是他的“哲学解释学”的一个立场。
三、“克己复礼”为“能己复礼”
行文至此,应把近溪对“克己”的解释答案告诉大家:“克”为“能”,“克己”为“能己”。其前提则是:“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这里先来看一段对话(分段录出):
问:“‘克己复礼’,以‘克’作‘能’,不识‘克伐怨欲’,‘克’字如何又专作‘胜’也?”
曰:“回之与宪,均称孔门高弟,亦均意在求仁,但途径却分两样。今若要作解释,则‘克’字似当一样看,皆是‘能’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体与天通,而用与物杂。总是生之而不容已,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观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灵不测,可爱莫甚焉。不善观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纷扰不胜,可厌莫甚焉。然见心为可爱者,则古今人无一二,而心为可厌者,则古今十百千万,而人人皆然矣。……”
“无奈及门之徒,亦往往互相抵牾,惟颜子于其言语无所不悦,故来问仁,即告以‘能己复礼,则天下归仁’。能复,即其生生所由来;归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原宪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滞于行迹,自思心之不仁,只为怨欲二端纷扰作祟。于是,尽力斩伐,已到二端俱不敢行去处,乃欣欣相问:‘人能伐治怨欲到得不行,仁将不庶几乎?’吾夫子闻知此语,颇觉伤残,漫付之一叹,曰:‘可以为难矣。’盖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岂是容易?至说‘仁则吾不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辞,亦深致惜之之意。宪竟付之不问,岂是其心犹疑圣言之不如己见也耶!”[6—p279~280]
这段对话记录于近溪逝世前二年,反映了近溪最晚年的思想。首先,近溪指出颜渊问仁和原宪问仁时出现的两个“克”字都是“能”字之意,进而近溪以孟子的“仁,人心也”这一命题作为依据,强调指出:人心具有“生生不容已”的根本特征。因其生生不容已,故而心与天能互为感通。若对此有一根本之了解,那么即便说“心即是天”,也未尝不可,由此则可以说人心“可爱莫甚焉”;反之,则会以为“心即是物”,落入纷扰世界之中,由此见人心便会“不胜可厌焉”。这是说,为什么“克”为“能”字之意,乃是因为“克己”的“己”字就是“仁”、“人”、“心”的涵义,仁就是人心,人心原与天通,生生不已,“可爱”至极!因此,“克己”的“己”字绝对不应是克制的对象,同时,“克”字也应当作相应的解释转换,结论就是:“克”为“能”字之意。如此则能在义理上与孔孟的仁学宗旨疏通无碍。后一段讲了孔子为何“以仁为宗”的道理,也是从“生生不已”的角度讲起,并将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径直改作“能己复礼,天下归仁”。按照近溪的理解:“能复”的依据就是生生之仁,“归仁”就是生生之仁的结果。因此《论语》文本中的“克”字甚至可以由“能”字来取代。
那么,何谓“能”?其实此所谓“能”与“能够”、“可能”等意接近,只是在近溪的场合,当主要是指人心的道德能力或心体的作用能量。关于这一点,我们透过他对陆象山的一个观点的引用,可以获得基本的了解:“象山解‘克己复礼’,‘能以身复乎礼’。似得孔子当时口气。”[8—p61] ⑦ 可见,“能己”即“能以身”之意,亦即“可能”或“能力”之意。只是从心学的语境来看,所谓自己的能力,当是指心体的能力、良知的能力。
那么,释“克”为“能”,有没有经典诠释史上的依据呢?有人曾向近溪提问:“‘克去己私’,汉儒皆作此训,今遽不从,何也?”这里所谓“汉儒”,严格而言,应是指马融和王肃之流。其实,在《论语》的解释史上,以“约身”释“克己”,创自马融,而“训己为私”则滥觞于王肃。⑧ 对此提问,近溪答道:
亦知其训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己私”?《大学》“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耶?况“克”字正解,只是作“胜”、作“能”,未尝作“去”。今细玩《易》谓“中行独复”、“复以自知”,浑然是“己”之能与胜处,难说《论语》所言,不与《易经》相通也[8—p62]。
依《大学》文本,其引《尚书》中的《康诰》“克明德”,《大甲》“顾諟天之明命”以及《帝典》“克明峻德”,重在揭示“明”字的意义,而非“克”字的意义。⑨ 对于这三句话,两个“克”字,郑玄注曰:“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孔颖达疏曰:“能明己之德。”“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10—p1674] 可见,释“克”为“能”,“克明”意谓“自明”、“能明”,这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以来的注解。近溪以为找到了有力证据,但是“克明”能否转换成“克己”?换言之,“克己”与“克明”的“克”字能否互相诠释?严格来说,是颇成问题的。当然,我们也惟有从“哲学解释学”而不是从传统经学的立场出发,才能对近溪的上述解释获得某种同情之了解。对近溪来说,“克,能也”这一古训已足以支持他的哲学理解:“克己”绝非“克去己私”之意,而应当是指“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以达到复礼的目标”。结论就是:“克己复礼”应当理解为“能己复礼”。
然而近溪在反复重申上述观点的时候,却忽略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这条资料也是何炳棣用来批评杜维明的有力证据之一,亦即《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记载。据载,楚灵王在位十二年,以弑君自立开始,他凭借先王积累的雄厚国力,推行侵略扩张、兼并掠夺的强权政策,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却以兵败,自缢于乾溪而告终。后来孔子引用“古志”的史官文献,对此作了总结:
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可以看出,《左传》的这段记载有一清楚的历史场景,孔子针对楚灵王的不断扩张的私欲,引用了“古志”中的“克己复礼,仁也”这句话,旨在指出楚灵王没有做到克制“己私”,否则就不会发生“辱于乾溪”的悲剧。⑩ 据此,我们可以容易地了解到“克己复礼”的原初涵义与宋代理学家所理解的“克去己私”的解读大致吻合。由于《论语》“颜渊问仁”缺乏具体的场景设定,所以导致了后人在诠释上的种种可能。然而也必须指出,孔子利用“古志”之言所下的判定,与他自己后来向颜渊所揭示的“克己复礼”的道理,在内涵上未必是完全一致而无义理上的重新拓展。在我看来,孔子之说虽本诸“古志”,然而针对颜渊而说的“克己复礼”与针对楚灵王而说的“克己复礼”,由于对象以及场景的不同,完全可能导致思想内涵上的某些差异。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溪对“克己”的解释是以孔孟的“为仁由己”、“仁者人也”、“仁,人心也”等仁学宗旨为根本依据的;由此出发,进而推论出仁即人、人即己、己即仁等一套观念;在此基础上,近溪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推翻有关“克己”的传统诠释(特别是宋儒程朱一系),不能将“己”视作“恶”、视作“人欲”;通过对“克己”的重新诠释,近溪主张应当积极开发自己的潜能、充分发挥人心的能力,由“能身”进而“体仁”,如此便能真正实现“复礼”。近溪指出:
今有将“克己”“己”字必欲守定旧解,殊不知认“己”字一错,则遍地荆榛,令人何处安身而立命也?[7—p249]
大约孔门宗旨,专在求仁,而直指体仁学脉,只说“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决难语“仁”。故“为仁由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声声只说个“性善”。今以“己私”来对“性善”,可能合否?此处是孔颜孟三夫子生死关头,亦是百千万世人的生死关头,故不得不冒昧陈说[8—p63~64]。
可见,在近溪看来,若于“己”字认错,则令人无处“安身立命”,而“即人而仁”之观念实是孔孟的“生死关头”,也是世人的“生死关头”。近溪之所以要推翻“克己”的传统解释,其思想原因即在于此。
必须指出,在程朱理学的有关“克己复礼”的那套解释思路中,其关节点在于“己”或“身”都被看作是应当否定的消极的存在对象,是私欲的根源所在。这种解释思路反映了理学的一种价值观念。当然,与汉代经学家注重字意而忽略义理这一诠释路数不同,当宋代理学家将“克己”解释成“克去己私”的时候,其中已经注入了某种价值判断。而近溪对“克己”所作出的几乎是“颠覆性”的重新解释,与其说是针对汉儒,还不如说是针对宋儒。从经典解释学的角度看,近溪将“克己”释作“能己”,是其主张“得口气”(《一贯编·孟子下》)这一解释学方法的一个典型案例,然而从哲学史的角度看,通过这一诠释转换,近溪确立了这样一个思想信念:“人”、“己”、“身”不再是消极的存在对象,而应当是有正面价值的、有充分潜能的、“即人而仁”的、以仁体为自身之本质的主体性存在,所以人们应该重视自身的能力,重视“为仁由己”而不由乎人这一主体能动的力量。应当说,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提出,对于打破宋代理学以来对人心、人身的歧视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近溪思想不无批评的明末大儒刘宗周从“人心本无恶”的立场出发,肯定了晚明出现的有关“克己”问题的新解释,指出:“人心本无恶。近儒解‘克己’,不以‘去私’言,亦是。”[11] 事实上,围绕“克己”问题的新解释,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留下了不少的痕迹,我们可以从陈确、颜元、李塨、戴震等人的著述中看到不少与近溪相似乃至一致的观点(尽管他们大都未提及近溪)(11),这显示出明清之际的思想发展既有重大转向又有一定关联,同时也表明以批判宋明理学为己任的一些清代儒家学者,在有关儒家经典的解释方面,却有可能与心学的某些观念表述趋于一致,这一儒家经典诠释史上的历史现象及其所内涵的思想意义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12)
注释:
①分别见杜维明:《“仁”与“礼”之间的创造性张力》(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全集》卷四《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文集》所收,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14~24页。原为英文,载《东西方哲学》第18卷,1968年);何炳棣:《“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载香港《二十一世纪》第8期,1991年12月。
②杜维明:《从既惊讶又荣幸到迷惑而费解——写在敬答何炳棣教授之前》,载香港《二十一世纪》第8期,1991年12月。第148~150页。按,关于这场争论的经过及其所反映的问题,可参见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研究》附录一《杜维明研究述评》(2)“‘克己复礼真诠’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10~322页;郑永健:《“克己复礼”的争论》(载香港人文哲学会网站)。据郑文统计,前后共有九篇文章参与了这场论战。
③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篇》)按杜维明的理解,此所谓“为己”即指以修身为本的“为己”之学,而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伦理提倡社会优先于个人的见解显然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误读(杜维明:《学做人:从朱熹、王阳明到刘宗周的精神性践履》,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三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12月,第65页)。
④另可参见同上书卷三《书累语简端录》、卷五《竹堂会语》。
⑤这句话仅见于近溪方面的记录,参见《会语续录》卷上(《近溪子集》本)、《盱坛直诠》卷下。
⑥值得注意的是,李颙用近溪与山农的“制欲体仁”之辩来解释“原宪问仁”,指出原宪所说正是“制欲”,而近溪在山农的指点下所获得的了悟,才是真正的“识仁”(《二曲集》卷三十九《四书反身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92—493页)。
⑦按,经查《陆九渊集》,未查实象山语之出处。不过,在《陆九渊集》中,象山有关“克己复礼”的阐述几乎俯拾皆是,这里仅举一例:“以颜子之贤,虽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声色货利之累,忿狠纵肆之失。夫子答其(按,指颜渊)问仁,乃有‘克己复礼’之说,所谓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见之过恶,而后为己私也,己之未克,虽自命以仁义道德,自期以可至圣贤之地者,皆其私也。”(卷一《与胡季随·二》)从中可见,象山所理解的“己私”并不等同于“声色货利”以及“常人所见之过恶”,凡是“着意”追求都属“己私”。对此,朱熹曾严厉批评象山释“己私”为“失其本心”,故“克治”对象便是“思索讲习”而非“忿欲”,其结果必将导致“忿欲纷起,恣意猖獗”,均可视作“不妨者也”(参见《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第2973页)。由此可见,基于象山对“己私”的解释,极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程朱理学的诠释方向,导致对“克己”问题的全新理解。
⑧参见清惠士奇:《礼说》。关于汉儒对“克己复礼”的种种解释,详见参考文献[9]第817~821页。顺便指出,清代考据学家大多反对马融、王肃的上述解释,然对于近溪的“能身复礼”说却未见提及。例如,晚清经学家俞樾《群经平议》亦以“能身复礼”释“克己复礼”,且以为“己复礼”三字当是“连文”,应读作“身复礼”[9—p817]。
⑨按,《大学》于引文后有“皆自明也”一句。朱子释曰:“皆言白明己德之意。”(《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⑩关于这段史实的解读,可参见余敦康:《春秋思想史论》下篇,载《新哲学》第二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58~59页。
(11)可分别参见《颜元集》上册《四书正误》卷四,《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
(12)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已有详考,参见《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283~3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