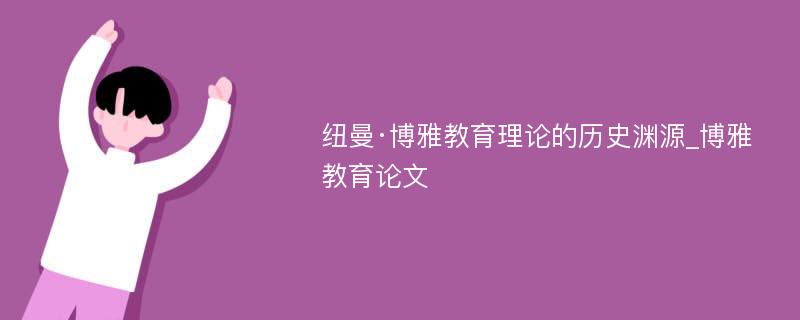
纽曼博雅教育学说的历史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雅论文,学说论文,纽曼论文,历史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6-0032-06
许多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对某一思想的渊源及其影响兴味甚浓,如有克里斯蒂勒对“文艺复兴思想及其渊源”的研究[1]、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对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的研究[2]等。纽曼的大学理念论述及其博雅教育学说也受到我国研究界的广泛关注[3],有论者注意到了赫钦斯与纽曼教育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与契合性[4],不过,纽曼的博雅教育思想的历史渊源问题,目前尚未看到相关的研究。而在纽曼看来,任何深刻的思想都必须建立在与传统对峙的基础之上,那些忽视传统、自铸新词的学说也许能风靡一时,但注定无法传之久远。在《大学的理念》一书的序言中,纽曼直率地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无任何“创新之处”[5]。这固然是纽曼的自谦之词,但也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纽曼的教育思想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理论学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之间,西方有大量关于博雅教育的论述。我们不禁要问,在纽曼的博雅教育学说当中,哪些部分源自前人,哪些部分是创新性的发展。
《大学的理念》是在演讲词的基础上成书的,就形式而言,该书是典型的“对话性文本”,它体现出纽曼与传统的对话。在这场精神对话中,纽曼向他的精神导师们——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基督教教父们——表达敬意,并向自己的思想对手们——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智者派、洛克、霍布斯、《爱丁堡评论》派、吉本、沙夫兹伯里伯爵(Shaftesbury,1671-1713)——发起攻击。笔者将以时代为顺序,对纽曼与前人之间的思想勾连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一、博雅教育理论的两重渊源与纽曼的立场
雅典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也是博雅教育理论的发源地。纽曼对雅典文明充满景仰,称赞雅典人是“天生的教师”,“仅仅生活在他们中间就是心智的培育”[6]。对古希腊的作家,纽曼提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伊索克拉底、智者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
博雅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布鲁斯·金博尔(Bruce Kimball)在其经典著作《雄辩家与哲学家:博雅教育思想史》(Orators & Philosophers: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Liberal Education)一书中指出,博雅教育思想史存在哲学家和雄辩家两条路线,前者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肇端,强调为真理而真理的探究精神和批判性的怀疑主义,课程侧重数学、逻辑与哲学;后者由伊索克拉底所肇端,强调通过经典文本的研读来培养引领社会的公民,在认识论上崇尚教条主义。[7]
然而,根据这一路线划分,纽曼很难被简单地归入其中任何一方。在布鲁斯·金博尔看来,纽曼“在这两个传统之间摇摆不定,他是一个试图打扮成哲学家的雄辩家”[8]。金博尔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在课程上,纽曼侧重古典文学,继承的是雄辩家的传统;而在理念上,则更为推崇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哲学家传统。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被布鲁斯·金博尔推为雄辩家式博雅教育思想之父的伊索克拉底,纽曼认为他和智者派乃一丘之貉,这两者都“为言辞所束缚,忽略思想或事物”,并表示“我无法为他们辩护”[9]。所谓的哲学家与雄辩家之争,诗歌与哲学之争,在纽曼看来并非如此壁垒分明,“我们有时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著作看成是哲学作品,有时则看成是文学作品”[10]。与此同时,对于开启哲学传统的苏格拉底,纽曼却颇为不敬,认为苏格拉底和塞涅卡一样,应该“被剥掉那件美丽的圣日外衣”。纽曼反对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命题,坚持“知识是一回事,美德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以理智教育为核心的博雅教育只能培养有教养的绅士,而无法培养具备纯正德性的“好人”。
《大学的理念》一书引证最多、最为倚重的古典作家是哲学家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纽曼尊亚里士多德为“古代的伟大哲学家”[11],“分析型的哲学家中最伟大者”[12],“古代最博学的知识分子”[13]。在《赞同的文法》一书中,纽曼甚至直呼亚里士多德为“我的导师”[14]。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纽曼在荣誉学位考试中所选的书目就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他对这本书非常熟稔,并做过详细的评注。纽曼还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做过评注,但对其诗学观点也颇多批评,认为亚里士多德过分重视情节在悲剧中的地位。
纽曼的博雅教育思想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纽曼指出,博雅教育、博雅知识的理念独立于基督教的教义,尽管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异教徒,但是在博雅教育理论方面,他永远是一个权威,是值得信赖的贤者:“只要我们还是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因为这位伟大的导师的确分析了人类的思想、情感、观点与见解。”[15]
《大学的理念》一书处处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论述。例如在描绘理智的完美状态时,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的一个独特的希腊词τετραγωνοσ(tetragonos)来加以阐释。[16]书中四度引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对“大度的人”所做的阐述。关于博雅知识、哲学的心智习惯、知识的等级与相互关系的论述,也处处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影子。就概念谱系而言,纽曼所说的“博雅知识”和亚里士多德的“适合于自由人的知识”(eleutherion epistemon)一脉相承,两者都坚持知识的内在价值和非功利性。
当然,亚里士多德和纽曼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纽曼首先是一个天主教教徒,他总是从宗教的角度看待各门知识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是古典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纽曼则反复强调理性的局限性,认定启示高于理性。
对于亚里士多德等人所代表的雅典文明,纽曼没有盲目崇拜。在纽曼看来,雅典文明的弊病在于过分神化“美”,美成了唯一的标准,其后果是正当的尺度被取消了。“如果美是判断正当的唯一标准,那么,没有任何优美、宜人的东西会是错误的。”[17]
亚里士多德关注的都是针对拥有闲暇的自由人阶层(绅士)的教育,奴隶甚至自由人阶层中的不拥有闲暇者(如工匠、农民)都被排斥在外。相反,基督教主张教育的权利应该向所有等级、阶层、种族的人开放。在这个问题上,纽曼坚定地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这是纽曼的博雅教育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又一区别。
西塞罗是古罗马时代最早提出“自由人的技艺”(artes liberales)这一概念的作家,也是古罗马时期博雅教育理论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他也是纽曼最为心仪的作家。纽曼在伊林学校时即开始阅读西塞罗的《论友谊》、《论老年》等著作。在正式入住牛津的前几个月中,纽曼精心研读古希腊罗马名著,其中就包括西塞罗的《论义务》一书。[18]1824年,纽曼还曾为《大都会百科全书》撰写西塞罗的词条。《大学的理念》一书对西塞罗学说的引用主要来自《论义务》一书。西塞罗学说对纽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知识的自为性(当然,这里也有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其二是言辞与思想、理性与语言不可分割的观念。纽曼指出,理性和言语不能分开,就像光与影不可分开一样[19],这一思想的源头显然来自西塞罗。
古罗马的斯多葛学派对纽曼的教育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提到,“健身学校对莱克格斯是一种符合自由人身份的训练,对塞涅卡而言却不符合自由人的身份”[20],塞涅卡的这一观点出自他的第88封书信,这表明纽曼读过塞涅卡的这封书信。在1859年纽曼所写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谈到了塞涅卡的第88封书信,提到了塞涅卡对于“自由人学科”的否定性态度:“塞涅卡谈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文法、音乐、几何和天文学,虽然他并不是那么推崇这些学科。”[21]
二、洛克教育思想:纽曼理智训练学说的源头
在纽曼之前,英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教育论著当属弥尔顿所著的《论教育》和约翰·洛克所著的《教育漫谈》,后者对18世纪的绅士教育或博雅教育理论有着异常深刻的影响。《大学的理念》一书对这两位作者均有所涉及,这里重点讨论洛克的教育思想对纽曼的影响。
纽曼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经仔细阅读过洛克的著作[22],尽管他并不赞同洛克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但有证据表明,纽曼的理智训练学说至少间接地受到洛克教育思想的影响。“理智训练”(discipline of mind)或“理智扩展”(discipline of intellect)是纽曼博雅教育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洛克。在洛克的《教育漫谈》一书中,理智扩展或改善理智的语汇已经占据显要位置,例如,洛克指出,自然哲学的学习可以作为“我们心智的扩展”,使我们更真实、更完整地把握理性和启示所揭示的“理智世界”[23],阅读、写作等文化活动可以“改善心智”[24],但若过度从事,则有害健康。除此之外,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一书更是对英国的理智教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智育”)理论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
洛克对纽曼的影响是间接地通过一位名叫以撒·瓦茨(Isaac Watts,1674-1748)的学者来实现的。以撒·瓦茨的思想在18世纪、19世纪初期影响非常大,他所著的逻辑学教材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牛津、剑桥以及非国教派学院的课本。早在19世纪20年代,纽曼就精读过以撒·瓦茨的著作《心智的改善:或,对逻辑技艺的补充》(1741)——该书在18、19世纪影响非常之大——其中一章的内容为“论扩展心智的能力”,纽曼关于“心智的扩展”的论述直接受到这一章的启发,并从中引用了一些例子。[25]如果再往前追溯,便可发现以撒·瓦茨的观点受到洛克《人类理解论》一书的影响。以撒·瓦茨极为推崇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在著作中多次以赞赏的口吻提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一书。[26]显然,洛克教育思想才是纽曼的理智训练学说的源头。
三、从“实用手册”上升至“理念”:纽曼对18世纪博雅教育理论的超越
18世纪是英国博雅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专门论述博雅教育的代表性论述有英国科学家普莱斯特里(Priestley J)1765年撰写的论文《面向公民和积极生活的博雅教育课程》[27],以及英国教育家维塞斯莫·诺克斯(Vicesimus Knox)1781年的著作《博雅教育:或,关于获取实用与文雅知识的应用性论文》。[28]这两个人的著作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普莱斯特里的论文在1826年前再版了16次,而诺克斯撰写的《博雅教育》一书在1781-1789年间就发行了10版。1797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教育”词条中一共提到两位18世纪英格兰的教育学家,入选者正是普莱斯特里和诺克斯。[29]不过,纽曼并没有引用这两个人的著作(也许是没有注意到),他大量引用的是其他作家的教育论述。《大学的理念》一书大量引用爱德华·吉本的《散论文学学习》以及沙夫兹伯里伯爵的《人、礼仪、观点与时代的特征》,可见纽曼对两者的教育理论非常熟稔。另外,纽曼对查斯特菲尔德勋爵(Philip Chesterfield,1694-1773)关于礼貌教育的论述也不陌生。
不过,总的来说,纽曼对18世纪英国的博雅教育和绅士教育学说的态度主要是批判性的。在某种意义上,纽曼已经和18世纪的绅士教育理论分道扬镳了。
首先,纽曼将博雅教育提升到了“理念”的高度。纽曼处理的是原则性的、哲学性的问题。他明确表示,他所讨论的是大学的“理念”、大学的“本质”、大学的完整性、教育的目的和原则、大学和教会的关系、大学和神学院的关系等根本性的和哲学性的问题。而所谓大学的“理念”,指的是大学区别于学院、教会、神学院、政府等机构的本质性特征,是大学的“独有的特性”和独立于教会的“本质”。[30]17、18世纪的很多博雅教育著作充满了如何学习拉丁语、如何处理师生关系、游学注意事项、职业选择等细枝末节的问题。维塞斯莫·诺克斯在其流传甚广的著作《博雅教育:或,关于获取实用与文雅知识的应用性论文》中自我标榜说,以前的很多教育论著(包括洛克的著作)都“太过思辨以致一无所用”。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纠正这种风气,主要探讨实践性的而非哲学性的问题。[31]而在纽曼的著作中,这些具体的问题让位于原则性的思考,诸如理性与启示、博雅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关系、知识与学习的关系等。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一书将博雅技艺、博雅知识、博雅教育这三个概念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博雅知识”成为最重要的论述对象,这在博雅教育思想史上实属前所未有。
其次,和18世纪、19世纪初期的博雅教育理论不同,纽曼并不强调博雅教育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18世纪博雅教育的主要阐述者普莱斯特里是一个激进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他秉承约翰·洛克的传统,指出公民自由与博雅教育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32]威廉·布克莱斯通也持相同的看法,他指出,法律知识,尤其是英国法的知识是“博雅教育”(liberal and polite education)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为宗旨。因此,以法律为主要内容的博雅教育必然也有利于促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33]而在纽曼看来,博雅教育指的是理智教育,因此是超越政治的。在政治立场上,纽曼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对民主和专制都有所批评。他所推崇的政府,应该既能提供保护(这是民主所不能提供的)又能提供自由(这是专制所不允许的)的。纽曼主张,在和平时期,建立在权利制衡基础之上的宪政政府是最佳选择。而在战争时期,专制是可以备选的政治形式。政治的普遍参与只会促进平庸而非卓越。[34]
再次,纽曼认为,以沙夫兹伯里为代表的绅士教育理论将德性建立在品位和美的基础之上,停留于表面和感官的层次,因而是不牢靠的,必须在这之上灌注宗教的精神,进行“心灵”的教育。
最后,与18世纪的博雅教育理论相比,纽曼更强调“心智训练”的地位。18世纪博雅教育理论的核心旨趣在于塑造一种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奉慷慨、友善、开明为教育的圭臬。而在纽曼这里,教育从“生活的技艺”转向了“认知的技艺”,“心智的训练”而非绅士风度才是博雅教育的首要宗旨。纽曼指出,所谓博雅教育,本质上就是心智的培育,是理智教育,而非道德教育、宗教教育或心灵教育,更不是18世纪的礼貌教育。17、18世纪的博雅教育著作会用很大部分的篇幅讨论如何塑造绅士的品格和美德,而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有关品格塑造的论述非常之少,整本书几乎都在讨论“知识”和“理智的培育”。当然,这并非《大学的理念》一书的特点,同一时期的威廉·休厄尔所著的《论普遍的“博雅”教育》一书也同样如此,处处不离“知识”的主题。对理智教育的强调为纽曼的博雅教育学说注入了“现代性”的因素。这种现代性的因素使得纽曼的教育学说能够在20世纪的才智社会、专业社会中继续发挥影响,“理智的培育”成为20世纪各家“自由”教育理论学说的基础。
四、纽曼对19世纪牛津博雅教育模式的坚守
19世纪是英国博雅教育话语激增并日益体系化的时期。在纽曼之前,19世纪英国博雅教育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曾两度执掌剑桥的教育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他的《论英国大学教育的原则》(1838)、《论一种普遍的博雅教育》(Of a Liberal Education in General,1850)等著作在英国影响很大。[35]一直到19世纪末,最为英国之外的人们所了解的博雅教育理论家可能还是休厄尔。思想史研究者约翰·梅尔茨(John Merz)在论及19世纪英国的博雅教育思想时,称赞休厄尔是“19世纪上半期对英国大学研究领域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但没有提及纽曼的名字。[36]今天看来,休厄尔所提出的“永恒性学科”(permanent studies)与“进步性学科”(progressive studies)的区分,以及关于两者在博雅教育中的地位的论述,是属于真正原创性的思想。纽曼在1853年发表的《大学教育演说附录》中引用过休厄尔《论英国大学教育的原则》一书的相关观点[37],但对休厄尔的博雅教育论述并没有实质性的借鉴。与纽曼相比,休厄尔更加推崇数学——尤其是欧几里德几何学——在博雅教育中的作用,他的教育学说更多反映的是剑桥大学的教育实践(在很长时间内,数学在剑桥的博雅教育中享有比古典文学更为高尚的地位,这一点与牛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牛津,数学的地位完全是附属性的),出身牛津并以牛津为模范的纽曼则更为推崇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自然也不会大量因袭休厄尔的学说。
如果说,威廉·休厄尔是基于剑桥的教育实践提出了自己的博雅教育理论的话,那么,纽曼则是通过回忆自己在牛津的教育岁月,阐发自己的博雅教育学说。从1816年入学,到1845年底离开牛津,纽曼在牛津度过了几乎30年的春秋。在这里,纽曼的角色经历了从学生到院士、导师的转变,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他的人生始终与教育须臾不可分割,而他始终也在思考教育的问题。
作为一名牛津人,牛津的古典教育模式对纽曼有决定性的影响。毫不奇怪的是,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与他的昔日同事们惊人地相似,而且,在很多地方,纽曼直接借用了他们的论述。19世纪初期发生在《爱丁堡评论》学派和牛津大学之间的大论争对纽曼的影响尤为直接。在某种意义上,纽曼的博雅教育理论是对《爱丁堡评论》的一个回应。作为此次论战中牛津一方的代表,约翰·戴维森(John Davison)、爱德华·考普斯顿(Edward Copleston)对纽曼的影响最为明显。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纽曼甚至大量引用爱德华·考普斯顿和约翰·戴维森的论述以代替自己的论证。在两人当中,纽曼与约翰·戴维森的思想更为接近。对比戴维森1811年所发表的《评埃德沃斯的〈专业教育〉》一文与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有关专业教育部分的论述,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雷同之处。[38]在第一次演讲中,纽曼也开宗明义地承认,自己在论述博雅教育理论时,大量依赖新教团体的成果。[39]约翰·戴维森和爱德华·考普斯顿都属于新教徒(考普斯顿后来还担任过兰代夫的新教主教),纽曼所指的新教团体的成果,主要指的是这两个人对博雅教育的阐述。
在19世纪30年代的牛津运动中,纽曼与理查德·弗劳德(Richard Froud)、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等人成为并肩作战的伙伴,纽曼的教育思想也直接受到牛津运动的影响,他曾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直接引用过约翰·基布尔的观点,虽然后者依然是英国国教的信徒。在牛津之外,纽曼的教育思想还受到柯勒惠治的影响。例如,他划分了大学和学院,认为前者体现进步性原则,后者体现稳定性原则,这一划分受到柯勒惠治的启发。[40]
五、结语
如上所述,博雅教育的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的“适合于自由人的知识”(eleutherion epistemon)以及西塞罗的“适合于自由人的技艺”(artes liberales)的观念。在纽曼之前,18世纪的维塞斯莫·诺克斯和普莱斯特里已经开始对博雅教育进行专门化的深入论述。而在19世纪,博雅教育的讨论一时蔚为大观,在纽曼之前,威廉·休厄尔撰写了厚达四百多页的《论普遍的博雅教育》一书,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观之,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阐发的博雅教育学说,确实是一个西方教育思想史的一个“老”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把握纽曼的博雅教育学说在整个西方教育思想传统中的位置,也因此能更加深刻地体会纽曼教育学说承前启后的思想史意义。
概而言之,纽曼的博雅教育思想是古希腊罗马传统、中世纪传统、文艺复兴传统、18世纪绅士教育传统、19世纪理智教育学说的一次交汇和综合。在主张知识自为目的方面,纽曼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衣钵;在主张雄辩与智慧的结合方面,纽曼受到西塞罗的启发;纽曼的恩典真理观以及他对博雅教育局限性的强调,则沿袭了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教父传统;他的理智训练学说则是来自洛克以来的心智哲学。纽曼上承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的思想以及18世纪的绅士教育传统,下启赫钦斯、白壁德的思想,在博雅教育思想史上的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因此,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一书可视为博雅教育学说的集大成之作,在所有论述“博雅”教育的著作当中,纽曼的论述最成体系,也最为详尽深入。在很大程度上,纽曼几乎成了博雅教育思想的代名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雅罗斯拉夫·帕利坎才对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一书不吝溢美之辞,称其为“有史以来关于大学的最重要的一本书”[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