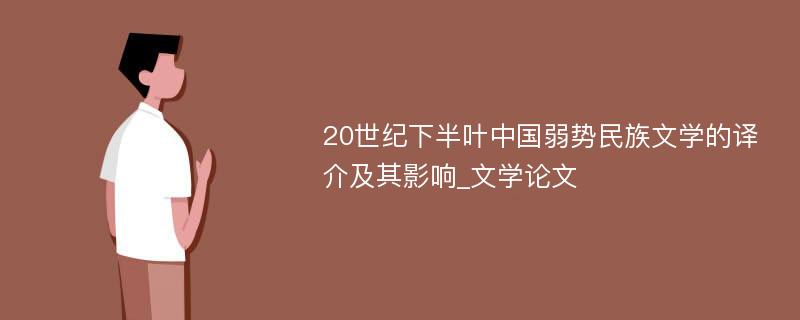
20世纪下半期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弱势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半期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3-0055-21
自20世纪初期开始,陈独秀、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就将“弱小民族”及“弱小民族文学”的概念引入现代启蒙话语当中。本文采用的“弱势民族文学”[1] 概念是对前者的沿用和改造,它是指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相对于英、法、德、美等西方强势民族文化的文学而言,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特别是处于(或者曾经处于)被殖民地位的民族文学,在20世纪下半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中,它又以一种变体形式得到延续。笔者认为,弱势民族文学的具体所指并非固定不变,它在我所设想的用于描述民族文学关系的话语整体中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特征,对它的语义分析也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综合考察主客体两个方面的因素。其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的语义变迁,一方面取决于运用这一话语的主体意图及其政治、文化立场;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又取决于世界局势和国内现实文化的复杂变化。以下试对20世纪下半期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做一个系统的论述。
一、前30年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确立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民族主权和领土两者均获得统一(除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之外),民族意识空前高扬,为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进行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同样是列宁所说的处于国际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之环节的成功,所以,中国在战后也不得不归于冷战的两大阵营中,并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所做出的“一边倒”的决定,既是政党的理想、纲领和意识形态的选择,也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出于民族利益的最大现实考虑。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仍然时时提醒中华民族的世界处境,民族意识再度成为动员社会力量的有力手段。但反映在对外文化交往上,则不得不逐步放弃了20世纪初期的开放态度,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采取敌对、批判和排斥的态度。并且,与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其他工作一样,建国后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也被纳入民族文学建构的规划之中。1951年召开“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又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文学翻译成为国家文化蓝图的一个部分。
这在建国初期的文学翻译实践中就已经显露出来。早在1949年7月,作为新中国文艺领导人的周扬和茅盾,一面批判以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欧美文学,一面强调应加强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的学习[2:19-46] [3:19-46]。1949年10月创刊的《人民文学》发刊词指出:“我们的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4] 具体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实践中,表现为全方位的译介俄苏文学①。对于欧美文学虽然仍有译介,但大都是19世纪之前的古典文学中反映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的作品,而对于现当代文学则主要限于革命文学的范围[5]。同时,在对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译介上,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标准恰好与民族意识的高扬相重叠,他们既在政治阵营的划分上同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是原来意义上的弱势民族国家,因此其译介也就比较频繁。此外,就是大量译介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了。
不过,其间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翻译的整体选择也有所调整。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中苏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对于东欧国家的社会变革也持批评和保留态度。为了最大限度地赢得国际支持,加强与非西方国家间的文化联系,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以维护民族独立,保卫民族文化,我国对于其他弱势民族国家采取了同情、援助等外交政策,亚非拉国家便成为中国的当然盟友。② 在文化和文学交流领域,相对于建国初期而言,苏联文学的译介明显减少,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文学译介也随之减少,同时亚非拉小民族国家的作家作品被大力译介。1958年的《译文》杂志,在第9、10两期,连续推出了“亚非国家文学专号”,11月号又设有“现代拉丁美洲诗特辑”。1959年《译文》杂志更名为《世界文学》,同年2月号上主要刊登的就是亚非拉文学的翻译,4月号则又开辟了“黑非洲诗选”栏目。这样,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全国出现了一个亚非拉国家文学的译介热潮。其中,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文学,在建国之前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译介。比如,建国前,印度文学只有迦梨陀娑和泰戈尔等极少数作家被介绍到中国,更很少有人直接从梵文翻译作品,“和我们有二千年文化交流关系的邻国印度,他的古代和近代文学名著,对我们几乎还是一片空白”。③ 其他如土耳其,则只有希克梅特的几首诗;波斯文学只有《鲁拜集》;阿拉伯文学也只有《一千零一夜》的节选,等等。这些情况在建国后的几年里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相对而言,同时期的苏联文学译介则不多,英法美等国文学更是限于数十部古典文学作品。
不过,从建国后17年的外国文学翻译总量来看,苏联文学仍然占很大的比重。据统计,从1949—1966年的17年间,外国文学翻译书籍总印数不低于1亿册,平均每种2万册。其中苏联作品遥遥领先,占17年间总量的一半以上④。在新中国的最初7年里,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作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196种俄苏作品。尤其以苏联作品的译介最为详尽、及时。同时,除德国以外的东欧国家作品也有大量译介,17年间这些国家的古典文学作品(19世纪之前的)译介有80多种、100多位作家的数百篇作品,其中包括密茨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塔杜施先生》和《密茨凯维奇诗选》等,还有陈冠商翻译的显克维支的长篇小说《十字军骑士》和《显克维支中篇小说选》,施蛰存、周启明翻译的《显克维支短篇小说集》,吴岩翻译的莱蒙特长篇小说《农民》,萧乾翻译的哈谢克《好兵帅克》,孙用翻译的《裴多菲诗选》等等。这些国家的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则体裁多样,出版有反映当代生活的许多短篇小说集,如《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徐萍等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阿尔巴尼亚现代短篇小说集》(多人合译,作家出版社,1964年),《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高骏千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捷克小说选》(魏荒弩译,晨光出版公司,1950年),《捷克诗歌选》(魏荒弩编译,晨光出版公司,1950年),《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陈登颐等译,光明书局1952年)等等,到50年代末至文革前,因政治原因才逐渐减少。其他北欧国家的文学也有一定数量的译介,但数量相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20—30年代明显减少。值得一提的是丹麦安徒生的童话作品,是由叶君健直接从原文译出,于1955、1958出版多次,成为几代读者喜爱的作品。此外,丹麦现代作家尼克索(1869—1954),也从50年代起被介绍到中国,对其作品的译介也比较全面,有代表作4卷本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是北欧最早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由施蛰存从法文本参照英文本译出。另外还有他的《蒂特三部曲》(邹绿芷等自英文转译)、《红莫尔顿》第一卷(徐声越从俄文转译)、《尼克索短篇小说选》(杨霞华从俄文转译)等等。
相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外国文学译介而言,20世纪下半期对于亚非拉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成果尤其显著,大部分国家文学的译介都是从无到有,大大扩展了外国文学的视野。17年间,先后出版了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缅甸、锡金、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约旦、以色列、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南非、智利、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35个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是历史上空前的。
而其中翻译最多的是朝鲜和越南。越南文学的译介同样以反映其民族独立解放的现代文学为主,影响较大的包括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的《狱中日记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现代著名作家中译介较多的有,诗人素友的《越北》(颜保等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素友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武辉心的长篇小说《矿区》(黄敏中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阮公欢的长篇小说《黎明之前》(谭玉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阮庭诗的长篇小说《决堤》(岱学译,作家出版社,1964年)和诗集《战士》(松柳等译,作家出版社,1965年)、苏怀的短篇小说集《西北的故事》(张均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等,此外还有综合性的译本如《越南现代短篇小说集》(北大东语系越语专业师生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等等,共计70多部集[6]。朝鲜文学以现代文学为主,17年间共有100多种作品(集)翻译出版,是同期我国翻译最多的外国文学之一,这与中朝两国的政治体制和在朝鲜“南北战争”期间结下的友谊有关,因此这一时期朝鲜民族文学的翻译只限于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与“大韩民国”几乎隔绝。最有影响的是20世纪30—40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如李箕永(1895—1984)的长篇小说《土地》(冰蔚等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故乡》(李根全、关山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韩雪野(1900—?)的长篇小说《大同江》(李烈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黄昏》(武超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塔》(冰蔚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等。此外还有赵基天的《白头山》(余振译,1951年,适夷译,1953年)、《生之歌》(李烈等译,1954年)、《赵基天诗集》(适夷等译,1958年),及《崔署海小说集》(李圭海译,1959年),黄健的《盖马高原》(冰蔚译,1960年),千世峰的《白云缭绕的大地》(冰蔚译,1963年),韩成的剧本《等着我们吧》(冰蔚译,1956年)等等。古典文学只有《春香传》(冰蔚等译,人民文学,1956年)和《沈清传》(梅峰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等。另外,印度文学作品30多种,包括小说、诗歌、剧本多种文体,涉及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近十位作家,此外还有季羡林、金克木等人翻译的迦利陀娑的古典作品等等。日本文学译介的重点则在无产阶级作家,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先后出版了《小林多喜二选集》3卷、《德永直选集》4卷、《宫本百合子选集》4卷等等。
拉丁美洲和非洲诸国的文学也有不少译介。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其中包括:1959年出版的《腹地:卡奴杜斯战役》(巴西,长篇小说,库尼亚著,贝金译)、《纪廉诗选》(古巴,纪廉著,亦潜译)、《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巴西,阿尔维斯著,亦潜译)、《秘鲁传说》(秘鲁,长篇小说,巴尔玛著,白婴译)、《深渊上的黎明》(墨西哥,曼西西杜尔著,林荫成,姜晨瀛译)、《时候就要到了》(长篇小说,巴西,巴依姆著,秦水译)、《阴暗的河流》(阿根廷,长篇小说,伐莱拉著,柯青据德语转译),以及《运征·圣保罗的秘密》(巴西,长篇小说,斯密特著,吴玉莲、陈绵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利约短篇小说集》(智利,短篇小说集,利约著,梅仁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风暴中的庄园》(乌拉圭,长篇小说,格拉维那著,河北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等10本作品,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对于拉美文学的译介。
这一时期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作家要数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和巴西小说家亚马多(Jorge Amado 1912—2001)了,他们在中国的译介,与其共产党身份和作品中所反映的倾向有着直接的关系。聂鲁达是共产党党员,曾是智利国会议员。1946年后流亡国外,从事世界和平运动,曾经到过中国,1950年获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金,1952年返回智利,1957年担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自新中国初期开始,聂鲁达就被译介进来。1951年有3本诗集出版:《让那伐木者醒来》(袁水拍译,新群众出版社,1951年;此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重版)、《聂鲁达诗文集》(袁水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初版,1953年重版)、《流亡者》(周绿芷译,文化工作社,1951年)。1957年,还翻译出版了由苏联学者库契布奇科娃和史坦恩合著的《巴勃罗·聂鲁达传》(胡冰、李末青译,作家出版社),之后相继有邹绛据俄文本转译的《葡萄园和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和王央乐翻译的《英雄事业的赞歌》(作家出版社,1961年),在50年代的中国诗坛具有较大的影响。亚马多在30年代参加巴西共产党,数度入狱或者流亡,曾担任巴西共产党主办的《圣保罗报》主编。40年代的代表作品是以农村为背景的三部曲,在50年代都有了中译,即《无边的土地》(吴劳译,文化工作社,1953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黄金果的土地》(郑永慧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和《饥饿的道路》(郑永慧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作家出版社,1957年)。
这种对于亚非拉弱势民族国家文学的译介,扩大了中国读者的外国文学视野,丰富了外国文学译介的对象,客观上纠正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作家创作外来资源上的偏颇格局,显然具有长远的积极的意义。但是,当时这种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翻译选择主要标准的功利性态度和译介方式,在增加和开辟新的外来文学资源的同时,由于人为地对于现代欧美文学给予排斥和抵制,从而使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从五四时期的开放逐渐走向狭隘的封闭,从以西方文化作为民族现代化的主要参照,演变到先是主要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交流对象,后又在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时代主流话语下,只对亚非拉弱势民族文学开放,使民族意识走向片面的自我肯定。特别是在50年代末以后,随着极左政治的逐步抬头,民族文化发展的格局日渐趋于封闭。
另外,在建国后的17年间,一些弱势民族特别是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古巴、阿尔巴尼亚、墨西哥等国的电影译制[7],也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一种直观的影像展现,对于建构民族文化及其想象,有着甚至比文学作品更为直接和广泛的作用。
至“文革”爆发的1966年,这种片面的民族意识与极左政治相结合而走向极端,整个外国文学译介几乎完全停止。所有的外国文学都被打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而遭受批判、禁止,在公开出版物当中,只留下诸如阿尔巴尼亚作家拉扎尔·西里奇的小说《教师》(戈宝权译,作家出版社,1966年)、朝鲜作家金载浩的戏剧《袭击》(北大朝鲜语教研室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出版,1966年)等极少数作品。文革前期政治斗争高潮阶段,所有文学出版业几乎陷于停顿。直到70年代初,才有一些内部出版物⑤ 登载一些苏联、美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少量作品,作为内部批判的材料。到文革后期,随着文化秩序的部分恢复,出版业也相应重新启动,这样,尽管对于外国文学译介的政治限制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毕竟已有一些作品重新得到翻译出版。如老挝作家伦沙万的小说《生活的道路》(梁继同、戴德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莫桑比克战斗诗集》(王连华、许世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朝鲜短篇小说集》(李尚植等著,张永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玻利维亚小说《青铜的种族》(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著,吴建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朝鲜诗集》(崔荣化等著,延边大学朝语系72届工农兵学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反映菲律宾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小说《不许犯我》(何塞·黎萨尔著,陈尧光、柏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巴基斯坦诗人伊克巴尔的诗集《伊克巴尔诗选》(王家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等。
二、后20年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
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又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民族国家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长期对垒之后,中国社会重新回到理性的起点。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新的开放的世界眼光,确立了民族文化的地位,也获得和认同了新的民族文化身份。但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处境有所不同的是,尽管前者在经济上处于明显的落后地位,甚至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停顿而严重加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西方国家)的距离,按照当时的说法,即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但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民族国家毕竟已经具有一定的实力。同时,由于没有外族政治和军事的直接侵略,国家民族的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威胁,民族政治地位也相对稳固。因此,面对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发达局面,深深的“民族落后意识”成为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和改革的现实前提。这样,世界化和西方化一度再次成为社会变革的目标,“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叙事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主流话语,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激进知识分子当中刮起的“蓝色文明”⑥ 风暴,对于中国文化传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这就是极端西方化和世界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表现。但这种西方化思潮倾向,其实是以民族复兴的急迫要求作为重要动力的,因此,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8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民族传统的继承和民族身份的认同要求便再次浮出水面,民族意识重又抬头。从文艺思潮的角度来看,在西方现代派思潮大兴华土之后,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界受到80年代初期的政治挫折之后,对于现代派文学学习、探索日渐转向晦涩,“寻根文学”随之兴起,文艺界的主流话语又转向了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探索。因此,80和90年代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尽管在总量上一直处于不断上升、不断繁荣的过程中,但如果从翻译选择的趋向来看,两个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来,而在这两个时期,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地位、功能和被重视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中国整个文化和文学领域对于外国文学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7年10月《世界文学》杂志的复刊,就是新时期恢复外国文学译介的标志。新时期伊始,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十七年对于小民族文学译介的路数,一开始,苏联文学与欧美经典文学的译介得到恢复,不久,随着整个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展开,西方现代文学的介绍很快得以展开,并且激发了中国读者和作家们的阅读和创作热情。在西方文学大量引进的同时,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也逐渐多了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共出版发表外国文学共100部篇,其中属于弱势民族文学仅10部篇,⑦ 而这个比例在80年代后期则有很大的变化。不仅如此,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内容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鲜因素,并埋下了触发中国当代文学创新的种子。
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文学中除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学外,主要译介了部分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作品,如《新世界的儿女》(阿尔巴尼亚小说,阿西亚·杰巴尔著,萧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瓦普察洛夫诗选》(保加利亚,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考什布克诗选》(罗马尼亚诗歌,冯志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呓语》(罗马尼亚小说,马林·普列达著,卢仁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德里纳河上的桥》(南斯拉夫小说,伊沃·安德里奇著,周文燕、李雄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好兵帅克历险记》(哈谢克著,星灿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契克著,蒋承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等。此外,像传统的弱势民族波兰文学则仍以介绍显克微之[8] [9] 等作家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在1978至1980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陈冠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你往何处去》(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和《显克微支中短篇小说选》(陈冠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至此,这位波兰伟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几乎全部有了中译。
亚洲部分以朝鲜文学居多,有朝鲜作家金永根的长篇小说《钟声》(葛振家、冯剑秋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白头山》(诗歌,赵基天著,张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回声》(小说,郑成勋著,田华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等。印度文学除了季羡林对于印度古典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一,《童年》,二,阿逾陀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81年)和金克木译《伐致可利三百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外,现代印度文学的译介有:泰戈尔的诗歌《采果集》(汤永宽译,《百花洲》1980年第3期)和小说《素芭》(冰心译,北方文学1982年第5期),以及《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克里山·钱达尔著,伍蔚典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有儿女的寡妇》(普列姆昌德著,殷洪元译,《外国文学》1981年第1期)和《印度现代短篇小说选》(阿墨尔、甘特等著,黄保生、倪培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这些差不多都是对于50年代甚至现代时期译介活动的继续。
在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学的译介中,对于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翻译同样延续了自20年代以来的传统,这一时期又有冰心翻译的散文诗集《沙与沫》(载外国文学季刊1981年第2期)和散文集《先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及《纪伯伦散文选》(韩家瑞等译,《世界文学》1980年第3期)、《雾中船》(小说,葛继远译,载《外国文学》1985年第8期)等。只有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名字是新的,他的《一张置人死地的钞票》(小说,范绍民译,载译林1980年第2期)、《木乃伊的觉醒》(孟早译,载《外国文学》1980年第6期)、《暴君》(静子译,载《外国小说》1989年第2期)开始了其在中国的传播,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拉美文学中,一开始的译介也是对于17年的延续。如:《拉丁美洲现代独幕剧选》(王央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墨西哥的神话小说《羽蛇》(何塞·罗佩斯·波蒂略著,宁希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和委内瑞拉小说《堂娜巴巴拉》(罗慕洛·加列戈斯⑧ 著,白婴、王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还有智利的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诗人米斯特拉尔(《柔情》,赵振江、陈孟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6月)和聂鲁达都有延续的译介(《聂鲁达诗选》,王永年译,《世界文学》1980年第3期、《聂鲁达诗选》,蔡其矫译,《诗刊》1980年第9期、《布尼塔基的花朵》,炜华译,《外国文学季刊》1981年第1期)。特别是聂鲁达作品的译介,80年代开始出现众多的译本。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至少有5种聂鲁达的诗歌和散文编译本[1] [11] [12] [13] [14];到90年代,又有8种。其中,仅他的回忆录就有3种译本[15] [16] [17]。此外还有《聂鲁达爱情诗选》(陈步奎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情诗·哀诗·赞诗》(漓江出版社,1992年)、《漫歌》(江之水、林之木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中英文对照的《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李宗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从50年代开始,这位智利诗人对于中国当代诗坛,特别是对于当代政治抒情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位共产党作家亚马多,在80年代之后仍保持强劲的被译介势头,到90年代初,作家自流亡之后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被翻译出来,有的还有重译本。先后有《拳王的觉醒》(郑永慧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加布里埃拉》(徐曾惠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孙承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浪女回归》(陈敬咏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死海》(范维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孙成熬 范维信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沙·巴蒂斯塔》(文华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大埋伏》(孙成熬、范维信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初版,1995年再版)等7部长篇小说出版。
不过,80年代最能体现弱势民族译介中的新鲜因素的,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的对于拉美当代文学的译介。之前对于拉美文学的译介,都限于20世纪中叶之前的近代文学,主要是19世纪拉美独立革命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和20世纪初期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对拉美当代文学的介绍,则主要限于聂鲁达、亚马多等几位共产党作家。对于19、20世纪之交(约30年时间)的现代主义文学则基本没有译介,而对自50年代起开始的拉美当代文学,特别是兴盛于60年代的“爆炸文学”,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不得不停止。新时期开始后,拉美爆炸文学在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所获得的惊人的地位,使得中国研究和译介者产生极大的兴趣,在延续五六十年代对于拉美文学译介传统的同时,拉美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整体上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弱势民族文学,被热切地介绍、翻译、谈论和模仿,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也相继被介绍进来。相对而言,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等作家最为受人瞩目。
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 1928—)最早的中译起始于1980年,《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发表了赵德明等译的《马尔克斯短篇小说4篇》,1982年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赵德明等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几乎就在该书出版问世的同时,马尔克斯作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很大的热潮,似乎给急于“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作家预示了一种努力的方向和成功的希望。1984年,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的中译本问世,并几乎同时有了两种译本:一是黄锦炎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本;一是高长荣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本,从而出现了一股译介马尔克斯的热潮。各种报纸、文学期刊和出版物中,关于马尔克斯的翻译、介绍不计其数,并且成为中国当代文坛长期谈论和学习模仿的一个对象。在普通读者甚至是某些专业读者眼里,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似乎就代表了拉美现代文学的一切,以至于人们把博尔赫斯、略萨等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倾向和文学追求的拉美作家,也归于“魔幻现实主义”之列。⑨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为止,马尔克斯作品翻译的单行本就有20多种,还不包括刊发于报纸和期刊上的译文在内,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了中译,并被及时地追踪当下的创作。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的译介最早起始于1981年,《世界文学》在这一年的第6期发表了王永年翻译的一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到1983年,先后又有《当代外国文学》第1期和《外国文学报道》第5期发表“博尔赫斯短篇小说3篇”(王永年译)和《结局》(解崴译)。同年,《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王央乐译)。博尔赫斯被智利诗人聂鲁达称为“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对于中国先锋小说具有重大的影响,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残雪、余华、马原、孙甘露等作家,几乎都从这位阿根廷作家身上汲取了养分[18],从而使博尔赫斯成为中国文坛最受欢迎和瞩目的当代外国作家之一。到90年代末,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5卷本《博尔赫斯全集》,包括小说卷(王永年、陈泉译)、诗歌卷(上下,林之木、王永年译)和散文卷(上、下,王永年、徐鹤林译),其中包括了几乎全部的博尔赫斯创作。另外,还有《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谈创作》(倪华迪、段若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赵德明译)和《博尔赫斯谈诗论艺》(陈重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以及博尔赫斯的传记研究译著。
略萨(Mario Vargas Llosa 1936—)的译介及其影响,要逊色于前面两位。与博尔赫斯一样,作为拉美“结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同样有被误解成魔幻现实主义的遭遇,而这种遭遇又都与马尔克斯的名声有关。这既反映了中国读者对于拉美当代文学丰富、多元格局之了解的有限,同时也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之大。不过,对于略萨的译介和影响虽然不如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但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译介数量也不少。从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赵绍夫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率先被翻译之后,又有《青楼》(韦平、韦拓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狂人玛伊塔》(孟宪臣、王成家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赵德明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酒吧长谈》(孙家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绿房子》(孙家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创作谈《谎言中的真实: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后面的5种,都是云南人民出版社以“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的名义推出的,略萨也是这套丛书中唯一一位秘鲁作家,也是在这套丛书中介绍的最多的作家。
另一种因素便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对于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的译介。虽然关于昆德拉的创作及其在捷克和欧洲的影响情况,早在70年代末就多少被介绍到国内,80年代中期还有李欧梵的大力推荐,但其作品的翻译直到1987年才开始。这一年,《中外文学》第4期刊登了赵长江翻译的短篇小说《搭车游戏》;紧接着又刊登了昆德拉的短篇小说中译《没人会笑》(第6期,赵锋译)。更有作家出版社接连推出的长篇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景凯旋、徐乃健译,1987年)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1987年),而尤以后者在中国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为最大,从此掀起了中国的“昆德拉热”。如果说,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在中国引发的持久热情,是因为其在整体上表达了现代化后发民族面对全球化进程时的生存处境和文化遭遇,从而触发了中国文学创作对于西方化倾向的某种反思,那么,对于昆德拉的热情,则除了同样面对西方强势民族文化的共同处境之外,还加上中国与捷克之间曾经在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格局以及知识分子处境上更多的相似点。
上述新时期弱势民族文学译介和接受的两个重要兴奋点,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得到了有力的延续。体现在拉美文学的译介方面,就有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其中包括综合性的中短篇作品选集、作家长篇作品或者个人选集和创作谈三个系列。综合性的作品集共有6本,分历代名家诗歌、现代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和中篇小说几个专题。作家长篇作品和个人选集系列包括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秘鲁、乌拉圭、智利、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古巴、危地马拉等12个国家28位作家的33部(集)作品。作家创作谈系列则包括略萨、科塔萨尔、马尔克斯、奥·帕斯、何塞·多诺索、若热·亚马多、卡彭铁尔、博尔赫斯等8位作家,可谓规模宏大。此外,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也有大量译著出版。在21世纪刚刚开始时,上海译文出版社还推出了“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使昆德拉的作品的译介与其创作完全保持同步。这一系列译介以及相应的研究实践,对于80年代中国文学中“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创作思潮,和90年代以来多元化创作的形成都相继起到触发和推动作用。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之后的国外作品版权的限制,外国文学作品在世纪之交的翻译,总体上比八九十年代有所减少,再加上英、日等强势语言的冲击,国内小语种翻译人才出现断档,这样,亚非拉等小语种文学的翻译出版在总体数量上出现了萎缩[19]。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正常的国际文学交流的趋势毕竟不可阻挡,相信全面开放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局面一定会成为一种常态。
三、本土文化规范与外来文学的创生性
同为弱势民族——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自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开始,中国对于亚非拉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继续得到鼓励和推崇。加以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参与并支持这种通过跨语际译介来建构民族文化的工程,因此,这些弱势民族国家的文学翻译出版,在总量上大大超过了20世纪上半期的50年;并且,由于在前30年间对于西方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压制和拒绝,欧美现代文学的译介远远不如二三十年代多,而50年代对于苏联和东欧文学的译介也很快因为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而趋于停顿,这样三个因素的相加,使得这一时期前30年的外来文学译介领域中,亚非拉弱势民族文学成为外来文学资源中特别瞩目的一个主体部分。在后20年的时间里,由于文化环境的相对开放和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外来文学的译介大致处于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的境地。与前30年相比,这一时期亚非拉文学的译介虽然在格局上有了重大的变动,原来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负载了狭隘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学文本的译介,比如北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家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创作文本的翻译,自然趋于减少;即使成为译介事实,也明显缺乏读者的认同。但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绝对数量仍然保持了相当大的规模。
不过,亚非拉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数量的多少,并不决定其在译入语文化环境即中国当代文学空间中的文学和文化功能。相反,后者才是决定其生命延续的主要力量。纵观20世纪下半期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真正在中国文学中产生影响的弱势民族作家或者思潮并不多,除去前30年不算,就是拿前者与新时期西方文学的译介和影响相比,也要逊色许多,在20世纪末短短的20年里,欧美文学思潮和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阵阵波澜,是不争的事实。而弱势民族文学思潮或者作家在后50年中能够产生比较重大影响的,在50年代只有巴西小说家亚马多、智利诗人涅鲁达等寥寥几位;在新时期,有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略萨等作家为代表的拉丁美洲作家群,还有昆德拉这样的东欧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相继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相对于中国文坛原有的文学传统而言,他们的进入,带来了新颖的文学创新模式。进一步说,这些作家的创作文本在源语文化环境中的艺术原创性、地位和影响,也不能绝对地决定其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反,译入语本土文化的规范,决定了外来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创生性的发挥。这里所谓创生性⑩,是指某一种文学模式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启发和触动,从而导致富有新质的文学文本产生的可能性和潜力。
因此,除非民族国家出于意识形态或者主权独立的迫切需要,推行国家民族主义的文化政策,采用权力控制的手段,对外来文化加以强制性的过滤,否则,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的胶着、冲突,始终是弱势民族国家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交往以及自身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本土(译入语)文学主体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状态下对于本土与世界、个体选择与社会责任、民族文化建构与文学审美等问题的两难处境。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特别是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背景,应该属于前者,而新时期以后的情形则更多地属于后者。
与五六十年代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虚假地位相比,新时期亚非拉和东欧国家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虽然重新面临了西方强势文学译介的巨大压力,但其本身毕竟也获得了一种开放多元的译入语环境,从而能够与西方强势文学同时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空间中进行竞争,既争夺读者,也争夺作家和研究者的青睐,同时更显示各自与本土文学的亲和力,发挥自己的创生性。
八九十年代中国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不仅通过跨语际交往实践,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造就了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昆德拉、略萨、艾特马托夫这样具有强大创生性的作家,同时也在弱势民族文学与西方强势文学的竞争中,凸显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学和文化问题。比如,在全球化日益成为现实的时代,文学中的本土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矛盾、对立和共存、转换的辩证问题。在这个问题之下,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一再通过其他方式呈现出来,比如怎样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如何被世界认同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同属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与博尔赫斯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接受对比,也是一个十分有趣并意味深长的现象。另外,在文学研究层面上,关于弱势民族(第三世界)文学的动力问题——文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对强势文化和文学的接受、抵抗还是自身传统的创造?文学的审美独立性和文化功利性对于第三世界民族文学来说是不是一种天然的两难?前者是不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学标准?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并非在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和接受视阈可以解决,但讨论这些问题,却离不开这一视阈的观照。
注释:
①据陈玉刚统计,建国后的7年中,“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作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196种俄苏文学作品”。俄国古典文学虽仅占俄苏文学翻译总数10%左右,但在1949—1953年也达114种。见《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出版,第347页。
②茅盾在《为了亚非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中曾指出,这些文学译介主要是“为了促进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郭沫若的《对亚非作家会议的希望》也认为,它有助于“加强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分别载《译文》1958年第9期,《文艺报》1958年17期。
③见茅盾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载《译文》1954年10—12月号。
④卞之琳:《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5期。1949年10月—1958年12月,俄苏译作共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量的65.8%强,总印数8,205,000册,占总量的74.4%。
⑤如上海创刊于1973年11月的《摘译》(外国文艺),就刊登有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以及部分文艺理论。
⑥“蓝色文明”作为“黄色文明”相对的概念,被用来指称西方和中国文明传统,出自电视专题系列片《河殇》,在80年代风靡一时。
⑦这个统计据陈鸣树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所录的译文目录得出,虽并不完整,但仍可以大致反映出80年代初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强/弱民族文学的比例。
⑧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曾作为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当选为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后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流亡墨西哥,其创作活动到50年代基本结束。
⑨直到21世纪初期,还有人将博尔赫斯作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谈论而受到批评。见文鸣《老调不应重弹》,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日。
⑩这里的创生性,类似于伊文·佐哈尔的能产性(productive),他在关于静态和动态经典的论述中,以能产性区分两者,并进一步将是否具有能产性作为文学经典模式的一级类型(primary)和二级类型(secondary)的标志。参见伊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载《中外文学》2001年8月第30卷第3期。
标签:文学论文; 巴勃罗·聂鲁达论文; 世界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作家出版社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作家论文; 中国社会出版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