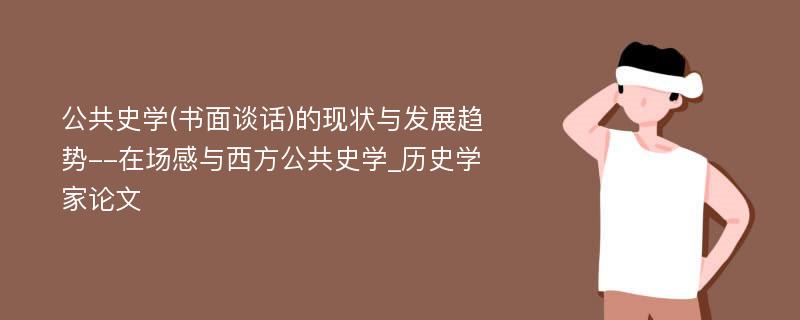
公共历史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笔谈)——在场感与西方公共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若以1978年创办的刊物《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与1980年成立的全国公共历史学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为标志,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公共史学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一门学科,公共史学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全美近百所高校设置了公共史学的学位课程,一批学生(甚至包括少数中国留学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公共史学并未赢得专业历史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美国国务院首席历史学家戴维·特拉斯克抱怨说,在联邦政府内部服务的历史学家,在历史学界受到了一种需要给予怜悯的对待,甚至把他们视为历史学界的二等公民,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是以玩世不恭的方式为权力服务的仆人,依靠向他们提供有偏见的历史来邀宠[1]。《公共历史学家》杂志编辑曾就“历史学界的未来”问题采访美国历史学会的执行秘书加蒙,他在回答问题时多次使用“我们这个学术团体”字眼,流露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2]。彼得·诺维克更是对此直言不讳,认为在“公众历史学”的名称下,有许多内容其实是“私人史学”,即为政府部门、商业部门或为其他职能组织服务的历史研究。它与普遍论所主张的公正的客观性完全背道而驰[3]。大学教授们表面上对公共史学的积极评价,不过是出于一种“职业的礼貌”。
一、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尴尬状况的产生?
首先,公共史学过于强调应用性导致理论研究的准备不足。按照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公共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的初衷,公共史学主要是为解决历史专业学生就业困难问题而设计的,针对性强、与实践联系紧密的职业训练课程。在《公共历史学家》创刊号上,他对公共史学做如下界定:简单地说,公共史学就是指历史学家的就业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运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历史学家无时不在工作,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的一部分。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资源的使用或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历史学家[4]。在凯利的理解中,公共史学具有较强的职业训练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用史学(applied history)是公共史学的代名词。
同为公共史学创始人的约翰逊(G.Wesley Johnson Jr)也与凯利一样强调其应用性,他承认公共历史学家是一种职业人士,他们拥有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技能,这些技能可以用于政府、商业、教育和一般的研究部门。不过,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过于强调应用性,可能会导致二等公民的状况,因此认为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应用史学的说法是错误的。公共史学家的训练无疑会包含实践的内容,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同样也是一种基础研究,也是在创造新的知识;他们同样需要具备专业历史学家的训练和技能,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他们对自己成果的质量要求与传统专业历史学家并无二致。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公共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在他们的资助机构和雇主所建议的研究种类中来设想和创造题目,他们没有专业历史学家所拥有的随心所欲地选择研究题目的自由[5]。但是他没有将这一看法进行充分阐释,反倒是凯利的功利性思想主导了公共史学的最初发展。
其次,公共史学过于挑战客观性导致与学术研究形成对立。本来,由于公共史学服务于特定的对象或雇主,使得专业历史学家对于公共史学家能否保持中立性的立场就存有疑问,口述、访谈的偏见或夸大都可能对历史认识造成扭曲,资助者的主观要求会形成另一种压力。未能等到约翰逊关于公共史学也在创造新知识的看法得到解释与获得认可之前,公共史学家们对于客观性的不当挑战,引发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进一步反感。一位公共历史学家写道,“能自由、客观和忠于事实地发表看法,完全按照自己的选择与读者说话,这些都是无懈可击的学者—历史学家。不过,这样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很早以前就变成了一种幻想。”[6]从理论上来说,这并没有错,无懈可击的客观性是一种不能企及的梦想。但问题是,这种逻辑证明了对方的不合理性,同样也证明了公共史学自身的不合理性,却没有为其合理性存在提供依据。正如诺维克所言,客观性问题是公共历史学家的一个痛处。
再次,公共史学以解释权的民主化解构了自身的合法性。由于受到七十年代各种权利运动的影响,一些公共史学家将公共史学解释为“谁拥有历史”的话语权之争。罗纳德·盖雷尔说,“公共历史学向我们允诺一个这样的社会,广大公众在其中参与构建自己的历史。……它以民主的方式宣告,它相信公众当中的每个成员最终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并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的认识。”[7]同样,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卡尔·贝克尔早就提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命题。但是,假如这一点得到完全认可,不仅专业历史学家变得多余,公共历史学家也会同样变得多余,公共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也是多余的。在这种背景下,必然会出现“谁是公共历史学家”这样一个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
二、那么,公共史学的真正价值到底在哪里?
南卡罗来纳大学公共史学教授舒尔茨(Constance Schulz)在某种程度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公共史学教学的指导方针是,了解和理解原始的历史材料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筑物、遗址、场景、文物、口述记忆、影像资料和电子文献等[8]。但如果只是作为原始材料,必然又涉及资料的批判问题,纠缠于此依然不会摆脱专业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梦魇。需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公共史学是在意识形态化史学与学术化史学遭遇困境与挑战时产生。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化历史学与令人生畏的学术化史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常以叙事的方式表达对历史的认知。但叙事不是认识的唯一途径,还可以有其他方式。维特根斯坦在对逻辑、语言和实在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指出,语言的词语永远不能表达出想要表达的符合,因而我们只能求助于显示——就是说图像论——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们就将陷于无穷倒退,即描述的描述的描述[9]。
如果说意识形态化史学提供了身份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学术化史学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知识,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那么重视图像等各种显示形式的公共史学所提供的,是与意识形态化史学与学术化史学不同的东西,我们可称之为“在场的历史认识”,同样具有合法的存在价值,且具有不可替代性。所有公共史学的实践,无一例外都重视现场,无论是访谈,还是在博物馆、遗址遗迹等的操作中,它所提供给受众的更多是一种融合视觉、听觉甚至嗅觉的复合感受与认识,是对政治化史学与学术化史学的一种有益补充,而不是完全的取代。历史的复杂性同样需要认识手段与方法的复杂性。
对于公共历史学家而言,提供“在场感”是一种复杂的技术工作,空间的有效利用、实物的布置、历史材料的呈现方式等都是传递信息的有效途径与手段。对于受众而言,从再现的历史场景中获得的是一种身临其境的独特感受,甚至还有各自不同的情感波动。情感波动不是对历史认识的否定,而是对认识的丰富。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表达的是一种期待,希望历史学家建立历史与生活的联系,不要将历史变成僵化的编年史。脱离了活凭证的历史都是空洞的叙述。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时,表达的是另一种期待,希望历史学家在思想中对历史过程进行重演,是理解后的贯通,而不是将历史变成剪刀加糨糊的历史。二者都希望复活历史。公共史学通过“在场感”可以获得复活历史的效果,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被拉近,历史与人们的距离也被拉近。正如克罗齐所言,一旦复活历史,对历史确凿性和有用性的怀疑就会烟消云散[10]。当在场感缩短历史与人们的距离时,历史不仅作用于现在,而且已经在参与创造未来。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兴分支学科,公共史学的实践价值目标不应当在于为某个人、某个组织、某个团体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在于以一种新的认知与表达手段增加人们的历史认识与体验。这才应是作为学科或者知识的生产者获得尊重的理由。公共历史学家不是“应招而来”的服务生,而是“主动探索”的研究者。当公共史学家们从这个出发点去开展工作时,相信专业历史学家们会投来好奇与致敬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