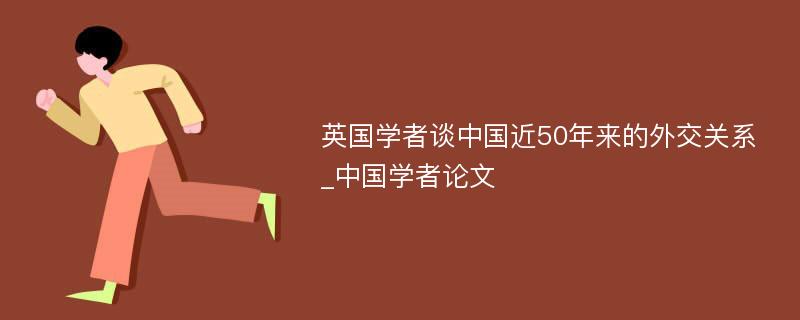
英国学者谈5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学者论文,年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
也许最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地位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难以回想中国建国前的凄惨程度。本世纪初,它被嘲笑为“亚洲病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描绘成“一盘散沙”。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现代中国史上首次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就给西方军队以致命的打击。正是中国人在朝鲜战场的突出表现使中国赢得了长期渴望的大国地位。中国的大国地位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被正式承认。从那时起,尽管中国依然只是个地区规模的大国,缺少苏联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却从来没有遇到真正挑战。
难以理解的是,在获得了那种大国地位以后,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其知识分子代表,都未能对运用大国地位达到何种目的表达出清晰的远见。一开始,他们否认中国会扮演大国的角色,坚持所有国家平等,反对强权政治恃强凌弱。毛泽东和周恩来习惯性地宣布中国将永不称霸。尽管如此,中国很大程度上仍表现出一个传统大国的作用。当中国变成了核国家和对外援助国以后,它开始与苏联发生了冲突并在相互平等基础上与美国达成了政治上的谅解。
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建立持续良好运转的关系上遇到了困难。除巴基斯坦外,中国与其盟友的所有关系最终都以相互间的刻毒攻击而告终,而它与巴斯斯坦的关系则经常被描述成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历届中国政府与那些较为强大的或者对中国构成潜在挑战的国家打交道时都经历了特别的困难。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当中国在50年代与苏联首次结盟,接着与美国在70、80年代结盟时,它的国际实力和影响据说是最大的。而中国与小国的关系之所以遇到困难主要是因为它把自身看成是个仁慈的国家,并不十分理解小国家未必会用那种眼光来看待它。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核心特征是其领导人要求其他国家应该平等地对待它。中苏联盟破裂的潜在原因之一是,毛泽东认为莫斯科要求他本人和中国完全服从于苏联利益。同样,中美关系固有的许多问题源于中国人对美国优势的担心和其自身的脆弱感。有意思的是,在大三角时期(1971-1989年),尽管中国在军事上缺少可比性,但它却获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尊重;80年代中国处于被两个超级大国追求的引人妒忌的位置。
也许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难以与其大国身份相一致。首先是过去长达五千年直到19世纪西方侵入以前中华帝国神话般的黄金时代所遗留下的历史包袱。当时,惟有中国文明辉煌壮丽,中国帝位的执掌者统治着“天下万物”。当代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无法与其祖先相比。第二个理由是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列强和现代性进攻之下中国实力和文明的崩溃。那种经历引发了“耻辱世纪”的虚构,在那个虚构里,中国被描述为一个拥有恢复失去的领土和恢复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及尊严权利的受害国家。然而,中国领土要求的许多方面都是武断的,中国把当代概念塞入过去的关系中,而后者与建立现代世界的原则和实践不相容。
面向新策略
在天安门事件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些中国领导人声称西方试图利用中国与外界日益增加的联系来破坏和改变他们的制度,并称之为“和平演变”政策。鉴于此,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年代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10年寻求把其国家融入国际体系的做法非常惊人。毫无疑问,正是邓小平个人鼓励这些作为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的发展。在1978年至1995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这种显著的经济增长在很大方面是由外部经济关系推动的。在同一时期,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百分比从不到10%增加至56%多,整个外贸的增长超过了13倍,从210亿美元增加至2800亿美元。与此同时,随着西方的影响和大众文化通过港台传播而在中国大陆的日益流行,他们自身也从信息流动、设计、技术、管理甚至政治理念等方面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
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已从开始时从国际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寻求单边好处转向不断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并促进自己的观念对国际准则和制度的影响。8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并开始改变一些官僚做法以符合它们的惯例。作为世界银行的一个最大和最受欢迎的客户,它开始获得了大量的好处。但是在90年代,中国开始在多边外交背景下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甚至接受了新型外交。中国于1991年和1993年分别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核心地区性组织。尽管这两个机构只有通过合作和一致才起作用,不是约束成员国的裁决机构,但它们使得中国参与了多边外交的持续进程。1996年中国还加入了由学术界发起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它是东盟地区论坛“第一渠道”外交的非官方的、对话性的“第二渠道”,旨在讨论广泛的建议和思想以进一步促进东盟地区论坛的各项工作。
在本地区之外,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的一个广泛参与者,它保证遵守国际条约,这些条约在某些方面限制了政府的行动权,这在以前被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国修正了以前的“原则”立场,于1992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不扩散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公约。中国已同意不同程度地遵守限制其行动自由的那些规则,加入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中国已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然而,中国遵从这种更加国际主义的策略的深度依然不清楚。中国依然处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其最高层的决策过程依然不明朗。共产党依然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在这种意识形态上附加上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设想。共产党领导人鼓励爱国主义情感的灌输并从中得到了好处。中国领导人对相互依赖性依然持某种怀疑态度。
陆上放心海上麻烦
中国历史上是个大陆国家,它的注意力很大部分集中于亚洲内部,只是西方国家的到来才使海上方面成为关注的前沿。当然,毛主义的中国与邓主义的中国之间的区别之一是前者重视内地和自强,而后者重视沿海地区和与外界打交道。中国领导人处理大陆关系要比处理海上关系更为从容则反映了这种历史经历。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现代历史上空前的相对安全时期,它无更强大的国家进攻威胁之忧。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在处理东亚海上关系方面享有某种程度的战略自由,这一点由于其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所达成的一系列协定而得到增强。这些协定不仅解决了几乎所有突出的边境问题,而且也在相互裁军和建立全面信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协议把这些曾经引起中苏军队相互重兵对峙的争议地区变成了“一个和平、友谊和合作的地区”。
中国并没有寻求利用对其有利的地区力量平衡的重大转变为自己捞取利益。这在中国处理蒙古共和国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苏联解体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就与蒙古签署了协议并相互承认了疆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不断增强,两国关系达到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层面。中国与安理会几个常任理事国及日本和德国建立了伙伴关系。除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外,只有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被称为“战略”关系,而其他关系则被称为“全面的”或“建设性的”关系。中国认为,对于不断增加的多极化趋势来说,这些关系都是恰当的。它们全都同意相互平等对待并保证不针对第三方。
北京打算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牵制全球化和美国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多极化、不同制度和宗教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被视为一个没有对抗的“民主的”稳定的世界秩序最主要的内容。相互依赖不应该损害“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不应该存在国际贸易的歧视,也不应该有“运用货币和金融杠杆把政治经济条件加强加于他国的企图,因为这违背任何一个国家合法的民族利益”。既不应当坚持单边主义,也不应当试图“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大国还应该“制止旨在扩大现有的或者建立新的军事和政治同盟的努力尝试”。此外,中国和有关国家还强调“维持和加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特殊重要性,这在过去是现在仍是保持世界战略稳定的基石之一”。
但是中国的这种构想所遇到的麻烦是它对被该地区其他周边国家视为秩序基础的核心内容提出了质疑。这些国家认为地区稳定依赖于美国与东亚沿海国家所建立的一系列正式的安全同盟。这些同盟被看作对在东亚建立较为松散的安全形式努力的一个补充。美国的军事存在已被视为符合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各方普遍利益的具有稳定性的一种影响力,尽管中国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从这一观点看,美日同盟被迫继续存在下去极为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极符合日本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利益。否则,日本及其邻国就得被迫面对承担自身战略防卫责任所固有的各种问题。东南亚国家感到头疼的是中国对它们与美国同盟的压力是针对它们而不是针对美国。虽然中国的新策略仍然正在演变之中,但是中国处理其陆地和海上外围关系的策略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与美国的关系
对中国来说,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核心关系。作为一个惟一幸存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世界和亚太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美国在被中国定义为“综合国力”的所有方面都很出色。尽管预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相对其他国家将继续显著增长,但兰德公司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断定,美国将在亚太地区继续保存其“军事优势”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
虽然多年来中国报刊一直在讨论美国的相对衰落,但中国人做的比说的多。美国已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和外汇来源。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渴望被美国平等对待。美国被视为要求中国信守一系列国际规则(从与核扩散和其他形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有关的问题到人权、知识产权问题、贸易问题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主要压力来源。在有关朝鲜、日本、台湾、南中国海和南亚方面的安全问题上,美国的部署和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这个含义上讲,美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领居”。而且最为重要的正是美国有一个促使中国政治变化的干涉主义议程。
基于中国相对弱的影响力,中国需要有极为高超的外交技巧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政府需要外资和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来继续创造保持执政或者保持“稳定”所需的经济增长。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它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在它所在地区范围内的和平环境。美国是确保中国能够实现这两种情况的关键要素。也许正是对这种不对称性关系所固有的潜在依赖性的关注,使得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政策特别敏感。每当两国关系生产问题时,基于双方利益的分歧和双方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中国作出的典型反应是认为这将会导致两国关系的“倒退”或者下滑。但是华盛顿所关注的则是其与中国的不好关系可能会再次导致东亚的冲突,这是自二战以来唯一一个美国人打了两次大的战争的地方——再次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中国。美国参与中美事务的另外一个理由依然是心照不宣的,即它担心中国解体对其本身、该地区和整个世界所造成的后果。
结语
自20年前改革开放进程开始以来,中国大踏步地加入了现代世界。冷战结束以来,这些步伐已经加快了。中国领导人为在本地区范围内建立一个有助于完成中国发展经济主要任务的和平国际环境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但是,中国处理它与海上邻国的关系和处理引起争端的海上领土的方法使这些国家仍需要寻求美国的援助。中国尚未在国内达到足够的透明度以使它真正被国际社会接纳。此外,中国仍处于大的转变过程中,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尽管在外交及内政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中国依然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标签:中国学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