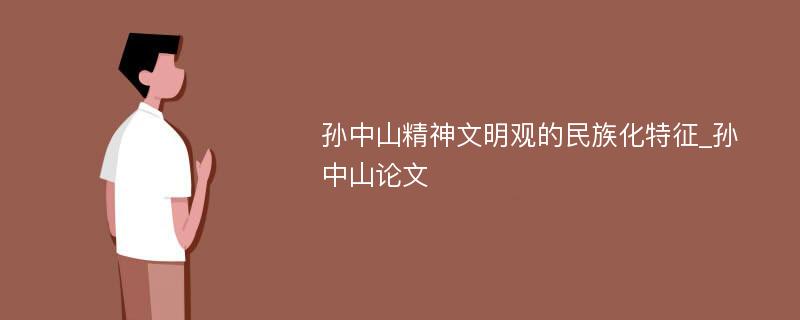
孙中山心性文明观的民族化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性论文,特色论文,孙中山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中山在他的新社会构想中,一直很重视近代心性文明(即精神文明)建设,常把它与近代物质文明建设并提,而其擘划的心性文明建设,又常以民族化为其思考前提、内涵,并与他构想的新世界理想相汇通,亦与一些世界著名志士和思想家有过互识互通互动互补,很有某种典型意义。
一
孙中山创作心性文明观的首要前提,是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已沦为世界列强的半殖民地。从文化角度看,西方文明随着殖民者侵华的深入而日益增多地输入,而这种文明既有先进的事物和思想,亦有有害于人们的奴化和腐败思想。这就给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十分迫切而又严肃的课题:为了改变中国落后、贫困、挨打的局面,必须忍辱负重地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但又必须剔除其糟粕。
孙中山家居久与外洋通商的珠江三角洲,早就得闻关于洋人的事情,因而渴望了解和研究外情。1879年(即他13岁那年),他随母远航到檀香山,开始接触西学和中国以外的世界,从此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西方教育。在进行革命期间,他常往来于欧美、日本、南洋诸地,接触资本主义文明,对西方精神文明亦早就饶有兴趣。他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里就提到他“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8页。)这是由于他深切感到我国虽有自己的文明,到近代已经“停滞不前”,“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所以,“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86页。);并认定“非求新知于世界, 断不足以救国”(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57页。),也就是说,“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使中国文明“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是“最守旧”的中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的关键。然而,“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 年版)第1卷,第277~279、327页。)。 孙中山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缺憾和腐败的一面,特别是有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他敏锐地指出:“近百年来,白种之物质进化,实超千古,而其心性进化尚未离乎野蛮,故战争之祸于今日尤烈”,表明“先进文明之国,每多为野蛮尚武之种所灭”(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5页。)。而且, 如果一味全靠外人提倡和输进现代文明,“这是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的大耻辱”。(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35页。)因此,决不能把西方文明全盘照搬,而是要进行鉴别和选择,并奋力追踪欧美,超越欧美,使之合乎中国国情,保持中国人的尊荣。
另一方面是孙中山反复认定的,中国是一个地广人众、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这使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在注重西方文化的同时,又认定“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其文明道德自必有胜人者矣”(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288、9、36页。)。 但由于他远瞩欧美,近虑现实,因而又使得他具有以下两个可贵取向。
其一,应取古为今用。他说:“且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孙中山之所以有此取向,除了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可资现代需要的精华,还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历时特长,传统思想习俗有其普遍的特深的根底,而孙中山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页。)。 这就使得他在清理和批判继承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如何因利乘便、易于为群众接受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免不了受到某种局限乃至出现消极反应,有时对传统观念消极面缺乏认识而予以接受;有时因还没有找到某种能够取代旧的传统的新思想观念而被迫迁就某种旧的传统观念,或做一些牵强解释。
其二,应取洋为中用,即力图把世界进步潮流和中国某些传统思想观念相应合。他说:“我虽然已广泛地了解西方和西方的科学,但仍然非常相信中国人”。他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内的西方许多学说、观念,都可以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找到源流或类似成品(注: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271页。)。他还宣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1页。)他对西方已出现的“人智益蒸”、“灵明日廓,智慧日积”、对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以及学问的日新月异,“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1、9、219页。)等方面多有赞词,他要人们重视“发现文明国家之新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页。)。但又明确表示:在心性方面,“不如彼者亦多”(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
可见孙中山有时出于强烈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而特别强调其心性文明观的民族化特色,言词未免失偏。究其实,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主导,不断推陈出新,对他加以肯定的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极力注入世界进步思想,作出新的阐释,以便在中国这样一个富于传统思想的土壤上,更易于开出洋为中用的奇葩异卉。不过,由于孙中山探首西方并想按照西方面貌来改造中国时,他又面对西方侵略与西方进步思想输入,西方思想理论、观念、制度与落后的中国现实,中国南北思想亦有一定差异等矛盾,迫使他瞻前顾后,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挑选武器时,常择取与中国某种传统思想相接应的东西,作出一些西学中源、中国失落,而西方国家却予接受并加以发扬的不全合乎实际的解释。
二
产生于上述前提的孙中山心性文明观的民族化特色,体现在孙中山构建心性文明观的中外合璧全过程中。这种中外合璧,就当时而言,就是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进步潮流和中国有价值的固有传统思想的结合。
近代民族主义潮流在中国的特征,有如孙中山所概括的:“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页。)就心性文明言,孙中山又特别强调它是“民族之正义之精神”。“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8页。)。这里讲的固有民族精神,就是要“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像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以恢复本民族的地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页。)。简言之,就是“不许外国人侵略中国,不做外国人的奴隶”(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0页。),反对洋奴思想和奴隶道德。他认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本来就“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它不但使“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因此,我们必须保存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固有道德,并藉此恢复固有的智能,恢复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246页。 )这里讲的“世界的新主义”,就是民族完全独立自由的“民有”,也就是孙中山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仰慕的华盛顿、林肯争取美国独立自由的主义。在解释上述中国固有道德的涵义时,孙中山显然注入了这一新主义的精神。比如:“忠”不是忠于君,而是“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效忠”;“仁爱”,“与孔子、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而且要学习外国人通过设立学校、开办医院等有利于近代化的措施来实施“仁爱”。他称赞中国人好讲信义,而日本等国却背信弃义,对中国、朝鲜发动侵略战争,使朝鲜丧失独立。至于爱和平,更是中国固有的极好道德,他尖锐谴责帝国主义者“都是讲战争”,主张“灭人的国家”。(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6~215页。)
与此相联系,孙中山把中国文化和亚洲文化称作“王道文化”,即顺乎自然力造成民族,“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即是“用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就是“行王道”;而欧洲近百年的文化,则“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即“霸道的文化”。用这种文化去压迫人、奴役人、征服别的国家就是“行霸道”。他严厉谴责英国之所以把领土扩张到全世界,成为“日不落”国,就是多年来使用战争等野蛮手段“行霸道”。他指出讲“仁义道德”、“正义公理”的“王道文化”强过“主张功利强权”、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文化”。前者使社会进步,后者使社会退步;前者使附属国心悦诚服,被称为“真文化”,后者则在被压迫者眼中“不当作文化,只当作霸道”。所以,我们要造成“大亚洲主义”,即联合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反抗欧美列强的侵略,“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而美国学者却荒谬地“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更要坚认“现在所提出的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得解放的文化”(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5~409页。)。他相信:“有我们以道德为基础发扬起来的优秀文化,如果再能谋求一个大团结,那么我们一定能有效地防御西力的东渐,能对付那以武力为基础的所谓西方文化”(注:王维耿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他甚至认为可以用中国和亚洲“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这里孙中山主要是出于反霸权反侵略和反对当时盛行于中国青年中的全盘西化思想的需要而发的议论,未免对中西文化的划分及其内涵功能作了非科学的、有失偏颇的解释,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也抬得过高。但他与一味尊崇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拒绝学习外国者显然不同。他又同时指出:在我们有了上述王道文化之后,“另外还要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7页。); 而且认为“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近代民主主义潮流与中国传统心性文明的关系,在孙中山的言论中亦其应若响。他表示:“彼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560页。)。他在决定选择共和政体为其奋斗目标时,即宣称:“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迄今“僻地荒村”之民,亦“皆自治之民”。(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172~173页。 )他认为中国人民早就很自由,如“唐虞的时候,尧天舜日,极太平之盛治,人民享极大平等自由的安乐”(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04页。)。他激励人民关心政治,改造人心,改造社会,提出“我国历史本素注意政治,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屡言于数千年前”,“故中国实为世界进化最早之第一国”。(注:《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32页。)“孔子且以政治为第一要务”,“况当今民权发达时代,人人负国民责任,人人负政治责任,而曰不谈政治,尤为大谬”。(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3页。)“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注: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34页。)是孔子的君子之道。孙中山亦把智、仁、勇作为军人精神教育的三要素,但他以民主共和精神作了重新阐释。指出智“在乎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即军人必须认清军人以卫国卫民为己责,为大利所在,坚决崇信三民主义,认定有主义与无主义战必胜无疑。“仁”包含“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其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救国救民。“勇”包含“长技能”、“明生死”,即掌握技能,不怕牺牲,勇于战斗,“为国效死”。其总目标是造成一凌驾欧美的“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亦即“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6页。)
孙中山很强调人须具仁心,待人和平,但他又是热衷于革命除暴的民主革命家。为阐明武力扫除残暴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他以孔子所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恶不仁者,其为人矣”(注: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2页。)为根据,驳斥梁启超对暴力革命的非议,指出:“革命的目的,以保国而存种,至仁之事,何嗜于杀”(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292页。)!
在对待人与人,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方面,孙中山指出:“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类当努力进行者”。这就必须去利己之心,“重于利人”;“则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之成为平等了,这就是平等之精义”。(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 第298~299页。)这就需要树立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的观念,就是古人所说:“天下者,是天下人之天下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1页;第10卷,第46页。)。他特别希望当政者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替人民来谋幸福”。不过他也指出:“近来经过了革命以后,人民得到了民权思想,对于尧舜禹汤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满意,以为他们都是专制皇帝,虽美亦不是称”。(注:《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62、322页。)这就是说,他希望在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塑造一种适应世界最新民主潮流、超越中国古代模式的更为平等、和谐的美满关系。
孙中山构建的心性文明观还与奔腾于世的社会主义潮流呈呼应之势。他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孔子的大同理想,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实行,“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页。)故他从1912年卸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后,即认定“中国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该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他吁请第二国际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注: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186页。)。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之精神”大体应与社会主义的心性文明观同一涵义。照孙中山看来,社会主义的关键是“循进化之理,由天演而至人为”。“天演”即“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主张人与人争,因是而生“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他认为“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社会组织之不善,虽限于天演,而改良社会之组织,或者人为之力尚可及乎?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其所主张,原欲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而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508页。)据此,孙中山主张通过平均地权、 节制资本、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制度以和平解决生产关系,消灭贫富之激战,“使不平者底于平”(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3页。);同时,十分注重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擘划,他号召:“我国主张社会主义之学子,当如何斟酌国家社会之情形,而鼓吹一种和平完善之学理,以供政府之采择”。他自己对此作出的审视结果是:
“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子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同立于平等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523页。)
“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页。)
综上并结合孙中山其他有关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潮流的推动下,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观达到了他可能具有的最高意境,即以中国古代出现过的最高精神文明意境为历史根据,以接纳欧美物质文明,大大发展物质生产、产品大大丰富为现实基础,贯彻人道主义、道德文明、公理良知,实现真正的广义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于是社会国家成为人民互助团体;道德仁义成为人人立身准则;天下为公、自由平等成为人人共同抱负,世界大同于以实现。这是对古代大同理想的改作、充实和提高,因它和激进的民主革命和改革相伴行,故趋近于可行性,即较前增加了较多实践性格。
为了促使人们提高精神境界,以便竭力为理想世界的实现而奋斗而献身,孙中山主张按照《大学》中所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他认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它可从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家族人手,“团结宗族造成国族以兴邦御外”(注:《孙中山全集》第9 卷,第217~250页。)。孙中山这样一种采用儒家教条来塑造人格、民族性、国格乃至获取治国、治世本领的方式,固然表明孙中山为了改造人和国家,还不能不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中国尚未出现新的组织形式的情况下,利用陈旧的甚至已是落后的原社会细胞组织,注入新的精神来规范人的言行,谋求发挥新的功能,取得新的效应。究其实,它和封建统治者用以灌输封建统治思想、培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有着原则的区别。诚然,这样一种对传统观念的迁就,也确有保存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家族宗族观念的消极性。
三
孙中山构建其心性文明观时,曾受到外国人士的关注和审评。特别是与孙中山处于类似地位的外国人士,此前或当时也在构建其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心性文明观,这就存在一个孙中山与有关人士互识互通和各自心性文明观相互影响、相互比较的问题,进入这一层次的探讨,将能更好地确定孙中山心性文明观的民族化特色的座标和价值。
对于欧美心性文明,孙中山固然强调其和东方文明有较大的差异,但也异中求同。
在欧美各国中,孙中山最推崇的是德国。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从我在世界上所见所闻来看,我认为,德国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我们现成的老师。德国与英国、美国及其他国家不同,它的一切都是极其认真地、系统地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创新,……。德国使一切都纳入科学体系中去。这恰恰就是我同一切传统决裂所需要的东西”(注: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中又讲到:“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正是德国,最注重用中国、印度的政治哲学,“去补他们科学之偏”。(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1页。)的确,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沃尔弗、康德、利希滕贝格尔,赫尔德等都曾赞美中国古代心性文明,认为“中国人的智慧自古以来遐迩闻名,中国人治理国家的特殊才智也令人钦佩”,孔子被称为“伟大的智慧的始祖”,中国人被视作“最贤明、最正直、最理智、最幸福的一个民族”(注:〔德〕贾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8页。)。莱布尼兹还认为“中国与欧洲相互补充,组成了一个世界文化;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中国盛行自然宗教,欧洲风行神启示的宗教。两者都迫切需要理解对方”(注:〔德〕贾瑞春编,陈爱政等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267页。)。黑格尔、马克思、梅林等都对古老中国的稳定不变社会结构不利社会发展方面提出否定意见,但他们或者如马克思那样对西方侵华进行揭露、谴责,赞扬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精神;或者承认中国是一个有民族特色、对世界文化有过巨大贡献的伟大民族;而且他们多把中国和印度以及一些东方国家作为一体来进行评析,对儒佛道在中国的连接亦予重视。孙中山在得出上述看法的时候,很可能已了解到上述情形,言出有因。特别是马克思,被孙中山尊称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之解决”的“科学派”“圣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1页。)。孙中山虽对其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及阶级斗争主张持有异议,但他认定:“一般讲社会主义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赞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8页。)。他们在重视解决经济尤其是分配上的平均问题的背后,是要建立一个真正平均自由而又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马克思曾经有条件地赞美俄国村社的“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认为“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孙中山于19世纪末20 世纪初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和俄国民粹派颇有交往,他于1905年5 月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也提出了利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吸收欧美文明的精华,“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年版)第1卷,第273页。)。可见,马克思和孙中山在以集体主义精神作为新社会精神支柱这一点上似存共识。
英国哲学家罗素,被孙中山视为罕有的“有很大的眼光”,称赞“中国文化超过于欧美”的大哲学家(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页。)。罗素也推崇孙中山为“中国激进主义的领袖,主张共和制度”,晚年奉行“开明的、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策”,“他要消除中国凄惨的贫困状态”,“希望恢复中国所丧失的独立”,“实际上得到了所有具有公共精神的中国人的支持”。(注:冯崇义:《罗素与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9页。)尽管他们在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上亦各有主张,但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艺术家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它包含着全人类应予珍视的价值,它“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他还认为中西文化可以互补,“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注:《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4页。)这和孙中山关于中西文化的估量和比较是合拍的,故孙中山引罗素为同道,赞赏他一到中国,就立即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较高的审评。
此外,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杜威,其经验自然主义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生活、行动、实践决定一切的观点(注:袁树涓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页。), 它同孙中山所主张的“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不知亦能行”以及把习练、试验、探索、冒险作为“文明之动机”等等强调实践的观点(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9~222页。),颇有相似, 故杜威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表示赞同时,孙以又获一国际知音而甚感欣慰”(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页。)。
在东方或半东方各国中出现的谋求民族解放的心性文明观,更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和嘉许。诚然,由于东方各国文化传统、习俗信仰、斗争理论和方式亦各有异,孙中山对这些心性文明观及其代表人士的看法和态度亦不全同,总的来看,则是求大同,存小异。这个大同主要是在共同面临的谋求各自民族解放情况下的主题——民族性。
当孙中山苦苦寻求中国二千年前“就具有的以正义、道德为基准的文化”却“不能战胜西洋近时才发生的以武器武力为主的无道义的文化”的答案时,经过俄国十月革命,他终于高兴地发现:“此次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俄国遂酿成一种良好风气,而此种风气传及欧洲,欧洲各国竟莫能抵抗”(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30页。)。照他看来,俄国已“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像这个情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握手,要和西方分家”(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 “他讴歌了苏俄否定西洋文化、以正义和人道为基础的文明”(注:王维耿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并认为俄国劳农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孔子希望营造的大同世界大体相同”(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36页。)。
孙中山在寻求中国心性文明观的东方盟友中,对印度特别注目。他说:“印度和中国之交通,自东汉时代已经开始,彼此以和平相往来,做学问思想的交换。彼此何等互相钦敬,互相爱慕,何尝有些微的冲突”。(注:王维耿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他对印度大文豪罗宾德拉纳特、 泰戈尔的景慕和亟欲交结的愿望,是20世纪20年代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泰戈尔一生以文艺为武器并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鼓吹复兴印度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推进民族解放运动。1924年4月,他为了“提倡东方固有文化的复活, 和亚洲民族的一致团结”应邀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发表了以复兴东方文化为主旨的演说,受到中国各方人士的重视。泰戈尔反对“完全依赖欧洲文明,全盘西化,而不顾自己特殊的文明与其价值”(注:转引自王聿均:《泰戈尔及其它》,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赞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创造了一个美的世界”;谴责西方对中国“任意地侵略、剥削和摧残”(注:《告别词》,《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主张“在东洋思想复活的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注:《晨报》1924年4月13日。)。它和其时孙中山强调恢复民族文化、道德、智能,以图振起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固有地位的主张很相契合。所以,孙中山虽和泰戈尔在斗争方式上不同,但他在写给泰戈尔的欢迎信中仍称赞他“不仅是一个曾为印度文学增添光辉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在辛勤耕耘的土地上播下了人类未来福利的精神成就的种子的杰出劳动者”(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0页。)。
亚洲的许多其他国家所呈现的心性文明观的民族特色,显然也引起了孙中山的重视。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造成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和东方专制主义并生的一神教,这在南亚、西亚更为突出,许多国家宗教政治化。19世纪下半叶以后,这些国家随着反抗外来侵略奴役的加紧和近代化的启动,出现了宗教改革,个别国家如土耳其甚至出现了废除宗教统治的世俗化改革。上述改革不仅和学习欧美的民主与科学技术相结合,而且在他们的宗教民族主义里注进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这样就使他们跳出了原来的狭隘的宗教政治文化观,而有与持其他信仰和政治文化观的人们在谋求国家独立和近代化方面找到结合点,特别是在反帝反殖问题上结成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或者是同气相求、相激相荡。而在中国,虽然儒家思想长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由于中国土地广阔,民族繁多,又很早和亚欧许多地区久有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所以中国很早就不是一神教或单一信仰,它具有文化和宗教的一定宽容性和溶合性,儒释道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多次渗合和新的熔铸。孙中山对这种情况可能有认识,故早就提出革命主义者“必须具有宗教上宽容的德”(注: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他尽量挖掘存在于各个教派的民族民主因素,乃至加以合成,以之激扬新的民族民主精神。他曾说:“士贵有志,有万世之志,有千年之志,有数千百年之志。如耶稣、孔子、释加牟尼,寿命最长,万世之志也”。(注: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甚至他给自创的“三民主义”亦以“行仁”来概括,而这种“仁”即前已提及的“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何谓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稣教,皆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即“所谓舍身以救世”。“何谓救人?即慈善家之仁”,即“抱定济众宗旨,无所吝惜”。“何谓救国?即志士爱国之仁,如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23页。)。他认为印度之不亡,在于存在佛教精神,他和印度甘地在斗争方式上显有区别,但他对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在不合作运动中所表现的民族不屈精神,和“用宗族团体做基础联成一大民族团体”以反抗外国压迫的做法表示赞赏。(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1页。)同时,他对土耳其、阿富汗、阿剌伯、埃及等国人民的奋斗精神也屡有称道。他希望保持回教在中国的地位来促进国际上回教徒的团结和共同奋斗,“现宜以宗教感情,联络全国回教中人,发其爱国思想,扩充回教势力,恢复回教状态”。其意图还在于以中国“不惟五族平等,即宗教亦平等”(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7页。)的形象昭示于世界。不过,由于中国宗教政治化较为淡薄,而孙中山又一贯放眼世界,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所以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观要较上述国家地区的宗教的,或浓厚地区性的心性文明观要显得更为顺应世界新潮流、世俗化,具有较多的大众性和科学性。
为广泛宣传中国人的现实斗争和精神面貌,孙中山曾拟办一英文杂志,“直接参加于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底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期得精神上,物质上之援助”,“排斥各种侵略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8页。)。此事虽未成,孙中山在亚洲志士的心目中仍享有崇高威望,印度志士尊称孙中山为“兼备孔、佛、耶之人格”的“亚细亚精神领袖”(注:伍达光辑:《孙中山评论集》,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版,第55页。)。
曾经受侮于西方列强而后又以侵略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为职志的日本,在孙中山眼中,是站在选择西方霸道文化抑或东方王道文化的十字路口上。对此,孙中山有过曲折的认识。由于中日同文同种常被日本侵略分子用作障眼物,与日本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半官方团体——东亚同文会,于1898年成立时即宣称:“日中韩三国之交往已久,文化相通,风教相同,情同唇齿,……岂与彼环宇列强之朝婚夕寇,互相攘夺可同日而语耶!”(注:〔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71页。)加之, 这些日本人士往往有“仗义勇为”的表现,对逃亡到日本的中国志士提供过一些帮助,使得陷入困厄中的中国志士常误引为同志和友人。孙中山也较长时间处于困惑中。他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华抱侵略野心,但又认为日本侵华是因受西方霸道文化的影响,可以通过陈明利害关系,使日本政府改弦更辙,实行中日和东亚联盟,共同对付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他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时,终于对日本上层深感失望,他殷切希望日本国民能提高觉悟,纠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倒行逆施,殷切指出“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 )验诸随后历史,此诚切要诫言。但这却遭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反对和蓄意歪曲。他们有的亦“主张应把儒家,佛教作为日、中、印三国提携的连接点”(注:〔日〕藤井昇三:《孙文之研究》,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219页。), 但他们是把儒家的“忠”字作为倡导的主点,使它与对外扩张的武士道精神相结合;而对被侵略者则用儒家的“恕”、“中庸之道”等等进行说教。孙中山1924年访日时反复阐明他的坚决反帝反军阀方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却发表社论,表示反对,说什么“切望自重,共同以孔夫子之教‘中庸’二字为经国之策”(注:〔日〕藤井昇三:《孙文之研究》,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210页。)。
综上可见,孙中山心性文明观的民族化特色,源出于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而又不甘世界列强奴役和压迫这一民族特点。这一特点也是许多东方国家如印度、波斯、阿刺伯等国大体同具的;而在新形势下,中国和许多东方国家,又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近代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进步潮流的促动,这就使得孙中山和其他东方国家志士的心性文明观大同小异或质同形歧;孙中山又以其思想、活动、建树及其影响,被公认为东方各国志士中的杰出代表,并且彼此间多有协作、互动或相互影响。因此,上述民族化特色既显示中国的特性,又具有东方国家的某种共性。
标签: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孙中山全集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