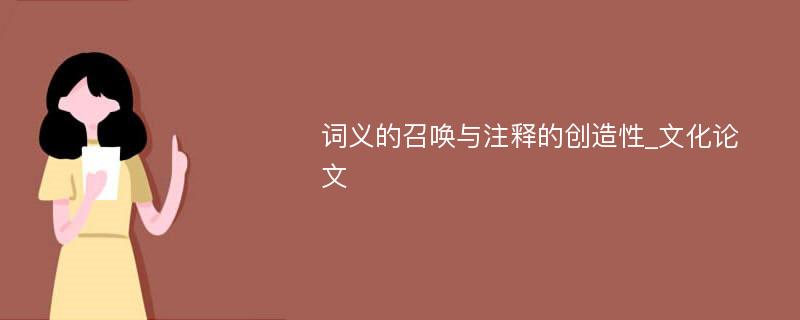
词义的召唤性与训诂的创造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义论文,创造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4-0100-07
引言
无论是研究汉语历史词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训诂学还是探讨词汇与训诂的互动共变规律,首要的工作似乎都应是深入阅读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于文化典籍的注疏解释,从中发现问题,并且获得解决问题的启示。而一当我们认真阅读古代文化典籍和历代学者所作的解释,总会见到如下几类词汇现象和训诂现象:
《诗经·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毛亨《诗诂训传》: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
朱熹《诗集传》:静者,闲雅之意。
《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朱熹《论语集注》: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白虎通》: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
《论语·里仁》: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王弼《论语释疑》: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
朱熹《论语集注》:贯,通也。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
王念孙《广雅疏证》:一以贯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云:“为之贯之”。贯亦为也。《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奉承贯行”。贯亦行也。
阮元《研经室集》: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
《论语·里仁》:以约失之者鲜矣。
何晏《论语集解》:奢则骄溢招祸,俭约无忧患。
朱熹《论语集注》: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
汪恒《四书诠义》:约者,束也。内束其心,外束其身,谨言慎行,审密周详,廉卑自牧,皆所谓约。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朱熹《论语集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极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为常。二说相辅而成。
《庄子·齐物论》: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郭象《庄子注》:夫成毁者,生于自见而不见彼也。故无成与毁,犹无是与非也。
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成毁,物之相戾者也。然无毁则无成,无成则无毁。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毁也;以之作室,则为成物矣。
《庄子·德充符》: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於心者也。
成玄英《庄子注疏》:与物仁惠,事等青春。
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随所寓而皆为乐也。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应物之际,春然和气。
宣颖《南华经明》:随物所在而皆同游於春和之中。
《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成玄英《庄子注疏》:寄言诠理,可传也;体非量数,不可受也。
释德清《庄子内篇注》:以心印心,故可传可得;妙契忘言,故无受无见。
在这几类现象里,诸如“静、学、贯、约、庸、春、成、毁、传、受”等词,都是基本词汇,都是常见用法,看上去不难理解。然而,历代学者却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它们大加训诂,并且由此形成分歧的意见和不同的议论。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一系列问题:这些常用词的意义有何深奥之处,值得学者们如此关注,并且为此各执己见?这些基本词的意义有何特别功能,使得学者们锲而不舍,并且由此阐发出一些精粹的议论?而学者们的这些训诂各自在词义的特性上有何根据?各自在议论的阐发上有何价值?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感到自己现在所知道的词汇理论和训诂学理论不太够用,有待突破。为此,本文试图提出“词义的召唤性与训诂的创造性”的理论范畴,希望首先能够藉此探讨并从理论上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进而能够以此为词汇学和训诂学乃至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增设一个小小的视角。
上篇 词义的召唤性及其形成与功能
词义的特性,是当代词汇学理论关注的问题。但是词义重要特性之一的召唤性,却不见有人探讨。我们所谓词义的召唤性,是指词义由于其结构中义素的空缺因而对于运用者和解释者能够形成一种吸引力、激发力使之填充其空缺义素的基本特性。如果说,词义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那么,词义的召唤性则反映了人在与世界关系中的主体精神。譬如动词“约”有“约束”一义,指称“限制使不越出范围”的行为。从一方面看,其词义是实在的,指称特定的行为;其词义是明确的,所指称的行为不同于其它任何一种行为;其词义结构包含着“限制”、“使不越出范围”等义素。但从另一方面看,其词义又是有空缺的。因为作为一种行为,“约”必有其对象、方式、程度等等,故而其词义结构中缺少“限制的对象、限制的方式,使对象不越出的范围”等等必要的义素,只有将它们填充出来,动词的“约”的词义才是具体的、完整的,才是可以用于具体表述、可以给出具体解释的。也就是说,一当运用,就能发现动词的“约”的词义其实是一种半实半空的“实空结构”,它具有促使运用者和解释者填充其义素空缺的基本特性,亦即召唤性。当人们在特定语境里运用动词“约”时,心目中自然有一种具体的“约”,它自有其特定的对象、方式、程度等等,并且总要将这些要素填充到“约”有词义结构之中,并运用种种表达手段将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来。例如孔子在说“以约失之者鲜矣”时,他已经表明,其“约”的对象是自身,“约”的方式是修养。于是,“约”的词义的“实空结构”依据其意向有所填充而变为“意向结构”。可是,孔子对“约”的方式的说明是不够充分而明确的,更未说明要使自身不越出何种范围,因而仍然在“约”的词义结构中留下了几处空缺。这种仍有空缺的“意向结构”,还是具有吸引人、激发人填充其空缺的召唤性。当解释者在特定语境里解释动词“约”时,总是既要填充其词义结构中本有的空缺,又要填充孔子在“意向结构”中仍然留下的空缺。正是在这种填充的效果中,解释者常常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体验。例如,汪恒解释“以约失之者鲜矣”时,他超越了何晏和朱熹的解释,进而填充了“约”的对象:“内束其心,外束其身”;填充了“约”的方式:“谨言慎行,审密周详”。填充的效果,是使孔子的这一理论有了更具体的内容和可实践的品格,同时也彰显出他自己的思想个性和解释的创造性。
又如名词“春”,其本义为“春季”,指称“一年中的第一个季节”。从一方面看,其词义是实在的、明确的,甚至可以用于计量。然而,正如语言哲学大师卡西尔指出的:语词“从未简单地指称对象,指称事物本身;它总是在指称源发自心灵的自发活动的概念”,亦即人们对它所指称的事物的体验和认识。[1](p58)而从这一方面看,“春”的词义结构就不可能不是开放的,就不可能没有义素空缺。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以农耕立国,特别关注春季,对于它的体验和认识是永远说不尽的。那些基本的共同的认识固然能够能以约定的方式凝聚在名词“春”的心灵概念之中,而那些因人而异、因群体而异的认识,则必须在“对话”活动中分别由运用者和解释者填充到“春”的心灵概念之中。这就是“春”的词义的召唤性。庄子在说“与物为春”时,是用名词“春”把春季引度到“对话”活动之中,巧妙地将自己对于春季的体验和认识融入其词义的结构,并且以此隐喻哲人真人的德行,从而告诉人们:凡是德行高尚的人,其心灵总能随物所在保持春天促使万物生发的那种生机与和悦。而历代的解释者,在解释这一语境里的“春”时,总是从各自的视界出发,即要填充其词义结构中原有的空缺,又要填充庄子在其“意向结构”中留下的空缺。成玄英所谓的“仁惠”,林希逸所谓的“为乐”,释德清所谓的“和气”,其实都是他们各自对于春季的认识与庄子的认识相互融合的产物,并且由此显示了他们各自解释的创造性价值。
汉语词义大都具有“实空结构”,具有召唤性,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与规律,自有其形成的基础和根据。
第一,可以从造词的角度看词义召唤性的形成。
语词指称的通常都是一类事物;分类是人类语言的根本特性,更是语词形成的基本前提。而分类,主要有两个程序:首先是根据社会生活的特定需要和事物本身的显著特征,将某种事物从其所存在的事物丛集(或整体)中分立出来,使之呈现;然后将分立出来的事物与其它有具相同显著特征的事物联系起来,分归一类。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某种事物浑沌地存在于事物丛集(或整体)中时,它与其中的其他事物原本有着多种关联,这才是存在的真义。而当人们将某种事物“分类”出来时,就暂时搁置或忽略了它与其他事物的多种关联,这种暂时的搁置或忽略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使某种事物分立出来、分归一类。可是与此同时,它也使指称它的语词的词义结构隐隐留下了义素空缺。而当运用语词指称某种事物时,而当通过语词认识某种事物时,人们又必须重视和复现它与其它事物的多种关联,积极地填充词义结构中的义素空缺,否则,他就难以真正有效地指说和认识该种事物。譬如动词“学”,指称学习活动;而学习活动,必定有其主体、对象、方式和效果等,必定与其它活动密切相关。但在创造这个词的时候,在这个词处于贮存状态的时候,所有这些都被搁置起来,在实际上造成了“学”的词义的结构中的义素空缺,亦即必然的不完整性,而有待人们在运用或解释时予以填充。这就形成了它的词义的召唤性。
词在指称事物的同时,还要表达关于该种事物的心灵概念。因此,人们将某种事物“分类”出来而为它命名造词时,还必须概括它的显著特征,以形成关于该种事物的心灵概念,心灵概念是词义的主体部分。而人们进行概括,又总是立于特定的角度,运用特定的方法,根据自己的体验,往往以偏概全,使事物的一些特征得到呈现和敞亮,另一些特征受到忽视与遮蔽。好在他并不断然以为自己某一次的概括成果就是事物全部特征的完整而权威的表现,而是为以后的概括、为他人的概括留下了开放性的广阔余地。因此,语词所表达的心灵概念,亦即词义的主体部分,总象是具有可容纳性的筐篮,既有实在的部分,也有空缺的部分,既有共同的部分,也有差异的部分,常常凝聚着人们关于该种事物的共同性的理性认识成果,却往往空缺了人们关于该种事物的个体性的感性认识成果。幸而,人类总有一种积极的求知精神和彰现自我的精神,乐于不断地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深化关于事物的心灵概念,勤于在运用或解释语词时填充其词义的义素空缺,使词义具体化、个性化。这也是汉语词义召唤性形成的一种基础和根据。例如“庸”与“用”同源,本义为“运用”,引申义有“可用”、“平常”等。单以“平常”而论,它值得表现的显著特征是什么?在充满实用理性的中华先民看来,“可用”的往往就是“平常”的,“平常”的常常最为“可用”。这种概括似乎是以偏概念,却也抓住了关键。对此,孔子予以认同,但同时还认为,“平常”的既是“可用”的,也是可贵的,正如人的德行。当他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时,是以自己的独特体验填充了“庸”的词义结构,使其心灵概念具有儒学宗师的个性色彩,并以委婉的方式在句中表达出来。
第二,可以从用词的角度看词义的召唤性的形成。
人们在对话中运用语词,其实质是将语词的指称对象予以具体化之后引渡到特定的语境之中,使之与其它语词所引渡的指称对象相互关联组合,以便表达自己对于它的认识或意向,引起对话者对它的关注或行为。其中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深究:第一,用词者并非完全按照已有的既定规则运用语词,而是将其词义具体化,使之由普指、泛指转化为特指、专指,以引渡特定的指称对象,并把自己对于其特指对象的体验以及意向填充到语词的词义结构之中,形成新的“意向结构”。第二,用词者运用语词以表达意义,或以直白的方式,或以修辞的方式,或者较多地交待了与其特指对象相关联的东西,或者较多地隐含着与其特指对象相关联的东西,总会使其词义的“意向结构”仍然留有或多或少的义素空缺,以待解释者的填充。第三,在对话活动中,解释者通过解读特定语境中的语词以面对它所特指的对象,既会观察用词者交待了的与之相关联的东西,也会探寻用词者隐含着的与之相关联的东西,既会了解并参用用词者所表达的相关认识和体验,也会激起并形成自己的相关认识和体验,进一步填充语词的词义结构,并应邀发出相应的自己认为是适当的行为。这就充分说明:一当进入对话活动中,语词词义的“实空结构”和召唤性就空现出来,对于用词者,对于解释者,它都能形成一种吸引力、激发力,使之填充其义素空缺。
例如动词“传”,指称“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的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交给”必有其内容,它可能是具体的物件,可能是较为抽象的技艺,还可能是更为抽象的思想;“交给”必有其对象,他可能是同时同地的,可能是同时异地的或异时同地的,还可能是异时异地的。而“交给”的东西不同、对象不同,其方式与效果必然也随之不同。在现实的言说中,所有这些,都必须召唤用词者和解释者去具体化,去填充它,否则,对话就不能顺利地有效地进行下去。哲人庄子也不例外。他在宣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时,首先是将“传”的词义予以具体化,使之特指把对“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的“道”的领悟交给他人的行为,然后是将自己对于这种行为的方式与效果的认识填充到“传”的词义结构之中,并在“传”与“不可受”而“可得”的组织中暗示出来,让对话者由此进行重新体验。如此看来,在运用动词“传”的过程中,庄子既利用了它本有的词义召唤性,又造就了它新生的词义召唤性,从而也就使我们加深了对汉语词义召唤性的认识。
汉语词义普遍具有“实空结构”,具有召唤性,既如上文已经论述的,自有其形成的深厚根据,也如下文将要论述的,自有其语用的重要功能。
语言是人的语言,人是语言的人。语词是指称对象的,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然而,语词能否指称每种想要指称的特殊对象,语言能否表达每种想要表达的特殊思想感情,却又一直是困扰许多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的繁难问题。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魏六朝时代,中国哲人学者就持续地进行着“言意之辩”。《老子》开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秋水》亦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易传·系辞》明白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而晋代学者欧阳建特撰《言尽意论》揭示相反论点:“欲辨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这种论辩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在西方也同样精彩。譬如黑格尔就强调:“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2](p306)。我们认为,考察分析词义召唤性及其功能,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因为,词义是具有“实空结构”的,故而既能“表达普遍的东西”,凝聚人们关于其指称对象的共同性认识成果,又能在特定语境中促使用词者,或者将其具体化,以表达他所想的“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或者使其充实化,以填充他关于其指称对象的个体性的独特体验。其结果,是“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物之精”者亦能表达。这就是词义召唤性的功能的重要表现之一。即如上文已例举过的名词“春”,原本也是“表达普遍的东西”,但因其词义具有“实空结构”,具有召唤性,所以使用庄子能够在“与物为春”的语境中,将自己对于春季的独特而精妙的体验填充到筐篮式的词义结构之中,并以此隐喻哲人真人的德行,从而表达出他所想的“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汉语词义召唤性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促成训诂的创造性。本文下篇将再作论述。
下篇 训诂的创造性及其根据与效应
中国的训诂和训诂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哲人学者在“哲学突破”之际对于文化典籍的创造性解释。到了唐代,训诂大家孔颖达在总结一千多年的训诂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诗经正义》开篇)。他所谓的“通异辞”,是以今语解释古语,以通语解释方言;他所谓的“辨形貌”,是以形象的语言解释和描绘典籍的句、段、篇的深厚意蕴,实现对其作者寄寓的思想感情的阐发;而他所强调的,则是“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诂”与“训”,都是为了“解释”,也都构成了“解释”,这是训诂和训诂学的要旨与精神。在以后又一个一千多年的文化学术进程中,孔颖达首创的简明而深刻的定义,得到了中国广大学人的普遍认同和阐释发展。笔者不敏,也因此先后在拙文《二十世纪训诂学研究的得失》和拙著《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明确认定:训诂是对文化典籍的解释,重点是对文化典籍词语的解释。而训诂学则是古典解释学的基本部分,主要研究文化典籍解释的目的、方法、原则、效果及其发展规律。本文所谓训诂的创造性,是指解释者怀着特定的目的从特定的“视界”出发,在解释文化典籍词语的过程中,回应词义的召唤性,与作者的视界相融合,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精神和创造性效果。譬如动词“贯”,指称穿连诸物以成串集的行为,其词义结构中留有“穿连的目的、对象、方式、功能”等义素空缺。孔子宣言“吾道一以贯之”,在其词义结构中填充了“对象(道)”的义素,留下了“方式、功能、目的等义素”空缺。对此,玄学创立者王弼,基于自己建构的“举本统末”理论,从自己的视界出发,从功能的角度有所发现而填充了“贯”的义素空缺,将其解释为“统”,揭示了孔子心目中“贯”的功能,进而阐发出“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政治哲学。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本着自己建构的“理一分殊”学说,从自己的视界出发,从方式的角度有所发现而填充了“贯”的义素空缺,将其解释为“通”,再现了孔子心目中“贯”的方式,进而阐发出“浑然一理,泛应曲当”的本体哲学。而乾嘉朴学大师王念孙和阮元,怀着总结传统学术的责任感,从自己的视界出发,从目的角度有所发现而填充了“贯”的义素空缺,将其解释为“行”,突出了孔子心目中“贯”的实践目的。他们的解释,都回应了“贯”的词义召唤性,三者非但并不相互抵牾,而且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既大致符合孔子的“立言本意所向”,又多少超越了孔子的“立言本意”,对各自当下的现实情境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后世学人颇具启迪作用。如果将它们联贯统一起来,则正好能使“贯”的意义得到充实、深刻和完整,因而使人们乐于认可其创造性精神和创造性效果。又如林希逸在解释庄子的卮言“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时指出:“成毁,物之相戾者。然无毁则无成,无成则无毁。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毁也;以之作室,则为成物矣。”这一解释,既是在探寻庄子的话中之话,又是在抒写自己的思索成果。你有理由说它溢出了“成、毁”二词的本来意义,超出了庄子用词的本来意义;但你却不能不承认只有如此解释,“成”与“毁”的本来意义才是更加清晰、更加完整、更加深刻的,庄子的本来意义才是更加突出、更加详细、更加富于哲理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庄子所欲言而未言的“成”与“毁”的辩证关系,使学人获得了更具体、更有力的哲学启示。这就是我们所阐扬的训诂的创造性,它反映了解释主体在其存在方式中焕发出来的主体精神和人生价值。
自从孔子在创立儒家理论的过程中倡导并践行“述而不作”实即“寓作于述”的文化经典解释精神以来,中国历代哲人学者都极为重视文化经典的训诂亦即解释,总是力图立足新的社会现实,面对新的思想课题,从古老的文化经典中阐发出新颖的思想理论,尽可能地促进经典解释富于更大的创造性,以便在新的时代里实现新的经世致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训诂亦即解释的创造性,也就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规律,成为两千年来文化经典解释的生命活力,并且自有其形成的根据与实际的效应。
第一,可以从词义特性的角度看训诂创造性形成的根据。
本文上篇已经具体论证,汉语语词的意义大都具有一种“实空结构”、“意向结构”,并且由此形成了召唤性,这正是训诂创造性形成的主要根据之一。试想,“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中的“传”,如果没有在选词过程中和用词过程中留下“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义素空缺并因此而形成召唤性,成玄英赁籍什么解释为“寄言诠理”?释德清有何根据作出“以心印心”的解释?当然,汉语中也有些语词,其词义结构中原本就很少留有义素空缺,自然也就难以对用词者和释词者形成显著的召唤性。汉语中也有些语词,进入了特定的语境之后,经过用词者严格地具体化,使它所指的范围明确,所表达的概念严整,填充了它的几乎所有的义素空缺,并予以充分的表达,自然就更难对释词者形成显著的召唤性。这些语词的词义特征,都不能促成训诂的创造性。科学论著中的名词术语大都如此。例如《墨子·经说》有云:“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又如《内经》有云:“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在这类句子中,词的词义结构中很少留有义素空缺,解释起来也就难以众说纷陈,各有所当。譬如对于“或告之,传也”中的“传”,就不可能作出“以心印心”的解释。另外如“以约失之者鲜”的“鲜”,“其至矣乎”的“至”,“无为无形”的“形”,也都如此类似。所有这些,都从一个相对相反的角度说明,作为训诂对象的词义的“实空结构”及其召唤性,是训诂创造性形成的主要根据之一。
第二,可以从训诂活动本身特性看训诂创造性形成的根据。
作为对文化典籍的解释,训诂既是文化典籍存在的方式,也是解释主体存在的方式。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研究成果已表明:解释者与一般人一样,总是社会地、文化地、历史地存在着的,由社会文化实践形成的价值取向,总会转化为特定的知识、情感、观念、意愿和思维方式等等,充实着解释者的“主体认识图式”,形成了他的“社会文化视界”。在解释过程中,社会文化视界往往决定了解释者解释典籍文本的目的、角度与方法,主体认识图式常常发挥着设定对象的选择功能、整理信息的规范功能和形成认识的解释功能。解释者自然十分关注典籍作者寄寓的思想感情,探寻典籍作者的“原初视界”,考察典籍文本的“意义蕴含”;但也同样关注作者所寄寓的、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对于现时代、对于他自己的启示价值或借鉴作用。这就是解释者在“文化视界”的基础上形成的“期待视界”。文化典籍及其词语的解释过程,其实是解释者的视界与创作者的视界以及典籍文本的蕴含对话、交流以生成“意义”的过程。而所生成的“意义”,亦即解释的成果,则是解释者的视界与创作者的视界以及典籍文本的蕴含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而共同创造的产物。这诚如中国古典解释学大师朱熹强调的:“读书须是虚心平气,优游玩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朱子大全》卷6)。正是在这里,滋生出训诂亦即解释的创造性。譬如朱熹,以重铸理学精神为己任,倡导“学者为己”,强调“内圣”事业,主张学人必须以后觉而效先觉,“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因此在他看来,“学而时习”的“学”就该解释为“效”,即“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而乾嘉学者刘宝楠,则以总结传统学术为己任,主张回到原典、强调考据作用,重视对儒家经典的领悟。因此在他看来,“学而时习”的“学”最好解释为“觉”,即“以觉悟所未知也”。
解释者解释文化典籍当然必须凭藉一定的解释方法。对此,中国传统训诂学非常重视,总结出了著名的形训、声训、义训三大方法。然而我们应该正视,这三大方法其实远远不是训诂亦即解释文化典籍的全部主要方法,而只是训释文化典籍的词语的方法;甚至也不是训释文化典籍词语的全部主要方法,而只是训释文化典籍词语的基础性方法。即使仅以训释词语而言,在这三大方法之外,还有更重要、更高级的方法,那就是乾嘉训诂学大师戴震总结并倡导的:“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相接以心”(《沈学子文集序》);“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古经的解钩沈序》);“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於千载之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郑学斋记》)。拙著《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曾经指出,戴震所总结的训诂亦即解释的方法,既符合两千年以来的实际,又开拓两千年以来的新境。“从其解释方法论的运作方式来看,与经典文本结构的‘字——辞——心——道’相对应,它以‘离词——辨言——以心相遇——闻道’四项工作相衔接,相贯通,层次分明,逐层上透。并且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既重视‘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又强调‘得其心志则可以通乎其词’,努力使‘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过程互相结合。”[3](p445)这才是中国训诂学的最高解释方法论。它强调,“离词辨言”亦即解释词语,不仅需要形训、声训、义训,而且必须与“以心相遇”贯通起来,从而达到“得其心志”以“终乎闻道”的最高目标。而戴震所推重的“以心相遇”、“得其心志”是一种心理解释,它本乎孟子首倡的“以意逆志”,继乎朱子拓展的“唤醒体验”,又加以新的系统化,在一定意义可以与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高扬的“视界融合”理论先后辉映。它也应该而且可以用于语词解释,当它与词语解释一般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就滋生出训诂亦即解释的巨大创造性。仍以“学而时习之”的解释为例:对于同一语境中的同一个动词“学”,朱熹解释为“效”,刘宝楠却训诂为“觉”。如果仅仅局限于形训、声训、义训理论,就不能对此作深入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而在我们看来:首先,这是他们运用声训的成果。“学”本来就是有“效”有“觉”,三者意义相通;“学”与“效”匣母双声,宵觉旁对转,“学”与“觉”匣见旁纽,觉部叠韵。三者应该视为同源词。其次这是他们“以心相遇”的成果。朱熹推重“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因而从中看到了“效”;刘宝楠强调对儒学原典的领悟,因而从中看到了“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再次,这是他们再创造的成果。人们没有理由否认这两种解释都是既符合孔子“立言本意所向”,又拓展了孔子“立言本意所向”,而且对后世学人具有启示作用。因此,它们的存在是“合法的”,有价值的。
文化典籍及其词语的训诂亦即解释普遍具有创造性,既如上文已经论述,自有其形成的深厚根据,也如下文将要论述的,自有其历史的显著效应。
中国古代原创性、经典性的文化典籍,大都创作于春秋战国那个令人神往的精神“轴心时代”,其中记录了古代哲人学者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开创性思考,揭出了许多我们今天仍然必须进一步思考的基本范畴,有其深厚的原初意义。但其原初意义却又不是封闭的、固定的整体。历代哲人学者感于现实需要而解释文化经典时,总是从自己的视界出发,努力将自己所理解、所认同的原初意义予以阐发,引入当下的现实情境之中,使之对于现实情境产生影响,并与现实情境相互协调。于是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总是在“通经致用”的文化氛围中,不断地被历代解释者有所选取、有所修改、有所丰富、有所发展,永远处于一种不断开放、不断生成、不断释放影响的过程之中,因而形成了一种不断产生效应的历史。这种“效应历史”体现了训诂亦即解释的巨大的、持久的创造性。正是训诂亦即解释的这种创造性,使民族文化经典能够跨越各个历史时期而现实地存在、永久地流传,使文化经典的意义得以进入各个历史时期而不断地丰富发展、永久地产生效应。如果深入了解一下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发生发展的契机,我们对此都不难理解。文化典籍的解释是如此,其中文化典籍词语的解释也具体而微,大致如此。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训诂亦即解释的创造性的历史效应。
具体就文化典籍词语训释的创造性而言,其历史效应既表现在语言层面上,如词义的丰富和引申,词语的派生和发展;又表现在“意义”层面上,如对理论范畴所产生的影响,对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影响。限于篇幅,对于比较容易理解的前者不作具体论证,对于较难理解的后者也只试举一例说明。据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焦氏笔乘》记载,北宋理学家李彦平曾经讲述一段亲身的经历:
辛丑春同试南宫,仲修中选,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伤,姑归读书可也。”某意不怿。仲修曰:“公颇读《论语》否?”即应之曰:“三尺之童皆读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即知读此,且道‘学而时习之’以何者为‘学’?”某茫然不知所对。仲修徐曰:“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既欲学圣人,自无作辍。出入超居之时,学也。饮食游观之时,学也。疾病死生之时,亦学也……”某闻其言,顿若有悟。[4](p4)
赵仲修解释动词“学”,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填充其“实空结构”,用自己的新颖理解劝勉学人,使“学”的词义有新的拓展,使学人由“茫然无知”而“顿若有悟”,并且将所悟引入自己的社会实践。显然,他的解释,不仅表现出词语训释的创造性,而且获得了这种创造性的现实效应。至于李彦平的“顿若有悟”,也应是一种新的创造性解释;他将所悟贯彻到自己的实践,引入到自己的著作,也应是一种新的现实性效应。后来朱熹以“效”释“学”,或许是对此有所总结和借鉴,终于形成了一种效应的历史。
收稿日期:2002-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