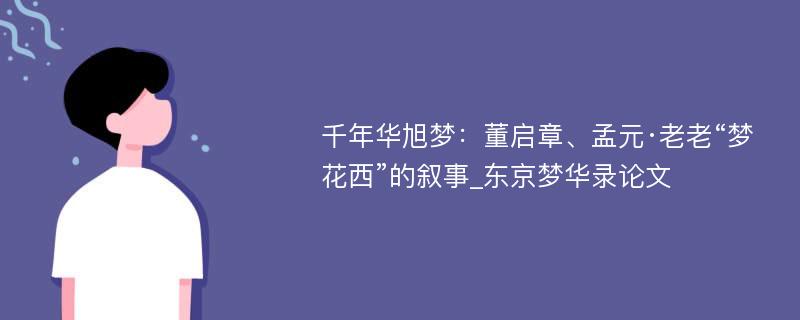
千年华胥之梦:董启章、孟元老“梦华体”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老论文,之梦论文,年华论文,华体论文,董启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1127年1月,来自北方的女真族渡过黄河,攻陷北宋(960-1127)帝都汴梁,掳走徽宗、钦宗二帝,并皇族、后妃、官吏及超过十万平民。这一事变,史称“靖康之变”,不仅王朝覆灭,也造成民族大迁徙。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是为南宋(1127-1279)。
公元1997年7月,英国政府将香港交还中国,结束鸦片战争(1840-1841)以来一百五十六年的殖民统治。香港“回归”是20世纪末的世界大事,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讯号。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中国政府承诺“五十年不变”。
这两场政治事件相隔八百七十年,除了各自见证时代兴亡的意义,似乎难以引起更多关联。但历史和记忆的千丝万缕,哪里是“宏大叙事”所能完全涵盖?借着书写形式的实验,前现代与后现代、南渡与回归,末世与盛世可以形成奇妙的对话,也凸显历史、叙事、虚构间的辩证关系。
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香港作家董启章的《梦华录》、《繁胜录》就是这样的例子。《东京梦华录》追记北宋覆亡前汴京的一晌繁华,早已成为此类写作的经典。董启章则在“回归”前后,以《东京梦华录》作为蓝本,为香港的未来预先写下一系列备忘录。①董启章故事新编,自然不乏后现代式的谐仿意图,但比起一般游戏之作,他显然对历史——不论过去与未来——更多了一分深思。他的作品不仅观照世纪末香港现象,也对《东京梦华录》的时代氛围投射新的认识。
董启章承袭了孟元老的汴京想象,打造了他的V城——维多利亚城。这是他心目中的香港,却比现世的香港更为靡丽魅惑,因为它有千年古都汴梁作为衬托。无论就崛起背景和历史位置而言,汴梁和香港都截然不同,董启章却看出其间诡异的重复性。靖康之变以后,汴梁的繁华一去不返;回归以后的香港号称“五十年不变”,但之后呢?从汴梁到香港,由绚烂到寂灭,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仿佛一场“华胥之梦”。由“城市考古”进入历史记忆的现场,这是董启章叙事的开始。
《东京梦华录》成书于绍兴十七年(1147),作者孟元老背景不详,但就其自叙,我们得知他在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1102-1125)居于汴梁,靖康之变后流寓江南,遂终老他乡。南渡以后,孟元老遥想汴梁二十三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生活,不禁有了恍若隔世之感。他于是援笔为文,记录汴京风物点滴:“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②
《东京梦华录》借文字所要留驻的不只是一座城市的经验,也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汴梁曾是上一个千禧年间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盛况空前。世变之后,对避居江左的人士如孟元老等,回忆昔日时好景成为日常生活的仪式。然而只不过二十年间,汴梁的印象已经开始模糊,后生之辈对这座城市的往事或流于道听途说,或者甚至无所关心。③孟元老的忧伤因此是双重的,他对已经失去的汴梁固然怀抱不堪回首之情,对行将失去的汴梁记忆更有着触目惊心的焦虑。在一切终将陷落于虚无的阴影下,他转向书写,借以寻求留存记忆、救赎时间的方式。
《东京梦华录》共十卷,所述汴京景物包括京畿城池河道桥梁建设、皇宫内外官署衙门、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民风习俗时令节日、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几乎无所不包。全书细腻琐碎,并无微言大义可言,但唯其如此,我们反得自物质生活的点滴流洗,遥想当年士子庶民的耳目口腹之乐、犬马声色之娱。这些官能的震颤也许浮泛得很,但往往成为追忆似水年华的最佳门径。我们可以想象曾有多少像孟元老这样的人士,流寓江左,午夜梦回,不胜欷歔,“岂非华胥之梦觉哉”?
孟元老的白描手法巨细靡遗,已经迹近百科全书式的叙事奇观。因此,《东京梦华录》提供了北宋城市生活史、社会史的第一手材料,有关研究不胜枚举。相形之下,此书连锁叙述和记忆的方式,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伊永文教授近年提出“梦华体”文学的观念,试图重新建立《东京梦华录》的文学坐标。④所谓“梦华体”的源头约有两端。一方面,中国传统叙事里以虚无缥缈的梦境投射现实人生的不足原就其来有自;孟元老所援引的华胥之国就是典出《列子》。除此,从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到唐代的《枕中记》、《南柯太守记》,都有脉络可循。另一方面,对(广义定义的)城市书写可以上溯到《诗经·小雅·斯干》,到了汉代,《蜀都赋》、《洛阳赋》、《东京赋》、《西京赋》等已经蔚为大观。之后的城市写作,有的记录风土民情(《风土记》),有的见证生活世态(《洛阳伽蓝记》),而唐宋笔记传奇的记载更是多彩多姿。伊永文指出,《东京梦华录》承袭了这些资源,又灌注了独特的庶民意识,因此,创造了一种“以俗为主……韵散相间、短小清新、上下通晓、亦庄亦谐”的“梦华体”。⑤
“梦华体”的观点提出以后,学者如郑继猛、霍有明等在其上继续做出观察,指出孟元老的叙事看似散漫,但却能“以点代事”、“以时代事”,或逼近审视,或纵观全局,铺陈出庞大繁复的时空动线,使得汴梁生活跃然纸上。⑥作者将生命百态、四时节庆融入自己的情感之间,形成一种神话式的循环,用以和现实历史的大陷落抗衡。李敬泽则从现代文学观点思考《东京梦华录》与卡尔维诺(Italio Calvino)、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西方作家、批评家城市写作的关联性:“那座名叫东京的大城不像是伫立在某时某地,而像是由词语精密复杂地堆砌,这位建筑者是个疯狂的家伙,他就像卡尔维诺笔下向忽必烈贾汗讲述远方城市的马可·波罗,让一座城市在符号的坚硬光芒中呈现。”⑦
但“梦华体”真正的吸引力还是在于孟元老面对历史与城市的姿态。他不动声色,却写尽声色之极;而他笔下的繁华靡丽不论如何眩人耳目,却终于归向空虚失落。《东京梦华录》的底蕴是关于事后——或后事——的美学(aesthetics of posterity),悼亡伤逝的动机挥之不去。孟元老之后,从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到晚明清初张岱的《陶庵梦忆》、余怀的《板桥杂记》,从晚清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涤浮道人的《金陵杂记》到现代陈定山的《春申旧闻》、梁实秋的《故都忆往》都有意无意地延续了“梦华体”叙事,艳说旧事,神游故地,形成正史以外重要的叙事传统。
在迤逦的“梦华体”叙事长河里,董启章的《梦华录》、《繁胜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1992年初次发表作品,二十年间已经跻身海外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比起上述“梦华体”作家,董启章其生也晚,但是在步武孟元老的写作风格上,他却堪称亦步亦趋;从《梦华录》、《繁胜录》等书名到书写形式无不刻意与《东京梦华录》相呼应。董当然不只是有样学样而已,他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寄托。香港曾是上个世纪末华人世界最繁盛的城市,犹如千年以前的汴梁。但“回归”为香港前途带来空前阴霾,所谓九七“大限”成为当时无数香港人的恐惧。董启章生于斯、长于斯,对这座城市的命运自然心有戚戚焉。他选择《东京梦华录》作为重写的对象,借此喻比的用心不问可知。
然而,有心的读者稍加对比,就会发觉孟元老写东京和董启章写香港的差别。首先,汴梁是北宋帝都,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一个是皇权一统天下的所在,一个是丧权辱国的焦点,政治地理的分歧何其之大!其次,从时间观点而言,《东京梦华录》凸显南渡之士的遗民情怀,充满黍离麦秀之思,而董启章的书写却将眼光投向未来,为香港“回归”五十年后的陆沉预作描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的“不正确”,也更是时间过去和未来次序的错乱:过去的完而不了,未来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更重要的是,《东京梦华录》是孟元老汴京经验点滴的记录,一向被视为具有可资征验的史实性;董启章的《梦华录》、《繁胜录》则摆明了是戏拟之作。如此,汴梁和香港的意义仿佛就被悬置在历史和虚构的两极之间。
这些观察所导致的理论问题以下将依序说明。我们首先须对董启章《梦华录》、《繁胜录》作进一步了解。这两部小说是董启章书写九七香港的四部曲“V城系列”中的两部(《地图集》[1996];《繁胜录》[1998];《梦华录》[1999];《博物志》[尚未出版]),顾名思义,分别以《东京梦华录》、《西湖老人繁胜录》为对应。但这两部南宋城市笔记书写的对象其实不同:前者缅怀汴梁,后者则是南宋首都临安生活回想。我们因此要问在什么意义上董启章将他们混为一谈。在《繁胜录》的序言里,董启章说明他的叙述其实源于“V城大回归时期”刘华生所撰之“本地城市风物纪录”:《梦华录》。但刘的《梦华录》已经散失,《繁胜录》为后起之书,即于“‘大回归五十年’由‘V城风物志修复工作合写者’、‘大回归时期新生代’维多利亚、维朗尼加、维奥娜、维慧安、维纳斯、维真尼亚及维安娜七人”,“‘于文献堆填区发掘出刘华生的稿件,经过重组和校正’,整理出‘第三代的梦华录’,也就是《繁胜录》了。”⑧
换句话说,如果《梦华录》是“大回归”的招魂之作,《繁胜录》则是2047年——“回归”之后五十年——后设、衍生出来的招魂之作的招魂之作。董启章看来后现代的可以,却点明了古今“梦华体”叙事一脉相承的征候。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杭州作汴州,或苏州、扬州、南京、北京、上海……如此香港就是另一个欲望与梦想错置的空间。
《繁胜录》分为三卷,每卷各有七章。卷一写V城的地理形态、制度建设;卷二写城中饮食娱乐、日常生活;卷三写四时节庆、仪式风俗。董启章仿《东京梦华录》的实录叙事,罗列各样细节不厌其详,形成百科全书式的奇观。论街道有油街、琴行街、书局街、糖街、雪厂街、庙街、西洋菜街、英皇道、太子道、皇后大道……;政府机关有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注册署、社会福利署、拓展署、拆毁署、税务局、渔农处、海事处……;酒楼食肆有幸运、好彩、叙福、嘉爵、君豪、天天、华园、港威、雅苑、通泰……;论风月行业有伴唱妓、伴舞妓、伴酒妓、按摩妓、蒸汽妓、冲凉妓、手触妓、鼓吹妓、舌尖妓、吞吐妓……;论民众有坐街人、游街人、跑街人、吻街人、摸街人、扑街人、撞街人、说街人、笑街人……
在董启章笔下,V城是个城墙之城,也是城中之城;是酒楼之城,也是傀儡之城;既庆祝端午中秋,也不忘复活圣诞。除此,他又介绍刘华生《梦华录》抒情的断简残篇,以及大回归时期新生代《梦华录》修复者的所见所思。如此产生的多声部叙事对话贯穿古今,本身就是众声喧哗的表现。
董启章的记忆游戏并不就此打住。在出版《繁胜录》以后的一年,他又写出《梦华录》,以九十九篇笔记小说尽情挥洒世纪末物质文明的奇技淫巧,并由此折射香港人事的浮光掠影。照道理说,《梦华录》应该是“大回归叙述者”刘华生的佚文,如何失而复得,董启章并没有交代。他仿造笔记体小说,写日剧偶像、应时潮货、电子产品、时尚品牌如何支配世纪末香港生活,闲闲数笔却能穿透事物表里。尤其他在貌似写实的文字上突然点染奇幻色彩,使得小说陡然有了志怪的向度。穿了Red Wing跑鞋的孤独少年不断奔跑到世界以外;沉迷深田恭子主演的《Colors》的女孩情到深处,患了色盲;Depsea Water仿佛是旷男怨女的云雨菁华;Temporary Tattoo让肉身伤痕成为春梦了无痕;真品的Prada人人认为是冒牌;最新IMAC散发穿透幽冥的魅力。但日光之下无新事,V城市民见怪不怪,一切的变异不过是寻常人生。
由此,我们回到董启章创作的初衷:城市、历史和虚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他所言,董启章不愿只着眼于他的书中如何描写城市景观,更要“反过来把城市视为观看的方法”⑨。他的V城书写虽然以中国古代城市笔记为模式,但以城市为观看世界这一点,却又接近西方传统:“希腊以城邦为政治单位自不待言,罗马帝国是由罗马城所统治的帝国,而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实为天国的隐喻,与‘世俗之城’(人类世界)成为对照。……而V城,历来就是以‘城’的方式存在。此‘城’实是中西两种城市观的合体显像。”⑩所以,《繁胜录》、《梦华录》尽管脱胎于中国古典,其实董启章带有现代作家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本雅明的深刻影响。这和上述李敬泽由《东京梦华录》联想这几位西方大师有了微妙的对应。
推而广之,作为一种历史发生的现场,城市汇集川流不息的人世活动,千变万化的政经现象,文化、建设和想象的永恒张力,已经有了虚实交错的能量。用城市史专家慕佛尔得(Lewis Mumford)的话来说:“城市就是社会行动的剧场”;所有发生的事件“无非使得这场社会剧演出……更有看头,就像舞台一样,设计精良,强化、勾勒演员的千姿百态,以及戏剧的行动。”(11)
鉴于香港本身的历史背景,董启章更得以发挥城市如戏剧的意义。十九世纪中叶香港因缘际会成为英国殖民地,由此兴起。香港的发展仿佛无中生有,原来就充满传奇意义。但董启章明白,不论作为殖民地,还是行政特区,香港的历史只能假手他人,香港人只得逢场作戏。你唱罢来我登场,在戏拟的——虚构的——过程里,这座城市的身份反而变得分外真确。
在这层意义上,香港和汴梁可以相提并论,成为董启章观看世界的方法。千年华胥之梦不只是汴梁和香港的命运,也是所有城市的命运:“虚构(fiction)是维多利亚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亦必是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12)孟元老写作《东京梦华录》是为了抗拒遗忘,董启章却拒绝将“遗忘”本体化,而视之为创造性的回忆——重组过去,想象未来——的起点。城市,不论是汴梁,还是香港,正是呈现建构与虚构、记忆与遗忘的舞台。这也是董启章对“梦华体”在另一个千禧年的贡献。
“梦华”二字,应是世界上所有曾经光辉一时的城市的终极归结。梦之必破,华之必衰,似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可是,当时间在写作中成为永恒的运动,过去与未来即成就于当下。梦未必虚,华未必堕,一切经验,一切存在,一经集之、录之、志之,就可以脱离单一的时空,成为无限衍生和延伸的世界。(13)
《东京梦华录》写于南宋初年,以汴梁的繁华盛世对照北宋皇朝的覆灭,孟元老从世俗观世变,从繁胜见虚无,不论题材形式,都是遗民叙事的重要典范。董启章的《梦华录》、《繁胜录》既然刻意模仿孟元老和西湖老人的写作,似乎也呼应这一遗民意识。但如上所述,汴梁和香港在政治历史上的地位其实大不相同。汴梁的失陷象征大宋的覆亡,宗室百姓的南渡带来国仇家恨的创伤。香港原来是英国殖民地,也是近代中国积弱不振、屈服于西方帝国势力两大威胁——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具体表征。果如是,九七“回归”意味着香港重投祖国怀抱、回归正统的契机。这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刻,何以香港作家如董启章却写出了一种怅然若失之感?
“梦华体”叙事在这两部作品中透露的遗民意识因此必须重新思考。遗民一词,原泛指“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14)。作为一种政治身份,遗民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商朝。(15)中古时代朝代兴替,但尽管忠义之说未尝稍息,事二姓、称降臣,而天下不以为耻的例子也所在多有。(16)论遗民论述的形成,仍在宋代以后。(17)宋室覆亡后,遗民文人无以为继,反而激发出文艺上的突破。“梦华体”重要的实践者周密(1232-1298)所作的《武林旧事》有言:“及时移物易,忧患飘零,追详昔游,带入梦寐,而感慨系之矣。”(18)遗民论述的高峰出现在明末清初。当时孤臣孽子的作为可以归纳出如下的方向:他们或另立共主,企图恢复旧业(如郑成功,张煌言);或退隐山林,追怀往事(如张岱);或皈依宗教艺术,寻求度托(如石涛,八大山人);或醇酒美人,自暴自弃(如冒襄);或著书立说,省思文明存亡绝续之道(如顾炎武,黄宗羲)。其中,张岱等的怀旧之作呼应了孟元老的心声。
到了20世纪的中国,强调忠君保国的遗民意识理应随着“现代”的脚步逐渐消失。然而,每一次的政治裂变,反而更延续并复杂化了遗民的身份以及诠释方式——遗民写作也因此历经了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的洗礼。我曾以“后”遗民写作的生成和影响谈论当代文学。我认为遗民指向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作为已逝的政治、文化的悼亡者,遗民的意义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体性摇摇欲坠的边缘上。后遗民的“后”颇有自遗民论述的窠臼解放之义。但事实不然。如果遗民意识总已暗示时空的消逝错置,正统的替换递嬗,后遗民则可能变本加厉,宁愿更错置那已错置的时空,更追思那从来未必端正的正统。(19)
我认为,如果以往“梦华体”叙事建立在遗民文学的基础上,董启章的V城书写就开拓了“后遗民”的风格。他既然无视大历史离散和回归的逻辑论述,他的《梦华录》与其说是“怀旧”情绪的展现,更不如说是推“新”出“陈”,发明一种“过时的美学”(an aesthetics of outdatedness)。(20)后遗民的逻辑最极致处竟能无中生有,串连出一个可以追怀或恢复的历史,不,欲望,对象。当历史被架空后,“‘过时’或‘不合时宜’,似乎比‘适时’、‘合时’更有意义”。(21)而所谓的“过时”也不过就是几年之间的事情,何以竟有了天长地久的错觉?历史记忆和当下体验成了奇诡的一体两面。就此,我们要说“后遗民”的“后”不仅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而不了。“遗”可以指的是遗失,也可以指的是遗“留”。如果遗民已经指向一种时空错置的征兆,“后遗民”是此一错置的再错置,但同时也成为对任何新兴的“想象的本邦”最激烈的嘲弄。
董启章不是20世纪末唯一将“梦华体”嫁接到“后遗民”小说的作者。台湾的朱天心(b.1958)、旅美的张北海(b.1936)、大陆的贾平凹(b.1952)都有作品足供我们思考。朱天心出身眷村,作为外省第二代作家,她面对90年代气焰日盛的本土主义有不能已于言者的疏离抑郁。而昔日所信奉的伟人已逝,主义不在,更使她怅然若失。她苟安于台北,实则有若游魂,在失忆与妄想的边缘游走,找寻历史的渣滓。1997年朱写出《古都》,以充满感伤的眼光回顾她成长的台北城。《古都》中貌似朱本人的中年女作家自日本回来,发现如果以一个伪东洋客的眼光重新审视台北,她所熟悉的城市居然出落得如此陌生,乃至恐怖。凭着一张日据时期的地图,她漫游世纪末台北的大街小巷,所见种种景观,从西门町到江山楼,从大稻埕到淡水河,无不寒碜丑陋如废墟,而亚热带草木花树仍在街头巷尾兀自蔓延。
朱天心仔细记录一切,几乎到了琐碎冗长的地步,但就像孟元老一样,笔下自有一种真情流露。《古都》的潜文本是川端康成的《古都》。但比起川端笔下那古雅典丽的京都,台北是一座忘怀历史、背弃记忆的城市,以致连孤魂野鬼都无栖身之地。《古都》成就了朱天心特有的后遗民书写的风格。朱之为“后遗民”,因为她所生存的世纪如此“民主进步”,何来故国前朝之思?当岛上的民主运动开花结果,摆脱了各种名堂的外来统治,终于“站了起来”时,朱天心者流退向历史暗角,兀自啃啮着世变后的苦果。她的书写充满了时不我予的尴尬。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但也正因为去古已远,她看似不合时宜的张致恓惶,反而引人三思。
张北海的《侠隐》(2000)以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为背景,敷衍了一则侠义奇情故事。张北海生于1936年,恰是《侠隐》故事发生的那年。1949年他随家人离开大陆,之后赴美留学就业,定居以迄于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他的北平经验仅止于少年时期。但这座城市已经让他难以忘怀。1949年之后移居海外的前辈“老北京”作家像唐鲁孙等怀念往事无常,于是有了惊梦之叹。张北海则反其道而行之,正准备要悠然入梦。北京的繁华,他“原来”就已错过,既然如此,他反而得以大肆发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奥妙。何况世纪末的北京又经历了一轮新的大建设,或大破坏。在一片拆迁更新的工事中,蛰居海外的作家却怀着无比的决心,要重建京城的原貌。
张北海所依赖的不是悼亡伤逝的情绪,而是文字的再现力量。除了怀旧,他更要创造他的理想城市。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张的主角回到北京,由秋初到盛夏,度过四时节令,遍历食衣住行的细节。张显然参照了大量二手资料,自地图至小报画报、掌故方志,巨细靡遗。他的角色特别能逛街走路。他们穿街入巷,干面胡同、烟袋胡同、前拐胡同、西总布胡同、月牙儿胡同、王驸马胡同、东单、西四、王府井、哈德门、厂甸、前门……所到之处,旧京风味,无不排闼而来。张北海如此怀念、书写北京的方式,识者或要不以为然。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就是“他的”“后遗民”故事?出虚入实,他的北京不乏人情世故之美,也无从避免已经和将要发生的忧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北京仍然拥有自己的传奇。他不再苦苦追忆那失去的盛年,反而能仔细咀嚼北平宜古宜今的都会魅力——一种最特殊的现代性。
陕西作家1993年的《废都》曾因情色描写引起巨大轰动,但我们多半忽视他对城市所投注的特殊情怀。西安曾是十三个王朝的帝都。相对于汉唐盛世,今天的西安只能成为废都。即使如此,这座城市魅力无穷,不只可见于各代文物遗址,也可见于饶有古风的日常生活。然而,贾平凹写出的《废都》却要让读者吃惊。小说里的西京时至今日早已是五方杂处、怪力乱神的所在。在这座灰暗郁闷的废都里,杨贵妃坟上的土滋长出花妖,青天白日里出现了四个太阳,市民生活毫无章法可言。一群好色男女正在陷入无穷尽的迷魂阵中,但就是偷情也偷得磕磕碰碰。评者因戏言,“颓废是颓废,可是土颓土颓”(22)。
西京杂沓苟且的乱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具体而微的现象。但贾平凹的眼光要远大于此;他会说西京之废,非自今始。千年以前当汉唐帝国式微时,它的倾颓已经开始。西京的居民坐拥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却在某个接榫点上错过了历史的因缘际会,成为内陆的黄土文明传统的遗民。正因为西京如今连颓废也失去了传承,成为“土颓土颓”的,它所显现的历史的怅惘,还有它承受的时间的断裂,才更令人触目惊心。一切曾经有过的繁华——包括最世故的颓废——怎么就没有了?西京就在这样“囫囵囵”的状态下体现它的后遗民意义。
以上这三位作家背景各有不同,但在现代中国历史板块变动之际,他们都有了身世之感。他们将自己定位在主流之外、之后,或托喻、或自白,他们写出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感触。“梦华体”之所以对他们有意义,因为他们各自就一座城市——台北、北京、西安——堆砌、罗列、感受各种物质生活的材料,企图从最基本的感官经验中,建立历史想象,并且一任有情的主体穿梭其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解构了“梦华体”,因为他们质问历史传承的天命必然,并且思考记忆的虚构本质。
比起这三位作家,董启章走得更远,他的文字实验也更激烈。他坚信香港既然是以城市形态浮出历史地表,也就没有向任何正统国家论述输诚的必要。如上所述,他将城市和虚构紧紧联合一处,以城市涌动的欲望想象,无尽排列组合的空间,挑战历史大叙述。他将香港一面与历史都会汴梁相接轨,一方面又视之为网络上的SimCity的现实倒影。(23)一个是已经过去的城市,一个是正在(虚拟情境中)发展的城市;一个是公共空间的显现,一个是想象空间的延伸。但诚如董启章指出,既名为城市,两者都暗含了灾难、劫毁的历史意识。如何进一步厘清、拆解这一历史意识,赋予宿命以外的意义,就是董的“后遗民”叙事策略了。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董启章已经推出《地图集》,俨然要为“大限”将到的香港重溯前世今生。全书体例混杂,以假混真,集文献图录,逸事新闻于一炉。书内按理论、城市、街道、符号四辑呈现;这四辑与其看做是四类文本(texts),不如说是四层位置(sites),或互相渗透,或互不相属。由此建立的驳杂的立体史观,自然与线状的历史大异其趣。看看“错置地”(misplace)、“非地方”(nonplace)、“多元地”(multitopia)这类专有名词的解释,或是裙带路、雪厂街、爱秩序街等来龙去脉,都不禁让人发出会心微笑。卡尔维诺、布赫斯等人的影响在在可见,而福柯(Michel Foucault)有关“异质地”(heterotopia)的特征尤其可以参考。(24)
《地图集》的副题,《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一个来自福柯的灵感(“考古学”;archaeology)。董启章要以小说家的特权为香港挖掘——或建构——她的身世。在众多空间形貌的交错间,香港的存在原就可疑,也就无所谓的出现与消失。它只是延伸,在权力配置图中延伸,在建筑蓝图上延伸,在文学天地中延伸。“永远结合着现在时式,未来时式和过去时式……而且虚线一直在发展,像个永远写不完的故事。”(25)香港成为他想象历史的隐喻。
到了《繁胜录》,董启章的“城市考古学”更是变本加厉。它采用了未来完成式的写法,透射大回归五十年以后V城的林林总总。这座城市仍然喧哗璀璨,但令人隐隐不安。这是一座架空之城,大回归以前的建设和记忆早已沉没海底;一座通道之城,熙来攘往的人群永远在过道上生老病死;一座影子之城,酒楼茶肆的喧闹遮掩不住鬼影幢幢,举目所见,包括桌椅门窗,可能都是物化的“人肉傀儡”。一切的祭祀礼仪无不有模有样,却又似乎只是行礼如仪。
董启章并无意“唱衰”香港,而是希望借虚构——作梦——的力量,重新发明,以及发现历史。“未来的考古学”并非预早宣布结局的宿命论,它是把结局当成新的创造起点的辩证法。把未来当成已然的事实,把过去变成未发生的可能。在期待和怀想的双重运动中,时间去除了那单向的、无可逆转的、无法挽回的定局性,成为了潜藏着无限可能性的经验世界。(26)是在这一关口,记忆与书写形成微妙的拉锯。前面已经谈过“遗”修辞术。“遗”是失去,是后无来者,但“遗”也是流传,是存亡绝续。藕断丝连的欲望油然兴起,想象的乡愁开始蔓延。
最后来到《梦华录》。借着对上个世纪末各种生活形式、品牌、发明的摩挲、解析、遐想,董启章惊叹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如此相与为用,不断创造新的奇观。《梦华录》仿真笔记小说,却能别有所见,而且透露抒情特色。就此,正宗左翼学派的论著可以斥之为商品拜物,异化之极,但董启章认为在人与物之交汇点上,总有灵光闪烁的契机,甚至带来生命启悟。“在这样的物欲横流中,不一定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这当中涉及一种‘物品的个人用法’也几乎是把大量生产的,非人的商品化为己用,成为独特的生命体验印记。”(27)更进一步,“城市”为一巨大的“人为物”及其中的物的总体呈现,又必然通过人的生存其中才能确立及延续其存在及其价值意义。(28)在这个意义上,《梦华录》就是对这样的城市物种演化的记录;董启章成为不可思议的“唯物论”也是微物论者。
《梦华录》只是董启章书写香港物质文化史的开端;另一本尚待出版的《博物志》,顾名思义,可以想见他的企图。在新世纪里,董再接再厉,写出《天工开物·栩栩如生》(2003)里他诉诸“天工开物”那种人定胜天、开“物”成务的知识论,提倡时间的“繁”史而非简史。而“物种源始”所指向的源头,与其说是正本清源的源头,不如说是多重缘起的源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以董虚拟的家族历史为背景,回顾一代香港人从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如何胼手胝足,造就了岛上日后的繁荣;另一方面,他以叙述者个人从七十到九十年代的成长经验,点明后之来者开枝散叶的发展。乍看之下,董启章似乎在写标准的家史故事,但他的作法不是塑造人物以为历史的铺垫,而是突出“人”与“物”,从两者之间或平行衍生、或交相为用的过程,看待(香港)历史主体生成与创造的关系。
董启章介绍了十三种器物——收音机、电报、电话、车床、衣车、电视机、汽车、游戏机、表、打字机、相机、卡式录音机和书——来展现人与物共相始终的历程。这些器物如此平常,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而叙事者要提醒我们的,恰恰是这人和物两者之间相互发明、习惯成“自然”、虚构成历史的过程。(29)
董启章的香港写作因此为21世纪“梦华体”开拓了新的可能,并且由此让我们理解《东京梦华录》与时俱变的新意。离开了感时伤逝的废墟意识,他投向未来,从未来的考古学思考历史多元发展的可能,传统的遗民叙事滋生出“后遗民”叙事。更重要的是,他企图走出国族论述的局限,从城市的物质性和发明、表演性思考历史如何被理解的方式。虚构和现实因此交相为用。究其极,董启章要说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排演梦华的舞台。从香港到汴梁,千年华胥之梦有忧伤、有期待。时间“惘惘的威胁”如影随形,但是因为有了梦的可能,城市因此出现,历史继续发生。
注释:
①《地图集》(1997,原名《地图集:一个想象城市的考古学》),《繁胜录》(1998,原名《V城繁胜录》),《梦华录》(1999),《博物志》(原载香港《星岛日报》副刊,1999年11月10日至2000年7月29日,尚未结集出版),见《V城系列出版说明》,《梦华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0页。
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
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仆数十年烂赏迭游,莫知厌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陎,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
④伊永文:《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梦华体”文学》,《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第114-119页。伊教授并作出极为详尽的谱系学研究。
⑤同上,第114页。
⑥郑继猛、霍有明:《〈梦华体〉补论》,《西北农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36-140页。
⑦李敬泽:《盛大,永恒的城——〈东京梦华录〉》,《散文》2002年第3期,第52-53页。
⑧董启章:《为未来而作的考古学》,《梦华录》,第4页。
⑨董启章:《为未来而作的考古学》,《梦华录》,第4页。
⑩同上。
(11)Lewis Mumford,"What is a City?" from Architectural Reader,in Richard T.LeGates and Fredric Stout,The City Reader(New York:Routledge,1999),93.
(12)董启章:《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13)董启章:《为未来而作的考古学》,《梦华录》,第7页。
(14)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有关(明清)遗民定义,见Lynn Struve,"Ambivalence and Action:Some Frustrated Scholars of the K'ang-his Period," in Jonathan D.Spence and John E.Wills.Jr.eds.,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327。有关宋遗民的定义,见Jennifer W.Jay,A Change in Dynasties: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Washington: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6。
(15)周武王克商后,为了控制中原,将商人迁徙至宋、卫、鲁、燕各地,造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商人感怀前朝,不能自已,力图保持旧时衣冠仪礼。遗民意识因而兴起。其时孤竹国伯夷、叔齐原已降周,因不满武王灭商,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史记·伯夷列传》:“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兮!”
(16)以曾事四姓十君为荣,自号长乐老的冯道(888-954)当然是最常被提及的例子。
(17)这应该与宋以来理学界所倡的忠孝思想极有关联。此一论点承蒙杨晋龙博士提出,谨此致谢。
(18)周密:《武林旧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9)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0页。
(20)董启章:《过时的美学》,《梦华录》,第283页。
(21)董启章:《过时的美学》,《梦华录》,第283页。如此,董当然反驳了新马学者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有名的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怀旧”的批判。
(22)扎西多:《正襟危坐说废都》,收入江心编:《废都之谜》,第11页。见王德威:《废都里的秦腔:论贾平凹》,《后遗民写作》,第223-244页。
(23)董启章:《从天工到开物——一座城市的建成》,《第八届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论稿汇编》,香港公共图书馆,2011年版,第231页。
(24)有关“异质地”的定义和讨论,见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1967)," http://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html
(25)同上,97。
(26)董启章:《过时的美学》,《梦华录》,第281页。
(27)同上。
(28)董启章:《为未来而作的考古学》,《梦华录》,第6页。
(29)王德威:《香港另类奇迹:董启章的书写行动和〈学习年代〉》,《学习年代》,台北麦田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