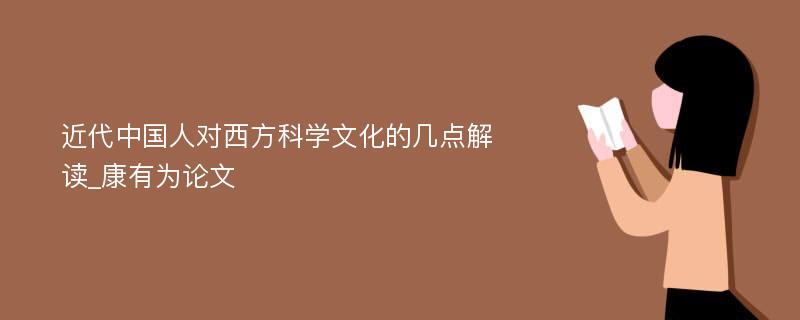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人对论文,科学文化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1—0049—07
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由基督教传教士以渗透的方式进行的。他们以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传授了一些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据不完全统计,自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年)进入中国内地,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布并厉行《防范外夷规条》,禁传天主教。这近二百年间,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著译约有370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约占120种左右。最突出的是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光学、解剖学、逻辑学、实验仪器,以及水利、机械、建筑、采矿、兵器等技术,还有哲学、音乐、绘画、历史方面的知识。西方文化的输入给中国人送来了一线科学文化曙光,但随着清政府的禁教与闭关政策,中西学术思想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中断,致使西方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因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知识未能及时传入中国,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与西方的差距愈拉愈大,扼杀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科学。近代中国人对西学的认知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对于近代西方文化东渐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大都偏重于对西方人文文化亦或政治文化东渐过程的研究,而对于西方科学文化东渐过程的探讨却十分薄弱。本文就是对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就教诸方家指正。
一 “采西学”说
耶稣会士传播的西方学术,不但有欧洲古典科技知识,还有近代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尽管传教士宥于宗教的目的所限,不可能完整和准确地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和科学,但仅就介绍的内容看,这些西方学术属于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学术体系,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启发了中国的思想界。最早觉悟的是一批经世派人物。如林则徐先后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各国律例》、《华事夷言》、《澳门新闻纸》(又选辑为《澳门月报》)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又如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以后不断搜集资料,1844年扩编为60卷,1847年则汇成百卷本巨著。魏源在扩编《海国图志》的过程中,不但辑录和引用中国历代史志有关域外著述,而且对明清之际以及鸦片战争前后外人的中文著述也十分注意。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贸易通志》、美国传教士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培端的《地球推方图说》、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地理备考》、英国人小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英美传教士合作创办的《每月统计传》、佚名《万国地理全图集》等。正是这些大量的外人输华中文著述,使魏源的《海国图志》比较准确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史地沿革,疆域大小、政教风俗、物产制造、科技教育、交通贸易等方面的知识。
在早期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解读中,最具影响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冯桂芬留给后人许多学术著作,如《说文解字段注考证》、《使粤行记》、《两淮盐法志》、《苏州府志》、《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正李氏恒星图》、《测定咸丰纪元恒星表》和《丈田绘图章程》等。但他在53岁写的《校邠庐抗议》在社会上影响最大。
《校邠庐抗议》共42篇,分为卷上和卷下两部分,其内容无不是针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提出的见解。其中《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以及后来被人们收入到附录部分的《借兵俄法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等篇,是冯桂芬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代表作。冯桂芬已经意识到,何以“国最大,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的中华,如今竟然受制于俄、英、法、美四国之下呢?冯桂芬认为,这种“不如”是必须直面的客观存在,“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由此在《制洋器议》中提出“不如夷”说,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以及“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1](p198) 冯桂芬开始将西方的文化作为儒家之外的一个独立的学问体系,明确提出了“西学”这一概念。他在《采西学议》篇中说:
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里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先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肆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学,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p209~210)
冯桂芬对西学的认知,实际上已经上升到对西方文化加以肯定的层面。在他看来,西方船坚炮利现象的背后,是浑厚的科学传统作支撑。他特别强调学习算学的意义,认为是西方科学技术中的一门基础学科。
上述,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早期经世派人物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解读,表现了他们对西方近代实用科学的接纳和务实作风。但无论是魏源,还是冯桂芬等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主张和建议,或许是为了救弊,或许是为了补偏,就当时他们的思想而言,都无意从根本上对封建政治制度加以改变,也不可能提出效法西方政治制度的明确建议。对于中学(道德文化)与西学(科学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只能是“如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本西辅”表述。[1](p210)
二 “道器”与“体用”说
19世纪中叶,向西方学习的实践活动——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是在“道器”、“体用”认知层面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的,他们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也始终局限在这个层次。其中李鸿章、张之洞的文化认知主张就是其代表。
李鸿章的文化主张一是“自强”,二是“求富”。“自强”就是学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应付西方文化的挑战;“求富”就是创办民用工业。洋务派创办的工业企业活动曾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反对,他们视西方国家的生产技术为“奇技淫巧”,害怕传入中国,败坏人心。认为“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的中国文化,足以对付西方列强。李鸿章反对这种陈腐的文化主张,他在给一守旧分子的信中说,西方科学技术“何可藐视”,“洋学实逾于华学者”,信中写道:
算学比于天文,生为六艺之一,圣人未尝不讲究。兄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术器艺来……“格致测算无非欲其用诸制造”。然天地万物万事,皆有制造之法之意,何可藐视……“统名之洋学局,疑于用夷变夏,名不正则言不顺”。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若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揉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此,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涂?且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于夷夏之防,则必真有攘夷之本领,然后不为用夷之下策。请问公有何术乎?[2]
尽管李鸿章大力提倡和推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但他的基本思想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变“器”而不变“道”。李鸿章只承认西方的“技艺”,而否定西方的制度和思想。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纲常名教“不必变”,因为中国的礼义教化远胜西洋诸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即西学为用,必须以中学为体。
张之洞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集中反映在他的《劝学篇》一书。《劝学篇》全书共4万字,24篇,分为内篇与外篇两大部分。内篇9篇文章,意在“务本”以正人心,即主张教导天下臣民坚持传统的纳常名教;外篇15篇,意在“务通”以开风气,即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政和西艺,在不触动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举办工商、学校、铁路等,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全书以“中体西用”为思想主线,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首先,什么是张之洞心中的“中学”与“西学”?他在《劝学篇》论及新式学堂的制度时说:“其学堂之法……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3](p121) 上引文,张之洞所说的“旧学”指的就是中学,“新学”指的就是西学。“中学”(“旧学”)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但张之洞视为“中学”之根基和核心内容的乃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孔门之学”。
张之洞在西学为“外学”,以“应世事”思想指导下,创办了广东缫丝局(1886年)、机铸制钱局和银元局(1887年)、广东织布局和广东制铁厂(1889年)、湖北炼铁厂(1890年)、湖北织布局(1890年)等近代企业。同时,张之洞还主持修筑铁路,编练新军,设立新式学堂,兴办商务,成为名重一时的洋务派实力人物。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必然结果。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组织人才译出400多部西方科技著作,创办了20多所新式学堂,并向欧美国家派遣数百名留学生。洋务运动率先掀起的学习西方文化热潮,不仅引进了西方科学知识,而且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不仅有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潜移默化地促进了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使中国知识阶层中一些人开始认识到,除了以经、史、子、集为内容的“国学”之外,这世界上还有能直接用之于国计民生的近代科学技术亟待学习掌握。
三 “以西释中”与“惟科学”说
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代表主要是康有为、谭嗣同的“以西释中”和严复的“惟科学”说。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书香门第,幼从著名理学家朱次琦问学,专攻程、朱、陆、王思想,有扎实的旧学根底。此外,他还曾参禅问道,面壁求佛,有较深的佛学造诣。康有为“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孟子微》、《大学注》、《中庸注》、《礼运注》、《论语注》和《大同书》等,几乎对儒家的经典都作了重新诠释。其中,《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和《诸天讲》等是康有为专讲西学的著作。《康子内外篇》写成于1886年,全书15篇,“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4](p119),是康有为接纳西学后比较完整地融会中西文化的著作。全书涉及西学的知识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光、电、声、化的自然科学知识、自然进化理论、人体生物解剖知识、天物地理新说和生物演化学说等。如在宇宙的起源问题上,康有为借用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知识“化西为中”,“以西释中”。他说:“立气之道,曰阴与阳,曰热与重;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者,热力也;义者,重力也;天下不能出此二者。”[5](p188) “若积气而成为天,摩励之久,热、重力生矣,光、电生矣,原质变化而成焉,于是生日,日生地,地生物。”[5](p196)
《实理公法全书》则主要表达了康有为社会学中的西学特征。他套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从简单的几何公理出发,借助逻辑推理来解释人文社会问题。《诸天讲》写成于1886年,是一部关于天文学著作。康有为在书中依据西方近代科学家对天体运行的观测和研究,对宇宙模型,太阳系起源,行星与太阳的关系,月亮的圆缺,彗星、流星、太阳黑子等等现象都作了一定的解释。
康有为这种“以西释中”尤其是对儒学的改造,标志着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文化从表层转向深层。康有为试图为西方文化披上一件儒学的外衣,或者将西方思想中国化。尽管这一步迈得还不够好,近乎牵强附会,但它毕竟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一种可喜尝试。
谭嗣同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亦是“以西释中”或“化西为中”,其主要著作是他的《仁学》。《仁学》内容极其丰富,在内容上“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以西学释“仁”或以“仁”释西学,形成“以太—仁—通—平等”的思想体系。正如他自己所说,凡为仁学者,应通佛书、西书(宗教及自然科学)、儒、道、墨等诸家学说。
谭嗣同《仁学》中的西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哲学内容上的解读,认为“以太”为“仁”之始,“仁”为“以太”之显用。“以太”一词最早是由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斯派提出来的。19世纪欧洲科学家为了说明物质运动的连续性和相互间的关系,将“以太”假定为一种可以传导光、热、磁、电的媒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先后翻译了《光学图说》、《光学须知》两书,将“以太”概念引入中国,把它理解为物质的始基,认为相当于中国的“一清之气”,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20世纪初期,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磁和光学理论,推翻了这种关于“以太”的解释)。[6](p287) 1896年2月,谭嗣同在上海访问了傅兰雅,接受了关于“以太”的解释,并将“以太”之说吸收为自己《仁学》中的思想资料。如他借用西方文化“以太”概念,从本原层次上认为“以太”是构成物质的本原,是“体”,“仁”为“以太”之用,有精神的一面,两者互为依存,相辅为用。同时,谭嗣同虽对“以太”规定了许多物质性的特点,但同时又作了许多精神性的解释,其目的在于将“以太”作为背景,而着重推出“仁”的概念,并通过对“仁”的解释,形成他的以太—仁—通—平等思想体系。谭嗣同以体用范畴讲“以太”和“仁”的关系,是为了进一步发扬“仁”的“通—平等”思想,用“通—平等”的思想来对抗“天理”和一切“网罗”,这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精髓。
谭嗣同虽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科学思想体系,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思考也尚未成熟;但他在《仁学》中引进的西方科学知识,所介绍的西方思想,正如梁启超所说,他“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6](p61)。
严复则是倡导“惟科学”说的先驱。早在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附设的海军学堂那里,他就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其中有数学、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等内容。后被保送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抱穆士德和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习科目有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诸学。学习之余,他注意考察英国的政治,大量阅读了西方的学术著作,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论著,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西方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比较真切的了解。严复认为,中国所需要的不是从古代的圣贤那里为西方思想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尽量系统全面地介绍西学。从1895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和《群已权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化的思想家。中国后来出现的惟科学主义思潮也从严复始。
首先是严复翻译和介绍的《天演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于1898年4月出版。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和宣传了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论是19世纪西方生物学界的一种关于生物界物种发生与发展的一种理论,也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每一节或每一段都加上自己长长的案语,案语中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对西方学术的源流,一一加以评述和介绍。因此,《天演论》不单纯是一本译著,而且也反映了严复本人的思想。严复认为事物变化的总趋势是:“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7](p02~03) 严复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用来解释社会,他说:“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8](p16) 用此道理向中国人敲起警钟,告诫人们不能再妄自尊大,号召人民起来自强图存。西方进化论思想迎合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多数先进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进化论思想。
严复的译著都是经过慎重挑选的。如他翻译《天演论》是为了保种,求自强;翻译《原富》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陆、王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提倡君主立宪。尤其是严复在系统介绍西学时,十分注重对西方科学方法论的介绍。他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所以优越,科学技术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各种理论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基础;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正确,又在于他们有新的方法作为指导,而这种新的方法就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深术也”[9]。他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9] “内籀”即归纳法,是从特殊到一般,通过对许多特殊的个别事物研究,得出普遍的结论。“外籀”即演绎法,是从一般到特殊,根据普遍的公理,推断出个别事物的性质变化。严复认为物理、化学、数学、医学、天文学各种学科都是反复运用这种方法的结果。严复用这种方法反对宋明理学,反对以书本为对象的经学方法。他说:“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穷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10](p64~65) 严复认为西欧用科学的方法,事事经过实验,认识也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而陆心学只是“师心自用”、“强物就我”,即要客观事物迁就他们的主观意识,而不问是否与事实相符合,只知背诵八股文,埋头考据训诂,讲义理、词章。严复称之为“无用”、“无实”的学问。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比较多地介绍西方文化的思想家,他的译著大约二百万字左右,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尤其是对西方自然进化论和逻辑学的介绍,这种近代的科学方法论,给中国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不再以易经的阴阳说和公羊家的三世说的历史循环论对西方思想加以附会,而是如何通过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得到可以确信的科学知识。可以说,严复已经触及科学哲学的两个基本点:重视试验和讲究逻辑。这种科学的理性精神,为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奠定了科学的认识基础。同样,严复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运用到社会,把归纳法扩展到一切领域,这种对科学方法理解的偏颇认识,这种过分地推崇方法的作用,也为后来的惟科学主义开了头。
四 “王道”、“霸道”文化说
辛亥革命时期,西学在中国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如在译书方面,1904年出版的《译书经眼录》,收录了1900年至1904年间出版的主要译著,分25类,所载译书目533种。西学传播的内容,也日趋全面系统,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西方的科技知识,特别还把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逻辑学和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介绍到中国,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译著。辛亥革命前后,在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中,孙中山提出“王道”与“霸道”文化说。
孙中山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接受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他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原则。他说:“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这里的“自然”,不仅指自然界,而且指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他把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他说:“元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此世界进化之第一期也”,“地球成后以至于今,按科学家据地层之变动而推算,已有二千万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也”,“人类初生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从动物性到人性,从竞争到互助,是世界进化第三时期。孙中山用“太极”,即他认为西方哲学中的“以太”,来说明世界的起源和进化,认为“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进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并将进化论的这种基本观点用于观察人类社会,得出“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是世界政治潮流必然趋势的结论。
在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即“王道”文化和“霸道”文化说。孙中山承认中国文化的落后,反对抱残守缺、自我陶醉,主张对西方文化持“开放态度”。但孙中山主张的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他批评一些留美学生“到了美国之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了以后,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所以他们在外国的时候,便自称为什么‘佐治’、‘维康’、‘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回国之后,不徒是和中国的饮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国的话也不会讲……甚至有在美国的时候,连中国人住的地方都不敢去,逢人说起国籍来,总不承认是中国人”[11](p538~539)。孙中山评价中西文化的标准有两个方面,即道德评判和物质评判。孙中山认为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他对西方社会的科学发达、物质昌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但对西方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脱节提出批评。他说:“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它的政治各方面。”“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物质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不仅没有促进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相反造成了道德的沦丧和倒退。用什么办法能够改变西方社会中这一矛盾现象,孙中山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可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他说:“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12](p533) 正是由于东西方科学文化与道德文化的差异,孙中山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概括为“王道”文化和“霸道”文化。他说:
专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于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13](p405)
孙中山用上述“王道”和“霸道”来划分东西文化,概括文化的本质,是不科学的,没有阐明东西方文化的阶级和时代特征。事实上,西方文化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还有与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即建立在科学文化基础上的民主传统。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不可能去补西方精神文明的不足。但就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性质而言,则是力图把西方文化,即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社会学说、政治学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社会模式同中国历史、现状结合起来,由变“器”到变“道”。
近代以来,在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的科学化活动。如早期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他们不仅参预了传教士的译述工作,而且在科技上也独有创造。又如洋务时期的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华世芳、徐建寅等人。他们在介绍西方科学,发展中国科学技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如李善兰翻译的《谈天》是我国近代最早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重学》是第一部介绍西方经典的力学著作,《代微积拾级》则是最早介绍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的著作,他的《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天算或问》等数学著作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这些准科学化的活动,这里不予详述,以后另文介绍。
五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学的认知过程,从早期的“采西学”到后期的“惟科学”提倡等西学认知,历时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而认知的层面始终局限于“道器”与“体用”之间,从而也构成近代中国人对西学认知的基本特征。
“道”与“器”这对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道”与“器”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根本问题。《易·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指有形的具体事物,“道”是无形的,指事物的道理或规律。如何认识“道”与“器”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早期思想家们经常辩论的哲学命题。“体”和“用”这对概念,也是哲学的范畴,在《论语》和《易经》中就已使用。唐代经学家崔憬对“体”、“用”二词有明晰的解释,“体”指实际的形质,“用”指形质的运用。到了宋代体用成了常用的范畴,并且从崔憬的具体意义变为比较抽象化的意义。这时,所谓体指永恒的、根本的、深微的东西,而所谓用指流动的、从属的、外发的东西。体是永恒的基础,用是外在的表现。这样,体用的概念,一般说来,体是根本的,第一位的,用是从属的,第二位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洋务运动兴起后,西学的引入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传统的“道器”、“体用”论便成为近代中国人理解“中学”和“西学”关系中的一种认识方法。
所谓“道器”、“体用”之辨,事实上亦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辨。东方与西方,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等条件不同,形成一方重自然,一方重道德的两大文化形态,即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主智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主德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特点就是其思辨的理性精神,或科学精神,中国文化的特点则是它的人伦道德精神,或人文精神。上述近代中国人在西学认知的过程中,将形而上的“道、体”概念,用来指中国文化,是第一位的;将形而下的“器用”概念,用来指西方文化、是第二位的,其目的是要阐言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这是一种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
近代中国人,关于“道器”、“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影响深远。如20世纪初期的科学主义思潮、二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40年代的科学与人文会通、80年代的“文化热”、90年代的“新儒学”思潮等,莫不是近代“道器”、“体用”之争,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争论的继续。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程度上的深浅与提法上的不同而已。“道器”与“体用”这种盲目自大的文化认知心态,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亦早被学界所批评。如科学家竺可桢早在他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中说:“我们提倡科学已近80年,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使中国人于光明灿烂的境界。”[14]
东西文化的选择已进入21世纪。近代中国人所使用的“道器”、“体用”文化观,虽已成为过去,但不能说它的影响已不存在。事实上,科学文化,主要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方法,而人文文化则主要是认识与发展人类自身的价值和由此而创造的精神成果,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科学需要人文(某种意义上就是哲学)的反思,而人文的进步则依靠科学的不断发展。总之,中国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中国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同样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未来中国文化的出路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创新,让“道器”、“体用”论的文化认知心态永远成为过去。
收稿日期 2006—09—01
标签:康有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科学论文; 校邠庐抗议论文; 严复论文; 天演论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孙中山论文; 劝学篇论文; 海国图志论文; 冯桂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