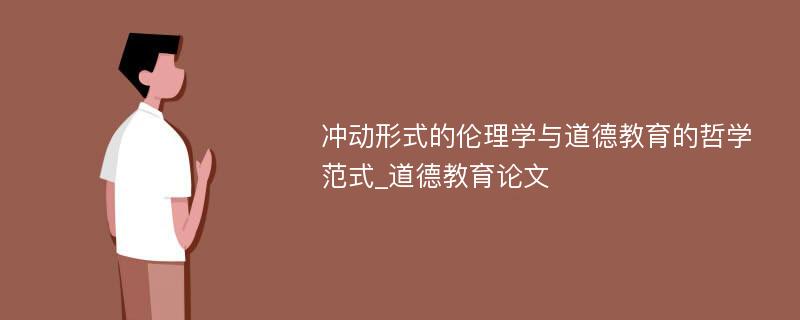
“冲动形态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的哲学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道德教育论文,伦理论文,形态论文,冲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010(2006)05—0007—06
无论是道德哲学体系还是道德教育体系,都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然而却十分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伦理精神至少有两种形态——思维形态或认知形态的伦理和冲动形态的伦理。遗憾的是,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的研究过于关注认知形态的伦理,而对冲动形态的伦理采取冷落甚至蔑视的态度。这种倾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伦理道德只是滞留于思维和理性的知识层面,而缺乏走向行为和生活的动力;道德教育缺乏自我生长的“否定性辩证法”(恩格斯语)。如果伦理要成为一种真正的精神,如果道德教育要培养具有实践品质和实践能力的人,就必须在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通过现象学向法哲学的辩证转换,在道德教育的哲学体系中通过伦理精神由认知向冲动的辩证运动,培育“冲动形态的伦理”。
一、认知形态的伦理与冲动形态的伦理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发现,人的心灵有两种能力:认知能力与欲求能力。它们各有不同的应用条件、范围和界限,对它们的概念规定分别构成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基础。[1]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康德的这“两种能力”发展为“两种态度”,即“理论的态度”与“实践的态度”。他认为,人的精神有两种结构:思维和意志。思维和意志不是两种特殊官能,而是精神的两种不同态度。然而,无论是“两种能力”还是“两种态度”,都在试图给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即康德所说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以概念基础,并没有在“一种哲学”尤其是实践哲学或道德哲学中将二者真正地统一起来,更没有在作为实践哲学的重要结构的道德教育哲学中实现这种统一。现代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通过对源头性传统的回归,在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哲学的体系中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
如果对中西方传统道德哲学体系尤其是传统道德规范体系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这些体系中都存在两种结构,即“知”的结构与“行”的结构,或用康德的话说,认知的结构与欲求的结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二者的文化构造尤其是人性机制有所殊异。两种结构或两种品质构造的统一,用王阳明的概念表述,就是“知行合一”。如此,我们可以假设,事实上存在两种形态的伦理,即认知形态的伦理与冲动形态的伦理。认知形态的伦理基于人的“认知能力”,是精神的“理论的态度”;冲动形态的伦理基于人的“欲求能力”,是精神的“实践的态度”。现代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哲学的难题是:认知形态的伦理如何向冲动形态的伦理过渡?冲动形态的伦理如何培育?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也许一提起“冲动”,就会将它与心理学相联系,并在心理学意义上加以探讨和研究。作为人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冲动当然具有心理意义,或者说,冲动最初的自然基础是植根于生理的心理。但是,有一个事实必须引起重视:在古典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冲动”是作为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概念而被讨论的。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冲动”的概念在伦理学中早于心理学出现,不过有一点比较清楚,至少在心理学还没有充分发展的那些时期,“冲动”已经成为道德哲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已经习惯于用心理学解释人的一切动机与行为的时代,让“冲动”的概念还原复归于道德哲学体系,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指证“冲动”是一个道德哲学概念并不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虽然没有“冲动”的语汇,但其语义指谓古来就有。王阳明演绎孟子的思想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进自然知恻隐。”[2] 这里的关键词有两个:“知”和“自然”。“知”显然不仅指思维、理性和知识,而且包括“行”,甚至主要是“行”。“知孝”、“知悌”、“知恻隐”的真义是“知行孝”、“知行悌”、“知行恻隐”,或者说“行孝”、“行悌”、“行恻隐”。“自然”的本义是说毋需思维和反思,不需任何中介,直接诉诸本能行为。这样,“知”在道德形而上学意义上,与“行”直接同一。“自然”的意思显然是说“知孝”、“知悌”、“知恻隐”不是一种间接性,而是一种直接性,是出自生命本能的冲动。于是,“知”既具有思维形态又具有冲动形态,“自然”与“知”的结合就是生命本性的伦理冲动和道德冲动。黑格尔将意志当作“冲动形态的思维”,认为思维和意志不是两种官能,而是对待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态度的观点,与孟子的“知”的意蕴正相契合。应当注意的是,黑格尔认为,“从意志的概念上来把握冲动”[3],是法哲学的内容。相应地,如果从理智或历史的概念来把握冲动,它们就是现象学或历史哲学的内容。因此,道德哲学的内容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冲动”的概念把握。在现当代道德哲学家中,丹尼尔·贝尔等就直接使用“道德冲动”的概念。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尼尔·贝尔将宗教冲动力或道德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相对应,虽然未对道德冲动作概念规定,但对它的确认却是无疑的。
“冲动”概念回归道德哲学体系的形上意义在于,“冲动”是一个道德哲学的概念,道德哲学体系不仅应当而且必须以“冲动”为重要研究对象。
二、伦理冲动的两种精神哲学形态
心理学在人的本性中诠释冲动的方法对伦理冲动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不过,伦理冲动的人性基础,应当是伦理性的文化本性而不是心理性的生物本性。
从逻辑和历史的意义上讲,伦理冲动的人性机制有两种:意志和情感,更准确地说,是伦理意志和伦理情感。但到底是以意志还是情感作为伦理冲动的基地和形态,则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紧密关联。确证这个假设的最简捷途径,是对中西方伦理精神和道德哲学的德性体系,尤其是作为其基础的基德或母德的人性结构进行分析。如果从源头性传统进行分析,中西方伦理的基德或母德恰好都是四个德目。理智、正义、节制、勇敢是由柏拉图提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系统阐发的“希腊四德”,它们是日后西方伦理精神的基德或母德;仁、义、理、智的德目的在孔子那里已经被提出,孟子将四者并列并形成严密的德性体系,从而成为日后中国伦理精神的传统,可谓之“中国四德”。对“希腊四德”(或“西方四德”)、“中国四德”的研究在道德哲学中已基本达成共识,就本文的研究主题来说,还需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两个德性体系的人性基础有何精微的文化差异?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西方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意志”;“中国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情感”。理性是它们的共同要素,但在二者的德性体系和人性结构中的地位不同;意志与情感分别构成二者的冲动机制或非理性结构。这两种人性结构在文化功能上相同相通,在文化性格上则彼此殊异。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的主体是灵魂。灵魂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理性,另一部分是非理性。灵魂的德性有两种:理智的德性与伦理的德性。① 伦理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勇敢、节制、公正,对象是欲望,人性基础是意志。“勇敢”的意志意义最明显,“勇敢就是如何对待忍耐和痛苦”[4],“勇敢的意义就在于能忍受痛苦”[5]。节制是灵魂非理性部分的德性, “是在快乐方面的中道(与痛苦联系较少并且不是同样的)”[6],同样基于意志。理智是思考的德性,它既有别于伦理的德性,又与之紧密相连,因为理性与欲望应该是一致的。“如果选择是一种真诚的选择,那么理性与欲望都应该是正确对待的。它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追求。”[7] 所以,伦理的德性既需要实践,即意志行为;也需要思辨性的思考,即理智。理智的德性,既是不同于伦理的德性的特殊德性,又内在于伦理的德性之中。理智的德性,不仅要进行真假和善恶的判断,而且要保证选择的真诚。关于公正,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似乎存在细微的差异。柏拉图将它放在理智、勇敢、节制之上,是灵魂的两个部分(即理智的德性与伦理的德性)的协调者;而亚里士多德把它放在勇敢、节制与理智之间。这种做法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将公正归结为伦理的德性,属于意志范畴;一是将它作为联贯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纽带,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协调灵魂的两种德性。后一种解释可能更审慎。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公正具有意志的品质,或至少兼具意志和理性双重品质。
由此,便可以演绎出“希腊四德”或“西方四德”的基本道德哲学原理:德性的主体是灵魂。德性的对象有两个——理性和欲望。德性有两方面的本性,“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追求”[8],“肯定”是思考,“追求”是行为实践。 德性有两种:理智的德性和伦理的德性。理智的德性以理性为基础,伦理的德性以意志为基础。理智是理智德性的内容,是思考或思辨的德性;勇敢、节制是伦理的德性,是“追求”或行为实践的德性;而公正兼具两种德性或介于两种德性之间。因此,“希腊四德”或“西方四德”的人性结构便是:理性+意志。理性是本体,意志是主体,四者中有三者基于意志。意志,是伦理德性与伦理冲动的人性机制。
“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在德目结构方面惊人契合,但在具体内容及其文化性格上却大相异趣。从字面上看,两者中直接相近的是“义”与“公正”(或“正义”)、“智”与“理智”。当然,“礼”与“节制”、“仁”与“勇敢”也有相通之处。“智”也可以被指认为一种理智德性,而且正像《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将“理智”放于勇敢、节制、公正之后那样,“智”在“中国四德”的体系中也位于仁、义、礼之后,是关于道德肯定即知仁行义的德性和能力。“智之实,知其二者弗去是也。”[9] 在中国传统伦理话语中,“智”的本体状态就是道德良知。“仁”是德性的起点和本体,其基本内容是爱人,“仁者爱人”[10]。“义”是爱人的正道,其要义是符合伦理地爱人,因而是一种伦理的正义。“义,人之正路也。”[11] “礼”的本性是节制文饰,“礼之实,节文斯二者也”[12]。这样,“中国四德”的体系便是:仁,宅也;义,路也;礼,门也;智,知也。其基本原理是:“居仁由义”、“礼门义路”、“必仁且智”。
“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最深刻的差异,在于它们所植根的人性结构。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四德,为人性所固有,它们分别对应四种人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3]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4] 从四德的人性基础来考察,“四心”之中,恻隐之心最根本,是道德的本源,它是一种与同情、怜悯同类的道德情感;羞恶之心、恭敬之心,严格说来都是情;是非之心可以说是理,但不是希腊式的思辨之理,而是性之理、情之理。“四德”—“四心”之中,四分之三是情感,四分之一是理性,因而是一种“理性+情感”并以情感为主体的特殊人性结构。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意志”的“希腊四德”与“理性+情感”的“中国四德”在文化功能上却是一致的,它们的道德哲学的形而上结构都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肯定”—“追求”体系。“肯定”即它们的“理性”结构,“追求”即它们的“冲动”结构。因此可以认为“肯定+追求”或“理性+冲动”是德性的一般形而上学的结构。灵魂的德性与伦理的精神,既需要理性也需要冲动,冲动的非理性结构是德性中比重最大的构成。中西方德性在理性结构方面相似,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冲动结构的性格,由此造就了中西方伦理精神的殊异品质。尤其需要探讨的是,意志与情感都是德性的冲动结构,这两种不同的冲动结构及其与理性的结合,到底给中西方伦理精神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谈到概括意志、情感及其与理性相结合所形成的伦理精神的特殊文化性格和文化气质的哲学概念,就不得不提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孟子的“自然”。康德把道德理解为“绝对命令”。他的道德哲学体系也确实需要“绝对命令”, 因为他将理性区分为纯粹理性(或哲学理性)与实践理性;纯粹理性要确证自己的全部实践能力,就需要发展为实践理性;道德既是纯粹理性的实践能力的确证,也是纯粹理性的实践能力的合理性所在。然而,实践理性如何从理性发展为实践?理性与实践之间过渡的中介是什么?这就需要“绝对命令”。理性向意志下达绝对命令,要求意志无条件地执行并诉诸行动,由此,理性就实现了向实践的过渡转化,真正成为“实践理性”或实践了的理性。所以,“理性+意志”的德性结构需要“绝对命令”作为过渡与中介。但“理性+情感”的德性结构却不需要这个中介,因为在这种结构中,理性向实践的转化,是毋需反思、毋需过渡的“自然”。“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进自然知恻隐。”理性直接转化为冲动,甚至与冲动直接合为一体,即所谓“知行合一”。
之所以如此,根本上是因为冲动的情感机制及其与理性的关系。与意志相比,情感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直接性和非反思性。意志与情感都具有冲动的品质和行为的功能。但意志的任务是将理性转化为行为,因而有待理性下达命令;情感则是基于生命直觉或良知直觉而引起的整体性反映,它直接见诸行为,其向行为的转化往往不需要任何中介,甚至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是一种“自然”。比较两种冲动机制,意志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与合理性,而情感则表现出更大的直接性和执着性。因而,中国伦理精神与西方伦理精神相比,具有更直接的实践性。“知行合一”就是“理性+情感”的德性结构“自然”的逻辑命题和道德哲学结论。
需要辩证认识的是,以情感为冲动结构的人性机制,是否具有合理性?实际上,以情感为道德冲动的根源,并不只是中国伦理的传统,西方伦理中也不乏学术资源。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把道德情感作为人类行为的驱动力。美国生物学家和伦理学家麦特·里德雷认为,道德的产生要求人类天生就具有负罪感和移情能力(即中国传统伦理所说的“羞恶之心”与“恻隐之心”)。杰洛姆·卡根强调:“人类情感,而不是理智,应成为人类行动的动因和力量的源泉。”[15] “除非他们意识到了中国哲学家们许久以前就已领悟到的原理,否则他们仍将不知悔改。这一原则就是:感觉,而非逻辑,才是超我的支撑力量。”[16] 正如心理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缺乏情感,人类将成为“理智的傻瓜”。
如果情感是冲动的直接机制,那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关于思维和意志不是两种形态,而只是对待同一对象的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分的观点,就应当被拓展甚至被修正。因为情感也是冲动的主体和人性基础。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意志理解为最广义的人类活动,将“观念”和“热情”作为历史哲学考察的两个对象,认为“热情”使“意志之所以为意志”[17],是观念与意志或理性与意志之间的中介。黑格尔将意志分为两种:客观的意志与主观的意志。客观的意志是行动,主观的意志是热情。情感只是一种特殊意志——主观的意志。意志与情感,只是“达到定在的冲动”的两种不同态度或不同形态。于是,不只是思维和意志,包括情感,它们是对待同一对象的三种不同态度。由此,情感作为冲动,同样应当也是法哲学研究的对象。
三、谁偷走了伦理
美国伦理学家麦特·里德雷在《美德的起源》一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谁偷走了社会?”效颦里德雷,这里也进行一个类似的诘问:谁偷走了伦理?
对道德危机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忧患与反思,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世界二十世纪的一块心病。无论在现象学还是法哲学的意义上,道德与伦理都具有因果性的生命关联,道德危机的背后是伦理的放失。如果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伦理是人作为人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共体,家庭作为这种共体的基本形态,就是自然的伦理实体;如果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伦理是人的一种“自然”能力,那么必须严肃反思的问题就是:人这种自然的良知与良能到底是如何放失的?我们又如何像孟子所说的寻找“鸡犬之放”② 那样寻找人的良知良能之放?
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及其冲突中寻求伦理道德危机产生的根源。但是,作为伦理学工作者和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者,我们的努力不能仅局限于此。因为这种思考的结果可能是:既然危机是“客观”后果,我们便无能为力,也难以作为,于是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于危机之外,尤其是将自己排除于危机的责任主体之外。久而久之,我们逐渐习惯于这种思维定势,不仅会消解了对伦理道德生活的责任意识,更严重的是,我们将逐渐丧失责任能力。这是一种可怕的职业本性能力的退化。狙击这种退化、恢复职业良知和职业良能的重要学术工程之一,就是在洞察时变以推动伦理道德与时俱进的同时,深刻而彻底地反思我们这些因享受社会的恩惠而有闲暇思考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问题、并且已经过着“优雅生活”的伦理学家和道德教育学家们,为社会所提供的可资充饥解渴的理论资源及其理论体系是否有足够的养份,是否健康,是否健全与合理,从而严肃地回归和对待我们所应当担负的那份学术责任。
仅仅从以上对伦理冲动的讨论考察中就可以发现,社会的与个体的道德能力在学术方面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伦理形态的健全,即认知形态的伦理与冲动形态的伦理必须兼备且形成有机的体系;第二个是推动道德行为的、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息息相通的人性结构、品质结构、能力结构的自觉与合理;第三个是构成伦理精神体系的那些文化要素和文化结构的健全及其自我生长能力的旺盛。围绕这三个要素,便可以从学术研究状况出发简单地回答“谁偷走了伦理”这一发问。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的诱惑和左右下,无论道德哲学还是道德教育,对道德认知与道德理性都表现出过高的热忱和太多的执着。现实的状况是,无论是现代人还是现代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哲学,都不乏对伦理道德的认知过程与理性能力的思考。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道德作为,其实并不需要太高的理性和认知能力。诸如孝亲友朋、扶危帮困,并不需要经过哲学的理性训练,而只需诉诸生命本性的良知良能就可以“自然”地做出判断和选择。在现代性诱惑下,不仅是西方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伦理学者和道德教育学者,已经过深地迷恋于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游戏,消解或丧失了道德直觉能力。其结果是,不仅品质结构,而且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哲学的体系,已经畸形地发育和发展。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古典的和经典的道德哲学家们都指出,伦理和道德的精神结构与理论体系,最重要的是它的冲动形态,认知形态的伦理只是它的基础,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都这样认为。因此,现代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哲学必须给“冲动形态的伦理”以充分的文化地位和学术地位。唯如此,才能恢复伦理的实践本性与价值本性,也才能真正康复现代人身上已经十分孱弱却是根源于生命本性的那份伦理元气。
其次,它与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及其态度、深度相关。二十世纪中国文明发展的主题之一,是文化批判。可以说,作为社会精英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把“五四”以来的那种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发展、衍生为一种批判性格,因而对本土的文化传统缺乏“敬意的理解”,对中西方文化、中西方哲学缺乏生态的把握和比较。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哲学的研究同样存在这一偏向。在上文对“中国四德”的讨论中已经指出,中国道德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下的伦理冲动的最重要机制是情;道德哲学的基本结构是“理性+情感”,以情感为统摄,是“情理”的冲动结构与道德哲学体系。这种结构与西方道德哲学的“理性+意志”结构,具有相同相通的文化功能,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事实上,即使是西方的道德哲学体系,也对情感的伦理功能尤其是在冲动形态的伦理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意义,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但是,在现代道德哲学体系和通过道德教育所建构的现代人的品质构造中,情或被沦为道德中立的放任,或被道德所驱逐。于是,全部的希望被放在了意志听从理性的“绝对命令”上。而当理性的上帝缺少伦理含量,或者这个上帝不再对伦理表现出热忱和关注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绝对命令”从人的意义世界中退隐甚至永远消失,剩下的就只是永无止境的本能冲动。“情理”的机制,是冲动形态的伦理中良知与良能的结构。没有“情”,就难以形成“理”的良知;“情”只有与“理”结合,才是伦理冲动的良能。中国道德哲学中没有“绝对命令”的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没有在人性结构中选择这一结构和概念,但它有自己的伦理冲动形态,这就是情与理相结合而形成的良知良能。所以,无论我们试图在道德哲学体系中恢复冲动形态伦理的形而上学地位,还是在人性中复苏伦理冲动的良知良能,都必须扎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道德哲学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返本开新”、“综合创新”。
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构成当代中国伦理精神体系的文化要素和文化结构不够健全且缺乏自我生长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对伦理道德的概念进行形而上学地分析与把握,更重要的在于把伦理道德作为文化设计和文明体系中有机而辩证的生命过程进行生态地把握。首先必须克服道德哲学研究和道德教育中“伦理”与“道德”不分的粗枝大叶的做法。缺乏深入而细致的概念分析,是不可能真正把握对象和建立缜密的道德哲学体系的。中西方文明、中西方传统道德哲学体系中,之所以出现“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是因为二者有不同的指谓和对象。在道德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育中对两者不加以区分,只能说明我们没有足够的概念辨析能力和敏锐的哲学洞察力。现代道德哲学,不仅要仔细探讨和研究伦、理、道、德、得这五个要素的概念结构及其发展变化,更重要地是要把握伦—理—道—德—得这四个辩证过程的转换条件以及由前者向后者转换的动力。唯有如此,伦理精神和道德哲学,才不仅是一个有机的体系,而且具有自我生长、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之,现代道德哲学和现代道德教育要找回放失的伦理,在学术上至少需要进行三种努力:建立认知形态的伦理与冲动形态的伦理二位一体的健全体系;对冲动形态伦理给予真诚而肯定的关注及充分的研究,尤其要重视对伦理冲动的民族机制与民族文化结构的回归;道德哲学概念体系和道德教育的健全与完整。
断言生活的危机根源于理论的危机当然失之公正,但理论至少应对生活危机承担一份严肃的责任。否则,不仅理论研究,而且理论研究者自身,都将成为社会文明体系中的多余者甚至是寄生物。
本文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重大招标项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思想道德与和谐伦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5&ZD040 )以及东南大学“985”项目成果。
收稿日期:2006—03—04
注释:
① “我们就把灵魂的德性加以区别,有一些我们称之为伦理的德性,另一些我们称之为理智的德性。”(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②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