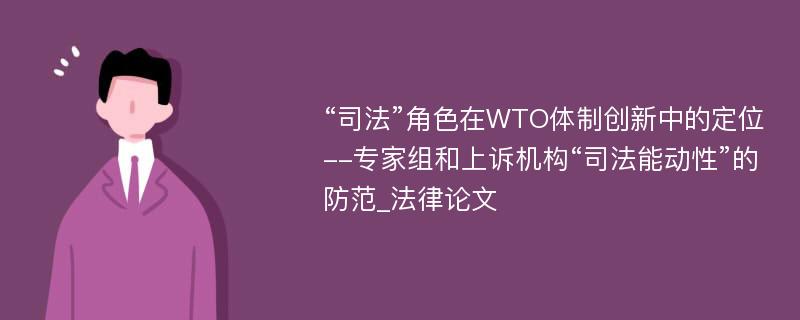
WTO制度创新中的“司法”角色定位——对专家组、上诉机构“司法能动性”的防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论文,能动性论文,专家组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调整政策纳入WTO法律体系存在三种可能的模式,即司法能动模式、(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上诉机构在解释WTO协议的时候,要使贸易规则更好地适应贸易和社会政策。有人主张WTO协议第20条b款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例外应解释为允许贸易和环境价值的平衡,第20条a款公共道德的例外应解释为允许国家针对那些以否认工人基本权利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采取贸易制裁措施。)
契约模式(注:事实证明通过谈判的方式把贸易政策和各种新议题连接起来是困难的。TRIPs协议要求成员方承认并执行知识产权。在其他一些议题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尚未有效纳入WTO体系。)和立法模式。(注:在国际层面上,立法模式的例子很有限。联合国安理会有10个理事国和5个常任理事国,决策的通过要求有9个以上的理事国投肯定票,其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这三种模式都关系到WTO决策的民主性和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公平性。在三种模式间进行选择,决定哪种模式是WTO立法更可取的方式将影响到国家的相对权力。在当前这个价值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不同的价值和利益如何在WTO成员间达成协议?WTO上诉机构能否基于对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理解把其他国际法规范并入WTO协议或发展WTO协议?抑或成员方代表国内人民的意志,应该由他们通过政治途径达成协议来制定政策?这些就是制度能力的问题,即决策权在成员方和WTO的各组织间的适当分配。
笔者所持的是契约模式的立场。契约模式要求发展国际社会政策应通过契约条约制度而不是司法能动性。国际习惯法和其他国际法规则不应该在一般意义上并入WTO法,除非有WTO协议的特别授权或国际法规范对程序性问题提供了有用的指导。“主权契约”模式是协调民主合法性、国家主权和社会政策的可取途径。
一、社会政策纳入WTO法律体系的三种模式
立法模式、司法能动模式和契约模式构成了国际政策制定的几种主要模式。每种模式在国内社会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WTO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根据。立法模式(在某些国家中由司法能动性进行补充)是国内立法的首选方式。在民主社会中,若法律政策经过立法机构中人民代表的多数或特别多数批准,则该法律政策通常被视为是合法的。(注:由立法机关发展法律规则和法律政策从两方面的意义来说是合法的:其一,若法律是根据宪法程序或传统程序制定出来的,就符合了形式合法性或者说是“法律”合法性的要求;其二,法律规则被视为合法通常是因为某一社会认可规范具有拘束力。)立法者通过定期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注:民主选举能够确保政府持续地对社会负责。)与国内法律体系不同,WTO的成员方主要是主权国家,各国的公民没有机会对决策直接投票,也无法通过选举代表立法来间接参与。只有国家是这个法律体系中的正式成员和正式参与者。若通过多数国家表决作出决策符合民主合法性的要求,这种通过多数表决的决策方式就必须由对人民负责的立法机构事先批准。
在WTO体系中,成员方的确对它的主要机构进行了有限的授权,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注:WTO协议规定部长级会议为主要的治理机构,但是部长级会议每四年才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休会时由总理事会行使部长级会议的职能。这两个机构都由每个成员方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有权以特别多数票通过对协议的解释和修正。而实际上,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都未曾行使过这种模糊宽泛的权力。这种立法权未能充分行使可能部分归因于3/4多数通过这一要求太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成员方认为订立新的协议更符合WTO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合法的立法程序。绝大多数国家仍不愿通过多数表决规则制定国际法,这种立场反映了国家一贯坚持的主权信念,即每个国家应该独立决定是否接受一项限制其行动自由的义务。(注:See Raj Bhala,International Trade Law:Theory and Practice,p.584(2d,ed.2001).)此外,不采纳多数决定原则也是国内民主性的要求。政府可能不愿意使其国民受到与他们利益冲突的制度的支配。反对一项特定解释的某些国家的国民即使在他们或他们选出的代表都没有批准该项政策的情况下仍对该项政策负有义务。因此,国家仍然把订立协议的方式作为制定新政策的首选立法模式。当新协议提交给立法机关批准时,国内针对该项决策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而这些不同的声音若采取多数表决的方式则可能会被忽略。
司法能动模式,是指WTO法律体系明示或暗含授予上诉机构法官一定的权力,使其能够根据国际社会的变化对WTO协议作出扩张性解释。通过司法能动性把非贸易价值纳入贸易机制是两方面的发展交互影响的结果:一方面的发展就是新的WTO争端解决制度取得了成功。现行的争端解决制度为成员方规定了强制性的争端解决程序,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在国际贸易体系内通过规则解决争端的机会。WTO成员方可以向专家组提出申诉,专家组裁决中的法律问题又可以上诉到专业性更强的上诉机构。理论上争端解决机构(DSB)可以推翻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裁决,但实际上DSB全部通过了这些裁决,这就使得这些裁决具有了司法裁决的效力。(注:See Raj Bhala,The Precedent Setters:De Facto Stare Decia in WTO Adjudication,9 J.Transnat'l.l.& Pol'y 1,p.4(1999).)另一方面的发展就是各国普遍缺乏一种协调一致的政治意愿来系统地解决像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持续性违反人权这样一些问题。(注:参见刘笋、李国赓:《关于“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及WTO调整范围的若干思考》,《法商研究》2003年第5期。)
支持司法能动模式的学者认为,WTO法律体系部分或在某些方面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国际法规则原则体系,这些规则原则可以支配上诉机构的裁决。这一理论又存在着不同的版本。Robert Howse和Makau Mutua认为条约法规范效力低于国际习惯法和强行法规范。(注:See Robert Howse & Makau Mutua,Protecting Human Pights in a Global Economy:Challenges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0).)David Palmeter和Petros Mavroidis主张《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DSU)把国际法的各种法源并入了WTO法,这些法源都与WTO协议的解释相关。(注:See David Palmeter & Petros C.Mavroidis,The WTO Legal System:Sources of Law,92 Am.J.Int'l L.p.398,p.399(1998).)Joost Pauwelyn主张,WTO法是国际公法的一部分,在WTO裁决中可以适用非WTO规则的国际法规范,除非成员方专门把某一特定规范排除在外。(注:See Joost Pauwelyn,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How Far Can We Go? 95 Am.J.Int'l L.pp.537-539 (2001).)在他们看来,用国际习惯法规范填补WTO法的空白是合适的。此外,嗣后建立在各方同意基础上的条约可以取代相应的WTO规则。
契约模式认为,WTO贸易制度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特定协议的基础上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这种模式把国家和个人作了类比,个人在国内社会中自愿地通过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创设法律。而在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WTO中,国家接受市场准入和非歧视等有限的义务,以此来换取其他国家的对等承诺。因此,WTO主要是由规则构成的,不存在一个立法权威。(注:See Bruno Simma,Self-Contained Regimes,16 Neth.Y.Bk.Int'l L.p.111(1985).)根据这种模式,一项新的实体政策,若没有所有受其约束的国家的协商一致,则必然会减损某一成员方的基本权利,由此相关新政策的并入要对契约进行重新谈判。
但是,实际上纯粹的契约机制却是不可能的。再详尽的规则也不可能预见所有将来的情形和消除所有用语的模糊性。WTO协议包括规则和标准。规则界定了需要实施的行为。标准,如WTO第20条b款关于人类和动植物健康例外的规定中,“necessity”这一词语只是给行为者提供了一个导向。(注:See Louis Kaplow,Rules Versus Standards:An Economic Analysis,42 Duke L.J.p.557,pp.559-560 (1992).)但日益人性化的国际社会和经济全球化新情势需要WTO对规则及其适用作出判定。这种不可预见的情势以及协议中空白和模糊的地方为司法能动性创造了机会。
二、司法能动模式运用于WTO政策制定的不合理性
(一)司法能动模式与WTO法律体系的性质不符
关于司法能动性,当前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1)并入问题,即国际习惯法和其他的国际法规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并入WTO争端解决的规范。(注:提出并入问题的学者认为WTO协议是国际公法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国际法规范可以适用于WTO,除非成员方通过契约特别排除某一规范的适用。国际法规范可以作为成员方违反WTO规则的证据。)(2)创造性解释问题,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WTO规定的过程中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自由裁量权造法。在WTO协议存在很多空白和模糊之处的情况下,对上诉机构的权限作出适当定位就要明确成员国在一般意义上选择了哪种模式来制定政策。
从GATT体制来看,GATT1947似乎更符合契约模式而不是司法能动模式。GATT是由23个缔约国在对等的基础上谈判达成的协议。(注:See generally Robert E.Hudec,The GATT Legal System and World Trade Diplomacy (2d ed.,1990).)其争端解决体制不具有强制性。GATT缔约方澄清和补充GATT规范是由一轮轮的贸易谈判实现的。(注:在1947-1995年间,GATT进行了几轮贸易谈判。前5轮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展开的,在肯尼迪和东京回合才开始针对一些富有争议的非关税壁垒问题进行谈判。)协议的变动需要取得其他贸易伙伴的同意。新的WTO协议从根本上改变了争端解决的结构和过程,但却继承了GATT契约性的条约机制这一传统。WTO协议明确界定了成员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日本酒税案中,上诉机构指出:“WTO是一个条约——契约的国际形态。成员方为了获得他们期待的利益,必须按照他们在WTO协议中作的承诺行使主权。”(注: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AB-1996-2,WTO DS 8/AB/R p.15 (Oct.4,1996).)
从DSU的规定来看,上诉机构并入非WTO规范和进行创造性解释都与WTO法律体系不相容。DSU第3条第2款明确界定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职能:“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损成员方在各涵盖协议项下的义务。”如果上诉机构并入非WTO规则来修改成员方的权利、推翻WTO规范或赋予WTO规则明确排除的贸易制裁以合法性,那么成员方的权利必然会减损。同时,DSU也明确排除了条约解释WTO协议的可能性。DSU第3条第2款规定,争端解决的首要目标是为贸易体系提供安全性和可预见性,保持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澄清现有的规定。这些规定都充分表明了现有的争端解决体系是一个契约性的法律适用体系,旨在维持现有的协议,而不是授权上诉机构根据他们对情势变化的判断解释WTO规则。
上述分析的惟一例外就是可以把“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并入WTO法。DSU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并入条约解释的习惯法规则。但该规定不是要一般性地并入国际法,而是要使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解释WTO协议。(注: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已经对第3条第2款中“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这一表述进行了解释,认为其指的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解释规则。)若无此类规定,上诉机构就需逐案地发展自己的解释规则。解释规则的并入是成员方选择的结果,是符合契约方式的。
笔者认为,DSU在实体规范方面创造了一个本质上自给自足的体系,(注:参见徐崇利:《从规则到判例: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的定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这一结论也可以通过DSU所规定的救济方式得到证实。DSU规定成员方对于不利的裁决可以选择补偿或接受报复等。(注:See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Apr.15,1994,WTO Agreement,Annex 2,Legal Instrumen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1994).)这种弱执行机制由于顾及了成员方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允许成员方在国内存在重大利益执行裁决困难的情况下不执行裁决或建议,因而发挥着安全阀的作用。
由此可见,DSU明确地规定了WTO各机构间的权力分配。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这种权力的划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国际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家间存在文化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这就要求利用政治方式有效地解决争端。
(二)司法能动模式不符合民主合理性原则
除了前面所述理由外,司法能动模式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还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首先,WTO的成员方对影响他们权利义务的决定无权参与和表示首肯。例如,在虾/龟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生物构成了“可用竭的自然资源”。上诉机构作出的这一断定不是根据成员方谈判达成的协议文本,而是参考了其他的国际文件。(注:See 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United States-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AB-1998-4,WT/DS58/AB/R,(98-3899),p.173 (Oct.12,1998).)由此,上诉机构发展出了一套新的演进式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与DSU所规定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解释方法是相冲突的。更重要的是,这一裁决实际上允许美国为了执行其认为适当的环保政策和救济措施实施单边的贸易制裁。上诉机构所实施的这种政策创新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发展中国家丧失了市场准入的机会,削弱了其在后面的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谈判能力的削弱会减少发展中国家获得补偿或财政援助以弥补其为满足西方环境政策而增加的成本。
其次,司法能动性在各成员方国内也侵蚀了WTO决策的合法性,因为这些政策没有经过选民代表的同意。上诉机构在缺乏明确授权以及无法使决策对人民负责的情况下制定重要的调整政策无疑是在冒险。要让各国绝大多数的公民乐意接受以这种方式制定出来的社会政策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反,用契约方法达成的协议通常都会提交给国内的立法机关批准。
最后,从虾/龟案来看,上诉机构允许国家采取单边制裁措施以达到社会规制目的,这也不符合民主的概念。(注:See Mark P.Gibney,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U.S.Law:The Perversion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the Reversal of Institutional Roles,and the Imperative of Establishing Normative Priniciples,19 B.C.Int'l & Comp.L.Rev.p.297,pp.305-308 (1996).)这实际上是允许一国把自己特有的社会政策域外适用于其他国家,而不需要这些国家的参与或同意。实施物种保护和保护成本之间的平衡是由华盛顿决定的,而不是东南亚国家或南美国家。受影响的国家既无法影响这些法规的制定,也无法改变它们。
从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的角度看,单边制裁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更关心生存问题,而不是高水平的环境质量。他们希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后代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些国家的国民优先考虑的事项与那些富裕的后工业时代国家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异。此外,西方发达国家那些规定货物生产方法的国内社会法规之所以能够产生也是内部利益群体施压的结果,这些利益群体包括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受影响的国内工业界。(注:参见王彦志:《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这些国内工业在狭隘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主张提高进口产品的生产成本以使其产品更具有竞争力。(注:有些学者主张,WTO司法的最重要机能是限制保护主义群体,促进贸易自由化,而不受一小部分群体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拥有的可支配收入比较少,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会选择那些只有最发达国家的国民才能够支付得起的昂贵的环境和劳工措施。
(三)习惯国际法的不确定性
司法能动模式的支持者们对习惯国际法怀有“崇高”的信仰,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环境、人权或劳工价值并入WTO体制。一些人主张习惯国际法规范效力高于条约法规范,在两者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优先适用。其他人则认为,习惯法规范是通过对DSU的扩张性解释并入WTO的。那么,习惯国际法规范究竟能否作为合法的法律渊源?
习惯国际法是指通过国家普遍持续的行为而接受为法律者。(注:See Anthony A.D'Amato,The Concept of Custom in International Law (1971); Ian Brownlie,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p.4-11 (4th ed.1990).)它由两个要素组成:(1)国家实践,这是习惯国际法的行为证据;(2)法律确信,是指国际社会对某一法律规范的效力已经形成普遍信念。习惯法是隐含的法律,是一社会的成员所一般遵守的行为准则。国际社会不是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而是由一系列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组成的,其缺乏国内社会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习惯国际法作为一种意图修改或取代WTO协定的法律渊源其自身有很多严重的缺陷。
首先,不存在确定国际习惯和国际社会“一般认可”的方法。国际社会在什么可以作为印证行为的国家习惯、如何权衡种类繁多的国家习惯的问题上观点大相径庭。在国际上也缺少一个拥有普遍管辖权、对确定习惯具有约束力和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法庭。由此可以看出,普遍接受不过是学者和法官选择自己所偏好价值的一个虚构。如果没有一种一致同意的方法就不可能客观地确定规范。
其次,国际习惯法规范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这更为WTO上诉机构的贸易专家提供了不受约束的裁量权,使得他们得以脱离政治程序创造规范。国际习惯法中的很多规范只是观念的问题,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别很大。例如,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关于国有化征收时按市场价完全赔偿的义务的观点不过是美国所持的政治立场的反映,这一观点在19世纪早期就遭到拉丁美洲国家的坚决反对。
最后,在由180多个国家组成的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的国际社会中,国际习惯法的立法过程是一个低效的过程。历史上只有很少的国家参加了所谓习惯规范的创设,持有异议的国家的观点经常被忽略。(注:See For an Extensive Analysis of the Defects of CIL legal theory,see J.Patrick Kelly,The Twilight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40 Va.J.Int'l L.p.449 (2000).)国际习惯法的立法程序和民主治理的价值互不相容。国际习惯法不允许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进行广泛的谈判,不允许慎重地审议其他政策,并且不提供调和不同价值的场所。(注:See Anthea Elizabeth Roberts,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A Reconciliation,95Am.J.Int'l L.p.757,pp.767-768 (2001).)这一过时的方式在交通、通讯落后的19世纪尚可理解,但在今天多元的国际社会中绝不是有效、明智的立法方式。
“并入理论”和“创造性解释理论”均认为,在国家间存在广泛的共同价值和规范,这些价值和规范可被用来澄清不完整的国际条约或填补国际条约中的漏洞。这些理论在价值和利益相对统一的国内社会中可能会起作用。因为国内的共同目标和历史传统可提供澄清立法价值和认同的规范,而国际社会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各国对于如何平衡社会政治目标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只有“契约方法”才能改善国家间经济利益的差异,调和国家间复杂的政策视角。
(四)司法能动模式引发了道德问题
WTO中的司法能动还引发了根本性的道德问题,影响了规范的生成。美国和欧洲的社会活动家宣称应将一些本质上与个人主义相联系的西方价值观引入WTO,如劳工权利以及西方社会最近的政策偏好。尽管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参与这些目标的制定,但这些目标仍将被施加于发展中国家。那些鼓吹禁止使用童工产品的人士根本就不了解人口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的严峻贫困现实,不了解儿童缺乏受教育的资源,不了解这些国家里家庭没有其他可替代收入供养这样儿童的实际。(注:See Anthea Elizabeth Roberts,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A Reconciliation,95Am.J.Int'l L.p.757,pp.767-768 (2001).)发达国家的劳工法不应施加给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初期这些法律也是不成熟的。
司法能动更严重的后果是经济上的。将发达国家的环境和劳动标准施加于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直接导致其生产成本提高,进而抑制了其经济的发展。童工法、工作安全法、最低工资立法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却是相对发达的中产阶级社会的产物。美国不是启动积极的政策、财政资助计划,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父母将未成年的子女送去上学,而是限制这些国家的贸易,这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给美国的经济增加了潜在的成本。
将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侧重点强加于经济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常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注:在人权领域,不同的国家持有不同的人权观。多边主义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其清除了伴随单边制裁的帝国主义和文化偏见。)在国际规范中道德要件不可缺少,因为遵守国际规范通常是基于互利。如果上诉机构准许实施单边环境标准(事实上其在虾/龟案中和其他情形下似乎已经允许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会在WTO中集体反对。在国际贸易领域,现在所谓的利益平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远非令其满意。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显示,尽管发达国家的关税普遍较低,但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优势的领域继续保留着非关税壁垒。(注:See Globalization,Growth and Poverty: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p.130(2002).)发达国家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单边主义的做法可能彻底破坏50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三、限制司法能动主义的司法克制原则
从契约模式和上文所讨论的法律权限与民主合理性原则出发,笔者归纳出几条适合于上诉机构角色定位的司法克制原则。从契约模式演绎出的第一个原则是:上诉机构可以在创设程序权利方面有重大的立法权,但却无权通过创造性解释WTO条文或随意在WTO法律规则体系中并入其他国际法律规范来改变、减损成员方的实体权利。DSU鲜见有关诉讼资格、举证责任等一系列程序问题的规范,因而这方面亟须司法立法。在实体权利方面,最近的一些判例显示上诉机构在拒绝使用其他条约或国际习惯法解释WTO协定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一致。在“欧共体牛肉案”中,上诉机构拒绝并入国际习惯法,其理由是:并入国际习惯法会修改成员方的契约权利与义务。上诉机构认为,虽然“谨慎性原则”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原则,但如果没有条文依据它就不能取代《实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定》中的具体条款规定。(注:See 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on European Communities-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 (Hormones),(Jan.16,1998).)
然而,在虾/龟案中,上诉机构的解释方法却令人担忧。上诉机构在该案中通过行使解释权利扩大了经济强国的实体权利,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首先,上诉机构对“可用竭自然资源”的发展型解释方法使得其他国际条约的条文和宗旨凌驾于WTO谈判条文之上,这与上诉机构保持成员方权利义务平衡的职责明显不符。上诉机构的职责决定了其不能推测当下国际社会对以往谈判议题的态度。其次,任何一国际条约中都包含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的微妙平衡。一个条约中术语的含义,如“可用竭自然资源”,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将GATT1947第20条g款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第20条b款的“人类和动物健康危害例外”损害了b款的原始立法意图,即市场准入和“保护人类、动物、植物生命”所必需的规章的例外。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上诉机构扩大第20条g款的适用范围违背了其无权改变成员方权利义务这一原则,但虾/龟案不应被认为是对单边制裁的许可。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该款序言中的“不合理歧视”应当被解读为鼓励多边合作。(注:See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Apr.15,1994,WTO Agreement,Annex 2,Legal Instruments,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1994).)上诉机构还指出,要求其他国家采取相同环境标准的措施带有歧视性,任何一项措施的实施必须首先探讨将该措施适用于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的出口国是否合适。
适合WTO契约体制的第二项司法克制原则是:在成员方没有就一项一般政策作出决议以至于无法可依时,上诉机构应当将该问题留给将来的谈判解决,而不是试图主观推定现今国际社会对此政策的看法。无法可依的情形在WTO体制下会经常出现,原因在于WTO协定并非一综合性的规范体系,而只是一系列限制成员方主权以求互利的契约安排。在虾/龟案中,动物是否属于GATT1947第20条所指的“可用竭自然资源”在以前的谈判中并未涉及,这一争议应当提请成员方共同解决。在此情形下,上诉机构应当将其视为一不适合其裁判的政治问题。(注:See Jeffrey L.Dunoff,The Death of the Trade Regime,10 Eur.J.Int'l.p.733,pp.757-759 (1999).)
指导司法决策的第三项原则是:其他国际组织的习惯和相关规则可以为WTO程序法立法提供借鉴,但这些规则和习惯不是决定性的,有的可能还不适合WTO。例如,在“欧共体香蕉案”中,上诉机构明智地抛弃了国际法院规则中有关起诉方必须具有法律利益的要求,允许每个成员自由裁量,决定是否申诉。在贸易环境下,任何成员方都有可能是出口方,都对国际贸易规则有经济利益,因此,上诉机构必须能自由裁量,进而创设最适合国际贸易体制的程序规则。
指导司法决策的第四项原则是:不应利用国际习惯、规则和其他国际协定将新的涵义注入WTO实体规范。其他国际协定的规范很难为解释WTO协定提供帮助。任何具体的协定或一般的国际法原则都不能为WTO协定术语的解释提供指导。例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其原则可指导政策决策,但在WTO中应当由成员方进行政策制定,而不是由没有经过选举、缺乏民主合理性的司法机构来制定政策。在虾/龟案中,上诉机构运用的“演进式”解释方法错误地阐释了上诉机构在WTO法律体制中的地位。上诉机构并不是一个有着创设一套综合性、一致性国际规范之目的和宗旨的机构。实际上,上诉机构最实际的任务就是根据现有的、经成员方谈判达成的不完整的权利和义务协议来解决贸易争端。
最后一项原则是:上诉机构不应当将WTO协定解释为允许成员方通过单边贸易制裁措施将其社会政策强加于他国的产品,除非该外国产品本身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构成威胁。当美国、欧共体这样的国家或组织利用单边制裁措施实施其环保和卫生健康等标准时,他们所适用的都是发达国家的政策标准,而这些标准的制定并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同意,这将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成本。国际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应当顾及单边措施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应当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允许WTO成员方通过单边制裁措施实现各自政策目标将损害成员方对WTO规则的尊重,动摇成员方通过争端解决体制解决争端的信心。
四、结论
WTO规则的合理性有赖于成员方的同意。WTO协定由成员方谈判达成,并最终由成员方国内立法机关批准通过。明确的国际同意和立法批准使得WTO协定在国内层面上具有民主合理性。上诉机构所拥有的一切权限都是由成员方通过契约型协定所授予的。WTO现有的立法程序就是通过一轮轮谈判来制定新规则、改善现有规则。当前有关谈判新议题的激烈争论显示了成员方在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成员方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不可能由上诉机构的法官来调和。
另外,DSU充分明确地表明上诉机构没有被授予修改WTO协定项下实体权利和义务的权力。为忠实于国家主权和民主合理性理念,当成员方对一实体规范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或有完全冲突的经济利益时,上诉机构不应该认为自己被赋予了创设、修改实体规范的权力。发展中国家不愿在将来的贸易谈判中谈判环境或劳工标准问题的一贯立场,也表明了其根本就不同意所谓的“默示授权上诉机构创设实体规范”的态度。
标签:法律论文; wto论文; 国际法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能动性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习惯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