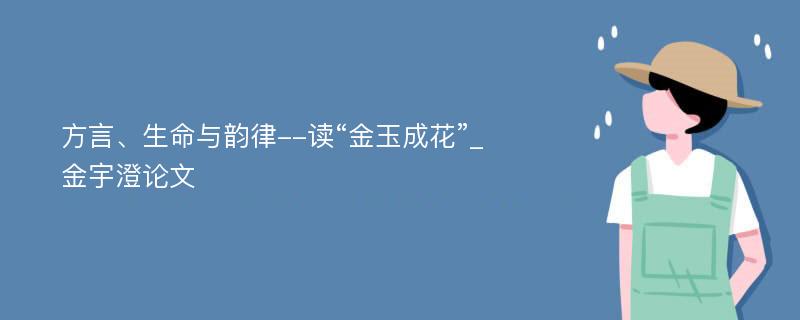
方言、生命与韵致——读金宇澄《繁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韵致论文,繁花论文,方言论文,生命论文,金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西飏说:“《繁花》的路数,几乎是现今小说潮流的相反方向,它的叙述部分被压缩至最低限度,对话量则无限放大,并承担起许多原本叙述的功能……写上海和上海人开口没那么容易。”①开口的上海人都是上海话,不再是改造的普通话,这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方言对话承担起叙述的功能,创造一种不同于同时代主流的语言方式和讲故事的方式,或许后者更为重要。 一 方言的引子 《繁花》的惊艳,首先来自一种借由方言起事的活力。方言提供了一种对既成文学形式、文学现状反动的可能。胡适等人开创的新文学及其语言方式,已经逆转而成为主导文学方式,反而在非自觉情势下不断挤压方言文学的空间。于是《繁花》的出现就回到了胡适的问题:到方言的文学里去寻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难之语就是要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摒弃僵硬的文学、濒死的文学、假的文学。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唯实写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实写社会之情状,不一定非要走上自然主义写作的道路,方言是一个写作方式上的靠近实际生活的选择,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②文学上的沪语方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征南方语言,它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具有某种潜在的对抗性质,除了在《海上花列传》《何典》《九尾龟》等明清小说中大量使用过沪语方言,1949年以来的上海文学创作,基本都是普通话为主的书面语写作,方言只有在人物对话中偶或使用。方言因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的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可供想象的表情、会意点,这些基本无缘成为实写社会之情状的小说的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一个特别尴尬的现象,上海作家所书写的上海生活与真实发生的生活隔着方言的帷幔,经由的中介是作家翻译成的普通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具体生活情态中原生的活力和复杂,当然这也是所有尚且使用方言地域的文学正在遭遇的尴尬。 我们因为方言文学重新发现了一个世界,那么是不是就认同方言文学是国语文学、普通话文学的一个简单的映照,是他们有益补充或者重建的基点?胡适又几乎推翻了此前作为新鲜血液的说法,他在《〈吴歌甲集·序四〉》中说:“至于方言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它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它们做原料而保存。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胡适提出了对方言文学的一种自足性的最高要求,方言文学不是提供材料,它本身是一种文学方式,并且能够创造出国语文学的另外景观。 金宇澄在《繁花》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以后,也不认同把它指认为一部“方言”小说,他认同的是方言“小说”,或者说是普鲁斯特意义上的文学语言,既不是方言,也不是书面语,是一种自造的外语,金宇澄在访谈中引用过普鲁斯特的话:“文学在语言中开拓了一种外语,它既非另一种语言,也非被重新发现的方言,而是语言的生成它者,是这一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是将它掠走的谵妄,是逃脱了主导体系的巫婆路线。”③这种文学通过创造句法,分解或破坏母语,并且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所以如果作为整体的语言不被颠覆或推至极限,推至由不再属于书面语言的视象和声响构成的外部或反面,那么就不可能在语言中形成一种外语。作为看者和听者的作家,写作的目的就是呈现生命在构成理念的语言中的旅程,将一种沉潜在方言中的生活和生命转译成方言文学。金宇澄说:“语言是为小说服务的。沪语小说最吸引读者的还是它独有的文学价值,也就是小说通过上海话呈现出来的上海生活。因此小说中的沪语应该是容易让人懂的且能增加读者阅读乐趣的沪语。这样既能让小说的文学价值被读者更广泛地接受,也有利于沪语的推广。否则,沪语小说只是有局限性的方言地域小说。所以我在书中抹去了大量阅读障碍,避免了沪语的拟音字,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舍弃。我营造出沪语的氛围和韵味,突出沪语的内在精神,所以书中的上海话应该连北方人都能读懂。”沪语的氛围和韵味,来自于更深层的沉淀,来自于方言对地方历史生活智慧的结晶。作为自幼习得的语言,方言本身是一种文化力量和文化模式,必然在更进一步的层次上包含着由地方文化观念、价值、准则、习俗所塑造的思想和行为之中。逃离了原生态的本地方言,生成了方言的文学。 当下小说写作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国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作家、批评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从思想能力的孱弱、想象能力的缺失,到批评精神的荒芜,语言的苍白,总之是无力奉出与这个焦躁、疲惫、价值观混乱的时代相称的文学作品。而作为与新时期文学几乎同步的文学杂志编辑金宇澄的看法可能更加具有现场感,只不过他更关注怎么写的问题,他在访谈中指出当下小说的一个症结是:“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残守故事完整性,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功能丧失殆尽。”④《繁花》的方言世界可以看做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金宇澄用《繁花》带来一桌低姿态方式的视觉、听觉的盛宴,并向语言索取了一种新的编码方式,由此所呈现的故事,必然带来惊奇、感叹。 二 生命的旅程 金宇澄说不希望自己的小说被作为方言小说来看,是对方言文学自足性的维护,也是对小说中从197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上海生活和“生命”的尊崇。我们都知道建立在社会语言上的文学语言永远摆脱不掉一种限制了它的描述性质,因为(在社会实际状况中的)语言的普遍性是一种听觉现象,而绝不是说出的现象。对话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呈现听觉的方式,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语言的囚徒,语言或者说话标志着、充分确定着和表现着人及其全部历史的。《繁花》有一段写沪生和老师的对话: 三年级上学期,沪生到茂名南路上课,独立别墅大厅,洋式鹿角枝形大吊灯。宋老师是上海人,但刚从北方来。有次放学,宋老师托了沪生朝南昌路走,经瑞金路,到思南路转弯。宋老师说,班里叫沪生“腻先生”,啥意思。沪生不响。宋老师说,讲呀。沪生说,不晓得。宋老师说,上海人的事体,老师不懂。沪生说,斗败的蟋蟀,上海叫“腻先生”。宋老师不响。沪生说,第二次再斗,一般也输的。宋老师说,不想奋斗了。沪生说,是的。宋老师说,太难听了。沪生说,是黄老师取的。宋老师说,黄老师的爸爸,据说每年养这种小虫赌博,派出所已经挂号。沪生不响。宋老师说,随便跟同学取绰号,不应该。沪生说,不要紧。宋老师说,考试开红灯,逃学,一点不难过。沪生不响。宋老师说,不要怕失败,要勇敢。沪生不响。宋老师说,答应老师呀。沪生不响。宋老师说,讲呀。沪生说,蟋蟀再勇敢,斗到最后,还是输的,要死的,人也一样。宋老师说,小家伙,小小年纪,厉害的,要气煞老师对吧。宋老师托一把沪生说,认真做功课,听到吧。沪生说,嗯。此刻,两人不开口,走到思南路,绿茵笼罩,行人稀少,风也凉爽。 在这一段中,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参差地平衡,基本全是小短句,停顿性强,配合对话者的语气和节奏,像是匀称运动的时钟,没有一分钟的延误,不疾不徐,跟时代的风起云涌刻意隔开了距离,做出了叙述者刻意放低的姿态。同时这一段也把沪生散淡的性格凸显出来,沪生在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把人生看出了眉高眼低,有一股未老先衰的暮气——蟋蟀再勇敢,斗到最后,还是输的,要死的,人也一样。关于斗败的蟋蟀这个形象,在后文我们可以看到沪生、阿宝、小毛等一干人的身上都有它的影子,他们无意识去成为一个时代的强者,也没有一份自信的面容。这也就为小说中俯拾皆是的边角料故事定下了基调,从一种主流化的故事世界逃脱之后,这个世界才会打开它的盒子,涌出一万个好故事,于是我们看到陶陶和芳妹的故事是这样的,经历万难恩爱同居,芳妹却不小心从阳台上掉下摔死,警察拿出她的日记,里边都是在骂陶陶,几月几号没交房租,几月几号在干嘛,两个人恋爱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特别懂事,特别好,陶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看到小毛下班时在汽车站等通宵车,遇到一个女人,搭讪中让女人到家里去洗衣服,进屋以后,女人一直不吭声,但很自然,像回家一样,正值夏天,把衣服脱了,文胸短裤,帮小毛倒洗澡水,给他擦身体,自己再放水洗澡,最后上床躺在小毛身边,两人开始做爱,早晨四点多钟,女人叫醒他说“我走了”。迷迷糊糊的小毛听见门锁的声音,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人。诸如此类的这些故事之所以被称为“好”故事,是因为他们被统辖了时代的故事占去了可以示人的尊严,或者在转译成书面语时遭遇了呈现的困难。沪语方言和低姿态给予了这些故事以生命和尊严,来充实上海都市生活的实感经验。 《繁花》这部小说的主体故事分成两个时代,六七十年代多半是悲剧,八九十年代以闹剧为多。 小说中的梅瑞跟沪生、阿宝都谈过恋爱,三个人的关系诙谐而实在。梅瑞说,沪生结婚大半年,老婆跑到国外不回来,沪生肯定有生理毛病。而阿宝,梅瑞则怀疑他有心理问题,因为两个人一直有联系,到关键阶段就装糊涂。梅瑞的评价多半是讲讲笑话,消遣一下自己交往过的两位男人。不过玩笑话里也可以看出两位的生活态度,都在有意无意地逃避那个世人所趋之若鹜的“正常”。整部小说大半篇幅都是些花花草草的故事,添枝加叶,故事有荤有素,多半来自他人的讲述,也是所有故事最热闹的部分。而他们自己的故事,却都是寥落的,沪生、阿宝的故事几乎都很平淡,或者当事人在重逢旧事时不响而过。阿宝跟蓓蒂、雪芝、梅瑞、李李,沪生跟姝华、小珍、兰兰、梅瑞,点缀在八九十年代的生活中。这就使得小说三个主角阿宝、沪生、小毛三入党中,有两个人对世界是冷冷地观望的,就像八九十年代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流连于各种各样的聚会宴席,应了小说以对话为主要呈现方式,人生就是旁听侧谈。小毛相对另外两个男人来说是一个异数,他的世界中有剧烈的情感,有一种执着,先是对银凤动了心,在不明原因的分手后,跟沪生和阿宝由于误会,伤心大恸,决定拗断与二人的友情,彻底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友情的世界。小毛在母亲的安排下寻到春香结婚,走上了一条循规蹈矩的庸常之路,他从不情不愿到最后爱上这个女人。不过小毛的世界总是福祸相依,阻隔了他郑重选择、努力经营的生活,春香死于难产,留下小毛单身一人。从生活形式上来说三个都是一样的单身男人,只不过阿宝和沪生是主动的选择,小毛是被动的选择,是命运的手划过他的脸庞,所以小毛是悲剧感最强的一个人。 小说中沪生的出场是从旁听侧谈开始的,在沪生和阿宝与小毛拗断友情之后,替代小毛位置的就是陶陶,陶陶一入小说就是他绘声绘色讲述菜市场的各种八卦绯闻故事、男女私情。吊诡的是,陶陶几乎成了小说中最具八卦性质的主角。陶陶和芳妹是正经夫妻,陶陶先是招惹了潘静,潘静三番五次骚扰芳妹,闹得家庭不安静,陶陶甩掉潘静。不久,陶陶发现了让他欲罢不能的小琴,最后要离开芳妹,和小琴厮守。恼羞成怒的芳妹与陶陶之间开始拉锯战、家庭大战,一幕幕的狗血剧上演,陶陶乐在其中不疾不徐,终于获得自由身,抱得美人归。不承想却乐极生悲,小琴跌落阳台殒命,陶陶看到小琴的日记,原来自己幻想的好女人与爱情都是镜中风景,折腾到最后,居然是一场空。梅瑞、梅瑞妈妈与香港小开关系不清不楚,先是热闹红火地做生意,随后生产线出了问题,变成上海瘪三。李李突然皈依佛门,邀请朋友们去见证落发为尼、撇掉红尘的过程,主持的方丈是个和尚,李李落发后离众人而去。汪小姐与徐总在罗生门式的一夜情后怀上孩子,而且要坚持生下孩子,孩子的父亲不知道是现任老公还是徐总,老公离婚,徐总回避,为了给孩子一个合法身份,汪小姐跟小毛假结婚,而这个在一团矛盾中来到的孩子还没出生就被检查出是一个怪胎。 这些从生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故事,一个连着一个,仿佛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几乎组成了故事的泥潭,浓得化不开。当然所有的故事都是有头有尾,有来由的,一方面由主要人物小毛、沪生、阿宝为起点,不断递接外延,在两个时间段之间来回闪现,交叉出场,彼此毗连,圆和在一起。另一方面,也是铺开生活面的过程,从市中心到工人新村,到江苏常熟、到新疆、黑龙江、香港等故事人物偶现的地点,到各自的生活圈子和生活足迹,像一张大网,慢慢笼络起这个城市的各种不同人生,看起来不想干的人物,阶级、生活方式、品味、经历大相径庭,却又不是泾渭分明,通过各种潜在的关系扭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生活流,翻滚着朝前走。 每一个故事说到底都是以欲望为推动力的,政治的欲望、生理的欲望、金钱的欲望、爱的欲望,或者以其他的面目呈现出来的需要。不过在这个泥潭之上,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小说中人物,对这种生活本身的超越、疏离。比如阿宝的邻居蓓蒂,她和阿婆的故事是《繁花》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阿婆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自己的外婆在南京做天王府宫女携带黄金逃跑的经历,绍兴家乡的老坟则是她唯一的牵挂。带黄金逃难的故事在新社会不能乱讲,家乡的祖坟也不见了。蓓蒂的父母参加社教运动那个,被人举报回不来了,一老一少相依为命,蓓蒂最爱的钢琴又在抄家运动中石沉大海。这一老一少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无可依侍,于是她们只能做些梦,生出很多幻觉,最后又以幻觉的形式消失在铭记她们的世界里。再无回声,却也消失不去,蓓蒂像一个符号,被作者写出了神话的味道,她是滚入世俗生活的姝华眼中的那一丝希望,是阿宝不肯结婚的一个心理疾病。蓓蒂的出现和消失都不在现实的轨道上。小毛的老婆春香像是耶稣送来的一个搭救他的女人,小毛的故事都是在春香这里打下了底,春香在小毛处境困难的时候突然就降临小毛的生活,并且琴瑟相和,过了一段神仙眷侣的生活,在与沪生、阿宝拗断的时光里,春香一直安慰小毛。春香的死也是生活法则对美好的无情破坏,和蓓蒂、李李遁入佛门一样,留给这个年代和世界的只是背影,和带有宗教意味的一束光。 上海这个城市注定没有办法像一个普通空间一样被编织到一个寻常故事中,它太过炫目的历史与传奇色彩,对于以上海为描写对象的作家来说,是无法抛弃的随身行李,却不是福音。在一个城市自带的光环与重新上釉之间,到底是谁吸纳了谁,难辨你我,这也许就是一个地域自身的画地为牢,它往往带来叙事的限制与难以规避的陷阱。另起炉灶是逃离限制的一个直接的巫婆路线,作者金宇澄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下小说形式语言,与旧文本间夹层,会是什么。以前西方专家评论中文作者,‘摆脱了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是一句好话,同时也提出中西都存在的问题——现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够到传统文字里寻找力量,瞬息之间,具有‘闪耀的韵致’。”⑤按照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来说,就是颠覆之颠覆,讲故事的方式回到说书人的视点上去,作家的叙述部分尽量退缩,对话成为故事的主角,游走在故事里的人物,如走马灯,最主要的对象不是某个人,而是说话本身。批评家程德培的文章题目十分传神地概括了小说的这一特征——你讲我讲他讲,闲聊对聊神聊。在满腹语言的世界里,重新讲述上海都市的生命故事。说书人这一弱化的叙事者,降低了俯瞰生活的视线,使得故事宕开了收紧的发条,沿着平面发散开去,朝着一路放松的笔致而行。主人公小毛病重后,阿宝和沪生恢复了跟小毛的联系,小毛断断续续说,我只想摆一桌饭,请大家吃吃谈谈。吃吃谈谈就是上海城市生活中闪耀的韵致,是灰白的记忆中跳跃的精神,也是生命意志由高昂到平淡的一路游走。 《繁花》以港片《阿飞正传》的最后一个镜头为由头开始讲述,世人眼中繁华至极的都市生活,转到光影的背后,多半都是相似的面孔,就像作家重述的梁朝伟的那一串那分解到最小的动作。“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的味道。”一种味道或许就是这部小说的开幕词,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伴随着娓娓的语调,分立在眼前:奉命维谨的年代,和风里苏州河的潮气,咸菜大汤黄鱼味道,那些鲜活动人的少年时光;抖擞扩张的年代,觥筹交错欢乐场,又有莺声燕语和通风不良的镬气。在偌大的上海,一部小说不过是几个生活片段,几段时空,几个人物,这些散落的人生,有繁复的粗枝大叶也有繁复的浓墨重彩,随着时间落幕终止。而城市的味道永存,风流云在,打散了再集聚,集聚了再遗失,循环往复,增删添漏,无止无息。而抓住味道,的确也如西西弗斯神话一样,需要作家们反复轮回,燃起希望,收获失望。胡适所冀望的方言小说多少年来都没有继续出现,《繁花》的出现也是一桩福祸相依的事情,其他作家再写出一部方言小说,难免重蹈覆辙或者在这条道路上习惯性滑行。《繁花》打开了一个丰富绚丽的世界,却并不是开创了一条通衢大道,文学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探索寻求的原教旨光环。 ①吴越:《“上海爷叔”的心灵史》,《文汇报》2012年11月10日。 ②胡适:《亚东本〈海上花列传〉序》,《重印亚东本〈海上花列传〉》,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③[法]吉尔·德勒兹:《文学三论》,尹晶译,《上海文化》2009年第2。 ④⑤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文学报》2012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