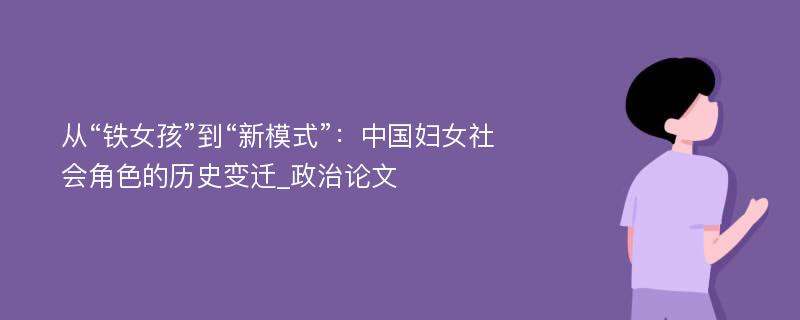
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典范论文,姑娘论文,角色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的社会性别话语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反思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妇女身份的打造作用。现代中国从未有过独立于民族运动或社会运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范畴向来从属于更为宏大的民族主义议程,在国家话语的笼罩下运作。“五四”运动对缠足、包办婚姻、纳妾制陋俗进行批判,中国妇女在中国式启蒙运动中获得露出水面喘息的机会。一大批所谓的都市“新女性”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来,为经典的文学形象提供生活原型。女性解放后来始终成为中国国民运动和民族运动的内容的一部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出现一大批革命女青年和妇女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果参照就业、领导职位、教育等指数来看,妇女似乎获得了谋求妇女解放的现实基础和广阔空间,她们可以以“半边天”的姿态与男人站在同一平台上。然而实质上,两性平等的表象建立在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而服务于政治的官方社会性别话语通过凸显阶级差别和阶级意识来抹灭性别特征和性别差异。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解放始终被看成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只有通过社会运动的杠杆才能得以实现。妇女的最终目标只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而不是争取男女平等。这最终导致中国妇女的“社会意识”远远大于其“个人意识”。①笔者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政治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并探讨当下语境中的社会性别话语的重建工作。
一、政治化的女性性别角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的政治运动对妇女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妇女的社会地位随着运动性质的变化而波动。从1949年至1954年,主要存在着两种政治化趋势:一是将家务劳动本身政治化;二是使妇女从“家庭中人”变为“社会中人”。一方面,家务劳动被认为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家庭妇女被歌颂为“社会主义母亲”或“社会主义妻子”;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家庭妇女通过参加生产性劳动而非生育性劳动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②妇女无疑为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妇女成为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作了不懈的努力。1958年爆发了“大跃进”运动,它人为地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丰富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这场运动使城区妇女就业呈蓬勃之势。先前的家庭妇女大量地投入到城镇的工业生产中去,如:纺织业、制鞋业、食品加工业、服务性行业,等等。
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中的权益。同样地,婚姻法和劳动法在立法上确保妇女享有平等权益和保护。女性就业率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此外,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在增长,普通妇女有婚姻自主的自由,遇事可以寻求政府的帮助。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为女性提供了空前的契机。妇女可以自由地上学、就业、劳动、参政、结婚、离婚,妇女似乎得到了社会意义上的解放。基于此,周怡宣称:“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的成就是惊人的、令人瞩目的……可以说,从社会、国家等外环境的层面来看,中国妇女在许多方面已经获得解放,甚至这种解放在某种程度上已超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③
周怡的观点代表了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还是一个杜撰的革命神话呢?事实上,追求男女平等从未成为中国国家政策的焦点。在笔者看来,成文的法律往往在现实生活中触礁。宣称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妇女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不平等(包括教育、劳务市场或家庭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再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女性就业情况来说,大规模的妇女从业无疑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城市妇女经常被分配到街道工厂,那里技术含量最低,报酬最低,提供的福利也比国营工厂差得多。农村妇女投入到诸如伐木、驾驶拖拉机和筑坝等繁重劳动中,但劳动所得往往低于从事同等劳动强度的男性。事实证明,“同工同酬”的理想分配原则失败了。例如,工分制是中国农村分配不均的显示器。平均来说,妇女即使在相同时间内完成与男人等量的工作,也只能赚到6-7个工分(满工分为10)。不平等的干部用人制度同样非常突出。提拔女干部是中央政府的一贯政策,但是大多数女干部隶属于低级或中级权力部门,对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只能望尘莫及。
20世纪60年代,官方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一场关于妇女地位和角色定位的争论,妇女的传统家庭地位(而非其社会地位)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和支持。中国现代政治运动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合谋”,对妇女身份共同进行规约和束缚。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政治正确性”成为衡量人们社会行为的惟一标准。早期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争论中止了,因为它与阶级斗争的主导性观念水火不相容。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1973~1976年)发轫于对林彪的批判,但运动的矛头很快转向代表所谓“封建残余”的儒家伦理。中央政府号召妇女团结起来与封建思想作斗争,反对男女不平等,素来为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女性气质和性别意识因此遭到公众无情的批判。哈利特·伊凡斯(Harriet Evans)指出:“一种建立在女性性别雄化和男女服装和外表统一标准基础上的雌雄同体和男女同一,似乎成了社会主义理想。”④具体而言,“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正确性’部分体现在女人着男装,留短发,不使用化妆品,而对男性则没有如此这般的严格要求”。⑤那个时代的女性摈弃传统的“红装”,身穿国防绿以示自己“红色”的政治立场。
中央政府树立各种各样官方的模范和榜样,为的是鼓励普通妇女竞相效仿和赶超。尽管那些巾帼英雄们有着国家授予的各种荣誉称号,如“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但她们高度“原型化”:革命热情,无私品格,阳刚气质和朴素的穿着。以下的官方信息畅通无阻地传达给妇女:生理条件不能决定女人的命运,女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遵循男性准则来获得平等地位。模范农业公社大寨的“铁姑娘”个个气质阳刚,精力和体力旺盛,满怀革命热情,成为六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妇女典范。在“(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口号的号召下,性别文学被视为与国家政治不相符的异物。女作家写的小说力图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如草明写于1950年的小说《火车头》,描写的对象是一群铁路工作者,他们把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其另一部作品《乘风破浪》承袭雷同的主题命脉,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末大炼钢铁时的狂热场景。男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均被描写成雄性化的刚毅形象。革命样板戏《海港》中的女主角方海珍,成了备受推崇的“标准”女性。
二、国家与个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极左”政治的结束。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一系列新的社会性别问题随之而生,如遗弃女婴,女工失业,婚外恋,未婚女性数量剧增。然而,过去未曾解决的老问题,即女性在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中的角色问题仍然是公众讨论的重心。社会性别话语,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内或之外被加以重新阐释。对传统道德观的重新评价,标志着对政治化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化女性身份的反叛。在社会性别的重建过程中,各种楷模供中国女性竞相效仿,但她们全都与过去的官方榜样大相径庭。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女性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一方面,她们迫切希望寻回由于政治原因而泯灭的女性特征。同时,却又面临着掉入传统性别陷阱的危险。她们普遍厌烦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但又不能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虽说历史不能完全打造她们的生活,但是她们的现实处境与中国遥远和邻近的过去休戚相关。基于此,霍尼(Emily Honig)和赫沙特(Gail Hershatter)说:
在“文化大革命”及20世纪80年代,性别问题总是隶属于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文化大革命”时的阶级斗争与8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在这两个时期,女性被告知,她们有能力克服天生的局限并取得成功。“文化大革命”中女性成功的公式是挑战性别化劳动分工,让妇女从事修理高压线之类的工作。在80年代,虽然国家的政策承认劳动的性别差异,但仍教导女性,她们要想成功,必须像男人一样敢于思考和行动。⑥
两位西方汉学家的研究点明了当代中国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之间被忽略或被掩盖的历史联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妇女的地位仍然随着国家政策的波动而波动;妇女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亦随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一系列新的国家政策(计划生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下岗、股份制),在当代妇女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女性对国家政策的长久依赖,多少影响了她们社会性别重建的自主性。
尽管如此,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公众的注意力从集体转向个人。在20世纪80年代,诸如“自我发现”、“自我分析”、“寻找自我”、“个人价值的探索”及“重新找回个人的尊严和人格实现”等话题占据了公众讨论的中心。⑦这种强调“小我”而非“大我”的说法,标志着当代社会性别话语有趣的转型。80年代早期,全国妇联发动妇女“自爱自强”,具体行为准则为:自尊、自信、自决、自我实现。它反映了新形势下政府对重现的个性的某种政策性适应。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众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日常社会活动的管治。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政治非正确性”而受到挤压和排斥的个人生活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各类女人问题,从生理到心理,从教育到就业,从青春期到恋爱期再到结婚生子,通过官方或其他媒体得到公开讨论。
三、女性气质新概念
女性问题成为当代公众争论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核心问题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女人的理想和理想的女人”,90年代中期的“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90年代后期的“女人回家”等。⑧各方各执一词,就当代女性的社会角色问题和女性气质概念争论不休。尽管如此,争论各方普遍认为,“贤惠”和“善良”依然是中国女性的重要美德。
贤妻良母这一标准,部分反映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性别定位有助于确立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等差,并且划定高低贵贱的界限。东汉末年的班昭在一本写给女儿的“家训”中对女性角色、责任、义务、行为等提出具体要求,如“以柔为美”、“夫为妻纲”等。班昭的《女诫》一直以来被看成中国女性行为规范的第一本指南书。宋明理学延续和深化了汉代以来的中国礼教传统,对女性提出更为苛刻的礼法要求。中国礼教传统通过树立正面榜样和确立女性行为规范来达到教育感化的目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多为现实中的女性提供反面人物典范。她们中有通奸杀夫的潘金莲、凶悍泼辣的孙二娘、各种阴险狡诈的女妖精等。正反两种典范结合起来对女性的社会行为和身份进行规约。实践中的中国礼教传统给女性套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同时用缠足、家法、受刑等体罚形式对女性身体进行摧残。用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苏的著名隐喻“黑暗大陆”来形容中国女性的历史境遇毫不为过。
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借用旧的女性气质概念来阐释新问题的趋势。模范妇女被重新命名为“新贤妻良母”或“超级贤妻良母”,以此反拨政治化的中性人。人们利用新观点和新元素,修正传统附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缚和探讨当代中国妇女更为复杂的社会角色。“新贤妻良母”的标签标志着对当代中国妇女双重角色的普遍性认同。现代版女性气质对女性做出如下要求:首先,她们应该具有事业心,并且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其次,她们还必须履行传统观念所定义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的角色。也就是说,理想的女人是那些能够在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的女性。积极地看,这两方面的社会期望认可了女性的性别特质及其社会角色定位。消极地看,双重要求会使女性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角色冲突”和“分裂人格”的困境。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代所设定的女性典范遭到当代女性的非议,被新的模范女性取而代之,从而观照当代女性身份的复杂性和深度。女人的着装、举止和行动都要体现女性气质,女人不再需要从形象和心态上都遵循男性标准。这一要求重新强调了,社会性别是社会自然而有价值的划分。此外,不同角色的典范们代表了政府和社会对女性不同层面的要求。笔者把中国现代女性典范粗略地划为4类,以示与公式化、单色调的社会性别模式的区别:(1)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2)拥有出众才华或容貌的名流;(3)贤淑的家庭型女人;(4)女性知识分子。
李素丽堪当第一类典范。她是北京公共汽车公司的一名售票员。李素丽获劳动模范称号并非因为她有什么英雄壮举,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她具有超强的职业道德感:热情、勤奋、真诚和奉献,不计较肮脏、拥挤的工作环境。除此之外,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和手语。1996-1997年间,她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在北京,来来往往的公共汽车上几乎辆辆挂着“向李素丽学习,提供一流服务”的标语横幅。李素丽与老一代劳模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名女性,她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在正式场合下穿着优雅得体,并略施粉黛。她的照片曾登载于《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与其说她是一名劳动模范,不如说她是一名优雅妩媚的时装模特。
第二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质,即日益盛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中国文化中涌现出新一代“追星族”。中国社会对演员、歌手、流行作家、运动员之类的名人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和崇拜。电影明星巩俐,因其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中的表演而名声大振,其主演的电影有《红高粱》(1987)、《菊豆》(1989)、《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和《活着》(1994)。她的迅速走红,也许要归功于她所拥有的窈窕身姿和动人容貌。20世纪90年代,巩俐成为中国最红的女演员之一,她的照片、花边新闻频繁出现在报刊、杂志和电视中。
第三类反映的是,与“文化大革命”中“女性性别雄化”趋势相对立的传统价值观的复苏。一个例子是刘惠芳,她是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里的女主人公。这部戏在1990年引起了强烈反响,她塑造了传统女性的典范:柔顺、温良、忠贞、孝顺、智慧和仁慈。尽管有文章批评她保守和盲从,但刘惠芳仍然被公众推崇为理想的中国妇女。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广泛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随着西方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引入,过去曾被忽视或拒绝的外国女性形象逐步得到国人的认可。各大中学号召女学生学习居里夫人——世界上惟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有趣的是,中国报道更侧重居里夫人的女性气质,尤其强调她对丈夫的忠诚和挚爱。西方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当代备受中国人的尊敬。例如,20世纪80年代颇受中国女性欢迎的译著《第二性》,使西蒙娜·德·波伏娃成为中国女性艺术家(如雕刻家姜杰)和作家(如诗人翟永明)崇拜的知识分子偶像。她们不但崇拜波伏娃从事的职业,还倾心于她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各个层面的女性气质。知识女性在当代社会性别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女作家和女诗人以充满激情的姿态加入到这股思潮中。她们的言说与大部分的传统女性书写和先前的革命+浪漫的社会主义文学截然不同。当代中国女性诗歌充满自信,声音澎湃有力。女作家和女诗人用叛逆不羁的自我表达方式肯定自我,且有力回击了社会、文化历史、政治以及男性话语的羁绊。她们不断拓宽的性别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构成当代中国女性书写的驱动力。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性别及相关话语里既包含历史的连续性又体现着历史的断裂。当下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有所褪色,却依然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注释:
①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妇女研究》2000年第2期。
②E.Kroll,Chinese Women's Emancipation and Development,London:Zed Books; New York:M.E.Sharp,1983,p.78.
③周怡:《试论中国妇女研究面临的若干转型》,《妇女研究》1996年第2期。
④Harriet Evans,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Dominant Discourse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Oxford:Polity Press,1997,P.2.
⑤Lydia Liu,The Female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gotiating Feminism across East/West Boundaries,Genders,1991,Volume(12).
⑥E.Honig and G.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339.
⑦Ma Yuanxi,Self-instating and Coming to "Conscious Aloneness",Chinese Women Traversing Diaspora:Gender,Culture and Global Politics,1999,Volume (3).
⑧王凤仙:《论作为社会性别话语的“贤妻良母”》,《妇女研究》2000年第4期。
⑨童芍素:《双重角色冲突中的中国妇女发展问题》,《妇女研究》1994年第2期。
标签:政治论文; 社会性别论文; 妇女研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性别气质论文; 文革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