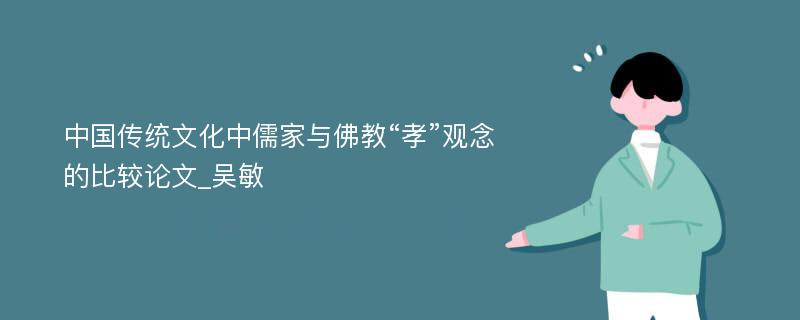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线,因为儒家的教化是从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人最基本的归属单位是家庭,在家庭关系中,孝又是最根本的。儒家认为孝为德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由此基础而兴,因此,钱穆曾说“孝”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汉代独尊儒术后,这种孝本位伦理思想观念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深入社会各个层面。而佛教入土中国后,想要在中国取得长远发展就必须符合“孝”这种主流观念的要求,于是佛教的“孝”观念开始了中国化过程,但是它们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本文从它们的出发点、实践目标和实践方法三个方面比较两者的差异,以期展现“孝”的丰富维度。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孝 儒家 佛教
一、儒家和佛教的“孝”观念的出发点
在出发点的问题上,需要研究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要孝”或者“孝的必然性根据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观念是儒家首先提倡的,因此,分析应该从儒家文化开始。
儒家以孔子为尊,而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孔子对“仁”的解释是:“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为什么能构成“仁”的根本(之一)呢?对此,杨润根的解释是十分富有启发性的,他指出,“孝”是“老”和“子”的略写的上下结构所组成的,因此代表者一种双向的伦理关系,而这种伦理关系主要内容就是各种人生道理,包括对人的生命本身,意志,情感,信念,理性以及事业等的认识的传授和接收,这是人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弟”与“孝”在这里形式上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但实际上“弟”只是“孝”的延展:“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很明显“孝”与“弟”其实都是围绕家庭提出来的,因为“出”就是指出离小家而进入到社会,“出则弟”就是将家庭中的“孝”这种美德扩展开去,因而儒家才有一种“四海之类皆兄弟”的“大家”观念。而出于对“大家”的爱,“行有余力”时,就要“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忠孝是一体的,它们没有根本矛盾,而只是只凭个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抉择。这些就是儒家强调“孝”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的“孝”是一种修养论的方法,因为儒家总是将“孝”的功用摆出来了的,指出“孝”对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和谐的作用。佛教讲“孝”更不带功利主义的色彩,因为佛教的孝是一种因果论的结果,而且这种因果是基于它的本体论的。佛教的孝是一种真正的感恩,因为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于是我知恩报恩。这种孝不强调子女的德性,而是强调一种因果性,由此出发,可以避免愚孝、假孝。
二、儒家和佛教的“孝”观念的实践旨趣
总的来看,孝的实践上,儒家在于“解困”,佛教在于“解脱”。儒家的“解困”就是解决生活问题,解决父母的身心之困苦。然而,身体方面的困苦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儒家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样,人的命运就是注定了的,人的努力不会起到扭转它的作用。因此,儒家将解心之困放在首位。而对于孝的实践的主要内容,孟子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注曰:“赵氏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由此可见,无后是父母最大的心病,而不能给父母生下传宗接代的孙儿是为最大的不孝。其次,儒家的孝又讲究一个“敬”字。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所以,儒家讲孝,是孝敬,但“孝敬”却将双向性的“孝”变为单边性的了,而且更强调父母的意志对子女的意志的决定作用作用,不允许子女发挥自己的意识能动性,这就是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愚孝的理论根源。佛教主张的“孝”的实践乃是子女帮助父母获得佛教意义上的解脱,解脱就是解决生命问题,发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以,佛教认为儒家的孝还是初级意义上的,更重要的内容儒家还没有发现——帮助父母解脱,则可以让他们免于轮回之苦,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感恩。所以,在这里,最大的冲突应该就是,佛教修行就得抛家弃子,就直接舍弃了儒家的孝的阶段,成为儒家心中最大的不孝。于是,佛教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讲究先安顿好自己的父母再入空门,或大力发展在家修行。
三、儒家和佛教的“孝”观念的实践方法
孝的对象上,儒家和佛教是相同的——孝不但指向在世的父母,也指向去世的父母,而且孝观念在儒家和佛教中都有一种延伸,即延伸到家庭之外。佛教认为“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因此过渡到了对众生的感恩,对众生的爱,于是自利利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儒家讲究一种“人伦父母”,于是君臣、师生、兄弟、夫妇等都可以将孝的观念加以引申而利用。所以我们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说法,也有“师父”的说法等。
父母在世时,对父母的侍奉是儒家和佛教的共同要求,对他人的爱显然也是一样的。两者的不同其实主要体现在对去世的父母的尽孝方法的不同。儒家讲究“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种葬礼和祭礼现在在中国的农村还有保留。“披麻戴孝”这个成语就告诉我们这两种礼节是孝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纪念”的意义。儒家要求“三年之丧”,孔子对此的最直接的解释是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怀。”也就是说,父母在我们最小、最柔弱——完全不能自理的时候,最最辛苦的照顾了我们三年,我们在父母死后,哀悼他们三年显然是应该的。佛教主张在父母去世后的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为父母行孝,称为盂兰盆会。从时间长短来说,似乎儒家更看重对父母的感恩,因为它要求以三年的时间来守孝,而强调感恩的佛教却只以一天来追念自己父母的恩情,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佛教虽然强调彼岸世界是解脱后的净土,但它却并不倾向于引导人们在父母死后才来尽孝,其强调的是现世生活中的修行,现世生活中帮助父母求解脱才能称之为“大孝”。
对于日常侍奉之孝与佛教所说的“大孝”联系与区别,我们可以从《五灯会元》中对儒家和佛教的孝的比较中得到更为清晰的线索,其将“孝”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仲尼之孝”,为身体发肤,弗敢毁伤。第二种是“释迦之孝”,往仞利天为母说法,成《地藏经》,被称为佛教中的“孝经”。第三种是“目连之孝”,目连以天眼通见其母在地狱受苦,便于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会”供奉十方僧众,并在其帮助下入地狱救母,这就是盂兰盆会的来历,我国的盂兰盆会最早可追溯到538年梁武帝为其母举行的法会。第四种是“兴化之孝”,他不上天入地,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为母说法,为母烧一柱香,以使其母获得佛教式的解脱。这种佛教行孝方式就明显的带有一种中国化的倾向,因为其在现在的俗世生活中为父母积下轮回中的善因,而非直接遁入空门,自求解脱。
参考文献
[1]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2页。
[2]杨润根:《发现论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3页。
[3]王明:《中国佛教孝道思想探析》【D】山东: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3:26-28。
[4]王明:《中国佛教孝道思想探析》【D】山东: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3:32
作者简介:吴敏(1995年—),女,汉族,四川仁寿人,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论文作者:吴敏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3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5/15
标签:儒家论文; 佛教论文; 父母论文; 观念论文; 是一种论文; 孔子论文; 不孝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3月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