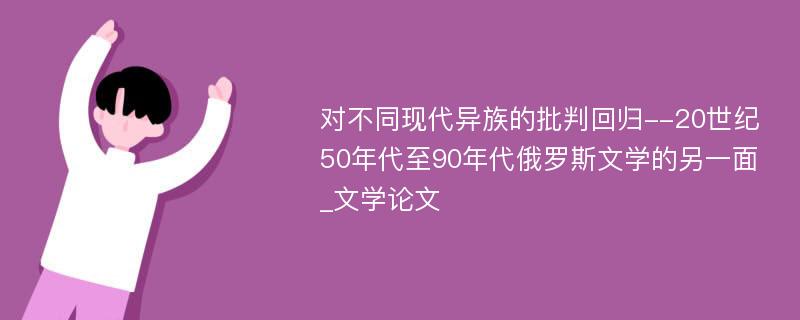
批判 回归 异样 现代 异域——50到90年代俄语文学的另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语论文,异域论文,异样论文,年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俄语文学创作的另一面——形形色色的背离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潮文学创作的社会批判文学、回归文学、异样文学、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侨民文学的勾勒与剖析,揭示出20世纪俄语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复杂的文学构成。
关键词 批判/回归/异样/现代/俄语文学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逝世,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以及苏共当时采取的一系列相应举措,如:为阿·布尔加科夫等人恢复名誉,成立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出版他们的作品等等,直接导致了苏联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法律、文学艺术等整个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探索的巨大动荡。文学中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成为非主潮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一大现象;但是,50年代末到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当局加强了控制,强调“艺术的思想方向”,部分作家或受到批判,或被驱逐出境,或被迫移居国外;一批作品或遭谴责,被搁置不用,或通过“萨米兹达特”(自发出版物,samizdat)在苏联国内私下流传,有些则在西方公开面世从而使地下文学和侨民文学成为主潮文学的一大分支。80年代苏联社会进入全面改革转型换轨时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极力倡导,1986年苏共27大“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的提出,苏联文学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潮文学的背离愈加强化,整个文坛真可谓成了社会批判文学、回归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及形形色色“异样文学”的喧哗与骚动。
社会批判文学是50年代中叶最早向主潮文学发难,并贯彻至今的文学现象。这一派文学面对几十年间的苏联历史和现实,继承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其血与火的心感身受,抚今追昔,大声疾呼捍卫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尊严,对社会的阴暗发出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既有“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之旨,也不乏全盘否定之意。其中大部分作品受到批判,有些则在当时难以问世,属于回归文学、侨民文学。
其一,暴露现实生活中社会政治矛盾的政治性作品。如: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是只靠面包》(1956),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法·伊斯坎德尔的讽刺作品《羊牛星座》(1966)等。其中《解冻》(第1部,1954;第2部,1956)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抨击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的弊端及其产生的社会官僚,重在展示个人情感世界和个人生活,提出了社会关心人的问题。作者的笔端还批判地指向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等历史事件,因此尽管《解冻》本身艺术上不足称道,却开社会批判文学之先河,并继之形成了“解冻文学”浪潮。
其二,对日常生活丑恶行径的道德心理批判,似乎要在人性匮乏的社会中找寻某种精神道德支柱。如:亚·雅申的短篇小说《杠杆》,田德里亚科夫的短篇小说《三点、七点、爱司》(1960)及特里丰诺夫以中篇小说《交换》(1969)、《滨河街公寓》(1976)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文学作品中对“现代市俗”的重笔浓描。
其三,披露劳改营和劳改犯生活的集中营文学。如:沙拉莫夫的《科雷马的故事》(1966—1978),多姆勃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无用之物系》(1988), 叶夫盖尼娅·金兹堡的回忆录《险峻的路线》(1990),亚·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 《第一圈》(1968),三卷本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1973,巴黎)等。这类文学大多都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熔自传、纪实、政论于一体,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记述、剖析作品主人公或作者本人怎样同被逮捕成为劳改犯,所谓的国家法律,劳改营、流放地的黑暗、恐怖,劳改犯的精神状态、个人遭际,以及劳改营中的反抗、暴动和逃亡事件等,将整个社会与劳改营加以类比,谴责社会的无法制和对法制的践踏,其中极端之作显然是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否定。
其四,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重新书写历史。一方面体现的是拨开迷雾见真伪,对真的感悟与执著;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观念位移导致的对原有定评的怀疑、动摇及至走向其反面,从而引出一股巨大的批判否定浪潮。如:鲍·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1988年在苏联国内发表)以永恒的道德标准、至善至美、个性价值、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审视十月革命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是通过一位俄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书写出来的暴力革命毁灭人性的社会史。鲍·莫扎耶夫的长篇小说《农夫与农妇》(第1部1976,第2部1987)描写了梁赞州30年代推进的全面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农民一夜间必须加入集体农庄等各种过火行为最终引发了宰杀牲畜,村民骚乱等一系列流血事件。显然,“莫扎耶夫是利用被‘没收财产者’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的”(彼亚内赫语,参看苏联杂志《星》,1988年第2 期)。其批判的锋芒已经直接指向最上层党的领导。这一类作品还有别洛夫的长篇小说《前夜》(1972—1987),谢尔盖·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瓦西卡》(1987),伊万·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纪实中篇《辛酸往事》(1988)等等。此外,对卫国战争的反思,也出现了诸如格罗斯曼将战争写成两大极权间争斗的长篇小说《人生与命运》(1988),艾特玛托夫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的长篇小说《卡珊德拉的印迹》(1994),以及阿斯塔菲耶夫通过长篇小说《受诅咒的和被处死的》(第1 部, 1992;第2部,1994)描述的是如同劳改营一样残酷、 人性泯灭的新兵训练营地和1943年红军解放基辅时混乱不堪、鲜血淋淋的反攻战场。笔者竭力渲染战争的不人道、战争的恐怖,进而完全否定卫国战争的正义性。
总之,从历史到现实,从国体、政权到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社会批判文学的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却良莠不齐,难以定评。许多作品的“轰动效应”只是在于它的“禁区”题材,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一个个题材禁区的被打破,随着人们政治热情的消减,进入人类文化宝库的只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验证的艺术精品。
回归文学是这一时期文学中的特殊现象。
长期以来有一批苏联作家在国内遭到批判或被镇压,被逐出境或流亡国外,他们的作品在国内被禁止出版或者重版,其创作可以说完全被排斥于当时的苏联主潮文学之外。但是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伴随苏联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人们审美方式、价值取向的转变,这些作家被渐次地恢复名誉,作品在苏联也陆续公开发表;与此同时,他们的创作也程度不等地受到世人的关注和探究。“回归”即是指这类文学向苏联文坛的复归,回归文学即是对本该属于苏联文学整体创作潮流之中的这一复杂文学现象的总称。
回归文学分为两个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当时回归文坛的主要有安娜·阿赫玛托娃、尼古拉·扎鲍洛茨基、列昂尼德·马尔捷诺夫和鲍里斯·斯卢茨基等人的诗集;皮利尼亚克、伊萨克·巴别尔、伊万·卡达耶夫、奥丽普·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蒲宁等人的小说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等文学创作。
第二次浪潮始于80年代中期。自1985年苏联领导宣布实行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执行和随之而来的某些政治性禁忌的打破,文艺政策的放宽,苏联文学界一改旧观,步入了一个新的空前活跃的时期。其表现之一便是各文学报刊杂志竞相发表过去被禁止和遭批判的作品,形成了回归文学的第二次浪潮。其态势之猛、波及面之广,犹如汛期洪潮,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谓之为“发掘热”。其中主要有普拉东诺夫、别克、特瓦尔多夫斯基、普里斯塔夫金、布尔加科夫、皮利尼亚克、雷巴科夫、田德里亚科夫、安·比托夫、杜金采夫、阿赫玛托娃、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弗拉基米尔·纳波科夫(西林)、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创作。
《切文古尔》(写于1928—1929,小说的第一部分1927年在巴黎完成并出版)、《基坑》(写于1929—1930,1969年在伦敦出版)、《初生海》(写于1934,1979年在巴黎《回声》杂志上发表),这组普拉东诺夫创作于20年代末、30年代上半期的三部曲,是作家创作高峰之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们典型地体现出了作家的艺术天才:运用象征、隐喻、夸张、假定、不规则组合等纵放离奇的手段,在理想的激情与淡淡的幽默、辛辣的嘲讽中,将种种乌托邦空想的荒诞逼真地外化出来。
《穿白衣的人们》是杜金采夫在因为发表《不是只靠面包》受到批判后,作品长期不能面世的巨大压力下,历经二三十年创作出来的一部力作。小说标题取自《圣经》“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他们是为体验巨大的痛苦而来。”喻指身着白衣,勇为科学献身的正直无畏的科学工作者。小说反映了40年代末期在苏联开始的生物学界李森科派对摩尔根遗传学派的迫害。
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发表后,反响空前,当时被称为近年来苏联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这部长篇小说《新世界》杂志曾计划1964年发表第1部,但因故停发, 后来作者又创作了它的第2部和第3部。小说之所以轰动在于它通过描写阿尔巴特街上的儿女们30年代的个人遭遇,揭示肃反运动前夕社会政治生活的不正常;通过叙写党内斗争,基洛夫被杀这一历史悬案,塑造出斯大林——专制暴君的形象。
《我们》是扎米亚京1920至1921年间以日记形式写成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作家通过精心构制的这个富有讽刺意味和幻想的未来社会图景,来“预告人和人类会受到无论是机器或国家的过大权力的威胁”(扎米亚京)。艺术上体现出作家独特的印象主义风格。这是扎米亚京创作完成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代表其艺术最高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小说完稿后,在苏联被禁,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私下流传,但是很快便在国外问世:1924年在纽约出版了英文版,1927年在捷克出版了捷克语版,1929年在巴黎出版了法文版,同年,待小说的俄文版也在国外(载于捷克的侨民杂志《俄罗斯意志》)发行时,苏联国内开始了对扎米亚京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迫使作家于1931年11月离开了苏联。
异样文学(请参阅拙作《无奈的现实和小说——谈俄罗斯的“异样文学”》,载《俄罗斯文艺》,1994,5 )主要是指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悄然兴起的一股文学新浪潮。主要作家有: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1933—1990)、维克多·叶罗菲耶夫(1947—)、柳·彼德鲁舍夫斯卡娅(1938—)、波波夫(1946—)、皮耶楚赫(1946—)、塔·托尔斯泰娅(1951—)等。这些异样文学家们既不刻意求取某种精神、观念的升华,也不完成价值体系的“使命”;只是冷静地、不动声色地回复到生存状态、生活事实的每一个单独的层面叙事之中。似乎,他们的美学使命正在于其审美视点着落于的无所适从的无奈的生活情境。
其一,它重视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它既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以历史的眼光评析生活,也不同于现代主义以个性内视角对世界的体验,而是力争写出生活的“原汁、原色、原味”,生存的无奈、扭曲和荒诞。如:彼得鲁舍夫斯卡娅的中篇小说《黑夜时刻》(1992)通篇是展示女主人公孤独无助的日常生活。她的短篇小说《生活的阴影》(1993)同样是以平实的手笔直叙生活的不易和苦涩怎样地包容了一个女孩生活的全部。它同叶·波波夫笔下只知道吃喝,口袋里有一瓶酒便觉得很幸福的人们一样(短篇小说《电子大手风琴》,1987),描绘的正是普通人不得不过的扭曲生活。这种扭曲生活的荒谬也典型地反映在塔·托尔斯泰娅的笔下。她在短篇小说《夜》(1987)中透过一个疯子的生活,写出了正常生活的不正常;在短篇小说《彼得尔斯》(1986)中运用许多华丽的词汇,通过阴暗、沉重的氛围渲染,揭示出惰性环境、社会对人的摧残和排斥,人与周围世界的隔膜,生活与人之间完全对立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主宰生活,而是人成为生活的玩偶。同样,皮耶楚赫的短篇小说《我和决斗者》和中篇《新莫斯科哲学》所呈现的“文学性气氛”的人的生存空间,都使人强烈地感到人所创造的力量是如何反过来统治和制约人,而结果只能是一场场闹剧和荒诞。此外,人与人关系的疏远和冷漠,人在世间的孤独是“异样文学”表现人生存状态的另一内容。叶·波波夫的短篇小说《见鬼》中的主人公助人为乐,但好心非但不得好报,还反遭诬陷。作者意在“向我们展示一颗无法在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寻找到应有的理解及施展其抱负的可能的心灵……”(维·什托克曼语,参看俄《文学报》1989.1.19);而以一组短篇《守卫者哀歌》(1991 )成名的奥·巴夫洛夫作品的主题便是孤独。阿·加夫里洛夫则在短篇《小工具厢》中描写一位管道工找不到谈话对象,只好对小工具厢倾述苦衷。
其二,典型的淡化。“异样文学”家们或者是以一种超然的眼光给出一种生活状态和心态,如:叶·波波夫笔下经历过婚变,又不得不再次与妻子离异的男人跳跃的思绪(《我是怎样堕落的》,1991);或者是向读者托出形形色色的“底层人”、“小人物”。这些被动的、可怜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压抑、不满、受难,却又无力追求,无力抗争,无可奈何地生活在失意和幻灭之中。如:塔·托尔斯泰娅的短篇小说《火与灰》(1986)中的女主人公除了在无奈的尴尬境地中艰难地跋涉外,别无出路。但是在弥漫着浓重的人们面对无情现实的无奈感的“异样文学”中,荒诞和反抗也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叶·波波夫的短篇小说《见鬼》中的文学家尽管知道他的行为不被理解,仍执著地把事情做到底。
其三,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的“异样”。一方面,在叙述形态上,“异样文学”程度不等地保持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描写特征,仍然沿续现实主义的情节、细节的生活化,人物描写的细腻性等,在他们的作品中的显著特征:反讽、怀疑,以及体裁结构上都能够看到俄罗斯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虽然它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某种存在主义与自然主义交融的陈列和写实;是对传统审美观念、思维定势、道德心理的背叛和反抗,也正因于此,苏联改革前创作的“异样文学”作品不被官方接受,成为当时“地下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与此同时,“异样文学”家们较之其前辈关注更多的则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他们那种心理的、情绪的、直感的介入,其中呈现出不同类型和特征的隐喻、反讽、意象的“反英雄”描写,以及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的体验,对日常生活中平庸、琐碎所作的揶揄、逼真和审美的描绘,又使许多人将它们纳入先锋派文学之列,或者将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家作品归入“异样文学”中。
诚然,“异样文学”是一个相当含混的概念,是一类文学宽泛的总称。它们在具有某些共同倾向、特征的同时,又有极大的内容艺术差别;并且其理论和实践都在发展之中,但是它无疑代表了文坛上的一种走向和势头,也自有其独特的地位。
现代主义文学经过三四十年代的相对“沉寂”,在60年代开始复苏。显然这与50年代中期出现的解冻思潮,当局文艺政策的某些改变,如:加强了对当代西方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有关。当时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等西方现代派文学家的作品都有了译介。但是这一时期即使是被称为“革新派”的阿克肖诺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创新”,也“几乎不会使一个熟悉现代西方作品的读者惊奇”,并且他们有限的创作很难见容于文坛,同本世纪初至2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在俄罗斯文坛的兴盛已是今非昔比。
主要作家作品有:瓦·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1),它塑造的主人公可称得上是苏联社会“垮掉的一代”的代表;卡达耶夫的中篇小说《圣井》(1966)、《小方块》(1969)现代派地处理了时间与空间观念;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的诗集《抛物线》(1961)、《三角犁》(1962)、长诗《奥扎》(1964),语言奇巧怪诞,结构繁复,诗人的关注中心即是词语及结构本身;别拉·阿赫玛杜林娜的抒情诗集《琴弦》(1962)、诗集《音乐课》(1969)则显示出这位女诗人操纵诗句乐感韵律和具有强烈隐喻性语言方面的精到典雅,自如脱俗。
到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现代主义文学仍然是步履蹒跚。较为有影响的作品是安·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1971)和萨沙·索科洛夫70年代完成的长篇小说《傻瓜学校》。此外,1979年瓦·阿克肖诺夫、安·比托夫、法·伊斯坎德尔、维·叶罗菲耶夫、叶·波波夫等人共同编辑了一部文集《大都会》,收入包括五位编者及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林娜、维索茨基等17名有现代主义创作倾向作家的作品,但是文集当时没有通过苏联官方的审查,后来是在美国得以问世。
如果说以阿克肖诺夫为代表的“60年代的青年”笔下出现的是“迷惘的城市青年”,那么《普希金之家》描写的则是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既找不到自己的过去,也无法在当今及未来中寻到落脚之地的困惑与迷惘。它同索科洛夫的那部以“傻瓜学校”象征封闭、停滞的外部世界,以一个生活在自我意识图画中的未成年人为主人公,以思绪的跳跃决定时间流动的无人物、无体裁的作品都被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正如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由于传统的思维观念、价值体系遭受挑战,直至否定,而引发的失落感和后工业社会现代文明下,人们面对核战争、生态平衡被破坏、人口爆炸等产生的绝望情绪在文学中的直接反映;当苏联社会进入全面改革的80年代中期,特别是苏联解体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是人们信奉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观被击得粉碎,精神上面临着巨大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混乱无序,弥散着浓烈的生存威胁带来的无望的世纪末情绪。此时,在某种意义上,以归谬的手段,通过无序的叙述和松散或消亡的结构来展示现存世界非自然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很快地被俄罗斯文坛接受,成为苏联解体后几年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如哈里托诺夫的长篇小说《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1)、弗·马卡宁的中篇小说《铺着呢毯、中间放有长颈瓶的长桌》(1992)、德·加尔科夫斯基的《没有尽头的死胡同》(1992)及阿·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1992)等。
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至今,由于各种原因,一大批俄苏作家侨居国外,他们的创作统称为侨民文学。从地域上划分,侨民文学主要分为欧洲、亚洲、美洲几大部分;从时间上划分,侨民文学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十月革命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时国内进行的十月革命、白色恐怖、国内战争及其它种种社会政治因素,使得许许多多的俄国文学家取道新西伯利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波罗的海的各个港口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流亡于伊斯坦布尔、布拉格、贝尔格莱德、里加、哈尔滨等地。1921—1923年在柏林形成了最大的俄侨文学中心,而后移至巴黎,自1940年起该中心转至纽约。包括的主要作家有:阿尔卡季·阿维尔钦科、马尔克·阿尔达诺夫(原名马尔克·兰道)、列·安德列耶夫、米·阿尔志跋绥夫、巴尔蒙特、 安德烈·别雷(1923年回国)、伊万·蒲宁、吉皮乌斯、亚·库普林(1937年回国)、德·梅列日科夫斯基、伊戈尔·谢维尔里亚宁、阿·托尔斯泰(1923年回国)、娜捷日达·苔菲、萨沙·乔尔内,以及1921—1923年侨居国外的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鲍里斯·扎伊采夫、格·伊万诺夫、阿·列米佐夫、符·霍达谢维奇、玛·茨维塔耶娃(1939年回国)、伊万·施米廖夫和分别于1924年、1931年移居国外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等。他们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俄文报纸(在欧洲各国,1920年有138种,1921年有112种,1922年有109种;在中国哈尔滨, 1926年有13种)、杂志[如:《未来俄罗斯》(巴黎)、《俄罗斯思想》(索菲亚—布拉格—巴黎,1921—1927)、《现代论丛》 (巴黎,1920—1940)、《界线》(哈尔滨,1926—1945)、《帆》(上海, 1931—1934)、《丘拉耶夫卡》(哈尔滨,1933—1934)、 《新杂志》(纽约,1942年至今)],并成立了数十家出版社[如:《言论》(柏林)、《火焰》(布拉格)、《俄罗斯大地》(巴黎)、《俄罗斯—保加利亚》(索菲亚)],印发了蒲宁、施米廖夫、扎依采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列米佐夫、纳博科夫(西林)、茨维塔耶娃、苔菲等众多作家的作品。
到40年代,随着希特勒铁蹄对欧洲的践踏,俄侨文学的大本营开始迁往美国。1942年俄侨文学杂志《新杂志》在纽约创刊,以出版俄侨文学为主的契诃夫出版社也相继成立。那些留在欧洲本土的俄侨作家则大多饱受法西斯集中营和战争之苦。而中国的俄侨文学中心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公开入侵东北,便自哈尔滨南下迁至上海。经过几年的兴盛,在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日益陷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后,上海的俄侨文学也开始呈衰落之势,同时战争也造成了这批中国俄侨作家队伍的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移居第三国,一部分返回苏联。这样,40年代时,俄侨文学在中国已基本消亡。至此,欧亚俄侨文学最辉煌的时代——俄侨文学的第一阶段始告完结。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这一阶段越过苏联国境线汇入侨民文学潮流中的作家并不多,主要有:诗人伊万·叶拉金、德米特里·克列诺夫斯基、鲍里斯·纳尔茨索夫;小说家鲍里斯·希里亚耶夫、谢尔盖·马克西莫夫、尼古拉·纳罗科夫、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等。这批人就其才华素质、创作数量、创作的艺术水平而言,都比前一阶段的侨民文学逊色得多,但他们使走向终结的第一阶段侨民文学有了承续,有了新的内容,而且仍然同现实的苏联社会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阶段:七八十年代。这一阶段出现的引人注目的苏联作家移居国外的浪潮几乎都与社会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如:三次入狱、两次入精神病院的索尔仁尼琴,1972年因为在国外发表了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1974年被驱逐出境;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因为在国外出版了短篇小说《士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及奇遇》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而后于1980年移居国外; 约瑟夫·布罗茨基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言人于1972年被逐出国境。当然这一浪潮也同此时当局对犹太公民出境的限制放宽有关,所以在大部分新侨民移居西方(美洲、欧洲)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侨居于以色列。
这时期的侨民文学主要包括:瓦·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燃烧》(1980)、《克里木岛》(1981)、《莫斯科的传说》(1991)、《冬天里的几代人》(1994),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布罗茨基那“超越时空的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评奖委员会的评语)的多部诗集及散文。在巴黎出版的侨民杂志《大陆》的主编弗·马克西莫夫的长篇小说《创世七日》(1971),F·弗拉基莫夫的中篇小说《忠诚的鲁斯兰》(1975 )、沃依诺维奇的《士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及奇遇》(1969),加利奇的诗集,弗里德里赫·戈连施坦的中篇小说《赎罪》(1979),弗·纳波科夫的长篇小说《玛申卡》(1926)、《洛丽塔》(1954)、《普宁》(1957)、《微暗的火》(1962)等及58篇短篇小说,两卷集的《文学讲稿》(1980)等,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愚人笔记》(1974)、中篇小说《市内散步》(1988),谢尔盖·多夫拉多夫的短篇故事集《皮箱》(1985),以及阿纳托利·格拉季林、H·科尔扎文、A·库兹涅佐夫、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尤里·库勃拉诺夫斯基、艾·里蒙诺夫 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萨沙·索科洛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创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这些作家以前完成于苏联国内,却被禁止在苏联面世的创作。
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浪潮)、先后拥有三代侨民作家的侨民文学是20世纪俄语文学复杂、特殊的一面。这三代侨民文学家的远离故土大多是由于政治原因。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创作中对国内政权制度,种种社会存在的不解、疑虑、揭露、批判、否定都占有极大的比重,所以便有了索尔仁尼琴纪实体的长篇《古拉格群岛》、《红轮》等一系列的小说及政论文章,有了安·西尼亚夫斯基不同寻常的内心独白《合唱队的呼声》,有了扎米亚京的怪诞奇文《我们》,有了阿克肖诺夫的讽刺幻想长篇《克里木岛》,有了苔菲对布尔什维克极尽嘲讽的小说和杂文,有了吉皮乌斯对苏维埃政权的诅咒,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反苏之作。但是不管他们身居何处,过着怎样的生活;也不管他们有怎样的创作观念和视点,他们终究无法摆脱掉缠于自身的“俄罗斯情结”。因此,几乎所有的侨民文学作家,特别是第一代侨民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都是流亡者对俄罗斯家园深深的眷恋,失落家园的孤独、悲观、绝望,对纷繁往事的不尽缅怀,如:蒲宁作品中无可奈何的乡思、伤感和绝望的情调;格·伊万诺夫诗集《1943—1958诗篇》等中极度的悲观;创作生涯多半在国外度过的女作家苔菲作品中对俄罗斯、俄罗斯人生活和品性的溯本求源。即使是在1977年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的约·布罗茨基用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构筑的诗文大厦中,对俄罗斯故乡的怀恋之情仍是其创作主题之一。那一幅幅有强烈视觉效果的诗文画景,也时时闪现着俄罗斯风景的迷人光彩,那一首首吟咏“生与死”等生命主题的诗篇,也昂扬出传统的俄国“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虽然“阅读他的作品就像站在一座山顶上,俯视两个世界,两个帝国”(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委员斯特·艾伦语)。而用俄、法、英语创作,成为美国公民的弗·纳博科夫的许多诗歌、小说反映的则是他在俄罗斯度过的童年、少年生活以及俄国流亡者的心态和境遇。可以说俄罗斯是他的梦境,他的神话,他的忆念,此时他无疑是一位温情的俄罗斯式作家。同时,他和一些侨民文学家一样,向西方译介了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伊戈尔远征记》在内的俄国文学名作,应该说这也是侨民文学家们怀乡之情的一种表现。不过后来,特别是在美国定居以后,博科夫变得更加贴近西方社会,走向了俄罗斯文学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之路,或者说他是在俄罗斯的文化背景上审视出了美国现实和英语。使他在西方一举成名的长篇力作《洛丽塔》正是这样的典型之作。由此又引出了侨民文学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和表现。这方面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是最成功的代表。此外,列·安德烈耶夫侨居芬兰时创作的《撒旦日记》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尼·巴伊科夫侨居中国时写就的长篇小说《大王(虎的故事)》(1936、1942)等塑造了中国猎人的形象,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东北地方色彩。
几乎所有的侨民作家在国内时就已经成名,并有了相当的成就,但在移居国外后,许多人的创作却并无更大的建树;然而,也有一些人则是在侨居国外后成了有名的侨民文学作家。如:鲍里斯·波普拉夫斯基(1903—1935)、弗·纳博科夫(1899—1977)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