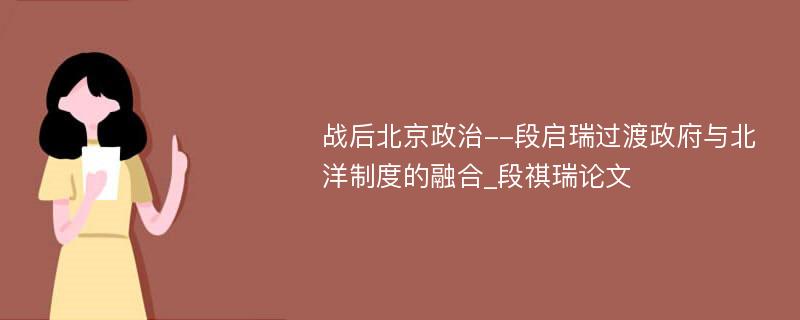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执政府论文,北京论文,体系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4-0064-09
1924年秋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军政实力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变化。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对中央的控制加强。自是以还,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帮助,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对北洋而言,可谓大伤元气的内争。战后一度形成奉军与国民军抗衡的局面,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各军阀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①。然而,由于段此时已缺乏实力,不能形成新的权势重心,其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不久军阀之间重启战端,本来被冀望于北洋体制内加以解决的中国政治问题开始转向体制之外的解决途径。国民党在北洋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基本置身事外,养精蓄锐,致力于自身的军政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而北方军阀却因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彼此严重削弱,逐渐走上末路。后来国民党以相对弱小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的巨大成功,大致可以从这一阶段中国政治的变化中寻得解释。
一 顾盼各方利益的政制选择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祸起萧墙的北京政变而告结束。政变之后,冯玉祥即按照北苑会商之法,筹组摄政内阁。但冯氏对于政治并无明确主张,政变之初,其与英文导报主笔柯乐文谈话,曾表示发动政变系“革军权万能之命,非革政治之命,故曹总统之地位,吾并未推翻”[1](p202~203)。在中枢无主的情况下,主张由现内阁摄政。但商之国务总理颜惠庆,颜不之许,且辞总理职。只好决定由与冯夙有联系的黄郛暂行组阁摄政,阁员包括黄郛、王正廷、杜锡珪、李书城、王永江、易培基、王廼斌、李烈钧等,仍以曹锟总统“任命”的方式发表[2]。以冯做后盾的黄郛摄阁显然只是政治上的短暂过渡。时人曾批评冯氏“对付政局之手续,始终承认历年之法统”,将政变之后的北京政局弄得“似革命非革命,似依法非依法”[3]。奉张则自恃“百战入关”,对冯氏“未折一矢……反占中枢,发号施令”表示不满,谋“有以挫折之”[4]。在奉张的压迫下,黄郛摄阁成了名副其实的过渡政权,存在时间只有24天。曹锟在黄摄阁成立之后3日被迫辞职,取代曹、吴统治的政治形式是由“执反直同盟之牛耳”、在当时最具实力的奉张在天津会议上操纵决定的。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曾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接到邀请后,复电允即北上。但当时的局势似乎对段祺瑞更加有利。多数地方实力派都把收拾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段身上,造成“非段莫属”的政治气氛②。对于段祺瑞出山,冯玉祥与奉张也持支持态度,不过用心颇为复杂。时论分析说: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只拥兵数万,且仅限于近畿地方而无支撑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号令天下,俾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所惧者为吴氏纠合长江势力,持拥段之态度。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巩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功。[5](p201)因此,政变之后不久,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就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而张作霖、卢永祥以及镇威军各将领则联名发出通电,推段为联军统帅。
由于各方“拥戴”,段祺瑞表示愿意出山收拾局面,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遂云集津沽,一时间,天津成为中国“政治重心”之所在,政制问题的讨论由是提上议程。1924年11月13日,天津会议召开,列席者有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李景林、张宗昌、贾德耀、陆宗舆、王芝祥、陈宦、章士钊、段芝贵等40余人。会议讨论了包括国会存废、战争善后等诸多问题,但与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则是“将来政府之组织,采何种制度”[6]。在这个问题上,因利益不同,各方意见分歧颇大。政变之初,北方国民党人徐谦等曾提出废除总统制,改行委员制的主张,得到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赞同。唐绍仪也主张实施委员制,由各省区“各举一人,组织委员会”,再由委员互选一人为委员长,主持政务,但其职权较总统为小。与唐联系密切的章太炎则从言论上予以配合,发表《改革意见书》,认为实施委员制,“以合议易总裁,则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有利于结束北洋派的武力统一政策,实施“分立数国”的地方自治主义。当时曾议及一旦实施委员制,当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若干社会名流,共同执政。[7](p654)
段祺瑞、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则反是。天津会议上,段之左右曾明确主张采择总统制,甚至提出“推孙为总统出洋,段为副座兼阁”的意见[8]。推孙为总统虽未必出于段的本意,欲维持总统制则是事实。孙中山及南方政权亦主张实施总统制,早在反直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就曾与在段祺瑞身边担任与各方联络工作的邓汉祥,为曹、吴倒后究竟是由孙中山还是段祺瑞担任总统进行磋商。当时曾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孙中山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一是段任总统,孙任总理。而邓汉祥的意见则是“孙先生任大总统最为合适”,曾承诺将国民党的意见转告段。[9](p415)在孙命胡汉民起草的致段祺瑞的电文中,有“国以内,兄主之;国以外,弟主之。在津候弟到,同入北京,商定国基”之语[10](p681),与段氏左右所言异词同义,可见南方国民党人亦主张总统制。
不过,两种政制的实施在当时均有困难。按照时人认知,总统制容易形成集权,与当时甚嚣尘上的自治思潮颇呈枘凿,被滇唐等联治派称为“国之祸水”[11]。即便不这样认识问题,在国会已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合法”总统如何产生也是问题。一些国会议员当时召开非常会议,企图选举临时总统未能遂愿,即证明了这一点。委员制的实施障碍亦不少。由于国民党“联俄”政策已大白天下,冯玉祥与北京俄国使馆人员的联系也为人所知,而苏俄政府的组织形式,按照时人的理解,正是委员制。于是反对该制度的人便利用一般人畏惧“赤化”的心理,称主张委员制的人有“赤化”倾向。西方国家外交团出于反对苏俄的政治需要,亦作如是观,致使主张委员制者不敢坚持此议。[12]
政制问题的解决因此陷入两难境地。此时孙中山尚在北上途中,段氏为了争取西南方面的支持,曾作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表态[13](p202)。但曹锟去位之后长江流域各督的态度,却使政制问题的解决变得刻不容缓。11月10日,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周自齐与蔡成勋、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杜锡珪等联名通电,拥戴段氏。13日,该各督再次通电,声言中央政府已经中断,对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承认。该通电的发表,引出“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的急切形势,迫使天津会议尽快解决政制问题,以建立能为各方承认的中央政府。由于不慊于委员制,总统制又因缺乏国会,无由产生,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等人乃决定采取“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目,以为过渡,得到段祺瑞首肯。[14](p1477~1478)所谓“执政”,按照李剑农的解释,一方面是表示已废除了“崇高的”大总统,一方面又表示不是委员制[15](p655)。
段氏同意接受“临时执政”之职,却不愿意立即晋京就职,而是故作姿态,“不得全国一致之拥戴,决不率尔登台”。直到“拥戴之电文,如雪片飞来,迎驾之代表,亦联翩莅止”③,方于11月22日晋京。之前一日,发表“马”电,标示政见,称曹锟贿选,已将“法统”破坏,无可因袭,惟有“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基于这样的考虑,段提出召开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的主张。[16](p1478)虽然后来如期召开的善后会议未能解决直奉战后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甚至会议本身也没能自善其后,国民会议也未能如愿召开,但段氏提出的对于国内问题分别标、本进行治疗的手段均为会议协商而非武力解决,释放出“和平统一”的强烈意愿。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在就职宣言中,段作出“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的表示。随即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国家政权由临时总执政、国务员、国务会议组成。临时总执政总揽军政、民政,统帅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务员由临时执政任命,分掌政府各部,襄赞临时总执政处理国务;国务会议由临时总执政召集,临时总执政发布命令及国务文书,由国务员副署。根据这一政制,段祺瑞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桑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另外,在宣布“革新政治,与民更始”的同时,规定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法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17]
为了筹备建设,厘定制度,段祺瑞于12月4日下令设立临时法制院。④次年4月7日,段氏召集国务会议,制定《临时参政院条例》,随后颁布《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令》,规定了临时参政院职能及“参政”的选举办法。临时参政院的权限主要有两项:一是议决权,包括省自治促成及国宪实施前规定省自治条例,善后会议及军事、财政两善后委员会决议执行事项,调停各省间及各省内部的纷争,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募集内外债及增加租税等等。一是建议权,将行使上述权限时所议决者,向临时执政建议,经采纳后交主管机关执行。[18]
段祺瑞就任执政之初所作政制建设,将民国肇建时所设政制中的府、院权力集于执政一身,虽无“总统”之名,却也表现出一定的集权倾向。段在“马”电中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承乏,一旦收束局面的善后会议结束,就将“卸责”[19](p23),似已承认临时执政只是政治上的一种过渡。但就职将近一年,“临时执政”兜揽府、院权力的局面仍未改变,致使执政府招致许多批评。褚辅成等在善后会议上甚至提出《修改临时政府制》的议案,非常国会亦频繁活动,企图恢复“法统”,给段祺瑞政府造成极大压力。
1925年12月下旬,借浙奉战争中郭松龄倒戈的形势,国民军控制直隶全省,就近构成对中央的压力。为争取冯玉祥的支持,并回应社会各界提出的恢复责任内阁的呼声,段祺瑞宣布改组政府,修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国务会议改由国务总理主持,国务文书改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12月31日,段任命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国民党人于右任、易培基、马君武分别被任命为内务、司法、教育总长。由于孙中山去世前曾发布国民党人不得出任临时政府职务之令,于、易、马等人未就职,许世英也不愿就任国务总理,只好由陆军总长贾德耀代理。此外,段祺瑞还指示国宪起草委员会拟订国会组织法、总统选举法和宪法。国会拟采取参、众两院制;总统选举法则规定以县为基本选区,由省选举会选举总统;宪法亦在国宪委员会三读通过。[20](p255~267)
这次改制,恢复了民元以来府、院分立的政制,对于国会政治的价值亦重新予以承认并作出重建国会、实施宪政的姿态,民国政制史上短暂的没有分权制衡机制、被批评为“狄克推多”的政权形式似乎出现了为“民主”政制取代的可能。但是,由于这次改制发生在执政府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之际,很大程度上已被执政府当成应付统治危机的手段,而导致这种危机的内外因素并没有排除。在一个政权的生存业已成为问题的情况下,其改制措施的命运前途,可想而知。⑤
二 平衡南北新旧的权力分配
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倾覆后,反直三角同盟不复存在。此时国内政治、军事力量形成相对独立的五支:一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二是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三是长江一线的旧直系残余,四是滇唐为代表的西南势力,五是孙中山领导的两广革命势力[21](p114)。就相互关系而言,本来奉张、国冯及孙中山领导的两广革命势力系反直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与战败出亡的吴佩孚及其亟欲联络的长江各督处于敌对位置。但是就政治分野及派别历史渊源而言,奉张、皖段、旧直系以及从旧直系中分离出来的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均属于北洋统系,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之间又有着某些共同利益。而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以及滇唐、湘赵、粤陈等“联治派”,则属于或至少是被时人视为“国民党系”[22](p97~98)。在地缘政治上,前者大抵属于“北方”派系,后者则当划归“南方”派系,两派相争具有政治上新、旧之争的色彩,但有时出于利益之需,不仅南北新旧各自内部发生分裂,即新与旧或南与北之某一部分亦可能暂时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其政治敌人,这就使中国政治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后面临的最大政治难题,是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在国民党北伐之前,由于其党人未能占居政治中心位置,加之民众尊崇正统的心理作祟,北洋势力依然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重心所在。所谓“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23](p282~283],客观反映了这一政治形势。因而对段祺瑞而言,实现统一的基本前提,就是对早呈四分五裂气象的北洋集团进行整合,使之集于自己麾下,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和权势中心。如是,则占据两广的国民党和僻处西南一隅的唐继尧等将不难对付。
为达此目的,段祺瑞作出的第一个表示就是摆脱安福系的政治窠臼,使自己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出而治世。安福、政学两系曾经是段祺瑞重要的政治力量,“段氏入京后,安福系、政学会等(政团)人物,集于其左右”[24]。段祺瑞曾多次电请安福系政治首领王揖唐来京,“倚王为东南锁钥”,有由王组阁之议,后来又任命为安徽督办,以致时论有“段派除以全力占领北京之各部署局所,以期恢复安福全盛之势而外,并无深合于人心之设施”的尖锐批评[25]。张作霖对此也深为不满。为摆脱政治窘境,段派要人在段就职不久即公开通电,作出取消安福系的表示[26](p239)。
接着,段祺瑞以超党派政治领袖的姿态处理政务。首先是平衡各实力派之间的关系,避免冲突的发生,其中最棘手的是处理国民军与奉张的关系。国、奉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两派,均力图左右中央政治,使段深感棘手⑥。段氏曾向各方作出驻守原防、保土安民的要求。但奉张以齐燮元通电长江各省独立,驱齐刻不容缓,且需护送倒直一役在江南发难有功的卢永祥南归就任苏皖宣抚使为由,力主沿津浦线南下[27]。虽奉系内部的“稳健派”如王之江等持“自重主义”,但其“激烈一派”则主张“乘此机会,最少限度,亦须将黄河以北,收归奉天范围之内”[28]。国民军不甘示弱,也借机向河南等地扩充势力。迫于压力,段祺瑞同意了由奉张等提出的重新划定各方军队驻防区域的要求,其区划大致为:京奉线、奉天廊房间、津浦全线归奉军守备;京绥线、京汉线、廊房北京之间,暂归冯、胡、孙各军驻守。这就打乱了段氏最初的设想,为奉军沿津浦线南下山东、安徽、江苏,最终引发新的军事冲突埋下了隐患。只因国民军控制北京这一政治中枢所在,且其军队数量已大大扩充,国、奉之间的平衡尚能暂时维持⑦。
在对待吴佩孚及长江各督问题上,奉张、国冯均主张用武,以便彻底打垮曹、吴[29](p28)。奉军在吴败亡之后,仍不废军事布置,大举入关,即出此考虑。冯玉祥甚至悬出赏格,无论军民,凡活捉吴佩孚,均赏10万元,击毙赏5万[30]。尽管在对待吴的问题上,奉张与国冯曾有一段时间的“弃嫌结合”[31],但段却有自己的打算。一方面,由于尚未占据稳固地盘的国民军在力量上不足与奄有富庶之东三省作根据地的奉张长期抗衡,因而国冯与奉张之间暂时的平衡势必打破。在奉张咄咄逼人的威逼下,冯玉祥被迫三上辞呈,即为平衡将被打破的表征。在这种情况下,段不得不寻求新的力量平衡。另一方面,就个人历史记录而言,冯氏曾数次反戈,政治上反复无常,他的“拥戴”是否可靠在时人看来也成问题⑧,因而不能不加防范。此外,由于直系将领普遍将已方的失败归咎于冯“背信弃义”,坚持对任何人均可宽恕,唯独不宽恕冯的立场,故冯在段氏身边的活动已经成为旧直系及吴佩孚承认中央政府的一大障碍。反过来说,冯提出辞职,也就向吴等提供了拥段的机会⑨。段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层,在冯氏第三次递交辞呈之后,即同意“给假一个月”,以后又尽量避免让冯氏身当要津,从而为接近吴佩孚及长江各督铺平了道路。
段祺瑞对付吴佩孚及长江各督的办法为刚柔并济。就职不久,段曾做出强硬姿态,令刘镇华、憨玉琨部“以兵逼吴”[32](p274)。与此同时,段又“迭与吴佩孚信使往还”,主动进行联络。吴为保存实力,争取地盘,派代表进京请段将河南军政民政,交其掌管。段虽未满足其要求,但派人向吴表示,“除地位问题外,举凡生命财产自由等,允为充分之保障”,且邀其晋京,面商善后。对于吴之过去,仅责以“拥戴非人”,而未及其他。段软硬两手,使业已穷蹙的吴佩孚不能不暂时就范。11月24日,吴复电政府,表示“解决大局办法,当与芝老(段)共趋一致”[33](p251)。其他直系将领,慑于奉张之威,以为曹、吴虽失败,北洋领袖尚有段在,既可借以自存,又何必陪曹、吴同亡?[34](p499)故苏齐(燮元)、赣蔡(成勋)、闽周(自齐)、浙孙(传芳)、鄂萧(耀南)、鲁郑(士琦)亦陆续表态拥段。尽管这些表态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毕竟还是加重了段制衡奉张的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完成“以直制奉”之部署后,段亟需对付的是西南实力派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西南实力派力量小而分散,滇唐(继尧)、湘赵(恒惕)、粤陈(炯明)在地理上彼此相隔较远,难以在军事行动上相互配合,其“会师武汉”之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即此证明[35]。孙中山穷于应付商团的敌对行动,且此时已与陈炯明关系敌对,自顾不暇。纯粹从力量上分析,西南实力派受中央重视的程度远逊北方实力派。但西南方面注重打政治牌。滇唐、湘赵、粤陈极力鼓吹“联治”,与上海方面的唐绍仪、章太炎等在政治主张上同调⑩,政治影响力不可小觑。孙中山在反直军事行动中虽作用不大,但毕竟是“反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加之曾任临时大总统,又有“三民主义”相号召,政治影响力实不在段之下。这就使段祺瑞不能漠视西南实力派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的存在。
应付西南的下手功夫是从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做起的。天津会议上,段祺瑞曾表示一切大政方针须待孙中山进京后共同商议决定,后因形势急迫提前登上临时执政位置。在安排政府各部官员时,段亦充分考虑了孙派代表。在政府新设立的9个部当中,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有唐绍仪、杨庶堪、叶恭绰等3人。李烈钧被任命为参谋总长,更是段政府对国民党作出的一种姿态。段氏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实施安抚,乃是出于争取西南实力派支持的考虑。时论明确指出:“惟统一西南事,须征中山意见,元帅推重中山以此;在中山未到津前,一切事未能决定,段颇为然。”[36]这一做法的“示范”效果很快显示出来。当孙中山表示出与段“合作”之意向后,西南实力派的表态也都差强人意。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一度因内部分歧而呈乱相,内部关系亟须调整,其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亦受到削弱,段祺瑞遂将重点放在了维系与滇唐及四川实力派的关系上。
与平衡各派势力相关的政治举措是大批疆吏的任命。围绕这一问题,各方明争暗斗异常激烈。执政府成立之初,张作霖曾声言,“对于执政府,不荐举奉系一人”。但实际上,其向执政府举荐之奉系官员为数不少(11)。冯玉祥不甘落后,也尽可能地举荐自己的人,主张像胡景翼、孙岳等,“必尽先与以好位置”[37](p645)。不过,由于多数省区表示拥戴中央,执政府又颁布了“文武百官照旧供职”的命令[38],可重新分配的地盘有限,故争夺范围主要集中在原先由直系控制的直隶、江苏、安徽、陕西、甘肃五省。
直隶屏蔽京师,地当中国政治冲要,历来都是政治家必争之地。该省战前系由直系将领王承斌控制。王的督办位置虽系曹、吴安排,但王毕竟曾与冯玉祥一起发动北京政变,系推倒曹、吴的有功人员。然而直省这样重要的位置,奉张岂能放心让王继续留任,加之王与冯关系密切,故奉张千方百计进行排挤。王对此不能没有感受,遂以收束军事为名,召集残部,驻扎天津,以谋抗争。正当王氏收编残部时,张作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兵压境,勒令王部缴械。王不安于位,避入日租界,通电辞去本兼各职。[39]
王被迫辞职,对冯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冯在日记中写道:“因张雨亭将王之军队解散,王即通电辞职。张之背约负友,其端已见,余亦寒心矣。”[40](p654)随后,奉张与国冯为直省督办一职展开激烈争夺。本来冯玉祥之意,是要让孙岳接替王承斌长直,段似已同意,故有派人向奉张疏通之举,但未得奉张同意。张氏最初曾有以其子学良督直之议,后出于与国冯竞争之考虑,又打出“直人治直”的口号,企图以此作掩饰,将奉系骨干、时任奉军陆军第二军军长的李景林安置在直隶督军兼省长的位置。段不得已而偏袒奉张,使李得补直督缺。好在李与冯关系尚可,故能接受这一安排,而奉张不知。后来郭松龄与国民军联合发动反奉战争,李倒向郭、冯一边,其与冯早有接洽,或即原因之一[41](p280)。
安徽省长一职最初蚌埠诸将拟推倪道烺出任,但段不之许,而任命王揖唐担任,并以之督办军务善后事宜。段氏此一任命,用意甚深。盖王氏控制皖省军、民两政,可以为段在家乡植一稳固地盘。且皖省位于苏、鄂之间,于长江统一前途,关系甚大。王与长江各督一向颇有联络,以王长皖,可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42](p407)这一任命没有遇到多大麻烦,不料王任职不到半年即辞职,幸其后任吴炳湘仍属皖系骨干,尚能贯彻段之旨意。
江苏军民长官的任命则相对棘手。先是卢永祥由奉军“护送”,以宣抚使名义南下驱齐,段对卢曾有苏督的任命。但卢表示不要地盘,且发表废督主张,故于苏省督办一职,迟迟不就。至于省长一职,奉张早有以郑谦担任之议并征得段同意。嗣因郑一时难以南下,卢之左右遂联络苏绅,主张以卢代理省长。[43]直至段以政府命令,敦促卢氏就职,卢方遵命兼办江苏军务。但在郑谦南下接替韩国钧任江苏省长之后不久,卢又决定辞去本兼各职。卢被时人视为“军人中之一政治家”,颇具时望,反直战争以来,注重调停奉张与皖段关系,他的引退,使“此后可以当疏通执政府与奉天间意见者,不复有其他适当人物”[44]。
8月底,执政府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孙岳为陕西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以填补卢永祥辞职之后形成的空缺,姜登选为安徽督办以接替前任皖督。加上早些时候作出的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等分任督办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善后事宜,以及李烈钧长赣、方本仁督赣等决定,段祺瑞初步完成了战后疆吏的人事调整。[45]
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的基本手段,是利用北洋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促成或维持各派之间的“均势”,利用各派间的力量制衡,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其苦心为冯、张分配地盘,将苏、皖畀奉张,陕、甘畀国冯,目的全在于此。在段的政治棋盘上,不能没有冯,否则无以制张;也不能没有张,否则冯将无法驾驭而构成对自己的威胁。但又不能对张、冯过于接近:近冯则长江方面将为之却步,如是,则“统一”将化为泡影;近张则难免为其傀儡,且可能遭致与控制京师的国民军发生对抗从而祸生肘腋的危险。而长江、西南各方,也都成为砝码,被段氏用来搞政治平衡。段氏为维持各方关系,煞费苦心,但其效果,正如吴虬分析的那样,“俨比老妇分苹果饵,务求燕雀均衡,以免群儿相斗。谁知国库帑藏有限,疆圻究有肥瘠,虽予取予求,不敢瑕疵,而馋吻并张,焉能悉偿其愿?”[23](p256)
从各实力派所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看,当时亦存在维系政治权力暂时平衡的条件。在各实力派中,奉张系反直三角同盟中“执牛耳”的一方,战胜之余,自不愿听命他人,其表示“拥段”,不过是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缺乏号召力,推出段氏,既有利于稳定局势,又便于奉方从幕后操纵。国民军方面拥段,系感受到奉张的压力所致,联段可造成国、奉之间的平衡,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在联段同时,极力渲染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关系,亦同出一种考虑。长江各督“拥段”则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盖长江各督多属直系,曹、吴倒后一时处于难以自立门户、无所归属的游离状态。吴佩孚在白坚武的策划下,打出“护宪军政府”旗号,企图将长江各督纠集在一起[46](p499)。而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周荫人等,既不愿意降服于奉张,又感到吴佩孚的实力已被抽空,不足依靠。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兼顾维持各方关系并能顾全自己面子的办法就是“拥段”。至于吴佩孚,以直奉交战故,视奉张为“公敌”;复以冯玉祥背叛曹吴,反目倒戈,视之为“私敌”[47]。因国、奉两大敌对势力的存在,自然会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而待段。对段表示“拥戴”,可借段之斡旋暂时避开奉张、国冯的军事压力,并借此寻求新的生存发展空间。以上种种政治平衡机制,被富于政治经验的段氏及其左右窥见并把握运用,其政治统治也赖以暂时维持。
三 预示北洋崩殂的政治结局
国内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被段氏维持了将近一年。这期间,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其中包括南下奉军与浙江方面的矛盾,国民军与奉军在京津地区的争夺,河南的胡憨之争,西南的滇桂战争,等等。虽然这些军事冲突尚未严重到足以动摇执政府统治的地步,其中一些冲突,如河南的胡憨之争和奉、浙之间形成的紧张局势,经和平斡旋与武装调停当事各方已勉强就范,但导致国内武装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尤其是奉军南下引发的浙、奉矛盾及国、奉之争,几乎无法弥缝,处理稍有不慎,就会牵动全局。
1925年10月,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浙、闽、苏、赣、皖五省联军以“拥段反奉”为号召,不顾段之调停,断然向奉军发起总攻击,浙奉战争爆发。国民军方面以为时机已到,开始与孙传芳密商反奉计划。不久又与奉军第10军军长郭松龄订约,建立反奉同盟,并暗约李景林加盟。奉张为对付国民军,决定暂弃前嫌,与吴佩孚结成直奉联盟。以后各派政治军事势力怀抱不同目的,彼此大动干戈,战场上的形势变化莫测,政坛局面亦波诡云谲。浙奉战争的爆发,宣告了段祺瑞整合北洋体系努力的失败,建立在各方“均势”之上的段执政的政治生命,也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临近终结。
段祺瑞没能如其所愿,成功整合北洋军政体系,当然也就没能延续临时执政府的命运。段与临时执政府的政治结局,与皖系实力过早衰退有关。段氏与皖系政治上真正可能有所作为的时代,是在袁世凯死后以国务总理身份控制北洋政府时期,以及讨伐张勋,“再造共和”,继续掌握政权的几年内。1920年直皖战争败给曹、吴之后,其权势的巅峰期已经过去。第二次直奉战后段能复出,不是因为具有实力,而是因为奉张与国民军争执不下,拣了个政治便宜。然而依靠权力平衡推出来的政治领袖,日子从来都不好过,因为平衡很容易被打破,维系政治统治所需的是实力。但正如时人所言:“段在今日,可谓毫无凭借,其部下只有德州胡翊儒之一旅,兖州吴长植之一旅,为心腹军队。”[48]可以说,蛰居复出的段氏,已经近乎“手无寸铁”[49]。奉军将领何柱国说:“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那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29](p28)所谓“罩得下”,是说在特殊情况下各方尚能接受他;所谓“吸不住”,指自身缺乏实力的段氏,已经不能臂使指应的调度指挥各路人马。执政不到两个月,便有人将段氏与徐世昌相比,指出他“已入十年东海境地”[50]。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政府要想成为早期袁世凯政府那样可以对全部北洋军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不仅是段祺瑞,在当时尚存的北洋各实力派人物中,没有哪一位具有重新整合旧北洋军政体系的能力。吴佩孚一度具备整合北洋的实力,且被认为是北洋正统,却因支持曹锟“贿选”丧失政治号召力,复因坚持“武力统一”导致北洋直派离心,加之新近战败,不足当此重任;力量相对强大的张作霖与北洋嫡传各派关系较远,吴佩孚就“一向不把张作霖当作北洋正统”[51](p25);从直系分离出来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反复无常,难以自立;至多只能算是北洋远亲的西南各军阀陷于内争,或不具备问鼎中原之实力,或本来就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整个后袁世凯时代,能够为北洋各派军政势力公认的政治权势中心一直没能形成。
相对而言,段在北洋军政系统需要重新整合的时候,还算是一个差强人意的人选,至少以小站出身、北洋元老及曾经“再造共和”的资格,他还能够将桀骜不驯的各方暂时“罩住”。既然段也没能完成重新整合北洋的使命,则他本人政治命运的终结,也就预示着整个北洋政治军事体系即将终结,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改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而一旦北洋系统丧失了最后一次整合的机会,等待它的就只能是无休无止的内争和内耗。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党在经历孙中山去世后短暂的内部关系调整之后,借助苏俄的援助而壮大,即便“反赤化”的旗帜也未能为北洋体系的成功整合提供新的机会,结果北洋体系彻底崩殂,以至于作为北洋后起势力的“保定派”新人也纷纷同情甚至投靠南方[52](p36)(p179)。中国的政治格局由是发生新的变化。两年以后的南北新旧之争及新一轮的“武力统一”以国民党“党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可以透过段祺瑞执政府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蒇其功,得到部分解释。
注释:
①中国政治史上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变化因此而发生:由于段祺瑞在否定旧的“法统”和国会之后未能如愿召开国民会议,实现国会制度的新旧过渡,民国以来国人追求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在作了生存的最后努力之后终于寿终正寝。中国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在此期间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弛张变化,既存政治力量中的“文治派”逐渐兴起,军人不得干政的口号呼声也越喊越响亮,“武力中心主义”开始失去信仰。随着中央政权的支配力量减弱,地方意识亦逐渐增强,中国政治呈现出区域化的明显特征,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中央政府为改变这种状况曾作出一定的努力,但事与愿违。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变化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有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 1926》,《史林》2003年第1期,《“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与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等。本人亦有数篇论文论及。鉴于以往的研究大多偏重“论”但相关历史事实铺陈却不甚清晰,本文采用纯叙事手法,试图为研究者认识直奉战后段祺瑞重新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提供经初步逻辑梳理后的历史素材。
②如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炯明、西南方面的唐继尧、熊克武、石青阳、但懋辛、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甘肃督军陆洪涛、陕西的刘镇华、山东的郑士琦、浙江的孙传芳、湖南的赵恒惕、安徽的马联甲、热河的米振标、察哈尔的张锡元等,都电请段祺瑞出山。当时的一篇报道曾明确指出:“此后可代曹吴政府之联合势力中心人物,除合肥之外,当无它属。此乃中外所公认者也。”引文见《段合肥与本报记者论时局》,《顺天时报》,1924年10月24日。
③截止11月6日,已有21省区疆吏通电拥戴段祺瑞出山,奉张、国冯及其主要将领,亦通电敦促,造成在拥段问题上“全国一致”的形势。见尧日《段祺瑞应时而兴》,《申报》,1924年11月14日。费保彦:《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2月21日。
④临时法制院由院长、评议、参事组成,内设事务厅及四处两股,任命姚震为院长,负责有关法规命令的拟订,审查条议有关宪政的制度、典章及临时政府特交审议的事项,收受审定有关法制的条陈,以及保存临时政府发布的有关法规性质的命令的正本,等等。见《临时法制院官制》,《北洋政府公报》,1924年12月3日。《临时法制院办事细则》,《北洋政府公报》,1925年1月12日。
⑤段祺瑞之后,出而主政的颜惠庆、杜锡珪及后续内阁均受直、奉军阀左右,有职无权,且因时值非常,在政制上仍然只能起过渡作用,没有建树。
⑥这一点,连冯玉祥自己也不讳言,他在日记中写道:“段公上台对军事不敢以命令式指挥,所以他夹于两大势力之间,凡事均不好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67页。
⑦据丁文江统计,截止1925年9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已达8万,加上岳维峻及孙岳部下,全部国民军的人数,应不下30万人,而奉军8部,共计35万人,从数量上看双方已较为接近。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6),第407页。
⑧冯玉祥亦意识到张作霖对自己不放心,其日记有言:“吴佩孚与我为良友,我既将其推倒,张雨亭何能放心于我?若不放心,将来尚不知发生何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59页。
⑨《吴佩孚致冯玉祥书》,《申报》,1924年11月29日。《冯辞后之中国时局观》,《申报》,1924年11月29日。昔日吴虽参与倒段之役,“然平居恒认段为中国唯一之当国人物”,其效忠曹锟,系束缚于旧礼教之缘故,而非敬重曹之才能。故只要冯辞职,其拥段是完全可能的。
⑩滇唐、湘赵等与在上海的唐继尧、章太炎等在联治问题上的呼应,可参阅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9~804页)中收录的有关章氏的言论及时论。
(11)截止1925年1月上旬,奉张向段政府举荐之人有:于冲谟,荐为驻日公使;朱庆澜,荐为直省省长或京兆尹;王大中,周大文,所荐职官不详,然其受张推荐则属实。《张作霖向段举荐之人员》,《申报》,1925年1月10日。
标签:段祺瑞论文; 冯玉祥论文; 吴佩孚论文; 张作霖论文; 孙中山论文; 直奉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长江论文; 北洋集团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