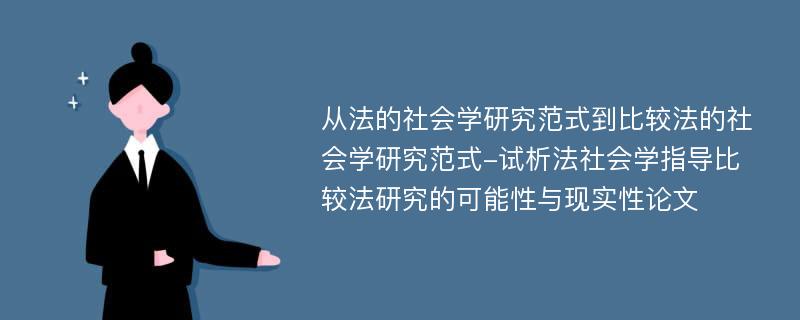
从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试析法社会学指导比较法研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毛皓强
摘 要 :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的联系要回溯到法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中进行理解,从法的社会学研究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不仅经历了比较法本身的复兴,同时也见证了法社会学和法教义学的理论之争。在理解比较法的教义层面和社会层面时,最好的先例或最佳的理解途径便是法社会学当初融合法学和社会学的事实经过,因此比较法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可以在历史中寻得。而与之对应的现实性难题则不妨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案例中进行理解,毕竟法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作为法律修改源头的社会事件本身,在这个层面上,比较法的法社会学研究也不能闭门造车,脱离社会现实而空谈教义。
关键词 :法社会学;法教义学;比较法学;社会学;法学
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纳入到法学研究的体系内已经成为了当下法学研究范式中的热门方法,这一发端于美国,成熟于欧陆的研究进路为曾经法教义学(legal dogmatics)一统天下的理论格局带入了新的学术活力。正如坎托罗维奇(Hermann Kantorowica)所说:“没有社会学的教义学是空洞的,没有教义学的社会学是盲目的”,社会学不仅在法学研究的实证领域指导着司法机构的法运用——这在普通法系尤为重要,更在法的理论层面发挥着重要影响,而比较法在理论法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长久以来,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们似乎一直对比较法和法社会学的关系存在着很深的误解。莱塞尔(Tomas Raiser)曾经指出,法社会学研究在德国的发展分为“沉寂、复苏、回落和升华”四个阶段,与之相对的时间点分别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60至80年代、80年代以后以及当下。在谈及回落阶段时,他毫不避讳地说道: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法社会学讲席的设置数量再度出现回落,并因此伴随着令人担忧的后果:其学术新生力量也将难以为继。反倒是在法律欧洲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中,比较法研究强势出位。[注] [德]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基本问题》,王亚飞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陶水旺在文城街上遇到表姐之后,跟着去了她杨湾家里表示感谢。见到李石磨,陶水旺自然又是一番感激,他一个大男人,说啥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李石磨留他吃饭,他也没太客气。
显然,莱塞尔将比较法在德国法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再度兴起视作了一种对原本法社会学研究的嬗替。[注] 说“再度”是因为比较法并不是在这一时期才出现在欧洲大陆的,19世纪中后期的欧陆便出现了比较法研究的热潮。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其实法社会学研究和比较法研究并不是非此即彼或是一体两面的,莱塞尔方才的评价显然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总结和描述而已,并非是针对学术研究本身而言的。诚然,在德国的法学学术发展体系中——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注] 如其所说的法学教育、研究兴趣以及学术新生力量等问题。 ——或许真的存在比较法学研究对法社会学研究的取代,但并不能说明这一趋势在其他国家会同样发生,这种观点本身就是运用比较法学研究国别法时的基本态度。那么,比较法学研究与法社会学研究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回到莱塞尔的文本,他自己就给出了答案——在谈到社会学有何可助益于法学研究的方面时,他认为至少在经验的社会研究和统计方法上、在理论和素材的收集上,以及在对既有法律的批判上,社会学对法学研究有着指导和借鉴的意义。[注] 同前引[1],第78页。 作为组成理论法学一部分的比较法学来说,法社会学的指导作用自不待言。然而,从社会学到法社会学的过渡就经历了韦伯(Max Weber)、庞德(Roscoe Pound)、埃尔利希(Eugen Ehrlich)、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卢曼(Niklas Luhmann)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从法社会学到“比较法社会学”是否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呢?从可能性上看,比较法本身就暗含着社会属性,比较法的研究主体并不是单一而独立的国家法,而是以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家法为表象、以其形成这些法律的社会因素为内核的一个综合对象;而社会学也并不是闭门造车、孑然独立的学科,历史社会学研究和比较社会学研究便是社会学的两种分析视角。[注] [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613—634页。 因此,两门学科的借鉴并不是可能。那么,比较法和社会学的结合有没有必要呢?或者说两门学科相互吸收的现实性存在吗?通过近几年来所发生的两起重大案件——“于欢案”和“昆山反杀案”——以及社会学理论内部的自洽,我们会发现,比较法研究和法社会学研究同时也存在着高度的现实性。
一、从社会学研究到法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而法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法律、法律行为实施者以及由法律行为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此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似并无多少联系实则有诸多交集。
首先,法学的研究是以法律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的,而没有实在法的规制就不会有所谓的法律个体,照此逻辑,法律个体是伴随着法律的创制才有其意义的,换言之就是先有了实在法才有了受实在法调整的法律个体。社会学中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此类推。那么,法律个体这个概念又是如何得来的呢?按照莱塞尔对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和法律人(Homo Juridicus)的划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对这个概念有所了解。“经济人”概念本身是一种个人主义式的提法,此范畴在波斯纳(Richard Posner)的文本中多次被提及,而这里的“人”同社会人、法律人一样是出于学术认知的目的,是源自社会现实而又抽象出来的一种构想,是一种学术创造出来的“人造人”(Homunculus),因此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被赋予的使命便是追逐经济利益。推而广之,“社会人”是莱塞尔基于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学术观点和著作而总结出的概念,有如经济人的使命就是趋利避害、规避风险一样,创设社会人就是为了让其完成社会扮演的使命,在社会学的框架中,为了更好地融入与其他社会人的交往中,这一概念是不允许染上任何色彩和任何学科背景的,当然,如此苛刻的要求也就使得社会人并不具备法律因素了。[注] 同前引[1],第54—61页。 而法学研究中所说的法律人就是学术话语体系中拟制出来的抽象个人,虽然有略微差别,我们这里姑且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上面提到的法律个体。[注] 差别就体现在法律个体更多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概念——受法律调整的个人,而法律人则不是,它更抽象更具有一般意义。 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探讨法律人和社会人的任务就有了合理性。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社会学研究的进程中不可能无视法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作为社会变量因素之一的实在法及其衍生出的诸如国王敕令、神谕一类的政治性条文时常在关键时刻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光荣革命如此、美利坚革命如此、法国大革命亦如此。与此同时,法学研究在对法条产生原因进行量化分析时更不可能单纯地回到文本中去抠字眼,社会背景的分析和考量都将成为法律创制和法律实施后认同感调查的重点研究对象。因此,至少从法律人和社会人的关系上看,二者相辅相成。
农村地区基层防疫检疫工作至关重要,涉及的范围较广,工作任务量较大,相关部门需要落实各项管理办法,设定相应的管理机制。整合各项问题,有针对性采取应对控制措施,提升防疫检疫工作质量,促进农村畜牧业长远发展。
其次,法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着相互吸收和借鉴的可能。按照拉伦茨(Karl Larenz)对法学的定义——法学就是以特定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注]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页。 其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的便是解释性的任务,亦即对法条的理解和阐释,其中又涉及到对法的概念的法律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的观察研究以及法官对制定法的续造等问题。简单来说,法学的研究方法并不复杂,其大致分为内外两种观察视角(这里所说的内外视角并不是仅针对法的概念而言)。所谓内部视角说简单一点即法律人研究法律问题,而与之相对的外部视角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其他人”所看待的法律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便一目了然——法律人群体中尤以普通法系中英格兰法官的职业群体观最为强烈,他们认为法律是自有法可依、有迹可查、有证可考的盎格鲁-萨克逊时代便流传并积累下来的惯习,这些惯习通过国王或巡回法官们的编纂和汇集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拘束力的话语体系;[注] [英]S. F. C. 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而社会学家从不会对法律是什么做出如此经验性的回答,马克思(Karl Marx)明确地说过法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卢曼也曾指出法律就是经过了时间化、人身化和事务化归纳的行为期待。[注] [德]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 概言之,这便是法学的内部和外部视角根本差异的一种表现。然而,即便这样的不同也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比如马克思在给出法是统治工具的定义时并没有否认法律的历史沿革、权威性评价等特征,卢曼在界定法律时明显兼顾了法律规范作为社会行为调整机制本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等属性。与之相对地,即使是比之社会学的出现和兴起还要早得多的,以柯克(Edward Coke)为代表的英格兰普通法院职业法官在强调法律职业群体的封闭性时,也无意间运用到了后来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法官和律师们只有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击垮詹姆士国王(James I)的工具。[注] 于明:《法律传统、国家形态与法理学谱系——重读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故事》,载《法治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 因此可以说,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和讨论,法学和社会学之间是存在着联系和互动的。
如果说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互动解决了从社会学到法学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法律发展本身的滞后性以及法学理论的滞后性又为社会学的引入提供了现实性条件。庞德曾经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文中对“何为法律”这个问题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在社会控制层面上看法律具有三个面向:
第一,法学家们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是指通过系统的、有秩序的政治组织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第二,法律是一批据以作出司法或行政决定的权威性资料;第三,法律是为了维护法律程序依照权威性的指示以决定各种案件与争端的过程——法律就是公务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注]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家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4页。
实际上,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考查便会发现,其实我们方才所论述的、所谓的“法教义学中的比较法学”仅仅只是一个抽象化和剥离化的理论模型而已,这种绝对主义倾向的研究进路在比较法研究的学术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而笔者将这种极端的情形搬出来讨论正是为了说明比较法学和法社会学并不是一体两面或者说非此即彼的,因此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环境内就不应当存在像前文所述80年代的德国那样为了争夺话语权而打破脑袋的现象了。
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解,与比较法学首先产生联系的便是法教义学。根据茨威格特的系统考察,最早的比较法研究可以追溯到15世纪福蒂斯丘(Fortescue)的两部英国法律史著作。在之后到来的人文主义法学时代和启蒙时代里,各国法律之间的比较逐渐成为常态,但无论是培根(Francis Bacon)、柯克还是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都没有明确提出比较法的概念,而仅仅在国家实体法的比较层面运用了被我们后人所总结概括出的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而已。与此同时,茨威格特更进一步指出:
“苏麦188”自2012-2014年连续3年在宜兴市进行了小麦新品种大区示范,产量分别为481.3 kg/亩、446.5 kg/亩、456.7 kg/亩,3年平均产量为461.5 kg/亩(见表1)。经过连续多年的示范种植,“苏麦188”具有较好的产量优势。
二、法教义学中的比较法学
回到莱塞尔的文本中,如上文所说,在《法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中莱氏将20世纪至今德国的法社会学研究划分为四个时间段,分别是“沉寂、复苏、回落和升华”。在谈到法社会学研究热潮有所回落时,他提到了比较法学研究复苏对法社会学研究所造成的冲击。按照茨威格特(Konrad Zweigert)对比较法所下的定义:
比较法(Rechtsvergleichung)是指一方面以法律为其对象、另一方面以比较为其内容的一种思维活动。“比较”可以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Rechtsordnung)之内的不同规则之间进行……比较法的意思当然不是指它,而是指更深层的含义。这个更深层的含义是超国家的(das bernationale)。因此,比较法首先是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法律秩序的相互比较。”[注]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图6所示,当被控对象稳定在工作点2情况下,做设定值阶跃扰动,采用与之前相同的两种控制器,被控对象的输出曲线。分析可知,当被控对象的工作点发生变化时,传统的控制器的控制效果也会减弱,超调量变大,调节时间变长;而多模型DMC控制器同样能够取得稳定的控制品质,验证了多模型DMC控制算法的有效性及鲁棒性。本文提出的基于加权算法的多模型预测控制策略具有较强的自适应能力,能够较好的适应对象参数的时变。
比较法并不是国内实在法之间的相互对比,而是以国家实体法为对比对象的跨域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法律秩序显然是针对法律运用和实证层面而言的,虽然没有提到法律的社会因素,但阅读茨威格特的文本却不难发现其在对比法律秩序时或隐或现的社会背景分析,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法社会学研究被纳入比较法研究体系中的可能性,但此处我们仍要对比较法的法教义学意义进行追问。
虽然所有人都看出萧飞羽是诚心问计,可无论铁卫、刀手,还是剑士昔日都是绞尽脑汁与黑旗会周旋,这会也如黔驴技穷似的面面相觑。萧飞羽见众人沉吟习惯地耸了一下肩膀道:“虽然黑旗会不会坐视分坛覆灭,但我会设法使他们来此的步伐略为迟缓,这样我也许能使我愚笨的脑瓜子乍现一缕灵光,你们也能一边从容修炼,一边细思量。”
按照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比较法研究有两个不同的研究进路,分别是“立法比较法”——在创造新的本国法律之际参考外国法,以及“学术理论的比较法”——为了更好地认识法律起见,对不同的法律制度进行的比较考察。[注] 同前引[16],第76页。
因此,从研究对象、方法、现实性等领域我们都可以得出法社会学与社会学和法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可见作为交叉学科的法社会学并不是一座可有可无的“空中楼阁”。
关于法教义学和法社会学的关系,熊秉元教授曾经有过精彩的表述。他认为传统法学里所讲的种种教义是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归纳而得出的,因为根据这些教义的指导所得出的结果往往是“好的”,因此法教义学(教义法学)可以说是一种速记式的和经过简化了的结论。与之相对的法社会学(社科法学)则正是法教义学的基础,它正是法教义学所言之教义的原因。熊教授进一步指出,法教义学之所以在法学院所主导的教育体系中压倒法社会学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是因为教义(doctrines)本身已经是思维简化了的速记,除非碰到特殊情况,否则无须每次都检验这些教义的合理性,法教义学的教授在时间成本上和理解成本上相较于法社会学要实惠的多。[注] 熊秉元:《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再者,法社会学是在了解社会的基础上设计和操作法律的,而法教义学则直接是在诉诸权威的基础上完成这些任务的,如此一来,即便是不了解社会的变化及其对实在法所带来的影响,教义学体系仍然健在,对法科生或者前文所述的法律人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既成的变化而已。
这两对范畴分别指涉了前文所提及的实在法的研究以及理论法的研究,与这两者联系最紧密的并不是法社会学这一后来者和新兴的交叉学科,而是法教义学这一相对简单和直接的传统学科。因此,在20世纪中后期比较法的复兴过程中与其直接进行对话的便是一套在卢曼看来“自我指涉”和“自我封闭”的法教义系统。就连茨威格特在《比较法总论》中也承认如果将比较法研究的对象扩大为包含了所有可能影响法律的社会因素,对研究者而言则要求过高了。[注] 同前引[16],第49页。
那么比较法的法教义学范式又是如何看待立法和学术理论这两项比较法的研究对象的呢?以19世纪的比较法研究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行考察。伴随着国际化程度的逐渐提高和国家间交流的渐为密切在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地,彼时的比较法研究都被提到了一个较为显赫的地位。以洋务运动以降的中华帝国为例,西方国家在所谓汉学家、传教士的带领下先后将中国的法律带到了西方,而以沈家本和翁同龢为代表的近代早期法律人则将西方近代化的法律思维带入了落后的中国。在将本国的法律观念带入中国的同时,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并没有分析过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例如威妥玛(Thomas Wade)在强调当时的清廷应当接受新政变法以图强时便一再强调设立海关以及发售国债等政策的重要性,[注] 李书源等:《筹备夷务始末》,中华书局2008年版。 殊不知此时的清政府在地方和通商口岸已根本无力设立能够有效发挥税收职能的机构了。与此同时作为法律继受方的中国也并没有在教义学层面接受“老师们”的教导,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翻译成白话即:理论上接受你的教义体系从而促进我本身既有社会状态的进步,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基于法社会学的比较法研究范式。在这个层面上看,那时的比较法也不过是一种“有一说一”式的法教义学输出罢了。
基于经验性的总结,我们差不多可以得出法教义学研究范式下比较法学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立法比较法一般流于形式上的法条比较而往往会忽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背景——这当然也是教义学的通病。我们知道,一般立法比较法的最终目的便是法律继受国对法律输出国的法律移植,而未经社会学考查的他国法律在教义学的蛊惑下很有可能在继受国引发“水土不服”的现象;第二,学术理论的比较法受法教义学的影响很容易给学习者提供一种先入为主的、甚至是错误的假象,但因为这项比较法活动不涉及法律的创制等问题,所以对作为学习主体的双方国家的学者来说并不存在国家及社会层面的进一步沟通。但学术的交流和发展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也会作用于政治和社会,进而也会与立法比较法的法教义学进路发生重合;第三,难以形成体系的比较研究方法。一般来说,教义层面的比较法研究往往都开始于国家交流的初级阶段。虽然按照熊教授的理论——法教义学是一种对结果的简单速记,但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对象是比较法层面的法教义学而非实在法和部门法领域内的法教义学,在法律输出和进行比较之前,具体的实在法已经在法律输出国(比较的一方)经受了一次法教义层面的浓缩,究其原因则是便于另一方的学习和理解罢了。而对于此种碎片化的法律,学习和比较这些法律的主体(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很难形成完整和健全的知识体系,长此以往——当“不求甚解”成为一种常态、比较的原因和结果已经无关紧要时,试问还有谁会去在意用什么方法来比较呢?
生产过程中,铜阳极板悬挂在电解槽内,其悬垂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其自身的物理特性:一是阳极板耳部重心所在铅垂面与阳极板身重心所在铅垂面之间的偏移程度;二是耳部支撑面的平整度。上述两种因素主要通过调整阳极板整形压力机和确定铣耳定位基准即可满足装槽使用[4-5]。
三、比较法学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
基于以上考虑,比较法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在经历了社会学向法学的转向以及法社会学向比较法研究领域的渗透后已经大致达到了可能性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在理论上,法社会学也必将作为一种研究手段为比较法的深入发展提供理论武器和智识基础。
这三个面向具体组成了法律的实然性状态,即司法实践的具体图景。若细细品读则不难发现,其中第一个面向侧重的是立法过程中的法律实然状态,第二个面向侧重强调司法运行过程中法律的实然状态,最后一个面向——正如其自己总结的那样——是公务执行和日常行政中法律的实然状态。这里的实然性和应然性之间又存在着理论上的时间差距。应然性本身算是一种对法律事件本身的直接回应,而实然性则是实在法在回应社会问题时的法律效果和过程的表述。基于这点分析,法律的实然性应当是紧跟着社会发展而随时变化的,说直白一点——若原有的社会关系有所变动,那么法律的应然性就应当随之而发生改变。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法律的应然性状态并不是社会学家提出的概念,也不是根据社会学质性研究或量性研究所得出数据以及对其分析的结果,法律中的应然状态是法学家根据原有社会关系和所发生的法律事件综合分析和归纳后得出的产物,正如柯克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新谷必定长自熟地”,[注] [美]小詹姆斯·R. 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之诸源头》,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法律的应然性不纯粹源于社会也不直接来自法律,而是此二者的结合。这就牵扯出了另一个问题——法学家所提出的应然性理论与实在法以及法律实践之间的时间差。要记住,正如社会学家没有学科背景便不能提出诸如法律的应然性这样的问题,法学家也不会有这样的智识能力针对社会现象本身以“社会的实然性”相回应,[注] 诚然,这一概念在社会学领域也应当被引入,当普通民众在街边怨天尤人、抱怨世风日下的时候,我们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实然性”理论。 此处的实然性是指法律的实然性,是针对原先的法律状态而提出的。从法律的实然性理论到法律的应然性理论之间就横亘着实现这种学术假说的时间差。简而言之,我们或许将从社会现象的发生到法律实然性的理论假设这段时间分为以下几个节点——“社会实然性(法律实然性)—社会事件爆发—社会应然性状态的回应—法律应然性状态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庞德说法学研究总是落后于法律实践是毫无问题的。[注]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页。 不需赘述也会发现,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学被引入法学的典型观察与总结。这种阐述和解答进路同样也是卢曼通过其所说的学科理论系统中的“观察”与“自我指涉”(selbstreferentielle and autopoietische Systeme)所欲回应的难题。
此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涂尔干(Emile Durkheim)社会分工理论的提出和证成,现如今每个主权国家内部的职业分工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按照卢曼的系统理论(Systemtheorie)进行推导,那整个社会就将是一个高度分化、各系统自涉、多线条并行的庞大体系。为了打破这种孤立,卢曼的方法是降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因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各个部分的总和”,[注] 同前引[1],第48页。 如果从系统外部无法观察其他系统,那么整个社会就将陷入一种片面的、非理性的状态,而这种非正常状态就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有了一定的关联性。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他引入了“系统理性”(Systemrationalität)的概念以填补其系统理论本身与韦伯和哈贝马斯立足于个体研究之间的差距。所以,基于系统理性对其他系统的观察就成为了两个子系统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以此来理解比较法学和法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也是行得通的。具体的问题便是比较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法社会学是否能够彼此关涉。例如,法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对社会学问题进行法律角度的解答并为相应的实在法修正和理论上的填补漏洞作出贡献——而比较法是否也存在这样的特性既二者能否顺利建立联系的关键。通过对单纯法教义学指导比较法研究的分析和批判来看,比较法和法社会学建立联系并不存在理论上的难度。
然而,面对日益功利的社会发展趋势和越发浮躁的法学学术界,现在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并不是比较法研究和法社会学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这样的结合有否现实紧迫性。如果说可能性问题解决的是比较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理论问题,那么对现实性的回应所欲解决的便是比较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社会实践问题,其本身便具有社会学的智识基础。诚如笔者方才所提出的“社会实然性(法律实然性)—社会事件爆发—社会应然性状态的回应—法律应然性状态的回应”几个时间节点,如果硬要把现实性问题塞在这几个时间点以内,则较为恰当的时间点便是介于“社会应然性”和“法律应然性”之间。基于这点认识,我们就不难分析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现实性问题了。
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2016年的“于欢案”和2018年8月末发生的“昆山反杀案”在社会学的层面看并不是罕见案例,当然更不是首例。我们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这两起案件的处理意见或许是刑法实务层面正当防卫司法实践的进步,但通过横向地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类似案件的对比却不难发现,我国的司法处理意见相较于美国和法国而言根本没有系统性和规律性可言,套用上节笔者所归纳出的观点进行理解:如果运用比较法的分析方法来看待这两起事件,我国法学界和社会学界还处在较为初级的状态,即还停留在对案件所适用的法条以及教义学理论的讨论上。包括后续的国别法对比也都是停留在实在法比较以及实务层面的区别上。[注] 具体内容可以参看孔帆:《昆山案后续:法国专家眼中的“最后两刀”;兼谈刘强东案及“华人自卫”,载欧洲时报》2018年9月11日第X版。 然而,并不能据此就得出我国的比较法研究还停留在基础的教义学层面,我们只能回到庞德的语境中理解目前比较法研究所处的尴尬境地,即法律实践层面的比较法和法学理论中的比较法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种脱节在社会事件发生时尤其明显——当下的中国,在茨威格特语境中的“学术理论比较法”所发生的场合往往强调法社会学的引入对理解其他国家法律规范甚至法律体系的重要作用,简言之,比较法的理论层面发展较为完备,而与之对应的实在法领域和法律的具体运用层面则总是停留在法条和教义层面,即便是“参考”其他国家的法律条文通常也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也难怪法国刑法学中的正当防卫理论运用在“于海明案件”时招致了舆论的一片谩骂。
为避免与教义法学理论指导下比较法研究的纯粹模型相混淆,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社科法学本身便是教义法学的前提和条件,因此法社会学指导下的比较法研究自然而然的便是比较法教义层面理论的前提,正如韦伯在完成《经济与社会》之前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对印度和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样,基于这点考虑比较法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与纯粹的社会学就产生了交集。但这里仍然要指出,比较法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前提应当与纯粹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相区别,这本身也是对社会分工理论的回应和证成。
最后,为了与前文提及的纯粹意义上的法教义学指导下的比较法研究相对照,我们似乎也应当为比较法学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做出相应的特点归纳。第一,在法社会学指导下所进行的比较法研究其对象应当是法律背后的社会现象以及通过现象的归纳和分析而得出的法律规则,其分析逻辑一定是先因后果而非法教义学一样“本末倒置”;第二,区别于社会学研究,法社会学指导下的比较法研究应当是以与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制相关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性研究都不应当笼统而模糊,其研究面不应当铺得过大;第三,无论是法社会学还是法教义学都是比较法研究的理论工具,以比较法学研究为中心的社会分析应当将这两个学术概念视作比较法研究的一体两面,过分强调一方只会导致无谓的学术分歧,甚至盲目扩大原本就已经十分繁复的法学学科体系。
硬件实践初步探索 硬件实践的目的仍然是发现理论课程中较少涉及而在实际工程中会出现的问题,使学生拓展知识面,提高对工程实践的认识。同时,硬件实践对学生的要求更高,因此在本部分的初步实践探索中,选拔对课程内容有较高兴趣、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对硬件实践意愿较高的学生参与,由教师全程指导。学生通过参加硬件实践,进一步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对硬件电路的认识。
法学研究领域内的学术概念本就已经十分繁杂,本文并无意创设新的法学概念和术语,无论是比较法学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还是纯粹法教义学话语体系下的比较法学都是原有学术概念的拼凑和嫁接而已。因此,关于这两组以比较法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学术模型并不是一直就存在于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这里笔者为了分析方便就直接“顺手牵羊”了。至于这样的划分有没有理论合理性和自洽性,更进一步有没有继续讨论下去的可能则要看比较法学和法社会学两个传统学术领域自身的研究有没有产生交集的可能性了。
小区内晚饭后散步的人比较多。面积不大的草坪上有两位女人和两条狗。两位女人很显然是两条狗的主人。两条狗的体形相去甚远,其中一条体格健壮,另一条身材娇小。两位女人咬着耳朵,不知聊的什么话题,不时爆发出笑声,很开心的样子。两条狗相互间似乎颇有好感,不停地向对方示爱,或许正处于发情期。吕凌子漫无目的地在小区内转了一圈,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了草坪边。草坪上的两条狗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做了,体格健壮的那条正躺在草丛里用舌头舔自己后腿跟那个玩意,那个玩意看起来非常丑陋。
作者简介 :毛皓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曾提交“第六届青年比较法论坛”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