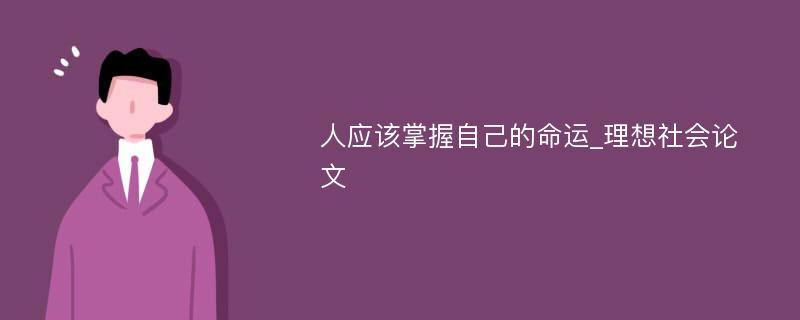
人应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应论文,主人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从一个侧面看,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他能改天换地,似乎无所不能。小时候,我看《封神榜》,觉得那些神与仙实在神通广大,不可思议。可是,现代高科技手段已经远远超过了《封神榜》中的神与仙的法力;而且还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从另一个侧面看,我们又可以说,人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他专门自讨苦吃,处处给自己设置困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今天面临的种种困难,全是他自己造成的。例如生态环境问题,便是由此而产生的典型问题。早在十多年前,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便发出了呼吁:人类的生产,如果照目前那样继续下去,那么,人在地球上可以生存的年月,将是屈指可数了。更为愚蠢的是:人还捏造了根本不存在的神,希望这种莫须有的最高存在来为人类解决自己似乎无力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源于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这是内在于人的存在方式中的生存悖论。否定了这种悖论,也就否定了人的存在。
人并不是某种永恒存在物,也不是神特殊创造的宠儿。人是从自然动物发展来的。但是仅有自然的发展,还不会有人;人是人的产物,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这就是说,人是在改造自然、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才超出自然界,上升成为人的。所以,人的存在方式不同于自然动物的存在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他的生活资料不是由自然界直接提供的,而是由他自己生产的。生产当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既定的自然资源的扬弃和超越。这样便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所特有的内在规定和内在矛盾:一方面人的存在和发展仍有赖于自然界,即要尊重给定的现实;另一方面,人要成为人,又必须克服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扬弃和超越给定的现实。从这个侧面看,我们也可以简单化点说,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动物;不断地超越给定的现实,是他永恒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在人的活动中,总是把不现实的东西看得比现实更高、更重要,如理想。理想之所以叫理想,就在于它还不是现实;理想一旦实现了,便不理想了,又成了新的超越对象了。而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超越的一面在人们的生活中便显得越来越重要,其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本来超越给定的现实,并不是要超越到虚无飘渺中去,而是为了要达到更高的新的现实。当然这个新的现实,并不是最后的终点,仍不过是新的超越的起点。这就是现实和理想、给定和超越的辩证关系。
但是,一旦把矛盾的双方对立了起来,便有可能在此岸世界以外,虚构出一个彼岸世界来,在有限的生命以外,虚构出某种无限的生命来。所以,费尔巴哈说,只有人才会有宗教,只有人才会在没有对象的地方发现对象。
本来人的存在方式的超越性的一面,是件好事,说明人比自然动物要高明,外在的条件限制不住他,他的历史要他自己来创造。因此,人是一种自主性的自由的动物。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误入歧途,超越到虚无飘渺中去。结果便成了对自主性和自由的否定。
二
当然,人实现自主的和自由,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从有人的那一天,人就充分享有了自主和自由。一般说来,这是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它是随着两个方面的条件的改善而不断前进的:即认识的条件和社会的条件。
人所以能通过改造自然而支配自然,就是因为人认识和把握了自然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近代以来,先哲们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点:只有在认识上把握了客观规律,行动上才能获得自由。
但是,认识活动中有一些矛盾,常常会使人们误入歧途,一些有神论者也常常以此来证明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这些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二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先说说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主张迷信和有神观念的人,认为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不管人的认识怎么进步,总有一大片未被认识的神秘的领域存在着。似乎这是一个永远不可克服的矛盾。
其实,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把有限和无限对立的基础上的。所以当然是错误的。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思维活动的本性来看,二是从思维活动的历史发展来看。
先说思维活动的本性。
什么叫思维?黑格尔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回答:“思维的简称叫我”。就是说,思维活动,至少从形式上去看,是一种以自己为对象的活动。谁都可以从幼儿的思维活动中发现,当他还说不出“我”和“我的”以前,便尚没有健全的逻辑思维;只有当他能说“我”和“我的”时,才会有建立在判断、推理基础上的正常的思维活动。也就是说,思维活动的核心是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便谈不上思维活动。这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早已认识到了的。例如,狄德罗便说过,什么叫思想,就是自我意识加记忆。不过只有到了康德、黑格尔才对自我意识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所谓“自我意识”,即以自己(“自我”)为对象的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当然是有中介的,是以感官提供的感觉经验为中介。也就是表现为:“我意识(知道)到我感觉到了……。”这是一个判断,即一个认识。在这个认识中,我(认识主体)的直接认识对象是“我”(认识客体);不过,不是抽象的“我”,而是“感觉到了什么什么”的我。在这里,“感觉到了什么什么”是通过作为客体的“我”而提供给主体的我的,是间接的对象。到此为止,清楚地反映出,思维活动的本性是辩证的。即就其表现形式说,它是无限的普遍的(因为它的直接对象是它自己,没有他物限制它);但就其内容说,它又是有限的特殊的(因为作为直接对象的“我”是以经验材料为中介的,即为经验材料所规定)。例如我们问张三是什么时,得到的回答是:张三是人。其实问的是一个特殊的个体,答的却是一个普遍概念。然而,大脑健全的人都认为这个答复是对的。这不就说明,在思维活动中是把个别当作一般来把握的。当然不能反过来,说“人是张三”。这种既统一又不统一的关系不就是辩证关系吗?所以,简单地把有限与无限对立起来,肯定是错的。实际上,我们在把握到有限时,即在某种意义上把握到了无限。
至于说,从认识的发展来看,更说明了有限和无限是统一的。断定人只能认识有限,不能认识无限是没有根据的。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与‘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们现在说,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出界限,那末,我们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但这终究是事实。“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我以为,恩格斯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很清楚了。我们在这里要补充的是:思维中的这种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不是相对于某种给定的终极存在而言的。即不是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越来越充分地认识这个给定的终极存在一部分或大部分,而是指人的认识在发展,外部世界也在发展,所以认识和它所反映的存在永远不会有完全重合的一天。如果重合了,世界就没有发展,即世界末日了。换言之,这种不重合,不仅说明不了认识的无能,恰恰表明了认识的生命力之所在。
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说,主观认识在发展,客观对象也在发展时,不仅是指自在的过程,而是指自在与自为辩证统一的过程。人为什么要认识外部世界,就是为了要改造外部世界。换言之,人们在实践中所要追求的存在,并不是要退到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去,而是要实现理想的存在。而这种理想的存在,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就此而言,认识的相对性与有限性,恰恰是它精益求精的表现,而不是局限性的表现。
往下我们再来分析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里,客观最终一定是不透明的神秘的王国。
所以,要克服这种神秘的误解,便得谈谈认识活动中的主观与客观的辩证法。例如,当我们说出:“主观的认识是对独立于它的客观对象的反映”这一判断时,人们完全可以问:这一认识(一个判断,当然是一种认识)是认识的结果还是认识的出发点?如果这是认识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还没有知道有独立的外物存在之前,便肯定了自己的认识是其反映。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不通的。反之,如果说,上述认识是认识的前提,这就等于说,在认识活动开始之前,人们已有认识了。这同样是不通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些所谓不通,只不过反映出人的认识在本质上的另一个辩证矛盾。也就是说,上述判断,既是人的认识的结果,同时,又是认识的前提。
因为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主观与客观是外在地完全对立的,所以才会提出如上的二律背反。在谈到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时,我们已经指出,在感觉经验中,其对象的确外在于感官,因此,感性直观中,主观与客观似乎完全是外在地对立的。其实,事实并不完全是如此。人们常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等等,这就表明了人的感官对象也不是简单地强加于人的,即不能仅仅从给予的意义上来了解何谓客观。至于说,由经验上升到思维以后,问题更清楚了。上面说过了,思维的直接对象是它自身,不过不是抽象的自身,而是由特定的感觉材料规定了的自身(思维)。因此,这种思维既不是康德式的没有内容的纯思维(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这在现实中没有),也不是贝克莱式的“存在就是被感觉”的纯主观的思维。也就是说,思维在形式上是自己决定自己,但是它在内容上,却为感官中给予的感觉材料所规定。或者说,思想在本质上是存在的反映,即是客观的思想。
所以,客观之所以叫客观,不在于它简单地排斥主观,而在于扬弃了主观的外在独立性,成了客观的一个内在环节。反之,主观之所以叫主观,也不在于它简单地排斥客观,而是扬弃了客观的外在独立性,成了主观的一个内在环节。这就清楚表明了,主观与客观是不同的、对立的,但是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的,即对立统一的。
这种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不是仅仅表现在认识中,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实践活动中。实践的发展过程,即是主客观的无止境的相互转化的过程。
三
人能不能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固然不可缺少认识上的条件,如要不断深入认识自然规律,甚至也包括要认识社会规律。但这个问题,主要不是个认识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如果在1949年前后,把这个问题交给理论界去讨论,我想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虽然在1949年前,曾有过一些人幻想过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但绝大多数人还是认识到了此路不通。只要三座大山还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自由、不可能有做人的自主权。科学、实业等等可能能起点救急不救穷、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只要社会政治制度不改变,那么最后连科学与实业自身也发展不起来,更谈不上救什么什么了。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难道雄辩的逻辑还能改变既往的历史事实吗?欧洲思想史上曾经有一种文化主义的观点,以为神的观念是由于认识上的迷误造成的,但这种观点在它的发源地也没有多少人信了。
历史上常常说,神是绝望中的希望。即人们在此岸世界中绝望了,因此便幻想在彼岸世界中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够来拯救自己。这个观点虽然不深刻,却不能不承认是现实的原因之一。这在旧中国的农村表现得十分突出。广大的农民,在平时,很难说他们是有神论者,即他们并不像西方的教徒那样,坚定地相信什么什么神。但是,遇到无力抗拒的天灾人祸时,又匆匆忙忙去求神拜佛。新中国成立前,一般说来,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有了些变化。人们普遍地相信党、相信马克思主义,对超自然的信仰越来越淡薄了。这在三年困难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60年代初,我国遭到了特大的困难。当时,我在京郊门头沟山区劳动。同志们之间,有时会问起:今天你吃到了几粒粮食。因为全天吃的都是杏树叶。这种树叶虽然泡了24小时,仍很苦。名曰与粮食放一起煮了吃,但粮食少得可怜,不知谁有幸吃到。所以一天下来,往往一粒粮食也没有吃到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即使困难到如此,我也没有发现有谁在盼望神的救助。相反地,人们有一股傲气在相互鼓舞着,即觉得自己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假朋友制造的。因此,人们觉得一定要咬紧牙关、挺起腰杆,克服这些困难,以便证明没有这些所谓的“朋友”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会更好些。
令人奇怪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普遍地有了改善和提高,为什么封建迷信反而倒多起来了,甚至盛行起来了呢?有人说,不愁温饱,便想健康长寿,甚至长生不死了。这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说法,比较切合老年人的心态,对年轻人未必切合。例如,你到公园里去看晨练的,甚至到香山去看爬山的,年老的比年轻的多得多。年轻人精力旺盛,朝气勃勃,生老病死似乎离他们还很遥远。摆在他们日程的是如何去奋斗、享受今天的生活。可是卷到迷信行列中来的青年中年并不少。如果你到普陀山去看大队大队背着行李、挑着贡品来此朝山进香的人中,老年人并不是多数。所以,我们仍然要问:这是为什么?
肤浅一点说,这是寻找心理平衡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心态的表现。本来1949年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了天上的救世主是不可靠的,地上的灾难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但是,很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树立一个地上的救世主。然而十年动乱,又使人醒悟到,地上的救世主也不可靠。这就导致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全社会所谓“信仰危机”。似乎谁都不可信,只有自己是可信的。而且这种思想又为当时“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商品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等等措施所强化。问题是:自己真的是最可靠的吗?在打破了大锅饭、打破了平均主义,允许能者为先、多劳多得、一切通过竞争来实现时,个人最可靠的假象很快便暴露出来。个人脱离了社会,什么也干不成。但是,社会提供给每一个人的机会与条件是不是均等的呢?不可能。最合理的社会(假定有的话)也不可能做到这点。而我们的社会,又是法制正在不断完善中的社会。在实际生活中,人治还远远高于法治。一级政府对一件事能不能办、应不应办而拿不准时,不是请教于法制,而是向上级请示。结果,在我们周围便经常发生不合理的事却是合法的,甚至把不合法的事变成了合法的,合法的倒成了不合法的。能者让,庸者上;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等都发生了。面对这些人们的心理能平衡吗?到哪里去寻找平衡呢?只能到与名利场无关的彼岸世界中去寻找平衡了。
这种寻找,本来是莫须有的东西,为什么仍然有人相信呢?因为就它要超越形而下的功利世界而言,也符合生命的永恒价值的取向。古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不就是要人们不要把现实的功利看得太重、超功利的价值更为重要吗?所以,即使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对现实的不平等感到无能为力时,也会觉得“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仍不失为一种取得心理平衡之道。
说到这里为止,所谓社会条件是些什么?简单点说,就是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的问题。如果人们真正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是现实生活的主人,他就没有时间去照顾彼岸世界的事了。
当然民主是有历史性和相对性的,不可能想象有一天民主会尽善尽美,再也无法前进了。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能以抽象的绝对主义的尺度来对待现实的民主制度。合理的要求是看看现行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一致不一致,对经济建设能起促进作用,还是相反呢?当然这也不是说,只要民主制度健全了,封建迷信、邪教异端就会绝迹了。不会。数学计算中有百分之百,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现实生活之所以叫现实生活,它是极端复杂的,不可能用数学或逻辑的公式来穷尽它。否则,人就等于神了。正因为生活不是由赤裸裸的必然性决定的,人才有能动的余地,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四
在历史上,认识条件和社会条件一直是分开的,似乎可以谁也不管谁,各行其是。现在不行了。由于现代通讯手段和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想要像封建时代那样“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是根本不可能了。例如,以往只要大权独揽,就可以逃避人民群众的监督了,现在呢,即使独揽了也逃脱不了人民的照妖镜。反之,我们更应该说,只有庶民共议,才能天下有道。因为,今天不管各国人民面临的任务,其内容上有多大不同,但在性质上有一个共同之点,即这些任务都十分复杂,即使是一件看来是非常具体的事,要取得理想的结果,仍然是一件十分复杂的系统工作。所以十多年前大家还比较生疏的“决策要民主化、科学化”,现在几乎成了社会上的口头禅了。
从这个侧面看,认识条件和社会条件可以简化合并为一句话:即要帮助人们树立高尚而科学的理想;并建立起引导人们为此而奋斗的激励机制。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为人类准备好了真正成为自己主人的必要条件。但是,要使这些条件发挥积极的作用,达到上述目标,仍有待于人们的努力啊!
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对自身命运主宰权的历史,不断地抛弃天上的和地上的救世主的历史。人类不断地在寻找天堂,其实,天堂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不过这个天堂不是任何神或人恩赐的,而是靠自己流血流汗去争取的。如果人们真是全力以赴地流血流汗在争取了,那么,他已经是在进入天堂的大道上了。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可以到此为止了,否则立即就会由天堂跌入地狱。奋斗吧!这才是天堂真正有效的通行证。
标签:理想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