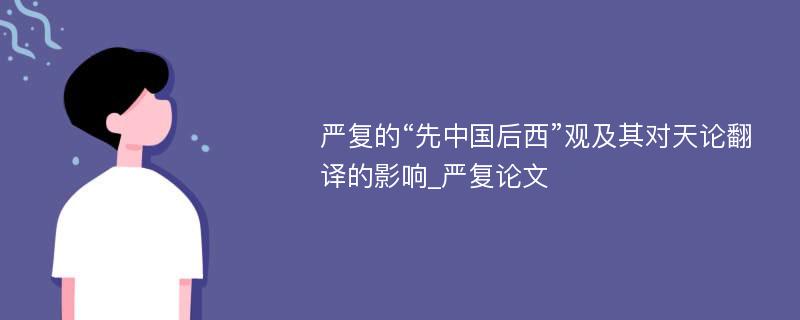
严复的“中先西后”观及其对翻译《天演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演论论文,其对论文,严复论文,中先西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3-0038-13
“严译八大名著”中,《天演论》的内容和思想与原作相差最大,影响却最为深远,它吸引了无数学者深入研究。自1898年《天演论》问世以来一百多年间,对《天演论》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近年来,在史学界、思想界和翻译界的共同努力下,《天演论》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严复《天演论》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比如,王佐良通过对《天演论》翻译的研究发现严复的翻译动机影响了其翻译理论[1:22-27];王克非分析了严复对进化论思想的摄取及其对《天演论》翻译的影响[2:33-62];俞政从严复翻译和修改《天演论》出发,认为其意译方法所造就的译文与穿插的自撰文字一起造成了《天演论》著译难辨的效果,并认为严复对译文的修改是从作文角度出发的[3:21-80];黄克武通过考证严复与吕增祥、吴汝纶之间交往的相关史料,分析了吕、吴二人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影响[4:22-31]。这些研究跳出文本层面,从严复的翻译动机、影响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社会因素展开探讨,使我们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行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更深入的认识。但笔者发现,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尤其是严复当时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以及这种立场对他翻译《天演论》所产生的影响等,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天演论》手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1896)与通行本“自序”(1898)与“译例言”(1898)等文本的细读,总结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过程中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并探讨这种立场对严复翻译和修改《天演论》所产生的影响。
一、“中先西后”——严复的中西文化观
一般认为,严复在对待中西文化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是“中西相通”的态度,这种观点可追溯到蒋贞金在《严几道诗文钞》序中对严复作品的评价。蒋贞金(1922)认为严复作品所传达的乃“中外相通之理”[5:1558-1559]。后来的学者如李承贵[6]、王民[7]、王天根[8]等基本上也都沿用了这一说法。但笔者发现,严复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不能只是概括为“中西相通”,而应再往前一步,概括为“中先西后”,即在严复看来,中学先于西学,西学的引入需以中学为参照,这种内涵在西学的印证中可以寻找到更适合当时中国发展的模式。
严复的这种“中先西后”观,无论是在当时未曾出版的《天演论》手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1896)中,还是在稍后正式出版了的《天演论》通行本“自序”(1898)中都有充分体现。比如,严复在“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中指出:
后二百年而斯宾塞氏出,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欧美二洲学术政教群然趋之,法制大变。其为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合质,辟以出力。”而《易》则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西洋自奈端治力学,首明屈伸相报之理。五十年来格致家乃断然知宇内全力之不增减、不生灭,特转移为用而已。而《易》又曰:“自强不息之谓乾。”夫物未有增减生灭而可曰自、可曰不息者也。斯宾塞得物变循环之理,自诧独知,而谓唯丁德尔为能与其义,而中土则自有《易》以来,消息盈虚之言,愚智所口熟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格物五十年,乃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有高下之差而后流也。今者太阳本热常耗,而以彗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罡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斯能耗热耗力矣。故大宇积热力毋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而《易》曰:乾坤其易之缊耶?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夫息矣。诸如此者,不可偻指。呜呼!古人之作为是说者,岂偶然哉!夫以不肖浅学,而其所窥及者尚如此矣,则因彼悟此之事将无穷也。虽然,由此而必谓西学所明皆吾中国所前有,固无所事于西学焉,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9∶1411]。
这里,严复为了引导读者关注斯宾塞的学说,突出斯氏“天演”学说的重要性,开篇便说“欧美二洲学术政教群然趋之,法制大变”,但进而指出,我国《易经》早已有类似的论述。接着又以力学和热力学为例,将斯氏学说与《易经》中的观点进行比附。就力学而言,他认为,西方自“奈端”(牛顿)以来方知“屈伸相报”之理,“五十年来”方知“宇内全力之不增减、不生灭”,而这些思想早在《易经》中就有“自强不息”予以表述:“物未有增减生灭”其实就是“自强不息”中的“自”或“不息”。而且进一步指出,斯氏的“物变循环之理”惟“丁德尔”才能理解,而在中国,“消息盈虚之言”则无论“愚智”都耳熟能详。在热力学方面,西方由“彗星来往度之递差”推知“地外”的“最轻之罡气”能“耗热耗力”,进而推断“大宇积热力毋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易经》则早已表达过几乎同样的思想:“乾坤其易之缊耶?”在此,严复认为中学先于西学的思想溢于言表。
严复的“中先西后”观在通行本自序中表露得更直接:
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10∶1320]。
该自序与手稿本自序虽有较大不同,但流露出的“中先西后”观却未发生根本变化。这里,严复更明确地指出,西方的“全力不增减之说”,中国早有“自强不息为之先”;西方的“凡动必复之说”,中国早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中国“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的思想更可与西方“热力平均,天地乃毁”的观点“相发明”。可见,在严复看来,中西学理不仅相通相融,而且还是中学先于西学。
既然中学先于西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沾沾自喜,抱残守缺,对西学采取排斥态度呢?当然不能。严复对于自己所阐发的“中先西后”思想可能会引起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手稿本和通行本自序中都明确表示反对这种态度,认为“无所事于西学”的态度是“大谬不然之说”(手稿本自序),“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或“其学皆得于东来”的看法乃“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通行本自序)。
其实,严复对待西学的这种开放心理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他作于1895年的《救亡决论》中就对那些自以为是、“扬己抑人”的保守之士表达了不满之情:
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羌无新奇[11∶52]。
正因为严复在对待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持有“中先西后”的态度,而且又不像当时其他士大夫那样对西学采取拒斥态度,因此他希望通过译介西学让国人了解西学,通过了解西学更深入地把握中学的精妙所在,以达到对中学“归求反观”的目的,即所谓“转籍西学以为还读我书之用”(手稿本自序),或“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通行本自序)。严复这种“归求反观”的译介西学的目的在《救亡决论》中也有明确表述:“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11:49]
综上所述,严复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不只是简单的“中西相通”立场,而是更趋“保守”的“中先西后”立场。这种中学先于西学的立场直接导致他将译介西学的目的定位为“归求反观”,试图通过了解西学“还读我书之用”,以最终达到“识古”的目的。严复正是在“中先西后”的前见的影响下,为了达到“归求反观”的目的而开始译介西学的。他在翻译和修改《天演论》时频繁采用的格义和会通这两种翻译手段正是这种“中先西后”观的具体体现。
二、格义与会通——“中先西后”观影响下的翻译手段
“中先西后”观对严复翻译《天演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他所采取的翻译手段上。从宏观上看,严复无论是在翻译还是修改《天演论》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采取了两种明显会不忠实于原作的特殊翻译手段:格义和会通。无论是从《天演论》手稿本和经过精心修改而成的《天演论》通行本,都可以发现大量通过格义和会通的手法而生成的译文。
1.格义
格义是我国历史上翻译佛经时采用的一种手段,在我国佛经翻译初期经常使用。传统上,“格义”是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阐释方法。由于语言和传统文化思想方面的差异和隔阂,在佛教传入之初,讲解者必须把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于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将本土原有的儒道学说与印度佛教作比较,使接受者借助于自己的知识经验,尽可能领悟佛教教义。[12∶52]
格义与比附密切相关,比附是格义的实质,格义“以比附为特征”[13∶23],所以格义内含比附。就翻译而言,格义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用现存的本土概念来理解、解释并最终比附外来概念的一种方法。对照《天演论》的译文和原文,不难发现,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频繁使用格义的手法,即为了使译文顺应中国本土文化的要求,满足当时中国主流知识阶层的期待,他经常用中国本土文化中已有的概念来比附原作中的概念,使之看上去好像是中国本土原本就有的观念或思想。例如:
原文:Thus 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which we began by considering,is far from possessing the attribute of permanence.Rather its very essence is impermanence.It may have lasted twenty or thirty thousand years,it may last for twenty or thirty thousand years more,without obvious change; but,as surely as it has followed upon a very different state,so it will be followed by an equally different condition.That which endures is not one or another association of living forms,but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 cosmos is the product,and of which these are among the transitory expressions.And in the living world,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 i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the competition of each with all,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selection,that is to say,the survival of those forms which,on the whole,are best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at any period obtain; and which are,therefore,in that respect,and only in that respect,the fittest[14∶4].
《天演论》手稿本:
由此而观之,则知不变一言,决非天道,其悠久成物之理,乃在变动不居之中。夫当前之所见,经二十年卅年而革焉可也,历二万年三万年而后革焉亦蔑不可。但据前事以推将来,则知此境既由变而来,此境亦将恃变以往。顾唯是常变矣,而有一不变者行乎其中。六合所呈,是不变者与时偕行之功效;万化陈迹,是不变者循业发见之前尘也。此之不变者谓何?非如往者谈玄之家,虚标其名:曰道,曰常,曰性而已。今之所谓不变有可以实指其用者焉。盖其一曰物竞,其二曰天择。万物莫不然,而于动植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9∶1414]。
《天演论》通行本:
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10∶1324]。
这里,无论是手稿本中的“天道”、“六合”、“万化”还是通行本中的“天运”、“天演”和“体”“用”,其实都是严复通过格义的方法比附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
原文中的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植物界的自然状态),严复在手稿本和通行本中分别比附为“天道”和“天运”。我们知道,“天道”和“天运”原本均为中国本土文化中已有的概念①。“天道”一说最早出自《周易·系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15∶321]《庄子》对“天道”也有阐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16∶324]。可见,“天道”囊括一切在内,广大无边,并操控万物的兴衰。这里,严复经过格义,将“植物界的自然状态”提升至中国本土文化中“天道(运)”的高度,与他在《天演论》“导言一”中提出的“天道变化,不主故常”[10∶1324]思想相呼应,从而以“天道”变化的恒常性挑战了晚清守旧派所坚守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这一比附不仅直接影响目的语读者对“天道”不变的解读,而且以“天道”的权威为“天演”的适用范围和稳定性做出了合理的铺垫。
同样,严复在通行本中首创的“天演”也是格义和比附的产物。the process在原文意为“产生宇宙本身的过程”,严复在手稿本中译为“不变者”,并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六合”和“万化”概念来说明“不变”在自然界的外在表现,认为“物竞”和“天择”对于“万物莫不然,而于动植之类为尤著”。而通行本将“不变者”改译为“天演”,并使“天演”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动植之类”扩大到“有生之类”,认为这对“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在此基础上,他又在通行本《导言二·广义》中对“天演”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解释:
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10:1326]。
对照原文可以发现,赫胥黎的原意其实只是“从生物界到地球的整个结构,从太阳系到宇宙都处于进化的预定进程”,“进化”的范围远不及严复“天演”那么宽广。由此可见,严复通过比附中国本土文化中“天”的内涵,使“天演”的外延大大超越了原作中的“进化”,从而将原作中“进化”的适用范围推广到了人类心理活动(“神思智识”)的变化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政俗文章”)的沿革,因为在严复看来,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当时中国读者对自身以及所处社会状态的关注。
在“天演”中引入“体”与“用”的概念同样也是格义的结果。原文中的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本意为“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严复手稿本译为“今之所谓不变有可以实指其用者焉”,通行本则改译为“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强调“天演”的功用,并进一步将“天演”的“体”和“用”结合起来,使进化的观念和功用正式成为完整的“一物”②。我们知道,体用二字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15∶322],“显诸仁,藏诸用”[15∶323],同样蕴含着作为中国本土哲学范畴的基本涵义。因此,这一比附使“体用”与“天演”紧密结合,不仅使二者在具体含义上密不可分,而且在哲学范畴上也具有合理性。
由此可见,严复在“中先西后”观的影响下,在译文中采用中国本土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影响深远(如“天”)和认可范围较广(如“体用”)的语词,在结合原作中某些概念的原义或部分原义的基础上通过格义和比附中学来传达原作的内容及思想。冯友兰论及这一现象时曾谈到,“严复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以西学为主,从西学看中学,对于中学做格义。”[14∶504]冯先生一方面看到了在严复的知识结构中西学成分占多数这一事实,但另一方面,从以上对严复翻译实践的分析可以看出,冯先生的看法有失偏颇,即他认为严复是站在西学的立场看中学的,而未考虑严复对待中学与西学的立场是“中先西后”。诚然,在严复的知识结构中,西学占了较大比例,但他的中学造诣同样很高,得到了吴汝纶[19∶1561]、康有为[15]、梁启超[21∶98]等当时社会名流的高度认可。相反,假如严复只是站在西学的立场看中学,那么他极有可能发现中学一无是处,因而未必需要甚至无法通过格义向读者传递西学的精妙之处。正因为严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文化)地位较高,内涵极其丰富,而后人却未能充分发扬光大(“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见通行本自序),所以他在“中先西后”观的影响下,力图在译作中通过格义来体现中学的内涵与优势。他在译作中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成分比附原作,主要是为了使这些成分“顺应”中国本土文化的要求,因为既然原作中的某些观念或思想中国早已有之,当然可用中国本土的语词予以“替换”。由于用来“替换”西学的中国本土概念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已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所以依附在中国本土语词之上的西学概念在新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语境中也就获得了新的含义。但这种概念与原概念在含义上往往貌合神离:二者表面上对等,实际上往往相差极大。所以说,严复在翻译中使用的这种格义手法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中学和西学的准确把握与取舍,也是对目的语文化及其读者如何接受异质要素的深入思考。
所以,对于严复的格义,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严复站在“中先西后”的立场上通过西学比附中学。虽然不能否认他的格义具有强调中西学之间的共性而忽视差异的倾向,但他却通过格义成功地把介绍过来的西学置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之中,并使其通过读者的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2.会通
会通也是严复经常使用的一种翻译手段。会通是通过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异、同要素的解读,分析其中所隐含的规律,并从该规律的角度彰显目的语文化要素及其特定需求的手段。格义倾向于使目的语读者通过目的语文化自身来理解译作所传达的原作信息,会通则侧重于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所传达的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共通的信息。严复曾对会通作过解释:“此大《易》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22∶93],可以看出,严复的会通手段是以“天下”(这必然包含中西学在内)为视域,寻求其中之“典礼”,而这种“典礼”正是通过“熔中西为一冶”而获得的。这种手段虽然表面上是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与中学相差较大的西学而凸显中西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在深层次上则是为了使译文内容服务于译者所预设的译作的功用。就《天演论》而言,这种功用不仅是严复对中西学之用的甄别,而且也是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参与社会变革的向往。正如吴展良所言,“严复早期的求道之旅体现了传统的儒学性格与思维方式与西方学术思想的互动。”[23∶239]所以,这一“求道之旅”不仅包括严复对中学和西学之间共通之处的探究,而且进一步促使他会通中西以对中学“归以反观”。这种会通手段很明显地体现在《天演论》的翻译和修改过程中。例如:
原文:And the business of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ascertainment,by the same method of observation,experiment,and ratiocination,as is practised in other kinds of scientific work,of the course of conduct which will best conduce to that end[14∶43].
《天演论》手稿本:
古者为学,形气道德之家,分而为二,今则合二为一。所论者虽道德治化,而其所由之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验证明形下者也。始于实测,继而推求,终于试验。凡政治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榷之,由以知其政之窒通,与能得其所祈响否也[9∶1437]。
《天演论》通行本:
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歧而为二,今者合而为一。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凡政教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榷之,由是知其事之窒通,与能得所祈向否也[10∶1358]。
以上手稿本和通行本中“术”的顺序和功用就是严复会通中西研究方法的结果。在原文,赫胥黎所主张的研究顺序是“观察、试验和推理”(observation,experiment,and ratiocination),而严复在手稿本和通行本中均将该顺序颠倒,把“推理”(通行本改译为“会通”)提到了“试验”之前,并将其作为“形上”与“形下”共用之“术”。严复此举,是为了强调古学“逊”于今学的根源,正是在于古学缺少“试验”这一环节:“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这是“古学”研究方法上的弊端,由于严复所言的“古学”是包括“中西古学”的,而“今学”实为“西学”,所以“中西古学”和“今学”都是他会通并得出“典礼”的视域,这正如他在《西学门径功用》(1898)一文中对“今学”胜于“古学”的进一步探究:
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观察演验,二者皆考订之事而异名者。盖即物穷理,有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有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是也。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此之典礼,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悮,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22∶93]。
在“今学”胜于“古学”的基础上,严复将西学研究方法的功用进一步扩大了。原文中赫胥黎仅提到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任务是采用此方法,达到“促进公民天赋能力自由发展的目的”(to the end of facilitating the free expansion of the innate faculties of the citizen),而严复会通中西研究方法,将“术”的功用从手稿本中“凡政治之所施”扩展到通行本中“凡政教之所施”。因为在严复看来,“保民”和“养民”的关键在于“独主持公道,行尚贤之实,则其治自臻”[10∶1357],而“政教”能否达至这一目标必须经过此“术”的验证。在这一点上,中西“会通”所得到的“典礼”与赫胥黎所言的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任务之间存在着共性,所以这种会通中西研究方法所得出的“术”,就能为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们所理解和接受。
严复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译介同样是通过会通手段实现的。例如:
原文:However regretfully,I have been obliged to admit that this rigorously scientific method of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evolution to human society hardly comes within the region of practical politics; not for want of will on the part of a great many people; but because,for one reason,there is no hope that mere human beings will ever possess enough intelligence to select the fittest[14∶34].
《天演论》手稿本:
夫主治者,或独据全权之君主;或数贤监国,若周共和;或合通国之权,如泰西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与弊[9:1434]。
《天演论》通行本:
夫所谓主治者,或独具全权之君主;或数贤监国,如古之共和;或合通国民权,如今日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弊。案:今泰西如英、德各邦,多三合用之,以兼收其益,此国主而外所以有爵民二议院也[10∶1353]。
以上手稿本和通行本中的“制”以及通行本中更为详细的“今泰西如英、德各邦,多三合用之,以兼收其益”,都是严复会通中西政体制度所得出的结论。
赫胥黎的本意是“进化原理应用到了人类社会,但这种严格的科学方法却很难应用于实际的政治领域”。这表明,赫胥黎是明确反对将生物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领域的,因为在他看来,“人类自身没有足够的智慧来选择最合适的生存方式”。但严复在翻译时却完全撇开原文,通过会通手段仅对其中的practical politics一词“取便发挥”,表述了与赫胥黎原意完全相反的观点。他首先指出,既然人为治理中存在趋于荣誉和私利的生存竞争(“人治物竞者,趋于荣利,求上人也”),那么统治者就应充分发挥人治的优势(“操砥砺之权,以砻琢天下”),从而将进化论顺理成章地引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政体制度。接着,他通过会通手段,指出所谓“主治”,无外乎三种模式,或“独具全权”,或“数贤监国”,或“合通国民权”,这是中西政体制度的较为相似之处。然后他在手稿本和通行本中提出对这三种政体制度的看法,认为三者“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弊”。后来在通行本中进一步通过案语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高度赞赏了“英、德之邦”的君主立宪制,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政体制度会通古今三种政体制度于一体,通过“三合用之”而“兼收其益”。由此可以推断,严复的言外之意是“英、德之邦”这种通过会通古今三种政体制度而得来的君主立宪制,才是当今中国应该效仿且又适合中国当时国情的政体制度。他对英式君主立宪制的溢美之词,同样见于他后来撰写的《政治讲义》(1906)中:
故柏来斯敦Blackstone谓英制一王二议院,鼎足治国,收三制之长,而无其敝云云[24∶1258]。
严复的这种会通手段正好印证了他在与吴汝伦书信中借郑侨之言“吾以救世也”所表达的翻译目的:他对西学的译介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认为从事西学可以考察中学的得失,即“公等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11∶49],因此希望当时的士大夫沿着他所指出的从“实测”到“会通”再到“试验”的途径,来变革当时中国政体制度。具体地说,就是采用能兼收“独具全权”、“数贤监国”和“合通国民权”三者之“益”的英德式君主立宪制。而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需要通过“试验”来进一步验证。这里严复特别强调“试验”的重要性,因为“试验愈周,理愈靠实”。所以说,严复通过会通手段所得到的这种启蒙思想,不仅指出了当时中国的问题所在,而且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另一方面,诚如黄克武所言,“严复以学术工作来从事政治参与,企图能‘主文谲谏’、有稗时政”[4∶2],因为严复预设的目的语读者是晚清士大夫,而他们又是能左右当时政局的阶层,所以通过启发士大夫变革现有的中学研究方法和政体制度,并接受这种会通中西研究方法的“术”,以及会通古今中外“兼收其益”的君主立宪制度,他可以通过学术间接达到改良“政教”之目的,即“始于学术,终于国家。”[11∶45]
由此可见,严复会通中学和西学研究方法以及古今中外的政体制度,都是为了达到政治变革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这正是他会通中西“归求反观”中学所得出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先西后”观对严复翻译《天演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格义和会通两种宏观的翻译手段,鲜明地体现在《天演论》的手稿本和通行本中。
三、结语
一直以来,学界认为严复对待中西文化所采取的是“中西相通”的立场,而未能进一步认识到他所采取的其实是一种“中先西后”观,从而也未能看到这种“中先西后”观对他翻译和修改《天演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严复《天演论》手稿本自序和通行本自序以及两个译本自身的细读,试图透过字里行间看到严复翻译《天演论》时的真正立场,以及这种立场和他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两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格义和会通——之间的必然联系,以期为严复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中先西后”立场不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并认识西学的坚实阶梯,而且开创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较为合理并积极有效地更为全面利用西学的先河。严复以翻译为名,通过格义和会通的途径使中学与西学相得益彰,并使中学通过他优雅的译笔焕发出新的活力。他译书的这种良苦用心当为世人永远铭记。
注释:
①本段取自《天演论》首篇,虽然严复在手稿本和通行本中分别使用了“天道”和“天运”两个不同的表述,但他在手稿本《卮言十五》和通行本《导言十五·最旨》对前14篇进行概括时均使用了“天道”一词,据此可以推断,在严复看来,“天道”其实就等同于“天运”。
②严复后来在《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中借用裘可桴的话表明了这一观点。见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