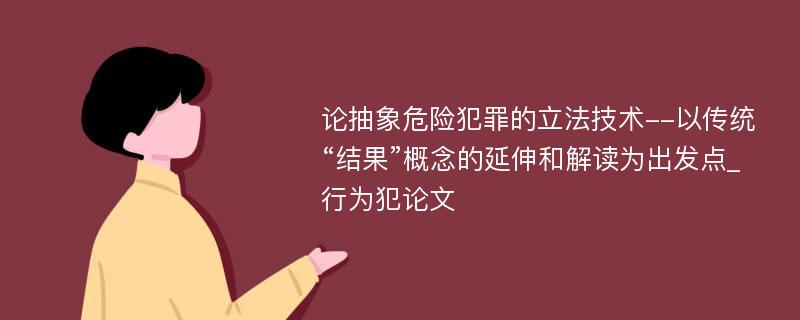
抽象危险犯立法技术探讨——以对传统“结果”概念的延伸解释为切入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切入点论文,以对论文,抽象论文,危险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13)08-0010-11
犯罪构成的经典构造是以结果犯为基准的,行为、结果、因果关系都是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结果必须可以客观地归责于行为并最终归责于行为人。①而抽象危险犯的法条文字一般只规定了行为,没有关于结果要素的文字表述,因此,抽象危险犯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就成了争议问题。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为例,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醉酒驾驶行为即一律入罪,还是醉酒驾驶行为必须危害公共安全才能认定为犯罪,学界观点不一,司法实务也一直饱受困扰。查阅近两年来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判决,笔者发现判决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行为的结果加以描述的判决书。例如,“被告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②;另一类是不对行为的结果加以描述的判决书。例如,“被告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③很显然,前一类判决将抽象危险犯作为结果犯,要求行为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后一类判决将抽象危险犯作为行为犯,仅要求行为人实施了危险行为。这两类判决呈现给我们两个选择:一是将抽象危险犯作为结果犯,这样有利于限缩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排除具体个案中根本不会有危险的行为,但为此必须延伸解释传统的“结果”概念,说明“抽象危险”是结果;二是将抽象危险犯作为行为犯,这样不必延伸解释传统的“结果”概念,但可能会扩大处罚单纯违反命令的行为,无法排除危险行为的类型化可能带来的“误差的风险”④。相比之下,第一个选择更加合理,所以本文主要以对传统“结果”概念的延伸解释为切入点,探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优化。
一、抽象危险犯不是行为犯
根据大陆法系的通说,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区分标准在于构成要件是否包含了结果要素:构成要件只规定了行为内容的犯罪是行为犯;构成要件中还规定了结果内容的则是结果犯。⑤因为规定抽象危险犯的法条文字一般只规定行为,所以通说一般将抽象危险犯理解为行为犯,认为立法者增设危险驾驶罪这样的抽象危险犯完全是基于现实需要和政策考虑,不包含任何损害因素。如马克昌教授曾指出:“抽象危险的确认依据,主要是行为实施的危险性,只要行为在法定的客观条件下实行,作为构成要件结果的一般危险状态就伴随而来,犯罪即既遂。”⑥据此观点,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基于行为的危险给予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在具体危险犯的场合才存在结果的危险,抽象危险犯一般被看作是没有结果的犯罪类型,只要单纯地实施了立法上规定的危险行为就足以构成。⑦据此观点,立法上规定的抽象危险行为本身就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所以行为本身就可以充足全部的刑事不法。更有观点指出,行为犯和抽象危险犯实际上已经转化为一个犯罪类型:“单纯的行为危险犯或者单纯的危险性犯”。⑧
将抽象危险犯看作行为犯的逻辑基础是:抽象危险犯没有构成要件结果,所以抽象危险犯仅有行为不法;行为犯也没有构成要件结果,所以行为犯也仅有行为不法;因为在犯罪构成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结构,所以抽象危险犯就是行为犯,反之亦然。笔者认为,这样的逻辑基础至少包含了以下错误:犯罪构成中没有规定构成要件结果,并不意味着成立犯罪不需要结果的不法。根据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情形又称为“不法”,不法具有两个面向:一是“行为的不法”,强调的是行为是否会侵害法益,是对行为性质所作的评价;二是“结果的不法”,强调的是行为是否造成了法益侵害,是对行为引起的法益侵害状态所作的评价。其中,行为的不法主要判断行为是否在性质上就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结果的不法主要判断行为是否在客观上制造了对法益的危险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抽象危险犯和行为犯都既具有行为的不法也具有结果的不法(违法结果),即便行为实施完毕、危险状态就同时出现,也必须将行为(危险性)与结果(危险状态)作为“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在逻辑判断上加以区分,分别进行判断,只不过由于缺乏构成要件结果,抽象危险犯和行为犯的这种结果的不法并不是通过构成要件结果体现出来的。构成要件结果与违法结果之间的这种关系类似于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中“行为对象”与“行为客体”之间的关系,也类似于日本学者所称的“行为客体”(作为行为对象的人或物)与“保护客体”(保护法益)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并无行为客体的犯罪,但并不存在没有保护客体的犯罪。换言之,即便在并无客体这一物理性存在的犯罪中,也有保护客体”。⑨即便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结果也并非所有犯罪构成必备的构成要件要素。在这一点上,四要件与三阶层不存在区别。尽管在规定了构成要件结果的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如出现构成要件结果是犯罪既遂的标志),但在违法性评价上,构成要件结果并不是必备要素。因此,犯罪构成中没有规定构成要件结果并不能成为将抽象危险犯看作行为犯的依据或者理由。
尽管从形式上看,规定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的法条文字一般都未明文规定构成要件结果,但从实质上看,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都必须具有违法结果。构成要件结果与违法结果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结果概念。例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要成立犯罪,并不要求给居住权人造成物质性的损害结果(构成要件结果),却要求侵犯居住权人的合法权益(违法结果)。通过这样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构成要件结果与违法结果的区别,也可以看到,不管是行为犯还是抽象危险犯,虽然立法者并未规定构成要件结果,却都存在违法结果。因此,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结果”概念(构成要件结果与违法结果的区分)导致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无法区分,而是在于构成要件是否包含了结果要素的通说并不能真正地发挥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有学者指出:“违法结果需要进行规范性的判断,由于违法结果被看做是结果的不法,因此其作为事物的一项新状态替代了实施构成要件行为所实现的现实意义上的结果。所有的犯罪类型,包括行为犯和具有构成要件结果的结果犯,都先验地存在违法结果,结果犯的结果不法的含义也相应地被打破。”⑩
因为按照通说并不能合理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所以理论上必须寻找其他的区分标准。张明楷教授认为,合理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的标准是“行为终了与结果发生之间是否具有时间上的间隔”,“即行为犯是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因果关系便不成其为问题;结果犯则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时间间隔的犯罪,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11)按照这一标准,抽象危险犯明显不属于行为犯:在行为犯中,结果与行为在时间、空间上难以分离,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而在抽象危险犯中,结果与行为在时间、空间上是分离的,只是在行为尚未产生结果之前就提前满足刑事可罚性的条件。因此,抽象危险犯是刑事处罚前置化的犯罪类型,并没有在犯罪构成上缩减刑罚的必要条件。
笔者赞成按照这一标准来区分行为犯和结果犯,根据这一标准可以在犯罪构成上明确区分行为犯和抽象危险犯。但是,理论上的任何分类都是相对的,行为犯和抽象危险犯的区分亦不能例外:结果与行为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仅在一般意义上成立;在特殊情况下,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之间也会丧失犯罪构成上的区别:例如,当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时空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无法明确分离时,很难说此种犯罪只能是抽象危险犯而不是行为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就是适例。又如,当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通过当前科学的标准加以解释,仅能从行为性质上断定这类行为是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立法者出于预防的目的事先假设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而将行为规定为犯罪时,也很难说该种犯罪只能是抽象危险犯而不是行为犯,侵害精神化的个人法益(自由、名誉、隐私等)的犯罪构成一般属于这种情况(如德国刑法第184条规定的犯罪),但是,特殊情况下的犯罪构成在刑法条文中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综上,鉴于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在犯罪构成上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可能在特殊情况下存在交叉,理论上若无视二者之间的上述复杂关系,笼统地说抽象危险犯就是行为犯或者行为犯就是抽象危险犯,将只会增加概念上的困惑、分类上的混乱,对于优化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无半点益处。因此,笔者认为,理论上应达成如下共识: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的本质区别仍在于二者属于不同的犯罪类别:行为犯是与结果犯相对应的概念、抽象危险犯是与实害犯或者侵害犯相对应的概念;如果必须将抽象危险犯纳入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分类之下进行检验,抽象危险犯也必须被归入结果犯,而不是行为犯。
二、抽象危险犯是结果犯
对于直接侵犯个人法益的抽象危险犯来说(例如侮辱罪),将抽象危险看做是具体的侵害结果,虽然不易具体地证明,但也不存在特别的困难;但对于侵犯超个人法益的抽象危险犯来说(例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益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而非个人的生命健康),要将抽象危险看作是犯罪结果,在传统的“结果”概念下似乎存在着理论上的障碍,为此必须延伸解释结果的一般概念。
(一)结果的一般概念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将犯罪结果定义为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和现实危险,(12)危险状态(尤其是抽象危险)是否属于结果,一直是理论上争论的焦点。赞成者认为,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物质性损害、精神性损害及危险状态(包括抽象危险和具体危险),故犯罪结果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危险结果。(13)反对者认为,将危险结果未发生的危险状态理解为一种结果,在逻辑上难以成立,危险状态归根到底还是一种行为状态,而非结果状态。(14)这种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危险状态是否属于结果,是结果的范围问题;而如何理解结果的一般概念,决定了结果的范围。以往的刑法理论注重结果的外部表现,根据结果的外部表现,将结果定义为侵害结果与危险结果、物质性结果与非物质性结果、严重结果与非严重结果等不同的种类,并根据结果的外部表现有无在具体案件中最终实现来划分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形态。实害、侵害、损害、侵犯等用语,往往被作为结果的同义语,用来指代行为对法益造成的侵害后果。但是,这样的用语偏重于描述结果的事实面,未突出结果概念的价值面。此外,结果形形色色、多种多样,这样的用语无法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涵盖多样性的结果。
刑事处罚的前置化做法要求理论上延伸解释“结果”的一般概念。随着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刑法不必等到行为给法益造成的损害达到了物质化、现实化的时点才进行干涉,只要行为对法益造成了价值上的损害(违法的结果)即可被评价为不法,理由很简单:行为对法益造成了物质性结果时,固然可以说侵害了法益,但行为对法益的侵害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性的层面,还有非物质性的结果(例如对体系、制度的功能性妨碍),如果理论上继续使用传统的结果的一般概念,将导致结果无法涵盖危害行为对超个人、集体性法益的功能侵害性,因为对这些法益的侵害性往往并不表现为事实面的物质性或者非物质性的侵害后果,而是主要表现为功能性妨碍等价值面的侵害后果。
通说关于结果的一般概念混淆了危害行为对法益的实际侵害与危险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性:前者是结果的外部表现;后者是对结果的法律评价。事实上,刑法理论关于结果的范围的一切争论都是因为混淆了上述两个不同层面的结果。在传统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中,由于采用的是“平面”的评价体系,结果的一般概念主要表现为“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与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作为选择法定刑根据的结果与在法定刑内影响量刑的结果”,影响着犯罪的既遂和未遂形态与量刑的轻重,结果的事实面可以发挥作用,但结果的价值面被掩盖在犯罪成立与否的总体判断中,被“社会关系”、“行为客体”等用语所替代。阶层式的三要件犯罪论体系使得结果的事实面和价值面分离得更加明显,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主要是物质性结果,是结果的外部表现;对结果的法律评价存在于违法性判断层面;物质性结果只是违法性评价的对象,而违法性判断层面的结果是对于对象的评价。所以,结果的一般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结果,并不限于实害、侵害或者损害等物质性表现结果,还包括其他的妨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结果的一般概念还可以用其他的用语来表述,例如,自然意义上的结果与规范意义上的结果,事实上的结果与评价上的结果,说的都是一回事。
(二)两个层面的结果
结果的一般概念包含了两个层面的结果。这一观点具有理论上的支持,例如,国外有学者指出:“应区分结果在犯罪论体系内的功能,是作为构成要件的要素还是作为不法的构成要素”。(15)从内容上看,这两个层面的结果是不同的:一个是构成要件结果,一个是违法结果;从功能上看,这两个层面的结果似乎应该并存,不能合二为一;即便要合并,也存在哪一个层面的结果吸收另一个层面结果的问题。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一直以来都不区分使用构成要件结果和违法结果的概念,这直接导致了理论上对抽象危险犯的认识混乱,以下试举两例。第一,对抽象危险犯采取形式化的理解。这种观点受到了风险刑法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风险刑法的立法意旨就是将社会已形成共识的典型行为视为一种当然可能会造成实害的行为,而为了预防实害的发生,就有必要将其作为被禁止的行为而直接入罪。”(16)“抽象危险是一种拟制的危险,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对行为本身是否具有危险性作出判断就可以依据形式上的典型行为肯定抽象危险的存在而因此具有实质的不法性”。(17)根据这种观点,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与抽象危险结果之间存在一种“强制”的关联性,只要具有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即被看作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至于行为事实上是否真正威胁到了法益则在所不问。但是,这种观点导致对于特定情形下,抽象危险行为并未产生任何危险的案件也予以处罚,可谓对于抽象危险行为的“一网打尽”,容易产生打击的误差风险,不具有合理性。第二,将危险结果作为危险行为的属性。这种观点在我国比较盛行,很多学者都将危险作为行为的危险(也称行为的属性)而不是作为结果的危险(即行为导致的对法益的危险状态)。“之所以将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与盖然性,是因为:一方面,危险状态这种结果取决于行为的危险;如果没有行为的危险,就不可能有危险状态;另一方面,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区分,只能根据行为的危险认定行为造成了危险状态”。(18)很明显,这种观点混淆了构成要件结果与违法结果,并且用构成要件结果吸收了违法结果,缺少结果的规范意义上的评价。
在结果的一般概念问题上,传统的四要件体系缺点明显,仅能体现构成要件结果,没有违法结果的体系位置,因而在抽象危险犯、行为犯都不适合明文规定构成要件结果的犯罪构成中,可能会出现认识上的混乱和认定上的误差。递进的三阶层体系优势突出,由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处于两个不同的判断层次,因此,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至少在逻辑上是应该分开的,也是能够分开的;行为的危险是评价对象,作为结果的危险是对对象的评价,这二者缺一不可。理论上没有必要在传统的结果概念之外再构建出一个新的概念来指代违法结果,因为一旦将结果分别定义为构成要件结果与违法结果,还要相应地将犯罪分为不同的类型,结果犯与行为犯的犯罪分类将无法准确地与这两个层面的结果相对应。因此,理论上最好的选择就是,将传统的结果概念延伸解释为包括这两个层面的结果,并且根据功能上的重要作用将结果主要定义为违法结果,因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所以构成要件结果具有指示违法结果的功能,而且违法结果在评价上必然包括对构成要件结果的评价。
违法结果在犯罪论体系中至少发挥着两个重要功能:一是沟通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评价,将违法结果归责于行为;二是沟通了不法与责任,将违法结果最终归责于行为人。将结果主要定义为违法结果与现代刑法的发展相吻合。事实上,传统的结果概念近年来一直在呈现延伸的趋势,构成要件结果已经无法涵盖所有的结果样态。随着刑法保护的抽象的法益越来越多,尤其是超个人的集体法益的性质决定了行为根本不可能对其造成物质性的侵害结果,即便造成了物质性的侵害结果也无法根据传统的因果关系加以认定,所以立法者无法将其规定为构成要件结果,否则会导致侵害集体法益的犯罪无法成立,反而不利于保护这类法益。当然,重视违法结果并不意味着否定构成要件结果。由于构成要件结果在犯罪构成上就与行为相分离,且结果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易于证明,所以构成要件结果对于结果的认定和违法性的判断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只不过在功能上无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已。
(三)抽象危险是结果
如何定义结果,决定了结果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如果认为结果是构成要件结果,结果犯的构造必须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行为和构成要件结果,那么抽象危险犯就不是结果犯;如果直接将危险结果作为危险行为的属性,不区分危险行为的性质与危险结果的判断,那么抽象危险犯就是行为犯;如果认为结果是违法结果,那么结果就是所有犯罪共通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抽象危险也是结果,不具有任何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犯概念必须得到刑法可罚性理论的否定,因为其既不具有违法结果,又不符合法益侵害原则。笔者认为,抽象危险是结果,结果是对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后果的否定性评价,而否定性评价不仅限于实害、侵害或者损害等物质性结果,还具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在造成损害、实害或者侵害之前,最好使用改变、影响或者妨害这样的表述”。(19)这样一来,结果的概念就可以同时包含物质性结果、精神性结果和危险状态(包括抽象危险)。绝大部分抽象危险犯都没有造成物质性结果,但都造成了违法结果,违法结果能够透过行为对法益的改变、影响或者妨害等表现出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具体化。
三、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反思
立法者为了实现刑事处罚的前置化,对抽象危险犯的犯罪化进行了技术上的处理。有学者梳理出现代刑法的八项立法技术,认为刑法凭借推定、行为范畴的拓展、犯罪标准的前移以及犯罪构成要素的增减等制度技术,减少了抽象危险犯的结果要素,司法机关无需在程序上证明行为对法益造成了侵害结果。(20)笔者认为,从形式上看,立法者确实对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进行了一定的技术修改,但从实质上看,立法者所做的上述技术修改并不足以改变犯罪构成的经典构造(结果犯)。
第一,采用推定规则规定抽象危险犯将抹杀司法定罪功能。我国刑法理论上倾向于将推定规则作为风险社会刑事立法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在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领域(如环境污染等公害犯罪、隐蔽性较强的毒品犯罪)存在着推定规则,这些推定规则“正是国家基于有效防控犯罪、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而创设的,具有明显的功利性,是风险社会中刑事法自身调整变迁的重要一部分”。(21)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防控犯罪、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采取推定的立法方法,有违“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也与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相抵触。对此,主张推定规则的学者也有所认识,认为允许被告人反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推定的功利价值与刑事法人权保障机能之间的紧张关系”。(22)但是,一旦认为推定是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就意味着立法者在犯罪构成上缩减了刑罚的必要条件,同时也缩减了被告人的辩护可能性,使法官屈从于立法者的决定,允许被告人反驳也不具有出罪的实践意义。此外,由于在抽象危险犯中,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仅仅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上,在行为尚未引起实害结果之前就对其进行处罚是为了防止或者避免行为在将来引起实害结果,如果在此基础上还允许立法上采用推定规则规定抽象危险犯,将导致立法者的判断代替司法者的判断,使司法者盲目顺从立法者的决定。
第二,在立法上规定抽象危险犯并没有对行为范畴进行拓展。从立法上的规定来看,新增的犯罪行为确实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拓展。如刑法第210条之一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将伪造发票行为的可罚性扩展到了预备行为和持有行为。但刑事立法对于预备行为和持有行为的拓展都未超过行为要素应有的边界,所以这一立法技术并不足以改变犯罪构成的经典构造中的行为要素。以预备行为为例,各国刑法都在扩张处罚实质预备犯,如果不确定预备行为的实质可罚性,将直接导致预备犯的处罚范围过分泛化、刑法主观主义的色彩过分浓厚,所以必须确定预备行为的实质可罚性;而一旦用实质可罚性来限制预备行为的拓展,就会发现,立法上规定的抽象危险犯其实并未怎么拓展行为范畴:无论是预备犯类型的抽象危险犯(例如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持有犯类型的抽象危险犯,还是近乎于实害犯(或者说与实害犯平行的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危险犯,其危险行为都必须具有类型化的危险性,这种类型化的危险性必须体现危险行为与危险结果之间的合法则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类型化的危险行为必须在具体案件中制造或者创设出危险,否则就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根据。
第三,犯罪标准的前移并不能解决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要素之难题。作为刑事处罚前置化的犯罪构成,立法者对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标准进行了前移,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立法者将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标准前移,只是意味着抽象危险犯对法益侵害成立的“时点”提前了,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法益侵害不再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换言之,犯罪标准的前移只是意味着,对于“结果”的认定要跟着法益侵害成立的“时点”前移(由实害提前到了危险),而并不意味着理论上可以彻底否定“结果”是抽象危险犯的成立要素,也并不意味着司法者“无需判断具体的结果性危险存在与否”,即可直接认定成立抽象危险犯。正是因为犯罪标准前移到了危险,而危险与实害相比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理论上更需要将危险概念在具体案件中予以客观化和现实化,立法者的“动机”不能作为抽象危险犯的定罪要素;危险概念要与实害结果具有一定的、至少是间接的联系,否则,犯罪标准的前移就不具有正当化根据。因此,刑事立法对法益侵害的标准前移,并不足以否定犯罪构成的经典构造中的结果要素。
第四,立法上规定抽象危险犯并不是犯罪构成要素的删减,司法实践中仍须在具体案件中认定现实的危险结果。一般而言,增加构成要件要素能够限缩犯罪化的范围;减少构成要件要素能够扩大犯罪化的范围。但是,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中,“实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要素”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在抽象危险犯中删减了结果这个要素。这有点像文字游戏,但事实上,“实害结果”从来都不是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素,也不是具体危险犯的构成要素,有无“实害结果”只是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区分要素”:危险犯的结果是危险性结果,而不是实害结果。(23)同时,实害结果从来都不影响抽象危险犯的既未遂形态,因为实害结果只存在于实害犯中,所以实害结果只能影响实害犯的既未遂形态。
反思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不难发现立法者并没有删减结果要素,只是对其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易言之,在抽象危险犯中,类型化的危险行为一旦遇到了合乎因果法则的必要条件,就会引起现实的危险结果,但由于抽象危险犯是刑事处罚前置化的犯罪类型,立法者规定在现实的危险结果出现之前就对于危险行为进行处罚,于是,危险结果被抽象化为不法状态(违法结果)、引起危险结果的必要条件(因果关系)也随之被抽象化为引起不法状态的必要条件。因此,“立法者对犯罪构成中规定的行为并未进行抽象化,而是要求行为必须在具体案件中制造或者创设危险。与之相反,行为要合乎因果法则地引起不法状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成了被抽象化的对象”。(24)
立法者之所以对抽象危险进行“抽象化”的处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因为将侵害法益的结果规定为典型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合适。例如,德国刑法第107条a(伪造选举罪)规定处罚不正确公布选举结果或让他人不正确公布选举结果的行为。一般认为,该罪侵害的是民主选举不受操纵的集体法益,如果将对这一法益的侵害规定为典型的构成要件要素,就意味着行为人要对这一法益造成构成要件结果,并且对这一结果具有侵害的故意,同时,刑事诉讼程序也要对行为是否确实造成了构成要件结果予以证明。但是,要证明行为对这一抽象的法益造成了构成要件结果在实践上是非常困难的。于是,立法者放弃结果犯的经典构造不用,转而采用抽象危险犯的构造,不明文规定典型的构成要件结果。不过,明文规定典型的构成要件结果“不合适”,并不意味着行为“不需要”对法益造成侵害“结果”,相反,在这种案件中,行为对于法益造成的侵害结果几乎具有与实害平行的重要性,一起伪造选举案件就可能足以动摇社会公众对民选制度的信心。其次,可能是因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但是很难在刑事诉讼程序上证实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立法者只能将因果关系作抽象化的规定。这里又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因为区分的困难。例如,德国刑法第231条规定:“参与斗殴或参与由多人实施的攻击行为,如果其斗殴或攻击行为致他人死亡或重伤害(第226条)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罚金刑”。(25)斗殴行为具有导致他人死伤的性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可能把个人的行为与其他数个共同攻击的人的行为与死伤结果从因果关系上区分开,又由于无法否认个人的行为与共同攻击的人的行为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连带性,立法者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抽象化。二是出于预防的必要性。有些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通过科学的标准解释,立法者出于预防的目的,事先假设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尽管科学上还未证实,但是这类行为明显的是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例如,德国刑法第184条规定:“在不满18岁的人允许进入或看阅的场所陈列、张贴、放映或以其他方法使其获得的淫秽文书”,(26)构成散发淫秽文书罪。科学的认识尚不能证明淫秽文书何时、会对哪些未成年人造成身体或者精神的损害,立法者为了对未成人提供预防性保护,将其规定为犯罪。三是“累积性”的因果关系。这种类型的行为具有特别的因果关系问题,个人的行为不足以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但是不能排除个人的行为不断重复或者累积实施会造成侵害结果。例如,德国刑法第324条(污染水域)和324条a(污染土地)规定的污染环境犯罪都属于这种类型。
因此,理论上应该对抽象危险犯的刑事立法技术进行反思。尽管抽象危险犯的法条文字中找不到“危险”这一结果要素的明文表达,但考虑到抽象危险犯的实质违法性就会发现,抽象危险是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虽然不是刑法条文明文描述的要素,但却是根据刑法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刑法条文对相关要素的描述所确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构成要件要素”。(27)以危险驾驶罪为例,如果危险驾驶行为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则难以认定为犯罪。
四、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优化
我国刑法理论一直在探讨如何促成抽象危险犯的理性立法。(28)笔者认为,抽象危险犯的实体法定位之所以模糊,主要是因为理论上认为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不存在实质性区别,所以,将抽象危险犯看做是结果犯有利于划清行为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的界限。立法者应该在将来的刑事立法中摒弃行为犯的立法模式,转而采用抽象危险犯(结果犯)的立法模式,尽力促成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上的合理化和危险行为的类型化。
(一)犯罪构成上的合理化
立法者为了实现刑事处罚的前置化,对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这种抽象化的立法技术并不是最理想的立法方式,很容易过分扩大刑事可罚性的范围。为此,在将来的刑事立法中,立法者可以考虑采用其他的立法技术,来促成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上的合理化。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立法上在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中就规定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尽量不要采用象征性犯罪构成。罗克辛教授认为:“对于保障和平的共同生活不是必要的,但为了谋求刑法之外的目的,就像安抚选民或者表达国家自我姿态的法律规定,是我所理解的象征性犯罪构成。”(29)德国刑法第130条第3款规定,否认或者粉饰在纳粹统治下所实施的种族灭绝犯罪的,予以刑罚处罚。这一犯罪构成并没有明确的保护法益,这种规定的意义在于表达德国是一个悔过自新的国家,对这一犯罪的追究并不是为了保护法益,即便认为是保护法益,那么其所保护的也只能是“扰乱公共安宁”这样的模糊概念,不具有明确性。对于这样的犯罪,立法上不能将其规定为抽象危险犯。有无保护的法益决定了行为有无实质的违法性,因而决定了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我国刑事立法亦是如此,不能认为现代刑法为控制风险可以制定仅具有“象征意义”的犯罪,不能将抽象危险犯作为仅仅违反规范的行为,对其适用的刑罚也不再是自由刑等实质剥夺犯罪人权利的刑罚,而是罚金、预防性监禁或者强制出庭作证等纯粹具有“象征意义”的刑罚。
第二,立法上在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中明文规定危险结果,说明行为一旦实施就会对法益造成的危险状态。明文规定危险结果对于抽象危险犯的犯罪构成而言,乍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国外刑法已经有此做法。例如,在1998年刑法典改革之前,德国刑法关于遗弃罪的犯罪构成并未明确要求遗弃行为要引起对被害人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的危险,但是,1998年德国刑法关于遗弃罪的规定修改为:“遗弃因年幼等需要扶助的人,并因此使之遭受死亡或者健康损害的危险的……”德国刑法依然将遗弃罪理解为抽象危险犯。这样的立法方式有利于保障刑法基于行为的实质不法给予刑罚处罚,也有利于将抽象危险犯与行为犯相区分。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立法方式会导致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无法区分,但事实上,抽象危险与具体危险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理论上应该破除这样的误解。抽象危险行为可以在对法益造成了抽象危险之后继续向前发展并发生具体危险,只要该具体危险并不构成具体危险犯,还是需要按照抽象危险犯进行处罚。例如,行为人醉酒之后开车的,行为已经发生抽象危险,构成危险驾驶罪;可是,行为人继续向前行驶一段距离,其他车辆躲避及时才未能发生交通事故的,行为人的行为显然已经超越了抽象危险的程度而发生了具体危险,但是,行为人的行为仍然构成抽象危险犯,因为我国刑法规定危险驾驶罪的目的在于:只要在醉酒驾驶与交通肇事之间不具有其他能够填补这个漏洞的犯罪类别,就都被抽象危险犯所涵盖,抽象危险犯的危险至少是抽象危险,也可以是具体危险。
第三,立法上明确规定刑事不法、行政违法与自由的不同情形。(30)换言之,如果某种类型的行为不具有任何刑事不法的内容,又与社会上一般意义上的适法行为比较相似,对于这类行为不宜实行犯罪化,否则就是在处罚纯粹不服从规范的行为,立法上将无法说明对这类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无法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也无法说明刑事可罚性与行政违法性或者其他自由行为之间的界限。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6条第1款规定了构成犯罪的情形:“未经许可在规定范围之外或背离规定的或许可的程序,存放、储存、排放或去除下列垃圾的(可能含有或产生对人或动物具有公共危险且能传播毒剂或病原体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该条第3款规定了行政违法的情形:“违反行政法义务,不将具有放射性的垃圾运走的行为,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该条第6款还规定了无罪的情形:“在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上,若不具有明显有害的影响(由于垃圾数量小,显然排除对环境,尤其是对人、水域、空气、土地、可食动物或植物的有害影响的),那么该行为就不具有刑事可罚性。”(31)我国刑事立法可以考虑的是:在涉及刑事违法与行政不法和自由的情形中,也根据行为的不同性质,设立不同的规定,以免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于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和自由的界限问题而争论不休。
(二)危险行为的类型化
抽象危险行为在性质上就具有侵害法益的一般危险性或类型化的危险性,由立法者选择和判断该等行为是否会导致不法结果、是否需要为避免这种不法结果的发生而预先将其以类型化的方式规定出来,作为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行为。由于行为的一般危险性或者类型化的危险性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和不明确性,立法者不能对此抱持如下误解:
首先,不能在“习惯性地”或者“通常性地”意义上理解行为的危险性,抽象危险行为必须是在“类型上”或者“方式上”会引起不法状态的行为。(32)当然,根据生活经验,习惯性地或者通常性地引起不法状态的行为,有可能经过立法者的选择和验证被规定为抽象危险行为,例如,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驾驶行为有多种,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行为都可能“习惯性地”或者“通常性地”引起危险状态,但只有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两种行为在“类型上”或者“方式上”会引起危险状态,所以被类型化地规定为危险驾驶行为。同理,随着毒品的泛滥,吸毒之后处于迷幻状态从而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否可以被类型化为犯罪行为,虽然在民众中呼声较高,仍有待立法上的选择与验证。
其次,不能为了追求精确而将危险的程度加以“量化”,并采用“决定性的可能性”或者“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于结果不发生的可能性(51%-49%)”之类的说法来衡量危险的程度,这方面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的。(33)事实证明,对危险的程度加以量化的做法在实践中一般是行不通的,而且,刑法上也无法规定出一个确定的危险量作为对危险进行衡量的参数,事实上,即便统计学的发展能够为立法者提供一个衡量的参数,这样的参数也只能作为证据要素,而不能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因此,立法上对于危险行为的类型化只能从行为的性质以及危险性的大小、高低入手,是规范性的选择与验证,而非纯粹事实的判断。
最后,虽然危险行为的类型化对于刑事立法至关重要,但类型化的含义以及如何对危险行为实行类型化一直都是不明确的问题,理论上对此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抽象危险犯在各国刑法中的数量都相对较少,缺乏类型化的实证基础;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界有一种普遍的态度,认为行为的危险性难以在刑法理论上一概而论地解决,根据实际发生的案件逐一判断行为的危险性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这样的观点无助于刑事立法的发展。从经验上看,如果某一类行为很容易、而且通常会对受保护法益造成侵害,那么这类行为就是“类型化”地具有一般危险性的行为,可以考虑将其犯罪化。但是,在经验上通常会引起不法状态的行为,也必须经过立法者的选择和验证才能被规定为抽象危险行为,而要建立行为与危险状态之间在“类型上”或者“方式上”的联系,还需考虑行为造成危险状态的条件、行为与危险状态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是否对这些条件和因果关系具有认识可能性等一系列问题。
注释:
①参见[德]约克·艾斯勒:《抽象危险犯的基础和边界》,蔡桂生译,《刑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②安阳市黄县人民法院(2012)内少刑初字第44号刑事判决书。同样表述的判决书还有很多。
③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2)沁刑初字第315号刑事判决书。同样表述的判决书还有很多。
④所谓的“误差的风险”,是指一旦从类型上来规定抽象危险行为,就必然会带有打击面过宽的误差的风险。参见林东茂:《危险犯与经济刑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1页。
⑤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⑥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204页。
⑦José Cerezo Mir,Courso de Derecho penal espa? ol.Parte general,Tecnos,6a ed.,Madrid,2001,Vol.II,p.154.
⑧N.Garcí a Rivas,Delitos Ecoló gico,Estructura y aplicació n judicial,Barcelona,1998,p.50.
⑨[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第59页。
⑩Marí a Acale Sá nchez,Los Delitos de Mere Actividad,Revista de Derecho Penal y Criminologí a,No.10,2002,p.26.
(1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12)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第191页以下。
(13)参见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14)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6页。
(15)Tatiana Vargas Pinto,Delitos de peligro abstracto y resultado,Editorial Aranzadi,SA,2007,p.166.
(16)陈晓明:《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17)高巍:《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和正当性基础》,《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8)周光权:《危险犯的认定》,《人民法院报》2003年3月21日第3版。
(19)Tatiana Vargas Pinto,Delitos de peligro abstracto y resultado,Editorial Aranzadi,SA,2007,p.152.
(20)参见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1)、(22)赵俊甫:《风险社会视野中的刑事推定——一种法哲学的分析》,《河北法学》2009第1期。
(23)张纪寒、周新:《论犯罪结果的本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4)Alejandro Kiss,El delito de peligro abstracto,Buenos Aires:Ad-hoc,2011,p.90.
(25)、(26)、(31)《德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第98页,第161页。
(27)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28)参见谢杰:《抽象危险犯的反思性审视与优化展望——基于风险社会的刑法保护》,《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2期。
(29)[德]克劳斯·罗克信:《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刑事法评论》(第19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30)、(32)、(33)See Alejandro Kiss,El delito de peligro abstracto,Buenos Aires:Ad-hoc,2011,p.234,p.171,p.171.
标签:行为犯论文; 结果犯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法律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