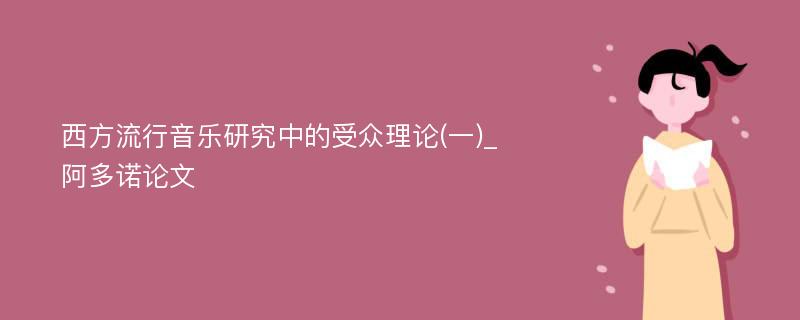
西方流行音乐研究中的受众理论(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众论文,流行音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人参与大量的音乐实践,那么,试图介绍音乐受众理论的这一章将不可避免地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毕竟,流行音乐的受众范围覆盖了数以千万计的聚集于露天大型运动场观看著名乐队和歌手表演(或许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通过广播和电视收看转播)的人们,以及那些在婚礼或生日宴会上随着音乐起舞的人们。音乐受众包括了积极参与到某些活动中的人们、路过购物中心时听到嘈杂的不同旋律与节奏的人群,以及某个骑自行车穿过乡间时聆听随身听里的磁带的人。 如果你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19世纪末音乐录音传播之前,以上活动中的大部分都是不可能的。音乐受众一直在音乐家表演的现场欣赏音乐和起舞,那么你将会意识到,音乐受众的途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里具有多样性。 这个介绍性的一章并不试图从解说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入手。相反地,在这里,我的主要关注点是,自现代录音技术发展以来,尤其是伴随着交往媒体技术及20世纪下半叶电影的发展,音乐受众是怎样被理论化的。此外,在本章中,我将要聚焦的受众的理论阐释主要涉及“接受”的问题——即,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人们参与具体社会活动中时是如何接受、诠释和使用音乐的。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方面之一,并且本章意欲成为这一特别研究的一项批判性的梳理与评价。 在采取这一焦点的过程中,研究音乐受众的理论家们多年来关注了年轻人的行为。在20世纪50年代,关注点是“青少年”。到了60年代,焦点转向了“年轻人”群体,并由此催生了大量有关年轻人亚文化的著作。到了80和90年代,又产生了对粉丝和音乐场景的广泛兴趣。 在追溯有关流行音乐与年轻受众的理论的发展时,我将详细叙述日益活跃的受众的情况。这一理论梳理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挑战,但也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提出的有关流行音乐欣赏的批评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因此,在本章中,我将首先介绍阿多诺在流行音乐受众方面研究的细节。 阿多诺的孩子们——聆听的倒退 阿多诺在20世纪20到60年代撰写了关于音乐与文化的著作。他是一个卓越的德国犹太学者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就是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并且他的思想经常有悲观主义倾向,而这种悲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所目睹的严重的政治混乱时期。阿多诺经历了1914年至1918年战争的流血杀戮、俄国1917年革命后遍布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及20世纪20年代后法西斯党的成长。当纳粹党于1933年攫取权力后,阿多诺不得不逃离德国,最终转而定居美国。 阿多诺生活在一个科技变革导致留声机唱片音乐日益流行的时代,一个无线电广播和电影中声音的引入为商业营销和政治宣传提供机遇的时代。当纳粹党在德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媒体技术时,阿多诺到达了美国,去寻找同样被用来产生和传播商业文化的媒体。于是,阿多诺的写作形成于现代传媒科技与大众媒体发展对流行音乐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 在流亡期间,阿多诺将他在德国和到美国之后所观察到的情况联系起来,发展了一种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对人们(被归纳为“大众”)的支配与操控明确地与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即“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散播相联系。在探寻这一理论的过程中,阿多诺关注文化形式如何帮助独裁统治,并阻碍政治批评或有助于解放的社会变革。在下一章中,我将阐述更多有关阿多诺将流行音乐作为大众文化的生产的内容;在这里我想概述一下他所谈论的消费问题。 对阿多诺来说,作为大众文化,流行音乐被音乐产业所传播,听众并不需要为此做出很多努力。他认为这导致了“非聚精会神的聆听”,听众拒绝了他们不熟悉的内容,并且行为举止开始像孩子一般。①阿多诺认为其中一种特殊的“孩子般”的消费类型就是他所称的“引述聆听”,意即,退化的听众沉醉于最明显的旋律片段,而非聆听音乐并试图从整体上领会一首作品。这样一来,听众们选择了一种“儿童音乐语言”并聆听不同的作品,“就好像交响乐在结构上与一首歌谣无异”。② 这样的聆听方式并非是因为听众生来愚钝,而是因为录音和出版发行产业促使了标准化、重复性音乐的产生:歌曲鼓励听众们聆听音乐时不做任何努力。阿多诺提到一种“不费力的聆听”的分类,这种分类方式认为,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说明音乐被精密地创造出来是为了鼓励听众分心的行为。他宣称这样的声音由最为人所熟悉的和声、节奏和旋律组成,并且对社会意识具有催眠作用。不仅如此,阿多诺声称这种音乐还阻碍了人们反思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业余时间里,倒退的听众们被音乐所安慰,而这种音乐仅仅使他们从工厂、生产流水线或办公室的无聊中暂时逃离。③ 阿多诺主张,音乐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应当具有唤起听众批判性地思考世界的潜能。然而,为了娱乐而被生产出来的流行音乐仅仅引向了消极被动。这样的音乐使人们接受现状并产生对独裁主义的顺从。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确实应当为造成社会的消极被动而负责,因为听众们倒退为一种“孩子般”的状态,从而容易为资本主义企业和法西斯国家的当局者所操控。 阿多诺的听众——于卧室中独处,在人群中迷失 阿多诺有关消极聆听的观点多少有些绝望色彩,于是其后的理论家们试图去挑战它。部分追随他的理论家及许多有关音乐消费的日常讨论都关注了阿多诺所提出的“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迷失于人群中的人,这类人容易为集体所操控。第二种是强迫性的人,这类人疏离于周围的人群,没有充分地融入社会生活中。 对于阿多诺来说,在20世纪40年代,在流行的舞蹈形式中,集体性的体验是最明显的,比如吉特巴舞。阿多诺认为这种华丽、急促的舞蹈形式是仪式性的,是一种强迫性的模仿行为。那些跳吉特巴舞的人丧失了他们的个性,像着迷的昆虫嗡嗡环绕般地回应着音乐。通过观察这种令人讨厌的形式,阿多诺评论道,跳吉特巴舞的人们在参与一种程式化的舞蹈形式,骚动抽搐,就像圣·维特斯舞或是残废动物的反应。④ 这样的评论显示,在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人们在理解身体与舞蹈如何回应音乐时的蹩脚理解。尽管如此,相似的词语依然被用来责备流行音乐的舞蹈,无论是查尔斯顿舞、摇滚乐、迪斯科还是电子摇滚乐。这样的担忧被用来联结对过分情感与性感的厌恶、对文明行为被原始节奏(常常是过分种族主义的)腐蚀的恐惧,以及年轻人正在被集群心理操纵的忧虑。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阿多诺对相反的音乐聆听类型进行了鉴定。对此他这样描述道: 对于急切地离开工厂并在安静的卧室中投入到音乐中的人来说,他是羞怯的、内向的,或许与女孩交往也没有好运气,并想要保护他个人的专门空间……20岁的他仍然处在男孩的令人嘲弄的边缘,忙于仅仅为了取悦父母的复杂结点上。⑤ 这是一个在自己卧室里(这是具有性别类型的)与世隔绝的、没有充分社会化的孤独者的形象。这个人在通过音乐获得的幻想的亲昵行为中取得安慰,并将其优先于和其他人的社会交往。在阿多诺写下这些内容40余年后,这一形象经常被用来讽刺史密斯乐队(The Smiths)及追随他们的吉他摇滚乐队的男性粉丝们。就如一位记者在对英国山羊皮乐队(Suede)第一张专辑的评论中所说的:“这是为那些不跳舞、宁愿在卧室里沉迷于自怨自艾的男孩们所做的音乐。”⑥ 阿多诺所定义的两种类型并没有像刚才所提到的引述一样仅仅被用来作为讽刺,但常常被用来证明与道德保护相关的忧虑是有合理性的。强迫性的个人经常被认为是重摇滚音乐的年轻粉丝,他们在一个小镇的卧室里独自聆听音乐,与家庭和朋友疏远,神经质,倾向于由紧张和持续地聆听这种音乐而引起的非理性的、自杀性的或侵略性的行为。更加社会化的、但仅是被音乐媒体产品所操控的,是社交场合中无组织的人群,他们聚集在空地和大型商店里,在晃动的手臂海洋和恍惚摇摆的身体中迷失了他们的个性。这两种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引发了宗教领袖、父母和社会工作者们的关注。这两者与40年前阿多诺所提出的两种类型非常相似。 这些对与流行音乐接受相伴随的社会行为的看法相当令人绝望。并且正是这些流行音乐听众的形象受到了提出“积极”音乐接受理论的作者的挑战。在阿多诺撰写有关听众类型的著作后不久,美国和英国“青少年”消费者的身份鉴别问题为更少操控成分的流行音乐消费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焦点。 积极的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对立 在1950年初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报告了他指导的一项研究,⑦这项研究是关于青少年聆听习惯的,它所做出的一项区分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长远影响。里斯曼在两种音乐聆听者的群体之间做出了区分:多数派和少数派。里斯曼的理论在阿多诺的观点和后来的亚文化理论家的观点之间建立了一条纽带。 在采访了芝加哥的一些青少年群体后,里斯曼报告称,他所与之交谈的大多数年轻人形成了一个多数者群体,该群体对流行音乐有着相近的口味。他们是大型广播电台和著名乐队的听众。这些年轻人关注歌星,聆听最流行的音乐。这个大多数者群体的成员并不十分关心音乐是怎样被生产的,他们的聆听习惯是相当杂陈的。音乐和表演者主要是他们肤浅的日常交谈和闲聊的对象。 对之形成对比的是,少数者群体采取了一种更为严格的和质疑性的姿态。里斯曼发现这一群体由有识别力的积极听众组成。这类听众建立了有关音乐聆听与欣赏的相当精细和成熟的标准。少数者群体的成员对音乐创作和演出进行详细的专门探讨。与多数者群体相比,少数者群体的成员往往不喜欢著名乐队和大歌星,而且对能从广播中听到的大多数音乐不感兴趣。相反地,这些听众更喜欢他们所认为的“非商业化的”、未做广告的、不那么著名的乐队。 里斯曼发现少数派成员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私有的语言”作为讨论他们喜爱的音乐和音乐家时独有的方式。然而,当多数派采用了“他们的”音乐时,由于觉察到其中包含了一个商业开发的过程,他们即停止了对这一词汇的使用。由此,少数派的成员们明确地将自己与多数派的品味对立起来,并置于后者之上。 里斯曼的区分是在积极的、反叛的少数派和被动的、无鉴别力的、墨守成规的多数派之间做出的。这种划分听众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阿多诺有关被动消极、墨守成规的音乐消费的设想,但此外又增加了更为积极的、更具参与性的少数派群体。并非所有的音乐消费都是被动的,尽管大多数仍然是这样。这种差别多年来被全世界大量的音乐粉丝用来将他们自己与其他听众区别开来,并且这一区分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初首次出版的一本书中,斯图亚特·豪尔(Stuart Hall)与派迪·维纳(Paddy Whannel)以不同代人的角度重新阐释了这种区分。⑧这两位作者将少数派称为“相对年轻的一代”。这被确认为在英国社会结构下的“有创造力的少数派”,就像豪尔和维纳所强调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相对年长的人和已步入青少年的人之间形成了“代沟”。 豪尔与维纳认为,这相对年轻的一代开始挑战古板的传统与中产阶级道德的“清教徒式的克制”。由此,他们发展了一种“亚文化”,结合了对性关系的新看法,并将其与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的各种表达相联系。有关这种亚文化的观点和态度常常直接与音乐消费相联系,尤其表现为对民间音乐、布鲁斯和摇滚音乐的聆听和参与。 豪尔和维纳观察到,年轻听众对音乐的运用是他们称之为“被制造出来的”和“真实可信的”的矛盾结合。像阿多诺一样,他们认为商业利益试图开发和操控人们对音乐的喜好和行为。但同时他们也指出,年轻人也在创造产品,这些产品“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兴趣,并以此与年轻阶层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这在“谁人乐队”(The Who)的音乐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这支乐队的唱片《我这一代人》(My Genercotion),其副歌部分不断重复唱道“谈论我一代人”就如豪尔和维纳有关流行音乐的描述所说的,象征性地申明了一种反叛与独立的精神。 尽管在分析中涉及了这首歌的某些情感,豪尔和维纳最终对紧张不安的这代人是否具有更广泛的潜力仍留有质疑态度。像提出了积极与消极音乐听众的里斯曼一样,他们指出,青少年文化一方面是“年轻人自我表达的领域”,同时还是“商业供给者茂盛肥沃的牧场”。⑨在标记这种区分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商业供给者的操控企图与听众诠释的回应之间的紧张。在正在创造一种“亚文化”的积极的年轻少数派和被动的年长保守的多数派之间的这种区分,后来被融入了进一步发展的亚文化理论。 亚文化与风格 早在20世纪30年代,亚文化理论最初由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在对犯罪和所谓非正常行为的研究中引入。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像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等研究舞蹈音乐家的作者们,探索理解与音乐相关的社会行为是如何包含对二中择一的价值体系(为了反对不正常的行为)的积极采纳的。⑩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这一方法开始被运用于研究年轻人的亚文化。 这里为这个研究方法作一个简要的介绍,我想避免浮光掠影地介绍不同研究的许多细节,而将重点集中于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即迪克·海博蒂(Dick Hebdige)的观点。海博蒂名为《亚文化》(Subculture)的著作研究涵盖了朋克音乐在英国的出现和随之出现的亚文化风格,这本书对后来有关音乐听众的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1) 在发展亚文化理论的过程中,海博蒂吸收了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关于普通人的文化的观念。古典主义和保守的研究关注作为美学标准并源于对欧洲“高”文化欣赏的文化概念,与之不同的是,威廉姆斯提倡这一术语的更为社会化的研究角度。这使得文化意指“表达特定含义与价值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艺术与学识,它还存在于社会惯例和日常行为中”。(12) 遵循着这一更少精英主义特质、更具人类学特点的概念角度,海博蒂开始检验文化更加广泛的含义,包括社会行为、意义、价值观、信仰、社会惯例、商品,并考虑这些因素是如何与“整个生活方式”相关联的。他是通过关注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即亚文化,来达到这一点的。 顾名思义,亚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然而,在英国的亚文化理论中,这个术语已经被专门用来指代次要、从属的文化群体。像其他的亚文化理论家一样,海博蒂强调,在英国并非简单地只有一种“文化”。人们个性化的社会经历和他们的文化行为是由多样化的具体因素如性别、种族和年龄所塑造的,此外阶层因素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文化生活应当被认为是由一些地位各异的文化形态组成,并且支配性文化和从属文化是伴随着鲜明的阶层差异被创造出来的。 在这一语境下,独特的青少年亚文化(如穿背带裤的男孩、摩登派和朋克)的出现被视为是对从属社会阶层地位的反映。亚文化理论家们反对保守的犯罪学家和相关政策制定者将这些群体的行为看作异常的反社会行为的观点,他们认为亚文化是处于从属阶层的群体试图争夺主导价值体系的一种方式。青少年亚文化的出现是一种尝试,通过宗教仪式和风格(而非传统的政治行为)去解决他们作为弱势社会阶层所遭遇的问题和窘境。 在采取这一方法时,海博蒂运用了风格的概念来谈论各种元素是如何结合起来产生意义,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向周围世界传达一种生活方式的。他将任意一种亚文化群体的风格进行了概念化的解读,亚文化群体风格由身体姿态、举止与行动、衣着、发型、“行话”(讲话方式与对词语的选择),以及包括音乐和各种商品使用的具体行为组成。在关注亚文化风格的过程中,海博蒂摒弃了之前有关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对比,而在亚文化风格和主流文化风格之间做出区分。这成了亚文化理论中一个关键性的区分,并对许多有关流行音乐的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海博蒂认为,亚文化风格通过一种“有意的”方式与主流风格区别开来,这种方式由亚文化成员制造出来,用来积极地构建一种不同于“大街上的普通男女”呈现出的传统的区别感。一种风格的建立包括已有的衣着、商品、语言、形象、声音和行为规范。通过一种重新定位的过程,这些因素被重新运用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亚文化的意义。因此,一种亚文化风格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不能被孤立地理解。它的意义是在与其他元素的关联中产生的。 在观察亚文化是如何对周围文化的传统规范造成挑战时,海博蒂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的位于欧洲的艺术运动)“激进的美学实践”中发现了相似的情况。在这段时间里,像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和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这样的艺术家们联合起来,将传统意义上不能相容的元素进行并置,试图颠覆常规,破坏中产阶级的传统。海博蒂将此与朋克时代中的听众和表演者的美学实践进行了这样的类比: 就像杜尚的“现成的”被制造出来的物体之所以有资格作为艺术品是因为他选择这样去称呼它们,这是最司空见惯的和不合适的——一根大头针,一个塑料衣架,一个电视机的零件,一个剃须刀片,一个止血棉条都会被带入朋克(反)时尚的领域……从最肮脏的地方借来的物品都能在朋克的整套行头中占有一席之地;盥洗室的锁链被装在一个塑料容器护套中以优美的弧形挂在胸前。安全别针脱离了它们在家庭安全中的作用,刺穿脸颊、耳朵或嘴唇成为令人厌恶的装饰……校服碎片(白色尼龙衬衫、领带)被象征性地弄脏(衬衫被涂鸦,或被伪造成血迹斑斑;故意松开领带)并和可怕的粉色马海毛上衣放在一起……(13) 与这些对已有传统在视觉上的“分裂、瓦解、崩溃”相伴随的,是对舞蹈、音乐唱片和表演主流风格的挑战。舞蹈变成了一种独自旋转的讽刺漫画,并发展成为摇滚音乐伴奏;朋克族采取了一种毫无意义、呆板的、矫揉造作的摇曳步伐或在现场狂乱地像弹簧一样地跳上跳下。 这样的音乐是不优美的,与流行歌手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和“创世纪”(Genesis)这样的“前进摇滚”乐队制作精良的工作室音乐截然对立。朋克音乐是快速的、始终如一的,并基于有限的音乐曲目,依赖于重复的鼓声和“吉他手的密集扫弦”。高声部突出,低音经常被淹没在浑浊的混合音当中,歌词以矫饰的声乐风格和尖叫咆哮的方式唱出,歌词故意表达出对诗歌与传奇故事创作传统的反对。海博蒂声称,朋克以表现“混乱”和“噪音”的方式,将音乐、舞蹈和视觉风格结合起来。这种噪音妨碍和瓦解了传统的衣着、音乐制作和舞蹈方式。 通过指出各种视觉符号和文化实践如何相互作用并集合起来、作为一种与其他风格相异的风格,海博蒂对有关音乐与衣着、舞蹈关系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论证了年轻人是如何积极地运用一系列已有的人工制品,并以此为旧的商品提供新的意义的。 如上所述,早前的作者们寻求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角度理解音乐听众,海博蒂的理论吸收并延伸了这些观点。海博蒂的这本小册子具有重要意义:它影响了有关粉丝的观点;它影响了音乐家们将音乐的和视觉的风格结合起来;它影响了之后的新闻记者撰写音乐风格的方式;它为后来的许多亚文化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模式。考虑到这一点,现在我想从四个方面介绍一下关于音乐听众的亚文化研究:其男性倾向、其精英主义、主流文化问题、同构问题。 亚文化与性别:大街上的男孩 主张性别平等的作者们很快发现了亚文化理论易于忽略女孩和女人的文化行为。就像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所观察到的,穿连体裤的男孩选择了爱德华时代的绅士风格;剃光头的人穿着的夸张的工人阶级靴子和吊带是男性的打扮;女性的朋克族穿着传统的“女性的”吊裤带。当涉及性别问题时,这些引人注目的亚文化看上去并不那么叛逆。麦克罗比认为,由于强调在大街上所能观察到的非常明显的、男性化的文化表达的公共形式,亚文化理论家们忽略了女孩和女人们的视觉风格和音乐实践。不仅如此,他们也忽略了女孩的音乐活动经常是以家庭为导向的,并且不那么明显。(14) 由于将亚文化的公共形象浪漫化,男性理论家们忽视了女性在大街上遭遇的非常现实的危险。由于具有女性卖淫的内涵,在街角过分的游荡可能被看作是对男孩们的性邀请。(15)不仅如此,大街还是一个公共场所,由于这样的内涵也许与性暴力和身体暴力直接相连,大街上的许多女性感觉到被排斥。结果,女孩和女人们经常被强迫转到“不同的悠闲的空间”,而这一空间从亚文化理论的视角来看是被边缘化的或不明显的。 麦克罗比与嘉博(Garber)认为这些更容易在家庭关系网、朋友圈以及年轻人俱乐部等大街以外的场所找到。在这一点上,亚文化理论完全忽略了家庭中的音乐消费。海博蒂甚至没有谈及,在进入公共场所之前,家庭是一个风格合并的场所。他同样没有考虑到在各种动态的家庭关系中聆听音乐的家庭环境。 在指出这些被忽略的问题后,麦克罗比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之间,是否存在消费和使用流行音乐方面的差异?(16)她认为,研究年轻人文化的理论家们应当在音乐活动如何与性别符号及对待性的不同态度相互作用的方式上进一步调整,并在女性和男性气质的观念方面有所改变。 亚文化理论的精英主义 由于觉察到大量的听众成员被忽略,加利·克拉克(Gary Clarke)认为海博蒂的理论是精英主义的,阿多诺的影响依然存在。克拉克认为,通过在积极的亚文化和无差别的被动的主流文化之间做出区分,大量流行音乐听众的实践被忽略掉了。(17)赖瑞·格罗斯伯格(Larry Grossberg)以相似的方式指出,亚文化风格在北美从来没有如此引人注目,结果这导致“大量摇滚音乐粉丝不仅拒绝任何特殊的亚文化身份,同时也拒绝任何出自流行音乐历史记载的显而易见的其他风格。(18) 此外,对亚文化理论中这一类型的关注是从属阶层成员的美学策略。海博蒂关注他们的“艺术”而非任何明确的政治活动;从这个方面来讲,“敌对”已经出现了。亚文化者们提供的“解决方法”最终被描绘成一种“象征性的反抗”形式。然而,许多朋克族活跃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治团体的矛盾并列中。朋克音乐听众经常参与到一些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尤其是试图参与政治活动的反种族主义摇滚运动,而这与象征性的反抗已经相去甚远了。(19)(待续) 本文编译自基斯·尼格斯(Keith Negus)的著作《流行音乐理论导引》(Popular Music in Theory:An Introduction)的第一章“受众”(Audiences)。《流行音乐理论导引》于1996年由英国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联合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Blackwell Publishers Ltd.)首次出版。 ①Adorno,T.(1991)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ed.J.Bernstein.London:Routledge,pp.44-45. ②Adorno,T.(1945)"A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Music",Kenyon Review,11,p.213. ③Adorno,T.(1976)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Music,trans.E.B.Ashton.New York:Seabury Press. ④Adorno,T.(1991)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ed.J.Bernstein.London:Routledge,p.46. ⑤Adorno,T.(1991)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ed.J.Bernstein.London:Routledge,pp.46-47. ⑥Gill,A.(1993) 'Going Belly up with Suede',The Independent,25 March,p.16. ⑦Riesman,D.(1990) "Listening to Popular Music",in S.Frith and A.Goodwin(eds),On Record:Rock,Pop and the Written Word.London:Routledge. ⑧Hall,S.and Whannel,P.(1964)The Popular Art.London:Hutchinson. ⑨Hall,S.and Whannel,P.(1964)The Popular Art.London:Hutchinson,p.276. ⑩Becker,H.(1973)Outsiders: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Glencoem IL:Free Press. (11)Hebdige,D.(1979)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Methuen. (12)Williams,R.(1965)The Long Revolution.Harmondsworth:Penguin,p.56. (13)Hebdige,D.(1979)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Methuen,pp.106-112. (14)McRobbie,A.(1980) "Settling Accounts with Subcultures:A Feminist Critique",Screen Education,34,pp.37-49. (15)McRobbie,A.and Garber,J.(1991) "Girls and Subcultures",in A.McRobbie(ed.),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London:Macmillan,p.5. (16)McRobbie,A.(1994)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 (17)Clark,G.(1990) "Defending Ski Jumpers:A Critique of Theories of Youth Subcultures".In S.Frith and A.Goodwin(eds),On Record:Rock,Pop and the Written Word.London:Routledge. (18)Grossberg,L.(1987) "The Politics of Music:American Images and British Articulations",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1,1/2,p.149. (19)Gilroy,P.(1987)There Ain't no Black in the Union Jack.London:Hutchinson; Widgery,D.(1986)Beating Time.London:Chatto & Wind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