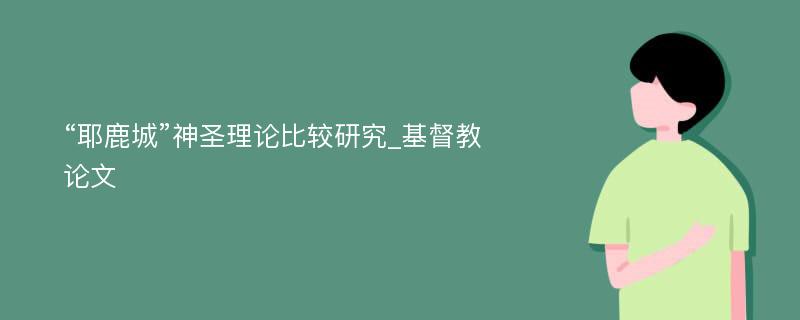
耶儒成圣论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儒成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4-0115-05
人能否成圣?基督教和儒教都给了肯定的回答。《旧约》中上帝说:“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利未记》11:35)这宣告了人成圣的可能。儒教“内圣外王”等理论,解决的是人如何成圣的问题。但是相同的肯定回答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产生涉及“上帝/天是什么?人是怎样的?天与人的关系如何?人是否、如何通过超越而达到与上帝/天相齐的至善成为圣人?”等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体现出耶儒成圣论的差异。
一、入圣之门:上帝与罪人
基督教的成圣理论建立在上帝观念的基础上。上帝是什么?或上帝是怎样的?根据《圣经》及相关文献的论述,上帝的性质大致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人类的创造者,人类一切的道德根源和伦理规范的合理性,以及完善之圣人的可能性和标准都来自于上帝。其次,上帝是全善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类的规定性是来自上帝的,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应该有着上帝的禀赋。上帝全善的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设定上帝是全善的,才能说明人为什么要向善。也就是说,上帝的全善为人类追求善、成就圣人提供了方向和动力。第三,上帝是慈爱的。因为上帝的慈爱,有罪之人摆脱罪恶、渺小卑微经常犯罪的人类革新向善才有了希望。同时,也为所有的人提升自己、成为圣人提供了希望。第四,上帝是高于人类的“超越的存在”。上帝所处的高度不是一般的人所能企及甚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上帝是全善的,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按此逻辑,人的应然状态是善的。然而,现实中的人时常为恶,基督教教义解决这一矛盾的理论就是原罪论。上帝创世、始祖犯罪、耶稣基督舍身为人类赎罪构成了人之形成的三个基本环节。
人是上帝创造的,《圣经》开篇即为创世记。上帝以“言”创世,分六天造好了宇宙万物,包括人。从逻辑上讲,上帝创造了人,上帝就是创造者,人是被创造者。被创造者的属性是由创造者决定的。上帝是全善的,他的意图是善的,创造的手段也是善的,因此,被上帝创造的人也应该是善的。支持这一点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出自《创世记》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另外,在五章1、2节说:“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九章6节:“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人因为具有了上帝的形象,所以人必然是善的,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那么后来的人为什么有罪了呢?这罪来自哪里?上帝刚创造出来的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和作为世俗人的我们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源自于人类原罪。在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之前,其本性是善的;偷吃智慧果之后,才犯下了原罪。所以,与始祖不同,后人一出生就有了原罪,就是罪人。
原罪是因为人类乱用了自由,做成了违逆上帝的事,而人本性与上帝是合一的,因此,也是做了违逆自己本性的事情。人类因违逆而破坏了自己善的本性,也就成就了恶。被破坏了的人的本性,成为人类社会恶的起源。人性的亏欠,也使得人无力自补,没有了达到全善的能力,无法找到自己善的本性了。人有了罪性,便可能在生活中犯下本罪(与原罪相区别)。
始祖犯下的罪,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后世,使他们有罪。这两个途径一是“种族的遗传”,一是社会的影响。人不能脱离社会,人生活在一个关系网中,一个人犯罪,必牵连到其他人。因此,人类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消除原罪,亦无法克服犯下本罪的可能。
如果上帝的创造物——人就这样沉沦罪孽,上帝的创世工作就没有意义了。上帝是爱的,不会让人类就此堕落下去,因此,上帝“二次造人”,把自己的独子送到人间,用他的宝血为人赎罪。上帝再次造人,是以圣灵的形式,把自己降临到耶稣的人性中,这就使得人又有了向善、为善、成善、成圣的可能。
那么人如何成圣呢?坚守“爱、信、望”三德,认罪忏悔,跟随上帝的旨意,做全善的事工,就可以成为圣人。只要爱上帝才会有积极的态度来服务天国,以真挚的心灵来爱自己的邻人和仇敌。只有信才会主动地虔诚地投向上帝的生活,寻找上帝的启示。只要对天国怀抱希望之心才会勇敢正视自己的罪和社会的黑暗所带来的磨难,坚定走向上帝,成就自己的圣德。然而,最终,上帝之门只有靠上帝之手才能开启,人是不能独自打开成圣之门的。
二、为圣之基:天道与人性
与基督教的上帝相对应,儒教的终极实在是天。儒教的天有自然之天、神灵之天和伦理道德之天三种含义。自然之天有几种含义:一是指自然存在的天体、天象和气象,如“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荀子·天论》);二指自然规律,即自然如此或应该如此的天道、天理,各种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法则,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三指天然,即没有后天的人为造作加于其上的事物之天然状态或本然状态,如“牛马四足,是为天;落马首,穿牛鼻,是为人”(《庄子·秋水》),神灵之天指的是主宰世界的至上神,也常以“帝”称之。这个天有几重含义:首先,天是创造万有的存在,也就是说,天是世界的创造者;其次,天是法力无边、不可战胜的存在,有着人类想象不到的智慧和能力;第三,天是至善而公正的,是世间善恶的监督者奖惩者,“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他以祸福的形式,来行使道德赏罚的职责;第四,天是命运的主宰,天命不可违,人应顺天命而行。伦理道德之天的含义也有几个方面:第一,天是伦理之天,即有其完善的结构和运行规则,而这种规则是至善至美的,因而是人间伦理道德模仿的原本。董仲舒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见《汉书·董仲舒传》),程氏所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尧舜之道也”(《程氏文集》卷一),强调的都是天的伦理性质。第二,天是道德之天,即天具有至善至美的品格。儒家认为它生生不息,化育万物,具有“仁”的品德。《易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思孟学派所谓“诚者,天之道也”,“知性则知天”,宋明理学家认为天道“廓然大公”,主张人亦能效法天道,去私无我,达到浑然与物同体、与天为一的境界,都肯定了天的道德性。在儒教中,自然之天、神灵之天、伦理道德之天是三位一体的。自然之天是人可感知的天的外在形式,人可以用感官去感知;伦理道德之天是天的基本属性,人可以用心灵去体悟;神灵之天是天的不可知的神秘之处,人只能去尊崇、敬畏和信仰。
儒教意义的天是继承周的天帝观而来的,并在后代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周人的天,是至上神;人的命运,是由上帝来安排的。当人尽到了责任,讨得上帝的欢心时,就能得到福禄和好运,反之,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周人敬畏上帝,但并不完全依赖上帝,而是把得天命、得福禄的根本途径寄托在人事,即“以德配天”,周公言:“皇天无亲,以德是辅”(《尚书·仲裁之命》)。上帝不会根据奉献牺牲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而是根据人的德行有无来降福降灾。这样一来,天的道德性被凸显了出来,天成了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的道德实体。所以,人要得到上帝的宠爱,只有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做起。要做天子,就要“明德修身”“明德慎罚”“敬德保民”。自此,古代宗教摆脱了重祭祀、重鬼治的倾向,开始走向重人治、重德行的人文宗教。在孔子那里,这一宗教人文化的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①
孔子之后,儒教开始明确打通天和人、天道和人性。《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天与人、天道与人事联系在了一起。孟子则直接把“天道”和人的“心性”连结起来,倡“天道”、“心性”一贯之说,更是推进了儒教人文化的进程。在孟子那里,天还仍然是一种人格之神。《孟子·万章上》记载了孟子和其弟子万章关于天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孟子对天的基本观念。焦国成教授认为这段话有几个基本的观点:第一,天有类似于天子、诸侯的人格,它有自己的意志,可以拒绝或接受天子所推荐的人。所谓“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有天下,乃“天与之”。第二,天不言,只是以行与事示人。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就是接受的表示,反之,则是拒绝。第三,天无形,以民众的意志为天的意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1](P76)。孟子强调了民意的重要性,但仍然承认天是人格神。
汉儒和宋明理学对儒教的天观做了继承和进一步的改造,把天和人直接联系了起来。尤其在宋明理学看来,天与性、理、气、道等是同等的概念,人性与天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人性就是天道,天道就体现在德性中。由宋明理学开启的道德形上学的传统,直接用人来关照天,从人事入手来体贴天道,把天塑造成一个至善的道德的来源。而这种对天的界定其实也在同时界定着“人”。所谓“心即性”“性即理”等等命题表明,心学、理学、道学界定天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确立。因此,此后儒教思想中更是把心性,尤其是本心、本性等概念发扬到了天道的高度,成为可与天互用的概念。儒教本是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的体系,儒教的天本来就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再加上宋明理学吸收佛家的思想,努力构建起心性形上学体系,使得心性等概念由人而发,人理变成了宇宙的原理。
人性与天打通一气,也就意味着人性必然承接天道,成为至善之存在。所谓知性知天,便建立在人性与天命、天道统一的基础上。人性与天道合一,从率性、知性到知天,这个过程在逻辑上是很完满的。由此,在实践上,人根本没有必要到自身之外寻求所谓的天道。天道与人性的合一,是合在了人之内,而非外在于人。所以儒教认为,天道是内在于己的;反求于己,便可知己知天。因此,儒教的伦理便直接以人为核心,天道的标准实质上直接就是人性的标准,人性直接就是天道的承载。成圣便可直接返回自己的本性,并将本性扩大推广出去,至于兼善天下的境地。
三、成圣之路:待上帝与求诸己
“圣”是基督教和儒教对理想人格的称谓,“成圣”也是二教对教徒的一致要求。耶儒二教均认为“圣”是每个人应该能够达到的最高的道德境界,要想达到这个境界需要人付出很大的努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第五章讨论了教徒成圣以及成圣的普遍性问题,他们坚信,耶稣作为一起圣德的起始者和完成者,对所有身份的所有信徒,都宣布了生活的圣德。一切信徒,包括平信徒和更为宽广慷慨的灵魂,都应当可以响应上帝成全、成圣的召唤。因此每个信徒要努力响应上帝的召唤,以耶稣为楷模,发挥牺牲精神,成就圣德。儒教更是肯定每个人成圣的可能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但这仅仅是从可能性而言的,从现实性来讲,要做到圣和仁是很难的,孔子尚且不能,何况他人?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这不仅是孔子的自谦之词,也道出了为圣之难。
对应于耶儒二教成圣论的相同之处,发掘二者的不同之处是更有意义的工作。概括起来,它们的差异突出表现在成圣可能性的根据、圣人的标准以及成圣的努力方向三个方面。
首先,成圣可能性的根据不同。基督教成圣可能性的根据是上帝的恩典,儒教的根据是人性自身。
基督教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其成圣的核心在于人期待着神的拯救。人需要努力向善、为善而成圣,但这些努力的前提是对上帝的爱、信仰与希望。因为上帝是全善全能的,人是有罪的,有罪的人与全善的上帝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对人而言,这条鸿沟是不可逾越的,确切地说,是永远也不可能从人这一方面跨越的。只有依靠上帝的力量,等待上帝的恩典,人才能得到跨越鸿沟走向理想状态的能力和道路。要成为圣人,只能依靠上帝的眷顾才能够实现。如果上帝遗忘了一个人的存在,救赎就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更谈不上成圣。所以杜维明说:“人作为一种被创造物是根本不同于作为其存在之终极依据的上帝的。说人可以通过自我努力,无须经历一场信仰的飞跃,就能够同造物主合成一体,这在犹太—基督教框架中,如果不是亵渎神明,也是十分新奇的。”[2](P6)因此,在基督教这里,说人之成圣的可能性来自上帝,确定的说,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存在本身并不直接为一个人的成圣提供机会,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为人的成圣提供可能。
儒教伦理以人为目的和归宿,人的本性与天道齐,所以人直接就是道德的根据和来源,完满人性就是成圣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之成圣可能性最充足的根据。儒教关于人与天齐的理论,实质上论述的是人与人齐——人向人的本性的回归。所谓成圣就是实现人性,实现人性就是扩充自己的本性到大我的程度,也就是达到与天合一的德,所谓与天合一就是要充分实现自己的人性。这个过程是以人的本性开始,通过自我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但这个境界,实际上也是人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如此一来,人在自身之中就可以完成由人到神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就是反求诸己的过程。天的作用,只在于为人性提供善的内容。对人的信仰和修身而言,天作为超越的存在,已内化为人了。
其次,“圣”的标准不同。基督教之圣人,永远是罪人而无法企及上帝;儒教之圣人,只不过是完满实现本性之人。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全善全能,而人是有原罪,人性是有亏欠的。因为人与上帝的性质决然不同,所以,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人是无法企及上帝的,人也无法与上帝交通。人与上帝的交往需要借助一个中介——耶稣。耶稣是神,也是人。一方面,根据三位一体理论,耶稣是以上帝之子的身份降临于世的,他来自上帝而具有了全善全德;另一方面,耶稣降世为人,有人的肉体和感情,有人的局限,因此他可以给人类提供行动的榜样。耶稣的存在,可以为人与上帝之间架设一条桥梁。但正是由于这一桥梁的存在,彻底割裂了人与上帝同一的可能。人所能做到的,只能是耶稣式的人,而不可能成为耶稣式的神——上帝。成圣只能效仿耶稣作为人的行为,上帝式的人是不存在的。
而在儒教看来,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至善境界。神与人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但该距离并非大到不可逾越。由于人人都具有纯然的本性,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圣。只要做到率性而为,开启显发自己的本性,就能够完成内在超越,成为有道德的人。对于人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儒者根本不加怀疑。人必然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达到天道,这是儒教人性观中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儒教设定的圣人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脱离了人的某种实在。只是这个人并非实然状态的普通人,而是应然状态的本性之人。另一方面,应然状态的本性之人因与天齐,因此“圣人”能够与天地同流、与天为一,也可以说就是天、神。
孟子提出所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提出所谓“涂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提出所谓“满街皆是圣人”等等,都充分表明了人完全可以成为圣人。这是儒家或儒教是对人的基本看法,它表示了对人的基本肯定。圣人之性即人之本性,即天道之性,儒教之圣,是与天合一的“圣”人。而依据基督教教义,不可以直接地说“人人皆可以为上帝”,也不能说“人人皆可以为耶稣”,而只能说“人人跟随基督”。人永远达不到上帝之善的高度,基督教之圣只能是远离神圣境界的圣“人”。
第三,成圣的努力方向不同。如果说基督教成圣论给人提供的努力方向是向外追寻,那么儒教提供的方向是向内反求。
在基督教看来,上帝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善的归宿。另一方面,与上帝的至善相对应的是罪恶的人生,这就使得人与上帝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人要追求至善,就需要向上——上帝——寻找来源。而单凭人的追寻是无用的,拯救的主动权把握在上帝手上。因此,一个人要想赎罪而成圣,就必须等待上帝的爱从空而降。人去罪成善、获得拯救、成就圣德的力量是由上帝发出的,是由神给予人的。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人要成圣,要追求至善,必须向外——己之外的上帝——努力。
如果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一语来分析,似乎儒教论证人性本善的思路是从上而下的模式。因为从天命下来成为性,而性又与道相联,天和道都是善的,所以性也就是善的。但是,因为儒教在修养和教化方面要培植人的善性,所以必须承认天赋的良心是善的。儒教实质上是从论证的目的而反推论证的思路。
儒教论证人性本善的另一种思路,更能体现儒教的本质。这可以称为自下而上的路子,即孔孟的“仁义内在”的路子。孟子的“四心”说就是这一论证思路的代表。所谓尽心即可知性、知天,人的本性即是天的本性,因此,只要按照人的本性去做,就能达到天,知晓天。《中庸》由己而推天道,也是这种思路:“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由于人人都具有纯然的本性,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圣。但有些人之所以达不到最高的境界,不能够跨越人与天之间的距离,原因只在于他们没有真诚地去追求,反而时常被世界中的种种诱惑所吸引,偏离了追求神圣的大道。因此,人只要认清本性,做返身求己的努力,从人自己的本性出发塑造人格,就有可能与神同一,达于至圣。人成圣只要向内——内在于己的人性——努力即可。
耶儒成圣论的不同不仅仅是理论的分歧,而且造就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民族伦理和民族精神。西方人经常说中国人太骄傲了,认为自己能成为圣人。中国人会觉得西方人太消极了,什么都等待上帝的安排。但是,这样的判断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解读。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成圣理论强调一份谦虚的心,这在人处于顺境的时候尤为可贵;而儒教的成圣理论给人一份向上的心,尤其在困境之下,需要人有一份自信,去完善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人。
注释:
①应该肯定,孔子还是承认主宰之天的存在的,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论语·季氏》),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等等。这些关于“天”的论述,通常被当作后人讨论儒教成立与否的根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立场的不同也造成了解释的不同。而此不同是来源于孔子对天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我看来,孔子对人的重视并不能说明他否定了天,而只能说他存而不论。而这种不论也是建立在一个对天的信任上:天与人不是冲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