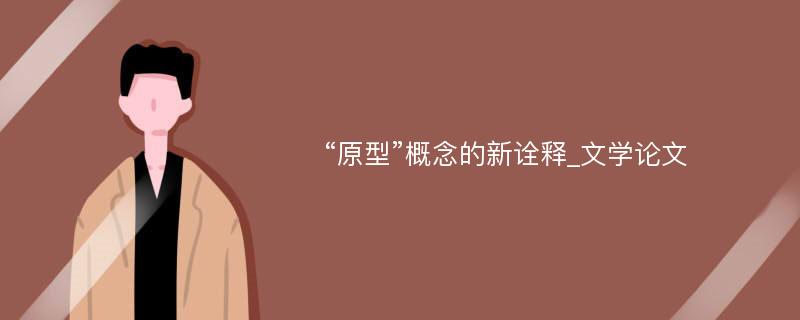
“原型”概念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型理论在国内外都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国内在理论本体研究方面尚不够充分,一些学者对其理解尚不够深入,批评实践中用之不当和用之无用的现象还常常出现。国外一些著名的理论家们,如荣格、弗莱等人,对其阐释虽已相对系统,但他们的理论内部都存在着某种偏颇和弱点,这就使原型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发挥。相对而言,把原型理论与其它文学批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批评家们却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同时也昭示出原型理论的真正潜质及其理论本质。因此,对“原型”的概念本质进行新一轮的界定和阐释,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批评实践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原型”概念的多种阐释
概念是对内涵的界定,也是揭示本质的基点。每一个试图借“原型”一词建构、发展自身理论或进行批评实践的学者都必须言明自己所采纳的具体阐释。到目前为止,对“原型”概念所做出的界定已有多种。遗憾的是当这些概念进人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和批评实践时,其各自的弊端便显露出来。
根据荣格对原型的界定,“原型”(archetype)一词又被译为”原始模型”或“民话雏型”(转引自叶舒宪 98)其词源出于希腊文的“archetypes”一词,意义为“原始的或最初的形式”。他指出:
原型一词最早是在犹太人斐洛谈到人身上的“上帝形象”时使用的。它也曾在伊里奈乌的著作中出现,如:“世界的创造者并没有按照自身来直接造物,而是按自身以外的原型仿造的。”在《炼金术大全》中把上帝称为原型之光,这个词多次在狄奥尼修法官的著作中出现。例如在《天国等级》第二卷第四章中写到“非物质原型”以及在《天国等级》第一卷第六章中写到“原型石”。原型一词未见于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但文中是有此涵义的。例如他在《杂说》第八十三条中写道:“主要观点虽未形成……但确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中。”原型这个词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形式,为了我们的目的,这个词既适宜又有益,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这些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并关系到古代的或者可以说是从原始时代就存在的形式,即关系到那些亘古时代起就存在的宇宙形象。列维-布留尔所用的“集体的表现”一词是指那些世界的原始观念中的形象符号,但也同样适用于无意识的内容,因为它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事物。(荣格 53)
并且,“原型”一词“在神话研究中它们被称为‘母题’;在原始人类心理学中,它们与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现’概念相契合;在比较宗教学的领域里,休伯特与毛斯又将它们称为‘想象范畴’;阿道夫·巴斯蒂安在很早以前则称它们为‘原素’或‘原始思维’。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的原型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和毫无凭据的,其它学科已经认识了它,并给它起了名称”(荣格95)。1922年他又明确提出:“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无论这种形象是魔鬼,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过程),它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神话形象,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些意象时,我们发现,它们为我们祖先的无数类型的经验提供形式。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荣格 120)。到了1936年,他进一步指出:“原型概念对集体无意识观点是不可缺少的,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普遍地存在着”(荣格 94)。
可见,“原型”一词在内涵界定和运用范畴上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无定论可言。这就使它成为一个可塑性非常强的词汇,理论家们都可以对其进行新的阐释,从而使之成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要素。弗莱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把“原型”这个概念赋予新的解释后纳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弗莱对原型概念的界定和说明也有多次,并且每次都有所补充。在阐述神话相位时他指出:“在这个相位中的象征是可交流的单位,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原型(archetype):它是一种典型的或重复出现的意象。我用原型指一种象征,它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弗莱 99)。在同一本书中他继而指出,“如果我们不承认把诗与诗联系起来的意象中的原型的或程式的因素,那么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而获得任何系统的脑力训练是不可能的”(弗莱 101)。“在文学的一端,我们有纯粹的程式,……在文学的另一端,我们则有全然的变异,在这里有对新颖或新奇的有意尝试,结果产生隐蔽的或复杂的原型”(弗莱 105)。至此我们发现在弗莱这里“原型”一词的意义越来越等同于“程式”。同样的观点在他的其它著作中也有所阐述:“关于文学,我首先注意的东西之一是其结构单位的稳定性。比如说在喜剧中,某些主题、情境和人物类型从阿里斯托芬时代直到我们今天都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保持下来。我曾用原型这个术语来表示这些结构单位……”(转引自叶舒宪 101)
在弗莱这里,“原型”是在传统的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为人们所熟悉的一切程式化了的可独立进行交流的文学单位。显然弗莱的“原型”定义与荣格及其以前的理论家笔下的“原型”定义有一种质的差异,它已变为有理性掺杂其中、有程式可以捕捉的概念,其指向是具体的文学现象。
然而“原型”一词的含义并没有就此形成定论,费德莱尔也对“原型”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他说:“我说的原型是指由观念和感情交织而成的一个模式,在下意识里广泛为人们理解,但却很难用一个抽象的词语表达,同时它又是那么神秘,不经过周密的考察是完全无法分析辨明的。这种复杂的心理情结需要通过某种模式的故事,即体现它又象是掩盖它的真正含义;待到它的原型意义被分析出来,或者根据表达它的语言找出了它的寓意之后,整个奥秘才会昭然若揭”(转引自蓝仁哲 170)。我们可以说他对“原型”的解释和界定比荣格和弗莱都有优长之处,可谓“原型”概念的最佳定义。
在荣格那里,“原型”是一种原始经验,这让人难以把握;而在弗莱那里“原型”又几乎变成了纯粹的模式;在荣格那里它是完全内在的,因而是不可捉摸的,而在弗莱这里又变成了完全外化的,条分缕析的;在荣格那里是复杂得近乎神秘,在弗莱这里又过于简单,一切故事都可以纳入到相应的模子里去,文学变得千篇一律失去了色彩和生机。费德莱尔的概念首先承认“原型”是一种复杂的神秘的难以用抽象的词语言说的模式,同时这种模式又是由观念和情感交织在一起的。
这样,人们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把握的,即“原型”中蕴含着我们的观念和情感,它与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和感受联系在一起。荣格又指出,这种复杂的“原型”要通过模式化的故事表达出来,这就是弗莱所说的模式。显然“原型”不等于模式,模式是“原型”借以表达出来的途径,“原型”本身是观念与情感的交织。情感可以是非理性的难以言说的而观念却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因而费德莱尔的“原型”概念是“原型”批评得以走向综合批评的关键一步。后来“原型”批评实践的发展也证实他对原型的理解和界定要比弗莱更高明一些。
二、“原型”的本质特征
对“原型”概念的不同阐释如此之多,直接造成使用中的混乱。简单地接受其中的某一种并将其教条化为定论,是完全有悖于“原型”理论的批评宏旨的,更抹杀了“原型”理论应有的方法论价值。因而要想在当下的批评环境中有效地统理这些千差万别的阐释,使“原型”理论成为更有效的批评手段,我们首先需要对其基本特征进行一番综合考察。在这方面,荣格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一方面,“原型”具有无限共时性。荣格曾指出:
英国人类学学会的一位前主席曾问我:“你能理解何以像中国人这样高智力的民族没有科学吗?”我答道:“他们有科学,但你不理解它。这种科学不是建立在因果性原则之上的。因果性原则并不是唯一的原则;它只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东方人的思维与他们对事实的评价是建立在另一种原则之上的。对于这种原则,我们甚至还没有相应的称谓。东方人当然有表示它的词,可我们并不懂得这个词。东方的这个词就是“道”。……你终于明白:“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用另外一个词去指称它,但仍嫌这个词不够味。我把“道”叫做“共时性”(synchronicity)。当东方人察看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他们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西方人的思维却将其分解为很多实体与微小的部分。(荣格 72-73)
在这段对话中荣格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关于“道”的观点的认同和借鉴,原因在于他在他的“原型”和“道”之间找到了很多共通的东西,即整体观念。他对“原型”的分析方法与中国人对“道”的理解是一致的,都把它看作一个非实体的整体而不是实体的微小部分。对于“道”,我们只能说它可以是任何东西,而不能说它是具体的哪一种东西,“原型”也一样。我们可以说“原型”包含人类的一切心理经验,却不能说它是具体的哪一个形象。“原型”一词的这种整体观念实际上所描绘的是蕴含一切的原初状态。他又讲到:“这是事物的原始状态,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是永恒对立元素的统一。冲突已销声匿迹,万物平静,再一次回到最早的无差别的和谐之中。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理想的状态被称作道,它就是天地之间的完美和谐”(荣格 129)。可见“道”与“原型”的共通之处在于:整体的共时性,即整体状态中包含着一切。
把握“道”和“原型”的共同点,我们更容易理解“原型”一词的本义:原型——原初的状态,蕴含一切又能幻化为一切。
另一方面,“原型”具有恒久历时性。恒久历时性指“原型”能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和具体的个体事物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种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态,即形成它的置换变体。对此荣格指出:“由于它是原型,它就具有历史性一面,我们不懂历史就不能理解那些事件”(荣格 176-177)。那些历史事件正是“原型”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一次又一次复现,人们只有将历史贯通起来做整体的把握和研究才能发现“原型”。同时,“原型”具有强大而广泛的力量,它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无论大事小事中时时处处地存在着。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有它的影子:“当然,我们不能把法西斯或希特勒主义当作观念,它们是原型,所以我们说:把一个原型给予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就会一致行动,任何力量都不能抗拒它”(荣格 178)。显然荣格认为战争中的德国民族处于一种“原型”的控制之中,这种“原型”是当时德国具体的历史环境所激活的沉潜在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由此一种类似于完成天赋使命的冲动控制了整个德意志民族。这种“原型”显现出的具体形态就是所谓的法西斯或希特勒主义,“原型”被投射到这个民族身上,使他们相信自己具有某种神的使命或神的力量因而发起近乎疯狂的运动。同样,“原型”在生活中称不上“事件”的地方无处不在。荣格说:“把一长串原型记得烂熟于心是毫无用处的。原型是经验的集结,它们像命运一样降临在我们头上,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最个人的生活中被感觉到”(荣格 81)。荣格对“原型”所作阐述的科学成分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具体事物都不是“原型”,所有的事物只是蕴含着“原型”。“原型”历尽岁月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条件相互结合从而呈现出具体的形态,它永远只是具体的“这一个”而不是那变幻无穷的“原型”本身。
荣格其实对“原型”一词进行了十分深入而精到的分析。遗憾的是,当“原型”概念被纳入到他的分析心理学范畴时,对于其它学科的人们来说它变得越来越无法驾驭。荣格说:“现代人在体验这原型的时候,慢慢地知道了那最古老的思维形式是一种自主的活动,人们便是这一自主活动的对象”(荣格 89)。“原型”甚至可以“与一切理性和意志相对抗,或者制造出一种病理性的冲突,也就是说,制造出一种神经病”(荣格 100)。“它在梦中的象征里表现自己,或者说它被梦中的象征陪伴着,这些梦中的象征与‘集体的表现’有着联系,而‘集体的表现’自最远古的时候开始就以神话主题的形式描绘着精神的历程”(荣格 93)。这就使从事文学批评实践的学者们很难在其原型理论指导下进行真正可行的、有效的批评。
与荣格相反,另一位伟大的“原型”理论家弗莱对于“原型”概念的阐述,正如我们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把“原型”变得过于容易把握,干脆成为了类似于“类型”的模式。其实,弗莱在其批评实践中形成的这种客观结论并不符合他的初衷。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一直力图建构一种伟大而恢宏的批评体系,希望通过“原型”可以把握文学整体。而过于近似于“类型”、“模式”的“原型”内涵,显然无法实现这一伟大的批评宗旨。
三、“原型”概念新释及其理论意义
荣格和弗莱都在“原型”内涵的阐释上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同时他们也犯了性质相同的错误。一方面,他们意识到“原型”一词所独具的无限深广性,另一方面却狭隘地把它纳入到某个学科领域。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这样指出:“本书涉及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技巧和方法,其中多数是在当代学术领域中已经使用过的。……本书无意抨击任何一种批评方法,只要它的课题是明确的;本书所要推倒的是这些方法之间的围栅。这些门户之见的围栅,易于把批评家局限于某一种批评方法,这是大无必要的,并且它们倾向于同批评之外的各种学科去建立其基本的联系,而不是同其他批评流派去建立这种联系”(弗莱 448)。弗莱比其他文学批评家伟大,他乐于打破不同的批评流派间各执一辞的狭隘局面。可同时,他又反对文学理论家将文学批评与其它学科结合起来,这便是他所持有的另一种偏狭。
他们二人都未能捕捉到“原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而形成的那种类似于“基因”的特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恰恰是“原型”最根本性的价值所在。“原型”最初蕴含的所有成分都会在拥有它的那一个民族的文化进程中永远起支配作用。同时,“原型”因此而具备了与其它多种理论乃至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达成更有效更博大的文化批评的能力,这一点已为近年来“原型”理论在国外批评界的运用走向所证实。越来越多的批评流派由于与之相结合而走向综合性文化批评。“原型”批评与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读者接受和反应理论以及现象学和阐释学相结合,在各领域都取得了创造性的批评成果。“原型”批评与其它理论的结合不仅仅表现为两两结合的模式,在它的统率之下多种理论相互结合的批评态势日趋强劲。“原型”批评正呈现出多元结合的文化性批评模式(注:参见叶舒宪:“破译与重构:原型批评的发展趋向”,《上海文论》(1992)21,29。)。
至此,“原型”一词有必要被赋予一种新的解释。“原型”本质上是人类早年经历中所蕴含着的后世一切文化的基因。它是一种尚未明确整理的非抽象非概念的感觉世界,因而更多地体现为无意识状态。并且由于生产力和个体能力所限使人类先民的生存(包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的漫长历程)以种群意识为意识主体,这种无意识也就带有更强地集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荣格把“原型”界定为一种沉积而成的集体无意识是有道理的。
对“原型”的内涵做出这种新的阐释,对于文学批评理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裨益:
首先,区分“原型”与“象征”、“意象”、“模式”、“神话母题”和“仪式”这一组概念不再困难。
从本质上说,“象征”和“意象”更为接近,正如弗莱所说“意象是一种象征,通常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被当做是整体文学体验的一部分”(弗莱 365),都需经历一个抽象的过程。当我们说某一形象或色彩或某种文学因素是“象征”或“意象”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经历了一个将其蕴含之意约定俗成的过程,无论它如何隐晦,也是在人们首先明了或基本明了了一种感受之后,而将其寄托在此一载体之上的。可以说“象征”和“意象”本质上是对一种明确的心理因素的委婉表达。而“原型”则不同,它的最大特点在于蕴含丰富。比如《旧约》,作为对西方文明源头的最为原生态的记载,其中究竟蕴含着多少东西,我们已言说了无数个时代,而今依然无法穷尽。此三者的第二点区别在于,“原型”绝不是一个形象或几个形象,更不是简单的“钟”“鼓”等寄托了人类某种情怀的事物可以充任的。“原型”朴实无华,它描绘着一切,那就是生存,就是人类,就是历程,也就是本质:人类的本质,生存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它不是具体形态,自然与“模式”更不类同。其实,最易与“原型”相混淆的概念内涵是“仪式”和“神话母题”,这一点在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金枝》中弗雷泽用了大量篇幅讲述阿都尼斯神话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存在现象,从而证明这一神话超越民族的文化价值。从这三个概念都具有文化广度与深度这一方面来看,它们极为接近。然而,它们之间仍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异,那就是表与里、狭与广的关系。“仪式”作为行为模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其中蕴含的就是“原型”。并且从“仪式”中所能挖掘出的最为深广的价值内涵也止于“原型”,因为我们已赋予“原型”以终极性的文化定位。另一方面,“原型”是“仪式”的终止意义所在,而“仪式”却不是“原型”的唯一载体。同样,“神话母题”也只是我们可以把握“原型”的最基本的一种固化了的语言形式,而不是“原型”本身。“原型”本身既不是具体事件也不是具体的文学模式或行动模式。我们理解“仪式”和“神话母题”是要与其中的“原型”对话而不是与创造神话和仪式的人或神话与仪式的具体模式对话,因为“仪式”和“神话母题”所呈现的一切固态形式都只是“原型”所包蕴的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它们本身也仅是所有“原型”载体的一部分而已。
其次,区分“原型”批评与“神话”批评也更容易。我们必须承认,“原型”批评的着眼点与“神话”批评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向人类先民早年经历来寻求对人类的本质发现,从而来说明文学世界的种种现象和种种变迁的根由所在。但另一方面,弗莱曾指出:“有关原型的研究是一种文学人类学研究,它关涉到那些诸如仪式、神话和民间故事所提供的前文学种类”(弗莱 333)。由此我们知道,有关“原型”的研究,并非只与神话有关,而是与仪式神话及民间故事都密不可分。这说明原型批评的定位却在于人类早年的种群经历和种群意识,它要关注一切富含这种意识的事物,因此就不仅仅要对神话进行研究,还要把人类早年各种文献,即所有记载人类早年经历的资料都拿来为己所用。它作为文化研究,其关注点是人类早年实实在在的经历和先民对其所做的实实在在的记录,而非神话这一个方面。而“神话”批评的定位是在神话,重在发现神话中蕴含的一切价值,由此出发达成解释人类早年神话内蕴价值的目的。“原型”批评不等于“神话”批评,也没必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另立“神话——原型批评”之名。
再次,将“原型”的本质定位为文化因子有助于我们接受一种对世界文化圈进行划分的新的标准和结论。既然人类早年经历富含后世文化最原初的因子,文化圈的划分就应基于人类早年种群意识的不同而分野。同时,我们前面已经阐明,这种人类早年的种群意识直接来自于他的经历,经历的特殊性便决定着文化因子的独特性。进一步推理,人类先民的活动和经历直接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自然条件恰恰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种群意识:自然条件优良的“人定胜天”型;自然条件平常的“天人合一”型;自然条件恶劣的“原罪救赎”型。这既是“原型”的第一层级的划分,同时也是世界三大文化圈的划分。
最后,“原型”批评由此可定位为文化批评。对“原型”的审察视角是文化层面的,而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因而,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原型”批评其立足点也不可局限于文学范畴之内,而应定位为文化研究。弗莱和荣格二人以及他们之后对“原型”加以界定和使用的学者没有给予“原型”以足够的施展空间,这使得“原型”批评或者走向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神秘境地,或者走向文学模式的僵化陈列,或者走向个别文学形象的意象诠释。“原型”批评的真正价值未能得以充分实现。“原型”——凝眸人类本根的理论工具,我们已经发现了它,只有打开广阔的视野,才能真正发挥其不同寻常的深广价值,它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的导引,同时也是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乃至宗教等学科的研究走向文化批评的导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