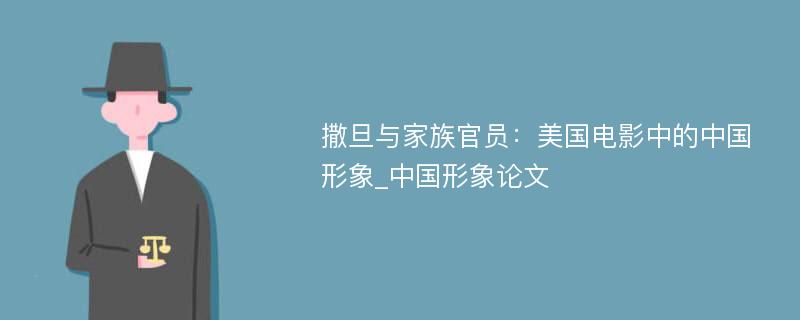
撒旦与家臣——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臣论文,撒旦论文,美国电影论文,形象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目前看到的最早一部华人形象剧情片《华人异教徒与周日学校教师》(The Healthen Chinese and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s,1904,缪托斯科普—比沃格拉夫公司)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百年间,好莱坞制造了数百部华人形象影片,而所有华人都被描述成两种刻板形象(stereotype):“魔鬼撒旦”与“奴仆家臣”。尽管华人形象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但无论在哪个阶段,负面的华人形象都逃脱不了以傅满洲原型的“撒旦”形象。他们与生俱来地怀揣攻击美国土地、政体、女性的丑恶目的。这类故事总被描绘为正义与邪恶之战:即如果不是英勇的白人英雄赶来阻止,华人阴谋家就即将得逞,白人的和平世界行将灭亡。而正面华人形象——即使寥寥可数——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听命、服从。从20世纪30年代的查理陈到70年代的李小龙,再到90年代的成龙、李连杰扮演的角色,都自甘为美国政府效命,成为名副其实的“家臣”。撒旦形象在美国电影史上曾经两度辉煌:一、从电影诞生之初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了坚决拥护排华法案,同时也为了神化美国殖民野蛮中国的合理性,华人形象被描绘为威胁美国安全的“黄祸”撒旦。二、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红色中国成为美国的恐惧之源,华人从生理属性上卑劣的“黄祸”演变为意识形态上疯狂的“红祸”撒旦。
同时,家臣形象也经历了两个高潮:一、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末,美国在二战中扮演世界救世主角色,华人则被描绘为驯服的、等待其拯救的、自甘称奴的家臣形象。二、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美建交、冷战结束,美国新霸权主义抬头。华人或者成为大熔炉精神关照下的模范公民,或者成为美国政府的雇佣警察,与黑人、白人形象一起将“双种族伙伴侦探电影”类型推向高峰。
华人形象徘徊于撒旦与家臣之间,完全出于美国社会的需要:如果华人不能被美国利用,则是危险的、罪恶的“撒旦”,需要立即被除去;假如华人能够为美国利用,则变成效忠的、顺服的“家臣”,自觉为美国政府服务。从这一意义上看,好莱坞确信无疑地遵从了西方的东方学信条,即“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①。
一、华人“撒旦”形象
华人“撒旦”一词最初来源于英国作家萨克斯·若莫尔1912年撰写的小说《邪恶的傅满洲博士》:“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人,高个、瘦削,像猫科动物一样高耸着肩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一样的脸型,尖窄的头盖骨,细长的眼睛闪烁着猫一样绿色光芒。东方民族的所有狡诈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最后拼成这么一个高智商人物。想象一下这个糟糕的家伙:那么你们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傅满洲博士的形象,这是一个具体的黄祸的化身。”②傅满洲小说很快轰动欧美大陆,并迅速蔓延到好莱坞。由此,撒旦类华人形象贯穿了整个美国电影的历史。他邪恶、凶残、狡诈,时刻威胁着白人的生命安全,时刻准备摧毁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
华人撒旦形象对美国社会造成三种威胁:1、种族威胁,即华人出于种族仇恨而对白人进行攻击。2、性威胁,即华人男性对白人女性进行性侵犯。3、政治威胁,即华人在意识形态上处心积虑地破坏西方政治秩序。从这三种威胁演变出三种危险“撒旦”形象:黄祸、男性“强奸犯”、红祸。
1.黄祸
19世纪以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冲击了美国纯粹的白人社会理想。从1882年开始,美国出台并执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美国,并对美国本土内的华人实行种族政策,将其圈入种族文化孤岛——唐人街。一时间,“黄祸形象”泛滥于美国的文学、漫画、摄影、戏剧等领域。好莱坞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与华人形象的最初接触。黄祸形象最初可以上溯到1914年,纽约影戏公司(photoplay Company)制作的《神秘的傅武春先生》(Mr.Wu Chun Fu,photoplay Company,1914)第一次出现了黄祸撒旦的雏形——一个暗设牢房的黑帮头目傅武春。傅武春之后,“黄祸”恶魔吴方于1915年在三集系列默片《伊利安的爱情故事》(The Romance of Elaine,1915)的第二集出现,这位“魔爪联盟”的成员用吸毒、催魂术、毒箭、陷阱等下三烂的办法威胁着白人女主人公伊利安·道奇(Elaine Dodge)的安全。
1922年英国斯托(Stoll)公司第一次把傅满洲的缔造者萨克斯·若莫尔(Sax Rohmer)的小说搬上银幕,在《黄爪》(Yellow Claw,Stoll,1922)塑造了唐人街黑帮老大京先生:
“一道白色的光线突然劈开了黑暗,从一辆正在拐弯的大型轿车的前灯照射出来。我跟着进了一条很窄的街道。车在我前面十码远的地方停下了。一个穿着时髦的司机打开了车内灯,跳下车,给他的乘客开门。我看见了一个高个子的、显贵的中国人,但与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不同。他穿着很长的黑色轻便大衣,戴一顶奇怪的羊羔毛帽子……傅满洲就这样诞生了!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说‘你相信是你创造了我,我却相信只要你抽烟,我就会永远活着’。”③事实上,萨克斯·若莫尔既缺乏与唐人街黑帮打交道的实际经验,也从来没到过中国,他宣称书中的背景都是根据他看过的中国书本和中国地图来编造的。④
1923年斯通公司制作了15集连集片《傅满洲的神秘》(The Mystery of Fu Manchu,Stoll,1923,15 episodes),这是邪恶的傅满洲博士第一次在银幕上正式亮相。不久,该公司又拍摄了8集《傅满洲的进一步神秘》(The Further Mysteries of Fu Manchu,Stoll,1924)。派拉蒙公司也毫不示弱,连续拍摄了4部长片。《神秘的傅满洲博士》(The Mysterious Dr.Fu Manchu,Paramount Famous Players-Lasky,1929)、《傅满洲的归来》(The Return of Dr.Fu Manchu,Paramount,1930)都塑造了一个复仇恶魔傅满洲的形象。1931年,派拉蒙公司找到正冉冉上升的华裔明星黄柳霜出任傅满洲影片《龙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Paramount,1931)的女主角。影片中隐姓埋名20年的傅满洲再次来到伦敦报复比丘一家,他毒死比丘博士,负伤从秘密通道逃到舞女梅玲那里。临死前他告诉梅玲,他是梅玲的爸爸,让她替父报仇。梅玲用色情对比丘的孙子进行诱惑,小比丘渐渐地爱上了梅玲。最后,当梅玲将比丘与他的白人女朋友绑起来准备复仇时,侦探阿基及时到来,解救了白人危机。梅玲却与日籍影星哈雅卡瓦扮演的阿基双双死去。影片除了告诫白人男性远离华人女性之外,还展示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可怕力量——华人对西方的复仇具有血统上的延续性。随着傅满洲这一人物形象逐渐成熟,他的破坏力也渐渐加大,被假想成整个西方世界的和平破坏者。在《傅满洲的面具》(The Mask of Fu Manchu,Paramount,1932)中他企图从成吉思汗的墓里获取面具,一旦戴上这面具,整个亚洲就会听命于他。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逐渐进入蜜月期,黄祸撒旦也逐步淡出银幕。共和制片公司1942年准备拍摄《傅满洲的回击》(Fu Manchu Strikes Back),但在中国政府的抵制下取消了拍摄计划,美国官方也希望该公司推迟拍摄,“不要让我们的盟友脸上难看”⑤。战后,美国再次掀起傅满洲拍摄高潮,1955年,电影合作共和体(Republic Pictures Corporation)宣布斥资400万美金买断若莫尔先生傅满洲小说的电视、广播和电影改编权,首先准备拍摄78集半个小时长度的电视电影。⑥
直到1980年,西方还保持着对傅满洲形象经久不衰的偏爱,《傅满洲的恶魔诡计》再次设计了一个现代撒旦,他准备窃取作为镇国之宝的乔治五世的黄钻石,还企图劫持玛丽女皇。由此可见,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主义时期,黄祸撒旦形象仍然保有强烈的生命力。影片《龙年》(Year of the Dragon,1985)塑造的新时期唐人街黑帮老大周泰就是另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傅满洲,他阴险、狠毒、杀人如麻,完全不受美国法律管束。当然,与傅满洲一样,他最终无法逃脱被白人警察杀死的命运。
2.男性“强奸犯”
在跨种族性爱的影片中,华人男性总是妄想与白人女性展开一段罗曼史,但实际上影片却没有让他们做出任何出格的“性”动作,甚至连接吻都没有发生过。即便如此,华人男性也被影片假想为“强奸犯”,死亡是他们的最终结局。美国学者吉纳·玛契提因此认为,“好莱坞关于黄祸的叙事类型就是以丑恶的亚裔男性对纯种白人女性的强奸和强奸威胁为特征”⑦。格里菲斯的《破碎的花朵》(Broken Blossoms,1919)是这类影片的始作俑者。影片讲述了华人程环为了向西方宣扬不要以暴易暴的佛教思想,乘船来到英国。一天,遭受父亲巴特林·布鲁斯毒打的小女孩露西来到程环的小铺,唤起了他的爱情。他温柔地照顾她,准备亲吻她的双唇,但最终只是亲吻了露西的袖子。巴特林来到程环的店铺,拖走露西,将她暴打致死。程环赶到后,只看见露西的尸体躺在地上,他愤怒地杀死了巴特林·布鲁斯,然后在露西身边自杀。格里菲斯采用各种手段布设了不得跨种族恋爱的警戒线。他利用字幕“我们”一词将观众纳入父亲巴特林·布鲁斯一方,再把露西设定为15岁的童女,强化了白人观众对“白色的花朵”的同情,黄人触犯了跨种族性爱与跨种族信仰传播两种禁令,罪不可恕,死有应得。
紧接着,斯登堡创作了《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1932),该片曾获得第5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最佳导演与最佳作品提名。影片讲述了一趟从北平开往上海的列车路遇劫匪的故事,同样塑造了一个对舞女“上海百合”(黛德丽扮演)有强奸意向的中国军阀常将军。这一华人恶棍劫持快车,对西方构成了三方面的威胁:人身安全、政治要挟、性占有。最终,中国妓女惠菲(黄柳霜扮演)杀死了他,“上海百合”安全地回到她的白种情人哈里身边,替西方解除了恐慌。
卡普拉在1933年《袁将军的苦茶》中再次利用“强奸犯”模具制作出军阀袁将军的形象,他在战乱中抢夺了白人传教士的未婚妻密根,把她软禁在夏宫中。密根却利用女性的魅力进行传教,最终将一个冷酷无情的异教徒引向善途。故事快结束时密根跪在袁将军面前述说她的爱意,卡普拉却毫无逻辑地让袁将军喝下了一杯毒茶,迅速地中断这个跨种族的爱情故事,达到了惩罚华人男性的终极目的,最终让密根回到了她传教士未婚夫的身边。
虽然这些华人“强奸犯”具有性进攻的企图,但他们却被电影做了去男性化的阉割处理,从未在银幕上对白人女性进行过实质性的性攻击。华人男性被剥离了男性特征。《破碎的花朵》中程环的女性化表现在他精心的打扮、无精打采的手势和动作上。软焦和散光更勾勒出了他轮廓的女性化,而很少体现他的棱角特征。因此,吉纳·玛契提指出:“程环充分体现了西方想象中的女性特征:顺从、肉欲、神秘、奸诈的亚洲。”⑧
华人男性表面上威胁了白人女性的性安全,实际上触犯的是白人男性的性霸权。在男权制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白人女性是白人男性的征服物,决不允许黄人心存觊觎。
学者霍本斯坦特(Hoppenstand)甚至认为美国电影中黄种男性对白种女性的强奸象征着对白种社会的强奸,“黄祸的刻板形象很轻易地被编入了基督神话之中,东方人就成为了恶魔。东方人对白种女性的强奸,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对白种社会的强奸,被定义为精神上的堕落”⑨。
3.红祸
随着20世纪50年代的到来,冷战给黄祸撒旦披上了红色外衣。萨克斯·若莫尔表示,“傅满洲随时可以上路去参与到反共的行列中”⑩。朝鲜战争爆发后,《撤退,他妈的!》(Retreat Hell,United States Pictures,Warner Brothers,1952)等一系列战争影片“把中国人客观地、不露痕迹地刻画为或指明是‘共党’或‘红党’”(11)。《不博士》(Dr.No,1962)中的不博士与《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1972)中的韩先生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占据着某个堡垒、某个岛屿,自封为王、作恶多端,完全不在美国政权和国际公法的控制之下,但他们最终都会被美国政府派来的正义斗士毁灭。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权、西藏关系、香港回归等问题成为美国攻击的目标。好莱坞很快地顺应了这一潮流制作出丑化中国的影片——《红色角落》(Red Corner,1997)、《昆顿》(Kundun,1997)、《西藏七年》(Seven Year in Tibet,1997)等。从黄祸、红祸、强奸犯这三类角色看来,直到今天,好莱坞的任何一部妖魔化的华人形象作品,都不断地回到傅满洲这一“撒旦”形象中吸取灵感。就像学者史景迁所指出的那样,“傅满洲这一形象成为描述邪恶的中国人时所采取的一种持久且权威的国际形式”(12)。这些形象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
(1)与生俱来的阴谋家。撒旦形象被西方定义为与生俱来的阴谋家。在最初的影片中,傅满洲的仇恨还事出有因——他的妻、子被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杀死。在后来的影片中,傅满洲摧毁西方文明的决心和统治世界的野心除了用天生的“撒旦”来解释,别无理由。华人撒旦对西方的仇恨与生俱来,就像《神秘的傅满洲》中傅满洲对他的白人养女所说的那样:“我讨厌你那令人憎恶的白皮肤。”
(2)极大的破坏力。华人撒旦具有较强的破坏能力。从智力和学识上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傅满洲获得西方博士学位,袁将军能够吟诗作画、智力超群。不仅如此,他们还掌握足以毁灭西方的秘密武器,或者是成吉思汗的面具和权杖。若莫尔说傅满洲“他的科学知识超过了西方世界的所有的科学家”(13)。
(3)无法无天的万恶之王。无论是傅武春、吴方、傅满洲、黄先生、义和团、周泰等黑帮帮主形象,还是常将军、袁将军等军阀形象,他们都毫无法律观念,爪牙众多,并毫不迟疑地替主子卖命,毒蛇、蝎子、毒箭、迷香、迷幻药等等是他们的常用武器。若莫尔也正是这样塑造了傅满洲,“他控制了东方每一个秘密团体”(15)。
(4)死亡结局。影片采取欲擒故纵的叙事模式,这些华人撒旦总是在西方看客的目光之下耍尽花招之后,阴谋即将得逞之时,不是被及时赶到的白人侦探杀害,就是自杀身亡。
二、华人“家臣”形象
尽管美国文化极力打造华人“撒旦”形象,并在虚构故事中一次次将其消灭,但是华裔却并没有因此从美国社会消失,招安与树立顺服公民的典范便成为美国治理有色人种的新手段,因此华人“家臣”形象应运而生。这类华人基本上被美国社会认同为可以利用的“自己人”,前提条件是为其所用。
按其实用价值“家臣”可以分为四类:1、能够提供劳力的仆人、厨子、佣人等角色。2、能够帮助美国治理家务、看管家门、维护治安的警卫。3、能够提供性服务的“性奴”。4、能够依照美国价值观实行自我改造,同时还乐于把美国文化体系向同族人推行,自觉担任美国价值观的“吹鼓手”。
1.劳力
美国电影中最初的华人形象就是以厨子、仆人、洗衣工等角色出现在喜剧中,“他们拖着一条长辫子,讲几句洋泾浜英语,常常是被人嘲弄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幽默角色(16)。”《华人异教徒与周日学校教师》中华人洗衣工邀请白人女教员到自己的洗衣店做客,并拿出鸦片请她们共同享用。这时警察闯入,把华人关进监狱。华人洗衣工不仅社会地位低下,最重要的是堕落、危险的本性。虽然整部影片的长度只有2分半钟,但是华人洗衣工的命运线索非常明显,即“堕落”—“危险”—“惩戒”三步曲。卫景宜认为,“种族歧视的主题被暗喻为:华人就是引诱白人妇女堕落、危害社会的道德沦丧者。美国的影视媒体从一开始就完全控制了描述华人的‘话语权’,华人形象的演绎完全基于白人主流社会的利益要求与‘期望值’,这种情形几乎持续了整个20世纪美国影视的华人叙述”(17)。
2.警卫
上世纪20年代的某一天,作家比格斯(Biggers)为了创作小说《没有钥匙的房间》,来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寻找素材。他在查阅檀香山当地报刊时注意到一则短消息:檀香山警察常·阿帕纳如何英勇对付贩卖鸦片的中国同胞。他马上就决定在小说中增添一个华人侦探,“邪恶的、令人讨厌的中国人总是出现在过去的神秘故事中,但站在法律和秩序一边的善意的中国人还没有被描写过”(18)。查理陈就这样在《没有钥匙的房间》中诞生了。百代影片公司立即购买版权,拍成了十个段落的连续影片。随后,四家电影制片厂争先购买版权,前后制作了48集系列片,使得美国银幕在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查理陈高潮。中国侦探查理陈之所以在美国大受欢迎,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正面的、睿智的华人形象,更因为他是美国价值观的杰出的遵循者和卓越的维护者。查理陈具备以下几种特征:
(1)睿智。他具有超越普通华人的智慧与办案的精明作风,是华人的杰出代表。他总是出口成章,自编了很多哲理名言。比如“仓促的结论很容易做,但却像一个泡影”(《查理陈在埃及》),“错误之后的建议就像死人葬礼后的药”(《查理陈在坚持》),《华盛顿邮报》称他为“中国侦探哲学家”。(19)
(2)听命。查理陈在电影中是一个美国官方侦探,他忠心耿耿,效忠美国,影片常常花费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他的领命过程以强化美国国家功能。比如查理陈领命时背景的美国国旗、中情局大楼等国家符号常常在画面中滞留。他不仅替美国看家护院,还踏遍世界各地:非洲、亚洲、欧洲,查理陈的足迹无处不在。这使他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欲望下国际警察的化身,满足美国插手世界事务的私念。
(3)缺乏魅力。查理陈虽然机智勇敢,但缺乏个人魅力,也缺乏英雄形象应该具备的男性特征。这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效忠者——“家臣”,而不是一名受人崇拜的英雄。他的主要扮演者华纳·欧兰德(Warner Oland,1880-1937)、西德尼·托勒(Sidney Toler,1874-1947)、罗兰德·温特斯(Roland Winters,1903-1989)在担任这一角色时都已经年过半百,缓慢与老态被毫不掩饰地强化,他从未对女性表现出任何性欲,就凭这点他就足以被排挤到“美国式英雄”的概念之外。
(4)族群关系美国化。影片在强化美国价值观对查理陈的吸附力的同时,有意识斩断了查理陈与中国的血脉关系。除了他那一口错误百出的洋泾浜英语和开口闭口的孔夫子曰间接证明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外,我们看不出他任何的华人特征。从外貌血统上看,查理陈曾经先后由六个演员扮演,但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演员。从语言来看,当他那几个华裔后代在银幕上时不时来上两句广东话时,他立即愣在那里,一种无法掩饰的语言局外人身份马上彰显出来。因此,与其说查理陈是一个中国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美国化改造后的美国“自己人”。
美国华裔对查理陈的反感成为共识,“陈具有奴性,没有性特征,易怒,而且喜欢逢迎,从来不用‘我’这个词。说查理陈是一个正面形象,只是跟傅满洲相比而已”(20)。但这一形象影响了所有美国电影中华人正面形象的塑造。
在1973年香港与好莱坞的合拍片《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1972)中李小龙担任了美国政府的特派员,替国际社会除掉公海恶霸韩先生。李小龙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效忠美国,最后美国军队登岛。对西方来说,这一结局暗示美国战胜了红色阵营的中国——美国政府可以名正言顺收归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岛屿。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元族裔、混血家庭在美国社会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华人也开始与白人、黑人共同办案。成龙主演的《尖峰时刻1》(Rush Hour 1,1998)、《尖峰时刻2》(Rush Hour 2,2001)描述了华人警察与一个搞笑的黑人警察之间的合作,他们一起替美国政府完成了跨国案件的调查。影片照例延续了查理陈电影模式,黄人听从于白人,黑人则是黄人的助手,“重申、支持和维护原有种族秩序中文化和道德的边界”(21)。靠着家臣类的警卫形象,成龙终于成功地叩开好莱坞大门。李连杰的好莱坞经历与成龙相差无几。《致命罗密欧》(Romeo Must Die,2000)、《救世主》(The One,2001)和《狼犬丹尼》(Danny the Dog,2005)都延续了查理陈电影模式。成龙与李连杰的好莱坞经历再次证明,美国银幕华人正面形象只不过是忠实顺从的“家臣”。
3.性奴隶
跨种族爱情片一方面绝对禁止华人男性觊觎白人女性,同时又以皮条客的面孔把华人女性贩卖给白人男性,供其消费。性奴的特征为:
(1)外形妖娆。从造型上看,华人女性被装扮得妖艳、淫荡,成为西方观众期待的东方性诱惑,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看者的西方权威感和视觉欲望。(2)地位低下,职业卑微。华人女性不是没有职业,就是妓女或者舞女,与生俱来的职业身份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性消费对象。(3)即用即抛。从命运结局来看,华人女性在满足了白人男性的性消费之后,最终都避免不了被抛弃的境遇,自杀或被杀成为华人女性生命的终极走向。(4)缺乏父权或者夫权制的保护。在白人女性与华人男性的爱情片中,白人女性常常处于其父权制或夫权制的保护之下。但华人女性直接暴露在白人男性面前,既缺乏父辈的约束,也缺乏同族男性的保护。这保障了白人男性能够毫无阻碍地随意使用这批性奴隶。
为了进入好莱坞,第一位华裔女星黄柳霜不得不忍辱扮演此类角色,去尽量符合“性奴隶”的形象需求。黄柳霜的银幕形象完全是西方视阈的女性奇观:夸张而神秘的中国服饰、裸露的肌体、扭动的身躯,伴随着性的挑逗和暗杀的诡异气氛。《北洋画报周刊》一篇文章这样评论她在《中国鹦鹉》中的表演:“在这部影片中,我看到黄小姐赤身裸体在一群白种人面前起舞,粗俗地扭动着她的屁股。除此之外,她的舞蹈就没有别的动作了。”(22)因此,皮乌克把这类东方形象定义为西方的产物——“她/他是非西方人,却把自己置身于西方的影像之中:西方的经验,西方的设计,西方的期望。”(23)
黄柳霜扮演过6次舞女,2次妓女,若干次被抛弃的普通少女。1922年,17岁的黄柳霜第一次作为女主角在《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1922)中亮相。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人工着色的彩色影片。莲花在海边救了溺水的美国青年阿兰·卡维尔(AllenCarver),两人产生爱情,并有了孩子。卡维尔走后,莲花坐在岸边的礁石上盼望他的归来。孩子3岁时,卡维尔带着他的白人妻子来到中国。当莲花知道真相后,痛苦地把孩子托付给卡维尔和他的妻子,临别时告诉孩子“我只是你的中国保姆,这才是你的美国妈妈”,然后就跳海自杀了。
黄柳霜出色地扮演了白人男性的性奴隶,在结束时还把自己的孩子也奉献给了这对白人夫妇。同时,莲花树立了决不反抗的性奴典范。尼克·布朗指出这部电影具有重要意义,“要论及美国的亚裔电影,不谈论该片是无论如何无法进行的。这些最初的成功的版本都是西方把‘东方’建构为征服和统治的性对象和性从属空间”(24)。
基于莲花被抛弃的命运悲剧,女性剧作家弗兰西斯·马瑞恩指出这部电影“在实践中步了《蝴蝶夫人》的后尘”(25)。性奴赤裸裸地向白人男性提供性享受,但是任何一个性接触的动作都不得在银幕中表现,这已经成为好莱坞心照不宣的教条。接吻的场面被黑场省略,或者干脆被剪掉,另一些影片中的接吻相隔一寸距离进行。好莱坞扮演了皮条客与捉奸者的双重身份。冷战时期,性奴角色很快又寻觅到了新的扮演者——关家倩。《苏西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1960)中的香港妓女苏西黄(华人影星关家倩饰演)在一家小酒馆里夜夜充当英国水手的“猎物”,美国落魄画家罗伯特成为她主动奉献的对象,可是罗伯特却断然拒绝了她的性奉献。影片通过“脱冕”与“加冕”仪式,使苏西黄从肉体到心灵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由此得到罗伯特的拯救。这一细节与《破碎的花朵》中程环拿出宫廷公主装给露西换上一般无二。影片安排了一场山洪,割断她与香港的血脉联系,最终苏西黄与罗伯特一起双双离开香港前往美国。
当关家倩逐渐淡出银幕,陈冲又被好莱坞选中担任《大班》(Tai-Pan,1986)的女主角。陈冲扮演的角色美美是一个性礼物——清朝官员金桥送给鸦片贩子头目大班的性贿赂品。马克林评价此片说:“《大班》以暴力与性作招徕……而片中的中国形象则依然是中国女性被支配的典型”(26)。
由此可见,华人女性在好莱坞的跨种族影片中永远是卑下的性商品提供者,而此类影片经久不衰的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被禁的欢愉,保留了激动人心的、不平等的种族、性和阶级的高位”(27)。
4.吹鼓手
“吹鼓手”是家臣中地位最高、也出现最晚的角色,他们接受西方价值观,并主动向同胞传播西方思想,以期同化族人。
最早出现的“吹鼓手”雏形是《大地》(The Good Earth,MGM,1937)中的大儿子。虽然大儿子并非该片的核心人物,可他是影片唯一的亮色。影片把阿兰塑造为麻木顺服的中国家庭女性,把王龙塑造为一个没有道德束缚,最终必然走向堕落的传统农民形象,只有接受了西方高等农学教育的大儿子以拯救者的姿态回来,用西方科学挽救了蝗虫的灭顶之灾,也化解了家庭危机。大儿子的命运向中国农民指明了出路——只有接受西方的教化才能走向一条背弃大地的道路。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美冷战升级,把“有志者”从红色阵营中吸引过来是美国梦寐以求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华裔作家黎锦扬的《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61)盛行一时的原因。影片讲述了中国传统女性李梅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与未曾谋面的未婚夫完婚的故事。李梅的寻夫之路就是精神改造之路——从一个中国父权制和夫权制下的女性变成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独立女性,最终融入美国“大熔炉”。最后李梅拒绝与父母指定的未婚夫结婚,按照美国式自由恋爱观寻找意中人。
王颖导演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93)以华人女性为视角,讲述了四个家庭历经磨难融入美国的故事。这四名妈妈每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中国往事,于是来到美国开始新生活。影片所要表现的并非四位母亲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她们初闯美国的艰辛为影片所省略),而是四位母亲与完全被美国同化了的四位女儿之间的文化差异。影片采取了把外在冲突内化,把文化冲突家庭化的叙事策略,最终以母女两代人的和解创造了一个华裔女性顺利进入美国的乌托邦神话,这种乌托邦神话正是通过母亲一代与故土中国的距离割舍到女儿一代与中国的价值观割舍完成的。
成龙在《上海正午》(Shanghai Noon,2000)中饰演的清廷大内高手王冲(Chon Wang),罗燕在《庭院中的女人》(Pavilion of Women,2001)里扮演的吴太太,都在渴盼美国价值观的普照,如饥似渴地等待着被教化、被改造。主人公历经磨难,最后幸福地进入美国价值体系之中。
无论是仆人、警卫、性奴,还是吹鼓手,家臣形象都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
(1)具有超越本族同胞的优秀品质,他们必然聪慧、睿智、身手不凡,能够胜任美国政府的各种任务。(2)认同美国价值观,不惜割裂与中国的土地关系、血缘关系和情感关系。(3)服从美国政府及代言人的召唤,愿意完成美国的国家使命,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和性。
三、结论
从好莱坞百年历程可以看出,撒旦与家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华人形象按照美国的需要在两极间摆动。这两类形象看似迥然不同,却很容易相互转换。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是撒旦与家臣取决于是否为白人所用,而二者的基本特征完全相同。
(1)小聪明。美国社会普遍认为黑人是愚蠢的,但华人是小聪明。撒旦的狡诈与家臣的聪慧从根本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2)顺从,无主见。中国人频频被西方描绘为蓝蚂蚁、羊群,但是美国乐得利用这一性格特征对华人形象加以控制,使之变成在美国社会中驯服、听命的家臣代表。
华人形象在两种品性中来回游移,暗示了华人性格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Lsaacs)在50年代对美国社会作了大量的访谈调查后,认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相互对立,“对这些美国人来讲,中国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以相互对立的两方面出现。中国人被看作是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异常恼人的野蛮人和极具吸引力的人道主义者;贤明的哲人和虐待狂般的刽子手;勤俭而令人尊敬的人和狡猾而阴险的无赖;喜剧的战士和危险的斗士”(28)。
因此,美国电影表面上塑造了撒旦与家臣截然不同的两种华人类型,位于价值坐标的两端,实际上,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美国价值的核心地位、是否服务于美国,这是美国种族主义的电影展示。美国电影的华人形象暗示了种族主义心理病症:对华人破坏力假想的恐惧和对华人统治快感的期盼。从电影与现实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华人的破坏力是白人疑虑症的产物。实际上,美国华人退缩到唐人街寻求生存,“退缩到他们自己的与世隔绝的交往圈子里,并且更甚者,退缩到被美国人认为是毫无反映的呆板的过度警觉之中”(29)。
与此同时,美国电影还要通过制造顺服的、皈依的家臣形象,来体验统治的快感。英国学者霍尔认为帝国的权力只能通过构建他者来体验快乐,“对我们自己意义上的身份来说,‘他者’有多必要;即使是占支配地位的、殖民的、帝国主义的权力,也只能通过建构的他者来体验它自己的统治权力的快乐”(30)。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对他者的需要战胜了对他者的恐惧,他者不仅不被放逐到蛮荒之地,而且必须被纳入“我”的体系,令其与“我”的统治快感同时存在。
注释:
①[美]萨伊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85.
②Sax Rohmer:The Insidious Dr.Fu-Manchu; Dover Publications,1997,pVI.
③(13)(15)Sax Rohmer:How Fu Machu Was Born; Los Angeles Times (1886-current file); Sep 29; 195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Los Angeles Times (1881-1985); pgK28
④Sax Romer Author Dead;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1954-1959); Jun 3,1959;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Washington Post (1877-1988); pg.B2.
⑤转引自英文网站www.illuminatedlantern.com.
⑥Fu Manchu to Republic; New York Times(1857-current file); Jun 18,195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1851-2001)pg.31.
⑦⑧(27)Gina Marchetti: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Race,Sex,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University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0,35,5.
⑨Gary Hoppenstand:Yellow Devil Doctors and Opium Dens:A Survey of the Yellow Peril Stereotypes in Mass Media Entertainment,Bowling Green,Ohil:Bow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1983,p174.see Gina Marchetti: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Sex,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University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3.
⑩Sax Rohmer Dies,a Mystery Writer; New York Times (1857-current file); Jun 3,1959;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1851-2001)pg.35.
(11)(14)(16)[美]陶乐赛·琼斯著,邢祖文,刘宗锟译: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1896-1955),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37,53,63.
(12)(23)转引自:[英]齐亚乌丁·萨达尔著,马雪峰,苏敏译.东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64,136.
(17)Philip P.Choy,Lorraine Dong & Marion K.Hom,1994,转引自: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14.
(18)Creating Charlie Chan; New York Times (1857-current file); Mar 22,193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1851-2001)pg.X6.
(19)Warner Oland:"Charlie Chan" of Screen Admires Original; the Washington Post (1877-1954); Sep16,1934;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Washington Post (1877-1988); pgO1.
(20)David Hwang:Are Movies Ready for Real Orientals? New York Times (1857-current file); Aug 11,198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1851-2001)pg.H1.
(21)[美]海蒙·格里,观看的竞技:电视和“黑”的挣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5.57,转引自:[美]玛丽·C·贝尔特兰著.赵小兰·沙丹译.新好莱坞种族性的消解:唯有速度、激情和多元种族方可生存.世界电影.2007.(2):7.
(22)《北洋画报周刊》,1927年11月30日,1928年5月8日,8月29日。转引自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Anna May Wong:From Laundryman's Daughter to Hollywood Legend,PALGRAVE MACMILLAN,2004,p83.
(24)Nick Browne,"the undoing of the other Woman:Madame Butterfly in the Discourse of American Orientalism",转引自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Anna May Wong:From Laundryman's Daughter to Hollywood Legend,PALGRAVE MACMILLAN,2004,p37.
(25)转引自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Anna May Wong:From Laundryman's Daughter to Hollywood Legend,PALGRAVE MACMILLAN,2004,p37.
(26)转引自: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9.
(27)Gina Marchetti: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Sex,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5.
(28)(29)[美]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Lsaacs),于殿利,陆日宇译.美国的中国形象.中华书局,2006,43,102.
(30)斯图亚特·霍尔.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3.
